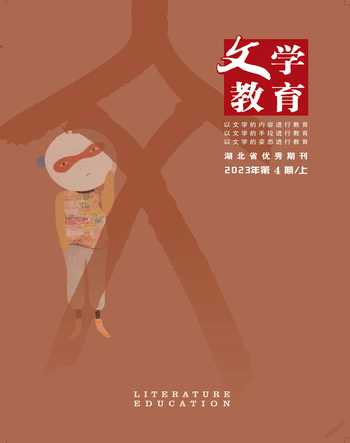《台阶》中父亲形象的美学意蕴和情感密码
蔡育峰
内容摘要:李森祥小说《台阶》中的父亲,是一个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具有复杂而丰富的审美内涵。从“农民”身份切入,从“农民”形象的文化结构,解读父亲作为中国传统农民典范的美学意蕴;从“父亲”身份切入,从儿子视角解读父亲形象确立与崩塌的普遍性心理结构;从“老人”身份切入,从自然人的角度解读父亲面临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时的无力感与绝望感,引发生命哲学层面的深刻思考。本文将父亲作为“农民”“父亲”“老人”三重身份分别剥离而又糅合,阐释三种身份蕴含的普遍性文化结构、心理结构,以此揭示父亲形象背后藏着的人类普遍性的情感密码和美学意蕴。
关键词:李森祥 《台阶》 三重身份 父亲形象 文化结构 心理结构 美学意蕴
李森祥的小说《台阶》1988年发表在《上海文学》[1],入选人教版和苏教版语文教材,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为什么《台阶》中父亲形象能有这么深广的情感力量?本文将父亲形象分解为“农民”“父亲”“老人”三重身份,阐释这三种身份蕴含的普遍性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以此解读《台阶》父亲形象的情感密码和美学意蕴。
一.农民:中国传统农民的美学典范
父亲身上具备中国几千年传统农民的普遍性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培育出来的农民形象的美学典范。父亲作为农民形象的美学意蕴,契合了中国人关于农民形象的美学想象,因此具有广泛的情感力量。
父亲具有农民勤劳的美德,彰显了农民形象的劳动美。父亲为建造高台阶的新屋所做的准备,从“一块砖”“一片瓦”开始,是非常琐碎而漫长的。这种准备工作是低效率的,是农业的生产方式,但这勤劳奋进的精神,某种程度上却与中国传统文化里“愚公移山”的精神是契合的。
父亲具有农民吃苦的精神,彰显了农民形象的坚忍美。父亲在生活苦难面前所展现的坚忍,构成了中国传统农民美学形象的一部分。父亲从不畏惧辛苦,为了砍柴卖钱,起早贪黑,鸡鸣时出发,黄昏后才回,一个冬天穿破底的草鞋就堆得超过了台阶。然而其中的辛苦疲累,从未将父亲击倒。
父亲具有农民的淳朴谦卑,彰显了农民形象独特的人格美。新屋建成了,这是父亲劳苦一生的高光时刻,父亲要放四颗大鞭炮以示隆重。但是父亲“居然不敢”放鞭炮,只让“我”来点火。在鞭炮声中,在被炸起的鞭炮碎纸中,父亲不知所措,“父亲的两手没处放似的,抄着不是,贴在胯骨上也不是”,只好露出“尴尬的笑”。当新屋建成,父亲坐在九级台阶上,举止失措,令人啼笑皆非!有人从门口过,问父亲“晌午饭吃过了吗?”明明已经吃过了午饭的父亲,却因为谦卑而下意识地回答没吃过。这种淳朴的谦卑,既是中国传统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体现,也构成了中国农民形象独特的人格审美。对生活的逆来顺受,深刻到骨子里的谦卑,使得中国传统农民形象具有一种令人悲悯怜爱的特质。
建造九级台阶的新屋,是父亲作为农民对生活朴素而美好的热望,也是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寻。父亲一辈子与土地纠缠,在目光所及的狭窄世界里执着追寻生活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父亲终其一生的理想,就是拥有一所有高台阶的新屋,因为在父亲的世界里,高台阶是地位的象征,是尊严所在。王君认为父亲用尽一生的力量建造九级台阶的新屋是一种精神冒险,并且盛赞“这筚路蓝缕的追求充满了神话式的传奇色彩和寓言式的精微深意”[2]。
父亲以建造九级台阶的新屋作为其人生价值的追寻,具有历史局限性,也揭示了中国传统农民的宿命。父亲以外在于生命本身的“高台阶的新屋”作为其精神追求和人生价值的确认,注定是荒诞而悲剧性的。九级台阶新屋建成了,父亲也老了,腰也闪了,生命也进入了枯竭。父亲的一生,由最初的雄心勃勃而始,由“若有所失”而终,令人深深感伤遗憾。这样的结局,论者众说纷纭。杨先武赞扬了父亲坚毅执着的精神,但认为父亲把人生价值寄托在高台阶的新屋上是可悲的[3]。王君从教学价值的角度出发,认为“必须要讲出父亲的伟大”,不必去批判父亲的精神境界还不够高,用“精英阶层”的意识去嘲笑父亲的“台阶意识”是荒谬的。她认为父亲是艰苦创业的草根阶层的典型代表,是中国的筋骨与脊梁[4]。论者众说纷纭恰恰体现了这一结局复杂而丰富的审美意蕴。在漫长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除了生儿养女,中国农民终其一生的价值就是建造一栋新屋,这是他们一生最重要的光辉事业。现实生活中,老一辈农民的个人幸福和尊严就是与一栋新屋联系在一起的。令人不能不深思的是,作家李森祥在小说《台阶》最后却并没有让父亲获得这种幸福与尊严。这体现了李森祥对农民命运与生命意义的思考。
《台阶》发表于1988年,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时期。农民这一身份及其族群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正在发生溃败和革新。如果以今天的视角看,《台阶》中的父亲作为农民所具有的劳动美、坚韧美、谦卑的人格美,及其对生活朴素而美好的愿望,依然具有普遍性的美学意蕴,但是其中的具体方式,如“一块砖”“一片瓦”的建造方式,逆來顺受的坚韧谦卑,以“高台阶的新屋”为精神追求与人生价值确证等,是有其时代的局限性的。《台阶》发表至今三十余年,父亲作为农民的美学形象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但也正在遇到新一代读者的挑战,尤其在城市里长大的一代,早已失去了理解其美学意蕴的生活基础。但正因为如此,《台阶》具有了社会学史料的价值,让今天的新一代年轻人能由此窥见中国传统农民曾经的生存境况与人生追求。
二.父亲:“父亲”形象的确立与崩塌
关于《台阶》中父亲的形象,论者多从农民的身份言说。部分论者虽题为探究“父亲”形象,但其实质依然在探究父亲的“农民”形象,如苏宁峰《精神困境中的父亲形象——人教版课文<台阶>教参解读指瑕》认为《台阶》主旨在追问农民的精神存在和转型时期农民的精神生活[5]。蒋云斌《“坐着”的父亲——浅谈<台阶>的“父亲”形象》实质上依然从“农民”身份言说,认为父亲与“世世代代的中国农民”一样,“一辈子都坐在两样东西上——一是土地,一是传统”[6]。也有人注意到了父亲作为“父亲”这一角色,但其论说多局限于父亲的人物形象本身,如胡丹《“儿子”的崇敬与伤感,“我”的理解与感恩——<台阶>文本细读》从“儿子”的视角论述了小说中“我”作为儿子对父亲形象的理解,但其侧重点在阐述“儿子”视角的意义,且未从普遍性角度探究父亲形象的确立与崩塌[7]。
笔者以为,《台阶》从儿子视角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父亲形象的确立与崩塌的普遍性寓言,一个父亲形象接受史。
作为“父亲”形象,父亲在“我”的情感建构、人格建构和理想建构中都曾承担起“父亲”光辉伟岸的角色。
像绝大多数中国传统父亲一样,父亲沉默寡言,小说关于父亲的语言描写极少。但从仅有的语言描写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父亲的温情。童年的“我”是顽皮好动的,“我”喜欢在三级青石台阶跳上跳下,有一次“我”想一步跳到门槛上,结果狠狠地摔了一跤,父亲拍拍我的后脑勺说:“这样会吃苦头的!”这里用极琐碎的文字描述了三级台阶给“我”的童年快乐,以及父亲对“我”顽皮好动的包容与理解。父亲“拍拍的我后脑勺”,动作如慈母般温柔。有人却认为父亲说话的语气太过刚硬,语气中透露着复杂的信息:既有辛酸,也有警示,还有夸大苦难的意味,而年幼的“我”根本不体会父亲的心理,因此推断父亲有人格障碍,因为父亲与最亲近的家人之间也沉默寡言无法有效沟通,情感上比较疏远[8]。笔者以为这样的观点稍显偏颇,有过度阐释之嫌。父亲提醒“我”“这样是会吃苦的”,恰恰承擔着父亲教诲的职责。而每到过年,母亲端水给父亲洗脚的场景是温馨而柔软的。事实上,在父亲主导下,《台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孝子的温情家庭结构。父亲用爱与责任为“我”构建了一个温情的情感世界。
父亲的坚忍豁达,曾为“我”树立人格榜样。父亲坐在台阶上洗脚,“要了个板刷沙啦沙啦地刷”。这个印象深深地印在“我”心里,让“我”感受到父亲的农民本色与豁达的性情。父亲和泥水匠们抬青石板时腰闪了一下,却依然一手按着腰坚持着。父亲挑水时闪了腰,倔强而粗暴地推开了想要帮忙的“我”。这些细节,让“我”铭记于心,因为其中有一个父亲最倔强的坚强。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父亲始终扮演中与母亲不同的角色,在儿子的精神世界里,父亲必须表现出男性的力量、坚韧、顽强,面对苦难始终不低头的倔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亲用他坚韧倔强的一生完成了对“我”的人格塑造。
父亲终其一生建造九级台阶的新屋,为我树立理想建构的典范。为了实现理想,父亲从“一块砖”“一片瓦”开始,用大半辈子来完成,这种面对理想的坚韧执着的追求,令我震撼。而更重要的是,父亲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那快乐自足的态度,认我着迷。父亲从早忙到晚,晚上只睡三四个钟头。“我”担心父亲身体会垮掉,可父亲却很兴奋,脸上总是含着笑,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这样的细节让“我”明白了心中有梦想的人是最快乐的,让我感受到了梦想的伟大力量。
父亲形象从最初的高大、充满力量美到衰弱、颓废,经历了父亲形象的确立与崩塌的过程。小说一开始极写父亲的高大强壮,“三百来斤重”的青石板,“父亲一下子背了三趟,还没觉得花了太大的力气”,这是极度张扬的力量美;父亲坐在三级青石板台阶上时屁股在最高一级而两只脚板在最低一级的样子,令“我”印象深刻。此时的父亲伟岸如山,映射在儿子的心理,产生了无限崇拜的热情。后来的父亲,和泥水匠们一起抬青石板,却闪了腰,在挑水时又一次闪了腰,母亲在父亲闪腰的部位刺九个洞,用竹筒拔火罐,从父亲的腰里吸出“一大摊污黑的血”,然后父亲迅速衰老和颓废了下去。在李森祥极度感伤的抒情化描写中,藏着一个父亲的衰弱与颓废,也藏着一个儿子面对父亲形象崩塌时的感伤与失落。
“父亲”形象的确立与崩塌,都具有普遍性。在父与子的代际传承中,儿子由弱到强,而父亲由盛到衰。每一个长大的“儿子”,眼里都有一个由盛而衰的“父亲”,这是人类共同的心理结构,也是《台阶》中“父亲”形象具有深广的感发力量的深层次情感密码。
三.老人: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者
叙事时间的起点与终点的选择,将深刻影响小说的主题。引导读者关注小说叙事的时间结构,将有益于深化对小说主题的理解。《台阶》讲述了父亲为了修建九级台阶的新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叙事,完全可以在父亲实现建造九级台阶梦想这样的高潮部分结尾,由此我们将看见一个高大的、充满力量美的强壮父亲、一个年幼的充满童真快乐的儿子、一个由严父、慈母、娇儿构成的温馨之家;我们将看见一个中国传统农民“愚公移山”般充满神话式传奇色彩的奋斗史;我们还将看到一个中国传统农民在达到事业与人生顶峰时的幸福与喜悦。可是李森祥没有在父亲实现建造九级台阶梦想这样的高潮部分结尾,而是花费了不少笔墨去写父亲圆梦后的失落。
语文统编教材七年级下册选录的课文《台阶》,采纳了“怎么了呢,父亲老了”这个结尾。查阅《台阶》原来发表的《上海文学》和语文统编教材选用的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小说集,小说结尾是有这句话的。可是作者在2007年将此文选入小说集《台阶》时删除了这个结尾[9]。杨凤辉主张“怎么了呢,父亲老了”这个结尾宜删,认为只有去掉“怎么了呢,父亲老了”这个结尾,小说才更具美学价值、思想价值,也才能避免读者把父亲的人生看成是个人的悲剧[10]。笔者认为,恰恰是结尾这种悲剧色彩,使得父亲形象更具有普遍的抒情性,也使《台阶》在追问人生终极意义上走向深刻。
父亲作为“老人”这一身份,使其天然成为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者。“老人”一般有两个焦虑,一个是死亡焦虑,面对衰老和死亡产生的恐惧;一个是回顾、总结一生的焦虑,即对自我人生价值的终极追问。这两种焦虑是交织在一起的,正是因为有了死亡,我们才需要在短暂的人生中努力创造,实现人生价值。父亲用大半辈子的人生实现了建造九级台阶的人生理想,可他却突然发现,他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幸福感与尊严感。父亲必须要有新的人生目标来提供新的动力,可是“老人”临近死亡的现实,使这种新目标很难建构。他每天都“若有所失”,陷入巨大的失落与虚无,因为他不再年轻,不再健壮,体力迅速衰减,也不再有人生目标和前进的动力。
但这种失落与虚无,或者父亲老了的悲剧性结局,并不是消极的。如果《台阶》在父亲实现建造九级台阶梦想这样的高潮部分结尾,无疑是一个更加乐观且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结尾。但这种乐观与浪漫主义是危险的,遮蔽了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和精神处境,也将使小说《台阶》失去主题的深刻性与普遍性,而流于浅薄。笔者认为,正是父亲人生理想的悲剧性,提供了一种震撼心灵、净化心灵的作用,提醒读者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去思考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的价值追寻,深刻理解他们生存与精神困境,也因此获得了书写的真实性与普遍的情感共鸣。
如果我们将父亲诸如“农民”“父亲”等社会身份全部剥离,仅仅将其作为单个的“老人”来审视,父亲的失落与虚无,其实是人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面前的无力感与绝望感。这种无力感与绝望感是人类共有的生命体验,是超越了身份与文化而存在的,抵达了生命哲学的层面。郭跃辉认为,应该将“父亲”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社会、文化、思想因素全部剥离,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父亲形象。[11]笔者认为,我们并不是要剥离附着在父亲形象上的社会、文化、思想等因素,而是要将父亲作为“农民”“父亲”“老人”的三重身份融合、糅合在一起来看,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父亲这个人物形象复杂而丰富的美学意蕴。
注 释
[1]李森祥《台阶》,《上海文学》1988年第6期。
[2]王君《从<台阶>看人生的困境》,《语文教学通讯》2008年第3期。
[3]杨先武《可敬而又可悲的父亲——<台阶>意蕴新探》,《中学语文教学》2007年第8期。
[4]王君《必须要讲出父亲的伟大——<台阶>意蕴新探》,《中学语文》2009年第1期。
[5]苏宁峰《精神困境中的父亲形象——人教版课文<台阶>教参解读指瑕》,《中学语文》2012年第10期
[6]蒋云斌《“坐着”的父亲——浅谈<台阶>的“父亲”形象》,《语文教学通讯·初中》2015年第1期。
[7]胡丹《“儿子”的崇敬与伤感,“我”的理解与感恩——<台阶>文本细读》,《语文教学通讯·初中》2019年第4期。
[8]向浩、童庆杰《<台阶>中“父亲”人格障碍分析》,《中学语文教学》2019年第11期。
[9]李森祥小说集《台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10]杨凤辉《真的是父亲老了吗——<台阶>的结尾段宜删》,《中学语文教学》2021年第5期。
[11]郭跃辉《“怎么了呢,父亲老了”是画蛇添足吗?——小说<台阶>的一处细节解读》,《语文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