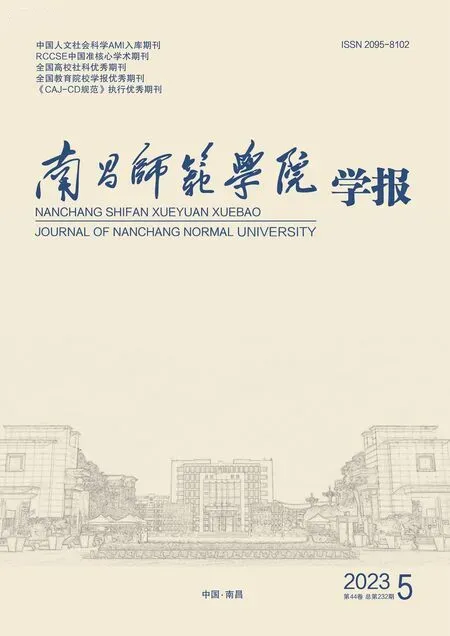铁凝《玫瑰门》叙事伦理问题
王 青
(1.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32;2.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27)
作为铁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而且涉及了伴随着塑造女性形象而来的女性题材写作和女性话语建构等问题。另外,小说中有关“文革”的描写也让许多人关注到了小说的叙事伦理问题,这一点在近几年也有许多评论家对此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而且,作家作品如何对待和解释这段特殊的时期以及身处其中的人成为学界回望和叙述这段历史的新视点。
一、叙述话语的反叛
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玫瑰门》时,有过这样的介绍:“反思‘文革’的一部直面惨淡人生和丑恶人性的成功之作。”如果依据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来说,这可以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也可以是一部反映中国特殊时期革命历史的小说。因此,追究小说到底是借人物写历史还是通过革命写女性命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铁凝如何在这样一部一直被称为“女性主义”文本的小说中完成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回望“文革”、思考人性的过程。而且,不单是铁凝,活跃于20世纪80、90年代文坛的这些作家,他们在创作上做出的这份努力,直接反映在有关当代文学和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整体性危机的争论——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作家们和评论家们激烈地讨论着文学中人性的沦丧和现实生活中欲望的无限膨胀等问题。确然,新时期以来的创作仿佛走向了两个极端——内容与形式的双重背离。不论是新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还是先锋小说进行的叙事革命,无一不指向了作家叙事伦理上的选择。按照刘小枫先生的表述,“叙事伦理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生命感觉的问题,营造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它不同于理性伦理学执着寻求生命悖论的合理解答,而是着眼于个体生命的真实感受和道德实践。”[1]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个体叙述的真实性和明确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道德实践有可能是虚构的,甚至是模糊的。换言之,新时期以来作家游走于个体与集体之间,在其间的模糊区域寻找突破口,完成文本叙事伦理的构建。这种创作上的自觉与努力,正是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对文学史的独特贡献。
作为一位拥有悲悯情怀的作家,铁凝在《玫瑰门》中以回忆的形式叙述了一个与“文革”,与女性有关的故事,写了“文革”中畸变的人(特别是女人)和人性,但小说最终却回归到生命之善这一点上。她写历史压迫下人性的扭曲是为了挖掘人性之善,她写丑陋的女性身体是为了抵抗女性被肉体化、欲望化,但她并不否认女性身体蕴含的强大力量,也不逃避历史。在处理“文革”这个题材或是这段历史时,铁凝呈现出来一种积极又回避的写作姿态,积极表现在细致描摹身体和心灵的伤痛并给予关怀,回避表现在承认历史的合理性。“身体”从未在铁凝的小说中消失,她借助女性的身体抵达了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只有身体和精神同时在场的写作,才能最终指向一种给予人文关怀的叙事伦理,为了找到这种叙事伦理上的善,铁凝在文本中进行了实践,并将“文学表现生活”创作原则贯彻始终,实现了小说与生活的相互指涉。
《玫瑰门》讲了庄家三代女性的故事和浮沉命运,展现了女性在解放前、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四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铁凝在文本中建构起独具个人风格和价值意蕴的话语体系,这种极具个人特色的话语帮助她完成了对革命话语和集体话语的反叛和对20世纪80年代文坛流行的私人化的话语体系的颠覆,正是对文本内部话语和现实话语的双重反叛,让铁凝在叙述关于女性成长、社会变革等问题时始终保持着清醒,让女性的本相和光彩在“文革”叙事中更加可靠和真实,也让“文革”在日常生活叙事中显得更加合理,但并不是肯定这场带有狂欢性质的文化革命,而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其进行冷静克制且舒缓的叙述。小说第一章落笔现实,交代背景,突出苏眉和苏玮两姐妹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借此展开一段关于“成长”的回忆,小说也强调了,长大后的每一个人需要的是一份实在的日子,如果日子不实在,那就会不安、焦躁甚至疯狂。从第二章开始,小说叙述视角的切换非常频繁,儿童视角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成人视角也并未退出,而是蛰伏在一旁,在重要时刻将读者拉回残酷的现实。这是铁凝的良苦用心,也是她进行“文革”叙事的策略之一。
从儿童视角出发,小说隐晦地提及了“批斗”“破四旧”“背语录”等事件,重现了“文革”时期的社会现实,但这种带有个人生命体验的叙述带给读者一种疏离感,早慧的苏眉的所感所知并不能很好地为读者解释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但凭借着女性特有的敏感和潜意识,苏眉对自己的经历作了合理且浪漫的解释,“当愉快消失了痛苦也就不存在了。就像你的眼泪流完了你还有什么眼泪?你笑得没了气,笑也就消失了。”[2](P23)这是苏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对突变的社会的切身感受,带有强烈的个人话语色彩,“愉快”“痛苦”等情感性词语的使用印证了苏眉作为一个儿童对世界的认识,也道出了铁凝对于“文革”的整体看法和感受。苏眉的成长见证了社会的逐渐脱轨,但一个少女对于自我和生命独立的意识却悄然觉醒,这种觉醒首先体现在苏眉对于女性身体的认识、接受与欣赏的过程中。童年时期的苏眉因为画报上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对怀孕的妈妈的肚子产生了恐惧,她下意识认为妈妈的大肚子不好看。在中国文化中,母亲孕育生命是件值得骄傲并带着神圣光辉的事情,但苏眉一开始便否定了这件事情的合理性,生命的传承在懵懂的儿童眼里成为一件可怕的事情,这在小说中直接表现为苏眉与司猗纹之间别扭的祖孙关系。我们进一步思考,铁凝对于“生命”的理解或许在那个特殊时期产生了变化,她目睹过疯狂与残酷,因而更珍视生命,更难以忍受生命的畸变。在“确立生命之可贵和生命之善”的叙事伦理的统摄下,小说借助苏眉的个人话语完成了“文革”叙事的第一部分。
在庄家长大的苏眉,第一次意识到女性身体的美好是因为竹西,在帮竹西搓背时,她觉得“这身体很壮大很丰硕很逼人”,她在面对竹西的身体时,心中只有那一个念头——每个人都应该用善意的目光去看她的舅妈。但事实是,人们从来不曾用善意的眼光看过女性的身体,不论是小说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女性身体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欲望与性,因此“人们将身体从文本中剥离,抽空了写作中的身体细节,忽视身体在场时的生活景象,最终使写作变成了一种知识的演绎,或者修辞的表演,语言也不再是有身体的、活泼的语言,而成了一堆死去的词语,一个生命的废墟。”[2](P477)着意于话语反叛的铁凝意识到,身体的缺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也是急症,她无意治疗,但希望迎来身体的回归和对身体的直视,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还预示着个体生命的本真状态的呈现。这种对身体的描写不同于林白、陈染等作家进行的“身体叙事”,通过“身体”宣泄和表达现代都市中的种种情绪,竹西、司猗纹等人的身体带有“神圣性”与“崇高性”,是女性突破自我局限的重要表征。不论是带着欲望气息的竹西的身体,还是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苏眉的身体,小说首先确认了“身体”的时刻存在,并赋予其美好的特征,接着又为苏眉依次揭开了关于女性身体的其他秘辛。姑爸在“文革”期间被铁棍捅穿了下体,最终在啃食完大黄后悲惨死去,那是苏眉(也是庄坦)第一次认识到女性身体的残破与丑陋。但我们并未在后续的情节中看到叙述者或其他人对此事发表看法,只有罗大妈的一句“要是大旗在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一个生命的消逝作出总结。如果铁凝此刻跳出来强烈指责“文革”对人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害,那么姑爸残破的身体和姑爸的死就完全变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笼罩下的牺牲品和暴力事件,铁凝着力在小说中强调的女性个体意识在姑爸身上的体现便被完全消解,姑爸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抗争和对尊严的维护便完全失去了意义。铁凝执拗地放弃了常规性的解释,继续讲述着其他女性的命运。这与以压抑肉体和个人为主的“文革”时期的叙述模式和话语体系完全不同,这正是铁凝的又一处反叛。苏眉第二次认识到女性身体的丑陋是被司猗纹带去见司猗频,司猗频在抄家时被自己的儿子泼了热油,身上留下了丑陋的伤疤。但司猗频在叙述这些时平静自如,叙述者的态度引导读者走向历史纵深处,读者得以触碰到历史的真相,由破碎的女性身体带来的历史真相。当铁凝在试图叙述历史真相时,她选择先满足个人的叙述欲望,叙述身体的疼痛与欲望的迸发,先解决个人的生存疑惑,再去深入历史。铁凝试图告诉我们,写作需要身体和精神同时在场,承认作家自己在创作中的存在,承认女性身体的美好与丑陋,以及她们的欲望和独立意识,只有承认,才能给予关怀,才能从人的本质出发触及生命本身的善。
视角回到苏眉,在看到司猗频身上的伤疤后,她想要摆脱人类,本能地排斥所看到的一切。叙述视角的来回切换说明一个问题:铁凝拒绝用“革命”话语来解释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却将真相和真情放在了一个儿童身上,由她说出一切的压抑与不满,由她说出女性身体带给人们一切的幻想与情感,而不是带着性与欲的意味去审视。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随着时期的不同交替出现,叙述的角度与情感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为保证历史叙述的相对真实和有效,小说用成人视角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极具伤痛的几幅图画,用儿童视角对这些事件进行了情绪化和个人化的点评,不涉及批判,但十分有力量。苏眉在成长中的一切疑惑与不解,关于个人的秘密也好,关于由社会转变带来的冲击也好,都由另一个“苏眉”来解答,她成熟、理性,接纳童年苏眉的一切怪癖与不安,在每一个崩溃瞬间给予童年苏眉慰藉。这在小说中通过在偶数章节设置童年苏眉与成年苏眉的几段含混不清的对话来展现,含混本身则通过标点符号的减少和带有意识流特征的语言来达到。在这些章节中,作家意识或退居幕后,或与小说主人公意识处于平等状态,在不断地进行“微型对话”的过程中实现了小说主人公苏眉自我意识的交锋和其他人物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而“小说中各主人公身上表现出来具有充分价值的互不相融的独立意识,从而构建起一个‘复调’的‘意识世界’。”[3]成年苏眉与童年苏眉之间的对话很好地塑造了“苏眉”这一人物形象,展现了包括司猗纹在内的多个人物的思想。以细碎的倾诉和情感的慰藉作为叙述的主能指,这便是小说的创造性实验所在,也是构成铁凝的个人性话语的重要部分。
基于以上的努力,铁凝终于完成了话语的反叛,构建起文本中基于对身体在场的肯定的叙事伦理和“肉体与精神同频”“个人突围”的叙述模式。在小说《玫瑰门》中,对女性身体的自我审视和他者审视,都体现了铁凝对“身体”在场的实践,每一次身体的出场,都伴随着一种话语的出现,伴随着一段尘封历史的被揭开,也伴随着人的成长和变化。而小说主人公的成长则使小说的内涵愈加丰富,最为明晰的一点在于作家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不断肯定又否定,不断亲近又疏离的过程。这篇成长小说(或称之为女性成长小说)背离了叙事时间以暴露和绝望为主的创作主流,也背离了故事时间以口号、伪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为主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而是诉诸苏眉、竹西、司猗纹个人的非主观感受和自我成长。铁凝坚持以个人性的话语去观照普通民众、概括社会情绪、剖析历史苦难,而这一话语体系的出现也说明铁凝回望“文革”的积极姿态和对当下现实的思考与忧虑。
二、叙述内容的背离
就20世纪的中国文学而言,现代性问题一直是其追寻与创作的核心,而对于现代性追求的具体表达从“国家意识”到“民族意识”再到“人的意识”。铁凝这一代知识分子“提前了文化‘断乳’,他们没有受到完整的国家规范化教育,他们观念的形成一是源于“文化大革命”狂热而盲目的冲动,一是源于‘文革’后知青生涯的幻灭困顿。”[4]因而他们倾向于在文学中寻找精神之根,着意于作品中的现代性关怀,更多地关注人类的基本价值和需求,“人”本身被放在了文学的核心地位。正是基于这种价值追寻,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出现以“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先锋小说”等为中心的多样创作,并建立起一整套以“人”的话语为核心的叙事体系。这套叙事体系在铁凝这里有了更丰富的所指和更深刻的意义,作为一名女作家,文学的经验化进程对她造成的影响在于挣脱身体束缚,推进意识觉醒。女性作家叙事的基础在于对个人生命经验的文学性处理,但不能让“经验”占据主导地位,那样很容易沉溺于经验化表达的快感,而忽视掉写作中的伦理感觉。“跳出性别的包围圈,从第三性视角去关注每一个人,获得每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体会性别中的共性成分,体会一种普遍的人类关怀。”[2](P481)而要达成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首先要达成对个体生命独特性的认可和接受,先承认个体存在的合理性,并为这种合理存在找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将萦绕在每个人身上的欲望、意识、变态心理完全展现出来,以一种不加干预的叙事态度进行叙述,从伦理的层面认可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从而与文本内在的逻辑形成悖论,再通过个人化的叙述打破这个悖论,达到小说精神内核的凸显与发散。
在《玫瑰门》中,铁凝对人的关注可说到达空前状态,不论男人还是女人,不论在场还是缺席,他们首先被承认是一个个体,之后才被投入社会和历史的洪流中,任意漂浮。在生活与社会极其动荡之时,男性与女性同样被历史裹挟着,负重前行,意识到这一点作家才有可能到达普遍的人类关怀的境界。与多数写女性的作家一样,铁凝笔下的女性依然挣扎于欲望和命运的怪圈不能自拔,不同的是挣扎过程中的不彻底的反抗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前文提及苏眉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文革”带来的苦难在小说中也被内化为苏眉个人的斗争史与逃离史,她的反抗与觉醒贯穿小说始终,并最终获得阶段性胜利。这证明了一点:《玫瑰门》中的女性生命力异常强悍,自成一套话语,而男性则处于缺席和失语的状态。许多作品告诉我们,当女性被裹挟进历史的洪流中,不论是否存在反抗,抑或是反抗成功与否,都避免不了被剥夺姓名和话语、成为失语者的命运。但铁凝偏偏让女性呼喊出声,每个人轮番上场,疾言厉色,个性鲜明,虽结局不尽相同,不完全美满,但爆发的力量让人难以忽视。
要说《玫瑰门》中的呼喊得最大声的女性,在我看来非姑爸莫属。姑爸的登场颇具意味,半分挑逗半分慵懒,说不上迷人,但又让人移不开眼。在苏眉眼里,这是一个女人,一个像男人的女人,但这个“像”停留于外表和装扮。姑爸因为新婚丈夫逃跑而被送回了庄家,此后她便抛弃了女性特征和义务,以男性面貌示人,达到掌控自己和掌控他人的目的。小说在叙述这个故事时,形成了受挫—自我放弃—敌对一切—掌控一切的内在逻辑。姑爸出场时便定了自己的话语基调,那是一种跳出了女性自我约束的藩篱后形成的出于自保和反抗的话语体系,她用这种话语对抗所有一切她不满意的事情,司猗纹上交家具她不满,司猗纹送出金如意她不满,最令她不满的是大黄的死,所以她选择了最惨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通过啃食大黄,让它得以完整。与其说让大黄完整,不如说让自己完整,因为姑爸的故事在未涉及婚姻之前是美好的,她的婚姻出于自愿甚至带着欣喜,父母对她的婚姻也足够重视,撇去一切悲剧的因素,姑爸的悲剧没有明确的原因和解释,因为新郎的逃走无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换言之,姑爸的反抗源于一个未知的男性和未知的原因,她的不完整源于生命重要组成部分的无故缺失,在此处,姑爸的新婚丈夫一直未露面,是缺席的,所以姑爸的后期转变并不能追究到这个缺席的男性对她造成的伤害上去。铁凝跳出了女性必须挣脱男性审视和女性一开始便依附男性的叙事框架,转而将每一个女性放置在男性缺席的处境中,这就不存在挣脱束缚—自我觉醒—获得独立的叙事伦理,而是转变成女性模仿男性,不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以此来获得认可和独立,即使是这样,这种觉醒和反抗依然没有完全成功。因为姑爸并非死于下体被捅穿,而是在“自己完整”的愿望终于达成后放弃了求生。大黄是个男猫,在姑爸终于与大黄融为一体时,她感觉自己正常了,也就是说姑爸执着的一直是新婚夜被抛弃的事实,这让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完整正常的女性,表面上她极力放大这种不正常,内心却无比渴望纠正这种不正常。通过姑爸的故事,铁凝告诉我们,部分女性对于自我性别和身体的认可与接收依然建立在男性的接纳与包容上,失去了婚姻的庇护,这种接纳与包容是不稳定的,甚至是无法达成的,建立在这种认知上的反抗与觉醒,自然无法获得成功。
与姑爸在性别与身体上的反抗不同,司猗纹进行了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反抗,但司猗纹身上本身就存在悖论,因而在探究她反抗不彻底的原因时,我们必须时刻返回到她早早失贞这一“原罪”上。因为司猗纹的“失贞”,司太太受到惊吓而缠绵病榻,愧疚感让司猗纹不得不服从父母的安排嫁给庄绍俭。因为司猗纹的“失贞”,失恋的庄绍俭更加厌恶这门婚事和司猗纹。因为司猗纹的“失贞”,司猗纹与庄绍俭的婚后生活毫无激情,只剩疯狂的欲望。骄傲且对婚姻存有期盼的司猗纹在庄绍俭一次次的一夜不归和离家出走中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她决定声讨男人,可这个男人却走了。小说中的庄绍俭一直在出走—归来的模式中切换,在司猗纹生命的大半时间他都属于缺席状态,每一次的归来都是为了让司猗纹解决麻烦。这时,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分工便被颠覆了,司猗纹的能干与从容衬托出庄绍俭的无用与懒散,这是庄老太爷最不堪最气愤的一点,而且庄家所有人并不认可司猗纹的付出,因为她是带着“原罪”的,因为她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女人,为摆脱这种被忽视的状态,司猗纹抗争过。在奇迹般治好庄绍俭传给她的“花柳病”后,她用自己那具光洁白净且浸润过毒液的身体对人生来了一次亵渎,对象是庄老太爷,这是小说第一次将极致的美与丑融合在一个女人的身体上,对身体的反叛让司猗纹获得了重生。有趣的是,这场抗争带着“不伦”的内核,被庄老太爷等人奉若圭臬的伦理习俗此刻被消解得一干二净。在庄家的几十年,司猗纹一直希望能摆脱家庭主妇的身份,因此她在“文革”时期讨好罗大妈以获得生存之地,希望能将自己的声音融进集体的声音中。而在“文革”结束后,又希望通过苏眉获得更多的关注,从未有一刻是真正地依靠自己,认可自己。不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人,永远无法摆脱社会和其他人对你的影响与伤害,这是司猗纹的悲哀所在。铁凝认识到这种悲哀,因而赋予这种不彻底的反抗和觉醒以合理性——失贞,传统贞洁伦理对于女性的压迫与影响在小说中被解释为女性悲剧命运的源头,这与小说内部逻辑形成悖论,因为庄老太爷甚至庄绍俭提前知道了司猗纹和华致远的事,但庄老太爷无法拒绝上司的好意,庄绍俭也不敢违抗父命,传统道德伦理和官场伦理掩盖了司猗纹“失贞”的事实,双重不可抗力预示这件事的走向和结局。因此,司猗纹的不彻底觉醒与“失贞”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于自我认知的局限,始终未跳出依靠他人审视获得自我审视和自我认可的权利的怪圈,最终失去了解放自己的机会。
在小说中,女性的不彻底觉醒常常伴随着男性的缺席与失语,前文所说的庄绍俭是如此,他的儿子庄坦也是如此。小说里提到,“庄坦是目前庄家唯一的男人。司猗纹常常觉得她和庄绍俭把他造就得有点匆忙。从精神到肉体他好像都缺乏必要的根底,哪怕是人最起码的那点根底。”[2](P243)母亲的对其性别特征和成人资格的否定从根源上便使庄坦失去了作为一个男性,特别是家族中唯一一个男性的骄傲与尊严。确如司猗纹所说,庄坦在面对母亲侧耳细听他和自己妻子的私房事时,他感到恐惧,随着达先生的一声惨叫他丧失了性能力,那是他仅存的男性标志,或许在他目睹了姑爸的死时,他对于“人”之恶便产生了恐惧。如果不仔细去看去挖,你或许很难在小说中寻到几处庄坦的身影,但他的死却值得推敲一番。在竹西肆意放纵欲望,并将这种放纵的快感转移到老鼠身上时,庄坦有点焦虑,因为“他终生的恐惧莫过于和老鼠打交道,他觉得他甚至会死于老鼠对他的恫吓,结果真如他所说,他被竹西手中的老鼠胎儿吓得呕吐,最后死在一锅煮着花生米的小锅前。”[2](P251)他产生了幻觉,再次看到了老鼠胚胎,再次感受到被竹西、司猗纹切割的痛感。“文革”时期,生命的脆弱和被忽视、被践踏,这一事实在小说中经由竹西和庄坦的双重演绎得到本质上的升华。庄坦的失语源于“生命”本身被否定,后又在目睹“生命”本质后逐渐加深。他对竹西无表情地解剖老鼠感到恐惧,他对达先生的惨叫感到恐惧,他对疯狂的社会感到恐惧,这是那个时期的常态,在小说中却被解释成源于他自身的缺陷。因为这就是每个人的人生状态以及他们的人生存在的悖论,叙事伦理呈现的就是这些。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也是铁凝的大悲悯与大关怀,她承认了男性的缺失和软弱,并给予关怀,从人的本质和历史的真相出发触及生命的脆弱与美好。小说中另一个男性叶龙北的失语并不指向个人,也不指向男性与女性的关系,而是针对个人与集体。叶龙北是个知识分子,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被批判改造的对象,虽然他暂时脱离了牛棚,可却不适合参加“早请示”这类活动。他不和人交流,专门和鸡说话,因为时代不允许他和人说话,怕他传播有毒思想,所以被动地处于“失语”状态,只有在司猗纹让众人参观小玮的大便时,他与司猗纹争辩了一番,最后却因为这一次的“放言”而被揭发,落寞地离开了四合院。他离开后,他埋在土里的鸡被罗大妈吃掉了,也就是叶龙北被吃掉了,小说在这里对叶龙北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寓言化的阐释。而且,知识分子代表的科学精神和实证精神也被湮没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中,没有出头之日。铁凝借叶龙北道出了“文革”的另一面:不需要真实,只需要激情和乐观,她以一种平缓柔和的节奏叙述着集体对个人的压制,叙述着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并不完整的历史,不直面也不逃避,这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也是作家的叙事态度。
三、叙事价值的呈现
莫言在谈论长篇小说的内涵时提到一个词:悲悯情怀。他认为“中国式的悲悯是建立在中国的哲学和宗教上的,需要作家正视人类之恶,认识自我之丑,描写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这才是‘大悲悯’,这样才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5]这一点与谢有顺评价铁凝的《玫瑰门》时提到的“生命之善”指向同一个追求——文学创作之于现实的意义与价值。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争论不休,文学无法远离现实也无法对时代亦步亦趋,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文学成为每个时期都难以解释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不论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还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文革”文学,文学的使命感一直存在,虽然各时期的文学范式有所不同,但从未脱离这一主题进行创作。时间来到转折的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不同的政治观念、文学想象,以及权力机构中的利害关系,演化为一系列的论证与冲突,譬如“向前看”与“暴露黑暗”,“朦胧诗”、人道主义与“异化”等。[6]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溃败及作家的危机感日益加重,致力于精神返乡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时代抛弃,以上种种都指向一点:文学主体的模糊,作家、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呈现出更复杂的形态和关系,作家们意识到“自由的向往”实现之后,自己反而失去精神寄托,被普遍意义约束太久,已无法找回个人存在的基本意义和价值,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对文学两大危机——媚俗与自娱提出批判的主要原因。铁凝这一批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现实时,希望通过文学找回自己,找回文学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重新倡导被赋予了深刻时代意义的人文精神,坚持在文学创作中对人类命运、人的生存价值、人的个性与尊严予以强烈而深沉的关怀。
小说中,疯狂女性的代表司猗纹虽对苏眉管束极严,却也会在图清净外出吃早餐时给苏眉带回一个蜜糖麻花。她也会买上一份天福园的酱肉去看望朱吉开的母亲,并给她做炸酱面,这也是小说中难得地给予了司猗纹一份温情与和顺,并通过这两件事的叙述,司猗纹希望成为独立个体的诉求被打破了,在这生命温情的时刻,她是作为苏眉的外婆和朱吉开的恋人而存在的,铁凝挖掘生命之善时,也完成了个体生命的圆满。竹西作为欲望女性的代表,在小说中一直是冷漠、理性、流浪、放纵的代名词,但她却会在苏眉因姑爸的死而受到惊吓时前去安慰,也会在司猗纹瘫痪之后搬回响勺胡同照顾司猗纹,竹西从不追悔从前,但却平静地将自己归回了从前,铁凝希望她回来,回来才能获得生的希望。小说最后苏眉与竹西的那段关于“爱”的对话值得我们好好品味,苏眉爱司猗纹,才能用手还给司猗纹以微笑,竹西不爱司猗纹,才能用手使司猗纹的生命在疼痛中延续。这段玄乎其玄的对话其实在说一件事,苏眉最终接受了司猗纹对她的病态的爱与关注,并将这份爱延续到了刚出生的女儿身上,爱的被接纳和延续给予她圆满的生命。竹西接受了自己无法付出爱的事实,认可了自己的平庸与冷漠,才最终回归了生活的正轨。出走的“娜拉”们回来了,但她们是自愿回来的,带着善意与希望回到了生命的起点。每个人的个体性和集体性不再对立和斗争,复杂的“人”最终接受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人情、人性也找回了自己在文学中的位置。
以上种种都是铁凝通过《玫瑰门》挖掘出的“善”,人性的善,生命的善,命运的善,面对陷入绝望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她反其道而行之,借“善”来反抗人文精神丧失带来的时代的绝望,她以一种温和轻柔的叙述告诉每一个人,人是善的也是恶的,人的身体是美的也是丑的,生命是残酷的也是美好的,善与恶、美与丑、残酷与美好却并不是对立的,人的复杂性在每一个时期都不曾消失,接受它,才能获得力量,获得生存的力量我们才能给予他人关怀,而这是作为一名作家不应抛弃的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