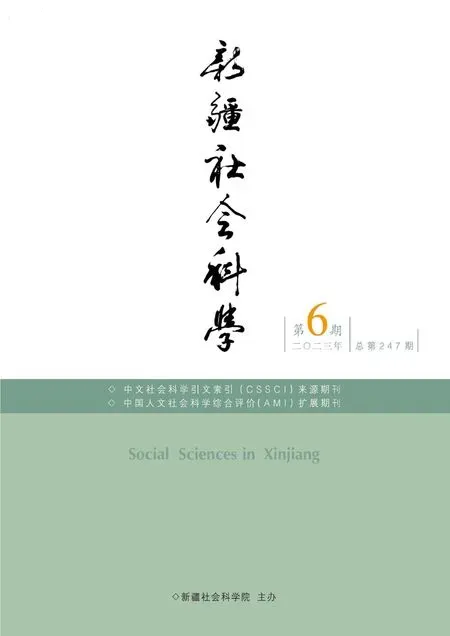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解释论证成及其界限*
梁蒙娜
内容提要:网络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孕育并脱胎于注意义务。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网络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但其在规范上存在解释的可能性。如《民法典》第1195条蕴含着平台对通知中初步证据的审查义务,第1197条“应当知道”中包含平台对特定内容的审查义务。为明晰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合理界限,我国宜基于解释论立场,从类型化认定思路出发,构建网络平台基于通知的事前审查义务,同时在比例原则下动态提升其事后审查义务的主体范围、审查对象及审查程度。
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是在侵权判断中衡量平台方过错的客观化标准,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对相关规定却付之阙如。《著作权法》未明文规定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设立的正当性,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共识,理论依据包括平台预防成本最低、(1)崔国斌:《论网络服务商版权内容过滤义务》,《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平台是离“危险源”(即侵权行为)最近的危险控制人、(2)司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的设定》,《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平台承担审查义务有利于实现对各方的有效激励(3)虞婷婷:《网络服务商过错判定理念的修正——以知识产权审查义务的确立为中心》,《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等。在我国立法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亦对此作出相应规定。《民法典》第1197条新增了“应当知道”的表述,这虽然明确了网络平台对用户利用其网络实施的侵权行为负有一般注意义务,但如何判断“应当知道”却是个实务操作极具难度的问题,这涉及到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界限。若判断标准过宽,则可能使网络平台承担普遍审查义务;若失之过严,则可能严重影响著作权人利益。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在不断寻找促使网络平台适当履行审查义务的平衡点。然而,法律规范的高度抽象性使得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范围和限度具有不确定性,这造成了解释及适用上的问题。比如,网络平台对适格通知中的内容应作何种程度的审查?采取“必要措施”时是否包含预防侵权内容上传?又如,网络平台对热播影视作品审查的范围和程度是什么?
在上述背景下,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界限成为当下值得研究的问题。网络平台应负何种程度的著作权审查义务?有学者主张网络平台仅承担较低注意义务即可,不宜实施较高程度的审查,(4)孔祥俊:《网络著作权保护法律理念与裁判方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第233页;陶乾:《论竞价排名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边界》,《法学杂志》2020年第5期。其背后理由包括促进自由竞争、(5)Niva Elkin-Koren,Yifat Nahmias,Maayan Perel,Is It Time to Abolish Safe Harbor?When Rhetoric Clouds Policy Goals,Stanford Law &Policy Review,Vol.31,2020,p.47.、预防平台“霸权”(6)Farhad Manjoo,Why the World Is Drawing Battle Lines Against American Tech Giants,N.Y.Times (June1,2016),https://perma.cc/P3X7-25GR.保障言论自由(7)谭洋:《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一般过滤义务——基于〈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知识产权》2019年第6期。等多方面因素。有学者主张网络平台的注意义务宜上升为过滤义务,理由在于如此在侵权防范上更具效率优势,(8)崔国斌:《论网络服务商版权内容过滤义务》。且合理分配了预防成本。(9)田小军、郭雨笛:《设定平台版权过滤义务视角下的短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研究》,《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3期。为得出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合理界限,本文将立足于“解释论”的立场,从现有法律出发,首先探讨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在法律解释上的可能性,认为审查义务孕育并脱胎于注意义务,并对《民法典》中为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留有解释空间的条款进行分析。其次,本文将采取类型化认定思路对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进行讨论,最终得出其合理界限。
二、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在法律解释上的可能性
当不同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可以通过法律解释这一外部证成的方式来促进法律与其他规范的对话,并在法律推理等内部证成中推进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一般规范与个案情形的反思性整合。(10)彭小龙:《规范多元的法治协同:基于构成性视角的观察》,《中国法学》2021年第5期。我国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法院不得因网络服务提供者未主动审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而认定其具有过错。(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第2款。但在一些情形中,平台若不主动实施一定审查则会被认定为“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存在,继而被认定存在过错。(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由此产生如下问题:注意义务与审查义务的关系为何?我国网络平台对用户上传内容究竟是否负有著作权审查义务?本章将从解释论角度出发,为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在法律解释上成立的可能性作以阐释。
(一)从网络平台的注意义务到审查义务的逻辑推演
在网络侵权领域,对于行为人过失的判断通常需考量其注意义务之履行。过错是侵权责任构成中一大重要因素,其形式包括故意和过失状态。其中,过失是指行为人对他人侵害其民事权益之结果的发生应注意而未注意的心理状态。(13)程啸:《侵权责任法》第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295页。换言之,过失的行为人之所以要在法律上承担责任,是因为其行为背离了法律、道德对其提出的注意义务要求,以至于造成他人损害。(14)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1页。然而,注意义务的判断通常较为抽象,这使得法院仅能在具体案例中进行价值衡量,有时甚至会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形。例如,在“北京麒麟童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诉斗鱼案”中,一审法院基于涉案直播行为比普通的用户分享呈现出更强营利性,及被告公司对直播内容存在直接获利两点理由,认定被告对涉案侵权行为在主观上“应当知道”,构成侵权。二审则纠正了一审判决,对于原告主张的三种被诉侵权行为作以区分,最终认定被告仅对其中一种方式的侵权行为负责。(15)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民终2905号民事判决书。上述情形出现的原因在于,网络平台的注意义务本就是抽象的,法律法规并未给出明确界限。对于何为网络平台主观上的“应当知道”,法律法规仅能对基本判断标准作出指导性规定,然后交由法院在个案中具体认定。
在此背景下,在解释论层面明确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并明晰其范围与界限,有利于帮助过失要件在网络平台侵权责任判断中具体化。所谓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是指网络平台对平台上内容的著作权合法性进行审查与保障的义务。在网络侵权案件中,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依据平台类型、经营规模、传播内容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同时,任何法律制度设计都应实现成本与收益的均衡,(16)程啸:《侵权责任法》第3版,第314页。在确立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规则时,还需依据经济负担将损害风险公平分配到受害人以外的行为人身上。总之,明确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界限有利于在网络侵权责任认定中实现过失判断的客观化,如此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责任范围的不当扩大,(17)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7页。同时起到督促行为人适当行为的作用。然而,我国在立法上缺失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明确规定,司法上又常常将注意义务与审查义务进行并列使用或混用,这使得二者的边界愈发模糊。如“百度网讯公司诉华夏未来基金会案”中,法院判定百度网讯公司“已经尽到了应有的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对他人侵权行为并不知情,不构成侵权。(18)天津高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五终字第0020号民事判决书。如此表述说明法院认为审查义务与注意义务为并列关系,二者相互独立。但在“王某诉成都伦索科技案”中,法院认定平台构成帮助侵权的理由在于其“未尽到应尽的审查注意义务”。(19)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1)川0193民初6445号民事判决书。此处法院将二者进行混用的表述又表明其认为审查义务与注意义务是具有相同含义的同一概念。
注意义务与审查义务究竟为何种关系呢?二者是否相等?要探究审查义务的界限,就需首先回答上述问题。在我国,关于注意义务与审查义务之间的关系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并列论,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审查义务与注意义务是两种不同概念,其中审查义务是指网络平台负有监控网络信息内容、寻找侵权活动的义务;注意义务则是针对网络平台在发现涉嫌侵权作品时应采取的防止侵害进一步扩大的注意要求。(20)胡开忠:《“避风港规则”在视频分享网站版权侵权认定中的适用》,《法学》2009年第12期。第二种观点是等同论,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审查义务与注意义务均要求网络平台对用户上传内容进行主动审查,并对未经授权上传内容采取必要措施。第三种观点是包含论,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审查义务与注意义务虽具有功能和效果上的一致性,但仍有区别,本质上来说审查义务属于较高层级的注意义务。(21)虞婷婷:《网络服务商过错判定理念的修正——以知识产权审查义务的确立为中心》。上述并列论的观点未认识到审查义务与注意义务均是衡量网络平台是否具有过错的客观形态,二者具有功能和效果上的一致性。(22)虞婷婷:《网络服务商过错判定理念的修正——以知识产权审查义务的确立为中心》。等同论的观点虽认识到审查义务与注意义务之间的关联性,但混淆了二者之间的概念。实际上,审查义务侧重于要求网络平台针对抽象的侵权行为采取一般性的预防措施,而注意义务则重在强调网络平台针对具体、特定的侵权行为负有认知义务。(23)尹志强、马俊骥:《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知道”要件之重新检视》,《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本文赞同包含论观点,认为审查义务孕育于注意义务,并逐渐发展成为注意义务的下位概念。首先,著作权法语境下审查义务的概念起源于注意义务。早期关于注意义务的司法解释之中蕴含着审查义务,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2款规定,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依据著作权法第48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2款。其中出版者的“合理注意义务”可以解释出其对出版物具有审查义务,只有当出版者对相关出版物的授权、稿件来源等信息来源合法性进行主动审查,才符合履行合理注意义务这一要求。这表明审查义务孕育于注意义务,司法实践中最初将审查义务蕴含在注意义务的规定之中。其次,审查义务在注意义务的涵摄范围内,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判断过失程度的客观标准。在实践中,诸多法院将网络平台是否履行适当的审查义务作为衡量其注意义务履行程度的重要因素,以此来判断平台是否应承担过错责任。如“北京麒麟童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诉斗鱼案”中,法院指出被告所应承担的注意义务包括一定程度的审查义务,被告应采取与技术手段相适应的主动过滤措施以防止侵权信息传播。(25)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民终2905号民事判决书。可见,法院将网络平台是否正确履行审查义务作为判定注意义务乃至过错的客观标准。因此,审查义务包含于注意义务,是过错侵权认定中过失的具体判断标准。
(二)《民法典》为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提供规范依据
《民法典》的颁布确立“知道与应知”规则,为网络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提供了规范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确定的过错原则为我国侵权认定的基本原则,第1197条进一步将过错原则融入进网络侵权规范之中,规定当网络平台对用户侵权行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时,平台即具有过错,构成帮助侵权。与原《侵权责任法》第36条相比,现行法律中蕴含的平台审查义务有所提升。
首先,在判断平台是否构成“知道”时可结合《民法典》增设的“通知与必要措施”规则进行分析,相比于原网络侵权条款,现行法律增加了对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要求。实践中对于平台“知道”的判断通常结合间接证据进行推定。具体可依据《民法典》第1195条的“通知与必要措施”规则进行判断,即平台收到通知后未及时行动即具有过错,需就扩大损失与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该条规则为网络平台提供了避风港,当平台及时将权利人通知转送给用户,并根据初步证据及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时,可以免于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款蕴含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具体体现在平台需针对权利人提供的涉嫌侵权的初步证据进行初步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采取必要措施。《民法典》颁布之前,根据原《侵权责任法》第36条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5条规定,平台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时,需立即采取删除或断开链接的措施,不需进行审查。而《民法典》第1195条则要求平台对权利人的身份证明及其提供的初步证据作以审查,与既往“通知删除”规则相比,该规定增加了对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要求。在审查时,平台需要以一个正常理性人标准,基于一般专业知识来确定是否应当支持权利人的请求,(26)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126页。主要目的是防止出现虚假通知、恶意通知等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的情形。(27)王若冰:《〈民法典〉视角下网络虚假信息的规制》,《当代法学》2021年第6期。
在“通知与必要措施”规则中为平台增设著作权审查义务有利于更好的平衡平台与权利人承担的责任,扭转对平台“一边倒”保护的局面。根据原《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平台在收到通知后未及时处理尚且需要与侵权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而在平台因错误通知或恶意通知导致合法内容被误删时,平台却不需承担责任。如此一来,平台在收到通知时会倾向于直接采取必要措施,以避免因未及时行动而承担潜在的侵权责任。在上述规定下,部分权利人势必会通过恶意发送海量通知以进行不正当竞争,这将使部分用户无端受到平台制裁。(28)马更新:《“通知—删除”规则的检视与完善》,《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10期。《民法典》第1195条为平台增设对通知中侵权初步证据的审查义务,有利于敦促平台对不当处理错误通知承担相应责任。这意味着避风港规则的适用门槛将更加严格,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平台受到过大保护。美中不足的是,《民法典》并未对第1195条中蕴含的网络平台审查义务的限度作出规定,这使得平台对通知中包含的涉侵权初步证据应作何种程度的审查尚不清晰。关于平台错误移除的后果,有学者提出用户可将权利人和平台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也可单独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责任,或依据网络服务合同要求平台承担违约责任。(29)程啸:《论我国〈民法典〉网络侵权责任中的通知规则》,《武汉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问题在于,在网络平台错误移除合法内容这一侵权行为中,平台的主观过错通常是难以判断的。《民法典》第1195条一方面对权利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不作要求,仅运用“初步证据”的表述,另一方面却要求平台在错误实施必要措施后承担责任,如此必将导致平台与权利人承担责任的失衡。
其次,我国立法上将“应当知道”的表述纳入《民法典》,司法上在判断平台主观过错时亦以注意义务标准代替红旗标准,有效扭转了我对于网络平台的审查责任狭隘解读的局面。我国在于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首次引入“应知”标准。关于“应知”含义,受红旗标准影响的学者认为“应知”等同于推定知道。(30)吴汉东:《侵权责任法视野下的网络侵权责任解析》,《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推定知道这一概念源自美国帮助侵权的主观要件。在美国,帮助侵权人需知道(Know)或有理由知道(Have Reason to Know)他人特定侵权行为之存在。(31)Fonovisa Inc.v.Cherry Auction,Inc.76 F.3d 259 (9th Cir.1996).其中“有理由知道”等同于推定知道(Constructive Knowledge),即行为人虽不实际知道,却可依据一定事实,按照一个正常的、理性人的标准,意识到侵权行为的存在。(32)Restatement (Second)of Torts§12 (1965).避风港规则中以红旗标准代替有理由知道(即推定知道)的概念,红旗标准更加强调用户侵权行为是否“明显”这一要素,排除了其他可能导致推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用户侵权行为的事实因素。(33)朱冬:《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移植与变异》,《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由于我国的避风港规则是从美国移植而来的,受红旗标准规则影响,上述学者将“应知”解释为推定知道。如此解释的弊端在于,网络平台的审查责任在我国被狭隘解读,著作权保护受到消极影响。将“应知”解释为推定知道,是应用了英美法系下主观过错的概念,将过失排除在网络平台侵权责任的过错形态之外。在此种解释方式下,网络平台仅需承担较低程度的注意义务,平台仅在意识到侵权行为像“红旗飘飘(Red Flag)”般明显却不采取行动时才构成侵权。这种对“红旗标准”规则的直接照搬未认识到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立法背景的差异,不恰当地提高了我国归责所需的过错门槛,极易产生解释上的难题。
当前我国的网络侵权规则已逐步向传统侵权法回归,法院在判断平台是否构成“应当知道”时会考量其注意义务,平台有时也会承担超出一般注意义务的较高注意义务乃至审查义务。《民法典》颁布后,让中国的网络侵权规则回归到传统的解释轮框架之下的呼声不断。(34)薛军:《民法典网络侵权条款研究:以法解释论框架的重构为中心》,《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在我国侵权法框架下解释“应当知道”,并非是对避风港规则的完全否认,而是重拾“应知”概念在大陆法系侵权法中的固有含义,防止过失概念悄无声息的在网络平台间接侵权责任中消失。(35)朱冬:《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移植与变异》,《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在实践中,法院在判断平台主观过错时会衡量其是否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有法院进一步将合理注意义务划分为一般注意义务、较高注意义务及事前审查义务,较好发挥了司法裁判规则的引领作用。例如,在“英度诉爱奇艺案”中,法院根据网络平台主体类型、经营模式及作品类别三个因素判断被告负较高注意义务,甚至事前审查义务。关于何为较高注意义务,法院在判断被告是否具有主观过错时指出:被告未尽应有的审查义务,放任用户在其网站传播影视作品,且提供分类上载及搜索观看服务,未履行其负有的较高注意义务,因此构成应知。(36)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0)渝0192民初7216号民事判决书。从法院判决中可得知,较高注意义务要求平台主动对用户上传内容进行审查,且审查行为不以收到侵权通知为前提。关于何为事前审查义务,法院提出,平台基于所获利益,应当对用户上传作品的权属“进行必要审核、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预防、制止侵权影视作品的传播”。可见,与较高注意义务相比,事前审查义务在要求平台审核用户已上传内容之外,还进一步要求其对用户准备上传但尚未上传成功的内容提前进行审查,以起到预防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民法典》为网络平台承担著作权审查义务留出了法律解释的空间,法院在司法案例中也对网络平台应承担一定程度的审查义务作以肯定,这说明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在我国有生存的土壤。
三、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界限的类型化认定思路
依据平台是否需要预防今后上传内容中出现的涉侵权内容,可将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划分为两类:事前审查义务与事后审查义务。本节依据事前审查义务、事后审查义务这一分类标准,对网络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可能的范围和限度分别进行讨论。
(一)事前:“基于通知的审查义务”之构建
事前审查义务依据平台审查对象的不同,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普遍性的事前审查义务与针对特定对象的事前审查义务。“普遍性的事前审查义务”的常见表述还包括“普遍审查义务”及“主动审查义务”,其要求网络平台对所有用户上传的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换言之,假如平台上出现侵权内容被上传的现象,即可推定负有普遍性事前审查义务的平台具有过错,平台需就此承担侵权责任。出于技术层面、产业发展层面等多方面考虑,世界各国普遍否认网络平台具有普遍性的事前审查义务。“针对特定对象的事前审查义务”是指网络平台仅对特定对象负有合法性审查并预防上传的义务。例如,欧盟的《数字化单一市场著作权指令》第17条第4款c项规定,平台在收到权利人发出的充分实质通知(Sufficiently Substantiated Notice)后,不仅应及时移除特定内容,还应尽最大努力防止它们将来被上传。(37)Directive (EU)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 (Text with EEA relevance.),Art.17(4)(c).此处,平台需要预防相关作品被再次非法上传的义务就属于平台对特定对象的事前审查义务。
在著作权法领域,我国网络平台是否对用户上传内容的合版权性负有事前审查义务呢?当前我国法律法规明确排除了网络平台在著作权方面的普遍性事前审查义务,但是对于针对特定对象的事前审查义务规定不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法院应依据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设置便捷程序接收侵权通知并及时对侵权通知作出合理的反应”来判断其是否构成应知。(3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第4、5款。其中,“合理的反应”虽在《民法典》第1195条又被进一步解释为“删除、屏蔽、断开连接等必要措施”(3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5条。,但仍具有解释的空间。
网络平台对权利人发送的适格通知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宜进一步解释为包含事前审查义务。平台对适格通知相关内容负有事前审查义务,意味着平台在收到权利人发送的合规通知后,不仅需对通知中指向的具体侵权内容采取删除链接、屏蔽等必要措施,还应预防平台上再次出现相关侵权内容。要求平台对特定侵权行为进行预防,本质上是要求平台对用户上传内容实施过滤,即用户一旦拟未经授权上传权利人发送通知中指向的相关作品时,平台需自动阻止其上传。一直以来,关于平台是否适合采取主动过滤,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赞同给平台施加过滤义务,因为如此一来权利人只需起诉平台,而非所有上传作品的用户,从执法成本的角度看给平台施加过滤义务提升了司法效率。(40)Garry A.Gabison,Miriam C.Buiten,Platform Liability in Copyright Enforcement,Columbi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Review,Vol.21,2020,p.245.有学者则反对给平台施加过滤义务,因为算法的不透明性使得公众对平台的过滤行为难以监督。(41)Maria Lillà Montagnani,Virtues and Perils of Algorithmic Enforcement and Content Regulation in the EU,Journal of Law,technology &the Internet,Vol.11,2020,p.26.欧盟在颁布《数字化单一市场著作权指令》草案后,第13条(现第17条)“过滤器条款”就曾受到上述争议。虽然最终通过版本删除了关于“可以采取有效的内容识别技术”的表述,但仍保留了网络平台需“尽到最大努力来确保特定作品或其他内容不被获得”的义务。我国当下也适宜让网络平台对适格通知中包含的作品承担事前审查义务,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从技术成本来看,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在诞生之初是负有激励功能的,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平台降低成本,在权利范围内制止侵权。(42)苏冬冬:《论〈电子商务法〉中的“通知与移除”规则》,《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而在现有算法技术下,在平台已获得权利人提供的相关作品的必要信息(如原始视频、代码、作品的授权情况等)的前提下,让其采取相应技术预防、制止相关侵权作品传播不会给平台造成技术障碍与过分经营负担。其二,从救济程序的正当性来看,平台对适格通知中的内容采取事前审查措施后,仍然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95及第1196条规定向用户和权利人进行转通知及反通知等流程。若权利人不认可用户的抗辩主张,其可提起诉讼或向有关部门投诉;若权利人不进行起诉或投诉,平台则需及时解除事前审查义务采取的必要措施,恢复用户上传的内容,如此确保平台行为的正当性。基于上述理由,让网络平台对权利人发送的适格通知中的相关内容负有事前审查义务具有合理性。
在对平台针对适格通知相关内容的事前审查义务的具体实施上,我国可借鉴德国《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责任法(Urheberrechts-Diensteanbieter-Gesetz)》(以下简称UrhDaG)的相关规定。UrhDaG是德国根据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著作权指令》转换而成的国内法,该法已于2021年8月1日起实施。根据UrhDaG相关规定,本文针对基于通知的事前审查义务在我国的构建与适用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第一,为保障发送通知的权利人的知情权,可规定权利人有权要求网络平台公开屏蔽侵权内容方式的相关信息;(43)UrhDaG第19条第2款规定,权利人可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在依据第7条、第8条对未经授权内容采取屏蔽措施时的技术方式及相关信息。Act on the Copyright Liability of Online Content Sharing Service Providers of 31 May 2021 (Federal Law Gazette I,p.1204,1215),Art.19(2)。第二,为保证该义务的实施具有可操作性,可对视频、音频、文本及图片的合理使用认定作出规定,平台仅需对超出合理使用标准的内容实施过滤;(44)UrhDaG第10条规定,下列内容的使用只要不用于商业目的或仅产生微小收入,可被视为构成第9条第2款第1至3项中的次要使用(Minor Uses):(1)对影视作品、动态影像每次不超过15秒的使用;(2)对音频每次不超过15秒的使用;(3)对文本每次不超过160个字符的使用;(4)对摄影作品、照片或图片每次不超过125KB的使用。Act on the Copyright Liability of Online Content Sharing Service Providers of 31 May 2021 (Federal Law Gazette I,p.1204,1215),Art.10.第三,针对包含部分合法内容的侵权内容,网络平台宜将合法部分进行标注并予以保留,以确保审查行为的正当性。(45)UrhDaG第11条规定了平台在过滤时应对具有法律授权内容进行标识并保留的情形。Act on the Copyright Liability of Online Content Sharing Service Providers of 31 May 2021 (Federal Law Gazette I,p.1204,1215),Art.11(1).
(二)事后:比例原则下审查义务的动态提升
事后审查义务是指平台对平台上出现的具体侵权内容负有及时审查并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当前我国对平台著作权事后审查义务的要求主要蕴含在平台负较高注意义务的情形之中。如当平台将热播影视作品置于首页或对相关内容进行整理、推荐,以及平台上存在同一用户重复侵权行为时,法院可依据侵权事实的明显程度具体判断平台是否构成应知,(4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第12条。此时若平台未及时履行事后审查义务,就存在被认定侵权的可能性。在实践中,法院通常结合平台的服务性质、管理信息能力、经营模式等因素对平台所负事后审查义务的程度作出判断。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今日,为充分平衡各方利益,有必要在实践中结合比例原则动态提升平台的事后审查义务。
以比例原则划定网络平台的责任边界,有利于防止其权利无限扩张。比例原则最早源于德国公法,旨在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个人权利。(47)德国药房案最早确立比例原则的三阶理论(Dreistufentheorie)。BVerfGE,377。对于比例原则可否适用于私法规定,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赞同将比例原则应用于私法领域,理由在于如此能够捍卫私法自治之价值,且有利于推动民法在理念、制度层面之更新。(48)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有学者不赞同将比例原则在私法领域扩张,其认为强行适用或对私法自治产生不正当干涉。(49)梅扬:《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限度》,《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本文赞同前一种观点,认为在私法自治所不及或过度之时,将比例原则适用于私法规范是适宜的。事实上,上述反对将比例原则在私法领域扩张的学者未意识到,对公民权利产生干涉的强制性力量并非完全源于国家,现代民法领域中同样存在可能对私法自治构成威胁的强制性力量。以网络平台规则制定为例,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大型网络平台日益增多,其通过保障竞争、监督质量、管理价格等方式发挥着市场规制者的角色。(50)Jean Tirole,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pp.379-392.可以说,网络平台事实上拥有并行使着监督、影响、定义交易人及利益相关人的巨大权力。(51)刘权:《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以电商平台的法律规制为视角》,《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然而,在平台制定规则时,更多考虑的是平台的单方意志。与平台相比,权利人与用户往往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无法有效、及时的与平台进行对抗,更难以对平台规则的制定产生影响。(52)刘权:《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以电商平台的法律规制为视角》。在涉及到平台规则的实践纠纷中,法院往往以格式合同的规定为依据,只要平台规则满足形式及程序上的特殊规定(例如平台在首页持续公示平台规则),且不违反法律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法院就会认定平台规则属于反映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法合同。(53)金美蓉,李倩:《错误成本分析理论下互联网平台准监管责任的问题与完善》,《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适度的运用比例原则这一公法原理去规范网络平台私权力,以防止其权利无限扩张。
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大子原则。适当性原则要求主体的行动能实现其目的,必要性要求主体在实现其目的时应选择对他人利益损害最小的方式,平衡性原则要求主体的行动目的在价值上不可小于被损害的他人的利益。(54)于柏华:《比例原则的法理属性及其私法适用》,《中国法学》2022年第6期。由于平台的事后审查义务不宜在法律上进行明确界定,法院可结合比例原则在实践中对平台的事后审查义务的主体范围、审查对象以及审查程度进行动态提升。
1.事后审查义务主体动态扩大:确立基本判定标准
首先,在事后审查义务的主体范围方面,我国宜在比例原则下确立具体认定标准,动态增加适用平台类型。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新型网络平台,从小程序服务平台,到云服务器租赁服务平台,再到信息流推荐服务平台,平台类型愈发多样化。对于上述新型网络平台的定性问题,法院通常采取个案认定的方式,在对具体案情分析时附带性的进行讨论。如此虽可避免对平台性质“一刀切”判断给后续带来的禁锢,但为便于统一化认定,亦需明确平台注意义务乃至审查义务的基本判定方式。在新型网络平台的运行模式下,判断平台是否有必要承担事后审查义务,可结合比例原则下的适当性和必要性要素进行判断。具体而言,可参考以下两个标准:一是平台的经营模式是否建立在侵权行为之上;二是平台是否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其服务的侵权性利用。(55)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断网络平台审查义务时也曾引入这两项考量因素。BHG,August 15,2013,No.I ZR 80 /12 - Rapidshare,Para.(b).以信息流推荐服务平台为例,一方面,该平台的经营模式建立在促进侵权短视频大范围传播的方式之上,自身存在着提高侵权传播效率、扩大侵权传播范围、加重侵权传播后果的风险;另一方面,信息流服务平台通过其技术优势帮助侵权用户在网络上获得更多曝光,并以此为自身获取更多流量与市场竞争优势等利益。由于信息流推荐服务平台符合上述两项标准,因此赋予其更高程度的事后审查义务符合比例原则下动态性和必要性的要求,是恰当的。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上述标准对新型网络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进行判断时,还需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分析,即便是同一类型的平台,在不同情况下承担的审查义务程度亦有区别。(56)例如在“老九门案”与“圆桌派案”中,被告平台均使用了算法推荐服务,但法院作出相反判决。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苏02民终4040号民事判决书;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3)沪73民终287号民事判决书。对于日后新增的新型网络平台,亦可采取上述认定方式,在比例原则之下动态扩展事后审查义务的主体范围。
2.事后审查义务对象动态扩大:纳入上传标题等其他信息
其次,在事后审查义务的审查对象方面,关于平台的审查对象除用户上传内容本身之外是否还包括上传标题等其他信息这一问题,相关司法解释语焉不详,仅规定当平台上存在“可以明显感知相关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为未经许可提供”,但其未采取合理措施时,平台构成“应知”。(5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第3款。较为常见的平台可“明显感知”相关内容未经授权的情形是其将热播影视作品置于首页,或对热播影视作品的内容进行整理、推荐等操作。除此之外,从比例原则出发,还有一些情形也可视为平台可以“明显感知”相关内容未经授权提供。在比例原则的适当性要素要求下,将用户上传内容的标题等信息纳入平台事后审查义务对象中,有利于实现著作权法促进作品传播与繁荣社会文化的立法目的。(58)焦和平:《算法私人执法对版权公共领域的侵蚀及其应对》,《法商研究》2023年第1期。若侵权内容上传标题包含“XX卫视”等信息,网络平台在现有技术下一经审查便可发现作品权属来源不合法。因此,用户上传内容标题这一信息同样可解释为包含在《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12条平台可“明显感知”相关内容未经授权的情形之中。
3.事后审查义务程度动态扩大:依据平台经济负担进行价值衡量
最后,在事后审查义务的审查程度方面,我国宜在比例原则下逐步对平台的审查程度作以动态提升。平台审查程度的要求蕴含在平台注意义务的规范中。根据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当侵权行为具体事实明显,平台的注意义务应基于平台服务性质、作品类别、平台管理方式、对侵权通知的反应机制等因素综合考虑。(5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其中,注意义务的考量依据即为平台是否针对侵权行为作出适当的审查。该条款在第7项考虑因素中还加入了“其他相关因素”这一开放性表述,在实践中法院可结合比例原则中的均衡性要素,以价值平衡作为价值冲突情景中的合理性基准,(60)于柏华:《比例原则的法理属性及其私法适用》。对“其他相关因素”的范围作以动态扩展。在判断平台的合理审查程度时,可结合该审查程度是否会给平台带来过分经济负担进行综合判断。(61)欧盟颁布的《数字化单一市场著作权指令》中也提及比例原则,该指令第17条第5款明确指出“在确定服务提供者是否遵循第 4 款规定的义务时,应考虑比例原则”,并且附带了可供参考的因素,其中包括“履行义务的手段给服务提供者带来的成本”。Directive (EU)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 (Text with EEA relevance.),Art.17(5)。以“平台的事后审查义务是否应上升为全面事前审查义务”这一问题为例,有学者表示赞同,提出我国已经具备引入版权内容过滤义务的技术基础与现实基础。(62)崔立红:《区块链视角下互联网平台的版权内容过滤义务》,《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事实上,当前若要求平台进行全面过滤,将会过分加重平台的经济负担,不符合比例原则中均衡性子原则的要求。一方面,平台需建立全方位的正版数据库作为过滤识别依据,另一方面,不依据权利人发送侵权通知,平台难以得知被传播内容是否已获权利人授权。因此,当前不适宜将平台事后审查义务上升为全面审查义务。但若仅要求平台对适格通知中的内容进行事前审查,采取避免上传的预防措施,是恰当的,因为平台可通过权利人发送的原始视频、代码、授权情况等必要信息建立正版数据库,对平台上的内容实施有针对性过滤。总之,法院在实践中判断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具体边界时,可结合审查程度是否不合理增加平台经济负担进行价值衡量,给平台设置符合比例原则的著作权审查义务。
对于用户上传到平台上的内容,网络平台需承担相应的著作权审查义务,我国《民法典》为此提供了解释依据。由于法律无法对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界限予以明确界定,我国宜采取类型化认定思路,将审查义务划分为事前审查义务与事后审查义务分别讨论。在“通知与必要措施”规则下确立网络平台对适格通知中相关内容著作权合法性的事前审查义务,符合当下技术水平,且不会影响后续转通知及反通知等流程,具有合理性。网络平台事后审查义务的界限宜在比例原则下进行动态扩大,在主体范围上确立基本判断标准,在审查对象上纳入上传标题等其他信息,在审查程度上依据平台经济负担进行价值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