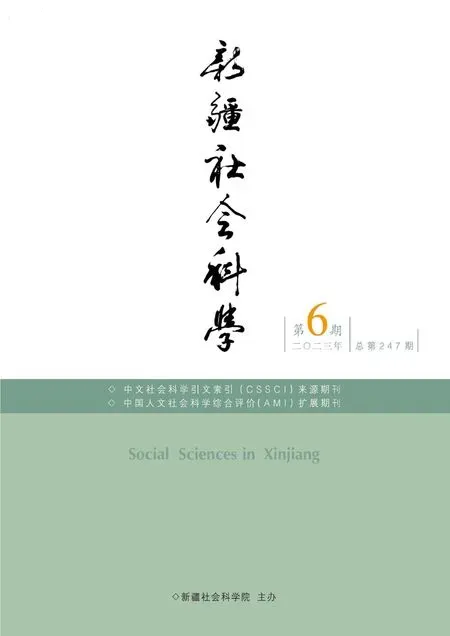帝国的“知识殖民”:认识十九世纪沙俄对中亚空间秩序建构的新视角*
黄达远 彭雪滢
内容提要:当前,国内历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学者十分关注“帝国转向”的议题,尝试重新从空间秩序的角度切入帝国史与殖民地关系史研究,从而也影响到中亚史研究领域。文章认为,与其他殖民帝国相比,19世纪的沙俄帝国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对殖民地区域的地理空间认知的全新塑造,进而推动区域空间秩序的变革。这种空间秩序依托维尔内、塔什干、比什凯克等现代城市的崛起以确定新的中亚中心、依托中亚区域内铁路网的建设以替代传统的驼队商路、印制新式中亚地图取代缺乏现代科学要素的传统地图以重构认知。因此,只有对沙俄以“殖民现代性”建构中亚秩序的过程进行充分的系统的历史与知识反思,才能更深刻理解提出“共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重要意义。
尽管长期以来中亚的历史重要性广为人知,但并没有反映在对该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之中,(1)恰赫里亚尔·阿德尔:《中亚文明史》第6卷,吴强、许勤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科教文组织,2006年,第7页。即中亚史研究缺失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18世纪以来的西方人类学和东方学学者在研究“非西方社会”时,并未将研究对象视为“现代国家的现代社会结构”,故而其研究也并非以国家为中心。然而,地区研究兴起后,历史学等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将“非西方世界”引入自身经验领域,把非西方地区也纳入到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模式之中。就中亚史研究而言,历史学学者需要以更长时段视野研究中亚地区的历史,借助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回答中亚的“本质”。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18—20世纪的“帝国”进行了再认识,出现了“帝国转向”,对其构建的殖民世界秩序、霸权的政治与文化的多重内涵进行了更为细致与深刻的分析。这类讨论注意到,作为一种世界秩序,殖民主义为殖民地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2)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苏联解体与美国霸权形成的历史背景下,“帝国”问题再次引起学界关注,与过去的讨论不同,学界不再过分聚焦“帝国主义”问题。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及来自历史、政治哲学、国际关系等领域对后殖民批判的运用,关于“帝国”的殖民世界秩序,其霸权的政治与文化多重内涵被更为深刻地进行了分析。参见殷之光:《发明“帝国”:20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秩序观的演变与帝国主义的国家观》,汪晖、王中忱主编:《区域》第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这类变化被概括为“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3)美国东亚历史研究者汤尼·白露(Tani E.Barlow)1990年代最早提出“殖民现代性”概念,认为“殖民主义”与“现代性”是工业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产生的一对“双生儿”,而“殖民现代”性概念正是为了解释这两者之间既矛盾又共生的复杂关系。参见Barlow,Tani E.,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有学者曾撰文讨论沙俄建构的以乌拉尔山为欧洲-亚洲的边界,从而形成“欧洲俄罗斯”和“亚洲俄罗斯”的认知,指出沙俄亦曾以“科学考察”为依据构建“新亚洲”、以“中央欧亚”取代“鞑靼利亚”来摆脱鞑靼身份使俄罗斯人彻底欧洲化、“文明化”,并基于“文明-野蛮”合法性向中亚输出秩序。(4)黄达远、孔令昊:《文明论视角下的“沙俄·中亚”空间建构及其对晚清中国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5期。这种“文明-野蛮”的等级秩序中就有“殖民现代性”因素。沙俄对中亚的征服不仅是中亚历史演进的最大变量,更为重要的是沙俄在知识上重新定义了“中亚”。因此有必要对19世纪沙俄在中亚地区的一系列行为进行认识。
一、以“综合地理学”(Обшир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的名义对中亚进行“科学考察”
沙俄征服中亚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对哈萨克汗国(今哈萨克斯坦大部)的征服;第二阶段为对七河地区、锡尔河及中亚其他地区的征服 。其中的一条征服主线是从西伯利亚沿着中国边境南进,经过哈萨克汗国的“中玉兹”部分,越过巴尔喀什湖。沙俄首先将中亚草原收入囊中。失去了保护性的草原缓冲带后,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国也陆续沦为沙俄在中亚的殖民地。1867年,沙俄将土耳其斯坦总督区划分为两个地区:以塔什干为中心的锡尔河地区和以“维尔内”(5)俄语意为“忠诚”,即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为中心的七河地区。这一时期,多国学者都曾在中亚地区进行地理、历史、文化考察,而俄国学者在其中占有主要地位,天山地区更是其探险考察的重点。19世纪,沙俄对其亚洲边疆以南,即里海东岸到蒙古、新疆、西藏的“大中亚”地区的地理知识知之甚少,因而里海至中国长城之间的亚洲中心地带是沙俄最重要的探索领域,(6)Keay,John,ed.,The History of World Exploration,New York:Mallard Press,1991.伴随着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对新殖民地和控制的半殖民地进行区域地理考察成为沙俄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以后进行殖民和经济活动做准备。
1845年10月7日,俄国地理学会在圣彼得堡成立后,立即组织学者对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地理考察。这一时期的沙俄地理学家普遍接受了洪堡和里特尔的主张。根据二人的界定,地理学具备广泛性,研究地球及其居民之间的所有互动。(7)Martin,Geoffrey J.,All Possible Worlds: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由此,沙俄地理学界反对18世纪百科全书式的探索,主张应系统地收集某一未知地区的大量数据,将地形学、气候学、人种学和东方学等领域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即“综合地理学”。此外,“综合地理学”具有鲜明的军事性特征,1855年,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反思克里米亚战败之耻,进行改革重振军队,时任军务部长德米特里·米柳京(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илютин)负责此项改革。他认为:“军事力量不仅仅包括军队或船只的数量……它包括一个国家可以为战争调动的所有资源和能力。”(8)Brooks,Edwin Willis,D.A.Miliutin:Life and Activity to 1856,Ph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1970.为此,除了引入军事统计学,沙俄还重建了军事地理学。沙俄军事统计学科综合体系与洪堡和里特尔的地理学整体方法非常相似,为帝国的战略情报评估建立了一个更为客观、严谨、科学的现代指标体系。
具备军事性特征的“综合地理学”成为了帝俄殖民扩张的理论工具。俄国地理学会不仅是沙俄在亚洲收集关键地理信息的学术平台,更是其领土扩张的“先锋官”。负责地理学会40余年的谢苗诺夫·天山斯基(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Семёнов-Тян-Шанский,1827-1914)曾在柏林求学,师承洪堡与里特尔。在亚洲腹地探险期间,他收集了从西伯利亚至天山山脉广阔地区的地形、地貌、气候、植物、矿藏、人口构成及生活状况等方面的大量信息,填补了关于这一地区的“综合地理学”信息空白。谢苗诺夫认为,“环境的力量促使沙俄进入亚洲深处”,“这是未来最重要的任务”。(9)Semenov,Petr Petrovich,Istoriia Poluvekovoi Deiatel’Nosti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Geografcheskago Obshchestva 1845-1895(The History of Half a Century of Activities by the Imperial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845-1895),3 vols.,St.Petersburg:Tip.V.Bezobrazova,1896.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沙俄的扩张寻找新的殖民地——易于开发的土地。他认为,天山中部的山谷完全处于森林植物界限以上,不适于农业移民,而外伊犁阿拉套的四条纵向山谷(10)即克宾河谷、奇里克河谷、杰尼什克河谷和阿瑟河谷。完全处于森林植物地带,因而非常适合农业移民,更适合发展畜牧业,“维尔内和外伊犁山麓的所有俄国居民点,都分布在外伊犁边区的农业地带。这就使俄国殖民者有可能在伊塞克区域扎下根来”(11)〔俄〕П.П.谢苗诺夫:《天山游记》,李步月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24页。。职业军人出身的加斯弗尔德(Густав Христианович Гасфорд)曾以西西伯利亚总督身份亲自到西西伯利亚的南北两端进行考察,并将注意力集中于开发七河地区,修筑通往七河地区、区域内居民点之间的道路,并向亚洲腹地推进。(12)〔俄〕П.П.谢苗诺夫:《天山游记》,李步月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24页。
以谢苗诺夫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和加斯弗尔德为代表的职业军人共同建立了一套基于综合地理学的“帝国档案”。在帝国背景下,博物学的活动——制图、采集、整理、分类、命名等,这些活动不仅代表着探求事实的科学研究,也反映着认知领域的侵略性扩张。(13)Fan,Fa-ti.,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89.在19世纪,科学考察通常包括采集、测量、制图与旅行,最终是要全面准确地书写全球博物史。这不仅源自与欧洲扩张相伴而生的地理观、自然观,也源于一种认为欧洲科学家“有权”不受干扰地游历、观察、书写其他大陆的傲慢。正是这种自封的“权威性”认知构筑了掌握“认知权力”的信念,为之后的“知识帝国”建设“殖民现代性”。
二、构建俄式现代“文明”中心
(一)七河草原上兴建军事重镇“维尔内”
借用地理学家们的考察成果,在外伊犁阿拉套山脚下的阿拉木图河出口附近,加斯弗尔德勘定设置移民定居点并修筑堡垒,定名为“维尔内”,成为沙俄封锁浩罕汗国北部边境的第一个堡垒。为配合维尔内要塞的建设,加斯弗尔德还在距中国塔城不远的阿拉湖的一条支流上修建乌尔贾尔镇,在阿拉套峡谷中修建列普辛镇,形成了以维尔内为中心的小型城镇群。此外,还修建了从阿拉套山脉至科帕尔、塞米巴拉金斯克至伊犁河的道路及沿途哨所,并配备一定数量的军人驻守。以维尔内、列普辛、乌尔贾尔三个城镇堡垒为支点,辅之以穿越高山峡谷、连接水源的道路网,形成了沙俄统治七河地区的重要核心城镇群。
随着沙俄的南下征服,如何统治当地人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东方学家往往受命参与其中。作为沙俄治下七河草原历史地理文献的主要编撰者,巴托尔德(В.В.Бартольд)将七河地区视为中亚游牧文明的中心,认为从额尔齐斯河、额敏河到天山,从巴尔库、大宛(拔汗那)到巴尔喀什湖的游牧人居地,自渺无记载的年代起就是一个文明区,(14)〔俄〕巴托尔德:《七河史》,赵俪生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68页。历经乌孙、突厥、葛逻禄、喀喇汗朝、哈喇契丹(西辽)、察合台汗国、帖木儿汗国以及准噶尔汗国八个政权的历时性统治,并为之编制了年代表。为了凸显俄国在该地区的中心地位,他对于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治理不无贬低与刻意忽视,“而直到沙俄在七河地区建立起主权之后,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这才享有实效上的自主”(15)〔俄〕巴托尔德:《七河史》,赵俪生译,第92页。。一方面,巴托尔德主张“应为欧亚大陆各民族建立与欧洲历史相同的历史演变规律”(16)巴托尔德写给罗森的一封信(1892年),参见Крачковский И.,Избранные Cочинения,т.1,с.V (Москва и Ленинград,1958),с.348。,以“历史民族志”将欧亚大陆各民族纳入欧洲知识体系和历史分期的框架之中,为中亚游牧草原塑造出一个“文明中心”,弱化或忽视其原有的文明中心,重构欧亚大陆的“文明秩序”。另一方面,修建维尔内城镇群以塑造“文明中心”的现实载体。沙俄通过建立军事城镇,以利于军队和殖民者控制草原民众并威吓中国戍边官员。1867年,维尔内成为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区七河州的行政中心城市,不仅有效控制了七河地区,而且依托与额尔齐斯河上各要塞之间的交通网络控制哈萨克草原,其影响远远超越了原有政治中心。
(二)河中地区兴建“俄罗斯塔什干”新城
1865年,沙俄军官切尔尼亚耶夫(Михаил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Черняев)攻陷河中地区重镇塔什干后,在旧城附近兴建新城,名为“俄罗斯塔什干”。1867年,沙俄在此地设置土耳其斯坦总督府,考夫曼(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Кауфман,1818-1882)为首任总督。考夫曼任职期间,划定了塔什干城区界线,(17)А.И.Добросмыслов,Прошлая П Настоящая Пстория Ташкента,Ташкент:Электро-паров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О.А.Порцев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1912,стр.63-79,5-6.新城得以迅速发展。“土著城区”和“俄罗斯城区”(塔什干新城)共同构成塔什干“双城”。1868年塔什干共计11 518户,1869年户数迅速增至14 222户。此后,沙俄政府还先后进行了三次塔什干城区人口普查(见表1),“俄罗斯塔什干”人口数量呈指数增长,反映出新城区的迅速扩张和发展。考夫曼还通过推广灌溉农业、扩大城市腹地、发展贸易以促进城市化建设,推动新经济文化中心形成,在原有的塔什干城市边缘建立现代欧洲殖民城市的样板,与古老传统的亚洲老城镇形成鲜明对比。(18)Ergashevich,Ergashev Bahtiyar,et al.,Tashkent by the Interpretation of Russian Research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and Multireligious Understanding,7.10 (2020),pp.409-414.

表1 塔什干三次人口普查后“双城”人口对比情况
随着新城区建设和发展,塔什干历史也被写入沙俄殖民史。作为考夫曼的随行官员,多布罗斯·梅斯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Добросмыслов,1854-1915)(19)沙俄历史学家、民族志学家,沙俄地理学会奥伦堡分会和科学档案委员会成员,1888—1901年,在托尔盖地区担任兽医。曾著有《塔什干的过去和当下》(《Прошлая и настоящая история Ташкента》,1912),称塔什干的历史或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当时中国旅行家玄奘曾提到过这座城市,名为“石国”,被视为“中华帝国”的附庸。714年,阿拉伯人袭击河中地区,塔什干统治者向中国皇帝求助无果,716年为阿拉伯人征服。阿拉伯人离开后,河中地区内乱不止,中国派遣大将高仙芝治乱,塔什干统治者投降,并向中国总督派遣使者,但使者被杀害,因而塔什干统治者转向阿拉伯人求助,从此阿拉伯人的势力在这里得到了加强。,(20)А.И.Добросмыслов,Прошлая П Настоящая Пстория Ташкента,Ташкент:Электро-паров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О.А.Порцев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1912,стр.63-79,5-6.“当中国人试图向中亚地区扩张势力时,塔什干人为抵御强大的敌人,与阿富汗埃米尔艾哈迈德·沙赫(Ахмедъ-шах)结盟”。(21)А.И.Добросмыслов,Прошлая П Настоящая Пстория Ташкента,Ташкент:Электро-паров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О.А.Порцев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1912,стр.23,12,18,79-80.18世纪,钦察草原乌兹别克汗国阿布海儿汗通过奥伦堡远征军首领基里洛夫(Кирилов Иван Кириллович,1695-1737)向安娜女皇(Анна Иоанновна)俯首称臣,以求庇护。(22)А.И.Добросмыслов,Прошлая П Настоящая Пстория Ташкента,Ташкент:Электро-паров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О.А.Порцев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1912,стр.23,12,18,79-80.这套叙事话语为沙俄“文明征服中亚”进行了辩解。
以考夫曼为首的沙俄殖民当局,一方面将塔什干原有的城市空间一分为二,通过公共设施建设等不断凸显新旧两个城区作为公共空间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力图拉近塔什干与俄罗斯欧洲部分之间的“距离”,将塔什干打造成一个“大都市”,而不再是远离首都的殖民地。(23)А.И.Добросмыслов,Прошлая П Настоящая Пстория Ташкента,Ташкент:Электро-паров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О.А.Порцев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1912,стр.23,12,18,79-80.在此过程中,塔什干成为沙俄向其亚洲殖民地展现“文明使命与权力”、向殖民者和土著民进行“权力博弈”的场域,其结果是塔什干的“欧洲俄罗斯”属性不断增强,而其作为本土绿洲城市的“亚洲俄罗斯”属性,则成为衬托俄罗斯文明欧洲化与现代化的“参照物”。
作为沙俄在传统中亚地区新嵌入的两个中心城市,维尔纳和塔什干新城获得了帝国的优先扶持。19世纪80年代沙俄结束对中亚的军事征服行动后,制定颁布有关在中亚定居的法律法规并在当地建立新的财政体系。在修筑铁路的同时引入棉花种植技术,开始大规模开采当地自然资源 。随着工业经济发展和定居政策的施行,传统绿洲城市的社会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塔什干铁路竣工后的数十年间,塔什干的定居人口增加了近一倍,1869年为41 799人,1897年增至87 017人。(24)А.И.Добросмыслов,Прошлая П Настоящая Пстория Ташкента,Ташкент:Электро-паров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О.А.Порцев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1912,стр.23,12,18,79-80.
三、中亚铁路与区域的“时空变革”
1867年,沙俄在设立土耳其斯坦总督府后,立即将建设与其欧洲部分相连的交通通讯设施提上议程。(25)Wheeler,W.E.,The Control of Land Routes:Russian Railways in Central Asia,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1934,21(4),pp.585-608,585-608.法国工程师莱塞普斯(Ferdinand Marie vicomte de Lesseps)向沙俄当局提交了一份关于修建从奥伦堡到塔什干的铁路的可行性报告。(26)Turgaiskaya Gazeta,1901a-Turgaiskaya Gazeta,Turgay Newspaper,1901a,No.22,Orenburg:in Russian.奥伦堡哥萨克军队上校索博列夫(Соболев)也基于“在土耳其斯坦军区驻扎4万人”的需求,希望政府当局“将俄罗斯欧洲部分与塔什干连接起来”(27)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Оренбургской Области,Ф.6.Оп.10.Д.8420.Л.90 об.。其时俄国跨里海铁路业已建成,而“俄属中亚”的政治中心日益向土耳其斯坦转移。最终,中亚铁路的建设从里海出发,由西向东途径布哈拉、撒马尔罕到达塔什干、安集延,而后沿西北方向跨越哈萨克草原到达奥伦堡。此后,奥伦堡—塔什干铁路成为沙俄在中亚的主要战略交通线,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亲王称之为“帖木儿时代伟大的呼罗珊路线的复兴,连接了中国、波斯与欧洲的商业,拯救了濒临崩溃的中亚城市”(28)Wheeler,W.E.,The Control of Land Routes:Russian Railways in Central Asia,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1934,21(4),pp.585-608,585-608.。沙俄则通过控制这些陆路贸易干线获得了在欧亚腹地的主导权。
沙俄以新兴的中亚城市为舞台,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欧洲先进的技术、法律和文化冲击,而中亚铁路的修建是促使中亚城市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9)恰赫里亚尔·阿德尔《中亚文明史》第6卷,吴强、许勤华译,第683、33页。是中亚“工业革命”的重要开端。在俄属土耳其斯坦,沙俄殖民者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主要是通过市场方式来完成的。(30)恰赫里亚尔·阿德尔《中亚文明史》第6卷,吴强、许勤华译,第683、33页。由于铁路的开通,南部绿洲城市与俄国欧洲部分的空间距离被大大“压缩”,使得沙俄对中亚的影响达到顶峰,并得以加强对中亚的军事控制,同时将中亚作为原材料供应方,与俄罗斯工业发展联系起来。(31)Searight,S.,Russian Railway Penetration of Central Asia,Asian affairs,1992,23(2),pp.171-180.
铁路建设对草原社会的影响更为显著。铁路沿线也开设有便利的牲畜销售点,因而铁路运输逐渐取代了最重要的游牧贸易——马车运输,草原上的货物流量大大增加,运输成本增加也导致草原物价飞涨。(32)Избасарова,Г.Б.,Оренбургско-Ташкент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И Казах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в.(на примере Тургайской Области),Bylye Gody,2019,54(4).同时,铁路沿线贸易也扩大了贸易范围,商品需求量增加,为游牧民提供了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的机会。此外,在歉收年份,通过铁路可以在短时间内调度面包和干草,甚至在灾荒时期可以将牛羊运输到合适的牧场。(33)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Оренбургской Области,Ф.6.Оп.10.Д.8420.Л.62.不过,修建铁路的工人的到来挤占了游牧民的生存空间。干草加工业的发展改变了游牧周期,游牧民节约了原来的冬牧时间,可以有空闲时间参与工业和手工业生产,这也推动着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等游牧人口逐渐向半游牧、甚至定居转变。哈萨克草原上出现了大量冬季定居点和住宅,加速了维尔内等草原防御工事向现代城市的转变,草原传统牧区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在此后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文化和历史后果。(34)Избасарова,Г.Б.,Оренбургско-Ташкент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И Казах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в.(на примере Тургайской Области),Bylye Gody,2019,54(4).
及至19世纪中叶,哈萨克草原的外来人口主要为哥萨克人。1861年沙俄农奴制废除后,历经土地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大量外来者得以不受限制地涌入哈萨克草原,其中俄罗斯人占绝对多数,而农民成为定居者中的最大群体。1853—1905年间,沙俄侵占了四千万俄亩的哈萨克牧场土地,约占今哈萨克斯坦全部领土的20%。1897年,哈萨克草原上的人口总数为4 147 800人,其中哈萨克人计3 392 700人,占比约81%,至1912年,人口总数为5 910 000人,其中哈萨克人计3 825 000人,占比下降至65.1%。(35)恰赫里亚尔·阿德尔:《中亚文明史》第6卷,吴强、许勤华译,第17页。哈萨克草原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情况也变得更为复杂,但是逐步定居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中亚铁路建设促进了中亚现代城市的出现,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人口聚集和社会分工,后期则颠覆了中亚传统的丝路贸易体系,以新的“文明秩序”引发了中亚地区的“时空变革”(36)此处借用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e)在其《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一文中提出的“文明十要素”,其中包括城市的出现,以及相关的人口聚集、社会分工、长短途贸易。参见V.Gordon Childe,The Urban Revolution,Source:The Town Planning Review,Vol.21,No.1(Apr.,1950),pp.3-17.。中亚铁路的开通,使得地理空间被大幅“压缩”,草原居民点、绿洲城市、草原与绿洲之间的地理距离被现代交通技术“弥合”,地域环境对社会关系的限制作用被削弱,传统社会的“时空关系”被改变,赋予了中亚人群“跨越时空”的想象能力。“脱域”机制使得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被无限重构的时间关联中“脱离出来”(3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采矿、冶金等现代性的社会活动得以从早先专属于“欧洲俄罗斯”的地域化情境中被提取出来,超越时空距离重现于“中亚情境”,重组了中亚的社会关系。铁路运输增强了人口和物质的流动性,“脱域机制”使得中亚的地方性因素与全球性因素结合起来,并将个体与社会结构中的诸维度连接起来,赋予了中亚人群一种全新的“时空观”,中亚地区的现代性在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转换中得以展现,为中亚“新地图”的出现奠定了新的区域空间。
直至17世纪,在传统的草原驼运贸易体系下,布哈拉商人活跃于沙俄及西伯利亚,形成了众多相互依存的专业化组织。(38)Burton,A.,The Bukharans:A Dynastic,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History 1550-1702,2003,pp.407-425.而19世纪80年代之后,中亚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沙俄的控制之下,采矿业、石油业等新的经济活动得到快速发展。沙俄向棉花种植业、铁路工业等主导性产业的集中投入,对当地和地区市场造成了强烈影响,并最终促使本地经济转变为一种依赖于沙俄帝国全球性政治与经济需要的殖民地经济。(39)恰赫里亚尔·阿德尔:《中亚文明史》第6卷,吴强、许勤华译,第28—29、9页。
中亚铁路成为沙俄整合中亚殖民地与“欧洲本部”的重要工具。至19世纪60年代,沙俄已经将草原和绿洲上的诸汗国收入囊中,而加强殖民地与“欧洲本部”的联系成为下一个重点。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亲王(40)Князь Алекс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Л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1824-1896),代表沙俄于1879年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君士坦丁堡合约》、1896年与清廷签署《中俄密约》(又称《李-洛巴诺夫条约》)。曾指出,“俄罗斯无法再进一步扩张领土,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守护和发展已经拥有的领土。”(41)转引自Wheeler,W.E.,The Control of Land Routes:Russian Railways in Central Asia,pp.585-608.领土并非纯粹的地理空间,而是被一种特定权力控制的一个区域,(42)〔英〕斯图尔特·埃尔登:《领土论》,初冬阳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9页。在不同权力的互动和竞争中形成。沙俄领土的中亚部分基本成型于英俄“大博弈”期间,对于幅员辽阔的帝国来说,军事机动性至关重要,英国的机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海军,而沙俄的机动性则取决于其铁路。(43)Searight,S.,Russian Railway Penetration of Central Asia,pp.171-180,171-180.随着19世纪60年代对高加索地区征服行动的落幕,沙俄在接下来的20年里努力在中亚建立南部边界。(44)Searight,S.,Russian Railway Penetration of Central Asia,pp.171-180,171-180.铁路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是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和管理国家领土空间的重要方式,铁路则是这一过程的物质标识之一。(45)王浩宇、汤庆园:《边疆交通建设与政治空间生产——以川藏铁路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作为反映沙俄帝国的具体可见的“景观”,铁路建设是其实施“领土工程”的主要工具。作为陆权国家,沙俄在完成对中亚的征服后,还需整合草原与绿洲,巩固其对边境地区的统治。中亚铁路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沙俄在中亚南部的物理边界,维系并强化了其在草原与绿洲结合部的统治。1895年,沙俄军事地形局制图部(Карт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деление Военно-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绘制出版了《亚洲俄罗斯军事路线图》(《Военно-дорожная карта Азиатской России》),该地图涵盖了从里海到鄂霍次克海的广大“亚洲俄罗斯”领土,并注明了定居点和建设中的铁路。1919—1924年间,在1895年初版的基础上该地图被重新编制出版,特别添加了新的铁路线。沙俄帝国晚期的中亚地图已经成为一张以铁路网络、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用欧洲工业文明“描绘”的空间秩序图。
英俄“大博弈”期间,沙俄经西伯利亚南下河中地区,英国自印度北上阿富汗,中亚的大部逐渐被沙俄控制,其社会政治与文化延续的两大支柱,即伊斯兰教和成吉思汗世系统治的正统合法性,出现了一系列断裂。(46)恰赫里亚尔·阿德尔:《中亚文明史》第6卷,吴强、许勤华译,第28—29、9页。在欧洲中心观和沙俄中心观(文明等级论)的宰制下,中亚地区亦经历了一场“空间革命”。任何一种基本秩序都是一种空间秩序,因为真正的、源初意义上的基本秩序,本质上都建立在明确的空间界限和界限设定的基础之上。(47)〔德〕卡尔·施密特:《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林国基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45页。而这一“空间变革”依托维尔内、塔什干、比什凯克等现代城市的崛起以确定新的中亚中心、依托铁路网的建设以替代传统的驼队商路、以新式中亚地图取代缺乏现代科学要素的传统地图等方式得以展现。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中亚”构图最终完成,并逐步获得了世界的承认。
四、结语:从“中亚”构图理解“殖民现代性”的知识陷阱
中亚地图的出现作为一种对空间的图示形式,使得沙俄得以实现对中亚土地和政治空间的掌控。交通地图是政治空间的投影,对于政治空间的治理至关重要。沙俄通过描绘新的现代城市、铁路线路,并借助现代地理的“科学性”,将中亚自然地理空间抽象化,建构起一种包括结构、中心方位、距离、面积等的空间认识视角,进而强化国民对国家地理分布的了解和认知,从而实现对领土空间的控制,并维系政治空间内人员、资源、信息的流动。由此,沙俄得以优先将欧洲属性的政治空间映射到地理空间,将领土在现代交通(铁路)地图上作为政治空间再现,从而将中亚整合进国家领土,使中亚自然空间逐渐具有权利内涵,并由自然空间向政治空间演进,成为沙俄国家的构成要素和主权的核心内容,并与“他者”区分开来。
以中亚铁路为载体搭建起来的交通网络,以及工业化交通地图的再现,将深入到草原与绿洲的殖民城市联通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张“文明地图”,取代了传统的丝绸之路地图,以及草原、绿洲传统汗国的地图。实际上,这是沙俄殖民者急于抹去中亚业已存在的社会和地理文化形式,并准备以新秩序投射于其上、取而代之。这种“知识殖民”的现代性一般很难被察觉,甚至到了苏联时代,一些地理学家还在“赞扬”说,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沙俄对中央亚细亚的考察是继承性和坚定的目的性,考察对有计划地开辟路线,以便把中央亚细亚地图上的空白点分成越来越小的地块。(48)〔苏〕H.M.休金娜:《中央亚细亚地图是怎样产生的》,姬增禄、阎菊玲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
综上,我们认为,今天在使用“中亚”(49)中亚的地理解释,俄语中以“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汉译:中央亚细亚)表述广义之中亚范围;狭义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是指苏联亚洲地区的一部分,西起里海、东到中国与苏联边界、北至咸海—额尔齐斯分水线、南达苏联同伊朗和阿富汗的边界,本文主要取狭义中亚的地理范围。这一概念时,不能简单化地借用沙俄帝国时期的“中亚”地理名称,而是要了解其地理概念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建构。宋念申认为,“地图不是对地理空间的再现,而是人们对地理空间的主观解释。而对空间的解释,直接关系着对这个空间的使用和占有方式。现代殖民帝国兴起于欧洲‘地理大发现’,伴随着对地球空间的重新理解,帝国也开始了对新空间的占取和利用。因此,16—19世纪代表性的欧洲地图作品,不但是殖民帝国新地理知识的体现,也是其殖民权力和帝国意识形态的体现。”(50)宋念申:《地图帝国主义:空间、殖民与地球规治:“帝国转型与国家建构”专题(一)》,《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期。由此,在中国—中亚峰会的背景下,我们认为,要共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应该对“中亚”概念使用保持清醒。对于过去沙俄殖民主义的知识体系进行反思,跳出“知识陷阱”。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将“中亚”还原到绿洲、农耕、游牧之间的文明与区域共同体的概念之中,对建设中国与中亚地区建立山水相邻、休戚与共的友邻关系,落实中国—中亚峰会精神更有迫切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