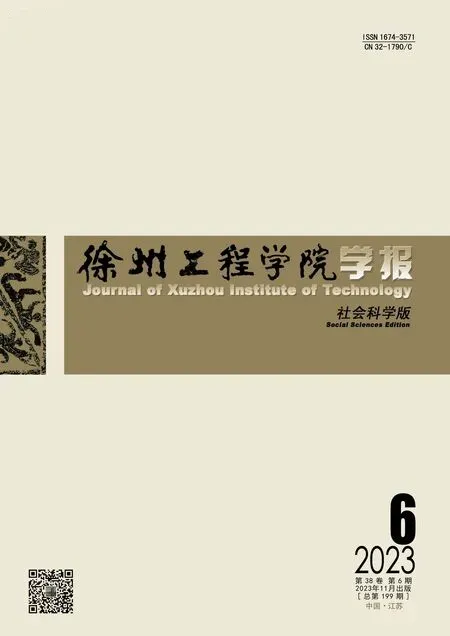秦观词“伤心”基调之呈现
赵宏烨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冯煦在《蒿庵论词》中对秦观有非常重要的评价:“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1]3587自此以后,“伤心”一直是研究秦观词作不可忽视的切入点。秦观以心为词,从离别题材的书写、隔绝迷蒙境界的营造以及贬谪之痛与罪人意识的流露三个方面,将伤心之语全部展露出来,形成秦词独特的风貌。
一、情景选择:身世之悲与离愁别绪的双向渗透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是传统诗词中历久弥新的书写主题,秦观对羁旅行役的创作,在其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正是对这种题材和情感选择,使得秦观的词大面积地呈现出伤感的基调。少游满怀壮志,却落第,人生的进程一再耽搁;后又卷入党争,一贬再贬,飘零半生。离别本身就带着忧伤,再加上词人生平坎坷、遭逢不偶,屡试不第导致的蹉跎感和贬谪带来的漂泊感熔铸于情景之中,更显悲痛。秦观善于在最易动情的离别时刻,使万千感慨借由离别道出,情意言之不尽、吞吐不休。
羁旅行役之苦的印记首先体现为秦观词中所包含的漂泊无依之感。秦词常用“飞絮”“飘萍”“浮云”“落花”等意象来呈现无所依凭的姿态,用“流水”来展现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动不居,人就像水中的落花、飘萍,风中的飞絮、浮云,在命运的洪流中来来回回,却把握不住自己。“池上春归何处?满目落花飞絮。”(《浣溪沙》其五)[2](1)本文所引秦观词皆出自龙榆生《淮海居士长短句》(中华书局1957年版),下文不再另外出注.23“杨花终日空飞舞,奈久长难驻。海潮虽是暂时来,却有个堪凭处。紫府碧云为路,好相将归去。肯如薄幸五更风,不解与花为主。”(《一落索》)薄幸的风将飞絮、落花裹挟,使之四处飘散,无所依靠,倒不如暂时涌起的海潮,不仅来去自由,而且每每前来都有海岸拥抱着它,给它以凭靠。秦观时常借飘萍、落花来自嘲身世沉浮、半生飘零,“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饮罢不妨醉卧,尘劳事、有耳谁听?”(《满庭芳》其二)“流水落花无问处,只有飞云、冉冉来还去。持酒劝云云且住,凭君碍断春归路。”(《蝶恋花》)这些漂泊的事物在秦词中反复出现,它们不再仅仅只是自然界中客观规律的呈现,更成为词人自身的写照。
另一个印记体现在淮海词多有对遗憾、孤独等情绪的描写上。秦观词中“恨”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在少游心中,“恨”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痛苦,他将它比作“春风吹又生”的芳草,“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尽还生”,人在重重“恨”的重压之下,如何还能感受到生活的欢娱呢?所以在词的结尾,词人千般感慨:“怎奈向、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八六子》)再如:“身有恨,恨无穷,星河沉晓空。陇头流水各西东,佳期如梦中。”(《阮郎归》其二)词人心中有“恨”,形体终有一天会随着死亡的来临而消逝,但是心中的“恨”呢?这“恨”却是无穷无尽的、无法逃脱的,又是孤独的、无从寄托的。“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减字木兰花》)颇有温庭筠“千万恨,恨极在天涯”之感,一腔幽怨,极写恨意。
再看他的《木兰花慢》:
过秦淮旷望,迥潇洒、绝纤尘,爱清景风蛩。吟鞭醉帽,时度疏林,秋来政情味淡。更一重烟水一重云,千古行人旧恨,尽应分付今人。
渔村。望断衡门。芦荻浦、雁先闻。对触目凄凉,凋岸蓼,翠减汀萍,高正千嶂黯。便无情到此也销魂。江月知人念远,上楼来照黄昏。
全词情景交融,通过景象的变化来表达情绪的波动,上阕“更一重烟水一重云,千古行人旧恨,尽应分付今人”构思尤为奇特,千古行人已然逝去,但是他们的“旧恨”却没能随之消散,而是分别赋予了今天的人们。时空交织,古往今来的人们隔着时间长河,在“一重烟水一重云”的幻境之中,共享着这份悲哀与遗憾。下阕后半部分赋予江月以人的情感,好像它也看出了游子的乡情,特意爬上高楼来。此情此景,本来无情的江月也为之销魂。
秦观半生漂泊,离愁种种,他借着离愁别绪,“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周济《宋四家词选》)[1]1652在词中寄寓身世的做法早在柳永便已开始实践,柳永的羁旅行役之词,多以情节性取胜,将个人情感在叙事中层层铺排开来,在“如话家常”般的诉说中展现一个个关于离别的故事。秦观部分词作在结构上似乎有意学习柳永慢词的作法,在羁旅行役词的创作上呈现出极强的个人特色,他以小令笔法写慢词,含蓄蕴藉,精巧玲珑。相比于柳永抒情模式的刻露直截,秦观的情感则更为凝练隽永,他的词中并不具体描写离别的始末,而是将满目所见都收进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之中,他所要呈现的是一种瞬时性的凝固的情感,有时像是雾里看花似的,在给人以触动的同时又使人产生一种捉摸不透的困惑。正因为秦词没能像柳词一样,利用记叙和铺陈的方式将心中的愁绪层层舒展开来,反而使情绪向内郁结,似是无端而来,故而无处排遣。
秦观词作受苏轼影响,但苏轼更多地是以诗为词,在词中记录人生轨迹,抒发一腔慨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但苏轼总是能以哲学的思索来消融生命的痛楚,因而其羁旅送别之词往往呈现出旷达的一面。王水照敏锐地指出苏词写别离,对象往往是同志之人;秦观离别词则承继柳词,多写与歌妓之别离。[3]385-390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谓:“少游屡困京洛,故疏荡之风不除。”(王灼《碧鸡漫志》)[1]83苏轼少年意气,怀揣着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秦观却蹉跎青春,与歌儿舞女为伴。因此,苏轼离别词中除了临路之悲外,往往还包含着彼此勉励的意味;而秦观则于细腻深致的抒情中,诉尽个人的孤独与惆怅。
赵惠俊指出词体“儒雅的雅化路径主要由宋代士大夫词人选择与完成,核心任务实际上是将流行歌曲的类型化情感表达转化为士大夫自我个性情感的抒发。”[4]从柳永到欧晏,再到苏轼,士大夫不断将个人情感与理想熔铸于词中,扩大了词的抒情空间。秦观词在保持词体抒情婉转深致的基础上,造语精巧,身世之悲融于离别之痛,情真意切。相比于柳词的故事性和模式化,秦词更显典雅庄重;相比于苏轼词中以议论与理趣自我疏解,秦词则运用词境来凝聚深情。南宋人孙竞《竹坡词序》有言:“昔蔡伯世评近世之词,谓苏东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兼称者,唯秦少游而已。”[5]870所以秦词的怅惘似乎更加无法释怀,这种情感超越于言语所能够表达的范围,在更高也更加虚无的层面上对人们的心灵造成冲击,著名的《梦扬州》便是例证:
晚云收。正柳塘、烟雨初休。燕子未归,恻恻清寒如秋。小栏外,东风软,透绣帷、花蜜香稠。江南远,人何处,鹧鸪啼破春愁。
长记曾陪燕游。酬妙舞清歌,丽锦缠头。殢酒为花,十载因谁淹留。醉鞭拂面归来晚,望翠楼,帘卷金钩。佳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
全词几乎通篇写景物,却凝聚了徘徊幽深的情感。上阕视角由远到近写迷蒙凄清仿佛寒秋一样的春景,再用一句“江南远,人何处”荡开,转到“鹧鸪啼破春愁”,开始书写自己的无限春愁。下阕今昔对比,道出“十载为谁淹留”的苦涩心声。少游往往将个人的身世的悲哀隐藏在词作中,更显出离愁是多么难以忍受。再如这首《江城子》: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秦观以苏门四学士的身份深陷党争漩涡,竟在《元祐党人碑》上名列“余官”之首,仕途坎坷,一生漂泊。当他将身世的感慨、人生的无奈揉进词作时,便成为“古之伤心人”了。该词上阕写离别之愁,回忆故人旧事;下阕首句便是对时间流逝、韶华不待的怅惘与遗憾,春江流水就像词人的眼泪,悠悠迢迢,无尽无休。绵延的春江水又与上阕“人不见,水空流”形成了呼应,上阕是人有情而流水无情,下阕江水却承载着词人的泪与愁,无情之物亦沾染了有情人的泪。
别离本身便易让人动容,秦观词中多以此为题材进行书写。秦观沿着柳永、苏轼等人以词感怀身世的路径,扩展了羁旅行役词的抒情外延,然而他将自己满腔心事寄寓词中,既无人携手泪眼,又不借助哲理来自我宽慰,他总是以有情之眼去观察万事万物,又将种种悲情凝结于词作,情滞于中,无计可消。
二、词境营造:困窘境况与迷惘内心的艺术外化
配合着怅惘的离愁别绪,秦观往往营造出一种隔绝而迷蒙的境界,置身其中,则显出无尽的孤独与悲伤。从表象来看,秦观词中多有阻碍之感,以隔绝之态尽显无路可出的困窘;从内心来看,秦词喜用破碎、迷蒙的意象,营造不清晰的情景环境,透露着无法可解的困惑与迷惘。
(一)被隔绝的外部世界
与陶渊明、林逋等人主动地与世隔绝不同,秦观的与世隔绝是被动的,是完全处在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下,他企图与外面的世界产生联系,却始终无法打破隔断他的壁垒。这种隔绝感首先来自距离上的遥远,秦观一生多次贬谪,使得他的词中多有对“远”“万里”“迢迢”等距离的描写,如:
江南远,人何处?鹧鸪题破春愁。(《梦扬州》)
那堪万里,却寻归路,指阳关孤唱。(《鼓笛慢》)
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浣溪沙》其四)
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阮郎归》其四)
通过展现时空距离,秦观一直把自己置身于“边缘地带”,以一个“望而不得”“寻而未果”的“被放逐者”的身份出现在词作中。距离上的遥远给人以阻隔之感,在秦词中,不停地出现“断”这个词,不仅是在空间距离上,而且在情感关系上。
时空距离上的断,如:“高城望断尘如雾,不见联骖处。”(《虞美人》其一)“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望海潮》其三)“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点绛唇·桃源》)词人利用种种阻碍与隔断,把自己放在一个无人问津也无法向外界寻求倾诉的孤独的世界中。再如《风流子》一词:
东风吹碧草。年华换、行客老沧州。见梅吐旧英,柳摇新绿,恼人春色,还上枝头。寸心乱、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烟两岸,数声横笛,一叶扁舟。
青门同携手。前欢记、浑似梦里扬州。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楼。算天长地久,有时有尽,奈何绵绵,此恨难休。拟待倩人说与,生怕人愁。
该词同样上阕写景,下阕抒情,值得注意的是词中这样的句子:“寸心乱、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楼。”这些词句中,秦观将自己居于中间位置,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全都写到,却无一处是归宿,仿佛四面都是阻隔。《草堂诗余》卷六谓此词:“东西南北,悉为愁场。”[6]5377通过对来自四面八方的阻隔的描写,秦观把自己困住了,身处牢笼一般,无法逃脱。秦词中颇多这样的写法,再如《江城子》其二: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元符三年(1100),东坡量移廉州,六月二十五日过雷州,少游出自作挽词《江城子》。秦观与自己的老师苏轼久别重逢,经历了贬谪之痛的二人此刻百感交集,别后纵有“无限事”,如今两衰翁相对,亦不知从何说起。南来北往鸟儿偶然在途中相逢,短暂的欢聚后又要迎来长久的分别,怎能不令人惆怅!正如奔波在世路上的人们,落花流水分头而去,各自西东,别后的时光最是难熬,再见又不知道会在何处了。这首词的首句“南来飞燕北归鸿”描写相逢,“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描写分别,形成鲜明对比,东南西北,世路无穷,却无归路。秦词将四方都作为“愁场”,可见其伤心之情无处寄托。
相比于时空距离上的隔绝,秦词中还有更深层的情感上的疏远。秦观有许多句子写到了现实与期望的差距,他赋予自然界事物以人的情感特征,利用“差错”式的对立和“不解”式的隔膜,来呈现内心的孤独与怅惘,由此产生情感上的疏远之感。如:“怅佳期、参差难又。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水龙吟》)再如“闷损人,天不管”(《河传》其二),“游蝶困,乳莺啼,怨春春怎知”(《阮郎归》其一)以埋怨似的口吻倾诉着内心的苦闷。
“天不知”“天不管”展现出人的期望与自然规律的种种矛盾冲突,所谓“天行有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心思细腻的秦观更能够感受到天不遂人愿所带来的苦闷,但这不是一个能够用道理来化解的麻烦,命运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毁掉一个人,人却无法反抗。“大自然在各种事物之间没有任何偏好,它以一种完全不偏不倚的方式摧毁着一些事物,又孕育着一些事物,它似乎对自己的任何作品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尊敬’。就像大海冷眼看着自己的一层波浪覆过另一层波浪,却从不试图特别保存其中的任何一层,大自然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生灵的。”[7]上天对待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不公,因而也不会懂得词人心中的苦闷,刻意来怜惜这个沦落天涯的伤心人。这种隔阂相比于时空的界限而言,是词人完全没有办法去克服的。
面对人与自然、与命运之间的种种对立,秦观心中的怨愤呼之欲出,他没有老师苏东坡那样“并物我为一”“浩瀚无涯”的旷达,不可能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这样张扬的句子。他只能退回到那个四面八方都被牢牢封死的玻璃罩子的小小角落里,舔舐着自己的悲伤。秦观的世界往往是物我对立、有所隔阂的,在这样的隔阂之下,或带着愤懑,或带着无奈,或带着不解,秦观在他的词中塑造了一个敏感而困惑的自我形象,他不停地发问:
乱山深处水萦回,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虞美人》其三)
伤怀,增怅望,新欢易失,往事难猜。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满庭芳》其三)
正如花开却无人欣赏,秦观将仕途的不遇、身世的坎坷、人生的无奈全都寄托其中,问花为谁开,便是自问“用舍行藏”。有时情绪积攒到无以复加之时,秦观就不再以草木花鸟为托,而是直接质问自己为谁停留,为谁憔悴:
十载因谁淹留……佳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梦扬州》)
篱枯壁尽因谁做?若说相思,佛也眉儿聚。(《河传》其一)
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画堂春》)
还有最为著名的那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此句直让东坡道出:“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8]《草堂诗余》论此句:“少游坐党籍,安置郴地,谓郴江与山相符,而不能不流,自喻最凄切。”[6]5339问句的使用,使得情感经过或虚或实的种种景物的铺垫、深化,最终爆发出来,成为秦词向外界倾诉的出口。可是,这些问句大多都无法得到回答,词人也并不渴望得到回应,这只不过是秦观迷茫而痛苦内心的一种显现。苦苦追问意义的背后,是怀才不遇所带来的种种关于人生的怀疑与对现实的绝望。因为距离和情感上的阻隔,加之无法被理解的痛楚,秦观只能局限于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中,发出没有回答的问题。他试图用“难”去分析这种隔阂,用“不见”和“空”来回避着这个无法解决的困惑,于是他的词中便多有这类令人感到无奈和疏远的句子,提到“难”的句子,如:
任青天碧海,一枝难遇,占取春色。(《雨中花》)
勤勤裁尺素,奈双鱼、难渡瓜洲。(《长相思》)
楚台魂断晓云飞,幽欢难再期。(《醉桃源》)
又有多处提到“不见”“空”的表达,如:
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江城子》其一)
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千秋岁》)
《阮郎归》其四是将时空的隔绝和情感的隔绝结合得尤为精彩的一篇:
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
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天色渐晚,庭院深沉而又空虚,高楼之上,《小单于》的曲子吹罢,只有清夜远远消逝而去。年岁在羁旅和相思中增长,衡阳尚有传书的鸿雁,郴阳却无雁来和。上阕写景,已然营造出辽阔而凄清的氛围,在寂寥的背景之下,词人是那样的渺小,个人的情感始终熬不过岁月的冲刷。孤独和思念在寂静的夜色中被无限拉长、深化,至下阕起首二句,情感积攒到极点,但没有猛地爆发出来,只是轻轻流泻,其中无曲折幽怨,却在结尾两句,荡开一笔。南来北往的鸿雁,本是乡思的寄托,此时却也不见踪影,想见郴阳之遥远。“郴阳和雁无”一句,将词人禁锢在一个封闭、边缘而又寥廓的环境中,断绝了他和外界全部的联系,甚至连他情感的小小寄托也一并没收,只留下苍茫天地间的无比孤寂渺小的身影。“无”一字作结,更是将这种寂寞感蔓延到整个时空之中,与上阕“虚”字遥相呼应,人生在世永远是孤独相伴,眼前所见、耳畔所闻,一切都只是虚无,亘古不灭的虚无。
(二)朦胧破碎的内部世界
秦词利用“远”和“断”造成了一个与周边形成阻隔的空间,这个空间偏僻、遥远、空旷寂寥、无人问津,同时,这个空间的内部又是无限阔大和深邃的,它以朦胧、恍惚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颇具美感,而这,正是秦观复杂敏感内心的体现。
这种迷蒙之感首先由“烟”“霭”“云”“柳絮”等具有迷蒙属性的意象造成的。这些事物本身就带有一种缭绕遮蔽的性质,它们虽然没有阻隔观察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却使得人们无法准确清晰地把握所关注的事物,由此产生种种奇妙的联想。
在秦观词中,这些意象或被置于词作的起首,借助这种“看不清”的效果,渲染出亦真亦幻的景象,为展开词人怅惘多情的内心作铺垫。如“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踏莎行》),“宿霭迷空,腻云笼日,画景渐长”(《沁园春》),有时这些意象也被置于全词的结尾,将情感散在迷蒙的景色之中,产生余音绕梁、挥之不去的效果,如:“巷入垂杨,画桥南北翠烟中。”(《望海潮》其一)纵观淮海词,对“烟”“雨”等词的使用比比皆是,而且常常配合着带有昏暗、残破、荒凉之感的修饰词一起使用,如:“那堪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八六子》)“斜日半山,瞑烟两岸;数声横笛,一叶扁舟。”(《风流子》)“烟瞑酒旗斜。”(《望海潮》其三)等等。
此外,秦词中还多用凌乱琐碎的意象来强化迷蒙的意境。残碎散乱的事物在视觉上产生模糊感,将本来完整真实的景象碎化虚化,由此造成如梦似幻的景象。秦观喜用“乱” “碎”“点”等词语来进行修饰,这些修饰词常常和“花”“草”“絮”“云”等轻柔之物组合,在凌乱琐碎的同时,给人以美感。如“但乱云流水,萦带离宫”(《望海潮》其一),“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望海潮》其三),“乱花丛里曾携手,穷艳景,迷欢赏”(《鼓笛慢》)等,“乱云”“乱花”甚至“乱分春色”都将画面变得模糊不清,而在这画面中发生的一切都变得有些缺乏真实感,不知是回忆还是梦境。
这种迷乱的景象,常常令词人感到困惑和愁苦,如:“碧水惊秋,黄云凝暮,败叶零乱空阶。”(《满庭芳》其三)“乱花飞絮,又望空斗合,离人愁苦。”(《河传》其一)“花影乱,莺声碎……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秦观善于在词中使用“点”化的意象,“点”的出现,使得一段愁变成了千点万点的愁,人可以排遣掉一段愁绪,这漫天的如飞红般的愁,要如何排遣呢?何况这千点万点的“愁”还迷住了人们的眼睛,让人看不清眼前的事物,更看不透自己内心的想法,因为看不清,所以困惑;因为困惑,便想要寻找一个答案;答案的不可得,便带来了忧愁;忧愁慢慢积攒,便成了“伤心”。模糊的景致代表着词人内心的迷茫,尽管词人尝试以各种方式来寻求解脱,渴望借助佛道等途径来消解痛楚,但似乎都无法真正走出伤心的世界。
“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冯煦《蒿庵论词》)[1]3587无论是写与外部世界的隔绝,还是展现内部世界的迷蒙,都可以看作是词人心绪的艺术外化。秦观把自己的内心情感进行加工,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他的伤心之情引起读者的共鸣。
三、身份认同:贬谪文学与逐臣心态的别有怀抱
由于仕途的坎坷,秦观的词可谓一部“罪”的文学,处处可见贬谪之痛留下的印记。这种深刻的烙印,是一种隐藏在性格深处的“罪人意识”,使得其词不断呈现出被放逐、被隔绝的感情。
在宋代士人身上,这种“罪人意识”多有体现,苏轼尤为明显。苏轼因诗获罪,在很长的时间里,他都对写诗保持一种“避祸”的态度,甚至在写给友人的信笺中嘱咐收信方“勿以示人”。[9]“罪人意识”在秦观词中也有所体现,而且几乎与他的贬谪之痛相生相辅,成为其词作重要的内容。尽管秦词中并未直接提及“罪”,也没有像苏轼那样屡次提到“不言”“咂舌”,但是,秦观在词作中设置了一间牢笼,死死地把自己关在里面。这间牢笼的设置是通过一个被放逐、被隔绝的词人的自我形象塑造来完成的。秦观常常把自己置于边缘化的境地,通过距离的遥远和不被重视来强化“放逐”感,如著名的《满庭芳》其一: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词则·大雅集》卷二谈及此词时说:“诗情画景,情词双绝。此词之作,其在坐贬后乎?”[10]起首三句便已勾勒出一幅苍茫而寂寥的景象,结尾三句又远远荡开,无论是寒鸦还是灯火,全词都以一个“望”的视角来构图,可见距离之遥远。蓬莱旧事回首已成烟霭纷纷,十年扬州也只赢得薄幸之名,岁月之蹉跎、人生之虚度跃然纸上。秦观将自己的生平经历看成虚无的存在,既是自嘲,也体现出他怀才不遇的悲哀。沈际飞评价此词:“人之情,至少游而极。结句‘已’字,情波几叠。”[6]5358全词上下阕出现“断”“空”各一次,利用距离的遥远和生活的无意义反映出“逐臣”的落寞心态。
前文已论述,秦观时常在词中营造出一种阻隔之感,这种阻隔不仅仅来自空间上的距离遥远,更源于情感上的种种疏离。如《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上阕只用“失”“迷”“断”“孤”“闭”等词就将空间上的隔绝之感呈现出来,下阕则用一个问句强化了情感上的隔绝,如是,秦观就将自己困在了牢笼之中。还有一首词也很能体现这种隔绝之感:“恰似小园桃与李,虽同处,不同枝。”(《江城子》其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亲近,就像一个小园子里的桃花和李花,在春天一同绽放;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那么遥远,桃花与李花虽然开在一处,却在不同的枝头,他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彼此,即使身在人群中,却好像还是有一间密不透风的牢笼把自己困住,这便是秦观身上无可逃脱的“罪人意识”,他感到自己并不是天地中自由不羁的存在,而是被命运的枷锁牢牢困在监狱里的囚徒,他被放逐、被关押,因而他永远只能是“望断”,只能是“和雁无”。
其实这种“牢笼”式的封闭环境的塑造,早在唐人的贬谪之作中便已出现。柳宗元《囚山赋》:“攒林麓以为丛兮,虎豹咆代狴牢之吠嗥。”[11]171这篇赋文通篇写景,通过描写永州山水之险恶,野兽之令人惊怖,来凸显所处环境之恶劣,从而将永州比作一个巨大而恐怖的囚笼。在任永州司马期间,柳宗元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被囚”的状态,如“罹摈斥以窘束兮,余惟梦之为归”(《梦归赋》)[11]160,不仅被“摈斥”,而且还“窘束”不得自由,只能于梦中归去。又如“余囚楚越之交极兮,邈离绝乎中原”(《闵生赋》)[11]152,“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轗轲”(《惩咎赋》)[11]139,将自己谪居之地径直视作牢笼,身居此处便是被“囚”。这一被“囚”的形象是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特殊贡献,它代表了中唐贬谪文化下的士人们的典型心境。《旧唐书》本传记载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即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12]。通过骚体赋的创作,柳宗元将贞元、元和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和中唐士人贬谪心境的不同侧面展现出来,丰富了“士不遇”文学母题的发展,也促进了骚体赋在中唐的复兴。
秦观并未在词中直写贬谪之地环境之恶劣,也没有强调自己被“囚”的“罪人”心态,但他的词总是充满阻隔感,他动情地观察着世界,精心描绘着四方景物,起笔却是“八面愁来”,塑造了被驱逐、被隔绝的孤独形象,无处可逃,也无法可解。
在宋人的政治生活中,“贬谪”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苏轼的诗词中便多有对贬谪的描写,如《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3]2641苏轼早年因诗获罪,对于自己的言行一直十分谨慎,他的诗中多次自言为诗文所累,如“吾穷本坐诗,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闭口洗残债”(《孙莘老寄墨四首》)[13]1322,“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其二)[13]1006,尽管他曾落魄畏惧至此:“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14]391但在贬滴中能保持旷达乐观的态度。“苏轼进行诗文创作外还耽于学术研究,在人生晚年以著述为乐”[15]76,他在诗词中寻求各方思想的慰藉,将自己视作“痴儿”“老翁”反复自嘲,甚至在困境中完成了《易传》《书传》和《论语说》三部学术著作,一边漂泊失意,一边试图以这种方式来自我消解。
面对贬谪之痛,柳宗元选择了骚体赋,远追屈贾,感慨士之不遇;苏轼以诗词为慰藉,超脱人生的苦难;秦观则将自己封入词中,抒发“伤心人”的怀抱。就词体而言,秦观以其“伤心”大量创作贬谪词,扩大了词的抒情境界,在词史上有着主要价值。他的《千秋岁》曾引起了苏门师友的共鸣,先后有七位词人和作。这一组词不仅可以窥见元祐党人的贬谪心态,也因其绵延两宋的写作和唱和活动成为宋代贬谪词创作的高峰: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千秋岁》)
秦观此词回忆往昔,感慨身世漂泊,故人不见,年华蹉跎,结句“飞红万点愁如海”极写忧愁之深,无计可消。在和词中,孔平仲虽同少游一样一吐愁绪,但结句“仙山杳杳空云海”似以游归仙山来获得精神上的安慰。黄庭坚以同门之谊慨叹少游之逝世,“人已去,词空在”“波涛万顷珠沉海”,重在怀念少游,抒发斯人已去的悲伤。老师苏轼并不沉溺于贬谪之痛,并在和词中给予勉励:“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以示初心不改,实现对苦难的超越。和词涉及元祐党人如何自处的问题,展示着他们以何种方式来消化贬谪之痛。如果说苏轼词呈现出个人与命运抗争时超脱的那一面,那么秦观则更多展现出个体生命在遭受时代碾压时的痛苦与挣扎,那是最真实的、不加任何缓释的痛感。
冯煦概括秦观的生平遭际及创作风格曰: “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 后主而后,一人而已。”[1]3586在宋代词体雅化的道路上,当苏轼已经开始用词书写阔大宇宙与人生,当黄庭坚已将词作的视野扩展到日常生活,秦观仍然保持着词婉约传统的本色当行,伤心之至,字字泣血。他没有慰藉,不加掩饰,直击疼痛本身,记录着贬谪语境下的被驱逐的个人的际遇,为元祐党争之祸留下了痛苦的记录。面对命运的捉弄,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老师苏轼一样“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更多的是像秦观这样失望与希望交织、囿于现实的困境中无法逃脱。秦观的“伤心”在词中找到了归宿,词体之“要眇宜修”也因秦观深婉的诉说而尽显美感。
古人说少游是“古之伤心人也”就秦观现存的词作来看,充斥着感伤与惆怅,几乎无一首不“伤心”。他融身世之悲于离别之情,兼取柳苏之长,深化了词写羁旅行役、抒发生平感慨的写作路径。他营造着隔绝而迷蒙的孤独境界,哭诉着无路可逃又无法可解的伤心。他将满腔幽愤凝结在词作之中,以个人的记忆与真实的疼痛,为古今命途多舛遭逢不偶的士人们留下了沉痛的一笔,扩展了词体抒写“士不遇”主题的维度。
贬谪、离别,终其一生,秦观都处在被放逐、被隔绝的状态,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生的困惑,却无人能为他解答,“伤心”成为他情感的最终归宿。他曾说:“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阮郎归》其三)秦观的伤心较之别人更加敏感、更加细腻。当他词风一改往常,写出《好事近·梦中作》时,他生命中那些不能释然的痛苦,也便随着生命的消逝而散去了:
春雨路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
飞云当面化龙蛇,矢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
《古今词统》卷五谓“少游此词如鬼如仙,固宜不久。”[6]4308《宋四家词选》也说:“概括一生,结语遂作藤州之谶。造语奇警,不似少游寻常手笔。”(周济《宋四家词选 》)[1]1653这首词恬静、闲适,描绘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再也没有秦词之前出现的种种隔绝与朦胧,甚至也察觉不出丝毫的情感,这是一个清晰的明亮的世界,是对一个千古伤心人的终极关怀。当“伤心人”的词中不再困惑、不再追问、不再流露过多情感,秦观终于还是走出了那个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