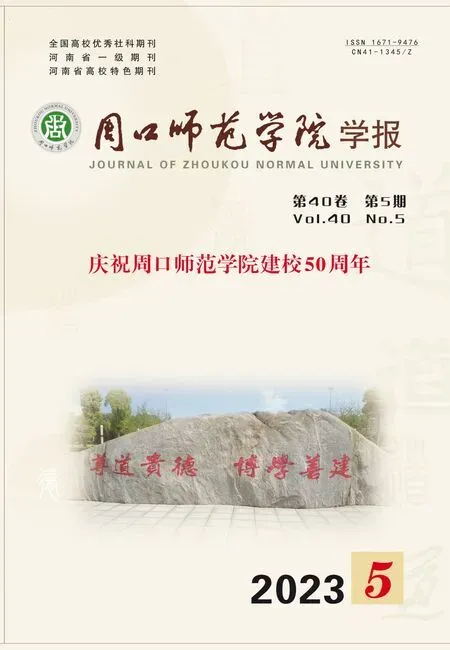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多元价值诉求
陆相欣,李 亚,顾拓宇
(1.周口师范学院 教务处;2.周口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1.6%,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将意味着入学机会的增多、授课形式的多样、学生就学形态的多样、教育机构的多样、办学类型的多样[1]等,单一的高等教育标准将无法满足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需求,多元价值取向将是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时代特征。
1 自由,人性的源初诉求
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程度将进一步扩大。随着高等教育类型、教育层次、系统的多样化,灵活性、开放性办学将是未来的一大趋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不可能再进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通过引导的方式使用公共资金,通过资源配置的方式间接管理将更有利于适应普及化的趋势。
学生和教师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多样化的学生和教师需求将更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学生在不同类型院校间可以自由流动,可以自由的选择课程和授课方式,学生推迟就学时间或“进进出出”现象都将成为常态[2]72-74。在美国加州,12.5%的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加入加州大学学习,是高度选择性的教育;前33%的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加州州立学院,是选择性的高等教育;前50%的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社区学院学习,是非选择性的[2]68-69。社区学院的学生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加州州立学院学习,加州州立学院的学生也可以进入加州大学学习,合格者可以授予相应学士学位。不同类型学校的教师可以自由的流动。 日本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为代表的选拔型的高等教育,也有四年以上的竞争型大学和不足二年的免试型短期大学[3]。
在我国,受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的影响,不同类型间的学生流动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国严把入学关口,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按照统一的试卷标准筛选不同类型学生,这就限制了学生对不同类型大学需要的诉求,而普及化的特点是学生的自由选择,通过多样化的选择方式、去标准化,通过严把出口关而非入口关才能解决学生自由选择问题。
教师的自由流动也是普及化的诉求。随着高水平人才的增多,不同类型院校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传统型从工作到退休终守一个单位组织的时代将成为历史,不同类型院校间教师流动加强,甚至国际间教师的流动也将成为常态。近几年来,很多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人才的流动现象更加频繁,这也体现了普及化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
2 忠诚,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学生自由选择授课类型或教育形态、教师可以自由的流动虽已成为普及化社会的主要特点,但对国家的忠诚、对社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仍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价值意蕴。
在人才培养方面,研究型大学要培养忠诚于国家的研究型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永恒的主题。再优秀的个体,一旦失去了对国家的忠诚、对民族的热爱,终将成为危害社会的败类、危及民族的劣质。应用型大学要培养忠诚于国家的大国工匠,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工匠精神,培养忠诚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性人才;职业类院校要培养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技能型人才和现场管理人才,可以直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生产力的技能型人才。
在科学研究领域,我国核心技术在世界占有率还很低,我国计算机系统的国产芯片不足22%,内存设备的芯片占有率不足5%,全球Top10芯片70%为美国所垄断[4]。这就需要一批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中华民族的科技创新人才为国家打开创新之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高层次的拔尖创新型人才、高级应用型人才,也需要服务于一线的技术工人。
韦伯提出“以学术为志业”体现了对学术的忠诚,我国药学家屠呦呦不牺以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研制出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在生命科学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不仅体现了对社会的忠诚,更体现了对学术的忠诚,对自身信仰的一种坚守。通过科学研究服务于国家需要就是科学家对国家忠诚的最好诠释。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建立更好的诠释了科学研究对国家的忠诚,柏林大学在40年内几乎囊括了当时40%的诺贝尔奖,使德国成为19世纪经济、文化等领域最强大的国家,柏林大学也因此成为世界大学的典范。
3 平等,每个平民的权利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限制于少数学术精英,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是属于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当一些人被允许做另一些人不能做的事,或不要求人做一些人必须做的事的时候,就有特权存在。一些人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而另一些人则不能获得高等教育时便是如此。
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产品将成为每个平民的权利。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要让大多数学生可以适应高度产业化的社会。衡量学生水平的尺度不应仅仅满足于优秀者,而应更多的朝向社会大众。每个平民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不再是优秀者的特权。马丁特罗(Martin Trow)认为普及(Universal)之意不是指“万人入学”,而是指“万人机会”,而且是“万人参与”。言中之意即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参与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就不再局限于仅仅指18-22周岁的适龄群体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社会成员中的每一个体(不再受制于年龄)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一目标我国已经实现,但这一实现也仅仅是拥有参加高考的机会,也就是说,只有通过高等教育资格考试者才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以直接进入高等院校。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万人参与”。
虽然近些年我国扩大了招生规模,但离实现“万人参与”的高等教育还有很大的距离。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主要承担者是地方院校,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院校依然保持着精英型教育方式。地方院校虽然承担着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也增加了普通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并没有因此享受到与重点院校同等的高等教育投入,这也是地方院校多次呼吁的平等权利。
4 优秀,大学永恒的追求
自由的学术探求没有国界,从柏拉图讲学的阿卡德米(Academy)到亚里士多德讲学的利塞姆,以及中国孔子讲学的黄金时代,都蕴育了优秀者对学术的不懈追求。中国有着长达300年的学术繁荣史,中世纪欧洲大陆的大学、16世纪和17世纪英格兰的大学、18世纪乌普照萨拉大学,以及19世纪德国的柏林大学[5],以一种对高深学问的探索成为永恒的主题。
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但并不意味着以优秀为主导的精英型高等教育就失去光彩。精英型高等教育将与大众型高等教育共同存在和发展。在大众化或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为多数人服务;精英化时代,高等教育则为少数人服务。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不仅为普通民众服务,还依然为少数优秀者服务,奥谢认为,阻止一个在智力或体力上属于强者的人取得凭天赋能力所能取得的成绩,其不公正、不民主和犯罪的程度正如阻碍一个弱者在与同伴竞争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一样[6]73。罗尔斯认为,在教育上的不平等是公正的。平等不是平均主义,我们不能因为关注平等而忽视了天才,我们必须在一个关心全体人民的背景下寻找天才。以期使每个人的特殊才能得以最充分的培养[6]74。
《2017全球创新指数GII》《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显示,中国在芯片、软件、医学技术、发动机、新材料、机器人等关键技术领域全面落后于发达国家[7]。截至2017年12月,我国高校授权专利14.4万项,专利出售4803项,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获得4万件专利授权,出售1407件,技术转移率不足5%[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2017)。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还没有掌握主动权,对技术创新的需要、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仍是我国的当务之急。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对优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以精英为主导的高等教育仍是普及化时代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