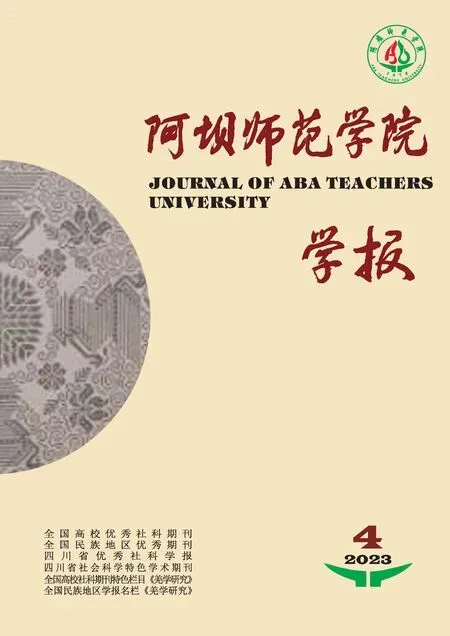《呼啸山庄》的现代性之思
刘洋风
《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是英国小说史上最为神秘、最受关注的小说之一。该小说与现代性的密切关系一直被研究者所注意。不过,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现代性的界定大为不同。现代性也形成于一个漫长的时期,绝非在某一个节点一蹴而就,也不是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着同样的价值取向。马泰·卡林内斯库提出存在着两种现代性,一种是资产阶级现代性,延续着启蒙观念,相信进步,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崇拜理性;还有一种是审美现代性,公开拒斥资产阶级现代性,具有强烈的否定激情。①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1 -438.尽管现代性概念有所差别,但有一点是共识,那就是现代性与宗教衰落有着紧密联系。“按照一种相当通行的想法,现代性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彼岸的圣经信仰已经彻底此岸化了。简单不过地说,不再希望天堂生活,而是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上建立天堂。”②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M]/ /刘小枫.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3.《呼啸山庄》恰恰演绎了现代性进程,展示了现代性内在思潮。
一、现代性缘起
《呼啸山庄》故事的起点是老恩肖从利物浦带回并收养了希茨克利夫。收养孤儿这一行为在19 世纪英国小说中并不少见。《爱玛》中简·费尔法克斯小姐被父亲的朋友坎贝尔上校收养,《简·爱》中里德舅舅收养了孤女简·爱,罗切斯特收养阿黛勒,《雾都孤儿》主人公奥利弗·推斯特被收养,《远大前程》中父母双亡的皮普被姐姐姐夫收养。收养孤儿,是出于仁慈之心,也多少有点被动性质,是因为亲戚、朋友等关系而承担的半义务,是经过了理性的权衡。奥斯丁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托马斯爵士作为一个深明事理的家长,将穷亲戚家的女孩芬妮接到自家抚养时,全面考虑过相关问题。他担忧如何让同一个屋檐下的芬妮接受她和表姐们的地位差别,芬妮的财产和前途远不如表姐们。他担心长大后的芬妮会和自己的儿子相爱,进而让儿子缔结地位不匹配的婚姻。《爱玛》中简·费尔法克斯被收养也经过类似的权衡。托马斯爵士、坎贝尔上校抚养孩子经过深思熟虑,而且考虑到了养子女和亲生子女的差别,既有地位的差别,也有爱的差别。狄更斯小说中奥利弗·推斯特的被收养实质上也经历了道德的考验。《简·爱》中里德舅舅收养简是出于对妹妹的同胞之爱,罗切斯特收养阿黛勒是因为阿黛勒疑似他私生女,是迫不得已的慈善行为。与这些收养相比,老庄主收养希茨克利夫则明显不同。他是在利物浦街头看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孩子并不是被别人托付或者自行跟上的,而是老庄主看到这个孩子后主动捡起来。这孩子浑身脏兮兮,衣服破烂,可能已经流浪有一段时间了,孩子的来历完全不清楚。这种收养在常人眼中是非理性的,他的妻子恩肖太太勃然大怒,怀疑他疯了。
这种不太符合常理的收养动机何在?有些研究者认为收养是对他夭折的次子的替代性移情的心理,老恩肖给孩子取名希茨克利夫,这本来是他们那个很小就死了的儿子的名字。也有评论者认为,“他完全是出于博大的人道主义的胸怀给这个可怜的孩子以爱”①曾岚.论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中对人类社会公正问题的思考[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42.。事实上,老恩肖自己的话可能更具有说服力:“我这辈子也没有给什么东西弄得这样狼狈,可是你还真得把这看作是上帝的馈赠,尽管黝黑黝黑像是从魔鬼那儿来的一样。”②勃朗特.呼啸山庄[M].张玲,张扬,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39.这个孩子作为上帝馈赠的礼物,在他心中具备宗教象征性。
上帝的礼物在基督教神学中是具有特殊的指向。《圣经》记载,上帝创造亚当,又创造了夏娃。夏娃听从魔鬼的诱惑,吃下了让人能辨别善恶的果实,并让亚当也吃了。事后,上帝问罪,亚当辩称是上帝赐予他的女人让他吃的果实,夏娃正是上帝赐给人类始祖的礼物。作为上帝的礼物,夏娃让人类从此具备了明辨是非的理性,也背负着原罪,永远离开了伊甸园。上帝的礼物蕴含了上帝权威与人的自由意志的矛盾,也蕴含着基督教信仰与理性、非理性的复杂关系。对这个故事的阐释,神学家奥古斯丁的原罪说影响最为深远。按照奥古斯丁的解释,“自由意志本身是一种(中等的)善,它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③卢毅.“无意之罪”何以归责?——哲学与精神分析论域下的“无意识意愿”及其伦理意蕴[J].哲学研究,2020,(1):90.,它使人摆脱了动物性生存状态,但是人滥用自由意志,违背了上帝的禁令,犯下原罪。此后,人类就不能凭借自由意志做出正确的判断,唯有信靠上帝。这种解释实际上是对理性的压制,承认理性的局限性,放弃理性,顺从信仰,才能真正接近上帝。但奥古斯丁用逻辑来证明上帝的礼物、堕落和惩罚的合理性,有别于格里高利一世、德尔图良等神学家提出的“无知而虔诚”“因荒谬而信仰”等观点,这正是对理性的认同和寻求。奥古斯丁的诠释体现了绝对信仰之非理性精神和希腊式的理性精神的冲突。就基督教而言,上帝的启示与恩典、圣灵的感动等带有神秘性的个人主观体验,本质上来说都是非理性因素。但这种非理性要借助理性的表达和标准。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壮大,人类的理性提升到越来越高的地位。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提出的“因信称义”,肯定了人的独立判断能力。笛卡尔的主体主义哲学则用形而上学的论证将上帝变成一个逻辑推理的对象,“也就是说,无论认识者内在的品性如何,这都不妨碍认识者能够通过理性能力而达到对上帝的认识和直观”④陶杨华.亚伯拉罕的上帝与笛卡尔的上帝:关于“上帝之死”的思考[J].世界宗教研究,2013.(3):147.。理性地位的提升,让人类从宗教权威中获得解放,“人自身内在的理性取代上帝的恩典,成了人的存在的终极依据和最后的慰藉”⑤陶杨华.亚伯拉罕的上帝与笛卡尔的上帝:关于“上帝之死”的思考:148.。这就开启了现代性进程。“在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时期趋近尾声之时,现代性的概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先前的中立性。它同宗教的冲突最终变得公开,做现代人差不多就是做一个‘自由思想者’”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M]/ /刘小枫.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62.。
老恩肖的家庭就演绎了这一进程。老恩肖出自非理性的宗教热情收养了希茨克利夫,这一热情依靠父权制的家长权威和仆人约瑟夫的宗教统治得以延续。约瑟夫是这个家庭的宗教领袖。“他对社会上层灵魂福祉的关心,他对魔鬼危险的警告,他对祷告和宗教事务的监督,他对孩子们的训诫——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宗教领袖的典型例子。”⑦G Tytler.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Wuthering Heights[J]. Brontë Studies,2007,(1):42.约瑟夫看似虔诚,实则专横自私。老恩肖做家长时,约瑟夫一味数落辛德雷、凯瑟琳。辛德雷做家长的时候,约瑟夫对凯瑟琳和希茨克利夫也是只有说教和惩罚。在这样的教育下,体制宗教甚至上帝的威信逐渐消减,反抗情绪日益滋长。老恩肖的整个家庭没有因信仰获得宁静和喜悦,反而滋生着无穷怨恨。信仰不再能回答人的生活意义的问题,不再能赋予人生价值,只带来了体制宗教的压迫。
在这个家庭里,凯瑟琳与希茨克利夫对此最为敏感。在等级森严的基督教父权制度下,凯瑟琳是女性,希茨克利夫是没有姓氏的孤儿,都处于体系的边缘位置。老恩肖做家长时,他们彼此依存。辛德雷做家长后,剥夺了希茨克利夫受教育的权利,对他们两人不闻不问。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却也游离于社会体系之外,这一冷酷的现实直到他们误入画眉田庄后才发觉。凯瑟琳和希茨克利夫发现画眉田庄时惊呼简直是天堂。画眉田庄是理性化体制化的天堂,在这一体系中,希茨克利夫根本不配到一个体面人家去,他成为一个“看不见的人”。而凯瑟琳则撕成了两半,一半作为恩肖家的小姐留在体系中,一半与希茨克利夫一样被驱逐。希茨克利夫和凯瑟琳的“我们”被分裂了。凯瑟琳无能为力,希茨克利夫只能隐忍。他们的怨恨与日俱增,这虽然是一种负面的情感体验,但能升华成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力量,他们的自我觉醒也随之而来。“一切不向外在倾泻的本能都转向内在——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的内在化;于是,在人的身上滋生了后来被称为人的灵魂的东西。”①尼采.论道德的谱系[M].谢地坤,宋祖良,刘桂环,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61.怨恨会产生个体心灵的觉醒,会进行价值重估。
不仅老恩肖家如此,作者还借洛克伍德的梦暗示社会也是如此。教堂里牧师宣讲布道文中的“七十个七次”是关于宽恕的经文,内容却是揭穿罪行、逐出教门的审判。布道的杰伯·布兰德亨和听讲的信众起先囿于牧师和信徒的身份勉强忍耐,最终不可避免地爆发为一场混战。从牧师到信众,人人都认为别人有罪,人人都在怨恨他人。人类逐渐撇开上帝,寻找新的精神皈依和终极慰藉,这是上帝之死的景象,也是现代性缘起。
二、现代性的内在浪潮
凯瑟琳和希茨克利夫在怨恨驱动下寻找新的价值支撑点,把认同的问题从上帝转向人自身。他们都转向世俗化道路。凯瑟琳答应嫁给有钱又体面的埃德加,打算借助丈夫的地位,摆脱哥哥的影响,提升希茨克利夫的社会地位。这是一条世俗化道路。但这条道路对于凯瑟琳行不通,希茨克利夫愤而出走,即使他没有出走,埃德加也不可能如凯瑟琳所愿。希茨克利夫出走数年后归来,埃德加同意他们保持来往。凯瑟琳也以她那番浓情蜜意给他以回报,不过凯瑟琳的幻想很快遭到了打击。希茨克利夫意图勾引埃德加的妹妹伊丽莎白后,埃德加和希茨克利夫彻底决裂。凯瑟琳发现自己的努力招来的是他俩的怨恨。凯瑟琳绝食三天,她发现画眉田庄成了牢笼。其实,呼啸山庄、画眉田庄就内在权力结构来说,对凯瑟琳并没有什么区别。凯瑟琳生前反对将自己葬在林顿家族的墓地,可是在洛克伍德的梦中她的幽灵依然以凯瑟琳·林顿的身份徘徊在呼啸山庄的窗外。作为一个女性,在父权社会,凯瑟琳是被规定被约束的第二性,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都没有她的位置。
希茨克利夫作为男性,他的世俗化道路更为直接,他改变自身的生存条件,获得新的社会地位,承担新的社会角色。在听到如果凯瑟琳嫁给希茨克利夫,就会贬低身份的谈话后,他离家出走。三年后,接受了教育,积累了财富的希茨克利夫重新回到了呼啸山庄,举止很有气派,他通过赌博等手段逐渐占有辛德雷的财产。他勾引伊丽莎白,打算通过婚姻和财产继承逐渐占有画眉田庄的不动产。不断积累的财富和不断提高的社会地位成了希茨克利夫的世俗化的自我。
希茨克利夫的世俗化道路是成功的,可也没有完全成功,因为恋人的死亡和儿子小希茨克利夫的死去不同程度地冲击着他的世俗化道路。小希茨克利夫是作为工具诞生的。他父母亲的结合是出于希茨克利夫的怨恨和财富扩充的需要。伊丽莎白不堪虐待逃走后,独自生下并抚养小希茨克利夫,这个孩子继承了林顿家孱弱的身体,长年生病。伊丽莎白去世后,小希茨克利夫由希茨克利夫抚养。希茨克利夫有意纵容这个孩子的自我中心和培养阶级优越感,为他请教师,让下人要尊重这孩子。这种工具性吞噬了他的自我。正如他渴望的天堂是在炎热的七月,在原野的中间,从早到晚躺着,阳光耀眼,天空湛蓝,万物都沉浸在陶然忘我的平静之中,这是一个理性的天堂。这种工具理性“不可挽回地被其自身消耗殆尽,自我的自主性、自由性和真理性不再能以自我意识的主观性为基础”①王振林.现代性哲学视域[N].光明日报,2008 -12 -23.。小希茨克利夫身体逐渐衰弱,人也越加自私。他被父亲逼迫着成为软禁、欺骗小凯蒂的帮凶,画眉田庄的全部产业通过欺骗和暴力的婚姻完全转移给小希茨克利夫。小希茨克利夫的死亡让父亲希茨克利夫借此获得了全部财产,同时也意味着这财富和姓氏无人传承,宣告着借助世俗财富进行自我建构的失败。
凯瑟琳的女儿小凯蒂、辛德雷的儿子哈里顿同样面临着自我建构的需求,寻找自己的价值支撑点。小凯蒂在父亲埃德加和女管家丁耐莉构建的秩序下长大。埃德加辞去种种社会职务,连教堂也不去,过起了隐居生活,他对女儿充满慈爱,教育也极其精心。小凯蒂被束缚在画眉田庄的小世界里,接受了正统的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天使的教育,也继承了母亲的热情。她对小希茨克利夫描述过自己的天堂。她渴望整个世界纵情于欢乐之中,万物灿烂夺目,在壮丽辉煌的气氛中狂欢。这种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纵情狂欢俨然是尼采所描述的酒神精神,充满着非理性的激情。被骗婚被软禁的小凯蒂并没有被怨恨吞没,小希茨克利夫活着的时候她尽一切力量照顾他,小希茨克利夫死后她逐渐与辛德雷的儿子哈里顿相爱。评论普遍将哈里顿和小凯蒂的结合看作是希茨克利夫和凯瑟琳的修正版,用他们的幸福结合来弥补上一代人的遗憾。不过,不应该忽略其他的可能。毕竟,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的联姻并没有幸福的先例。小凯瑟琳描述的天堂包含的非理性激情表明,她继承自母亲的激情,绝非仅仅是父亲教导出的温柔淑女。她和哈里顿的婚姻依然可能走向悲剧。哈里顿通过婚姻获取知识、财富和地位,通过理性和世俗身份进行自我建构,而小凯蒂则释放内在的激情走向积极虚无主义。
《呼啸山庄》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非常明显,凯瑟琳、希茨克利夫的人生悲剧否定了技术化、理性化以及中产阶级价值观,呈现出审美现代性那种否定的激情。按照施特劳斯的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划分来看,《呼啸山庄》所体现的正是与尼采相关的第三次浪潮,“构成它的是一种对生存情绪的崭新理解:这个情绪更多的是对恐惧与灼痛而非和谐与平静的体验,并且它也是(作为必然的悲剧性生存的)历史性生存之情绪”②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M]/ /刘小枫.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43.。这种激情不同于卢梭开启的现代性第二次浪潮。《呼啸山庄》的自然风景并不安宁,不具备救赎能力,儿童和成人一样充满了暴力和残酷,明显有别于浪漫主义理想化审美化的自然话语。这种恐惧与灼痛来源于对历史和人性的悲观,而对历史的进步性、合理性怀有的希望是毫无根基的,对人性也不抱希望。小说最后,希茨克利夫绝食而死,有人看见他和凯瑟琳的幽灵在荒野漫步,这表明了他们的爱情在人间难以实现,如同生命走向终点的凯瑟琳所期盼的“我会远远超过你们,高过你们,没人能比”③勃朗特.呼啸山庄:170.的彼岸世界一样,具有非现实性。凯瑟琳和希茨克利夫的爱情指向了一种类似尼采所说,是积极虚无主义的存在。他们精神之力超越当时一般人的追求,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力不够强的象征,从创造性方面来讲,不足以再次设定目的和信仰这样的问题,提出为什么”④尼采.权力意志与永恒轮回[M].沃尔法特,编.虞龙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209.。正如尼采在否定旧人的同时也寄希望于未来的超人,否定旧理想的同时,也重估一切价值,艾米莉·勃朗特借助在荒野中漫步的小凯蒂和哈里顿留下了微弱迷惘的希望。
三、现代性的困境
西方的现代性从诞生到发展都与基督教紧密联系。教会腐败,教派纷争冲突不断,体制宗教甚至上帝的威信逐渐消减,人类的理性精神自由判断逐渐张扬,现代性由此萌芽诞生,是现代性的第一波浪潮。不过,宗教体系固然在科学事实上变得越来越遥远和不可信,但理性也不能填补人们对精神家园的需求,这便是审美现代性的由来。以浪漫主义为代表的审美现代性构成了现代性的第二波浪潮。浪漫主义借助神圣的自然超越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借助美来弥合分裂的现实,在有限中寻求无限,建构精神家园,试图将自然之美打造成新的宗教替代物。可在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发展面前,浪漫主义的追求日益沦为主观的幻想。艾米莉·勃朗特所生活的时代,“伟大的浪漫主义时代已经几近尾声,而英国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即将开始”①Terry Eagleton. Myths of Power: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ës[M].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5:xi.,是一个后浪漫主义时代。故而,从时间上来看,《呼啸山庄》合乎现代性第三次思潮。
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相关思考。艾米莉的家庭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牧师之家,又是一个浪漫主义氛围充分浸染的家庭。这让艾米莉既有强烈的信仰渴望,又有着对美与自由的强烈向往,对宗教和浪漫主义双双衰落既绝对清醒又满怀痛苦。
艾米莉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出生于爱尔兰,他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后来成为霍沃斯教区的一位福音派牧师。艾米莉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这也是一个被死亡阴影笼罩的家庭。艾米莉三岁时,母亲去世。母亲死后,照顾孩子们的姨妈也同样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不到五岁的艾米莉·勃朗特和三位年长的姐姐曾经被送到考恩桥寄宿学校读书。这是一所为神职人员的子女开办的寄宿学校,负责人卡如斯·威尔逊牧师深受加尔文主义和福音主义的影响。这次求学留给勃朗特一家惨痛的记忆。艾米莉·勃朗特的两个大姐姐正是在这个学校感染伤寒不治身亡的。亲人的陆续死亡给艾米莉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长大后,她对离开家庭始终心怀恐惧。1835年,17 岁的艾米莉曾随姐姐夏洛蒂到罗海德的伍勒女士的学校求学。艾米莉的身体因为极度恋家很快衰弱,夏洛蒂担心艾米莉身体会垮掉,三个月后就将她送回家了。亲人接连逝去带来的创伤让艾米莉对上帝的仁慈有着隐秘的怀疑。1842年,在比利时留学的艾米莉写过一篇散文《蝴蝶》。“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创造人类?他折磨,他杀戮,他吞噬;他痛苦,死亡,被吞噬。整个故事就在这里。”②Emily Brontë. The Butterfly[C]/ / Sue Lonoff. The Belgian Essays.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178.在仁慈的上帝创造的世界里,好人受苦、死去,苦难绵延不断,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真的仁慈吗?她真切地感受到了上帝的消失,不仅仅是教会形式主义的弊端,也不仅仅是教派冲突背后的利益冲突,而是上帝已经不能赋予人生终极价值,不能回应人们心灵的呼声,也不能填补人们对家园的渴望。
对勃朗特姐妹影响至深的浪漫主义也是如此。它是艾米莉自小至大一直阅读的作品,是家庭的氛围,是时代呼吸的空气。“她们的父亲是独断专行的托利党人,从小给她们讲述的是英雄事迹和神话人物,教她们敬仰威灵顿公爵,热爱一切崇高尊贵的事物。这些都充分折射出浪漫主义时期极尽浮华夸饰的革命与反革命潮流。”③Terry Eagleton. Myths of Power: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ës.Introduction to the Anniversary Edition:xii.勃朗特姐妹的阅读范围相当宽广,1834年夏洛蒂给朋友艾伦写信,推荐了“一些可供你细细品读的”书:“如果你喜欢诗,那就看第一流的吧:弥尔顿、莎士比亚、汤姆逊、哥尔斯密、华兹华斯、骚塞、蒲伯(如你愿意读的话,我可不喜欢他)、司各特、拜伦、坎贝尔。看到莎士比亚和拜伦的名字,埃伦,你可别感到惊异,这两个人都很伟大,而他们的诗作也和他们本人一样。——别去看莎士比亚的喜剧和拜伦的《唐璜》,或许还有《该隐》,虽说后者是皇皇巨制。其余的则尽可放心大胆地去读。——司各特的甜美、狂放、浪漫的诗歌对你绝无害处,华兹华斯、坎贝尔、骚塞的诗也一样——至少骚塞诗作中最伟大的那部分是如此,而有一些则当然是要不得的。想读传记,那就看约翰逊的《诗人传》,哈克洛特的《彭斯传》,博斯威尔的《约翰逊》,骚塞的《纳尔逊传》,莫尔的《谢里丹传》和《拜伦传》,澳尔夫的《遗迹》。”④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勃朗特两姐妹书信集[M].孔小炯,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3 -14.这份书单显示了她对华兹华斯、骚塞、司各特、拜伦这些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熟悉和热爱。事实上,浪漫主义作家也是勃朗特姐妹的崇拜对象。1837年,夏洛蒂·勃朗特写信给骚塞,就诗歌创作和人生道路请教这位桂冠诗人。1840年,夏洛蒂写信给华兹华斯,就一个故事的创作进行请教。艾米莉与夏洛蒂的审美口味虽然存在差异,但姐妹俩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熟悉程度不相上下。1842年艾米莉与夏洛蒂去比利时留学时,学习语言的素材不少就出自欧洲大陆的浪漫主义文学。“夏洛蒂欣赏乔治·桑和维克多·雨果的法国散文,而艾米莉则喜欢德国的浪漫主义传统:法国小说激发和解放了夏洛蒂的天才,正如霍夫曼的故事给艾米莉以激励和动力。”①Birgit Van Puymbroeck.‘The Virgin Soul’:Anglo -French Spectres of Emily Brontë,1880 -1920[J]. Brontë Studies,2014,(4):322.除了阅读,勃朗特姐妹也喜欢沉浸在诗歌的幻想世界。1831年,艾米莉和安妮合作写《贡达尔传奇》,此后,这一浪漫传奇里人物的爱恨情仇陪伴了艾米莉的许多时光。她的日记里经常将贡达尔的日常和自己的日常生活并列交错叙述,游走在虚幻和现实之间。不过幻想世界终究是幻想世界,艾米莉对此亦有着清醒的认知,她的诗歌中也不时流露出希望消逝的痛苦。幻想只是自我逃避的港湾,不是精神的皈依。
艾米莉有着强烈的宗教情结,渴望超越短暂和有限的人类生命,寻找永恒精神家园,同时她也失望于主流宗教的软弱,觉察到浪漫主义的虚幻。失落的痛苦和强烈的渴望在这位牧师之女心中汹涌澎湃,使她在《呼啸山庄》流露出“一种异质的、同时也是执拗的力量,是一种拒绝充分表达的需要和激情,一种不论好歹都要破坏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②Terry Eagleton. Myths of Power: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ës[M].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5:xix.。正如牧师之子尼采喊出的“上帝之死”,既有对往日基督教的留恋怨恨,也试图给人类存在寻求新的终极意义。这是现代性的困境,也是人类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