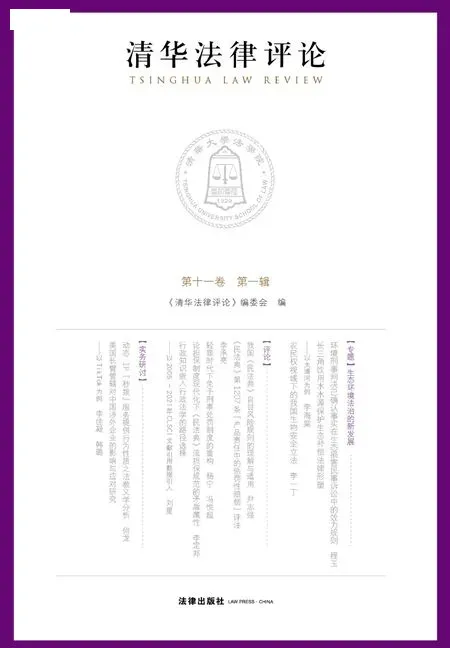我国《民法典》自甘风险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尹志强
目 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自甘风险是否为独立的免责事由
三、“文体活动”的界定
四、自愿参加的认定
五、参加者的范围
六、故意和重大过失的判断
七、自甘冒险的法律效果
一、问题的提出
自甘风险是侵权行为法上的一个古老的责任抗辩事由,也称风险自负、自甘冒险等。《元照英美法词典》解释为volent non fit injura,是依照法律,当事人不得就自己同意遭受的损害获得补偿,即如果当事人自愿置身于觉察和了解的危险中,则不得就为此所受损害获得赔偿。①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 页。即这种损害的风险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承受。自甘风险来源于19 世纪的个人主义思想,人们强调个人意思自治和个人自觉权,个人是自己命运的掌控者,有权作出自主的选择并对选择负责,所谓“自己选择,自己责任”。但实际上各国具体规范并不相同。我国在《民法典》前并无单独的自甘风险规则,实践中也比较混乱。《民法典》第1176条虽然将自甘冒险规则置于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定”中,但就内容而言显然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效力,具体要素方面也存在很大解释空间。比如,自甘冒险与受害人同意的关系问题,适用范围中“文体活动”有无限制?是否包括跳舞、爬山、“大胃王”等无对抗性的活动?“参加者”是否包括裁判、教练、服务人员,甚至记者、观众等?其中的“故意和重大过失”又将如何理解,比如,在拳击比赛中,如何认定“故意”等,上述问题理论上有不同观点,实践上也有不同做法。因此,深入探讨对正确贯彻立法思想,实现立法目的实有必要。
二、自甘风险是否为独立的免责事由
这一问题的提出,主要源自其与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等减免责事由的关系。“大部分欧洲法律制度认为,风险自负实际并非独立的法律范畴,不是独立的一般抗辩事由,而是一个须在赔偿责任法其他范畴内加以考察的因素。”②[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637 页。当然,这里的“其他范畴”欧洲学者也有很大争议,并集中在是否为受害人同意的特别内容,或者应该在共同过错制度中解决等。在法制史上,自甘风险制度与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制度也一直呈现交错发展状态。英美法系中广义的受害人同意包括自甘冒险,狭义的受害人同意主要适用于故意侵权,而自甘冒险主要适用于过失侵权。大陆法系的德国最初将受害人同意统一作为故意和过失侵权的抗辩事由,后来将自甘风险从受害人同意中区分出来,纳入与有过失的范畴。③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3 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352~353 页。我国《民法典》出台之前,多数学者将自甘风险视为受害人同意,如有学者认为,自甘冒险是一种特殊的受害人同意,其本质上是对损害结果的认同。④参见杨立新:《侵权损害赔偿》(第6 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 页;彭俊良:《侵权责任法论——制度诠释与理论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 页。或者直接认为自甘冒险规则与受害人同意规则在性质上相同,可以将自甘冒险规则归入受害人同意规则。⑤参见李超:《侵权责任法中的受害人同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8 页。还有学者认为,自甘冒险是对部分受害人过错情节的描述,是受害人过错的一种,可纳入过失相抵的范畴。⑥参见周友军:《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 页。第四次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王利明教授的建议稿的第1851条,参考《葡萄牙民法典》第34条,也将自甘风险和受害人同意一体规定。⑦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4 页。由于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学者主张自甘冒险规则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所涉及的问题应当通过过失相抵、注意义务的判定等规则解决。⑧廖焕国、黄芬:《质疑自甘风险的独立性》,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 期。司法实践中,将自甘冒险以受害人同意或过失相抵来认定的情形很普遍。⑨参见金某语、金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上诉案,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7 民终730 号民事判决书;赵某与贾某健康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 民终7967 号民事判决书。
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2017年10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室内稿”、2018年3月法工委的“征求意见稿”、201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审稿”,都没有关于自甘风险的单独规定。有部门、法学研究机构指出,参加对抗性的体育活动容易发生人身伤害,实践中此类纠纷经常产生,建议《民法典》予以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由这些活动产生的正常风险原则上应当由参加者自己承担,确立“自甘冒险”规则,对于明确学校等机构正常开展此类活动的责任和界限是有利的。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载《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3 页。因此,2018年12月“二审稿”于第954条加入自甘风险规则:“自愿参加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他人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他人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九百七十三条的规定。”⑪“二审稿”第973条是关于公共场所、经营性场所经营者和管理者、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对于其中的适用范围,有委员提出“具有危险性的活动”不够明确、活动组织者的责任不够完善等意见,⑫参见朱宁宁:《审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的三个焦点》,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c35775/201812/0fc8b5de72704c56bb190b60d5fc3f66.shtml。同时也有学者撰文指出该条的适用范围过宽,建议限缩自甘冒险的构成要件。⑬参见王利明:《论受害人自甘冒险》,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2 期。2019年8月“三审稿”始将其修改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九百七十三条至第九百七十六条的规定。”⑭“三审稿”第973条至第976条包括安全保障义务人、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责任的规定。而对于受害人同意,作为一般规则,除有学者建议外,立法活动中并未出现激烈争论。从中可以看出,《民法典》一方面将自甘冒险作一般性规定,但将适用范围限定于“文体活动”;另一方面未对受害人同意作一般性规定,而是以特别规范身份在医疗损害责任和人格权编的特别条款中出现。⑮参见《民法典》第1008条、1019条、第1033条、第1035条、第1219条。即从我国立法上看,对自甘风险和受害人同意是分别规定的,在实践中,应针对不同情况区分适用自甘风险规则与受害人同意规则。
而过失相抵,本质上属于损害赔偿法制度,在责任抗辩中属于受害人与有过失问题,我国的具体法律规范为《民法典》第1173条和第1174条。从该规定中可以看出,在受害人与有过失情况下,对加害人责任的减免,属于因果关系抗辩,其与自甘冒险制度中其他参加者不承担责任所要贯彻的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以及对诚实信用价值的追求是不同的。“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并不意味着受害人有过失,以自甘冒险为由认定受害人与有过失,并适用减轻或免除行为人的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一)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
在我国《民法典》语境下,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是不同的:
1.在适用范围上,作为责任抗辩事由,自甘风险虽然规定于“一般规定”,却仅适用于“文体活动”造成的损害,文体活动之外的侵权责任抗辩不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而受害人同意,虽然理论上认为其属于阻却违法是共识,所谓“有效的同意将排除一切侵权责任”,但并非适用一切领域,而是限定在法律的特别规定中。域外法中,除《葡萄牙民法典》在第340条作一般性规定外,立法上,即便规定也是在对诸如医疗措施的同样方面加以规定。⑯参见[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30 页。
2.在对行为人的主观要求上,受害人同意的情形是针对行为人的故意行为而言的,是其故意招致风险;而自甘风险则不适用于相对人的故意行为。从另一方面看,受害人同意无法针对过失情形;而自甘风险规则,则仅针对一般过失,如果行为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害,则不属于风险问题,行为人需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文体活动中,如果通过受害人同意规则来免除造成损害的其他参加者的责任是不妥当的,通过自甘风险规则,推定那些参与比赛的人都已接受依据运动本质而无法避免的损害结果,显然更为合适。⑰参见[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5、6、7 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29页。就此而言,尽管在手术志愿书中,可能存在对各种风险的提示,患者签字除了对手术本身的同意外,也包含对意外风险后果承担的意思,此时,虽有自甘冒险之意,但法律适用中,仍不能依据《民法典》第1176条,而应作为违法抗辩理由直接适用第1219条。其中的差异在于,在适用第1219条时,如果手术失败源自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的过失,不管是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医疗机构均需承担赔偿责任;而如果认为属于自甘风险,则只有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承担赔偿责任。
(二)自甘风险不同于与有过失
自甘风险和与有过失的区分问题也是国内外理论和立法的关注焦点之一。有学者认为“自甘冒险规则只不过是过失相抵、注意义务判定、过错责任原则以及责任的预先免除等领域内的问题,在我国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⑱廖焕国、黄芬:《质疑自甘冒险的独立性》,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 期。我国学者王泽鉴先生也认为:“自甘冒险不应定性为被害者的允诺,作为违法阻却的问题,而应纳入与有过失的范畴,由法院衡量当事人对损害和扩大的原因力,以合理分配其责任。”⑲王泽鉴:《侵权行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242 页。
与有过失分为促成过失和比较过失两个发展阶段,在“全有全无”的促成过失时期,其法律效果与自甘风险大体相同,均为直接免除加害人的责任;在以后的比较过失则主张依据加害人和被害人的过失程度,将损害结果在两者之间合理分配。比较过失出现以后,自甘风险理论受到冲击。有学者认为,受害人的损害毕竟是由于加害人造成的,加害人的过失行为和受害人的自甘风险都具有可责难性。相较于将损害结果全部归为受害人承担的自甘风险,使受害人获得一定补偿的比较过失更加合理。⑳See Fleming Jr.James,Assumption of Risk:Unhappy Reincarnation,Yale Law Journal 78,191-192(1968).这种观点在自甘风险广泛适用的情况下是有道理的。
而我国《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被限定在“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范围内,此与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过失相抵有明显区别,两者在行为认定上存在很大差别。认定过失相抵时,加害人需证明受害人具有过错,且受害人并没有作出自己承担损害的意思表示。而适用自甘风险时,加害人只需要证明受害人在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时已经认识到活动存在的风险,并作出了自愿承担可能的损害后果的意思表示。而事实上,因为参加文体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自甘冒险所涉及的活动均为法律不禁止的行为,冒险也非具有法律上可责难的心理状态,不能认为受害人参加有风险活动的行为即是一种过失,冒险与《民法典》第1173条、第1174条规定的与有过失并非相同。事实上,在自甘冒险具有长期发展历史的美国,其主要的默示自甘冒险主要适用于体育活动,而美国第三次侵权法重述采用比较过失制度以来,大多数的法院仍然保留了主要的默示自甘冒险,就是因为在体育活动中比较过失制度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另外,在比较过失制度下的过失相抵的效果是减责(当然在受害人故意时可以减责至全部),而我国《民法典》上的自甘冒险是免责事由,只要加害人非故意或重大过失侵权,受害人就不能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就此而言,根据原《侵权责任法》(现已失效)第76条(《民法典》第1243条)规定认为我国“在高度危险领域确立了自甘冒险的规则”㉑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12 页。的判断并非准确。因为该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自己已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本条情形下,受害人属于明知有高度危险,仍然进入相关区域,其行为属于“自甘风险”,但该条适用其实包含两个重要价值,即对违法行为法律不予保护;对受害人过错造成的损害不予保护。高度危险区域通常都与大众活动区域相隔绝,管理人应按照规定采取安全措施或予以警示,受害人未经允许擅自进入该区域或在该区域实施违法活动,一方面行为具有违法性;另一方面也是有过错的。这种情况下对于受害人的损害,管理人责任减免的原因,本质上恰恰不是因为受害人自甘风险,而是因为其行为违法且与有过失。法律适用上,管理人仅能依该条为抗辩,而不能依据第1176条为抗辩。
自甘风险和比较过失的两种制度,实际上反映了法律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倾向。自甘风险出现较早,秉承法律个人主义,认可参与人事前认可对权益处分的效力,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优于权益保护。比较过失与近代以来的法律社会主义相伴而生,受害人的不幸遭遇不仅是其与加害人的双方关系,更是社会正义问题,应当通过侵权责任法进行损害填平和风险分散。㉒参见曹权之:《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文研究》,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 期。
(三)自甘风险是独立的抗辩事由
虽然《民法典》规定了有关违法性抗辩、因果关系抗辩等各种责任抗辩事由,但在文体活动领域内,自甘风险规则有其独到的适用价值。文体活动是人们的生活日常,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活动,而且许多文体活动,如竞技体育活动中的拳击、摔跤、篮球、足球、橄榄球等天生就具有强烈的身体对抗性,项目性质决定了其允许参与者在合理范围内的过失行为,而这种激烈的身体对抗不可避免产生身体伤害风险。一旦出现伤害情形,违法阻却事由、无因果关系或者无过失等抗辩都难以适用,如果适用过失相抵规则要求参与者因过失而承担侵权责任,这将使参加者为了避免承担责任而畏手畏脚,其后果不仅使运动本身失去乐趣,也背离了文体活动的竞技初衷。
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将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限制为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这种本土化规定最大限度避免了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与有过失的适用范围的重合。独立的自甘风险制度,对结束滥用自甘风险的乱象,对解决体育活动中的侵权纠纷,避免侵权责任在文体活动中的滥用,无疑都是有帮助的;厘清开展体育活动的责任界限,也有助于此类活动的发展繁荣。㉓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18年12月),载 北大法宝2018年12月23日,https://www.pkulaw.com/protocol/17652f9c2ddc807f60a 5e14c333b9e13bdfb.html。除此之外,法律上独立规定自甘冒险,既合理分配了责任,也可以实现损害的预防。㉔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第2 版)(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58 页。即自甘风险作为一种独立侵权抗辩事由有司法价值,也有法政策的考量。我国的自甘风险规则区别于其他减、免责事由而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三、“文体活动”的界定
在《民法典》之前,我国的自甘风险规则适用是非常混乱的,这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自甘风险,理论上可能发生在任何领域。除前述的未经允许进入高度危险区域情形外,在其他如雇佣关系中,自愿接受具有一定风险的工作岗位,跳入湍急河流中救助他人等“见义勇为”等领域也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自甘风险,但雇佣合同与见义勇为等因涉及特殊利益保护,通常不能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在实践中,人们也常认为乘坐醉酒者驾驶的机动车的行为属于自甘风险,也常有法院作出在“好意同乘”情况下以乘车人自甘风险为由减轻赔偿义务人责任的判决。㉕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江民初1301 号。认为“受害人在明知他人酒后驾驶,仍搭乘其车辆的情况下,受害人的行为构成自甘冒险,应由其对酒后驾驶行为引发的损害后果适当承担责任,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责任”。另参见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川20 民终200 号、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云01 民终4402 号。其实,在明知对方饮酒或处于其他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下,仍然乘坐其驾驶车辆的情形,属于与有过失问题;而“好意同乘”情况下的减轻责任(非免除)其原理在于搭乘者的无偿性,此与受害人自甘风险不同,尤其在我国《民法典》对“好意同乘”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自然不能再以自甘风险制度适用之。那种认为“应该通过完善自甘风险规则实现特殊情况下的好意同乘减责”㉖张素华、刘畅:《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好意同乘条款的存废》,载《江汉论坛》2020年第1 期。的主张并不合理。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尽管存在自甘风险事实,如果不属于因参加“文体活动”受到的损害,应当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受害人如果不能证明行为人有过错,则应视为“人生风险”由其自己承受损害后果,而非属于《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下的自甘风险制度情形。如前所述,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有关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所以,虽然在一般意义上,自甘风险在广泛领域存在,但只有在“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范围内才可以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当然,即便将自甘风险限定在“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范围内,理论和实践中对何为“文体活动”,如何界定“一定风险”也还是有不同观点的。
(一)文体活动的认定
文体活动,是文娱活动和体育活动的合称。在司法实践中自甘风险基本是针对“体育活动”的,立法之所以使用“文体活动”,目的是涵盖不在传统狭义“体育”范畴中的风险性身体活动。㉗参见韩勇:《(民法典)中的体育自甘风险》,载《体育与科学》,2020年第4 期。考虑到一般文化、娱乐活动几无身体对抗,人身伤害风险不大,因此,立法中虽有“文”但其实大多并不适用。实践中如果在舞蹈㉘参见郭某与深圳市小百合明星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 民终3510 号民事判决书。或杂技、团体操等具有一定风险的文娱活动中出现意外,符合《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其他要件的,自可以适用。这里只以体育活动为目标展开讨论。
就体育而言,根据参加者参与体育的主要目的,可以将其分为竞技体育、休闲体育和健身体育。竞技体育以超越对手或自我、获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的,强调规则的完善、组织管理的规范和对比赛结果的评判;休闲体育以调节情绪、愉悦身心为主要目的,强调在开放自由的锻炼环境中获得精神需求的满足;而健身体育以增强身体机能、提高身体素质为主要目的,强调科学健身理念引导和方法指导。㉙参见刘转青、刘积德:《我国体育分类刍议》,载《体育学刊》2017年第1 期。竞技体育中,根据对抗性、风险来源及发生概率等虽也分不同类型,如以“伤害”他人为目的的拳击、跆拳道、自由搏击等;身体接触的非以伤害他人为目的的对抗性竞技体育如篮球、足球、橄榄球等,非身体接触的非伤害他人为目的的对抗性竞技体育如排球、藤球、羽毛球等。休闲体育运动本身通常少有参加者之间的身体对抗,如滑雪、溜冰、骑马、轮滑等;而健身体育主要是体育锻炼活动,其项目可以表现为竞技体育,也可以是休闲体育。
从中可知,虽然各体育类型中,均可能产生风险,但《民法典》第1176条中的自甘风险规则主要适用于竞技体育。休闲体育虽然有些项目有一定风险,如滑雪、冲浪等,且不时有纠纷发生,但该类纠纷主要源自组织者或场所经营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违反,㉚参见陶某、张掖七彩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分公司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7 民终885 号民事判决书。或者是因为当事人过错(如滑雪中不遵守优先规则等),㉛参见张某涵与北京市万龙八易体育运动优先公司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2 民终15845 号民事判决书。即其风险来自运动项目本身或组织者、管理者的不作为,而不是因其他参加者正常行为所致,因此该类活动产生的损害赔偿不适用自甘风险条款的抗辩。多人组团进行的非商业性旅游冒险活动中,参加者受到损害后,指控其他参加者有改变路线、准备不充分、未采取正确救助措施等过错,要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的纠纷时有发生。㉜参见张某1、张某2 等与吴某华等侵权责任纠纷案,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 民初4283 号民事判决书;刘某邦等诉陈某生命权纠纷案,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5)嘉南民初285 号民事判决书。但此类活动的风险并非来自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是来自自然环境,参加者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应当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而不应对其他参加者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这种自我承担责任的情形,不属于该条自甘风险条款的调整范围,而是《民法典》第1165条过错责任的调整范围,其他人不承担责任系因为缺乏过错要件,而非受害人的自甘风险。
竞技体育比赛强度大,场面激烈、刺激,人身伤害风险自然也高,但是,一方面,这类运动比赛规则更加严格;另一方面,参与活动的人多以此为业,与所在组织签有劳动合同,除有劳动保障救济外,基本都投有人身保险,因此,固然风险大,但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既可保证运动项目本身的开展,也不会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后果。
健身体育中,参加者主要目的在于锻炼身体,形式上主要以训练为主,或者仅为一般性竞技(比如几个好友相约打篮球等),通常风险不高,但因为对运动项目本身理解上存在差异,运动技能水平有限,运动风险也不可避免。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因为参加体育活动造成伤害产生的纠纷,多数并非职业体育比赛活动,反而是来自民间组织的体育活动或者健身体育活动。不管运动层级如何,只要有身体对抗或者运动本身存在的风险,自甘风险规则就有适用空间。㉝参见北京市笙辉国际体育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等与扈某等侵权责任纠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3 民终2882 号民事判决书。
对“文体活动”虽不能绝对精确界定,但从立法过程和立法目的分析,对自甘风险采取限制适用精神,所以,有些活动即便能解释为“文体活动”,也要看是否有其他参加者,以及是否为具有一定身体对抗或协同风险的文体活动等;不能解释为“文体活动”的,就不能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除此之外,该条所规定的“文体活动”是以合法性为前提的,违反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观或违反善良风俗等活动,被排除在自由处分权范围之外。因此,实际生活中的“约架”“飙车”,或者以赌博为目的的文体活动,不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二)“一定风险”的认定
从逻辑角度分析,并非所有的“文体活动”都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民法典》第1176条以“具有一定风险”限定,但因为用词过于抽象,给法律适用造成困扰。概括地看“一定风险”应理解为超出日常的特殊风险。司法实践中,是否为超出日常的特殊风险,应结合不同类型文体活动的特点,根据日常经验判断,比如,有判决书对篮球活动是否有“一定风险”解释认为:“本案中,魏某与陈某1 均为自愿参与具有一定风险的篮球体育活动,涉案篮球活动虽属业余性质,但身体激烈对抗可能引发受伤的风险性高于日常体育锻炼活动,因此,对魏某与陈某1 的行为均不能过于苛责。”㉞参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1 闽终2136 号。对某项具体活动是否具有“一定风险”可以考虑下列因素:(1)该文体活动是否具有对抗性。虽然立法中并未明确文体活动的对抗性,但通常缺乏身体对抗性的活动要么没有风险,要么不仅有风险,甚至风险极大,但除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外,与其他参加人无关,自然无法使“其他参加者”承担赔偿责任。比如,户外探险类活动,不仅存在是否为“文体活动”的争论,也因其不具有各参加者身体对抗性而不能适用该条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当然,这里的对抗性,除身体直接接触的运动外,也包括通过运动器械的对抗,如羽毛球、藤球、网球等。(2)“风险”是否为文体活动所固有。即风险需无法避免,㉟参见杜某与周某1、周某2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6 民初13580 号民事判决书。如果风险是文体活动以外带来的,如球员受伤系观众投掷饮料瓶导致,则不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该观众应承担过错责任。如果文体活动参加者的损害是因为场馆设施瑕疵,或者组织者疏忽导致,也不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而应适用组织者、管理者、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违反责任。
四、自愿参加的认定
自愿参加,是指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参加。概括而言,“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包含知道风险的认识要素和自愿承担风险的同意要素。认识要素即受害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活动风险;同意要素,即受害人自愿参加活动承担风险,系出于真正的自由意志决定,非受欺诈或胁迫。㊱参见邹海林、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 侵权责任编》(1),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31 页。如此,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文体活动的风险性,以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作出了愿意承受风险的意思表示,即可认定为该条规定的“自愿参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监护人事先同意的情况下的参加,也构成自愿参加。有观点认为,有效的自甘风险需要考虑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能力。㊲田雨:《论自甘风险在体育侵权案件中的司法适用》,载《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1 期。但是,我国对责任能力的讨论并不充分,实践中基本都以行为能力为判断标准,在自甘风险的认定问题上,虽然涉及责任分担,但主要还是对风险的认识问题,而不是责任承担能力问题,在要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参加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文体活动须由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认定是否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无须再考虑责任能力问题。
自愿参加意味着当事人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并非出于履行法律或道德上义务的要求。至于实践中运动员被教练要求参加比赛,或学生被老师要求参加文体活动的情形,应该认为,前者通常因为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合同,按照要求参加比赛属于事先承诺,当然属于自愿参加;后者除身体异常原因外,参加文体活动属于教育的组成部分也应视为自愿参加。
自愿参加,以当事人对文体活动的风险有所认识为基础。不同的文体活动,风险概率是有差异的,拳击、自由搏击等直接身体对抗的竞技项目的风险,一般人都有认知,但对羽毛球等看起来没有风险的项目,很多人缺乏风险认知,甚至有学者在讨论自甘风险的适用时也常将羽毛球运动作为少风险对待,有人即便认为羽毛球运动存在“一定危险”,也不认为危险来自羽毛球运动本身,而是“羽毛球拍不慎脱手”之类。这显然是对该项运动缺乏了解,实际上因为参加羽毛球运动而受到伤害的案例很多,《民法典》实施后的自甘风险第一案即出自羽毛球运动。㊳参见宋某祯诉周某身体权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 民初67259 号民事判决书。其实,本案中法院认为当事人参加该项运动多年,对项目的危险性应当知道的判断还是有进一步讨论余地的。毕竟当事人参加的是“三对三”比赛,与平时的单打或双打在风险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此,在实践中是否对运动风险有一定认知,还需结合年龄、运动的专业化程度、参与运动的经验等个案认定。
自愿参加的方式可以是口头同意,也可以表现为签订“自愿参赛责任书”㊴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云04 民终1328 号。“运动安全协议”㊵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13 民初8734 号。“承诺书”㊶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云25 民终1327 号。等明示方式,也可以是当事人的自愿行为等默示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自愿参加的文体活动是以合法为前提的,因此,对于私下“约架”,或者以赌博为目的进行的竞技活动,即便当事人自愿参加,甚至签订有“免责声明”,也不能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五、参加者的范围
该条规定中,涉及的主体包括“自愿参加”人、“其他参加者”“受害人”“活动组织者”。“活动组织者”的责任不属于自甘风险规则范畴,本文不作讨论。而“自愿参加”人与“受害人”相同,与“其他参加者”均为“参加者”。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参加者”的范围有不同观点。对于运动或活动本身的参加者,即运动员(包括替补队员)、教练员,以及裁判人员等都属于活动的组成部分,他们对活动本身的风险熟悉,而且因此受到伤害可以获得保险、劳动者保护等赔偿,即不会因受到伤害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对这部分人自然属于该条规定的“参加者”。而为活动提供服务的人员,如网球比赛中的球童、篮球场地清理人员等,虽有不同观点,但通常他们被运动本身伤害的概率很低,案件或出现纠纷极少,笔者认为,这些人无疑身处“文体活动的风险”之中,意外发生后,如果能通过劳动保障制度解决其赔偿问题,那么,在受害人与致其损害的“其他参加者”之间,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更合理。
争议较大的是观众是否为“参加者”?《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杨立新老师主持的建议稿第29条第3款将体育活动中的观众也视为自甘冒险者。其内容为:“参加或者观赏具有危险性的体育活动,视为自愿承担损害后果,适用本条第1款的规定,但行为人违反体育运动管理规则,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除外。”㊷参见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9 页。《民法典》出台后,有学者认为,该条的适用范围包括体育活动同场竞技参与者之间发生的伤害、观众在观看体育比赛时因场上竞赛行为发生的伤害、非商业性AA 制户外旅游探险活动中发生的损害。㊸参见韩勇:《〈民法典〉中的体育自甘风险》,载《体育与科学》2020年第41 卷第4 期。杨立新老师在谈到该条“受害人”时也认为“受到损害的不限于自愿参加者,还包括自愿观赏者”。㊹杨立新:《自甘风险:本土化的概念定义、类型结构与法律适用——以白银山地马拉松越野赛体育事故为视角》,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 期。而更多的观点认为该条的“参加者”不包括观众,“参加是指亲自加入活动或进入活动场地,而不包括仅作为观众欣赏”。㊺邹海林、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 侵权责任编》(1),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31 页。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观点认为:观众的目的是娱乐,一般都远离比赛场地,不能认为观看比赛具有危险性,也不能认定他们已经预见到风险并愿意承担此风险。㊻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 页。对此,一方面运动本身除职业运动员外,多数人亦为娱乐而参与活动;另一方面,有些运动场地与观众席距离非常近,如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汽车越野比赛等,也有些运动虽然场地与观众席距离较远,但也常有观众被伤到的情形,如棒球比赛等。如果因为运动员抢球时冲入近距离观看球赛的观众席,或者因为棒球飞入观众席而伤及观众,即由相关运动员承担责任,恐并不妥当。当然此种情况下,也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一般条款处理,但其适用条件比之自甘风险规则更加复杂。因此不能概括认为观众受到的伤害一律不适用自甘风险,而应视具体情况个案判断。判断标准可比照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认定,即是否认识到其近距离观看比赛或者观看特定比赛存在的危险性,是否明示或默示自愿承受由此带来的风险等。在域外法中,很多国家并没有明确“参加者”的范围,更没有对观众是否为“参加者”进行解释,明确观众可以成为自甘风险主体的是《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其第2068条规定:“在进行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对参加同一活动的人或在场观众造成伤害的人,如果不存在任何欺骗行为或者对运动规则的重大违反,不承担任何责任。”
当然,观众作为“参加者”同意承受的风险与直接参与者有明显区别,不应将二者直接等同对待。第一,文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之间适用自甘冒险规则,对于一般过失造成的损害可以免责,但观众同意承受的风险应远小于直接参与者,如,滑雪者违反“一人一圈”的要求,两人共用一个滑雪圈,冲出滑道至场边观众受伤,此时如果适用自甘冒险免责,则不符合一般人的合理预期。而如果是近距离观看越野车比赛,则对于可能的翻车致害,观众应该有合理预期。第二,观众同意承受的风险较小,但并非不承受任何风险。在致害者遵守活动规则的情况下,仍无法避免致观众损害发生的,应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如比赛用球意外飞到观众席上导致观众受伤、篮球比赛中选手救球冲出场外撞伤观众等,此类情形是观众近距离观赛时可以预见的风险,不应对参加者施加过重的注意义务。第三,如果受害人擅自靠近或横穿活动场所导致受伤,则受害人存在过错,不宜认为其属于“自甘风险”,而应根据过错责任一般规定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受害人的行为与文体活动本身没有关系,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自甘冒险,也不能适用自甘冒险规则,如在“李某横穿篮球场案”中,㊼参见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鄂0191 民初3557 号。一审法院认为张某有过失,而二审法院认定张某在篮球场上进行背身接球跑动,系篮球运动中的常规动作,即使与其他球员发生碰撞,不能视为其存在过错;反观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篮球场明显区别于一般道路是明知的,对球场上有学生进行对抗性的篮球运动是明知,能够预见到横穿球场面临的受伤风险,其仍然选择横穿球场,应当视其为自甘冒险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实际上李某的行为并不符合自甘风险要件,其行为与运动本身没有联系,不属于参加者,也不属于观众。其横穿球场是有过错的行为,应当直接适用过错责任一般条款,以行为人无过错为由,裁判不承担责任。就此而言,有学者认为该条的“参加者”不仅包括正式的参加者,也包括那些擅自进入场地的人,比如为陪同外孙女滑雪而擅自进入场地、穿越滑道的老人,或者擅自进入足球场地而未被及时发现的球迷。其理由为“若非如此,对其他参加者必然不公平,毕竟其他参加者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准确辨认出对方身份,并做出准确的规避和防范动作。”㊽邹海林、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 侵权责任编》(1),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31 页。对“参加者”不宜绝对限制在直接参与文体活动者范围是值得赞同的,但无论怎样,“擅自进入场地的人”不能视为“自甘风险”。其损害由其自己承受,而不是由“其他参加者”负担的原因,系因为其他参加者无过错,如果擅自进入场地的人造成“其他参加者”损害的,擅自进入场地的人则须承担赔偿责任。
六、故意和重大过失的判断
对自甘风险规则而言,实践中面临的难题或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行为人违反活动规则的行为是否仍然属于文体活动的固有风险?在体育比赛中如正式的篮球比赛中,一方违反运动规则的情形十分常见,违规的行为导致受害人的损害是否属于运动的固有风险?美国“在这方面,大多数法院认为,其他参加者典型的违规行为所导致的损害不会导致责任”,因为规则的违反是固有的而且可以预见的。㊾Davis Timothy,Avila v.Citrus Community College District:Shaping the Contours of Immunity and Primary Assumption of the Risk,17 M ARQ.S PORTS L.R EV.259,274(2006).但实际上,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并自愿承受该风险带来的损害,是以符合比赛规则或比赛规则允许(或能容忍)为前提的,而对超出比赛规则能容忍的范围的行为造成的损害,不是受害人事先能预见到的,当然也不能认定为其自甘风险。《民法典》第1176条将自甘风险规则适用的除外情形规定为“故意或重大过失”。民法上的故意指“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发生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后果,仍有意为之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㊿程啸:《侵权责任法》(第3 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91 页。即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后果,仍然实施该行为的情形。行为人主观上对损害结果不管是追求还是放任,均不影响故意的构成。重大过失,是指行为人连最基本的注意义务都没有尽到,或者说,行为人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违背了必要的注意。51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3 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90 页。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下,造成损害超过了文体活动本身的危险范畴,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强烈的可非难性。52参见赵峰、刘忠伟:《论体育活动中自甘冒险的适用范围》,载《法律适用》2021年第11 期。对此,行为人不得以受害人自甘风险抗辩损害赔偿请求。
一般情况下,竞技体育规则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为保护参加者的人身安全的规则,其确立旨在明确共同参加者的注意义务,不履行该类义务,造成损害的行为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类规则通常源自法律规定,在风险告知书中不需列举。二是为维护比赛公平竞争秩序的规则,该类规则目的不在于对参加者行为的限制,而在于使活动更加有吸引力,在此规则内的行为造成其他人的损害属于活动的固有风险,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行为人无须承担责任。在我国《民法典》的自甘风险规则项下,违反前类注意义务造成他人损害时,才可能属于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害。
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判断:(1)是否违反比赛规则。认定其他参加者的行为是否为故意或重大过失,首先要看文体活动的竞技规则是否被违反,竞技规则对活动参加者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而且,体育竞技规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制定,因此,符合规则的行为必然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承担法律责任。53参见刘铁光、黄志豪:《(民法典)体育活动自甘风险制度构成要件的认定规则》,载《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年第2 期。(2)文体活动对违反规则的行为的容忍程度。因为竞技体育的特点各有不同,比赛规则也有很大差别,在足球运动中双方在争球时“铲球”是被允许的动作,但在篮球运动中用“铲球”方式抢球,应被视为“恶意犯规”,可能面临被罚出场的后果。当然,如先所述,犯规是竞技体育的组成部分,绝对禁止任何犯规行为是不可能的,如果犯规违反的是为保证竞赛公平竞争类的规则,行为人主观上虽有一定的过失,但属于活动本身能够容忍的犯规,则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超出活动本身可容忍范围,受害人通常不会预料到的犯规行为,则应被视为故意或重大过失,比如拳击比赛时咬人耳朵、对无球队员的恶意犯规54在有些比赛中,可能会基于特殊战术考虑而有意犯规,如BNA 比赛中为争取比赛时间而对对方罚篮不准的球员的有意犯规等。当然,该类犯规目的在于使对方罚篮,而不在于伤害对方,所以,轻推一下即可实现目的时,不能打人一拳。等。(3)行为人对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否具有预见性。如果已经预料到自己的违规行为可能会给对方造成人身伤害,而不在乎甚至追求这种伤害,即可认定为该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
因为文体活动特点千差万别,不同项目规则不同,对故意和重大过失的具体认定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如拳击、自由搏击等运动,项目本身即是以有效击打对手为获胜标准的,运动员对对手的击打都是有意的,以此认定其为故意,并使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有学者直接认为,“在拳击等体育活动中,其他参加者遵守比赛规则的行为虽构成故意,但不适用该条,而应适用有关受害人同意的规则”。55周晓晨:《论受害人自甘冒险现象的侵权法规制》,载《当代法学》2020年第2 期。个人认为,在以击打对方有效部位得分为标准确定胜负的体育类活动中,应区分作为法律上要否定的主观心理的故意与日常生活中实施合法行为的有意。拳击比赛中的伤害不是拳手或比赛追求的目的,也不是判定比赛胜负的标准。比赛规则严格规定了有效得分区和禁止击打区,选手击打有效得分区域,没有主观恶性,不属于法律上要责难的心理状态,而是应鼓励的行为,不仅能得分从而赢得比赛,对造成的损害也无须承担责任,此损害是最典型的自甘风险规则范围内的损害。而如果选手击打禁止区域,但被裁判认定为无意的,则也应属于自甘风险范畴,而如果是有意的,或者在裁判警告过后仍然不注意的,则应该认定为恶意,属于受法律上责难的心理状态。考虑到我国民法典对受害人同意采取特别规定的模式,在没有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下,作为一项典型的竞技体育活动,不能将其排除在自甘风险范围外,拳击类比赛也不宜认为属于受害人同意情形。
在篮球比赛中,如何认定“故意、重大过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案件的判决中给出了值得肯定的意见,该判决认为,应结合多种因素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第一,判断行为人的具体行为,其针对的对象是篮球还是对方的人身。第二,结合体育运动的种类与特性,篮球比赛中参加者的注意义务应当较为宽松。第三,考虑体育活动举办的规格。第四,体育活动开展的目的等。56参见张某珺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 民终732 号民事判决书。
总之,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认定,应结合不同文体活动的特点。实践中,为对比赛规则有更专业的了解,对违规行为有更准确的定性,应当邀请相关项目的专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或组织专家论证给出咨询意见,在此基础上确定当事人的行为是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抑或是故意等。
七、自甘冒险的法律效果
有关法律效果的争议主要是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后果是其他参加者完全不承担责任还是减轻责任,有无与有过失的适用空间。许多学者认为在受害人自愿或自甘风险的情况下,不能一律认定构成自甘冒险就不承担责任,需要依具体情况而定,这样既可以导致免责的后果,也可以导致减责的后果。其主要理由有:采用比较过失符合比较法的发展趋势,需要判断受害人的过错程度决定责任承担,加害人过错程度难以判断,有利于法官根据实际情况平衡当事人利益。57参见王利明:《论受害人自甘冒险》,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2 期;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 页;李鼎:《论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与过失相抵、受害人同意的关系》,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1 期。其实,上述观点都是建立在广义的自甘冒险概念基础上的,是将文体活动之外的许多风险性活动都纳入自甘冒险的适用范围,如乘坐醉酒者驾驶的机动车、未经许可进入危险区域、医疗侵权、非法活动等。在广义的自甘冒险体系下,自甘冒险被认定为受害人的一种过错,适用过失相抵而作为减责或免责事由,有其逻辑性。如前所述,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第1款将自甘冒险的适用范围限定于“文体活动”的情况下,自甘风险是独立的责任抗辩事由,在此情况下无法将上述各种危险性活动包含在内,相关活动应通过过失相抵、受害人同意等其他减、免责制度解决。
“风险”是因不能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过失而引起的意外事故,因风险实现而产生的损害,由受害人承受具有合理性。根据该条规定,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后果是“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只能解释为免责,而不涉及“减责”问题。而在“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前句所谓“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是被“除外”的,意味着在行为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不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如此,即便是在文体活动中,如果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心理推动下实施侵害行为,也应适用一般侵权责任规则,在受害人也有过错的情况下,当然也就有了过失相抵的适用空间。
另外,本文没有讨论第1176条第2款组织者的责任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损害是因为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则不属于自甘风险规则调整范围,组织者也不能以受害人自甘风险为抗辩,但如果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过错,自然也可以适用过失相抵规则。
在自甘风险规则适用情形中,有无公平责任适用空间?在《民法典》颁布前,较多的自甘冒险案件同时适用公平责任,认定加害人无过错的同时判决其与受害人分担损失。在《民法典》第1186条修改了原《侵权责任法》公平责任的规定后,因为有“依照法律的规定”的限制要件,而第1176条又没有关于双方公平分担损失的规定,可见现行的自甘冒险规则没有公平责任的适用余地。所以,在“自甘风险第一案”中,法院针对当事人提出适用公平责任,要求其他参加者分担损失时,法院明确回应:公平责任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适用范围应受到严格限制,否则容易导致滥用,影响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应有规范功能的发挥。在该案中,根据查明情况,难谓双方当事人均无任何过失,且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损益情况等因素,该案并不存在适用公平责任之情形。58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 民终2688 号。
综上,作为我国法上一项新的制度,自甘风险是一项独立的法定免责事由,在其规则范围内,并无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以及公平责任适用空间,在参加文体活动时,在自甘风险范围之外,受害人有过错,才可能适用过失相抵以减轻行为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