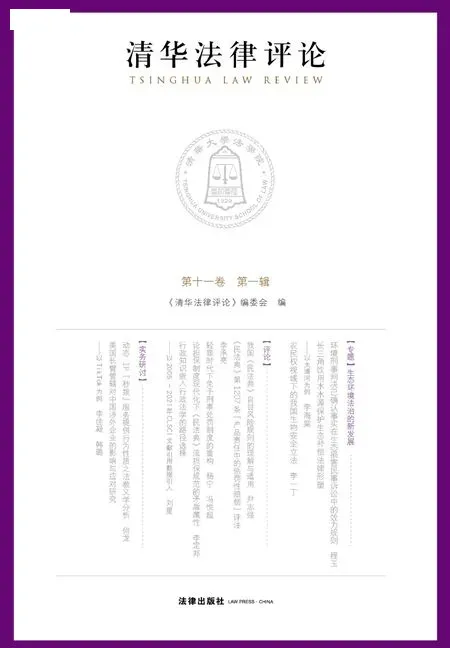长三角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形塑
——以太浦河为例
李海棠
目 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三、长三角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困境
四、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完善——以太浦河为例
五、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长三角水源水质改善有目共睹,但随着上海从太浦河取水规模和供水覆盖范围大幅扩大,导致长三角下游水源安全高度依赖上游来水。由于长三角地区跨界流域污染、沿江工业产业聚集等问题,对水源地安全带来极大隐患。造成长三角流域跨界饮用水治理困境的原因之一,在于跨界流域上下游对河流的定位不同、诉求各异,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虽然有关长三角饮用水水源保护的法律制度散见于各项法律法规中,但缺乏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的专门规定,致使长三角跨界流域水质未得到有效改善,水源地富营养化特征明显。例如,太浦河是长三角地区涉及沪、浙、苏一市两省的典型跨界河流,其所流经的上海青浦、浙江嘉善、江苏吴江同时也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所属区域。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重要骨干河道,太浦河既是吴江等地的主要泄洪通道,也是青浦、嘉善等下游地区的主要饮用水水源地之一,①参见甘月云等:《太浦河水质预警联动方案实践与思考》,载《中国水利》2019年第11 期。对长三角区域意义重大。但由于流域上、下游产业发展及功能定位不同,导致上、下游之间在太浦河流域保护与利用方面诉求各异。②参见杨梦杰等:《博弈视角下跨界河流水资源保护协作机制——以太湖流域太浦河为例》,载《自然资源学报》2019年第6 期。
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利用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的结合引导长三角饮用水水源的合理配置,平衡上、下游地区的权利义务,改善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水量状况。长三角地区目前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与实践主要集中于政府补偿,对市场和社会等多元化生态补偿探索较少,跨界流域饮用水水源生态保护补偿效果不显著。《长江保护法》(2020)作为首部流域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三角饮用水水源保护法律制度“碎片化”的窘境,规定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并将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作为补偿方式之一,但规定较笼统、缺乏实施细则,有关跨界饮用水生态补偿的规定未纳入法律责任体系。因此,亟须建立完善的长三角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2020年11月公布的《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公开征求意见稿)》,将“重要水源地补偿”作为水流补偿的内容之一;2021年1月公布的《上海“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共护太浦河、长江口等重要饮用水水源生态安全”“推动重点跨界河湖联保”;2021年9月发布的《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针对江河源头、重要水源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及“开展生态保护补偿、重要流域相关法律法规立法研究”等,以上法规政策文件的出台均为长三角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完善带来机遇。本文主要探讨如何通过法律规范化调整,激发社会资本、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以及如何在法律层面合理分配跨界流域饮用水水源保护各参与主体对水资源的增值受益。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国际生态补偿也叫“生态服务付费”(PES),指环境服务“购买者”自愿购买特定环境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环境服务,以有效填补其他政策空白。③参见朱桂香:《国外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载《中州学刊》2008年第5 期。国际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相对成熟,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纽约与流域上游农民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供水协议,购买上游生态环境服务并取得成功;④See Pollans M.J,“Drinking water protection and agricultural exceptionalism”,Ohio St.LJ 77,2016,p.1195.澳大利亚将流域生态补偿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治理成效显著;⑤Banerjee O & Bark R,“Incentives for ecosystem service supply in Australia's Murray-Darling Basi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29,2013,p.544-556.哥斯达黎加采用立法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生态效益补贴。⑥Steed B C,“Government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Lessons from Costa Rica”,J.Land,Use &Envtl.L 23,2007,p.177.以上各国均以生态补偿法律调控保障其流域水质及饮用水安全。
从国内来看,跨省界流域保护的外溢特征对传统的属地管理体制提出严峻挑战,⑦参见王彬辉:《从碎片化到整体性:长江流域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的立法建议》,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 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作为调整主体之间社会关系的有效工具,⑧参见曹明德:《对建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再思考》,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 期。可以平衡流域上、下游行政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⑨参见杜纯布:《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载《中州学刊》2018年第12 期。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包括政府、生态利益减损者、生态受益者、企事业单位和个人,⑩参见史玉成:《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与立法供给——以生态利益保护与衡平为视角》,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4 期。补偿标准指生态补偿范围界定后所进行的生态补偿额度的核算。⑪参见肖爱:《流域生态补偿关系的法律调整:深层困境与突围》,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7 期。同时,还需建构生态补偿制度的权利义务体系、⑫参见银晓丹、穆怀中:《饮用水源保护区法律制度完善研究——以辽宁省大伙房水库为例》,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 期。生成生态补偿权利的法律样态及法律准则,⑬参见杜群、车东晟:《新时代生态补偿权利的生成及其实现——以环境资源开发利用限制为分析进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2 期。监督受偿主体不产生污染水体的行为,并建立涉水产权生态补偿制度。⑭DU Q &CHE D S,“The gener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rights in the new era:based on the limit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Law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5,2019,p.43-58.综合来看,我国在长三角流域生态补偿方面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但仍有不足:一是缺乏对跨界流域生态补偿基础理论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二是生态补偿视角下跨界流域保护法律法规基础薄弱,适用性和操作性有待提高。三是缺乏完善的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生态环境权益交易流转体系未建立,难以调动相关方积极性。因此,长三角流域生态补偿应从权利义务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涉水产权法定、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予以法律确认。
(二)理论分析
1.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价值
第一,保障环境正义的合理配置。正义是法的最高序列的价值。正义应遵循两项基本原则,即权利分配的“平等”和责任分担的“差别”,⑮参见李海棠:《新形势下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巴黎协定〉为视角》,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3 期。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强调“最弱势利益最大化”为目标,⑯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4 页。为生态补偿制度的建构和实践发展提供正义价值的理论支撑。法律上的正义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基本权利和义务或者利益的分配。跨界流域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的正义价值,就是按照“谁保护,谁收益”“谁受益,谁补偿”的准则,对为跨界流域饮用水的保护和改善付出成本或者增加支出的“保护者”,按照特定标准和方式进行补偿,以弥补其损失,并激励更多主体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行动中。也即,正义价值是要明确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基于环境正义的需要,在对长三角地区特定民众财产权和发展权予以限制并公平补偿时,法律能够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1)限制和补偿同步进行。为保障长三角地区的饮用水环境质量和生态平衡,一般会对位于上游江苏吴江等地的经济发展权和财产权予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对超标排放的一些纺织厂和印刷厂等产业的关停等。但同时,作为获得了达标水质的下游浙江嘉善和上海青浦,在法律法规约束的范围内,应对上游的损失予以补偿。这也是流域上下游政府之间利用市场机制对跨界饮用水资源进行更加合理配置的表现。⑰参见王勇:《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型协调机制:策略及评价》,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4 期。(2)保障补偿请求权有效实现。例如,针对长三角地区,需明确提出生态补偿具体实施方案,尽可能在较短时间内给与财产权和发展权受限制的民众合理补偿,同时对于已经受损的生态环境予以及时修复或恢复。(3)确定有利的补偿方式。法律有助于当事人选择最有利的补偿方式。任何限制必须于法有据,且必须辅之以合理补偿。补偿方式也应得到足够关切,相对如何核算自己的补偿数额而言,生态服务提供者更加关注能够通过何种方式得到补偿。
第二,保障稀缺利益的公平分配。利益是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客观对象,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民众,需求也不同。利益的获得前提是收益大于成本。但这里的收益,不仅限于经济收益,还包含社会、环境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不仅是个人收益,还包括人类整体的利益。那些能给个人和集团带来利益,但会使社会总利益减少的生产活动,不符合生态补偿法律价值。自然资源总量的稀缺性和人类利用资源的无序性,导致人们需要对其进行重新配置,反映到利益层面就表现为利益分配的公平正义。太浦河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规制,是对太浦河上下游地区发展权和取水权进行利益分配。但是利益分配的公平,需要借助法律制度才能得以实现。法律在利益公平分配方面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指导分配的正义原则法治化,甚至可以具体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稀缺利益分配的法律表现是为具体的权利义务设置一定的标准。二是通过法律衡量不同利益价值以有效保障利益分配。当不同级别的利益或需求发生冲突时,按照法律参照程度的不同,法律需要在不同级别的利益之间进行选择,势必造成某些权益的特别牺牲,此时需要对这种限制所造成的损失予以合理补偿,这种合理补偿也是达到利益合理分配的一种形式。⑱参见王清军:《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度研究》,载《环境法评论》2019年第2 期。
第三,保障激励功能的有效实现。激励,可以引导人们按照对社会、经济、环境发展有益的方式调整自己的行为,同时也成为目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影响下相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关键机制。跨界流域饮用水生态补偿制度注重上游和下游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上游由于对土地利用和生产方式等进行了限制,积极从事生态保护活动,因而有权获得一定补偿;一旦未能从事生态保护活动,造成下游地区水生态环境的破坏或污染,使下游地区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一定限制,则需对下游地区实施补偿。跨界流域饮用水生态补偿制度激励功能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体现能动激励的基本要求。生态补偿请求权的立法确认,将改变保护者在生态补偿实践中长期的被动地位,并督促其从自身利益需求出发,实现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积极调整自然资源利用类型和产业发展,在保障相应生态服务供给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满足。二是体现了互动激励基本要求。长期以来,生态补偿保护者和受益者互动关系不畅的原因在于两者之间缺少互动平台,导致保护者缺少生态服务供给的内在激励。而生态补偿请求权,通过向具体的受益者或代理人提起请求权,以启动相应的法律关系,从而改变了生态服务供给不足的现状。保护者因权利行使而获得一定利益的可能性,受益者因一定的支付行为而要求保护者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双方权利义务通过相互博弈和讨价还价而逐渐明晰。
2.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正当性
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归根结底主要在于流域上、下游的诉求不同。作为流域上游,发展是第一要务,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或者过度使用流经本辖区的水域。但作为流域下游,可能该河流是其赖以生存的饮用水源,对其水质和水量均提出更高要求。为使流域上、下游利益均能合理受到保护,跨界、跨区域生态补偿是比较合理的方式之一。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础理论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正当性,而这一命题又可以分解成两个子命题:生态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和生态补偿制度的有效性。
第一,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大多数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公共物品特性,由于缺少奖励投资机制,使其同时受到过度消费和生产不足的影响。⑲See Ruhl J B,Kraft S E &Lant C L,The Law and Policy of Ecosystem Services,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13,p.87.因此,商品和服务受益人或购买者没有动力向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者支付对价,因为一个人采取的行动或承担的成本将使其利益受损,从而导致主动或尝试“搭便车”的行动。反之,提供者也没有动力提供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因为这样做并没有得到回报。以上就是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外部性”。外部性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一种特定活动的生产者或消费者不承担全部污染成本或其他形式的环境退化的情况,即为负外部性。流域饮用水水源破坏就是负外部性的典型例子。而正外部性是指“对公共物品的保护,不能得到充分的收益或报酬”。例如,流域提供了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气候稳定、饮用水水源、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等。由于缺乏产权或其他法律手段要求支付所提供的服务,市场通常无法为这些服务支付报酬。因此,政府介入纠正了这些“市场失灵”,并确保这些公共物品的供应。当环境负外部性存在的时候,就会导致市场价格失真,最后造成市场经济的无效率。
对于环境负外部性的应对之策,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机制。一是市场机制。即,创造一个生态服务市场。而这个市场被尝试建构以后,因为生态要素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有限性,并没有体现出市场应有的竞争性,价格也往往不受供需关系调整。所有权是一个抽象人造法律概念,其边界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发展而变化。目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就是界定生态服务所有权,包括流域、空气等生态自净系统,如果这些生态要素的所有权无法明确界定,或者界定出来了并不实现其财产权的排他性特征,部分生态服务就无法成为独立的财产,也不能实现有效率的流通。二是政府机制。解决跨界流域饮用水水源保护的传统模式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管理,虽然具有强制性也易于管理,但缺乏可持续性和市场活力。常见的政府管制方式有:设计标准或者技术规范;排放限额;环境质量或者基于危害的标准;产品禁令或者使用限制;计划或规划;信息公开;等等。⑳参见胡静:《环境法的制度工具》,载《经济师》2008年第1 期。同时,税收工具虽然是利用价值机制实现对负外部性行为的管控,但因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也可纳入广义上的行政工具。整体而言,这些行政工具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将环境负外部性内部化。例如,政府设置排放限额,对流域污染物排放进行管控。三是司法机制。“生态补偿”是否包含“生态赔偿”学术界一直有争议。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补偿”应包括“生态恢复型补偿”和“生态损益型补偿”,㉑参见郭武、张翰林:《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生态补偿的适用甄别——以流域生态保护为视角》,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 期。而后者与“生态损害赔偿”类似,所以“生态赔偿”应属于“生态补偿”的范围,而“生态赔偿”是对过错违法行为承担的法律责任,㉒参见吕忠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辨析》,载《法学论坛》2017年第3 期。属于通过司法机制解决流域生态服务外部性的问题。但也有部分学者将“生态补偿”和“生态赔偿”作为两个概念予以界定,并认为合法行为可以或者必须(取决于对补偿性质的理解)予以补偿,违法行为必须予以赔偿。虽然学术界对于“生态补偿”的法律内涵仍未达成统一定论,但是根据《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生态补偿指“生态保护补偿”,并不包括“生态损害赔偿”,后者主要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规制,属于过错违法行为后的法律责任。
第二,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之有效性。以政府为主的生态补偿主要以庇古理论为依据,以市场为主的生态补偿以科斯理论为依据。而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正是跨界流域饮用水水源保护的核心内容。
首先,以科斯定理为理论基础的生态补偿。科斯认为环境负外部性是由于行为权利和利益边界无法界定,其根本原因是产权界定不清晰。所以,要解决环境负外部性首先要明确产权,㉓参见黄飞雪:《生态补偿的科斯与庇古手段效率分析——以园林与绿地资源为例》,载《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3 期。具体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产权明晰的自然资源。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在于其中凝结了人类无差别的劳动,有的生态服务作为商品并没有凝结人的劳动,而仅是因其具有稀缺性。生态服务作为商品必须排他且相互不重合,这要求一种生态要素所能提供的生态服务不会影响其他生态服务,例如,某一流域的水资源具有自我净化的功能,可以认定水源的所有者应界定为生态服务的提供者,但如果该水系强烈依赖河岸的森林或土地利用体系以维持该水系的自净化功能,那么水系自净化的生态服务商品将会非常依赖于森林或土地体系的其他生态服务。因此,某种生态服务效用的独立性会受到极大限制而难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中流通,因为购买者的风险将大大增加。二是需要交易成本足够低。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很多,例如信息不对称。生态服务交易中信息的获取应当便利且双方对称。哈耶克认为,市场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更是信息流通的工具。市场的繁荣不仅是商品快速流通的表现,也伴随着信息的高速扩散和协商机制的高度发达。一些市场无法有效运转也可归咎于信息获取的成本过高。而在市场化生态补偿中,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导致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交易。三是司法救济工具对于生态补偿制度所予以的配套支撑较为薄弱。科斯指出,如果产权明晰、交易成本足够低,市场可以自我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并认为侵权法本身也有实现这种功能的可行性。在此论断中,可以看出科斯对司法功能的重视。可将司法审判视为科斯定律的一种代替方法,因为司法工具往往是最后救济的一道保障。但现行生态补偿制度中,无法将生态补偿行为纳入侵权法体系并予以救济(美国司法系统有所尝试,但成本太高且效果不好),所以一旦生态服务付费项目合同无法履行,则往往无法通过司法来实现功能替代。这也是目前亟须解决的司法技术问题。
其次,以庇古税为理论基础的生态补偿。庇古税是对某种产生负外部性的市场行为予以征收税费的税种之一。该税种对负外部性行为设置等同于其社会成本的税率,目的在于矫正市场非效率资源配置。庇古认为外部性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实现矫正。这种干预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针对正外部性行为予以补贴,另一种则针对负外部性行为处以成本增加。从而实现外部性生产者的私人成本等于或大于其所在社会的公共成本,最后实现整体社会福利的提升。但庇古税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西方经济学界存在一个争议:如何给外部性行为制定一个合理的税率。在生态补偿实践中,如何对一部分行为课税,进而影响到行为者成本,通常会受诸多因素影响,所以庇古税的征收通常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庇古税相较于科斯的市场方法,需要更多的行政权来行使,其成本也是其一大局限性。
最后,庇古型和科斯型相融合的生态补偿。如前所述,政府型生态补偿和市场型生态补偿各有不足,但是二者并不是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的关系,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高效融合。政府型生态补偿,主要通过规范性的规章制度,也称为命令与控制,实现环境保护的最普遍和广泛使用的机制。简单来说,它设定了一个目标,并规定了为实现该目标而必须采取的、允许的和禁止的行动,并对违规行为处以罚款。由于受监管的社区平均承担着负担,因此该机制不如基于市场的机制灵活。在这种机制下,通常用于处理环境污染的两种方法是基于技术的统一标准和基于性能的标准。虽然基于技术的标准要求使用特定的技术,但是基于性能的标准设定了特定的目标,但未指定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庇古型生态补偿与科斯型生态补偿二者单独都有不足,但二者的结合正是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价值追求,既考虑社会公平分配,也考虑市场性福利和非市场性福利的全面提高。单一的不依赖政府的市场手段无法实现多元化生态补偿的价值追求,需要政府机制、社会机制等进行补充和完善。
三、长三角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困境
(一)长三角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法规概览
目前,虽然我国还未形成专门的生态补偿立法,但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均有所涉及,并已逐渐成为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一,环境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保护法(2014 修订)》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环境保护法》将生态补偿制度确定为我国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制度,对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和制度体系建设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有关流域饮用水生态补偿制度在一些生态环境保护单行法中也有所涉及,例如《水污染防治法(2017 修正)》第8条,《水法(2016 修正)》第29条、第31条、第35条、第38条,《水土保持法(2010)》第31条、《防洪法(2016 修正)》第32条、《渔业法(2013)》第28条等都对生态补偿均有原则性规定,各单行法从不同的保护利用目标出发,大多规定对开发利用水资源行为征收费用或对水资源保护行为予以补偿,为长三角地区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提供上位法支持。
第二,行政法规中的相关规定。《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首部以“生态保护补偿”命名并作为立法追求的行政法规,是生态保护补偿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条例》规定了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相结合生态补偿方式。就上海市流域生态补偿而言,太浦河作为沟通太湖和黄浦江的人工河道,是上海的重要饮用水源,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跨界河流。《太湖流域管理条例(2011)》第14条、第17条、第18条分别规定太湖流域管理机构可对太浦河下达调度指令、制订取水计划等。同时,第49条还对流域双向补偿作出明确规定,全国首例“协议水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便以此为依据。
第三,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中的相关规定。长三角地区一市三省在流域生态补偿领域的地方立法方面也作了有益尝试。上海早在2009年就发布了《关于本市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若干意见》,开始针对基本农田、公益林、水源地和湿地开展生态补偿实践,江苏、浙江、安徽均在2017年颁布了省内流域生态补偿办法或方案,为各自省内生态补偿实践提供地方性法规依据。同时,长三角一市三省也分别制定了各自省市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地方性法规,其中上海、浙江、安徽分别专门规定了针对本省(市)内的以财政支付为主要手段的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从目前的立法现状来看,我国对流域及饮用水生态补偿主要采取分散立法的模式,相关条文散见于《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法律中。由于各部门立法侧重点不同,难免造成部门之间关于流域及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方式、法律责任承担等方面的冲突。《太湖流域管理条例》作为长三角地区流域生态补偿的重要依据,第44条、第49条明确规定了流域生态补偿的主要制度。但是,该法只是从宏观上对太湖流域生态补偿作出规定,具体的补偿标准、补偿方式、法律责任承担等方面都缺乏细化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导致生态补偿执法难以进行、流域及水源地安全隐患亦逐步显现。而沪、浙、苏、皖四地虽然在各自省市的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中,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流域或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制度,但主要以政府补偿为主,对于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等规定较为笼统,而且也缺乏对跨省界流域或者饮用水水源保护的法律规范。因此,亟须完善长三角流域饮用水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二)长三角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现实困境
第一,基于水质交易的模式——以“新安江流域为例”。新安江的上下游分别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对于安徽而言,新安江是其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对于下游浙江而言,新安江是其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备用水源地。㉔参见乐天中:《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政策探究》,载《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9年第8 期。为加强新安江流域的生态治理,2012年启动了全国首个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过前三轮试点,新安江已基本探索出政府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模式,并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多赢。
“新安江协议”将“水质”保护目标作为唯一构成要件和考核依据,构建了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虽然这种双向可逆的生态补偿责任制度,可以激发流域上下游各区段的水污染治理与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性,但从法律角度考虑,“新安江协议”还有几点值得商榷:首先,“协议”的法律属性未明确。有观点认为,由于协议方均为省级政府,其形成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适用行政法调整或者运用行政救济解决争议㉕参见杜群、陈真亮:《论流域生态补偿“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基于水质目标的法律分析》,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 期。;还有观点认为,由于流域生态补偿体现了生态利益的再分配,其本质是民法中关于自然资源的物权处分关系,应适用民法或者民事救济来解决争议。㉖参见潘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本质:民事财产权关系》,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 期。其次,协议主体未明确。我国《环境保护法(2014 修订)》第31条规定生态补偿受益方地方政府和保护方地方政府之间有通过协商确定具体生态补偿方案的权力,但未明确规定进行协商的适格主体应为哪一级政府,因此安徽和浙江省政府进行协商在法律上是否为适格主体,仍然存疑。最后,违约责任未落实。尽管“新安江协议”对水质不达标时安徽省政府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但是对于补偿资金不能合理使用时,应当如何救济并没有明确规定。㉗参见陈璐:《政府间环境保护契约制度研究——以“新安江协议”为例》,重庆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9 页。
第二,基于异地开发的模式——以“浙江金华—磐安为例”。浙江省磐安县地处天台山,是浙江的生态高地、经济洼地。为保护磐安县饮用水水源地,金华市出让磐安开发区,促进了磐安县经济发展,也推动了磐安县生态环境保护。上游的磐安县水体不受污染,下游就能享受清洁的水源。㉘参见陈坤:《长三角跨界水污染防治法律协调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132 页。“金磐模式”采用异地开发模式,给重要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敏感脆弱区提供了异地发展的空间和区域,帮助为保护生态而发展受限的地方政府实现“造血式”的生态补偿,促进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该种模式类似于国外的“区域土地发展权流转”制度,该制度有助于缓解分歧,使单纯的土地用途管制更加公平和高效。赋予区域政府可流转的土地发展权实质上是使用土地用途管制对包括流域在内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土地开发利用的限制来创建一个人为的开发权市场。区域土地发展权流转是许多基于市场的工具之一,用于保护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基于市场的机制,由于其成本效益和刺激创造力及创新的能力而赢得了许多环境决策者的青睐。
但是,该种异地开发生态补偿模式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法律困境:一是由于生态补偿立法阙如,导致在诸多异地开发生态补偿中,经济开发与生态补偿利益关系未明晰,一定程度上阻碍制度的实施。例如,在开发过程中导致生态损害或者环境侵权,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以及责任划分界限不清,难以通过法律程序保障权利的实现。二是资金及过程监管存在一定风险,异地开发生态补偿同时属于生态扶贫的创新模式,地方政府可能会过于强调对生态产业的培育,而缺少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深入关注,需要法律法规予以制度化的约束。同时,对于补偿资金的支付与保管,也应有法律监督保障,以使生态补偿落到实处。
第三,基于水权交易的模式——以“浙江东阳—义乌为例”。浙江东阳市作为金华江上游,水资源相对丰富,供水能力强,不仅能满足东阳市正常用水,还有3000 多万吨水富余。作为下游的义乌市水资源相对紧缺,市区供水能力每天只有9 万吨,不能满足义乌经济发展需求。因此,东阳市政府与义乌市政府双方约定,东阳市政府每年向义乌市提供5000 万立方米的饮用水,义乌市政府向东阳市政府一次性支付2 亿元。
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作为全国首例曾受到广泛关注,因为该案开创了我国水权交易制度的先河,㉙参见胡鞍钢、王亚华:《从东阳—义乌水权交易看我国水分配体制改革》,载《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20 期。但也随之引发一些争论。首先,地方政府是否有权对水资源进行交易?根据《宪法》(2018 修正)和《水法》(2016 修正),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东阳市并不享有水权,所以它不能进行水权的转让,东阳市不拥有水资源所有权,更不是水资源所有权的转让主体。㉚参见崔建远:《水权转让的法律分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 期。此外,在权属不清的背景下,政府推进的水权交易可能会损害相关利益人的权益。譬如,水权交易由于扩大用水总量会损害水资源体系,水权交易会损害水源地居民的利益。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并不能使水源地附近的农民直接受益,反而会影响其基本生存和经济发展。近年来,虽然水权交易的种类有所扩充,包括区域水权交易、取水权交易、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等,但是水权市场的完全建立仍受制于诸多实践难题和法律障碍。
(三)长三角饮用水水源保护法律困境之原因分析
第一,法律治理不足,多依赖政策驱动。长三角流域饮用水生态保护补偿,和国内诸多生态补偿实践类似,大多是以“补偿项目”为形式、以政府财政补偿为主要支付手段、以资金流转平衡区域间的生态保护利益为目的的“自上而下”型“输血式”生态补偿。项目制虽能协调与整合复杂的利益关系,丰富补偿资金来源,形成流域生态补偿的治理合力,在一定程度上对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因其具有临时性和碎片性,㉛参见史普原、李晨行:《从碎片到统合:项目制治理中的条块关系》,载《社会科学》2021年第7 期。导致很难从法律层面对生态补偿利益相关方进行规制和调控,具有临时性和碎片性,并面临诸多问题:首先,制定主体不同,补偿基准各异。例如,浙江省生态补偿指标以“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等作为主要指标”,㉜浙江省财政厅等四部门2017年发布的《关于建立省内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规定“各地可选取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以及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流量、泥沙等监测指标,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其中部分指标”。安徽省生态补偿指标包括“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和总磷”三项。㉝安徽省政府发布的《安徽省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暂行办法》(皖政办秘〔2017〕343 号)中规定“断面污染赔付因子共三项,包括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和总磷”。江苏省生态补偿根据不同断面的水质和水量情况规定了差别补偿标准。㉞江苏省在2017年落实《江苏省水环境区域补偿工作方案》过程中,进一步规定:“差别补偿标准,区分断面水质浓度和排放量,设定不同补偿标准;适时提高补偿标准,更大程度地发挥水环境区域补偿制度创新优势和财政投入的环境效益。”以上三省市在补偿标准方面各不相同且没有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难以实现长三角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制度的一体化建设。此外,三省市在生态补偿方式、补偿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和监管等方面也规定各异。同时,由于三省市有关饮用水水源保护的生态补偿制度主要体现在政府补偿方面,而各省市财政、人事、法规政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也导致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的难以协调性。
此外,虽然生态补偿政策较之法律制度更具灵活性,但政策本身的不稳定性及缺乏约束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生态补偿制度的长效性。有些生态补偿实践以一定时限内的“生态补偿项目”为依托,一旦项目不再继续,生态补偿资金的有序发放也将停止,影响生态补偿制度的连续性。例如,新安江流域水质交易目前进行到第三轮试点,每一轮试点的资金来源和金额均不相同,导致生态补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欠佳。2021年9月发布的《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也提出,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生态补偿实践出台相关法规规章,以进一步明确生态保护补偿法律关系中的各方权利义务。因此,需要适时将较为成熟的生态补偿实践加以提炼,㉟参见王清军:《法政策学视角下的生态保护补偿立法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4 期。并在条件成熟之时将生态补偿政策“法律法规化”,形成确定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相对稳定的法律法规体系。㊱参见陈海嵩:《生态环境政党法治的生成及其规范化》,载《法学》2019年第5 期。
第二,产权制度缺失,补偿主体识别难。在经济学中,产权明晰是交易的前提。只有水权界定清晰,才能将流域污染外部成本内部化,才能使流域水环境的保护者与受益者,有较强的动机维护自身利益。水质资产的分配不明确,导致污染物排放权的分配规则不清,同时也使水质产权的污染者、受益者责任不清。同时,也使市场化生态补偿方式难以推广。㊲参见曹明德:《对建立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思考》,载《法学》2004年第3 期。由于水质产权界定不清晰,导致上下游水权交易很难达成共识,容易使上下游之间相互推卸责任,使上游的发展权和下游的用水权之间产生矛盾,而且即使关于生态补偿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也会由于水权交易价格难以确定,而使交易无法真正落实。㊳参见胡涛:《中国流域水质管理:生态补偿还是污染赔偿?——基于美国跨界流域水质管理的教训》,载《环境经济研究》2017年第2 期。
法律调控下的市场化生态补偿,以产权明晰为主要实现前提。例如,美国纽约市为保障上游来水水质达到或优于饮用水标准,与上游卡茨基尔斯(Catskills)流域签订流域协议备忘录,投入14 亿美元对上游水源地附近农民的生产方式和土地利用类型进行改造,上游水质经过数年改造,常年保持较优,符合纽约市的饮用水标准,同时也节省了46 亿美元建造过滤设施的费用。该案的成功之处在于,纽约市政府直接与饮用水水源地土地权人进行交易,购买其未开发的土地和保育地权,使水源地附近土地使用者直接受益,使其改变土地利用结构的积极性更高,生态补偿效果更显著。㊴Mark D.Hoffer,“The New York City Watershed Memorandum of Agreement:Forging a Partnership to Protect Water Quality”,University of Baltimor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18,2011,p.113.反观东阳—义务水权交易案,该案的交易主体是两个地方政府,虽然二者代表国家对区域内的居民用水实行管理权能,但是对于水资源的真正使用者——东阳市居民而言,水资源权益并没有被充分考虑。水权交易的收益也并没有真正使水源地农民获益,从而遭到东阳市水源地附近农民的抵触,使得其并没有通过改变种植结构的方式节约用水,㊵参见王慧:《水权交易的理论重塑与规则重构》,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 期。不仅影响了水权交易的进一步落实,而且使生态补偿效果大打折扣。虽然我国居民个人不享有水资源所有权,但水资源产权个体同样对水资源享有用益物权,可以对其进行占有、使用和处分。因此,水资源用益物权可以构成水资源产权的核心内容。
四、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完善——以太浦河为例
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需各级地方政府间在整体观和大局观的意识形态下,协商一致、互利共赢,而缺乏法律保障的府际协商机制,很难在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因此,界定跨界流域生态补偿的权利义务主体、法律标准和法律方式等生态补偿权利生成与基本构造以及设立跨界流域生态补偿行政管理机构、明确涉水产权法定、健全纠纷解决机制等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包括太浦河在内的诸多跨界流域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重要考量。
(一)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权利生成与基本构造
1.确定跨界流域饮用水生态补偿的权利义务主体
权利决定义务,是证成义务主体及其义务的基础。㊶MacCormick N.,“Children's rights:A test-case for theories of right”,ARSP:Archiv für Rechts-und Sozialphilosophie/Archives for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al Philosophy,1976,p.305-317.跨界流域生态补偿请求权,指跨界流域受损主体向受益主体提出利益补偿主张或请求的资格。㊷参见陈婉玲:《区际利益补偿权利生成与基本构造》,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6 期。太浦河流域生态补偿的权利主体(受损主体),指在太浦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过程中有贡献或者受到一定损失,并且有权请求生态补偿的主体。一是对太浦河水环境改善作出贡献的主体。主要包括流域内环境保护的管理者、水源地生态安全的实施者。例如,为保护太浦河流域生态安全,势必会关停太浦河上游江苏吴江地区部分有污染的企业,上海、浙江作为下游地区得到干净饮用水源的同时应对流域上游财产权和发展受限的当地企业、居民和政府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合理补偿。二是太浦河流域环境污染受害者。例如,太浦河流域的上游吴江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其发展权,不仅对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也严重影响了下游地区公平享用太浦河流域水环境的权利。因此,上游地区也应为自己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负责,对下游地区进行补偿。
太浦河流域生态补偿的义务主体,包括由于太浦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而受益的群体或区域,也即环境效益的获益方。根据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由于流域和饮用水水源保护而获益的主体,应当对为保护水环境而牺牲一定发展权的主体予以补偿。对于“获益”的理解,应取广义,包括基本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以及生态价值、美学价值和娱乐价值等的提升,具体主体包括以下几类:㊸参见李小强、史玉成:《生态补偿的概念辨析与制度建设进路——以生态利益的类型化为视角》,载《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 期。一是中央政府。根据《宪法》第9条,“水流”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国家成为该自然资源的“代管人”。当整个流域的水质、水量、水能等自然资源属性及其生态、美学、娱乐价值有所提升时,国家也是“受益者”。㊹参见邵莉莉:《跨界流域生态系统利益补偿法律机制的构建——以区域协同治理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1 期。因此,中央政府理应成为跨界流域生态补偿的义务主体,应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履行生态补偿义务。同时,长三角地区各省市生态补偿政策和标准不尽相同,而中央政府作为三省市的直接上级政府可以通过财政、人事等方面的统筹协调,对太浦河流域各级地方政府进行指挥和安排。二是太浦河流域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流域或饮用水治理最适宜的主体,可以“让最了解流域及其管理的主体参与决策,以采用最有效的流域及饮用水保护策略”。㊺HirokawaK H,“Driving local governments to watershed governance”,Environmental Law,2012,p.157-200.正如前文所述,太浦河流域的上、下游政府在发展权和生存权的请求权基础上,均有可能成为跨界流域生态补偿的义务主体。
因此,跨界流域生态补偿的权利义务主体并不是固定不变且一一对应的。上、下游地区在特定的情况下,既是生态补偿权利主体也是义务主体,这也是新安江等流域“双向补偿”的法律基础。因此,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权利义务关系与传统权利义务关系相比更具复杂性,难以通过单纯的司法机制界定法律责任。由于跨界流域上下游主体间更多体现出一种“共同利益”,应当创建一种流域上下游的整体保护义务,在“全局观”和“整体观”的视野下,考虑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并将流域协商机制纳入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法律治理中,基于流域的“共享性”进行相互合作与利益分享。
2.界定跨界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标准
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中,无论补偿权利义务主体的确定、补偿方式的选择,还是补偿责任机制的有效履行,都离不开科学、合理且有效的补偿标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中,补偿权利义务关系主体、补偿资金分配、补偿方式的确立和补偿绩效的评估,也围绕生态补偿标准展开。
首先,确定补偿的法律标准。在太浦河流域生态补偿中,对上游吴江地区的财产权、发展权受限以及下游青浦、嘉善用水权受影响所遭致的实际损失进行补偿是推行公平、合理补偿原则的最低标准。在损失补偿中,损失常被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流域上游地区为了提供符合一定条件的流域生态服务,所投入的各种直接成本的支出。例如,上游吴江地区为保障太浦河水质和水量达到下游饮用水标准,对流域水环境进行恢复和治理所投入的所有支出,或者下游上海青浦为治理由于上游江苏吴江泄洪带来的雨水径流污染所付出的所有支出。间接损失主要是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回应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机会成本的法理依据是无论流域上游地区或下游地区,均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其次,明确标准制定主体。对于长三角地区生态补偿的制定主体可以有两种,一是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在上级共同政府(中央政府或国务院),或者太湖流域管理局的指导下,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各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理人,依据市场原则签署生态补偿协议,该补偿协议所确定的生态补偿标准实际上介于政府标准和市场标准之间,可以称之为准政府标准或准协定标准。二是市场主体。常见的就是流域生态保护受益者与生态保护者通过直接协商,经过邀约、承诺等系列合同签署程序确定的带有一定协定意义的补偿标准。例如,可以通过长三角地区企业与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政府之间签订生态补偿协议或者制定生态补偿标准。因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主体不同,其法律效力也不同。政府直接主导的补偿标准,因其主体享有法定职权,制定的补偿标准即便设定了一定的权利义务,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性效应,对于流域所辖下级政府具有规范效应。市场主体主导的补偿标准是市场主体之间经过协商,签署合同而确立,补偿标准已成为合同(协议)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违反标准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可能构成违约。
最后,标准支付基准和支付方式。依据不同核算方法核算出来的补偿标准需要一定的支付基准条件的涉及。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多采用基于结果的条件支付,具体包括一定的水质或水量结果,例如,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就是以水质、水量的结果为支付基准。太浦河流域生态补偿也可以参照该种支付基准。尽管这种以水质水量指数为支付基准的方式存在一定的不足或者规范化问题,但这会随着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的进步和完善而逐步趋于规范化。另外,标准支付方式,包括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直接方式包括货币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补偿,间接补偿中包括技术补偿、发展权转移等各种方式。货币补偿标准计算更加科学、更加公平;在非现金补偿中,优惠政策更符合可持续发展以及法治环境构建的要求。太浦河流域生态补偿,可以根据水质、水量或者水的利用效率等其他量化要求,将同一补偿标准划分为多种层级,每一层级采用不同的标准。以法定标准为例,可将其划分为最高标准、一般标准和最低标准。不同层级的标准采用不同的标准数额,从而适当拉开差距,彰显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激励或惩罚功能效应。
3.丰富跨界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定方式
长三角地区生态补偿主要以省内政府资金补偿为主。例如,《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2016)》第18条,对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作出明确规定。2014年,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省的“双向补偿”制度,㊻参见江苏省环保厅(现为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对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0520 号提案的答复(关于加快建设江苏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载江苏省人民政府网:http://www.jiangsu.gov.cn/art/2018/7/10/art_59167_7744421.html。2018年,浙江省全省启动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虽然以资金补偿为主的省内横向生态补偿方式已相对成熟,但也存在补偿方式单一,多以政府财政补偿为主的问题,而且对于跨省资金补偿的方式,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因此,对于太浦河流域生态补偿方式应该更加多元化。同时,跨界流域生态补偿应当注重协商原则。即,无论市场主体之间,还是政府主体之间,抑或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在生态补偿的具体实施中,均可根据各利益相关者的具体诉求,综合考虑相关因素,通过协议、磋商的方式达成共识,以实现各方利益均衡。《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还对协议签订、协议内容、协议实施评价和监督等方面予以系统规范。
首先,资金补偿。可以借鉴新安江的补偿模式,建立示范区生态补偿基金,由江苏吴江、上海青浦、浙江嘉善三省市各自按照一定比例出资,再由中央政府给与一定拨款,争取吸引社会化资金加入。同时规定,太浦河通过上游吴江流经下游青浦和嘉善的水质和水量必须达到一定标准。如果达标,可从生态补偿基金中领取一定额度的生态补偿金,如果不达标,则需向示范区生态补偿基金支付一定资金。对于出资比例的确定,可以根据三地为保护太浦河流域水环境所做的努力和牺牲来衡量,上游吴江可能因为关闭高耗能企业导致发展权受限,出资比例可以略低,而下游上海和嘉善相对因此而受益,出资比例可以略高。
其次,生态绿色产业补偿。太浦河上游吴江地区为保障下游地区优质的水源,其传统产业发展势必受影响,除接受资金补偿之外,还可以考虑向生态绿色产业转型,如打造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结合长三角地区发达的古镇文化旅游产业,包括青浦朱家角古镇、嘉善西塘古镇、吴江黎里古镇以及周边的千灯古镇和周庄古镇等,加之京杭大运河也从太浦河经过的独特地理优势,可以结合运河古镇文化,在长三角地区打造运河古镇文化产业新高地。与资金补偿相比,生态绿色产业开发和支持更加可持续,不仅有助于保护和恢复长三角地区水生态环境质量,而且对于受关停企业影响的劳动者,可以直接解决就业和生计问题,实现发展权和财产权的有效补偿。
最后,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生态补偿。市场化生态补偿,并非不依靠政府主体的完全市场化。因为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政府生态补偿仍然占据很大比重,而且从资金规模、补偿力度上来讲,政府补偿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而且政府在制定规则、统筹协调、监督评价市场化生态补偿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市场化生态补偿更具活力,是真正的“造血式”生态补偿,所以二者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太浦河位于长三角地区,依托其发达的经济基础和较快的市场化进程,可逐步探索一对一的生态补偿模式和基于市场的生态标记模式,使流域生态补偿更加灵活,资金来源更丰富。同时,也可借鉴欧盟流域市场投资计划中的具体实践和案例。例如,德国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不断加强,水质在许多水体中逐渐退化,主要由于肥料和其他化学品的过量负荷。因此,德国采取流域市场投资计划,通过改善农业管理做法来保护清洁水质。另外,2002年,西班牙为了恢复流域管理,在其东北部开发生态补偿PPP 项目,建立了公私合作自愿协议。该计划旨在逐步恢复其盆地下部的埃布罗河部分,公共和私人激励措施支持一系列洪水冲击,目的是恢复河流水环境,从而改善河流生态系统的各种功能。㊼Genevieve Bennett,Alessandro Leonardi,Franziska Ruef,“State of European Markets”Watershed Investments,Technical Report[R].2017:19-25.长三角太浦河流域也可引入PPP 机制,促进其生态补偿的市场化发展。
(二)完善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制度
1.设立跨界流域生态补偿行政管理机构
虽然根据《太湖流域管理条例(2011)》,太湖流域管理机构负责太浦河的流域管理工作,并对太浦河下达调度指令、制订取水计划等。近年来,还建立了太浦河水资源保护省际协作机制,提出《太浦河水资源保护省际协作机制——水质预警联动方案》。但是,作为水利部在太湖流域的派出机构,太湖流域管理机构只是一个事业单位,在协调长三角地区流域生态补偿中,其行政权力受到很大限制。而且作为派出机构,如无法律法规规章授权,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在行政诉讼中不能做被告。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0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由于太湖流域管理局行政权力和级别的限制,其不可能在太浦河流域治理中起到关键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考虑设立真正有权力、有灵魂的太浦河流域管理机构。2019年11月,成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该执委会成立两年多来,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在生态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努力和探索,例如正在建立生态环境“三统一”(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执法)制度框架、联保共治工作机制框架、跨界水体生态岸线一体化实施标准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第三方服务平台等,以努力实现标准统一、规则一致、市场一体,并将其成功经验复制到长三角全区域,实现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
此外,可考虑由沪浙苏三个省级单位牵头,会同自然资源部或生态环境部,根据各省在太浦河流域的流经范围或者对各省份的重要程度划分权力,成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流域管理委员会,其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对太浦河流域的管理职责,还包括整个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所有流域和水环境安全管理。例如,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和生态补偿的成功,主要在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成立。流域内的所有规划和建设均由该管理局全面负责,包括流域内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对流域内居民的直接生态补偿等。又如,欧洲莱茵河流域环境治理与生态补偿的成功,也是由于国际委员会(ICPR)对莱茵河流域的跨国管理和协调组织,实施了多项莱茵河环境保护计划。㊾参见王思凯等:《莱茵河流域综合管理和生态修复模式及其启示》,载《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1 期。对于太浦河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和实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也应起到重要管理和协调作用,具体表现在对太浦河流域生态补偿权利义务主体的确定、生态补偿法律标准的界定以及纠纷解决和责任承担等方面,进行宏观把控、积极协调,对长三角地区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行有效监管。
2.明确跨界流域水流或涉水产权法定
产权明晰是市场化生态补偿立法及流域生态补偿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水权作为水资源所有权和各种水权利与义务的行为准则,可以高效配置水资源,同时可以起到激励水资源保护和遏制水资源污染与浪费的功能。欧美发达国家生态补偿(PES)制度起步较早,发展也较为完善,可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提供经验借鉴。例如,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流域治理,㊿参见史璇等:《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流域水管理体制对我国的启示》,载《干旱区研究》2012年第3 期。美国湿地环境银行,51参见柳荻、胡振通、靳乐山:《美国湿地缓解银行实践与中国启示:市场创建和市场运行》,载《中国土地科学》2018年第1期。以及法国水质付费等生态补偿制度对该国跨界流域的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起到重要推动作用。52参见孙宇:《生态保护与修复视域下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2 页。而以上案例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皆因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明确,从而利用市场化生态补偿进行资源保护。
为使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得以顺利开展,水权的清晰界定必不可少。对于水资源统一确权规定,可以分步骤循序推进。首先,权利类型和边界的确定。对于“国家所有”的水资源应当分清是中央所有还是地方政府所有,对于地方政府所有的,应当明确规定所属政府的不同层级。严格来讲,这里的“地方各级政府所有”是“代理行使”所有权。其次,与“不动产产权登记”有机融合。由于自然资源产权更复杂,同一自然资源可能属于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所有。在权利的衔接和数据库的建设方面都存在很大挑战。因此,上海可以在立法和“数字化”化建设方面,率先做出尝试和探索。最后,丰富自然资源使用权权能。推动所有权与使用权等权能的分离,是促进自然资源资产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多元化需求,扩大生态产品的有效和优质供给,发挥生态资源资产多用途属性作用。只有权能丰富完善了,才能实现资源产权交易的顺畅进行,提高产权转移的规模、效率和效果。在坚持全民所有制前提下,以强化资源处分或处置权、保障资源收益或受益权为核心,丰富生态资源资产使用权体系,提高自然资源资产利用效率。例如,可以结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方案》的落地,考虑将太浦河也进行确权登记,规定太浦河的所有权行使方式,国务院可委托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代理行使水资源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太浦河流域水资源确权登记的法治化,将推动建立归属清晰的太浦河流域产权制度,同时对长三角地区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奠定基础。
3.健全跨界流域生态补偿纠纷解决机制
太浦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运行的法治化,不仅在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三地政府间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规范化与程序化,更在于流域上下游政府间因生态补偿而产生的纠纷处理机制的合法化和多元化。因此,健全太浦河流域以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生态补偿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
首先,磋商机制。它是介于行政机制和市场手段之间的机制,53参见陈华东:《区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年版,第77 页。可以针对特定流域的特定情况作出反应,因为该机制可以建立在当地知识的基础上,并制定与当地流域问题相一致的专门政策。此外,流域治理中的磋商机制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地打破竞争利益之间的不可溶性,建立一个信息共享的过程,并召集邻近的司法管辖区来实现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的目标。主要包括生态补偿权利义务主体间自行协商,或者通过非上级行政机构进行协调。跨界水资源流域生态补偿涉及多个省市,多个部门和多重利益体系,需要建立跨界流域生态补偿信息共享平台以及各方生态补偿谈判机制。
其次,行政机制。主要是指对于在生态补偿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可由共同的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调解或裁决。该种方式主要依赖权威而又中立的第三方上级行政机构进行争议的解决,具有一定强制性。在太浦河流域生态补偿中,应由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的共同上级行政机关仲裁解决,可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委托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牵头仲裁补偿方案纠纷,财政部门牵头仲裁补偿资金纠纷,仲裁期间不停止补偿资金划拨。同时,也可建立比三省市行政级别更高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流域管理委员会,通过该机构进行行政调解和裁决。
最后,司法机制。指通过司法审判机关的司法裁判解决生态补偿纠纷。虽然我国法律规定并没有对生态补偿的纠纷解决机制作出直接规定,但是可以借鉴《水污染防治法(2017)》第97条关于生态损害赔偿纠纷解决之规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省级政府之间的流域生态补偿纠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司法解决。另外,也可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之相关规定,54参见《民事诉讼法》(2017 修正案)第55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行政诉讼法》(2017 修正案)第25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检察机关提起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例如,对于由于流域上游行政区域内政府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流域生态环境受到侵害,致使下游地方政府和居民用水权受限的,可以通过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55参见邓纲、许恋天:《我国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法治化路径——面向“合作与博弈”的横向府际治理》,载《行政与法》2018年第4 期。
五、结语
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涉及多部门、多主体、多层次的利益协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最大程度地保障和协调上游发展权和下游生存权的统一。除生态补偿权利生成和基本构造以及具体的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制度外,区域(流域)统一立法,也是重要的解决策略。一方面,《长江保护法》(第一部流域立法)、《黄河保护法》的成功颁布,为长三角流域保护生态补偿立法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另一方面,2023年3月新修改的《立法法》在法律层面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开展协同立法,并增加地方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的规定56《立法法》第83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协同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有关区域内实施。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为长三角地区进一步开展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区域协同立法也将是长三角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和探索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