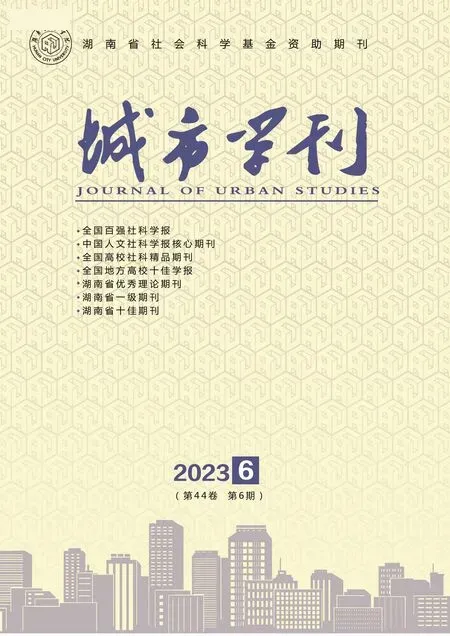情欲与创作的对话──论林白小说的身体诗学
秦世琼,邓福艳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小说创作开始从人性复苏逐步转向身体回归,其中以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三恋”为发端,继之有莫言与王小波的小说创作,他们对“身体与性”的探索凸显了身体所蕴涵的深意;90 年代又逐渐出现女性作家“身体写作”的热潮,它不再传达抽象化的“思想”符号,也不再囿于女性传统意义上被压抑的灵肉冲突,它超越女性的一般历史情境和现实境遇,深入女性生命本真,以童年记忆、成长期性意识、同性之恋和自恋以及母性意识作为书写对象,展现女性的身体与欲望,捕捉人物灵魂深处的真切感受,从而对人的生命意识作全方位观照。林白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在20 世纪90 年代末掀起学界对女性文学论争的一个高潮,丁来先、王小波、徐坤等评论家相继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论争。论争之中,林白有回应与澄清,也有其深陷詈骂与诘难时的自辩与矫枉,论争余波延续至21 世纪,至今未有明确的胜负之分,但通过这样的辩驳与反思,学界达成共识,即1990 年代林白的身体写作是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品具有女性文学的显著特征。2021 年林白新作《北流》横空出世,王春林盛赞林白彻底打开了自己,打开了生活,打开了世界,打开了人类的存在,可见林白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实现了身体品格的文化提升。而林白小说世界所呈现出的女性身体的生命本能,又可视为女性感知外部世界的肉体生命意识取径,这反映了她对女性身体的“爱恨交织”,展现出有别于男权中心话语与主流叙事的颠覆性特质,是她在努力寻找属于女性自我的话语空间。
一、异质空间的身体凝视
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异质空间”(heterotopias)来研究对立社会关系,他认为在异质地方总是预设了开放和关闭的系统,事物可以同时性地并置或呈现。在异质空间中可能存在一种混合的、中间的经验,可能是镜子。镜子作为一个乌托邦,是一个没有场所的场所。镜子作为异质空间的作用是:它使得我注视镜中之我的那瞬间,我所占有的空间成为绝对真实,和周遭的一切空间相连结,同时又绝对不真实,因为要能感知其存在,就必须通过镜面后的那个虚像空间。[1]福柯“异质空间”理论彻底颠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隐蔽的空间秩序,打破了单一秩序的宏大叙事,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空间重新界定。
林白的写作手法巧妙地与福柯的异质空间相结合,镜子在她的小说里反复出现,小说人物在镜子里成了自己的公主,镜子是通向性别、真我、记忆的康庄大道。通过镜中之我与镜外之我的相互凝视,分裂的自我在亦真亦幻间获得了暂时的妥协,也是女性展露自我情欲的手段,而不仅仅是“宣泄女性内心情感的文字堆积以及对女性身体的疯狂迷恋和‘自呓’”。[2]林白的小说注重自我的真实书写,大胆地将女性成长中的生理感知与心理流程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林白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是身材瘦弱的女孩,她们自小养成独自洗浴的生活习惯,唯有身体处在隐秘状态下才会觉得安全,即便是与其它女性在公共澡堂共浴,将身体裸露在同性面前也会让她们感到难堪、绝望。这种对自我身体的严密保护也造成了其内心的孤独,而此种面对自我身体的观感向外延伸,间接影响到她们与外界的交往,加强了她们性格中自我幽闭的倾向。“镜子”是窥视林白小说人物内心的捷径,她“将镜子里的那个形象当作女性的本源,‘镜像’意味着女性本来面目的呈现”。[3]《玫瑰过道》中有一段极具代表性的陈述,故事的叙述人称在“我”与“她”之间随意切换──当叙述者以“她”发声时,实际上即是“我”的自我反省,具有反讽的效果。
她无数次在夜里面对穿衣镜绝望地看过它们,看久了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既不像男人也不像女人。看久了连她自己都会感到害怕,但她常常不记得这点,因为她已经习惯了,甚至由习惯变得有点自恋了。[4]
由“绝望”“害怕”等字眼,可以看出叙述者“她”对自己的身体不符合男人喜好的标准而深感苦恼,更将恋情的失败归咎于自身“丑陋不堪发育不好”,从而一再否定自我,无视两人交往过程中情感付出不对等的危机。
镜子成了阻隔女人将欲望的触角向外延伸的屏障,就有一些女人试图破镜突围,自我情欲从封闭状态中流泄而出,而这个过程中往往给她们带来更多的伤害。璩是一个有钱却孤独的女人,她选择以金钱豢养男人,试图从中培养出一种类似爱情的幻觉,最后却因残酷的现实而引发强烈失落感,在自杀前发疯地用口红涂绘赤裸的身体:“她对着亮光在镜子里欣赏自己,她异常细腻的白色体肤上布满了艳红的印记,既像鲜血又像花朵”。[5]
当女人的内在情欲公然宣泄失败后,她们只能退回房间内对镜自我欣赏。《致命的飞翔》中有描绘女性对镜自照的情景,北诺由此对自己身体产生一种近于迷恋的自信:
在镜子里她看到自己细腰丰乳,她有些病态地喜欢自己的身体,喜欢精致的遮掩物下凹凸有致的身体。[5]59
北诺和林白小说中其它女性一样,只对自己的身体有着深刻的迷恋,甚至只是通过对镜想象便能使身体获得致命的快感体验,但一旦涉及与男人之间的性爱,她们对于性的美好想象便荡然无存。
二、疼痛失落的身体记忆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性爱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础,也是文学亘古的文化母题。“性”是林白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她以女性性意识的“异化”为切入点,充分展示其特有的女性写作立场和极端个人化的写作姿态,向人们崭露出当代女性摆脱被男权文化叙述命运的努力,充分表达了实现女性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
在林白的小说中,男女之间的性事往往充满痛苦与难堪的晦涩记忆。多米在某次只身旅游途中受到男子矢村诱骗而失身,“初夜像一道阴影,永远笼罩了多米日后的岁月”。[6]在那次性经历过程中,她收获的不是快感,而是伤害,被陌生男人强暴的绝望感使多米坠落到黑暗的“深渊”,她因男性对她的性侵犯而感觉到自己只是作为性对象的命运。后来与青年导演N 的性经历,同样没有唤起她任何身体快感,而仅仅是通过性爱来证明自己在他心目中还有地位。正是在这种感受的指引下,她明白,她对N 的感受不过是一种自怜与自恋,因此在离开N 之后,她几乎马上就忘了他。
在林白那里,即便是在婚姻秩序内的两性关系也远非和谐,《说吧,房间》的叙述者老黑自承“我从来没有过青春年少水乳交融的性生活”,为应付沉重而琐碎的生活压力,老黑已是精疲力竭,对性爱毫无兴趣,做爱中的丈夫“变形的面容、丑陋的动作、压在我身上的重量,这一切都使我想起兽类”。[7]此处的性爱彻底沦为使女性备受压抑的动因。
不难发现,床第之欢在林白笔下经常被描写成令人不悦的交媾行为。但在偶然出现的美妙时刻,林白多选择从女性视角呈现性爱的高潮感受,男人则被有意淡化处理,遭到大幅度的剔除,仿佛男人只是协助女人获得性快感的工具。
这声音又像是一根鞭子,抽打在男人的身体上,它被策动起来,奋力撞击,频繁往返,节奏有如奔腾的烈马,马鬃在飘扬,背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它的下面就是土地一样的女人,如同草原般芬芳起伏。她浓黑的头发散落在乳白色图案的枕头上,左右滚动、挣扎,像是要挣脱一次酷刑,她像一个疯子用指甲掐进那个想要制服她的男人的背部。[8]
性爱过程中的女人把男人想象成待驯服的烈马从而寻找自我快感,这恰恰是林白小说的特殊之处。在林白的有意形塑之下,女人作为对身体异常敏感的感受主体,更是主导、掌控自己情欲的主人。
不难发现,林白对于身体的书写是有节制的,她并不将身体写作当成一种游戏的消费主义实践,她笔下的身体书写,并不像卫慧、棉棉一样致力于展现女性生活的癫狂状态以及欲望的裸露,而是清醒地与身体书写的商业化及游戏化倾向保持距离。林白小说中男女之间的爱情总以失败而告终,缺乏情爱的性爱关系又令人不忍卒睹。有无爱情早已不是男女发生性关系的必要因素,即使没有男人,女人依然能以自慰的方式宣泄内心的情欲,并能获得比男女性爱更强烈的满足。
三、心灵创伤的身体疗治
西克苏(Helene Cixous)指出,女作家“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9]林白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驱逐男性的女性世界,这个世界里的女性用自慰与同性恋的方式逃离与反叛男权的压抑。
林白小说中表现出对女性她者美妙躯体深层的欣赏与迷恋、女主人公自慰所带来的无穷的快感,这一切都成了女性疗治心灵伤痕的灵药,“她的人物并非毫无欲望,只是在男性一头的绝望使其欲望变成无对象的展示,情色成为一种真正的自娱,在纯粹的意义上完成了女性的自觉”。[10]
《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由于当地居民习惯单独洗浴,致使她对体态优美的女性产生一窥其裸体的念头,而女演员姚琼“身体修长,披着一头黑色柔软的长发,她的腰特别细,乳房的形状十分好看”,[5]16成为多米最佳的幻想对象。当多米目睹姚琼在她面前更衣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渴望。这渴望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想抚摸这美妙绝伦的身体,就像面对一朵花,或一颗珍珠,再一就是希望自己也能长成这样。”[5]17年幼的多米身材瘦小,因此将美丽的姚琼视为女性形象的典范。在面对真实女体的当下,多米自认为她只是纯粹地欣赏女性美,而这种女性审美的目光中不含任何肉欲的成分,因此未曾兴起触摸她者身体的渴望,更不愿意由此被误贴上同性恋的标签。
《回廊之椅》里朱凉的身影显得虚幻而诡秘。朱凉虽然是被叙述的对象,却未真正现身,她只存在于七叶的怀想和陈述中,而“我”则成为七叶用来倒映朱凉身影的镜子。在“我”对朱凉的幻想中,朱凉是一名具有不可思议美感的女人:
在酷热的夏天,朱凉在竹榻上常常侧身而卧,她丰满的线条在浅色的纱衣中三分隐秘七分裸露,她丰满的线条使男人和女人同样感到触目惊心,在幽暗的房间中既像真实的人体又像某幅人体画或者某个虚幻的景象。[4]163-164
“我”对于朱凉的静态美以“远观”“遥想”的方式呈现,虽不是对女性之躯的实质描绘,却呼应着林白屡次在小说中精心雕塑的理想女体。
无论是《一个人的战争》对女性主人公接触她者身体经验的实写,还是《回廊之椅》虚写的神秘而美丽的女性形象,都传达出一个明确而重要的信息:女性借助同性之间身体的观照,进一步确认出自我身心认知的位置。这既是作品主人公所向往的理想女性形象,也反映出林白欣赏女性之美的审美趣味。
潜隐于女性内心的情欲一旦流露于外,其具体展现便是“自慰”。“自慰”是林白笔下的女性人物出现频率最高的性行为,她以诗意、优雅的方式描写女性从中获得的快感;而男女之间的性爱则多半丑陋而令人恐惧,两相对照之下产生强烈的反差。多米具有这种“经常性的欲望”,其自慰的举止被赋予优雅的诗意,游鱼与水液的意象彼此融汇,女人在 “挣扎”“犹豫”而又“固执”的自我抚触中得到一种“致命”的高潮,让自己心甘情愿地被极致的自足感所“吞没”。然而,林白对身体的自慰书写是节制的,她笔下的身体是敏感度极高的感受器,且所有的感受都指向了女性身体的自由与解放。
而在同性恋方面,林白展现给读者的模式更是充满失落和无望,在涉及同性恋的性关系之前,女主人公往往从一段可能发生的爱情中落荒而逃,早早遏止了同性恋的发生。多米虽然承认“我真正感兴趣的也许是女人”,但仅止于此,她一再辩称“在我没有爱上男人的同时也没有爱上女人”,[5]15《玻璃虫》的林蛛蛛也如此说:“虽然我向来喜欢欣赏美丽的女性身体,但仅限于欣赏,她们的身体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性的欲望,我也从来没有要与她们发生肉体关系的想法”。[11]两位叙述者声口一致,表现出对女性身体的渴望,却又极力否认其中具有同性恋因素。在林白的小说文本中,很难找到两情相悦的同性恋情,“林白在表现同性之爱时始终缺乏那种蔑视世俗观念的勇敢无畏的精神。她一直处于无法摆脱的矛盾冲突中:既对同性的身体充满憧憬和渴望,又不遗余力地压抑这种难以启齿、不为世人所容的欲望”。[12]不难发现,林白对同性恋的理解与想象仍较为保守,根本不及对异性之间爱欲书写那般大胆,这与林白主要关注异性恋女性面对同性恋关系的心理感知过程不无关系。林白小说中的同性恋偏向“无性”交往,即便是《玻璃虫》这部已经触及同性恋之间性爱的小说,结局依然设定为叙述者好奇有余而勇气不足,最后临阵脱逃。林白也承认,“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不过是一个理想的宣言而已,甚或只是市场需求于女作家的一种姿态罢了。林白小说所书写的同性恋大多缺乏稳固的情感基础,在世俗社会中挣扎生存的同时,更因彼此地位不平等或付出的多寡而导致分崩离析,女主人公最终选择远离同性恋的国度,开始向“自然的女性”(即“母性”)的身体回归。
四、回归母性的身体展演
美国当代女诗人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认为,“母职”是父权体系建构出来的;在父权社会的象征体系中,一直有两种女性概念齐头并进:一是女性是“魔鬼之门”,女体是不洁、腐化的,会造成道德败坏及健康恶化,对男性造成危险;二是女性是“圣洁的母亲”,作为母亲的女人善良、纯粹,无私地付出关爱养育子女,且与性无关。[13]林白关于母性的书写似乎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其小说逐渐剥落母亲神圣的面纱,回归女性性别本真,显示出其凡俗而驳杂的内心世界。林白对女性生命历程中母性的书写主要包括未婚先孕、人流以及生儿育女等女性独有的身心体验,而这恰是当代女性写作中较少关注的话题。
在林白一系列着重描绘女性成长历程的小说中,不少女性有未婚先孕的人生经历,这往往联系着一段她们自认为刻骨铭心的爱情。《一个人的战争》的多米和《玫瑰过道》中的“我”即是例证。在她们看来怀孕是确认爱情存在的唯一证据,“因为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照片、信件、誓言以及他人的流言,如果我不提到孩子,对我来说,一切就像是虚构的,是我幻想的结果”。[4]196-197她们对孩子的认定仅限于此,但孩子和爱情却构成了相互矛盾的两端,男友只要自由而不愿负起做父亲的责任,她们的选择却是拿掉孩子,“放弃了孩子,却获得了爱情,我想这是值得的”。[5]77多米与“我”在盲目的爱情中左冲右突,作为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执着远胜过成为孩子母亲的渴望。当女人为了保全爱情而决定放弃成为母亲的机会,终结孩子的生命使她们永远感到懊悔与歉疚,而爱情还是无法避免地走向幻灭,“我失去了孩子同时也失去了他”,[5]77女人成了最大的输家。她们的爱情并未因此得以延续,自以为神圣的牺牲在世俗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对置身于婚姻内的女性而言,怀孕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赋予的神圣使命,然而对未婚女性来说却是非常可怕的。她们对怀孕更多时候体现出茫然无助,不仅伴随着生理方面的不适感受,更有沉重、压抑的心理重担,具体表现在女性面对未婚先孕的心灵恐惧。当多米发现自己怀孕时,“这是一个异常严重的事情,我惊慌失措神经紧张”。[5]26曾经二度未婚先孕的老黑时刻感到自己就是个异类,她们一旦发现自己未婚先孕,往往陷入绝望无助的深渊,畏惧、恐慌像幽灵般挥之不去,令人窒息。
为了挣脱这层苦痛的纠缠,未婚先孕者万般无奈下躲进私人诊所施行人工流产。此举虽然解决了这些女人沦为单身母亲的窘境,但她们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们“身体深处”被刻画出一道永远改变往后人生的“伤痕”。此外,整个人流过程也是一个令人不安、被人羞辱的过程。从手术器械、诊所招牌到医生处的问诊,这一切在她们看来,无不透露出凛冽的寒光与歹毒的恶意。人流在此被描写为极度不堪的人生经历,医生缺乏人性的制式指令使她们饱受威胁与羞辱,一切尊严丧失殆尽,手术对身体造成的疼痛紧随其后。毋庸置疑,林白为读者描绘出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通过小说人物的诉说使读者在逼真的感受中发抖冷颤,从而对现实女性的处境多一分关注、理解与同情。
当然,在林白的小说中,也有少数女性已婚并兼具孩子母亲的身份。在成为母亲的前后,这类女性主人公的心理认知也产生了极大转变。《说吧,房间》塑造了“袋鼠母亲”的鲜明形象,老黑“年轻时决心不要孩子的隐秘理由之一就是担心自己变成一只难看的袋鼠”。[6]45然而,当老黑生下女儿之后,她的心态发生了极大转变,女儿成长过程中的点滴变化都给她带来惊喜:
这时候我完全跟袋鼠认同了,我完全不记得袋鼠有多难看了,我从来就不认为袋鼠难看,我现在坚信袋鼠的体型是世界上最合理最自然同时也是最优美的体型,我将以这样的体型向整个草原炫耀![6]48
自内心深处萌生的母性本能使老黑认同了“袋鼠母亲”的形象,她原本认为母亲一律是难看的丑妇,但当她自己成为母亲后,袋鼠形象却变成了“最合理最自然同时也是最优美”的姿影,这是对母亲形象的一次美化。尽管抚育孩子牺牲她们的事业和既有相貌,但孩子激发出了女性内心深处的母性,成为引导女人蜕变为母亲的华丽转身和美好救赎。
“肉体只有经过了诗学转换走向了身体的伦理性,它才最终成为真正的文学身体学……肉体必须拉住灵魂的衣角,才能完成文学性的诗学转换”。[14]林白小说的身体诗学可以说已经做到了精神与肉体的结合,她以诗性的语言、唯美的意象塑造一系列女性躯体,并以女性视角独自欣赏,赋予其特殊的审美内涵,亦着墨于女性对自我身体及情欲的探索,传达了女性自我肯定、自我认同的美好愿景。林白透过书写女性的身体及欲望,最终抵达女性精神层面的深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