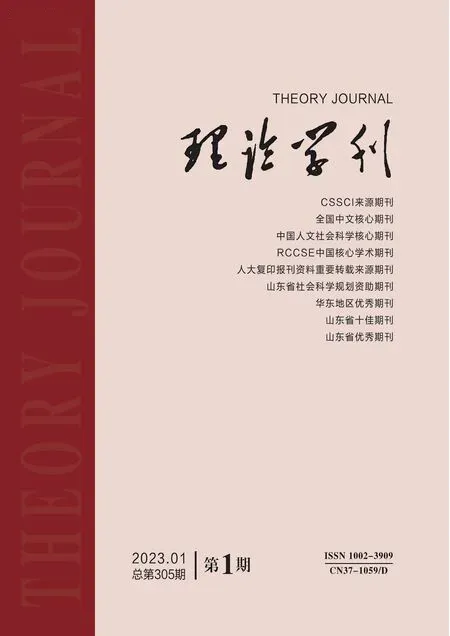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传统文化要素辨析
严 挺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8)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话语及其内涵解读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更是首当其冲。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这五大特征实际上区分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实践经验。众所周知,现代化一直都是政治学研究的重大问题,那么我们应如何从政治学理论角度评估中国式现代化?另外,“中国式”的提法本身就突出了中国经验与西方道路的区别,更是凸显了“文化”性质的区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依据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2)《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1月25日。。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些区分特征具体与哪些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相关联呢?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提出的本身就是对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的挑战和反思,所以上述研究问题的探索会是建立现代化理论中国观点和中国学派,甚至扩大中国特色政治学国际话语权的契机;同时,上述研究问题的探索能为中国式现代化主张提供学术论证和智力支持,增强我们的“四个自信”,并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观贡献中国经验和智慧。
一、政治学研究溯源:现代化、传统文化和中国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特征的表述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的经验总结,所以在更多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是较新的、基于实践的政策话语体系,这也意味着对应的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体系尚未形成,有待国内外学者的探索、创建和论证。但是,对现代化的研究和对文化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里由来已久,我们能不能从这些研究中找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逻辑或理论支撑呢?
(一)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现代化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衍生出了很多现代化理论流派(3)马克思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推导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韦伯指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李普赛特首次用数据资料展示了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关联。英格尔哈特则提出了修订版本的现代化理论,指出了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转变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价值观代际转变的关键作用。参见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英格尔哈特对这些现代化理论的共有概念和观点作了很好的总结,他指出,“现代化理论的中心观点认为,工业化进程与某些普遍的社会政治转型进程紧密相连:尽管前工业社会之间差别巨大,但只要它们专注于工业化,所有社会都会朝向一种可预见的‘现代’或者‘工业’社会模式发展。经济发展与一系列转变征候相关联,不仅包括工业化,还包括城市化、大众教育、职业分工专业化、官僚化以及通信的发展,然后它们又与更为广泛的文化、社会及政治转变相关联”(4)[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体系更多的是忽视或者质疑中国式现代化。
首先,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中心观点针对的是所有社会,追求普适性而反对国别性与特殊性。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这种理论倾向的典型,它宣扬的就是所有国家和社会在现代化道路终点上的一致性和同质性(5)Francis Fukuyama.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Simon and Schuster, 2006, pp.211-212.,自然也包括中国在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事实的确引起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反思,比如2004年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的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中国模式”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6)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pp.3-4.。但这只是少数声音,主流的现代化理论并不认可中国现代化是一种成功模式。相反,西方学者提出了中国现代化成就的脆弱性问题,认为不遵循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国现代化路径存在结构性矛盾并且前景黯淡(7)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9.。这种质疑和忽视持续至今。
其次,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体系认为现代性与传统是对立的,也就否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情境根源。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明确指出,“现代性与传统是根本不对称的概念,在现代性目标既定的情况下,任何不是现代性的东西都可标签为传统”(8)S. P. Huntington. The Change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 no.3, 1971, pp.283-322.。而且,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的标志——工业化要得以顺利进行,就必须要打破传统价值体系的束缚,即实现从传统权威到理法权威的社会转变(9)[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3、100—103页。,所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否定了一国传统(以及历史)的重要性和相关性。而现代性与传统的契合恰恰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所强调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68页。。很多学者也提出要超越传统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思维,用两者相辅相成的性质分析和解决中国现代化治理问题(11)王心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最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将现代化各维度看作是割裂式、串联式关系,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相悖(12)张翼:《从社会学角度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人民日报》2022年7月11日。。经济增长、文化转变、政治及社会转变之间的优先次序成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不同理论流派的争论焦点,至今尚未形成定论(13)[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3、100—103页。。与之形成对比,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既没有区分经济、政治、社会这些维度,更没有关于这些维度在发展次序上孰先孰后的提法,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更倾向于现代化各维度之间的同步发展和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把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比作是“并联式”与“串联式”发展进程的区别(1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这个比喻同样适用于描述西方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表述的分歧。
综上所述,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因为其普适性设定、与历史和传统的对立以及并联式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格格不入,看轻甚至看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现实,所以无法为后者提供理论支持。那么,涉及政治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学研究是否会偏爱中国式现代化呢?
(二)文化相对论与中国式现代化
与现代化理论体系不同,被称为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的政治文化理论流派认可一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并将之作为政治社会现象的关键解释变量。中华文化作为轴心时代肇始的三大文明之一,中国传统(文化)自然成为文化相对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理论要素。引起广泛关注的亚洲价值观理论就是使用中国传统文化要素解释现代化现象的文化相对论典型。
亚洲价值观是20世纪90年代由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出的,其核心观点是:亚洲地区独有(区别于西方)的文化倾向、信仰、规范和态度构成了该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以及进程的基础(15)So Young Kim. Do Asian Values Exist? Empirical Test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sian Value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10, no.2, 2010, pp.315-344.。需要指出的是,亚洲价值观强调的独有文化实际就是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它所指向的亚洲国家从历史和现实上讲都可以划归在儒家文化圈(区别于西方文明)之内(16)[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3、100—103页。。这一点在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17)Fareed Zakaria and Lee Kuan Yew. Culture Is Destiny: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Foreign Affairs,vol.73, no.2, 1994, pp.109-126.,也在众多政治学者中达成了广泛的共识(18)郑永年:《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亚洲价值观的核心观点有着很坚实的实证基础。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创造了现代化历史上的“亚洲奇迹”,先后步入发达国家与地区之列。随后,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也实现了经济腾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作为儒家思想起源地的中国大陆,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现代化成就。欧美发达国家达到现在的现代化水平花费了平均200年的努力,而上述亚洲国家和地区仅花费了50年不到。这么多的快速现代化案例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密集出现于这一块亚洲地区之内,不得不说与这个区域的特殊性即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
新加坡的政策实践是直接展现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关联的最典型案例。李光耀执政之初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自上而下地将儒家思想要素贯彻进新加坡民众的价值观体系之中。比如,他将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并称为“八德”,作为新加坡的治国之纲;1991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内阁提出的“共同价值观”,作为新加坡民众共同价值观建设的官方指引(19)李保英、高奇琦:《亚洲价值观与新加坡民主政治》,《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这些举措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上述价值观已经扎根在新加坡民众的思想之中,使得新加坡在经济发展、政治环境、社会风气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媲美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由此可见,与现代化理论不同,亚洲价值观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认为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对现代化有促进作用,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传统文化根源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支持。
但是亚洲价值观理论体系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解读不统一。李光耀直接从儒家教义中选取了节俭、勤勉、忠孝的家庭观以及对学问和教育的重视等关键词来阐释什么是亚洲价值观(20)Fareed Zakaria and Lee Kuan Yew. Culture Is Destiny: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vol.73, no.2, 1994, pp.109-126.。李保英和高奇琦等则脱离了儒家教义文本,进行了抽象概括并提炼出新的术语,认为亚洲价值观包括集体主义、威权主义和国家合作主义(21)李保英、高奇琦:《亚洲价值观与新加坡民主政治》,《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贝淡宁等则直接将亚洲价值观等同于“贤能政治”(22)贝淡宁:《从亚洲价值观到“贤能政治”》,李扬眉译,《文史哲》2013年第3期。。这种不统一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亚洲价值观理论的严谨性,也成为现代化理论诟病它的主要因由。与之相关,亚洲价值观的另外一个重大缺陷是:它缺乏一个关于传统文化促进现代化的逻辑推导环节。亚洲价值观支持者更多地运用实证倒推和对比的逻辑,即上述亚洲的成功现代化案例无法用西方现代化理论来解释,所以只能归因为亚洲特殊的文化传统要素。但是哪些要素对现代化起促进作用、又如何起作用,则成为亚洲价值观的理论黑箱(23)郑永年:《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86—87页。。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应的传统文化要素
我们从上面的政治学理论溯源中找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传统文化根源的学术支持,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对应哪些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亚洲价值观的研究是有方法论缺陷的。首先,它在列举中国传统文化要素清单的过程中没有以中国本身为研究对象。从李光耀到贝淡宁,在这些亚洲价值观代表人物的著作中我们基本找不到儒家经典的引用和考证,实证资料也基本上停留在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年代的案例之上,反而缺少对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大陆的资料考察和关注。所以,亚洲价值观提供的清单与国内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研究对象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比如杨光斌列举的、与中国现代化有关的传统文化要素:国家的大一统、民本、和为贵思想以及中庸之道等,大多不包含在亚洲价值观清单之中(24)杨光斌:《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中国文明基体论的延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版,第5—6页。。其次,亚洲价值观学说缺乏对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关系的理论解释。如前文所述,亚洲价值观支持者大多运用实证倒推和对比的逻辑来构建两者关系,但没有回答哪些传统文化要素会对现代化起促进作用、又如何起作用的问题。这就涉及了同义反复(tautology)的方法论问题,即它的解释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重述同一个观察到的事实,严重影响到亚洲价值观及其传统文化要素的理论效度(25)郑永年:《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84—85页。。最后,亚洲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要素缺乏严格的稳健性检验标准。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概念都能作为传统文化要素,比如夺情、丁忧等概念只出现和盛行在特定的中国历史阶段,并且已经为新时代民众所抛弃,显然不适宜列为要素。所以,传统文化要素必然是中华文化的一些核心要素,有着超强的稳定性,就像基因一样,代代相传、内化于民众身心日常之中,时至今日仍然成为国家治理和民众生活的依赖(26)Karl Jaspers. The Way to Wisdom: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98.。亚洲价值观理论体系并没有对它的传统文化要素是否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进行检验,这也是它引来很多专家学者批判的原因(27)郑易平、陈延斌:《亚洲价值观评析》,《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我们认为,比较历史政治的研究方法能够解决上述方法论缺陷,原因在于该研究方法强调历史分析与科学研究技术的结合,尤其适合跟踪研究特定历史文化要素发生和发挥作用的问题。一方面,历史分析方法意味着它承认一国历史情境和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并将之作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实证技术方法的引入也使得它避免了政治学研究对原有历史—文化分析框架的非科学性批评和冷落。具体到辨识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问题上,比较历史政治研究方法的优势能很好地校正亚洲价值观理论体系的缺陷。首先,它与原来历史—文化分析框架主导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后者将中国历史与文化本身尤其是儒学理念视为主要研究对象,产出了大量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文献,自然也提供了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清单。这个清单源自对中国本土历史情境资料的分析,并经过了历史—文化分析框架的推导和检验,在学术性和专业性价值上远超亚洲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要素清单,也就避免了中国性不足和同义反复的缺陷。其次,它同样可以从政治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文献中获得支持。英格尔哈特就基于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28)[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8页。。虽然结论指向了两者的相悖关系,但是它提供了如何验证中国传统文化和如何解读它与中国现代化政策关系的模板。
为最大化地发挥比较历史政治研究方法的优势,我们将在辨识中国传统文化要素时进行两个步骤的分析流程。第一步是甄选。由于我们的目标是与中国式现代化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因此甄选结果首先要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表述和政策实践的相关性解读。同时,甄选结果最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文献中得到提示和支持。最后,我们还需要对甄选结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进行推导以增强其理论效度。第二步是检验。一方面,有资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必须要昭示自身的存在并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不间断的印记,因此,历史延续性是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内部效度检验标准。这可以通过历史分析方法考察。另一方面,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区别在整个历史的不同时间点上始终存在,所以只有与西方文明形成对比的中国传统文化要素才有效。这是外部效度检验标准。我们将借助经验调查数据来进行验证。
(一)中国式现代化表述对应的传统文化要素
党和国家的政策语言体系支持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根源的论断。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29)《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聚焦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我们认为它至少折射了民本、中庸、德治和和谐这几个中国传统文化要素。首先,民本是基础。二十大报告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作为第一个特征,也就表明了“民惟邦本”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思维,其他几大特征的主语无一例外也都是人民。“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当家作主”“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利民为本”“最广大人民利益”等政策话语都是“民惟邦本”思维的集中体现。其次,中庸是治理之道。二十大报告在解释第二条特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时强调了“防止两极分化”,对应了中华传统文化追求边际平衡、避免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30)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13页。。另外,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并联式”的全面发展模式,也与中庸之道不谋而合。再次,德治是灵魂。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三条特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指出“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提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美德和“道德教化”责任的德治理念(31)[美] 迈克尔·桑德尔、德安博:《遇见中国——中西哲学的一次对话》,朱慧玲、贾沛韬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第72—81页。。最后,和谐是理想目标。第四条特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直接使用了“和谐”一词,而第五条特征“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使用了“和平”一词,这两个词都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谐、反对混乱和冲突的取向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中的每一个特征都能同时折射民本、中庸、德治和和谐这几个中国传统文化要素。比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除了体现民本基础、中庸之道之外,也能反映德治灵魂和和谐目标,因为共同富裕代表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美好生活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富有(德治)和解决两极分化的张力问题(和谐)。民本、中庸、德治和和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同样能得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佐证。徐大同提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最核心的要素包括有重民、重和和重德(32)徐大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2页。。这三个要素对应了民本、和谐和德治,中庸作为达成和谐目标的方式也可包含在“重和”要素之内。杨光斌将民本、和谐、中庸和德治都列入了中华文明基体的清单之内(33)杨光斌:《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中国文明基体论的延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版,第5—6页。。
(二)中国传统文化要素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
按照比较历史政治分析方法的要求,我们还需要对甄选结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进行推导,即我们该如何解释民本、中庸、德治和和谐要素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作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社会资本理论的模板(34)关于中国社会资本的研究,参见 Hongjuan Zhang, Rong Han, Liang Wang and Runhui Lin. Social Capital in China: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 vol.20, no. 1, 2021, pp.32-77.。普特南发现,良好的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和网络,意味着民众内部、精英内部、民众和政府精英之间建立了彼此之间信任、互惠和合作意识的基础,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并且会不断自我巩固的“公民共同体”(civic community),这种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能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达到公共均衡,使得国家和市场都更有效率(35)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 Press, 1993, pp.177-183.。以信任、规范和网络为特征的公民共同体是社会资本促进政府绩效的关键一环,而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其社会形态保持了稳定结构并具备公民共同体的上述特征。费孝通展示了中国社会结构中密集的社会网络(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可靠的人际信任、普遍认可的礼的规范以及偏重社会合作的倾向(36)费孝通:《乡土中国》,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因此,按照社会资本理论,这样的中国社会资本和社会结构能够带来良好的政府绩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驱动力。无论是社会资本还是社会结构,都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37)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pp.33-34.。普特南的社会资本及其形成的公民共同体都源自传统。中国的社会资本及其承载的社会结构也是如此,它们很好地诠释了民本为基础、中庸为方法、德治为灵魂以及和谐为目标的中国传统文化作用。我们认为,与西方社会相比,这些传统文化要素更好地发挥了社会资本的效率和公民共同体的优势,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的法宝。
首先,民本思想在构建公民共同体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民本思想提倡的是家国同构的共同体意识,而费孝通所描述的中国社会结构就符合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的逻辑(38)费孝通:《乡土中国》,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0、64—67页。,所以民本思想提供了公民共同体的意识基础。另外,民本思想的对象同时针对精英与大众,既扩大了公民共同体的基础,又使得精英和大众的默契配合成为习惯,大大增强了公民共同体的实力和效力。最后,民本思想的历史传承造就了中国民众对公民共同体的弥散性支持,也造就了中国社会结构以及公民共同体的历史稳定性。相反地,西方社会的公民共同体构建则遵循家国异构的社会契约思想和委托—代理式传统,因而稳定性较差,经常出现共同体失灵(如经济危机、政府停摆)、精英与民众对立(如民粹主义)的情况。
其次,中国悠久的德治传统是中国社会资本的底气及其发挥效用的灵魂。因为社会资本都是“道德资源”(moral resources)(39)Albert O. Hirschman. Against Parsimony: Three Easy Ways of Complicating Some Categories of Economic Discours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vol.37, no. 8, 1984, pp.11-28.,所以社会资本向绩效的转换效率取决于道德资源的社会化和内化程度。中国悠久的德治传统意味着相关道德资源的高度社会化和内化,中国的儒商现象可以作为德治传统在中国商人群体中的内化并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成效的示例(40)Tu Weiming, Bingyi Yu and Zhaolu Lu. Confucianism and Modernity-- Insight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Tu Wei-Ming.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 7, no. 2, 2000, pp.377-387.。西方社会没有这种德治传统,所以金钱政治、政治分肥、“旋转门”等道德弊病反而成为一种明面的政治常态。
最后,和谐和中庸对应了社会资本以及公民共同体发挥效用的目标和方式。社会资本以及公民共同体的目标是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即在民众内部、精英内部、民众和精英之间达成共识并一致行动,所以和谐是目标。达成这个目标需要各方在互动中寻找均衡点,避免冲突,即采纳中庸之道。费孝通强调中国社会结构中社会合作倾向和同意的权力,可以看作和谐和中庸的内化,而这种内化显然有利于中国社会资本发挥效用(41)费孝通:《乡土中国》,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0、64—67页。。相对地,西方社会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推崇竞争的方式和个人成就的目标,最终带来了现代化的各种危机(42)[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1页。,包括近期的政治极化趋势和大国关系恶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检验
我们用历史分析法检验这些要素的历史延续性,然后用经验数据分析这些要素的文化独特性。我们采用的数据是“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World Values Survey)(2005—2020)(43)EVS/WVS. European Values Study and World Values Survey: Joint EVS/WVS 2017-2020 Dataset (Joint EVS/WVS). JD Systems Institute & WVSA. Dataset Version 1.0.0, 2020, doi:10.14281/18241.2.和“东亚民主研究”项目(East Asian Barometer)(2013—2016)(44)本文数据来自胡佛和朱云汉教授主持的,由台湾教育院、“中央研究院”及台湾大学共同资助的“东亚民主研究项目”(2013—2016)。东亚民主研究项目办公室(www.asianbarometer.org)为数据独家发行方。笔者感谢上述机构及人员协助提供资料,而本文观点全由笔者本人自行负责。。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把日本作为比较对象,因为日本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并且日本文化与欧美接近但与中华文明相区分(45)S.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 vol.72, no. 3, 1993, pp.22-49;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p.57 and p.161.。
1.民本
民本,即一个国家的根本是人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据传最早出自夏朝流亡的泰康兄弟。春秋战国是民本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孔子呼吁“仁政”,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强调重民,从而奠定了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自此以后,民本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之中不断传承和发展。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基本都很推崇这个思想并尝试付诸实践,比如西汉政治家董仲舒、唐太宗李世民、宋代思想家程颐、明成祖朱棣、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等,都是民本思想的重要倡导者。统治者要落实民本思想以巩固国家的根本,首先要解决民众想要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看做是民本思想的民众视角。荀子认为,民众需要的是实质性的物质利益;而从民众角度看,能最大化这种实质利益的统治者才是真正地以民为本,因此民众角度的民本思想与统治者角度的民本思想是统一的。因为本文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主体是民众),所以我们在这里检验的是民众角度的民本思想。我们将它解读为民众对物质性目标而不是非物质性目标的获得感。民众的物质获得感与政权根基的关联贯穿整个中国历史。中国王朝历史上的太平盛世都要归功于统治者卓有成效的养民富民政策,相反,王朝的灭亡也大多伴随着统治者对民众温饱诉求的无视。源自民本思想的这种关联时至今日依然有效并被奉为圭臬。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要素通过了历史延续性的检验。
接下来我们考察民本思想是否具有中国独特性。我们选择了两个调查问题度量民众追求实质利益的获得感(民本思想):(1)你认为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人民的需求?(2)大多数人认为自由和平等都很重要,但如果您要在二者选择其一的话,您认为哪一个更重要?第一个问题是从字面意思度量民众从政府处获得实质利益的感觉,第二个问题是在平等(物质性需求)与自由(非物质性需求)之间的选择。赞同“平等比自由重要”的回复代表了受访者对实质性物质需求的偏爱。结果显示,66.5%的中国受访者表达了对政府回应其需求的认可,而只有37.2%的日本受访者表示政府能够回应人民的需求;65.6%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平等比自由重要”,而只有37.4%的日本受访者同样这么认为。因此,中国受访者远比日本受访者更执着于实质性物质需求的获得感,也就是说,追求实质利益的获得感(民本思想)具有中国特殊性。
2.中庸思想
“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孔子认为它是一种最高的美德。中庸的核心理念就是反对偏激和冲突,维护秩序的稳定性和事物发展的平衡性。“过犹不及”“不偏不倚”等都属于为人处事的中庸方法论。随着汉朝“独尊儒术”时刻的到来,中庸思想就开始了被作为官方哲学代代相传和扩散的历史。《中庸》原来是《礼记》的一篇,在从汉朝到宋朝的这段历史中它一直是教育和祭礼的重要内容。从宋朝到清朝,《中庸》更是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并且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成为科举入仕的必考书目和帝王教育的教材。虽然它的官方地位随着王朝政治的终结而中止,但是中庸思想已经根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在当代中国,中庸思想依然强大,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规划——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就深刻体现了全面均衡发展的中庸方法论。
综上所述,中庸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是治国的主导型思维,因而符合历史连续性的条件。如果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特性,那么我们理应看到中国民众表现出很强的中庸思想倾向。我们使用两个调查问题来度量它:(1)如果您不得不在下列目标中作出选择,您认为哪一项最重要(选项为:维持国内秩序、使人们在重要的政府决策上有更多的发言权、控制物价上涨、保障言论自由)?(2)您赞同/反对以下的表述——即使与他人有不同意见,也要避免冲突?第一个问题是用秩序稳定的优先考虑作为中庸思想的变量,第二个问题则用避免冲突的倾向作为中庸思想的变量。结果显示,认为“维持国内秩序”最重要的中国受访者比例为71.8%,大幅度超过日本(55.9%);92.6%的中国受访者倾向于避免与他人冲突,而只有61.5%的日本受访者有同样的倾向,前者超出后者30多个百分点。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结果一致,表明中国和日本在中庸思想上的差异非常明显,支持了我们把中庸思想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独特要素的观点。
3.德治
中国传统“德治”基本包括三方面内容:行德政(核心是统治者要“爱民”、勤政、廉政)、施德教(对百姓要进行道德教化,反对“不教而诛”)、修德行(统治者要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身作则)(46)徐大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2页。。中国德治思想萌芽于西周时期,以周公旦、召公奭为代表的政治家所倡导的“敬德保民”,意谓王者只有敬重德行才能获得天命,保有人民和疆土。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最先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思想,即统治者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就必须实行德治。《中庸》《大学》《孟子》等著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德治思想。随着汉代儒家独尊地位的出现,德治思想也就成为从汉唐到明清历代王朝的统治哲学。“三纲”“五常”由西汉政治家董仲舒首先提出,逐渐演变为德治最具代表性的工具,成为维护宗法等级秩序、使中国宗法社会得以绵延几千年的重要支柱,也是德治思想历史延续性的证明。虽然“三纲”“五常”的社会教条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德治思想依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社会舞台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行动可以看作是德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我们使用两个“东亚民主研究项目”的调查问题来度量德治思想的影响,受访者被要求对以下两个表述作出赞同/反对的评价:(1)如果我们的政治领导人道德高尚,我们可以让他决定所有事务;(2) 我们应在美德和能力的基础上选出政治领导人,甚至无需选举。赞同上述表述的回复被视作是对“德治”的推崇,因为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认为,领导人的道德品行与社会制度正义是一致的。结果显示,46.1%的中国受访者表达了对道德高尚的领导人的极高信任,而持同样态度的日本受访者比例仅为34.6%,相差10多个百分点;31.6%的中国受访者赞同以美德为基础遴选领导人,而持同样态度的日本受访者比例仅为24.7%。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结果一致,表明中国和日本在德治思想上的差异非常明显,从而支持了我们把中庸思想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独特要素的观点。
4.和谐
和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状态,是人对自身、他人、社会、自然这四者关系的协调和平衡程度的一种确认(47)黄刚:《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起源、本质及意义》,《华夏文化》2008年第3期。,体现为身心和谐、人际关系和谐、大同社会和国际和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和谐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史伯的“和同”思想。春秋时晏婴提出,“和”就像五味的调和、八音的和谐。孔子用“和同之辨”区分君子和小人,正式将“和”引入社会伦理,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 汉代董仲舒融合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指出了“中和”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宋明理学吸收了孔子和思孟学派的观点,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以“诚”为内质、以“理”为总纲的中正均衡的精神面貌(48)王毓:《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研究三十年综述》,《东方论坛》2015年第3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和话语,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彰显了和谐理念的存在和现实影响力,因此,和谐理念通过了历史延续性的检验。关于外部效度,我们使用两个“东亚民主研究项目”的调查问题来度量和谐思想的影响。受访者被要求对以下两个表述作出赞同/反对的评价:(1)我们在团队里应避免公开争吵,以维护团队的和谐;(2)如果人们组织很多小团体,共同体的和谐会遭到破坏。这两个问题都是从字面意思直接测量和谐思想的倾向,赞同上述表述的回答被看做是受访者和谐思想的体现。结果显示,88.2%的中国受访者倾向于维护团队的和谐,高于持同样态度的日本受访者比例(83.4%);74.0%的中国受访者担心“共同体的和谐会遭到破坏”,远超持同样态度的日本受访者的比例(42.1%)。该分析结果表明,和谐思想在中国民众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从而支持了我们把和谐思想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独特要素的观点。
三、结论和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的经验总结。党的二十大给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话语体系,而建立对应的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体系也亟待提上日程。因为主流政治学的现代化理论一直以来都是忽视或者质疑中国式现代化的,更不用说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提供这方面的智力支持,与主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抗衡从而扩大国际话语权。本研究对这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我们认为,亚洲价值观理论和实践可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话语体系的借鉴,然后借用比较历史政治的分析框架设计了辨识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程序,最后应用探索性分析锁定并检验了与中国式现代化对应的四个中国传统文化要素——民本、中庸、德治和和谐,展示了使用上述试验性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相关问题的可行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4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我们可以预见上述理论和方法用于其他政策分析领域的广阔前景。另外,中国式现代化对应民本、中庸、德治和和谐思想,这一发现本身可以给中国式现代化政策话语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提供素材,也可以为我们反思西方现代化和创建中国学派提供学术支持。最后,本研究尝试了政治思想史、实证政治学、政治文化研究之间的结合和智识成果共享,有助于开拓学术研究的新空间,同时也有利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湖北亿立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