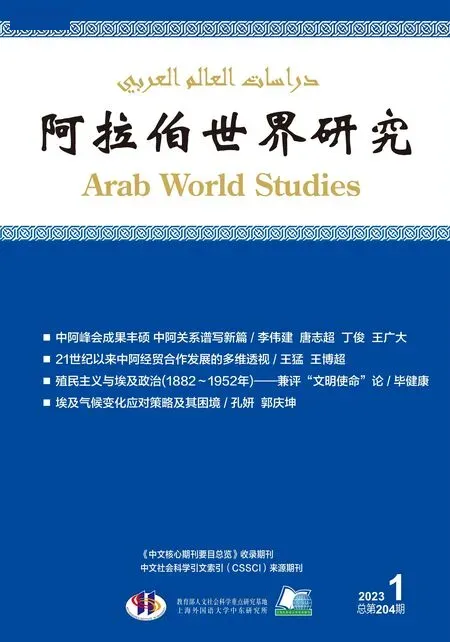殖民主义与埃及政治(1882~1952年)
——兼评“文明使命”论
毕健康
文明古国埃及是东地中海大国,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是从大西洋和欧洲通往印度洋和远东的交通咽喉,因而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觊觎之地。1798年和1882年,埃及先后遭到法国和英国的殖民侵略。虽则1922年2月28日英国单方面宣布埃及“独立”,但英国在埃及的殖民统治一直延续到1952年。70年殖民统治对埃埃及政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提出各种观点。
首先,心怀白人优越感、秉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殖民史学或帝国史学,把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叙述为“文明使命”。克罗默勋爵(1)本名埃夫林·巴林(1841~1917年),1883~1907年埃及统治者。这个赤裸裸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2)M. W. Dal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ume Two: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43.在《现代埃及》中认为,埃及是“半文明”国家(3)Evelyn Baring, Modern Egypt,Vol. Ⅰ, London: Macmillan, 1908, p. 2.,他对埃及的殖民统治与残酷剥削便是“文明使命”。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期盛行的现代化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对埃及殖民地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研究。例如,罗伯特·蒂格诺开宗明义地指出,英国殖民当局对埃及现代化产生了影响,英国殖民官员致力于埃及社会的彻底现代化。也有国内学者把殖民地时期埃及历史置于现代化视野下开展研究。(4)Robert L. Tignor, Modernization and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Egypt, 1882-1914,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ⅶ;哈全安:《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铁铮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再次,与“文明使命”论相反,埃及、中国和其他亚非拉国家主流学者洞悉殖民主义的本质,如实书写埃及殖民地时期历史,讴歌埃及人民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反殖斗争和独立运动。埃及开国元勋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中指出,政治革命就是“从一个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暴君统治下或者从违反人民期望而驻扎在祖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手中,恢复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5)[埃及]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革命哲学》,张一民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7页。他是指他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所进行的反殖反封斗争,也就是把埃及“从外国枷锁中解放出来”,而“(英国殖民统治下表面的)民主只是独裁的面纱”。(6)Abdel Nasser,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Vol. 33, No. 2, January 1955, p. 199.以阿卜杜·拉赫曼·拉斐伊(1889~1966年)为代表的埃及历史学家,揭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本质,讴歌埃及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7)参见[埃及]阿卜杜·拉赫曼·拉斐伊:《奥拉比革命与英国的占领》(阿拉伯文),1937年第1版,开罗:知识书社1983年版;[埃及]阿卜杜·阿吉姆·拉姆丹:《纳赛尔之前的埃及》(阿拉伯文),开罗:埃及图书出版总局1995年。郭应德、杨灏城等中国学者以埃及人民为中心,书写英国的殖民侵略与殖民统治、埃及民族独立运动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政治的历史。(8)参见郭应德:《阿拉伯史纲(610—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杨灏城:《埃及近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四,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埃及殖民地时期的政治进行迂回曲折地解构性叙述,粉饰英国的殖民统治。一些西方学者夸大细节和局部,以生动的笔触叙述埃及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同时把“殖民地”局限于欧洲殖民者在埃及聚居的社区。(9)James Whidden, Egypt:British Colony, Imperial Capital,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9.相关研究回避和淡化当时埃及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新经济社会史的书写方式,集中展示当时非主流事物,如埃及殖民地时期的性工作者与妓院等。(10)Francesca Biancani, Sex Work in Colonial Egypt, Women, Modernity and the Global Economy, London: L. B. Tauris Co. Ltd., 2018.这些西文文献对埃及殖民地时期历史的破碎化叙述,虽然丰富了原本复杂多样的历史叙事,而且可读性强,赢得了学界和部分读者的赞誉,却从根本上回避了英国殖民主义与埃及人民独立斗争这对根本矛盾,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亦不容小觑,需要予以警惕和辨析。
由于掉进西方学术陷阱,或者受到渗透力强的西方学术思潮和学术话语的影响,近年来以后殖民主义形式出现的(新)殖民史学,甚至在殖民主义的重灾区非洲卷土重来。(11)参见毕健康:《殖民史学在非洲卷土重来》,载《历史评论》2021年第6期。无论西方的帝国史学或殖民史学,抑或后殖民主义包装下的(新)殖民史学,还是以新经济社会史面貌出现的对殖民主义的破碎化叙述,都是改头换面的 “文明使命”论。在这种话语体系中,殖民主义是拯救东方野蛮民族或“半文明人民”的“文明使命”。“公开而愉快的”种族主义者轻蔑地使用“黑鬼”(nigger)、“沃格”(wog)和“吉波”(gyppo)等称呼所有类型的埃及人,佛罗伦萨·南丁格尔把阿拉伯人描绘成“介于猴子和男人之间的中间种族,是最丑陋、最奴性的面容”,亨利·韦斯特卡形容埃及人吃饭“像食槽里的猪”(12)James Whidden, Egypt:British Colony, Imperial Capital, pp. 88, 53-54, 58.,声称埃及精英把农民“当作狗一样对待”(13)Brome Weigall, A History of Events in Egypt from 1798 to 1914,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915, p. 222.,所以埃及农民是“文明使命”的目标,穆罕默德·阿里王朝是自由主义“改革”的目标。(14)James Whidden, Egypt:British Colony, Imperial Capital, p. 13.在对埃及和埃及人进行妖魔化叙事后,西方学者又将“东方暴君”、统治埃及达24年之久的克罗默勋爵吹捧为“埃及复兴的精髓”和“英国永远的光荣”。(15)Brome Weigall, A History of Events in Egypt from 1798 to 1914, p. 168.一些学者进而认为,英军占领使埃及进步巨大,以至于英国政府认为,撤离埃及无异于一种反人类罪。(16)Ibid., p. 241.这种叙事看似符合形式逻辑,却有违人类基本良知,更违背了基本历史事实。殖民主义从来就是以军事侵略、军事占领和铁血镇压为基础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英军对埃及的长期占领和英国对埃及政治的粗暴干预,激起了一代又一代埃及人民的英勇反抗,对埃及政治和现代化造成极为严重且深远的消极影响。“文明使命”论可以休矣。
一、 英国撤军谎言与对埃及的政治压迫
殖民主义叙事,往往夸大局部而掩盖事物的真相,因而具有迷惑性。在英帝国瓦解之前,“保护”其交通命脉是英国殖民侵略的首要目标,这也正是1882年英国悍然入侵并占领埃及的根本原因。这本来是基本的政治历史常识,但是许多西文著作通过渲染某些历史细节,突出英国国内政治或公众舆论在某些时候围绕从埃及撤军的分歧或争议,建构出一套英国原本无意在埃及长期驻军,只是为了保障埃及的政治秩序、促进埃及现代化而无可奈何地长期驻军的叙事体系。
(一) 撤军争论与撤军谎言
为了粉饰对埃及的野蛮侵略,1882年3万英军的侵略被叙述成“恢复(埃及)合法政府”。埃及民族领袖艾哈迈德·奥拉比被妖魔化成“暴徒”,抵抗侵略的埃及军民则被称为“乱党”。维多利亚女王认为,“奥拉比是反抗合法君主权威的叛乱领袖”。英国侵略军司令加内特·沃尔斯将军在布告中声称:“女王陛下政府派兵的目的是重建赫底威的权威。因此,军队只是在与反对殿下的武装作战……宗教、清真寺、家庭和财产将受到尊重……总司令将很高兴接待愿意协助镇压反抗素丹任命的埃及合法统治者赫底威的长老们的来访。”(17)James Whidden, Egypt:British Colony, Imperial Capital, pp. 74-75.残暴凶狠的武装侵略,被建构成“派兵”。(18)根据沃尔斯将军的官方报告,侵略造成2,000名埃及人死亡、234人受伤;W. S. 布伦特估计,死亡的埃及人约10,000人,英国人死亡57人、受伤380人、失踪22人。转引自James Whidden, Egypt:British Colony, Imperial Capital, p. 76。时任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拉斯顿在回答下议院提问时辩称,英国对埃及的占领是暂时的。1882年12月29日,洛德·格兰维尔在下议院宣布,一旦埃及恢复安定,英国立即撤军。(19)[埃及]穆罕默德·艾卜·加尔:《美国与1919年革命:威尔逊诺言之幻灭》(阿拉伯文),开罗:日出书社2019年版,第23页。达夫林勋爵被派到埃及进行调查,为如何统治埃及出谋划策,他被告知“英国政府打算很快开始从埃及撤军”。(20)Brome Weigall, A History of Events in Egypt from 1798 to 1914, p. 168.据说克罗默也主张英军尽快撤出埃及,他口出狂言:“给我2000人和权力,让我来处理英国政府和埃及政府之间的事务,我将保证在12个月内埃及不再有(英国)士兵。”(21)Robert L. Tignor, Modernization and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Egypt, 1882-1914, pp. 61, 69.据统计,截至1922年,英国先后做出撤军许诺不下66次。(22)[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迟越、王红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24页。克罗默虽然狂妄,却言不由衷,“担心”如果英军撤退,埃及统治阶级“不能控制其余人口”。(23)Robert L. Tignor, Modernization and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Egypt, 1882-1914, p. 87.
英国国内政坛围绕埃及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出于政治、战略和经济考虑,英国单独侵占埃及,因此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坚决反对撤军。英国右翼认为,必须把法国势力驱逐出埃及,埃及在英国的统治下保障安全,从而保障通往东方的交通大动脉畅通无阻。自由党左翼则警惕帝国主义扩张政策。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在野时攻击迪斯雷利的帝国主义政策,担心殖民冒险给英国财政造成巨大负担。1880~1885年执政的自由党内阁内部在埃及问题上分歧大。保守派主张采取断然措施,扑灭奥拉比起义。左派则感到,侵略埃及,使格拉斯顿政府背叛了自己的原则。(24)Ibid., pp. 13, 19-23.1885年出任首相的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重申,自由党政府制定的政策,在埃及的目标是恢复赫底威的权威和英军的撤退。索尔兹伯里似乎不愿继续占领埃及,命令沃尔夫与奥斯曼帝国达成从埃及撤军的协议。但这无非外交姿态而已,因为他当然认识到占领埃及的重要性,“是埃及而非君士坦丁堡成为英国在东地中海的新的战略中心”。克罗默争辩说:“重建埃及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从埃及撤军是愚蠢的。如果英国人从埃及撤退,就没有人可以运转复杂的政府体系。”(25)Ibid., pp. 82-84.
英军继续占领埃及,亦有一定的舆论基础。英军占领埃及之初,右翼报刊和活跃的帝国主义分子在反制主张撤退的左翼情绪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牵制了左翼,以便政府可以继续调整其埃及政策。但是,直到19世纪80年代晚期,这些集团才在帝国政策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英国多数公共舆论主张继续占领埃及。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言:“英国舆论没有做好从埃及撤退的准备,不放弃埃及”,尤其是保守党主张继续占领埃及。(26)Ibid., p. 87.
英国政界热闹一时的争论,以及资本幕后操纵但表面上自由的英国报刊舆论,为撤军谎言的叙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继续占领埃及的理由在殖民主义叙事下,显得高尚无比。在占领埃及的前十余年间,英国当局“承诺”,一旦埃及恢复秩序、苏伊士运河通畅,就从埃及撤军。然而,据说英国从埃及撤军影响到殖民当局对埃及的发展计划:“英国人局限于需要立即关注的项目和他们感到撤退后埃及人可能实施的项目。而且,在埃及的英国殖民当局对于国内的批评者可能解释为推迟撤军的项目,犹豫不决。这样的政策造成了巨大困难。英国人面临的尴尬是,国内对埃及的态度尤其是左翼批评者的态度,妨碍了积极的改革计划。”(27)Robert L. Tignor, Modernization and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Egypt, 1882-1914, pp. 22-23. 对于这种伪善的叙事,这里不烦讲述一个极为简单的事实,以揭露其真实面目。有一次,赫底威赛义德在王宫会见一位欧洲商人。他突然中断谈话,命令仆人关闭窗户。他说:“如果这位绅士闹感冒,会花费我1万英镑呢。”参见Robert L. Tignor, Modernization and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Egypt, 1882-1914, p. 41。
撤军谎言,被基本史实完全凿穿。从1924年扎格卢勒—麦克唐纳谈判到1927年萨尔瓦特—张伯伦谈判,再到1929年马哈茂德—亨德森谈判,1930年纳哈斯—亨德森谈判,1932年西德基—西蒙谈判,再到二战后举行的多轮英埃谈判,均以失败告终,其中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英军撤退。1946年英埃谈判失败,埃及愤怒地把埃及问题提交联合国,无果而终。1950年1月至1952年1月间,先后持续两年之久的英埃谈判失败,1951年10月15日华夫脱党首相穆斯塔法·纳哈斯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28)[埃及]阿卜杜·阿吉姆·拉姆丹:《纳赛尔之前的埃及》(阿拉伯文),开罗:埃及图书出版总局1995年版,第42-43页。1936年英埃谈判是唯一一次没有失败的谈判,其中撤军问题谈得最为艰难。英国不但坚持在埃及驻扎占领军,而且拒绝、拖延英军从开罗和亚历山大撤退到苏伊士运河区。在埃及宣布废除1936年条约后,埃及人民在苏伊士运河区发动了持续不断的反抗英国占领军的抵抗运动,或称为英军与埃及准军事部队之间的消耗战。然而直到1952年七月革命成功后,新生的纳赛尔政权与英国进行了极为艰难的谈判,英埃才就1956年英国完成从埃及的撤军达成协议。英军于1956年6月撤出埃及,3个多月后就又伙同以色列和法国侵略埃及,重演1882年入侵埃及那一幕!这些最基本的史实充分说明,英军自从1882年入侵埃及之后,就一直赖在埃及,从1924年到1952年持续了28年的双边谈判,谈不走英国占领军;只是在纳赛尔发动七月革命后,英国才无奈地撤军。即便如此,英帝国阴魂不散,1956年又妄图重新占领埃及。所以,关于英国撤军的叙事,无非混肴视听、掩人耳目的撤军谎言,为的是粉饰英国对埃及的殖民统治。
(二) 英国的超高压政治压迫
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29)《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卷,第114页。军队作为最重要的国家机器,是国家维护统治不可或缺的专政工具。长期驻扎埃及的英国占领军,是维护英国殖民统治最重要、最直接的暴力机关。不仅驻军时时刻刻威胁埃及人民,而且英国动辄另外派遣舰队驶向亚历山大示威,向埃及当局施加强大压力。1924年11月英国借口埃军总司令兼苏丹总督李·斯塔克在开罗遭到暗杀,向萨阿德·扎格卢勒领导的第一届华夫脱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当扎格卢勒政府无法满足最后通牒的无理要求时,英军占领了亚历山大海关大厦。由于埃及议员提出以埃及人取代英国人,担任埃军总司令,1927年5月29日英国派遣舰队到亚历山大和塞得港武力示威。(30)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Fourth Edition,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83, 285.1928年3月4日,英国政府不满埃及众议院审议集会法,第三次威胁使用武力。英国不吝使用武力,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下面以克罗默玩弄赫底威阿巴斯二世(1892~1914年在位)的1892~1894年政治危机和1942年“二四”逼宫事件(31)1942年2月4日发生,又称“阿比丁宫逼宫”事件。为例,具体说明英国殖民当局是如何赤裸裸地动用英国驻军,对埃及进行超高压政治压迫的。
赫底威(32)埃及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属地,其最高执政者由奥斯曼帝国任命。1867年,埃及的最高执政者伊斯梅尔及其后继者从奥斯曼帝国获得“赫迪威”称号。陶菲克(1879~1892年在位)引狼入室,甚至在1882年英军炮轰亚历山大时乞求英军保护,自然对英国殖民者言听计从,俯首帖耳。陶菲克1892年去世,年仅18岁的阿巴斯二世继任赫底威。克罗默洋洋得意:“我很快就把他玩于我的掌股之间,而他却浑然不知。”(33)Robert L. Tignor, Modernization and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Egypt,1882-1914, p. 156.1892年11月,他向索尔兹伯里报告:阿巴斯二世“在一些小事上愚蠢透顶,但是他太年轻,缺乏经验,所以不要对他匆忙做出判断。我用大白话但不友好的语言,给他上了一课,教训了他一通。我不觉得我暂时会与他难以相处”。(34)Ibid., pp. 156-159.1893年1月13日,他给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罗斯伯里写信:“这个年轻的赫底威显然要制造一大堆麻烦。他是极为愚蠢的青年人,不知道怎么与他打交道。……我觉得,他迟早得栽大跟斗,越早越好。困难在于难以找到合适的场合,以合适的方式给他一个教训……这个年轻人头脑发热,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问题就出在这里。”(35)Ibid., p. 159.
克罗默把埃及的最高执政者、名义上由奥斯曼帝国素丹任命的赫底威阿巴斯二世当作乳臭未干的小子训斥,当然是对埃及的政治压迫,必然引起阿巴斯二世的坚决反抗。1893年1月15日,阿巴斯二世在没有与克罗默商量的情况下,突然改组内阁,任命侯赛因·法赫里为埃及首相,取代穆斯塔夫·法赫米。撤换法赫米,是因为阿巴斯二世认为他是英国人的傀儡。危机的引爆点是赫底威警惕地注意到内政部的英国官员签发通告,命令各省官员向内政部的英国警察局长而非内政部长报告工作。克罗默在得到通报后,迅速做出激烈反应。他会见赫底威,要求赫底威承诺,在克罗默在与伦敦政府商量此事之前,不要公开宣布。克罗默声称,赫底威没有征求英国方面的意见就撤换首相,是越权行为。阿巴斯二世则指出,他作为赫底威有权罢免和任命大臣。阿巴斯二世拒绝退步,克罗默便向伦敦发出电报,建议英军接管电报局、占领一切政府机构。1月19日,克罗默又向伦敦发电报,要求向埃及增兵。他说,如果英国驻军得不到加强,他不能负责(埃及的)公共安全。虽然格拉斯顿对一位内阁同僚说:“我的生命对我完全是负担。派军队到埃及之日,就是我在西敏寺纵火之时。”然而,英国的确向埃及增兵了。在英国占领军的刺刀之下,阿巴斯二世屈辱地让步,正式答应:一切重要事务遵从英国人的“建议”。(36)Robert L. Tignor, Modernization and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Egypt, 1882-1914, pp. 164-166.这难道不是英国殖民当局动用占领军,直接对埃及进行政治压迫,剥夺埃及主权和政治决策权的铁证吗?
纳赛尔回忆到,在1942年“‘二·四’逼宫”事件之前,埃及军官们只爱闲谈玩乐,“现在开始谈论着牺牲和为保卫(埃及人民)尊严而献身的决心”(37)[埃及]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革命哲学》,第8页。,因为这个事件对埃及军人而言是奇耻大辱。为了扶持已经蜕化变质的亲英政党华夫脱党主席纳哈斯上台执政,英国不惜采用最后通牒的野蛮行径。在此情势下,1942年2月3日,法鲁克国王(1937~1952年在位)(38)1936年埃及国王福阿德去世,王储穆罕默德·法鲁克继承王位,1937年达到法定年龄正式登基执政。邀请纳哈斯组建联合政府,遭到纳哈斯的拒绝。时任英国驻埃及大使迈尔斯·兰普森通过王室总管,再次要求法鲁克国王授权纳哈斯组建华夫脱党政府。2月4日下午,法鲁克国王召集所有政党和其他政治领导人到阿比丁宫商议对策,而王室总管已经收到兰普森大使的最后通牒:“除非我在下午6点之前听到纳哈斯帕夏被要求组阁,否则法鲁克国王陛下必须承担后果。”(39)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p. 348.正在开会的埃及政要在听到宣读的最后通牒后,决定立即向英国大使发出由他们所有人签名的抗议照会:“英国的最后通牒构成了对埃及独立的攻击、对埃及内政的干涉,违反了英埃联盟条款。因此,国王无权接受损害国家独立的条件。”兰普森拒绝接受这封抗议照会,反而调集英军坦克、装甲车和其他部队包围阿比丁宫。(40)Ibid., p. 148.在斯通将军的陪同下,兰普森率领一队配带左轮手枪的英军官兵,闯入王宫。面对坦克包围和左轮手枪,在赤裸裸的退位威胁下,法鲁克国王屈辱地屈服。(41)James Whidden, Egypt:British Colony, Imperial Capital, pp. 74, 166-167.
这些史实铁证如山,证明殖民主义的撤军叙事纯属谎言,在埃英军无论称为占领军还是驻军,都是英国殖民主义压迫埃及的暴力机关。当然,面对这种超高压政治压迫,英勇的埃及人民绝不屈服,前赴后继地开展民族独立斗争。
二、 民族独立运动与埃及“三次革命”
反抗压迫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埃及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和主权独立,前赴后继地发动民族独立运动,开展反抗殖民统治的正义斗争。在英国对埃殖民统治的70年间,埃及争取独立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从精英运动到大众运动的“三次革命”,即纳赛尔在《埃及革命》中所指出的埃及 “必须经历的三次革命——奥拉比革命、1919年革命和1952年七月革命”,(42)Abdel Nasser,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p. 202.最终成功驱逐殖民主义,获得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
(一) “奥拉比革命”
从拿破仑入侵到19世纪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下埃及艰难曲折的发展,埃及现代化逐步启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萌生,在欧洲资本的渗透和官僚资本的挤压下,民族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同时,得益于近代西式教育,尤其是游学欧洲的先知先觉的埃及近代知识分子和埃及新式世俗教育的发展,民族独立思想逐渐产生和发展。埃及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主体,主要是受到政治压迫的埃及统治精英(如阿巴斯二世),土著军官和文职官僚,以及受过教育或半教育的城市阶层。所谓奥拉比革命,本质上是以土著军人为代表的脆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自发性民族独立运动,是失败的早期精英型民族主义运动。
艾哈迈德·奥拉比(1841~1911年)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小地主家庭,幼年在乡下念私塾,8岁时进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语言和宗教;13岁入伍,开始其戎马生涯。奥拉比得到当时的执政者赫底威赛义德赏识,6年内从无名小卒晋升为陆军中校。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口才极好,感染力强,颇具打动民众心魂的领袖品质和巨大魅力。(43)[埃及]阿卜·拉赫曼·拉费伊:《奥拉比革命与英国的占领》(阿拉伯文),第447-448页。包括奥拉比在内的埃及土著军官,深受土耳其族和契尔克斯族军官的压迫,组建自己的政治团体。1876年,一些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土著军官成立秘密组织青年埃及协会。1878年,咨议会部分议员为了反对“欧洲内阁”企图解散咨议会,秘密成立祖国协会。祖国协会成员除少数知识分子外,大多是开明地主。青年埃及协会主要代表初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基础较为薄弱,于是在地主阶级中寻求同盟军,1879年与祖国协会合并,改名为祖国党,以便“把祖国从屈辱、贫困、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44)杨灏城:《埃及近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11月4日,祖国党改组,奥拉比任党主席,但依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相当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对于埃及独立运动和民族国家的构建,祖国党贡献巨大,提出响亮而深得民心的口号——“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45)同上,第179-180页。。
由于殖民主义的傀儡、“欧洲内阁”首相努巴尔压迫土著军官,1879年发生了“二·一八”事件。土著官兵抗议示威,扣留努巴尔和财政大臣、英国人威尔逊,并占领财政部。这次事件标志着土著军人作为一支政治力量,首次登上埃及政治舞台。事后,赫底威伊斯梅尔暂时抛弃努巴尔,任命其长子陶菲克组阁,此即第二届“欧洲内阁”。英法通过在埃及内阁中继续任职的财政大臣威尔逊和建设大臣布里尼叶,在政治上控制埃及,在国债问题上压榨埃及,引起以议员为代表的地主豪绅的不满。1879年4月2日,在祖国党支持下,议员们拟定“民族法案”,反对宣布埃及财政破产,要求组建对咨议会负责的完全由埃及人组成的内阁,英法的双重监督仅限于对政府财政机构的监督。由于触犯了英法利益,赫底威伊斯梅尔被废黜,1879年6月陶菲克被任命威赫底威,陶菲克于1879年9月下令恢复英法的双重监督。在这种情况下,1881年9月9日奥拉比率领开罗驻军约4,000人在阿比丁宫举行武装示威,代表埃及民族提出三点要求:(1)利亚德独裁内阁下台,目的在于打倒这个内阁所代表的外国监护;(2)建立欧洲式议会,目的在于推翻赫底威的专制统治制度;(3)把军队员额扩大到1.8万人,以保护国家的独立。(46)[埃及]阿卜杜·阿吉姆·拉姆丹:《纳赛尔之前的埃及》,第40页。陶菲克不得不让步,1882年2月4日巴鲁底内阁组成,祖国党成员占多数,奥拉比出任陆军大臣,实际执掌内阁。该内阁制定的《基本法》是埃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确立了内阁向议会而非赫底威负责,议会有权讨论、通过与国债和贡赋有关的国家预算等重大原则,削弱了赫底威专制统治,沉重打击了英法殖民势力。同年7月11日,英军乘法国舰队驶离亚历山大之机,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由于双方实力悬殊,英军收买部落酋长和赫底陶菲克公然投敌,以及奥拉比陷入了英军的战略欺骗陷阱,英军偷渡苏伊士运河,从东线直扑开罗,9月14日占领开罗。奥拉比等被捕受审,遭到流放,抵抗殖民侵略的奥拉比革命失败。
(二) “1919年革命”
奥拉比革命的失败,使埃及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埃及民族运动暂时陷入低潮,但是精英型民族主义运动很快恢复和发展,其典型表现就是上述阿巴斯二世受挫的抗英斗争。阿巴斯二世并不甘心成为英国殖民势力的傀儡,直到1914年被英国人废黜。在他出任赫底威期间,既对英国殖民当局妥协,又暗中与英国斗争,支持埃及民族独立运动,他向1907年成立的新祖国党创始人穆斯塔法·卡米勒提供财政支持和政治掩护。20世纪初年发生的民族主义事件,促使埃及民族运动从精英运动逐渐向大众运动过渡。
1906年亚喀巴危机中,埃及与奥斯曼帝国围绕西奈半岛边境产生纠纷,英国坚决支持埃及。在整个事件中,埃及民族主义报纸一直站在奥斯曼帝国一边,克罗默“很委屈”,不解其意。正如艾哈迈德·卢特菲所指出,这次危机中埃及表现出的亲奥斯曼帝国情绪,不是埃及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利益不闻不问,而是反英情绪的曲折表达,是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抗议,埃及人民希望在奥斯曼帝国的庇护下实现独立。同年发生丁沙微事件,克罗默下令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与英军冲突的52名丁沙薇村民,判处其中4人死刑,2人终身苦役,以此吓唬埃及人民。结果适得其反,英国左翼几乎一致谴责特别军事法庭的严厉判决。伯纳德·肖尖酸刻薄地攻击克罗默和在埃及的英国官员,(47)Robert L. Tignor, Modernization and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Egypt, 1882-1914, pp. 280-282.克罗默因遭猛烈抨击而不得不于翌年辞职。丁沙微事件引爆了埃及的反英民族情绪,穆斯塔法·卡米勒将之视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决定性时刻,由此扛起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大旗。翌年,埃及出现了一批现代意义的政党,主要有代表大地主利益、亲英的乌玛党,卡米勒领导的新祖国党,赫底威阿巴斯二世支持的宪政改革党等等。(48)[埃及]阿里·丁·赫勒尔:《1803~1999年埃及政治制度的发展》(阿拉伯文),开罗:开罗大学政治研究中心1999年版,第62-66页。直到一战结束爆发1919年革命,新祖国党是埃及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政党。1908年卡米勒去世,开罗的学生几乎全部来为他送葬,送葬队伍中还有来自偏远乡村的农民,(49)[埃及]穆罕默德·萨布里·索布尼著:《埃及问题:从波拿巴到1919年革命》(阿拉伯文),[埃及]纳吉·拉姆丹·阿忒耶译,[埃及]艾哈迈德·扎克里亚·舒尔格校,开罗:日出书社2019年版,第86页。原文法文版1920年出版。是埃及民族主义情绪的爆炸性示威。
穆罕默德·法里德是卡米勒亲自挑选的接班人,在他的领导下,新祖国党开始成功地争取城乡无产阶级。法里德成功地把民族主义引进到城市无产阶级之中。他一再呼吁关注工人们糟糕的工作条件、低工资和埃及产业工人低下的生活水平。新祖国党鼓励埃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谈判,举行罢工以达到改善生活的目标。1908~1909年新祖国党开始向劳工组织渗透,建立民族主义领导人主导的工会。1909年乌玛尔·卢特菲组织了民族主义者控制的第一个工会,随后的两年里又建立了其他工会。农村经济发生分化,农业无产阶级表现出初步的认同感,在更高程度上组织起来,出现合作社运动。然而,1914年阿巴斯二世被废黜和新祖国党开始式微,是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转折点,早期精英型民族主义运动结束。一战结束后勃然兴起的大众民族主义运动——1919年革命,由应运而生的萨阿德·扎格卢勒领导的华夫脱党接过大旗。
扎格卢勒(1857年或1860~1927年)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地主家庭。他在乡村接受传统教育后,于1871年来到爱资哈尔大学求学。在酝酿宗教改革的氛围中,扎格卢勒进入伊斯兰教改革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的圈子,深受其影响。1880年,他被任命为阿卜杜的助手,负责编辑官方的《埃及公报》。1892年担任上诉法院法官,致力于法律实践、伊斯兰法庭和司法现代化。1906年到1910年担任教育大臣期间,扎格卢勒致力于扩大埃及人的识字率。他增加了包括乡村小学在内的学校数量,并开设成人夜校。1910年扎格卢勒担任司法大臣,因与英国高级专员兼总领事基切纳关系不睦,于1913年辞去司法大臣之职。1913~1914年,他当选立法会议议员,并被选为副议长。在议会被无限期休会前的几个月里(1914年1月22日到1914年6月17日),他成为在野的反对派领袖。(50)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pp. 257-260.一战结束后,扎格卢勒领导遭到解散的一批议会议员,他们大多是乌玛党和新祖国党成员,组成代表埃及全民族的华夫脱党,要求埃及独立,(51)[埃及]阿卜杜·阿吉姆·拉姆丹:《纳赛尔之前的埃及》,第41页。领导1919年革命。
扎格卢勒作为世俗温和派的代表,比极端民族主义者或泛伊斯兰主义者更容易为科普特人所接受。同时,扎格卢勒及其同伴虽然在城市经济中崛起,但他们在出身和社会环境上仍然与埃及农村的小农群体保持着联系。1918年,他们比其他任何团体更有优势领导全国性民族主义运动。扎格卢勒着手组织一个特别代表团(52)“华夫脱”为阿拉伯文wafd的音译,意为“代表团”。,由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阿里·沙拉维和他本人组成,拜访英国高级专员温盖特爵士,请求允许华夫脱去伦敦,向英国政府条陈埃及民族的要求。1918年11月11日,他们通过埃及首相提交了与温盖特面谈的请求,获准13日与温盖特爵士晤谈。在这次谈话中,温盖特以华夫脱没有正式身份为由,反对他们前往伦敦。因此,就在11月13日当天,扎格卢勒着手组织一个可以自称代表国家发言的代表团,即“埃及代表团”(Al-WafdAl-Misri),由6人组成,华夫脱党由此诞生。10天之内,又有7人加入,共13人。根据华夫脱党党章第2条,该党宗旨是“通过一切合法与和平手段,即通过与英国谈判,寻求埃及的完全独立”;党章第8条规定,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在代表团中加入额外的成员。(53)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pp. 260-261.直到1918年底,英国当局设法阻止华夫脱党和其他代表团前往伦敦或巴黎。巴黎和会开幕(1919年1月18日)在即,华夫脱党在政治上更加活跃,1月13日扎格卢勒就埃及独立权利发表讲话。他认为,埃及问题是国际问题;埃及的政治地位不可能在1840年伦敦条约的基础上发生任何改变,除非根据巴黎和会的决定;埃及的独立早在1840年就得到了穆罕默德·阿里和欧洲的保障;土耳其(对埃及的)主权已被废除。华夫脱参加巴黎和会的目标,是促使巴黎和会做出决议,废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承认埃及独立。随后,给各国元首和伦敦下议院拍发了一系列电报,但如同石沉大海。(54)Ibid., p. 263; 阿卜杜·阿吉姆·拉姆丹:《纳赛尔之前的埃及》,第159页。
扎格卢勒领导的独立运动遭到英国的暴力镇压。华夫脱党定于1919年1月31日在扎格卢勒府邸举行群众集会,英国驻军直接干预,粗暴阻止了这场集会。3月6日,沃森将军将扎格卢勒和华夫脱党成员召到他的总部,当面威胁他们。3月8日,逮捕了扎格卢勒、伊斯梅尔·西德基和哈马德·马赫尔,并将他们流放到马耳他。埃及人民不畏强暴,开罗、亚历山大和其他城市发生了一系列示威活动,交通运输业工人、法官和律师举行了大规模罢工。学生和妇女也参加示威,独立革命蔓延到外省各地,人们切断了铁路、电报线,捣毁了邮政所。英国占领军残酷镇压,甚至动用了飞机。英国方面估计,冲突导致1,000名埃及人死亡,36名英军官兵死亡。有的地区如里夫基,宣布起义和独立。(55)[埃及]穆罕默德·艾卜·加尔:《美国与1919年革命:威尔逊诺言之幻灭》(阿拉伯文),开罗:日出书社2019年版,第29-30页。面对民族独立运动的熊熊大火,英国不得不改变策略,艾伦比将军代替温盖特爵士担任高级专员。3月25日,艾伦比抵达开罗。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暗示,英国将继续对埃及的“保护”地位,引发了更多的罢工,最严重的是国家雇员停工三天。当伦敦确信巴黎和会将承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时,决定释放扎格卢勒及其同伴。4月7日,艾伦比宣布释放扎格卢勒等人,华夫脱党最终于4月11日决定前往巴黎。然而,华夫脱(埃及代表团)到巴黎仅3天后,1919年4月22日,驻开罗的英国殖民当局就散发美国驻埃及代表的声明,宣布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年、1912~1920年在任)承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56)[埃及]阿卜杜·阿吉姆·拉姆丹:《纳赛尔之前的埃及》,第162页。
华夫脱党领导埃及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给了英国殖民主义一记重拳,旧的统治形式难以为继。1922年英国不得不单方面发表“二·二八”声明,宣布废除对埃及“保护”,承认埃及“独立”,但是“四点保留”使埃及的独立有名无实:保障英帝国在埃及的交通安全;保护埃及免遭一切外来侵略;保护在埃及的外国利益和少数民族的利益;英埃共管苏丹。(57)M. W. Dal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ume Two,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50.埃及虽然1930年获得关税自主权,1937年加入国际联盟,并在1936年英埃谈判中废除了以治外法权为主的外国人特权,1949年最终废除混合法院。然而,以保护英帝国交通安全和保护埃及免遭外来入侵为借口,英国占领军继续驻扎埃及,最终使1919年革命半途而废,沦为“未完成的革命”。这场未完成的革命,由纳赛尔接棒,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1952年七月革命,最终驱逐了英国殖民主义,实现了埃及独立的梦想。在此之前,1923~1952年以英国驻军为后盾的英国殖民势力,肆无忌惮地干预埃及政治,造成埃及政党政治畸形变态和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
三、 英国殖民主义与埃及政治危机
“二·二八”声明使埃及获得形式上的独立,埃及的政治生态以1923年宪法的制定为起点,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英国殖民当局的授意下,三十人立宪委员会拟定了宪法文本,建构出以国王为中心的政治权力结构。国王兼掌立法权和行政权,享有法律创制权、批准权和颁布权。国王若不批准某法案,必须退回议会重新审议。如果议会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即成为法律。国王拥有解散众议院,召集议会两院开会及推迟、解散议会会议的权力。国王任命五分之二的参议员和参议院议长。国王享有广泛的行政权,行政机关由国王和内阁组成。国王建立和改组内阁各部及总署。国王有权任命大臣、高级宗教官员、王室侍从官员和武官。国王兼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军官。国王享有宣战权,缔结和平条约、同盟条约、商业及航行条约之权利。(58)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8页。这种表面上国王重权在握,实际上由英国幕后操纵的政治结构,造成埃及政党畸形裂变、宪法危机和政治动乱。
(一) 埃及政党与政党裂变
1923年宪法为代议制民主和政党政治提供了极为有限的运作空间。1923~1952年间,埃及的政党可分为左翼政党(如1921年成立的埃及社会党和1922年成立的埃及共产党),激进政党(如埃及女儿党或埃及青年党),自由贵族党(以立宪自由党和新祖国党为代表),贵族党或保皇党(福阿德国王支持建立的联盟党和1930年西德基成立的人民党),民族主义政党即华夫脱党。埃及的政党数量不少,投机性强,不时分裂组合,如从华夫脱党分离出萨阿德党和人民党,但是总的格局是华夫脱党在选举中一党独大却屡遭打压,小党投机成为国王或英国殖民势力的帮凶。
立宪自由党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是1923年宪法的始作俑者。1922年10月29日立宪自由党成立,起草宪法的三十人委员会全部入党,原乌玛党党员、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达官显贵也加入这个政党。该党每年收取5埃镑党费,把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党章要求结束英国占领,实现埃及的彻底独立;坚持苏丹不从埃及分离出去,保持对苏丹的主权和权利;开放关税协议谈判,进口商品关税平等,保护埃及制成品。(59)[埃及]阿卜杜·阿吉姆·拉姆丹:《纳赛尔之前的埃及》,第325页。事实上,立宪自由党从华夫脱党分裂而来,但并不意味着大地主阶级与华夫脱党分道扬镳,而是大地主阶级在华夫脱党和立宪自由党之间的分裂。而且,立宪自由党并不尊重宪法和宪政,其在政治上的投机加剧了该时期埃及政治的动荡。
保皇党则是国王专权弄权、打压华夫脱党的工具。1925年1月,叶辛·易卜拉欣帕夏为首的联盟党宣告成立,实际上由王室副总管哈桑·奈什艾特帕夏代表王室幕后操纵。联盟党出版《联盟报》,收购另一份法文报纸《自由报》作为自己的喉舌。联盟党臭名昭著,埃及人民十分厌恶,因而需要成立一个新的政党,此即人民党。1930年11月17日人民党成立,伊斯梅尔·西德基帕夏担任党主席,出版《人民报》日报。随后西德基帕夏公布党章,共7条。人民党党章最受关注的有两点:第5条规定保障国王权利,暴露了这个政党的保皇党本性;与英国就埃及与英国关系问题达成协议。(60)同上,第330-331页。后者显然是承认“二·二八”声明的委婉表述。众所周知,人民党是国王专权,支持更加独裁的1930年宪法的工具。1931年选举,遭到了除联盟党、人民党和新祖国党之外所有政党的抵制。
华夫脱党是这个时期埃及规模最大,、动员能力最强和政治上最重要的政党。华夫脱党最初的党员,大多来自乌玛党,有的来自新祖国党,随后大商人、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加入。1921年从华夫脱党分裂出立宪自由党时,这些资本家和大商人脱离华夫脱党,选择加入立宪自由党。“华夫脱党领导层仅来自于大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没有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大多数党员则来自大地主阶级。”(61)[埃及]阿卜杜·阿吉姆·拉姆丹:《纳赛尔之前的埃及》,第315、155页。
华夫脱党代表埃及大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其特殊性在于,该党以争取埃及民族独立的政党——全民党的形式出现。阿拉伯文“华夫脱”,意为埃及人民授权、代表埃及全民族与英国进行谈判的“代表团”。华夫脱党向巴黎和会发出呼吁,废除英国的“保护”,实现埃及独立。不同阶级和阶层以书面签名的方式,向华夫脱党授权的签名滚滚而来,以至于英国殖民当局要求埃及内政部予以阻止。在组织结构上,党主席享有权威,党章授予党主席充分的权力。党章第10条规定,“华夫脱党决议以多数人的意见颁布,如果票数相等,以党主席支持的一方意见为准”。第21条规定,每个党员承担自己的旅费和住宿开支,这不单反映了大地主—资产阶级的财富,而且说明华夫脱党把民族独立事业放在第一位。第26条就任命“埃及华夫脱中央委员会”做出规定,在阿卜杜·拉赫曼·法赫米贝克担任秘书长时,中央委员会成为党的核心,渗透到埃及的各个方面,在埃及的城市和农村影响巨大。(62)同上,第154页,第318-319页。
华夫脱党以民族团结和埃及独立为历史使命,却在抵抗占领和埃及国内政治阴谋中遭受夹击。在英国殖民势力和王室的打压下,华夫脱党不但没有合并其他政党,组成统一、团结的力量,自身反而不断分裂。1921年华夫脱党发生第一次分裂,原因是激进的扎格卢勒派和温和的阿德利派在民族事业的解决上发生分歧。在分裂出去的人中,科普特人占1/9,穆斯林占1/3,他们组成了立宪自由党。第二次分裂发生在1932年,是由围绕民族内阁问题产生的分歧造成的。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批准,“为独立而斗争”暂告一段落,政党倾轧更加激烈。原本华夫脱党代表的“民主大厦”发生裂痕和缺口,为反动势力分而治之提供了机会,1937年华夫脱党发生第三次分裂。这是对华夫脱党影响最大的一次分裂,诺格拉西和艾哈迈德·马赫尔从华夫脱党分裂出去,另外组建萨阿德党。1944年,华夫脱党发生第四次分裂,同样是由于争权夺利。(63)同上,第314、320-321页。然而,得到埃及人民明确授权、以埃及独立为使命的华夫脱党,同样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破坏民主原则。华夫脱党认为,任何其他不在其旗帜之下的机构或团体,都妨碍了自己的政治工作或民众工作,它们就是不合法的机构或团体,应当予以抵制、打击和解散。
(二) 华夫脱党一党独大与埃及政治危机
历史的讽刺在于,曾经坚决抵制1923年宪法的华夫脱党,竟然成为这部宪法的“受益者”和维护者。1923~1952年的28年间,只要华夫脱党不抵制选举,总是以较大优势在绝大多数议会选举中获胜:1923~1924年第一次选举中,华夫脱党获得195席(总共214席);1925年选举中,华夫脱党获得113席(总共222席);1926年选举中,华夫脱党获得171席(总共211席);1929年,华夫脱党获得216席(总共232席);华夫脱党抵制1931年选举;1936年华夫脱党获得190席(总共232席);1938年议会选举中,当局使用一切手段作弊,华夫脱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1942年华夫脱党获得232席(总共264席);华夫脱党抵制1945年选举;1950年华夫脱党获得228席(总共287席)。(64)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第65页。
由于国王大权在握、小党投机,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华夫脱党备受打压,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执政。在这28年间,王室执掌政权近19年,华夫脱党执政不到8年,与立宪自由党联合执政2年。选举产生由扎格卢勒领导的第一届华夫脱党内阁仅存在10个月,就在英国的高压下不得不辞职。君主立宪制的28年,埃及政治腐败泛滥、政治动乱不断、政党政治畸形发展。38届内阁走马灯式频繁更迭,内阁的平均寿命不到9个月。在1952年的前6个月里,4届内阁先后执政,平均每届内阁仅持续一个半月。第三届阿里·马赫尔内阁只维持了33天(1952年1月27日至3月1日),而最后一届内阁即艾哈迈德·纳吉布·赫拉利内阁只存在了不到两天(1952年7月22日至24日凌晨)。(65)[埃及]国家社会与刑事问题研究中心编:《1952~1980年埃及社会大全·政治建设卷》(阿拉伯文),开罗,第318-319页。议会也动辄被国王解散,极为不稳定。除1945年选举产生的那届议会,其余议会均没有完成宪法规定的任期,而被国王提前解散。1923年宪法规定,参议员任期10年,每5年更新一半任命和选举产生的参议员。众议员由选举产生,任期5年。然而,1923~1952年间先后举行了10次议会选举,平均2.9年举行一次选举,议会沦为国王手里随意摆弄的政治花瓶,并非真正的代议制政治机关。
这个时期埃及参与政治竞争的各方力量,无论国王还是英国殖民当局,华夫脱党还是其他小党,都不尊重宪法,不遵守代议制宪政政治规则,全然无视宪法条文。践踏宪法和代议制规则,造成埃及宪法危机此起彼伏,动摇了整个制度的合法性。据研究,从1923年宪法颁布到1936年的13年间,只有3年实施宪法。在短短的28年间,埃及共发生了5次宪法危机(1925年、1928年、1930年、1937年和1944年)。(66)[埃及]阿里·丁·赫拉勒:《1803~1999年埃及政治制度的发展》,第128、106-118页。”1930年西德基干脆废除1923年宪法,颁布更加专制的1930年宪法。1935年,华夫脱党为首的绝大多数政党组成联合阵线,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和政治抗议,迫使当局恢复1923年宪法,史称“1935年革命”。
当然,以华夫脱党为首的政治力量并不甘心屈服于国王专权弄权,多次领导护宪运动。华夫脱党在1925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再次获胜后,开始联络和团结其他政党,《华夫脱报》呼吁举行国是会议,要求恢复代议制政治生活。根据1923年宪法第96条授予议会的权利,无需国王召集,议会两院定于1925年11月21日自动举行会议。由于警察封锁了议会大厦,议员们在大陆饭店举行会议,发表抗议内阁违宪行为的决议,选举扎格卢勒为议长、立宪自由党的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和新祖国党的阿卜杜·哈米德·萨阿德为副议长。随后,根据1923年宪法第65条的规定,议会做出了不信任内阁的决议,(67)[埃及]阿里·丁·赫拉勒:《1803~1999年埃及政治制度的发展》,第110-111页。开了议会维护自身权利、不顾国王或内阁反对自行召集会议的先河。
在第二次宪法危机中,铁腕内阁先是将议会会议推迟一个月,而后于1928年7月19日发布命令,解散议会、将议会两院议员选举或任命推迟3年、国王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敕令从而直接执掌立法权,或称为“国王对宪法和议会的第二次政变”。虽然政府企图阻止议员们开会,1928年7月28日他们成功地在穆拉德贝克府邸举行会议,做出国王废止宪法、解散议会两院的敕令无效的决议,因为议会仍然存在,有权利举行会议。议会发布决议,谴责内阁违宪的政策,撤回对内阁的信任。1928年11月17日,议会两院在《埃及公报》社再次举行会议,重申此前的决议和内阁的责任。(68)同上,第113-114页。
1930年是埃及政治波涛汹涌的年份。是年,扎格卢勒昔日的同伴、曾经与扎格卢勒一起被流放到塞舌尔的伊斯梅尔·西德基,成立亲王室内阁,充当国王的傀儡,废除1923年宪法。1930年6月21日西德基发布命令,议会会议推迟一个月举行,原定两天后即6月23日举行议会会议。面对这种高压政治,众议院议长维梭·瓦西夫和参议院议长阿德利·叶肯达成一致,必须举行议会会议,在议会两院会议上宣读西德基首相的上述命令。瓦西夫拒绝向西德基承诺,即宣读命令后议员不进行辩论。西德基政府用铁链封闭了议会大厦,并派警察包围议会大厦。当参议员和众议员到达时,议长瓦西夫招来议会卫兵,命令卫兵移除铁链,打开议会大门。议会卫兵服从命令,因而这一天史称“砸碎枷锁日”。(69)同上,第125-126页。
宪法危机和政治动乱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宪法授予国王巨大权力。国王手握重权,鼓励小党与之勾结,参与执政而分得一杯羹。国王动辄解散议会,搞垮华夫脱党领导的内阁。国王独自行使内阁的一些权力,如任命高级宗教官员、王室侍从官、外交使节及(由任命产生的)参议员议员,授予勋章和绶带等,而且妄图通过1930年宪法使之合法化。结果,与华夫脱党频繁发生冲突,政治危机此起彼伏。在华夫脱党主席纳哈斯领导的7届内阁中,他不得不4次辞职(1928年6月、1937年12月、1944年10月和1952年1月)。法鲁克国王及其身边的官员建立法鲁克青年团,以不同于王室和国王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利用并加剧华夫脱党的内部分裂,在混乱的政治局势中火中取栗,扩大王室权势。(70)[埃及]阿里·丁·赫拉勒:《1803~1999年埃及政治制度的发展》,第132页。国王专权,迫使华夫脱党进行反击,埃及民族陷入了从国王手中夺回权力的激烈斗争。在萨阿德·扎格卢勒时期反击取得成功,游行队伍在阿比丁宫高喊:“萨阿德,或者革命!”但是,1937年革命失败了,当时人民群众再次走上开罗的街头,高呼“纳哈斯,或者革命!”(71)[埃及]阿卜杜·阿吉姆·拉姆丹:《纳赛尔之前的埃及》,第338页。
英国殖民势力是埃及政治动乱的罪魁祸首。1923年宪法建构的国王主导型政治权力结构,符合英国殖民主义利益,是英国在华夫脱党和国王之间实施分而治之,从中渔利的工具。扎格卢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外国势力包围下的国王大权在握有危险,那么,在外国势力控制下的国家,这就更加危险,更加严重了。由于军队的保护,王位安然无忧。留给国王的这种力量,实际上变成外国人的权利,他们用以损害祖国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72)同上,第351页。从根本上说,“二·二八”声明无非以英国占领军为基础,对埃及进行政治压迫的工具。英国殖民当局保留了与埃及的国家主权、自由和独立相关的最重要的权力,随时可以找借口干涉埃及内政外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名义上废除了“四点保留”,但是英国继续干预埃及政治。英军继续驻扎埃及,英国大使兰普森沉迷于动用英军,一再对埃及实施高压政策。英国的政治干预,包括威胁废黜国王,要求内阁辞职和组建符合英国利益的内阁。例如,当法鲁克向兰普森间接透露,打算在1937年12月罢免纳哈斯首相时,兰普森回应:“这可能是法鲁克的末日。”(73)James Whidden, Egypt:British Colony, Imperial Capital, p. 196.1943年4月,由于黑皮书事件,国王决定解散纳哈斯内阁,英国驻埃及大使(74)1936年条约签署和生效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改称大使。表示反对。当英国大使通知国王不再与诺格拉西合作时,诺格拉西首相于1946年2月辞职。所以,有学者得出结论:“离开伦敦的干预,就不能理解埃及政治危机的历史。每次内阁危机的背后,或是掩藏着英国的粗暴干预,或者由于埃英关系的发展变化。”(75)[埃及]阿里·丁·赫拉勒:《1803~1999年埃及政治制度的发展》,第131页。
四、 结语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资产阶级以廉价的商品,开拓世界市场,打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35-36页。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产物,殖民者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锐利武器征服世界,当然是历史的进步,开创了真正的世界历史。毋庸讳言,与欧洲资本主义相比,处于前资本主义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确处于落后状态。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是历史的进步,所以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献中,论述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7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86页。
埃及与印度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同样遭受英国侵略和殖民统治。资本主义作为先进的生产方式,瓦解了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埃及的封建主义,摧毁了当地传统工业,一句话,砸碎了旧世界,完成了破坏性使命。同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引进来,造成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乃至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艰难地开启建设性使命。以现代化学派的话语表述,就是启动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然而,破坏性使命与建设性使命孰轻孰重?显然,历史的丰富多彩意味着断语式结论逻辑上不周延,论证上有漏洞。本文以1882~1952年埃及政治为例进行考察,以具体史实证明殖民主义对埃及政治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破坏力强、建设性弱。根据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埃及人民是埃及的主人,英国殖民者没有任何托辞替埃及人民作主。英国对埃及的超高压政治压迫,侵犯了埃及主权和埃及人民当家作主的天然权利。这当然不是建设性使命,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非“文明使命”。相反,埃及风起云涌的反殖独立运动,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正义事业,是“文明使命”。逻辑和历史已然证明,1923~1952年间埃及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和政治动乱,根源在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和粗暴干预。此外,英国的殖民侵略和殖民镇压,造成埃及人民惨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这些事实不能一笔带过,更不容否认、不可粉饰。因此,就埃及政治现代化而言,建设性使命十分有限,殖民主义“文明使命”无从谈起。
以先进的资本主义取代落后的生产方式,推动历史进步,这是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建设性使命的意旨所在。然而,心怀白人优越感的殖民者秉持欧洲中心论,把上千万非洲黑人贩卖到美洲为奴,虽然促进了美洲的开发并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本原始积累和广阔的商品市场,却是以黑人的非人待遇和上亿黑人人口悲惨死亡为前提和代价的,是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页。狂热的白人种族分子把黑人和爱斯基摩人置于欧洲的动物园,(78)[美]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下册)》,叶建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5页。让游客观赏,暴露了殖民者最丑陋、最肮脏的灵魂。基督教有“原罪说”,极端的白人优越感下殖民主义犯下的羞于启齿的罪行,是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主义泛滥的“原罪”。为了掩盖这种滔天罪行,从基督教普世主义出发,杜撰和宣扬“文明使命”论,诓骗世人,掩人耳目。以拯救异端的灵魂、传播基督教的名义,促进东方发展这种占据道义制高点的“高尚”话语,行侵略、掠夺乃至杀人越货之实,实在有违资产阶级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博爱之价值。换言之,所谓“文明使命”事实上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审视,西方帝国史学或殖民史学渲染的“文明使命”论也于史无据,与现实不符。殖民史学或现代化学派宣扬殖民主义推动埃及现代化,主要指殖民地时期的埃及基础设施建设(如港口、铁路、邮政)和公共卫生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在英国侵略之前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后人执政期间,埃及基础设施、农田水利事业同样快速发展。因此,现代化的启动不是殖民主义的功劳,更非其“专利”,而是近代埃及的缔造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历史贡献,英国殖民统治反而中断了埃及自主型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英国殖民者在埃及修路建桥,建造港口,不是推动埃及现代化的高尚的人道主义行为或“文明使命”。恰恰相反,为的是剥夺和压榨埃及人民,正如牧场主饲养奶牛不是为了让奶牛每天吃青翠嫩草,而是为了挤奶挣钱。殖民当局兴修水利,大力发展棉花种植,以低价的棉花供应英国的棉纺织企业,再以廉价的棉纺织品倾销埃及市场,打击埃及民族工业,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一箭双雕。一方面,埃及畸形的单一经济卷入风高浪急的世界市场,任由西方资本宰割,经济危机频仍,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机遇和能力。同时,棉花种植抢占了粮食种植的耕地,埃及从世界粮仓变成粮食进口国,对外粮食依赖度越来越高,其恶劣影响至今祸害埃及人民。另一方面,宣扬埃及没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之类的“科学理论”,刻意抑制埃及工业发展,对埃及制成品征收8%的税,以抵消输入埃及的工业品8%的关税。难道这就是英国殖民者推动埃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善政良治?从1952年七月革命迄今,殖民主义给埃及造成的单一、畸形经济结构仍未得到彻底改变,可见其流毒之深重,影响之恶劣。如果比较全面和彻底地清除殖民主义流毒,在自主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彻底超越殖民主义,就可崛起为新兴工业国家。这反过来证明,唯有超越殖民主义,不受虚假的“文明使命”的蒙骗与危害,才能迎来真正发展的春天,践行真正的“文明使命”。因此,对于为殖民主义辩护或掩护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文明使命”论的话语和言说,必须细致辨析,有力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