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开罗区沙漠新城镇建设的历程、成效与问题
袁明辉 余玉萍
从10世纪法蒂玛王朝建都伊始,尤其是19世纪以来,开罗的城市空间几经扩张,直至发展成当代中东和非洲最大的城市。19世纪末,开罗向尼罗河西岸扩张,此后又向西边的吉萨区、北边的舒卜拉·哈伊麦扩张,20世纪60年代初步形成了贯通开罗省、吉萨省和盖勒尤比省的大开罗区(Greater Cairo Region)。大开罗区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南端,是目前世界第七大城市集聚群。根据2008年埃及政府的城市行政区划,“大开罗区的范围涵盖开罗省的全部、吉萨省和盖勒尤比省的9个农村地区、吉萨和舒卜拉·哈伊麦两个城市以及开罗周边的8个新城镇”(1)“Arab Republic of Egypt Urban Sector Note: Volume 2, Towards an Urban Sector Strategy,” World Bank, June 2008,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19433, p. 27,上网时间:2022年5月11日。在该定义中,“开罗周边的8个新城镇”指十月六日城、谢赫·扎耶德、欧布拉、五月十五日城、舒鲁克、斋月十日城、巴德尔和新开罗。,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
城市规划是国家指导和调控城市化进程的基本手段。20世纪下半叶,由于过度城市化的弊病日益凸显,埃及政府决定开辟城市外围区域,发展并优化开罗的城市结构,构建城市新的可持续开发模式,大开罗区沙漠新城镇建设因此成为几十年来国家城市发展战略的中心支柱。通过在现有城区之外建立新区域,可以实现三个目标:在社会层面,按照居民需求提供住房、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在经济层面,创造新的经济基础,鼓励和吸引投资;在城市层面,合理规划城市布局、平衡人口分布以及满足国家战略安全需要。(2)Reham M. Hafez, “New Cities between Sustainability and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 Case Study of New Cairo City,” Housing and Building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Journal, Vol.13, No.1, 2015, p. 90.
国内外学界对埃及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不乏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新城镇建设是为了解决过度城市化所产生的人口和住房问题。毕健康指出,城市边缘区是过度城市化的必然产物,埃及政府试图通过国家大型工程,提高可居住面积。(3)毕健康:《当代埃及的城市边缘区问题》,载《世界历史》2002年第6期,第12页。陈天社等人认为,建立新城镇是埃及政府为解决就业、住房、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而实施的重要政策。(4)陈天社、武立志:《1981年以来埃及住房发展状况、困境及其成因》,载《外国问题研究》2022年第1期,第111页。刘昌鑫认为,埃及政府实施的新城镇项目,是为了缓解大开罗区的巨大人口压力,满足中低收入家庭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5)刘昌鑫:《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埃及城市变迁》,载《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第60页。关于开罗周边新城镇建设的战略地位,多纳·斯图尔特(Dona J. Stewart)认为,开罗周边新城镇正在演变为大开罗区的外围节点,城市的去中心化趋势将导致以前的沙漠地区并入大开罗区。(6)Dona J. Stewart, “New Egyptian Desert Cities,” in Harvey Lithwick and Yehuda Gradus, eds., Developing Frontier Cities:Global Perspectives-Regional Contexts, Beer Sheva: Springer-Science+Business Media, 2000, p. 301.车效梅等学者认为,位于大开罗区内的十月六日城、斋月十日城、欧布拉、巴德尔、舒鲁克等新城镇,是埃及北部三角洲三条城市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7)车效梅、李晶:《埃及北部三角洲城市走廊探析》,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8期,第139-140页。关于新城镇建设缘何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戴维·西姆斯(David Sims)认为,开罗周围的沙漠开发耗费了政府过多的财政资源,不断增加的能源消耗和水资源成本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去甚远。(8)David Sims, Understanding Cairo:The Logic of a City Out of Control,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0, p. 209.他还强调,政府治理能力低下、缺乏评估和反馈机制是新城镇建设失败的关键因素。(9)David Sims, Egypt’s Desert Dream: Development or Disaster?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5, p. 217.易卜拉欣·里兹克·赫加齐(Ibrahim Rizk Hegazy)等人则认为,新城镇的空间形态和土地分配政策不完全适应埃及的城市化进程。(10)Ibrahim Rizk Hegazy and Wael Seddik Moustafa, “Toward Revitalization of New Towns in Egypt Case Study: Sixth of Octob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 Vol.2, No.1, 2013, p. 13.关于新城镇建设不力的政治因素,埃里克·丹尼斯(Eric Denis)认为,穆巴拉克政权将沙漠新城镇的廉价土地划拨于房地产开发,借此拉拢有权势的精英阶层。(11)Eric Denis, “Cairo as Neoliberal Capital? From Walled City to Gated Community,” in Diane Singerman and Paul Amar, eds., Cairo Cosmopolitan: Politics,Culture and Urban Space in the New Globalized Middle East,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6, p. 58.贾德森·多尔曼(W. Judson Dorman)指出,威权政治的权力分配削弱了埃及政府对首都的治理能力,各方力量对国有沙漠土地控制权的争夺使开罗的扩张趋于无序化。(12)W. Judson Dorman, “Exclusion and Informality: The Praetorian Politics of Land Management in Cair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37, No.5, 2013, p. 1586.亚当·阿姆维斯特(Adam Almqvist)认为,新城镇帮助埃及政权完成了从国家社会主义到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在相对孤立的城市飞地积累了高度的官僚能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城镇成为威权统治的重要工具。(13)Adam Almqvist, “Rethinking Egypt’s ‘Failed’ Desert Cities: Autocracy, Urban Planning, and Class Politics in Sadat’s New Town Programme,”Mediterranean Politics, March 8, 2022, p. 3.关于塞西执政以来军队在新城镇建设中的角色,赫巴·哈利勒(Heba Khalil)等人认为,军队通过控制政府机构的采购和招标过程,逐步将新行政首都等大型工程转移至有军方背景的企业。(14)Heba Khalil and Brian Dill, “Negotiating Statist Neoliber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Revolution Egypt,”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45, No.158, 2018, p. 585.王建指出,“埃及新首都、新城镇建设等大规模工程都是在沙漠地区推进,控制沙漠地区的军队依靠重大建设项目,越来越成为埃及经济建设的中心”(15)王建:《军队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中的作用》,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6期,第95页。。
上述成果对理解大开罗区沙漠新城镇建设富有启发意义,但仍有未及之处。第一,既有研究普遍认为沙漠新城镇建设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并侧重于强调裙带资本主义所滋生的腐败和土地投机破坏了沙漠发展的潜力,而较少统筹观照这一国家城市发展战略的积极成效。第二,现有成果多从政治层面入手,剖析威权主义在沙漠新城镇治理方面的缺陷,未能充分关注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下资本结构的重新配置对沙漠新城镇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所带来的影响。第三,此前学界并未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理论,透视沙漠新城镇建设所产生的居住差异、房地产投机等现象背后难以克服的深层原因。
鉴于以上因素,本文拟综合各方数据,挖掘大开罗区沙漠新城镇建设方案自实施以来所产生的积极成效,分析其产生弊端的必然性及其深层原因,并提出一些施策建议。
一、 大开罗区沙漠新城镇建设的历程
大开罗区建设以开罗周边沙漠为主要开发目标。在现代历史上,开罗城向沙漠的扩张可追溯至20世纪初英国殖民时期赫利奥波利斯的建设,彼时,开罗东北郊沙漠由外国开发商占据并开发为高档社区。1952年革命后,在纳赛尔工业化思想的推动下,埃及城市建设有序展开。政府鼓励在现有城市的沙漠土地上建造工业卫星城,并着力发展开罗南部的赫尔旺、北部的舒卜拉·哈伊麦、西部的印巴巴和吉萨等区域。(16)Nezar Alsayyad, Cairo:Histories of a Cit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46.1958年,政府在开罗城区和赫利奥波利斯之间破土兴建纳赛尔城,旨在促进开罗东北郊沙漠的开发。由此,纳赛尔将开罗的城市发展轴延伸至沙漠地带,奏响了向沙漠进军的“序曲”,其相对成功的实践经验为萨达特时期大规模的沙漠开发奠定了基础。
(一) 萨达特时期“新城镇建设计划”的发起与实施
1969年纳赛尔曾提出“大开罗区总体规划”的建设构想。(17)Dona J. Stewart, “Cities in the Desert: The Egyptian New-Town Progra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86, No.3, 1996, p. 462.20世纪70年代,继任者萨达特正是在该构想基础上提出“新城镇建设计划”,作为国家城市建设的支柱政策。该计划制定了两大目标:建设自给自足的新城镇,以容纳大开罗区的新移民;控制现有聚居区,以结束城市对可耕地的侵占。(18)Michel Fouad Gorgy, “The Greater Cairo Region: Land Use Today and Tomorrow,” in The 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 ed., The Expanding Metropolis:Coping with the Urban Growth of Cairo, Singapore: Concept Media/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 1985, p. 178.其具体动因如下。
首先,该计划有助于保护农业用地。埃及境内约95%的地表为沙漠所覆盖,有限的可耕地资源集中于尼罗河沿岸的狭长地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纳赛尔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促使大量农村移民涌入开罗,加之城市原有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住房需求旺盛,大量棚户区和非法住房因此在城市内部和边缘地区蔓延。这些非正式社区大多建在城市正式社区附近的农田或开罗郊区的沙漠中,使得尼罗河谷宝贵的农业用地受到侵吞。1967~1973年,埃及政府忙于与以色列打“消耗战争”,无暇顾及农业投资,粮食短缺问题日益突出。埃及政府被迫进口更多粮食满足生活需要,并在小麦等食品进口价格上涨时实行补贴政策。埃及粮食进口额在1973年和1974年间翻了一番,食品补贴成本从1972年的1,100万埃镑升至1974年的3.29亿埃镑。(19)Kathy Funk and Jean-Jacques Dethier, “The Language of Food,” The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roject, March/April 1987, https://merip.org/1987/03/the-language-of-food/, 上网时间:2022年7月18日。因此,开发开罗周边的沙漠地带不仅是为了缓解城市化的压力,更是为了保护尼罗河谷有限的可耕地资源。埃及政府希望通过新城镇计划,推动城市东部和西部沙漠出现新的经济中心,使开罗的城市化朝着东西向轴线的沙漠地带扩张,以便遏制历史上南北方向扩张导致的尼罗河沿岸农业用地的流失。
其次,该计划有利于实现人口再分配的目标。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是现代城市快速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开展新城镇建设的普遍动因。20世纪60年代,开罗的城市扩张已从尼罗河两岸延伸至吉萨和盖勒尤比省。据统计,埃及人口从1800年的400万增至1970年的3,600万(20)Andre Raymond, Cairo:City of History,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0, pp. 373-374.;埃及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1907年的19%增至1975年的44%(21)“Coun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Statement: Egypt,”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86, 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naau940.pdf, 上网时间:2022年7月17日。。人口规模不断攀升,城市无序扩张,带来了住房危机。埃及政府意识到需要落实新城镇计划,疏散开罗中心城区人口。新城镇建设计划旨在增加开罗周边沙漠地带的人口密度,降低开罗和三角洲地区的人口压力,同时为不断增加的大批移居开罗的农民提供新的居住场所,以形成多枢纽、多中心的大开罗区。
最后,该计划符合国家安全考量。20世纪60年代,在与以色列之间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中,埃及政府意识到,人口和经济利益集中在尼罗河流域对国家安全极其不利。(22)Anwar Sadat, “Tasks of the Stage: Or a Comprehensive Civi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October Working Papers, Cairo, 1974, pp. 77-78.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埃及军队系统开始在沙漠中部署军事设施,如修建防御工事、空军基地。埃及因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军事机密遭到暴露,促使萨达特总统寻求建立“埃及新人口地图”(23)Ibid., p. 77.,试图在沙漠中建设多个外围屏障,为城市中心提供缓冲地带,进而形成一定的国家安全保护机制。1974年“十月胜利”纪念日之际,萨达特总统签发了《十月文件》,为开发开罗的周边沙漠做出政治承诺,明确启动名为“门户开放”的经济政策,制定在埃及全境建设沙漠新城镇的国家计划,试图分流开罗、亚历山大港和尼罗河谷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24)Ibid., p. 78.1975~1979年,埃及城市社区管理局共主持规划了18个新城镇,多以萨达特执政以来的重大事件的日期命名。譬如,坐落于开罗—伊斯梅利亚沙漠公路地带的斋月十日城、坐落于开罗南部赫尔旺附近以服务业为主的五月十五日城、坐落于开罗以西吉萨区附近的十月六日城等。1979年,埃及住房部正式出台《新社区法》,设置了负责管理沙漠新城镇建设的“新城镇社区管理局”(NUCA)。管理局将大开罗区新开发的区域划分为三类:一是新城镇。这类区域距离中心城市较远,具备独立经济基础,主要建设在开罗的东西向轴线上,如斋月十日城,需要发展强大的就业基础、住宅区和相应的配套服务。二是卫星城。这类区域距离开罗40公里以内,如位于开罗东北部的欧布拉、西南部的十月六日城、南部的五月十五日城。三是新定居点。这类区域在开罗边缘地带,主要目的是分流非正式住宅区的人口。(25)Aga Khan Program for Islamic Architecture, “Cairo: 1800-2000, Planning of the Capital City for the Context of Egyp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 ed., The Expanding Metropolis:Coping with the Urban Growth of Cairo, Singapore: Concept Media/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 1985, pp. 104-105.
(二) 穆巴拉克时期开罗周边卫星“新定居点”的开发
穆巴拉克继任埃及总统后,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私有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延续了萨达特的新城镇建设政策。这一时期的新城镇建设,除了受实现人口再分配、保护可耕地的基本目标的驱动外,还为了满足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的新需求,巩固威权统治。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下,政府不再着力于发展独立工业城市,而是将重心转向开罗周边利润产出丰厚的地段,将新城镇作为吸引私营投资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模糊的沙漠土地分配政策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使新城镇成为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联姻的试验场,政府通过“以权力换忠诚”的利益交换模式,力图进一步巩固威权统治的根基。
1983年,穆巴拉克启动开罗周边卫星“新定居点”即第二代共9个新定居点的开发,成为该时期开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基石。这些新定居点都位于开罗东部和西部的沙漠中,是进一步开发开罗东西向轴线这一战略思维的体现。政府强调根据“同质化社区”的概念来组织同质化社区,其目的是将大城市群有组织地分割成一系列城市次单元群,在保证大开罗区各区域市场独特性的同时,通过集中化来加强生产力。譬如,一些区域被定位为中心行政区或第三产业服务区,另一些区域被定位为轻工业区或重工业区。每个“同质化社区”计划容纳100万~200万居民,每个社区内至少必须雇佣80%的地方劳动力,从而减少与其他社区的通勤。(26)Gertel Jorg, “Space,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Food Security in Cairo/Egypt,” Geo Journal, Vol.34, No.3, 1994, p. 280.在该思想指导下,三个东部新定居点被合并为新开罗,两个西部新定居点被合并,成立为谢赫·扎耶德市。新开罗扼守开罗—苏伊士沙漠公路交通要道,靠近开罗国际机场,是大开罗区向东开放的重要出口,因此在所有新城镇中获得了最大的投资份额。后来,政府又在公路旁开发了占地3,800公顷的大型城市发展项目,将新开罗的土地面积扩展了近四分之一。(27)Reham M. Hafez, “New Cities between Sustainability and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 Case Study of New Cairo City,” p. 91.
20世纪90年代,沙漠新城镇建设的一些理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此前新城镇开发的主要目的是建设国家补贴住房小区,以满足工薪阶层的住房需要,而此后各种旅游和娱乐投资也被纳入新城镇建设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一种为高端房地产开发服务的工具。时值埃及新自由主义经济环境下的结构性调整,私营部门和外国投资获得了更加便捷的参与机会,大型私人房地产开发公司成为新城镇建设的主要代理人,大片土地被准许以低于市场价出售给埃及新兴的房地产开发商,“门禁”社区和高档住宅楼开始出现,开罗周边沙漠的新城镇逐渐成为资本新贵的首选地。譬如,新开罗的拉哈布占地615公顷,80%的居民来自中上阶层,因毗邻开罗—苏伊士高速公路和开罗外环线而获得区位优势。吉萨的哈达耶克占地654公顷,位于俯瞰金字塔的高地上,毗邻开罗外环线,居民也主要来自中上阶层。(28)Aboulfetouh Saad Shalaby and Mohiedeen Saad Shalaby, “Service Provision and Prosperity in Urban Communities in the Greater Cairo Region,” Urban Forum, Vol.29, No.2, 2018, p. 243.
21世纪以来,埃及政府继续推进开罗的沙漠新城镇建设进程。埃及实体空间规划总组织(GOPP)曾出台若干与萨达特的《十月文件》类似的文件,其中包括2007年起草的一份名为《开罗2050愿景》的城市发展规划。该规划由住房部主导,合作方包括联合国人居署、世界银行、德国国际合作协会、日本对外援助机构,旨在将居住在尼罗河谷非正式社区的数百万人口迁移到沙漠新城镇,为开罗城区的更新换代腾出充足的空间。(29)“Vision of Cairo 2050,” Egypt’s General Organization for Physical Planning, 2008, https://cairofrombelow.files.wordpress.com/2011/08/cairo-2050-vision-v-2009-gopp-12-mb.pdf, 上网时间:2022年7月4日。
(三) 穆尔西时期关于大开罗区新城镇建设的战略设想
穆尔西执政期间及其下台后的一段时间内,囿于时局不稳,埃及的城市建设项目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在2012年,埃及实体空间规划总组织曾发布《大开罗城市发展战略》,其中指出,在未来20年(2012~2032年)中,新城镇将建造370万套住房,其中94%必须分配给低收入家庭。(30)“Greater Cairo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Egypt’s General Organization for Physical Planning, 2012, p. 163. 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9-05/greater_cairo_urban_development_strategy.pdf, 上网时间:2022年7月7日。2013年12月,该组织还批准通过了《2052国家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强调将在大开罗区沙漠新城镇内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鼓励和吸引投资,修建新道路连接新旧住宅区,以平衡空间、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31)“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Urban Development 2052,” Egypt’s General Organization for Physical Planning, 2014, p. 22, https://andp.unescwa.org/sites/default/files/2021-10/The%20Na ̄tion ̄al%20Urbnan%20Development%20Plan%202052-.pdf, 上网时间:2022年7月6日。
(四) 塞西执政以来的开罗新行政首都建设工程
塞西就任埃及总统后,围绕大开罗区的未来,提出了一个由国家主导的政治化城市发展的新构想,试图在开罗以东45公里处的沙漠地带建设一个智能、绿色、互联的“新行政首都”(New Administrative Capital),以提高埃及这一文明古国的国际声望,彰显现代化政府的治理能力。2015年3月,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埃及经济发展会议上,塞西政府正式宣布建设开罗新行政首都。
塞西的新行政首都项目延续了埃及历任总统新城镇建设的基本路径,使沙漠扩张的城市规划理念得以赓续,其动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行政首都可以缓解现有城区的人口负荷、交通拥堵、住房危机等长期积聚的城市问题,同时借助大型项目在吸引外国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优势,为埃及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鉴于2011年开罗解放广场“街头政治”的教训以及此后持续多年的社会动荡,新行政首都相对偏远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塞西政府维护政治安全、管控公共空间。最后,作为2011年以来埃及城市建设的标志性成就,新行政首都是塞西个人政绩、权力和人格魅力的集中表达,能够为其政权提供必要的合法性支持。
规划中的开罗新行政首都面积是现在开罗市区的两倍,占地700平方公里,预计容纳700万人口(32)“New Administrative Capital,” 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 March 15, 2017, https://sis.gov.eg/Story/108220/New-Administrative-Capital?lang=en-us, 上网时间:2022年7月10日。,毗邻新开罗这一成熟社区,与开罗市区、开罗国际机场和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的距离都不超过50公里,区位优势明显。新行政首都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有望带动整个尼罗河三角洲区域的协同发展,为埃及远期规划的其他新城提供样板。
近年来,塞西政府利用国内巨大的人口红利支撑,以及埃镑贬值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的便利,大力发展以新行政首都为代表的大型基建项目和房地产行业,以期为埃及经济注入新动能。2018年,埃及房地产行业拉动GDP增长1%(33)“Egypt Economic Monitor: From Floating to Thriving,” World Bank, July 2019, p. 9,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260061563202299626/pdf/Egypt-Economic-Monitor-From-Floating-to-Thriving-Taking-Egypts-Exports-to-New-Levels.pdf, 上网时间:2022年7月9日。;自2021年4月以来,建筑业表现出相对的韧性,为新冠疫情下埃及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大支持(34)“Egypt Economic Monitor: The Far-Reaching Impact of Government Digitalization,” World Bank, December 2021,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754121644245654929/pdf/Egypt-Economic-Monitor-December-2021-The-Far-Reaching-Impact-of-Government-Digitalization.pdf, p. 1, 上网时间:2022年7月10日。。根据牛津商业集团(OBG)的统计,2022年4月埃及共有价值约5,190亿美元的建设项目正在施工,是非洲最大的项目市场,也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第三大项目市场。(35)“Egypt New Cities &Mega-Projects Focus Report,” Oxford Business Group, June 29, 2022, p. 19, https://oxfordbusinessgroup.com/news/focus-report-new-city-and-mega-project-are-dri ̄v ̄ing-gr ̄ow ̄th-egypt, 上网时间:2022年7月4日。目前,新行政首都与新开罗、十月六日城并列,成为埃及最受欢迎的住宅投资区域。2022年第一季度,十月六日城和新开罗的住房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8%和6%。(36)Ibid., p. 18.
二、 大开罗区沙漠新城镇建设的成效
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罗周边开启的沙漠新城镇建设是现代埃及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举”,其规划和愿景呼应了被称作“多中心的大都市区域”(MCMR)的人类定居空间新形式,“这是自工业时代开始以来,人们组织他们生活和工作安排的第一种真正的新方式。”(37)[美]马克·戈特迪纳、雷·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黄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作为埃及当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支柱,大开罗区沙漠新城镇为埃及公共住房建设和工业化建设开拓了重要的发展空间,它在面向开罗城市去中心化目标的同时,有助于实现大开罗区空间布局的大规模动态扩展,进而带动整个尼罗河三角洲大都市带的形成。大开罗区沙漠新城镇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益包括以下方面:
(一) 推动了埃及国家保障性公共住房项目的发展
埃及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历届政府都致力于在开罗周边地区兴建新住房。纳赛尔统治时期,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将大规模的公房建设项目作为国家向穷人进行再分配制度的一项内容。多数公房项目或以工业区为依托,或在农业用地和城郊空地上单独兴建,如南部的赫尔旺工业区、北部的舒卜拉·哈伊麦、西部的印巴巴和吉萨。在这一阶段,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控制租金的法律,以减低或冻结租金,这些法律促使了私营部门从租赁市场撤出。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家、地方政府和住房部继续主持建设公房项目框架下的低收入人群住房,包括城市内部的老房改造和新城镇里的新房建造。开罗周边开发的新城镇很快成为公共住房的一个主要来源,新城镇建设项目也开始主导埃及的城市发展和预算分配,至今仍然是公房存量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据统计,1982~2005年间,新城镇社区管理局共建造了23.7万套公共住房,其中80.1%位于开罗周边的新城镇。在高补贴的“穆巴拉克青年住房计划”(1996~2005)下建造的6.84万套公共住房中,约83.3%建造在开罗周边的新城镇。(38)“Arab Republic of Egypt Urban Sector Note: Volume 2, Towards an Urban Sector Strategy,” pp. 57-58.这些公房项目多位于远离市中心、地价低廉的沙漠地带,与内城区老房改造相比,其可操作性更强。在早先的政策指导下,这些公房主要以成本价建造并出售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买家,有时也通过补贴租赁的方式转让。(39)Ziad Koussa, “The Politics of Public Land Dispossession in Egypt: 1975-2011 and Beyond,”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58, No.2, 2020, p. 242.在新公房法出台后,国家将住房所有权以一个象征性的价格转让给居民,不再征收低廉的租金,但也不再承担此后房屋维护所需的费用,从而节省了财政开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时会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为了吸引私营开发商参与投资和建设,提高项目的进度和质量,住房部和投资部联合出台新方案。作为回报,国家保障开发商以低价获得土地权,后者则承诺按照国家住房计划的图纸盖房子。
2014年,塞西总统重启了穆尔西时代停滞的国家保障性住房项目,承诺为低收入家庭提供100万套新住房,这些新住房分布在十月六日城、五月十五日城、巴德尔和欧布拉,大部分由军事承包商建造。(40)“A Million Units for Whom? Six Facts about the Social Housing Project,” Built Environment Observatory, May 28, 2018, http://marsadomran.info/en/facts_budgets/2018/05/1543/, 上网时间:2022年7月6日。2019~2020年间,新城镇社区管理局共建造住房68,258套,其中国家保障性住房45,002套,占其住房总量的65.9%。(41)“Arab Republic of Egypt — Bulletin of Housing in Egypt 2019/2020,” Egypt’s CentralAgency for Public Mobilization and Statistics, December 29, 2021, https://censusinfo.capmas.gov.eg/Metadata-en-v4.2/index.php/catalog/532, 上网时间:2022年7月5日。2014~2022年间,大开罗区沙漠新城镇建造的公房数量分别为:巴德尔59,016套,五月十五日城24,792套,舒鲁克4,416套,新开罗2,064套,欧布拉1,864套。(42)《新城镇公共住房项目》(阿拉伯文),埃及住房部,2022年,https://img.mhuc.gov.eg/images/2552a014-cbe4-47a6-ba5d-fd18bff65a25.pdf, 上网时间:2022年12月18日。
(二) 促进了埃及的工业化发展和私营部门的回流投资
虽然埃及政府将重新安置人口作为建设新城镇的一个主要动因,但在早期的新城镇项目中更侧重于工业化建设,“随着中东和平进程所取得的进展,埃及的沙漠边界已从概念上被视为发生战争时保护开罗和三角洲地区的屏障,转变为在经济活动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的地点”(43)Dona J. Stewart, “New Egyptian Desert Cities,” p. 310.。沙漠新城的经济场所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释放。萨达特启动的“门户开放”政策旨在向外国投资开放埃及经济,同时允许国内私营部门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此前纳赛尔实施的国有化政策已使私人资本逐渐被国有资本所取代,“1966~1967年,公共部门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创造了制造业近90%的附加值,私营部门几乎被排除在大型工业活动之外”(44)Samer Soliman, Stat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Egypt,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8, p. 11.。因此,推动私营部门回流投资既非一件易事,也可能产生潜在的政治风险。萨达特决定利用新开发的沙漠城市重新整合商业阶层,这一举措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新城镇的地域范围有限,拥有独立的行政、法律和监管框架,政府可以适当调整补贴和税收政策,以鼓励停滞不前的私营部门对经济的回流投资;另一方面,新产业政策在诸如如何控制重新焕发活力的创业者资产阶级、管理重新参与经济活动的私营部门等方面面临考验,而边远的沙漠新城镇能够为政府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试验区,以减少和规避对全国经济面可能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45)Adam Almqvist, “Rethinking Egypt’s ‘Failed’ Desert Cities: Autocracy, Urban Planning, and Class Politics in Sadat’s New Town Programme,” p. 7.
为了鼓励沙漠新城镇工业化的发展,萨达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制造业的激励措施。《1979年第59号法》规定对所有利润、所得税和外币信贷利率实行10年免税期。(46)Samer Soliman, The Autumn of Dictatorship:Fiscal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Egypt under Mubara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23.在政府的激励措施下,斋月十日城作为埃及首个以工业区为主的新城镇,凭借其毗邻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的独特区位优势,迅速吸引了大批制造业企业。此后,埃及相当一部分制造业产能陆续落地新城镇。截至1993年,十月六日城运营的工厂数量达286家,斋月十日城有531家。(47)Dona J. Stewart, “Cities in the Desert: The Egyptian New-Town Program,” p. 468.
沙漠新城镇对埃及工业所有权的重组做出了重大贡献,公共部门对工业领域的投资比重从1970年的30%以上降至1980年的20%左右,1995年仅为4%;相反,私营部门在工业领域的投资比重从1981年的15.9%增至1995年的45.9%。(48)Samer Soliman, Stat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Egypt, p. 19.如今,整个大开罗区容纳了三分之一的埃及民族工业企业,主要工业有钢铁、水泥、化肥、设备、粮食加工、制砖、电力等,为该区域提供了许多工业就业机会。据统计,截至2013年,埃及境内新城镇共拥有7,630家工厂,创造了53.3万个就业机会。(49)“Arab Republic of Egypt National Report,” UN-Habitat, 2016, p. 19, https://habitat3.org/wp-content/uploads/Egypt-Final-in-English.compressed-1.pdf, 上网时间:2022年7月24日。对于政府而言,将工厂企业迁至新城镇进行集中化发展,不仅能够提高管理效率,还有助于改善城区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问题。对于工厂企业而言,由市区迁往郊区卫星城则可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包括利用其更便宜的场地和更廉价的劳动力,从而有效地降低产品成本。
(三) 带动了埃及北部三角洲城市走廊的区域一体化建设
尼罗河北部三角洲是埃及城市分布最密集的地区。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区域人口5,500万,占埃及总人口的76%,是埃及几乎所有工业活动的所在地。”(50)“The State of 2008 African Cities: A Framework for Addressing Urban Challenges in Africa,” UN-Habitat, 2008, p. 65, 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manager-fil ̄es/The%20State%20of%20the%20African%20Cities%20Report%202008.pdf, 上网时间:2022年6月3日。为了实现北部三角洲地区的协同发展,形成一体化的区域城市网络,埃及政府提出了以开罗为出发地,以周边卫星城镇为节点向外辐射,建设“城市发展走廊”的设想,旨在进一步分散过度集中的人口,为工业区、贸易中心和其他开发项目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坐落于开罗—亚历山大城市走廊上的十月六日城,开罗—伊斯梅利亚—塞得港城市走廊上的斋月十日城、舒鲁克和欧布拉,开罗—苏伊士城市走廊上的新开罗和巴德尔等沙漠新城镇因而成为最重要的节点。它们参与到城市走廊的布局和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沟通和链接作用。“随着埃及城市化的速度加快,城市空间向大型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以开罗为中心的三条城市走廊初具规模。”(51)车效梅、李晶:《埃及北部三角洲城市走廊探析》,第136页。
便捷的交通和政府的扶持是位于城市走廊内的沙漠新城镇实现自我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它们借助城市走廊的辐射作用吸引投资,进而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每个新城镇的发展定位不尽相同。譬如,《2052国家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提出,十月六日城将通过先进技术和电子产业的本地化,建设成为集居住、娱乐和商业于一体的智慧城市,并着力发展卫生保健领域,建立医疗城;新开罗则将在科学、教育、商业、金融、卫生和展览领域,发挥作为知识和跨学科社区的作用。(52)“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Urban Development 2052,” p. 28.各个新城镇在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模式上也有明显差异,以便政府通过资源整合和统筹配置实现区域内的优势互补,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合理流动,进而推动北部三角洲城市走廊的产业升级和区域工业一体化建设。
新城镇和城市走廊的建设相辅相成。如前所述,新城镇里常分布有大小不一的工业区,产业集聚现象较为显著。而随着城市走廊和环形公路的建成,新城镇里还衍生出了高科技产业园。譬如,开罗—亚历山大沙漠公路沿线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青睐,商业中心在此竞相落地,2008年底,沿线的十月六日城开设了首个被称为“智慧村”的高科技产业园,成为120多家国际公司的办公所在地。(53)“The State of 2008 African Cities: A Framework for Addressing Urban Challenges in Africa,” p. 42.此外,新城镇内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丰硕。2022年7月,斋月十日城电气化轻轨项目建成通车,项目一期日均载客量50万至70万,该项目是连接开罗市区与新行政首都、斋月十日城与东部沿线卫星城的重要纽带,将对大开罗区的经济发展和北部三角洲城市走廊的区域一体化发挥重要作用。(54)《一条巨型发展动脉:电气化轻轨为大开罗区的发展复兴提速》(阿拉伯文),载《金字塔报》2022年7月3日,http://gate.ahram.org.eg/News/3591468.aspx, 上网时间:2022年7月9日。
(四) 发挥了额外的政治功用
萨达特统治时期,其经济自由化政策的执行是与压制独立工会主义紧密相连的。随着经济政策的右翼化,劳工运动中左翼分子的反对情绪高涨,因此政府对防止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破坏经济自由化进程极为关注。1976年,萨达特制定了禁止独立工会的《第35号工会法》,进一步加强对工会的垄断。在这一过程中,沙漠新城镇成为政府抑制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前,以公共部门为基础的罢工常常利用工厂和社区网络来维护纳赛尔时代取得的利益,而新城镇的工人们一开始就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网络,新城镇内部社会密度的缺乏对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抑制作用,罢工屈指可数,且都以失败告终。(55)Adam Almqvist, “Rethinking Egypt’s ‘Failed’ Desert Cities: Autocracy, Urban Planning, and Class Politics in Sadat’s New Town Programme,” p. 10.因此,沙漠新城镇帮助政府阻止了工人激进运动的出现。
同理,塞西政府在开罗以东沙漠建设新行政首都也有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新行政首都试图将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中心从麻烦不断的开罗迁移出去……该政权正在将自己与开罗及其狭窄的街道隔离开来。”(56)Maged Mandour, “The Sinister Side of Sisi’s Urban Developmen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10, 2021,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sada/84504,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8日。政府计划在新行政首都建设六个核心智能基础设施,其中一个名为“安全城市”,包括用闭路电视摄像机和控制传感器覆盖城市的所有部分,集成到城市控制中心,实时跟踪行人和车辆,预防交通拥堵或犯罪活动等情况。鉴于此,有观点认为,开罗新行政首都巨大的规模、现代化的设施加上远离开罗市中心的地理位置,有助于扼制未来有组织的抗议活动。(57)Maged Mandour, “The Sinister Side of Sisi’s Urban Developmen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10, 2021,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sada/84504,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8日。
此外,塞西通过新行政首都等大型项目获得了军方的支持,降低了潜在的政治风险。“经济军事化”是军人出身的塞西执政以来经济改革的一大特色,旨在通过满足军队的经济利益以获得支持,以便稳固新兴政权(58)黄超、刘欣路:《新冠疫情冲击下埃及经济改革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3期,第71页。,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则是军方介入埃及经济的主要途径。军方接管了数千个基础设施项目,新行政首都正是其中的旗舰项目,由此强化了埃及军队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传统核心地位。2016年2月,塞西颁布总统令,授权武装部队土地项目管理局(APLPA)监督在军方控制区域进行的两个大型工程项目,即新行政首都建设项目和谢赫·扎耶德新城镇建设项目,并赋予其组建合资企业的权力。(59)Laila Sawaf, “The Armed Forces and Egypt’s Land,” April 27, 2016, https://marsad-egypt.info/en/2016/04/27/armed-forces-egypts-land/, 上网时间:2022年7月9日。同年4月,为推进新行政首都项目的开发建设,埃及军方和新城镇社区管理局合资成立了行政首都城市发展公司(ACUD)。(60)“Administrative Capital For Urban Development,” Egyptian Commercial Service, April 21, 2016, http://www.ecrg.de/images/Download_pdf/Brochure.pdf, 上网时间:2022年12月4日。军队凭借自身特权和政治影响力控制生产要素,在项目的采购、规划和执行方面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抑制了相关私营大企业在穆巴拉克时期所拥有的经济增长活力。
三、 大开罗区沙漠新城镇建设的主要问题
大开罗区沙漠新城镇建设计划旨在解决开罗过度城市化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在该计划框架下,一大批卫星城相继在开罗周边的沙漠地带建成,产生了一些积极成效,实现了项目规划所预期的部分目标。但是,由于这些卫星城与开罗主城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地理距离,加之私营部门投资的涌入所导致的房价高企等原因,沙漠新城镇建设计划不仅未能实现大开罗区人口的合理再分布,有效阻止周边农业用地流失,还造成了严重的住房资源浪费,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社会阶层隔离和贫富分化现象。此外,在国家政策和权力精英的共谋下,沙漠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建设已蜕变为一个资本竞相角逐的投机场域,成为滋养社会腐败和经济泡沫的“温床”。
(一) 公房项目未能有效疏散开罗中心区人口
沙漠新城镇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分流挤占城市资源的非正式社区人口。然而,低收入人群并未按照政府规划,如期搬迁到周边沙漠新城镇的公共住房区。其中一个原因是,多数新城镇距离开罗主城区几十公里开外,且彼此较为分散,而公房项目又通常被分配到其中位置最差的地段,对于居住者而言需要负担额外的交通费用。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在许多时候出于追逐利润的目的有意打造精英社区,在这些区域禁止零售商店、作坊、街亭等微观经济活动,给低收入家庭就地谋生带来许多不便。于是,穷人依然选择固守于城市边缘地带,非正式住宅的高出租率与新建公共住宅的低入住率形成了鲜明对比。
出于上述因素,大开罗区虽已建成大量沙漠新城镇,但建设结果并未给低收入阶层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从而无法有效地吸纳开罗中心区人口,各城镇现有人口数量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根据埃及新城镇社区管理局的统计,截至2020年,主要新城镇实际容纳人口数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1995年规划的新开罗预期人口目标为600万,实际人口仅为250万;1979年规划的十月六日城预期人口目标为550万,实际人口仅为180万;1977年规划的斋月十日城预期人口目标为210万,实际人口仅为85万;1978年规划的五月十五日城预期人口目标为90万,实际人口仅为33.5万。(61)《新城镇概览》(阿拉伯文),埃及新城镇社区管理局, 2020年9月30日,http://www.newcities.gov.eg/know_cities/default.aspx, 上网时间:2022年7月5日。
(二) 规划模式未能有效阻止周边农业用地流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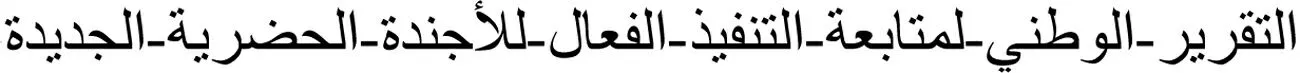
(三) 新城镇内部高端住宅过剩,造成严重浪费,并加剧了阶层隔离
20世纪90年代初,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国家不再将公共住房项目作为新城镇的优先考虑,而是将其未来全盘交给了私营部门。后者转而在新城镇为精英阶层兴修设施豪华的“门禁”社区,对街道、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实施封闭管理,将城市服务私有化,以体现经济的“新自由化”。别墅和豪宅群因此得以兴盛,开发商称之为“城市社会的复兴”。一项对大开罗区周围5个新城镇的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466个高端“门禁”社区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主要受益者是富裕的私人承包商和开发商。(65)Ziad Koussa, “The Politics of Public Land Dispossession in Egypt: 1975-2011 and Beyond,” p. 247.
在新城镇内部趋之若鹜地修建豪宅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资源浪费。20世纪90年代,埃及的空置住房合计价值达400亿埃镑,与当时的外债持平。(66)Eric Denis, “Urban Planning and Growth in Cairo,” Middle East Report, Winter 1997, p. 8.根据2017年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CAPMAS)数据,大开罗区内的8个新城镇共有148.7万套住房单元,仅有58.7万套有人居住,平均住房空置率高达61.2%。其中,巴德尔的住房空置率高达82%,舒鲁克高达71.5%,斋月十日城高达62%,即便在开发相当成功的新开罗也高达60%。(67)《2017年度人口、住房和企业普查》(阿拉伯文),埃及中央动员与统计局,2021年12月28日,https://censusinfo.capmas.gov.eg/Metadata-ar-v4.2/index.php/catalog/1723, 上网时间:2022年7月8日。
与新城镇新建住房空置率高、人气不足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非正式住宅在离市中心更近的郊区蓬勃发展,居民包括公务员、工人、医生、小业主、艺术家、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等不同职业者,似乎更有烟火气,但也埋下许多安全隐患。该现象若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的角度来考察,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指出,空间既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者。另一位理论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据此认为,“居住条件差异实际上是阶级不平等的表现,也是阶级差异的重要‘文化源泉’,通过居住差异能够发现城市空间结构与社会阶级结构的关系。”(68)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6页。资本的逐利性塑造了带有明显等级化的城市景观,无形中加剧了埃及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富人们生活在设施优越、保卫良好的“门禁”社区中,而低收入阶层聚集在居住条件十分不完善的边缘地带,城市因此在等级化的对立格局中不断地被分裂,社区生态的两极分化变得更加严重。
(四) 新城镇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助长了沙漠土地和房地产投机现象
穆巴拉克总统上台后,私营企业为利润所驱,将新城镇投资从工业制造业转向了房地产业,一种隐形的土地投机政治由此衍生。在这种政治模式下,虽然国家在名义上对沙漠土地拥有绝对控制权,但诸如新城镇社区管理局、住房和农业合作社等公共部门、军方、警察部门和私人企业的资本都可以参与竞拍土地的开发权。1984年,市政方进行了一次开罗周边沙漠土地的确认工作,以便对低收入群体的住宅发展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却发现许多地皮被不止一个实体认领,边界完全混乱,关于沙漠土地所有权的文件几乎不存在。在争夺沙漠地带的开发权时,军队和警察部门通常胜过其他竞争者。(69)David Sims, Understanding Cairo:The Logic of a City Out of Control, p. 82.
20世纪80年代后期,埃及经济开始走向新自由主义。1991年,埃及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达成协议,加速了这一进程。一揽子经济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方案包括货币贬值、减少公共开支,促进私有化等。该方案关于城市发展规划最重要的调整是削弱国家的作用。譬如,鉴于出售土地资源是私有化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在规划整个工业城市时不再界定其详细用途,而是直接将大片土地卖给私营企业,让它们自行规划。于是,所有的沙漠土地开始被不加限制地出售给私人开发商,在开发时还能得到政府的高额补贴,由此掀起了一股沙漠土地的开发热潮。许多有经济实力的个体出于投机心态,也纷纷在开罗沙漠地区购买土地和住宅。为迎合该市场需求,沙漠新城镇的房地产开发迅速转向了为小众精英阶层建设高质量住宅。
国家将沙漠土地分售给主要的建筑承包商后,并不介入住房生产。为了保证公共住房建设,新城镇社区管理局制定了一套复杂而模糊的土地分配程序,其中一个程序是土地换股权。这是一种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形式,即允许私人开发商获得土地,再将一定比例的土地返还给政府,用于建设公共住房。譬如,塔拉特·穆斯塔法集团在2009年以极低的价格从新城镇社区管理局手中购买了一大块有吸引力的土地。作为交换,该集团将其中7%的土地指定为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并承诺开发配套的基础设施。(70)Adam Almqvist, “Rethinking Egypt’s ‘Failed’ Desert Cities: Autocracy, Urban Planning, and Class Politics in Sadat’s New Town Programme,” p. 16.上述措施使得大实业家和资本家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价获得土地开发权,他们通常是在埃及私营部门拥有长期权力基础的家庭或是房地产行业巨头,沙漠新城镇的投资模式由此渐渐发展成一种裙带资本主义形式,培养了一批依靠政府投资项目获利的官商资本家阶层。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城市在资本的瓜分下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占据,在一定程度上分裂成了郊区、边缘地区和卫星城市群,它同时也变成了权力的中心和巨额利益的中心”(71)[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列斐伏尔曾将资本从工业生产与流动生产领域向房地产领域的转移指称为资本的“第二次循环”,并指出,当“房地产投机变成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即“成为实现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时,“第二次循环取代了第一次循环,变成根本性的东西……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状况”。(72)[法]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等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2页。而在传统政治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经济联合模式运行下的埃及,资本则更加“如鱼得水”,土地与房地产开发作为获利最丰厚的投资渠道不仅产出了暴利,还滋生了严重的腐败。穆巴拉克之子贾马勒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沙漠工程的一位狂热支持者,他曾在内阁改组后推出经济重组计划,意图加速沙漠地区的发展。(73)Clement Moore Henry, and Robert Springborg,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91.《2007年第350号法》颁布后,埃及政府取消了对外国企业和个人在埃及购买房产的所有限制。由于该法的实施,开罗周围新城镇的土地价格一夜之间飙升了116%,2003至2013年间年均上涨了148%。新城镇社区管理局宣称,2015/2016财年仅靠土地销售就能获得500亿埃镑的收益(约合59亿美元)。(74)Yahia Shawkat, “Property Market Deregulation and Informal Tenure in Egypt: A Diabolical Threat to Millions,” Architecture, Media, Politics, Society, Vol.9, No.1, 2016, pp. 4-5.就这样,一个巨型的且危害力极大的投机性房地产泡沫就此形成。
四、 结语
作为埃及主要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多数埃及人的工作机会所在地,大开罗区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国家城市战略的试验区,见证了埃及几十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其发展经验和教训也对人口增速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划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为了保护有限的可耕地资源、吸收和重新分配城市人口,20世纪70年代埃及政府正式着手实施沙漠新城镇建设计划,以广袤的沙漠为主要改造对象,旨在将城市扩张引向周边沙漠地带,使开罗从一个单一中心城市变成多中心的、分散性的城市集聚群,大开罗区的面积也由此得以不断地扩展。客观地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践,沙漠新城镇建设在推进国家保障性住房项目、辅助工业化发展、鼓励私营投资、助力尼罗河三角洲大都市带的形成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并在阻止工人激进主义、维护政权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额外的政治功用。但是,建设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弊端,在传统政治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联姻下,各方资本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竭尽所能,导致住房的“供给与需求在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平衡被严重打破”(75)刘昌鑫:《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埃及城市变迁》,第65页。、城市社会的阶层隔离、土地和房地产投机之风盛行不止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新城镇建设总体效果与原先的设想大相径庭。
毋庸置疑,城市规划是各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种积极的干预因素,国家介入土地的开发和利用规划,有利于统筹发展,合理布局,保障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但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利用的性质与形式更多地受到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的影响”(76)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第73页。。19世纪恩格斯从巴黎欧斯曼规划谈到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柏林、维也纳等城市的扩展时曾指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房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种例外”(77)[德]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这其实也是一百多年后大开罗区沙漠新城镇建设产生弊端的一个深层原因,它使得建设的真正受益者并非平民百姓。新城镇建设基本上是与埃及政府的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同步展开的,资本结构“国退民进”的进程也是包括公房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被瓦解的过程,由于资源和利益杠杆在多数情况下向权钱阶层倾斜,城市空间在重新生产的过程中走向失衡,社会矛盾因此变得更加尖锐,民生问题持续叠加,最终演变成2011年“一·二五革命”的一个催化剂。
对于埃及政府而言,为实现新城镇建设的预期目标,需统筹各方资源配置,充分利用现有住房存量,精准匹配国家保障性住房供给与低收入人群需求,实现从供给侧向需求侧的转型,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增强新城镇对开罗中心区人口的拉力;或可设立透明的监督机制,进行定期评估和反馈,避免产出效率低下及对国家财政资源过度消耗的项目,打击官商资本家阶层对沙漠土地开发的绝对垄断。总之,如何克服资本的诱惑,将中下阶层的核心关切纳入整体城市规划,减轻市场化导向对社会体制的破坏和消极影响,避免空间生产失衡所导致的城市危机,是大开罗区沙漠新城镇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