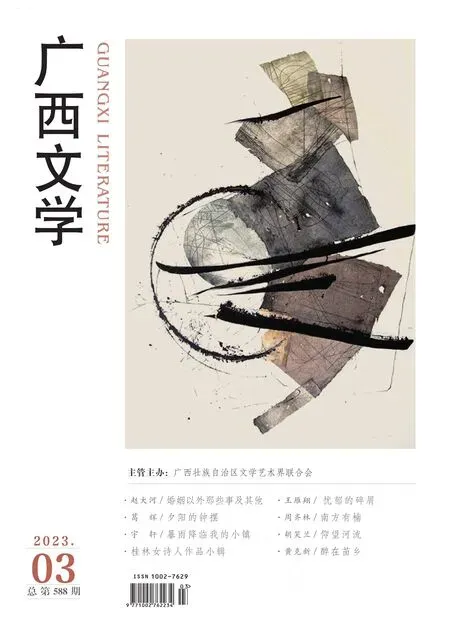婚姻以外那些事及其他
赵大河
婚姻以外那些事
到剑桥,一定要到咖啡馆坐一坐。我知道,我不可能遇到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也不可能遇到艾略特,因为他们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我只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
我和妻子要了两杯咖啡,坐在临窗的位置消磨时间。冬日的阳光打在窗户上,给人以温暖的感觉。
临桌,一位老人在说话,我们偷听到一些。他说:“我一生都非常幸运,曾住在最美的城市,生活在最激动人心的环境里。我有很优秀的学生。包括我的婚姻以及婚姻以外那些事——对我来说相当重要——也都是幸运的。我的运气好极了。”
老人对面的中年人抓住他话语中一个敏感的词:“婚姻以外那些事?”
老人狡黠地一笑:“你明白的。”
“能谈谈吗?”
“你知道,我是研究沉默的。”
“更是研究语言的。”
他们哈哈一笑。
“有些事只需要推理即可。”老人随即讲了一个段子,他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年轻数学家们到了晚上才回家,跟妻子丝毫不谈论自己的工作。一个字都不谈。但其中一个妻子跟我解释说:‘在床上做那事时,我能辨别出哪些白天他发挥出了创造力,哪些白天没有。’瞧,这很简单。”
我知道他不可能去讲“婚姻以外那些事”了。我忽然发现我在偷窥别人的隐私,心头浮现出一片小小的不道德的阴云。
走出咖啡馆,我突然想起维特根斯坦的临终遗言,他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能在临终说出这句话的人,人生是多么圆满啊!
刚才,咖啡馆里的老人,看上去有八十多岁,双目炯炯有神,他有资格说“我一生都非常幸运”。
我们去逛书店,看到门口挂着刚才那位老人的图书海报,上面有照片和姓名,噢,是鼎鼎大名的乔治·斯坦纳,我读过他的《语言与沉默》。
“知道他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
“什么?”
“他后悔年轻时没搞创作,没能写几本小说或戏剧。他怕失败,所以没去尝试。……其实他发表过小说,不过,那是五十岁之后的事了。晚吗?也不晚,这个年龄才开始写小说的也不乏其人。他有一篇小说写希特勒,名叫《运送希特勒到……》,地名我记不住了,是以叙事的形式进行的思想对话。他还写过一个小说,叫《证明》,讲的是一名逐渐失去视力的校对员的故事。”
“评论家想当小说家?”
“是,他说小说家与评论家之间的距离是以光年计算的。”
避 雨
雨下大了。我的同道田君指给我看,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正慌忙跑到屋檐下避雨。那女人用手帕裹着头,衣服都淋湿了。
这是雨中很平常的一幕,没什么新鲜。田君让我看什么呢?
——一个女人淋雨了,我说。
——是,田君说,淋湿了。
——她出门时没想到会有雨,那时云已压得很低。
——离家不远,她大意了。
——她是在想心事,忽略了天气。
——她拎着盒子。
——她去替人打酒买菜回来,盒子里面是酒菜,你瞧,还冒着热气。
——她原本没想躲雨,她想尽快赶回去,所以衣服淋湿了?
——有人在等着酒菜呢。
——她在看天,有些着急。
——飘风不过午,大雨不终朝,这雨很快会停的,可她等不及,你瞧——
雨刚刚变小,还没停,那女人就匆匆走了。田君与我相视一笑。我们看着那女人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田君让我看的这一幕就这样结束了。
一个女人躲会儿雨,然后走了,没有任何戏剧性。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
——是没什么特别的,田君说。
——只是避雨。
——只是避雨……你晓得书里是怎么写的吗?等了一歇,那雨脚慢了些,大步云飞来家。
——嗯。
——试看这句话里面,有云,有雨,有雨之脚,有女人的步子,雨脚慢,而女人的步子大,写得何等优美而灵动。
——确实写得很美,充满意象,如同诗歌。
——你觉得这个女人如何?
——女人淋雨,淋得精湿,怪可怜的。
——避雨,湿衣,不知怎的,这个人物一下子很有人情味,是吧?
——是。
——你讨厌她吗?
——一个淋雨的女人,我为什么要讨厌?
——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女人的身份呢?
——她是谁?
——邪恶无耻的王婆呀,瞧,那儿写着紫石街,她是去替西门庆和潘金莲买酒菜……
刽子手桑松的日记
可怕的一天。断头机吞掉了五十四个人。我已筋疲力尽,勇气顿消。那天夜里,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妻子,我可以看到我的餐巾上的血迹……我不能自称拥有我并不拥有的任何感知能力:我太过经常、太过贴近地目睹了我的人类同胞所遭受的痛苦,以至于并不容易受到影响。如果我所感受到的不是怜悯,那必定是由于我神经质发作而导致的、大概是上帝之手在惩罚我对某种东西表现出来的怯懦和柔顺,这种东西与我生来所服务的正义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这是陈列在断头机旁橱窗里的一页刽子手桑松的日记。桑松说的“可怕的一天”,是指1795年6月7日。五十四个人是作为密谋者被处决的。其中有杂货商、教师、音乐家、推销员等。那时候断头机统治着法国。从1793年起,已有数万人被杀。虽然起用了断头机,但刽子手并没有失业。可能是需要杀的人太多,断头机忙不过来吧。
砍头是桑松的工作。这项工作并不是谁都能胜任的,它不但需要勇气、胆量,还需要技能。手起刀落砍掉一个人的头颅的困难超乎想象。1587年,刽子手砍了三下才砍下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头,1541年处决索尔兹伯里女公爵玛格丽特波尔则砍了更多下。桑松就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手起刀落,人头落地,那是对被处决者的尊重。让被处决者少受罪,同时也有尊严。在人生最后时刻,保持尊严是必须的。那是一个人最后的表演,不能搞砸。
桑松见证过很多最后时刻的表演。大多数人都能够从容面对死亡。比如陆军副官博伊居永在断头台上摆好姿势,对桑松说:“今天是实际演出,你一定会惊讶,我对自己的角色多么熟悉。”也有因恐惧而崩溃的,比如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里夫人被送上断头台时,不停地尖叫,她留给人世的最后的话是:“再等会儿,行刑官先生,就一会儿。”
桑松为刽子手这个职业赢得了尊重。他说,任何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被判死刑,他家里的刀斧便会铿锵作响。他还说,当他站到断头台上时,他稳如泰山,他在即将被砍头的人身体上唯一能看见的痕迹,是脖子上一条细细的红线,那是刀斧要砍下的位置。
回到这可怕的一天。每有处决,人们就像看演出一样踊跃。报贩在巴黎大街上高喊:“这里有最全的断头台抽奖名单,谁想看这份名单?今天有六十个左右。”桑松提着明晃晃的利斧从大街上走过时,人群一阵骚动,有人吹口哨。
桑松处于舞台的中心。他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必须心无旁骛,把杀人的活儿干得干净利索。众目睽睽,他不能有丝毫懈怠,不能有半点失误。他要维护刽子手的荣誉。二十八分钟,他砍下五十三颗头颅。最后,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她叫妮可布沙尔。她多么脆弱单薄啊,一只老虎都会怜悯她。一个助手过去绑她瘦小的手腕,对她说:“这只是一个玩笑,不是吗?”此时,妮可破涕为笑,答复道:“不,先生,它是真的。”
在桑松的职业生涯中,他认为妮可的最后表演最完美。但是,他忍受不了这样的流血。如果放下刀斧,能救妮可一命,他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可是,他知道,谁也抗拒不了命运。他的命运是杀人,妮可的命运是在十八岁时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于是,他屈从于命运,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他这天的工作。
黑泽明自杀未遂
门突然被撞开,东条忠议像一阵旋风刮进来,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果然,他将手上的报纸往桌子上一摔,叫道:“小野,出大事了!”
他的声音,真是吓人。
小野看到报纸上的大字标题:
黑泽明自杀未遂
突然,天塌下来一般。小野呆坐片刻。她站不起来,仿佛成吨的悲伤和恐惧压在身上,她不堪重负。
小野从给黑泽明的《罗生门》做场记起,已追随黑泽明二十多年,参与和见证了黑泽明的辉煌。《罗生门》《生之欲》《七武士》《战国英豪》《恶汉甜梦》《用心棒》《椿三十郎》《天国与地狱》《红胡子》等,都有她的一份心血。她的青春差不多就是在黑泽明的片场度过的。
黑泽明为什么要自杀?好莱坞电影《虎!虎!虎!》最初的日方导演是黑泽明,黑泽明也倾力去做,却被炒掉。这件事对他的打击难以估量。之后,黑泽明振作起来,迅速拍了一部《电车狂》,票房又惨遭滑铁卢。
噢,这就要自杀吗?
她立即赶往山王医院,去看望黑泽明。一路上,她都在头脑里排演如何安慰这位“黑泽天皇”。正如电影开拍前,导演和演员在一起讨论这场戏如何演一样,如何安慰他呢?首先,不能哭哭啼啼,那像什么样子,黑泽明不会喜欢的。其次,说点什么呢?说点让黑泽明高兴的事。至于什么事能让黑泽明高兴,她一时半会想不出来。也许到病房急中生智,就想起来一件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控制好情绪。
病房里只有小泉一个人陪护。黑泽明的肚子和手腕都缠着绷带。他看到小野,声音沙哑地说:“啊,小野来啦。”
小野看着黑泽先生,忘了一路上排练的内容,突然失声斥责起来:“我不能接受!您以后不要再这么任性了!”眼泪随着话语飞溅出来。
天啊,演砸了,演砸了。她头脑中有一个声音警告她,你怎么把身份搞颠倒了,像大人训小孩一样。你的语气也不对。你是来安慰的,来激励的,不是来指责和训斥的。赶快弥补吧,要不然你就完蛋了。
她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圣诞装饰品给他看:“圣诞节已经到了。”
黑泽先生竟然没计较她的失礼和不敬,让小泉将圣诞装饰品挂到对面的墙上,让他能时时看到。
多年之后,小野在接受访谈时,讲了这个故事。她说她走出医院时腿都是软的,谢天谢地,黑泽先生没事。否则,世人将看不到《德尔苏·乌扎拉》《影武者》《乱》《梦》等杰作。按照迷信的说法,黑泽先生的寿限未到,他还要再活二十七年,还有很多电影等着他拍呢。
鸡毛店
二十二年后,当我坐到她面前,我认出了她。她就是当年我在鸡毛店邂逅的女人。
1988年春天,我在山西采风,收集民歌,一天晚上住进了长城脚下的鸡毛店。鸡毛店非常简陋,我睡的床只有三条腿,另一条腿是用土坯支的。其他可想而知。好在便宜,住一晚只要一点二元。吃饭另算,也不贵。但没什么好吃的,就是家常便饭。我刚住下,就来一个高高大大的女人,背着大行李包,风尘仆仆。她穿着一件醒目的红外套。高鼻子,大眼睛,白皮肤,一看就是老外。她只会说一句汉语:你好。别的就不会了。她说英语。店主夫妇是朴实的农民,哪会英语。我会一点英语,读、写还可以,听、说很差。店主夫妇说我是大学生,救助于我,让我翻译。我赶鸭子上架,只好担当了翻译,不过我们之间更多是比画和猜测。
天色已晚。她要住店。这里只有这一家店,别无选择。她累了,放下行李,要水喝。男店主给她倒了一碗白开水。店钱?我告诉她一点二元。吃饭?五毛。她没说什么。她给两元钱,店主收下,说正好,早餐是两毛。我没意识到店主算错了,多算了一毛。女老外没说什么,她可能以为多出的一毛是小费吧。
女店主打开一间屋子的门,里面有三张床。女老外把行李放下,一屁股坐到床上,床吱呀叫一声,吓得她跳起来。女店主说不碍事,塌不了。女老外又轻轻坐下,床摇晃。她又试试另两张床,也是一样。
屋子里除了看不出颜色的被褥,什么也没有。女老外比画一个洗脸的动作,女店主说脸盆在院里。院子里有个搪瓷盆,大家共用。女店主将盆子里的水倒掉,从缸里舀两瓢水,示意女老外洗脸。
女老外洗脸的时候,店主夫妇已经在烧火做饭了。趁天色还没完全黑下来,店主夫妇要为我们张罗饭菜。这期间,我们通报了姓名,她的名字很长,她又说得很快,我根本没记住。我又问,她说你就叫我娜娜吧。嗯,娜娜,这个好记。
一会儿工夫,四个菜端上来,分别是:油炸花生、炒萝卜丝、炒青菜和炒鸡蛋。主食是馒头和玉米粥。因为人少,我们一起吃。“我们”指的是我、娜娜,加上店主夫妇。
没有电,我们在院子里吃。还有少许天光,不需要点灯。吃着吃着天就黑下来了。娜娜会用筷子。我夸她,她说她来中国已经三个月了。旅游吗?她说不是。那是什么?她说的英语我没听明白。她把两个手掌合到一起,说一个手掌是男人,一个是女人,然后又分开。我还是没明白。其实也不完全是没明白,只是不敢相信罢了。她的意思是来这里与男友分手。
你的男友是中国人吗?
不是。
他是……
德国人。
你呢?
罗马尼亚人。
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罗马尼亚人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分手?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要分手也得两个人一起呀,她男友呢?她说在路上。随后,她在地上摆一根棍子,说这是长城,她从东头走,他从西头走,他们到中间会合。
我说,你从山海关出发,你男友从嘉峪关出发,你们在中间会合?
她说是。
然后,我比画个分开的动作。
她看懂了,点点头。
但分开是什么意思呢,分手,还是暂时奔赴不同地方?我说不清楚,她却明白了我的意思,做个一刀两断的动作。
店主夫妇也很感兴趣。他们听不懂,就问我。我说给他们听,他们根本不信,以为我翻译错了。哪有这种事,他们笑着说,她又没疯。他们的潜台词是:我们也不傻,你别骗我们。
娜娜问我,你们说什么?
我说他们不相信你说的。
娜娜大笑。
饭后,大家都不急着睡觉。女店主点上油灯,我们在院子里连比画带猜地聊天。店主养有鸡,鸡已上笼,偶尔会有声音。虫子觉得夜晚是属于它们的,纷纷出动,比赛着歌唱。蛾子总往灯火上扑。飞蛾扑火,前仆后继。
一顿饭后,我们和娜娜熟了,聊天很放松。因为我英语很差,大部分时候,娜娜说了好多,我只听懂几个单词。我根据自己的猜测翻译给店主夫妇,他们听了就笑。娜娜也笑。看得出来她兴致很高。突然,娜娜沉默了。她在黑暗中看着我,就那样看着,一动不动。
这个画面切换到现在——201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她一袭曳地红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面前一张桌子,公众可以坐到桌子对面,与她对视。想对视多久就对视多久。沉默。我坐到她对面,看着她明亮的眸子。我想起了1988年的鸡毛店。她呢,她还记得那个萍水相逢的大学生吗?
时间静止了。
她就是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一个举世闻名的行为艺术家。二十二年前她说的全是真的。她的确是到长城与伴侣分手的。她的伴侣叫乌雷。他们一见钟情,在床上待了整整十天。她说:“我沉醉在爱意里,说不出话,也动不了。”然后,他们一起浪迹天涯,共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来到1988年。不爱了。那就分手吧。作为一对行为艺术家情侣,分手也必须是一件作品。于是,阿布拉莫维奇从山海关出发,沿长城向西行走,乌雷从嘉峪关出发沿长城向东行走。他们用三个月时间走完了万里长城,在山西的二郎山重逢,拥抱,亲吻,挥手作别。从此再没相见。直到此刻——
我从座位上起来,一个胡子花白满脸沧桑的男人坐到我刚刚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一直面无表情的阿布拉莫维奇,像一个融化的雪糕,眼泪悄然滑下,她伸出双手,放到桌上,对面的男人也伸出手,他们的手指触碰到一起,再往前,互相抓住,牢牢抓紧……
你们可能已经猜到,这个男人就是乌雷。他们和解了。
展厅中响起热烈的掌声。
好奇怪啊,二十二年过去了,阿布拉莫维奇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她像是穿着那件红衣从长城直接走到了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不知当年长城脚下那个鸡毛店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我很想给那对夫妇讲讲“娜娜”的故事,她说到长城中间与男友分手是真的,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我翻译有误。
坚如磐石
上帝往人间瞥一眼,看到这个在大街上急匆匆行走的人。马上明白了他的处境,喟叹一声:可怜的人啊!
大街上灯火通明。
戏剧散场之前的寂静。
大天使加百列问: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上帝说:他刚从海马克剧场出来,这会儿要赶往圣詹姆斯剧场。
加百列说:海马克剧场上演的是王尔德的《理想丈夫》,圣詹姆斯剧场上演的是亨利·詹姆斯的《盖伊·多姆维尔》,他要看两场吗?
上帝说:这怎么可能,两个戏同时演出,他没有分身术,怎能看两个戏呢。《理想丈夫》演出很成功,演员正在一次次谢幕。他不等谢幕结束,匆匆出来,赶往圣詹姆斯剧场,不是为了看《盖伊·多姆维尔》,而是去看谢幕的。
加百列:看谢幕?好奇怪啊……
上帝:知道他是谁吗?他正是《盖伊·多姆维尔》的剧作者,那是他的戏,今天首演……
加百列:这就更奇怪了,他不看自己的话剧首演,却去看王尔德的话剧,他觉得王尔德的话剧好到如此程度吗?
上帝:恰恰相反,他看不上王尔德的话剧,他说王尔德的话剧无论从主题到形式都很幼稚。
加百列:那我就更不明白了,他该有多瞧不上自己的戏,才会做出如此举动……
上帝:加百列,你真是不懂心理学啊!他呕心沥血创作出这部话剧,又挑选伦敦最棒的剧团排练,男女主角也是他亲自选定的。他要一炮打响,震惊整个伦敦。他怎么会瞧不上自己的戏呢?!
加百列:那他为什么不看自己的戏?
上帝:紧张!加百列,他紧张!他不敢看,他怕晕倒在剧场里。
加百列:瞧,他走到圣詹姆斯剧场了。他时间掐得多准啊,真是恰到好处:大幕正徐徐拉上。马上就该谢幕了。
上帝:但愿他没赶上。
加百列:他赶上了……演员和制作人出来谢幕了……观众在高喊:作者!作者!作者!他听到了,瞧他激动得满脸红光……剧作者应该享受这种荣耀时刻,这是他应该得到的……
上帝:快阻止他!
加百列:舞台经理亚历山大看到亨利,向他摇头,意思是不让他上台……
上帝:他应该领会亚历山大的意图。
加百列:他看到亚历山大摇头,但没有理会……凭什么不让我享受这种荣耀时刻?……他冲到舞台中央,去接受喝彩。
上帝扭过头去:好了,别看了,让他去吧。
加百列:……听,那是什么声音?好像不是喝彩声,喝彩声我熟悉,刚才海马克剧场响起的就是喝彩声……哦,真不敢相信,是嘘声,嘘声……好难听的声音啊,不如喝彩声响亮,却更具穿透力,像蜂箱里的声音,不,比那个还难听,哎哟,谁受得了这个……瞧,他傻了,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这会儿,他恨不得舞台裂开一道缝,好让他掉下去。
上帝:好了,别看了,但愿他能够坚强。
亨利·詹姆斯说过,演出结束要请全体演员吃饭,他兑现了承诺。这顿饭吃得没滋没味。回到家后,他立即给兄长威廉写信,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最后,他说:别为我担心,我坚如磐石。
少女之死
苏菲·绍尔。
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名字。
“除耶稣基督和他的直系亲属之外,如果还有算是完美的人,那这个人就是苏菲·绍尔。”克莱夫詹姆斯在《文化失忆》中这么说。如果你对苏菲的事迹有所了解,你就会明白这并非夸大其词。
苏菲有个哥哥叫汉斯,他创建了一个“白玫瑰抵抗小组”,揭露和抗议纳粹对犹太人的残酷行为,号召人们起来反抗纳粹暴政。
汉斯不让妹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苏菲了解后,坚决要求加入。“如果被抓,是要杀头的。”汉斯说。但他无法动摇妹妹的决心。苏菲最终成为抵抗小组的一员。
他们散发传单和小册子,鼓动人们奋起反抗。
1942年,正是纳粹最为猖獗之时。
慕尼黑,则是纳粹发家之地。
盖世太保如何能够容忍这种反抗行为,他们抓住汉斯和苏菲,要杀一儆百。审讯时,苏菲说:“最终还是需要有人来开个头。我们只是说出和写出了许多人的想法,他们只不过不敢表达而已。”
汉斯的命运已经决定,他必须死。对苏菲,盖世太保说:“只要你悔过,就留你一条性命。”
这是个选择题:生与死,二选一。
苏菲毫不犹豫地选了死。她不悔过,无过可悔。再说,她还是个孩子,她才二十一岁,如花似玉,天真无邪。而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
首席刽子手后来作证说,他从没见过任何人像苏菲那么勇敢地面对死亡。苏菲热爱生命,正因为热爱,所以慷慨赴死更显悲壮。她没有恐惧地呻吟,也没有遗憾地叹息。她冷静地看了看明晃晃的钢刀,躺了下去,从容就义。
苏菲是超凡入圣的。记住这个名字,每当想起崇高这个词语,头脑中便会有一个生动的形象。
王后之美
美,是一个人独享,还是与人分享?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扰着一位国王。他的王后太美丽了。美丽,这个词语如果刚刚诞生,他第一次使用,那么用来形容王后是恰当的。可是,这个词语已被许多人使用过,简直用滥了。所以,他说王后美丽,无法传递他所感受到的那种美。美即震撼,非亲眼所见,不能体会。
王后的容颜,众皆可见。可是王后玉体,却只有他一个人看过。王后玉体美轮美奂,全天下却只有他一人知道,岂不可惜。
他想与人分享。与谁分享呢?自然是最亲近的人。他想到贴身侍卫,这名侍卫知晓他所有的秘密。侍卫也常听他感叹王后玉体之美。他想让侍卫看看王后裸体的样子,那……才是人世间的至美。
国王把想法说给侍卫,侍卫吓坏了,拒绝了国王的建议。可是国王一再坚持,并发誓确保侍卫的安全,甚至下达了命令。侍卫无奈,只好从命。
国王安排侍卫躲到寝宫门后的角落,偷窥王后更衣,一览她的裸体。
王后随国王走进卧室,脱掉衣服,放到椅子上……裸体呈现出来。侍卫看到了王后的裸体!欣赏美,不需要学习。国王所言不虚,王后的身体美得无法形容。侍卫差不多快要窒息了。这个瞬间,美的瞬间,将成为历史的拐点。侍卫尽管震惊于王后裸体炫目的美,但他没忘记他应该在王后背朝他时溜走。他是这样做的。但由于紧张、慌乱,或者捉弄人的偶然性,他被王后看到了。王后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王后由于害羞,没有叫出声来,装作什么都没看到的样子。
裸体被人看到是奇耻大辱。王后一夜未眠,心里盘算着如何进行报复。第二天,她将侍卫叫到跟前,告诉他,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杀死国王,他来当国王,并娶王后为妻;二是他马上自杀谢罪。生死攸关。当国王娶王后,或者死亡,二选一。
侍卫选择了前者。
夜晚,王后将侍卫引入寝宫,交给他一把匕首,让他还藏身于他偷窥时藏身的那个门后角落。当国王熟睡时,侍卫杀死了对他无比信任让他欣赏世上罕有之美的国王。然后,侍卫当上了国王,并娶了王后。
这个故事,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国王因为在睡梦中被杀,他到死都不明白他的杀身之祸来自何处。如果,他正在做梦,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呢?会是他和侍卫在讨论王后的裸体之美吗?
国王生错了时代,他早生了两千七百年,如果生在今天,他可以让王后上《花花公子》封面,请顶级摄影师为王后拍写真,让王后成为模特或电影明星,王后的美将为世界人民所欣赏。国王,也会是个开明君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