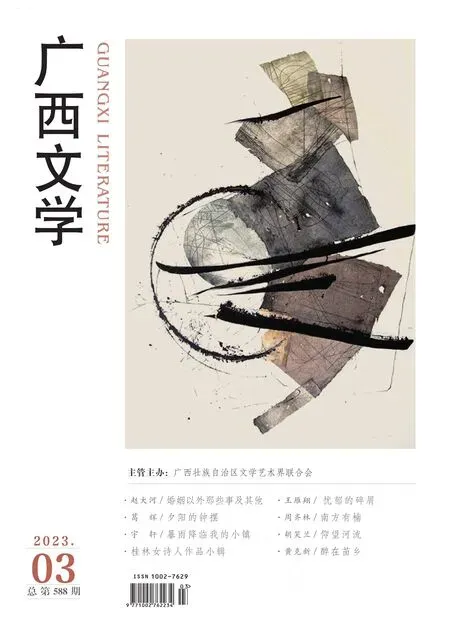另一种空间
浇 洁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让自己陷入悲伤。
婚姻是女人的防弹衣,一旦褴褛,必将遍体鳞伤。我无法在一个地方安静地待上十分钟,丈夫又一次向法院起诉解脱。
泥一脚水一脚,共同生活了十七年,理智在我们的屋檐下早已提前退场。我和他都是二婚。本性中的自私与狭隘,五千多个日常的冲击,让我们举步维艰。
何为婚姻?婚姻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冒险最恐怖最势利最甜蜜的,太过明哲者或会望而却步。没有任何血缘的男女,靠荷尔蒙、多巴胺的激情和幻想结合,零距离的长期契约,一方要吃住一方,且势均力敌,依赖子女的强力黏合剂,方能长久维持。他们心甘情愿相互制约和恩爱、互相折磨与纠缠。
明知我是茅火柴,他是吹火筒,但我惧怕孤寂,孤寂是人生最可怕的敌手,我想病老时互助有个伴,稀里糊涂了却残生。
人在高处方能自由飞翔,窘境中总期望上苍的救赎,臆想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扭转乾坤。谁说不是呢?连地球都是宇宙大爆炸时的一个产物,无中生有,有归于无。只要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都不轻言放弃。爱是一个人的自得其乐。在我的字典里,婚姻早已不只是爱,或某个具象的男人,而是一种能力的再现,一种信念的支撑;或是已然成为一个习惯,而习惯具有自我欺骗的无限能力,让人产生无法言说的归属感,哪怕这种归属感是惯性的桎梏。一个女人,一生能经营好波谲云诡的家庭这一件事,就很了不起。
因为害怕失去和荏弱,寻求那种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成了我的本能:德高望重的老师,双方的上级同事,各自的亲朋好友,找敬畏、寻软肋、托能量足者……拜菩萨求签是其中之一。寺中住持看我满脸忧戚,安抚道:“抽上上签,是佛菩萨对你的加持;得下下签,是佛菩萨对你的提醒。”正如云门禅师所云:“日日是好日。”
宗教,或许是许多人困顿时的拯救。纠结似魅影挡住了万千景色,令我企求事情转好的精神寄托。学辉法师为了宽慰我,还用我的笔名和本名写了两句藏头镶尾诗勉励:“浇灌花枝丽,洁白我自珍!”其心之诚,令人感动。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我相信万能的时间,相信潜意识。每晚睡前祈祷,用一念转千万念,视烦恼为菩提。无助的我除了半夜往朋友圈晒美图,便是以关注运势吉凶作消遣,迷信天地之间冥冥之中必有一双手掌控着我。偶尔也自我安慰,许是近几年的日子过得太顺了,才安排这一场劫难,这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与唤醒,为了使我更臻完善。当然,天地所有的指引,都是为了让我脱离迷障,自己能开出花来。任何时候,挺胸前行都比曲弓匍匐来得省力。
家已成战场。为了避免相见两厌,我除了晚上十点后回家,关上房门睡觉,日夜躲在离家不远的办公室。工作地成了避难所,一日三餐随意果腹。头晕目眩,心痛、失眠、抖颤,其煎熬无以名状。
母亲曾说过,我出生时犯鸡啼官,一生有流不尽的眼泪。求天不应求地不灵,精神失助,万般无奈,唯一天到晚找闺蜜倾倒负能量:
“我就是放不下,我不想活。”
“人家死了老公怎么过?拳要攥得拢,撒得开。总有一天,我们要一个人面对孤独,孤独教人强大。你要想想未来美好的事……”
伸开手掌直把心,闺蜜掏心窝子。无法,除了一天几小时地让我电话倾诉,一有机会就邀我游山玩水,带我走寺庙求“娘娘”,找心灵慰藉。
我家不远的小区宿舍里,有一个拐子,人称黄娘娘,是位四十多岁粉头圆脸的男子,皮肤白皙,爱穿白色唐装。住一楼三室一厅,家室宛如一座寺庙,供着几尊菩萨,设有风水转运球,四周墙壁和桌凳上挂满或叠放着“求子得子”“求福得福”的锦旗。据说,他家里从不用起伙食,自有妇人们跟在他屁股后宴请他。
听我和闺蜜敲门,他笑着打开。惬意地坐在一张舒适的靠背皮椅上,自得地用木梳梳着本来就溜光的头发,顺手端起一面镜子,自赏地左右瞧了又瞧,扭了扭腰身,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满意而缓缓地对我们说:待会儿要下乡去看风水,有车来接,你们只有二十来分钟。
娘娘问了问我的出生时辰,丈夫的出生时辰,随口一掐算,对了对桌上一张暗红的命格表,说我今年命犯太岁,丈夫听不得我说话。接着便问我要“祭”掉吗?我点头。他瘸着一条腿,脚一点一点地向神点香、敬拜、烧纸钱。然后执起一条朱红的木“敕”,我也不知叫什么,在我头顶转了一圈,呵斥了一声,问我:舒服些吗?
我没作声,他又就近掏出两个小红袋,就是符,嘱我放枕下枕上一个星期,期满随身携带。在家中每个角落洒白醋,十五分钟后拖掉,过了农历七月自会转运。
我似信非信,心神不宁时上他那坐一坐。他眼神坚定地对我说,一定会转运!尽管黄娘娘自己结了七次婚又离了七次婚,按他的说法,他不带婚姻缘,一辈子打单身的命。
虽说我知道,求仙问卦是一种安抚麻醉剂,世上所有的惊喜和好运,都是自己累积的温柔和善良,化解之方只在内心,当你开始向内觉察,找回内在的力量:自信、勇敢、笃定……外面的一切皆如风掠过。自己强大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可那段时间黄娘娘还是成了我的一座心理凉亭,前行的“助产士”,让我疲累迷蒙的心能够休憩拥有期望,直至接到侄子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
我母亲得了急性心肌梗死,剧痛难忍,前胸后背都痛得钻心,蜷曲一团。
侄子本想次日清早外出打工,刚刚上山挖春笋回家。紧急开车把母亲送乡到县,县医院亲戚医生忙做了心电图后,联系救护车用最快的速度将母亲送到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小弟用颤抖的手签下病危通知书。一家大小簇拥着,弟媳还系着下厨的围裙,侄子一身的黄泥。母亲上了手术车,我慌乱招手和母亲说“再见”,亲戚医生忙制止,言不吉利!瘦得只剩下七十来斤的母亲随时有生命危险。一家人惶恐不安,亲戚医生假装镇定以话语安抚。一个多小时,市医生在母亲大腿上通过动脉,介入药物涂层球囊无植入手术,让她感觉像针扎了两下般,成功地推了出来。我和女儿向坚强的母亲竖起了大拇指!市医生提醒,术后有一个星期的危险期。随之而来的,便是母亲一晚近十多个小时的胸闷、疼痛与叫唤。心率常常亮起红灯,只有三十几甚至一条直线,血压降到70/30多一点。我当起了母亲的陪护,母亲成了四十床。一天四五瓶盐水,护士隔两个小时量一次血压,问一次屎尿。
三月底至四月的春满人间,医院院子里紫杜鹃盛开,篱笆墙上的蔷薇长出蓬勃的新枝,我以折食蔷薇嫩枝为唯一之乐。帮母亲端屎倒尿、洗抹身体,消受她的情绪垃圾,成了我的日常。
其间,因为慌怕,乞求丈夫先撤诉,丈夫以不愿等待、无法与我共居一室为由拒绝。
我想起母亲发病前一天的事:车流飞奔的马路中央,呆立着一只白色的美丽蝴蝶,我走过去了,不忍心又折回,把它救至路边的绿化带杜鹃檵木丛中。过一个小时去看,它不见了,我希望它是飞走了。当时想,救下它,是救出我自己吗?没想到这只身处险境的蝴蝶,会是母亲。
危难激发本有的情爱,爱能让一切屈服,包括困顿与迷惑,它能让人重新回归柔弱的阵营。我帮母亲想方设法排屎尿,用医院提供的微波炉和开水,想法子给她煮面条、做面粉糊、化葛粉藕粉、炖婴儿米粉……床上一个病人,床下一个难人!除此,便是与一批批同室的病友交谈共处。
四十一床胡木英,是个八十岁的老妪,双脚浮肿,鼻子边打吊针边流血。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几年前,心脏从体内被端出来动过大手术,花了十四万。之后陆续上医院,每次一万多,如今是医院的VIP病号,十天半月要来一次。丈夫得了老年痴呆,由三个儿子摊派请护工,每月三千六百元。她共带大了七个孩子。现住院自己花钱请护工,一百五十元一天,这些费用都是她原先酿酒开店挣来的。在医院十多天,只见一个看起来年轻、戴棕色假发、穿卡其色呢大衣的时髦媳妇,跟丈夫带着儿子来看她。不待丈夫和儿子问候老妪,时髦媳妇立马就把他们赶回到病房外,冷脸硬声对老妪说:自己死里走了一转,得了乳腺癌,天天跑医院,希望老妪不要去她家,把衣服晒到她家院子里,“我好,你儿子一家就好,我不好,你儿子一家就不好。”
老妪一直默默听着,不敢吱一声。待儿媳走后,才和我们埋怨:我儿媳既会做大又会做小,她做公婆,她媳妇忘记关卫生间的门就过去撕媳妇的嘴,与我不和,扯了我头发,往墙上撞。气得我几多夜没困,唾液都愁没了……
“哇事要哇头道事,人老了可怜,哇一句事都没有人应!”老妪感叹,“住院也有好处,至少有个哇事的病友。”哇事就是说话,她对我们爱说直话,见我心情不佳,和母亲拌嘴,要我让一让母亲,万事依着她,“她是你亲娘呃!”过一会儿又小声与我说,你母亲娇气、性躁。见母亲屙不出屎,她在旁边教母亲吃火龙果,努劲。我走开一会不在身边,母亲吃乳果糖后腹泻忍不住,她急其所急忙递尿盆,尽管她自己身上挂满了各色输液测量的管子。从母亲口中,知我夫妻闹矛盾,她耐心劝慰:一个人再停当跑不过命!女人要甘做下层磨,家庭不和外人欺,夫妻不和他人看偏低,嫁一家靠一主……其朴素的智慧和友善,令我信服不已。
“禾当割总有一回”,她很乐观,“只要仔女好,我就高兴。”
胡木英出院后,第二天来了一个新四十一床,叫占爱萍。上午在家带外孙,见到外孙笑眯眯,自己也笑嘻嘻的,突然之间“嗵”地倒在地上。她丈夫见了,掐人中她才醒来。她还迷糊,不知发生了什么,照常跟着丈夫到工地上担卵石拌水泥灰。次日,丈夫不放心,送她到医院,一量血压高至二百四十,身体却无半点不适。生命就在一瞬间,生命就在偶然。
尽管她像无事样,丈夫严格按照医嘱不让其下床,担心医院食堂的包子不好吃,骑摩托车到外面买了肉包裹在胸口,热乎乎地捎来。他们有一个女儿正在另一家医院临盆,那女儿来的是四季月经,怀孕几个月还未知。我母亲接着他们的话聊,有的女子天生就是个雌雄人,每天只有半夜子时才是女人,故有这样一句话:“客官如要来,半夜子时开一开。”大家在聊这些时,病友之间惺惺相惜,关爱融洽。
四十二床沈品英,已八十五岁,高血压患者,原是此医院护士。她始终保留着用本子做记录的习惯。床头柜、床栏上擦抹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她不吃医院食堂的饭菜,每天五十多岁的女儿送伙食,六十多岁的儿子来探病陪护。她身上清清爽爽,一儿一女对她皆软语温存。听她母子俩对话,令人心气平和:
“现在怎么舒服怎么穿。”
“终于想通了?”
“昨晚灯这么亮,我都睡着了。”
“这就好,想通了就好。医保卡、身份证我帮你保管。”
…………
出院临走前,沈品英跟我们道别:“祝你们早日康复!”
儿子搀扶着她,立马笑着夸赞:“妈,你这话说得有水平!”
沈品英笑嫣嫣的。老人要哄,真是不错的。
过了一天,又来了一个新四十二床,名叫余香秀,七十八岁。八十二岁的丈夫耳背,护士要她用温开水或橙汁泡药喝,他听不清,一直问橙汁是什么?稍安顿好,就逮着我倾诉:“我吓蠢咧,她痛得嘴都乌了,在床上打滚,背也痛,手脚冰凉。”“我吓蠢咧。我自己还刚出院,还好小儿子在家……”
给妻子喂药时,只见这个老丈夫倒了热水,用手摇荡着搪瓷把缸,边吹边用自己的嘴试了几次,觉得温适,才异常轻柔地对妻子说:先漾一下口,好吗?少年夫妻老来伴,令人羡慕眼馋。
趁她老公不在时,做妻子的悄悄跟我们秀恩宠:一次她动脑手术,麻药过后很疼,人烦躁,疼得就抓挠老头子,抓得老头子手臂上一条条血痕……
第二天,余香秀的几个儿女和兄弟姐妹全赶来了,送钱递物,满满一病室,有说有笑的,都惊动了医院的警卫赶来劝阻。
老丈夫接走了,留下最贴心的大女儿照料。这大女儿与我年龄相仿,名叫牡丽,话多声响,不一会便与我无话不谈。
一切法从脸上现。只见她长一双少见的狼眼,双眼形似锋利的倒“八”叉,紧紧地钳住鹰钩鼻,眼眶深陷,四白眼,眼光尖锐,一副凶狠相,但对母亲搀上扶下,轻言笑语,照顾得极为细心。除此之外,便是炫耀自己的家庭,而她老公也的确常来电话嘘寒问暖。余香秀当我们的面笑谑女儿:不晓得你头世积了什么德,招得这样一个人!牡丽听后更来劲了,爆竹般向我们滔滔不绝:女人就是要管得住老公,日子才好过。古话说得好,要使家庭和,老公怕老婆。我叫老公往东,我老公不敢往西。去年十月我出车祸,老公抱上抱下几个月床前服侍,一下不如我的意,我就打骂。我老公总是笑嘻嘻:老婆你骂累了吗?我倒杯水给你喝。一回,他不知何事轻轻地拍打了我一下,我拼命捶他,他抓住我两手,我就用嘴在他身上死命咬。他痛不过,身体扭转,转到哪儿,我就咬他哪儿,咬得他全身青紫。啃到他手指时,“嘎”的一声,骨头都会响。我妈妈看不过,心疼地骂我。我老公事后还谄笑着对我说,我是狗头上那撮屎,你甩也甩不掉,就是剪掉了,也还会生!
我问她,为什么丈夫会对你这么服帖?她说,我帮他生了一儿一女,他从小就没有娘,把我妈当自己的亲妈。
人啊!如不是为了骨肉成全,谁甘愿服输,谁愿当愁眉罗汉?
邻室一老妪进来听后,下巴尖如锥的嘴撇了撇,乜斜了牡丽一眼,边走边在门口轻嗤道:“吹牛!”据说,此老妪和她丈夫都七十多岁了,却至结婚起,各用各的钱,各烧各的饭,即便有多余,宁给他人也不予对方。一个屋檐下,无儿无女,冷冷地生活了一辈子。这回,丈夫突发心脏病,是她及时打了120。不过,丈夫得每天给她一百元,她才勉强来服侍的。
“火柴盒”样的万千之家藏有万千悲欢,想想自己,一股切肤之寒涌入心脏。
而在此住院部四楼走廊上,常见一位头发花白稀疏的老翁,带哭腔大声哀叹:“不给治哦,天啰唉!不给治哦……”他手指已畸形,右手中指上肿长出一个多余的指头。唉,真是狗老生狗蝇!见人关切,他捋裤管,露出一条瘦弱如竿的细腿给人瞧,又哀叹一声:“天啰唉,不给治哦,天!”不知这不给治,是无治,还是他儿女没钱给他治。老翁的哀叹,让人不由联想到安全通道楼梯口那一地的烟头。
还有同楼二十四床一对明星老夫妻。妻子在给老夫喷宽胸气雾剂时,不小心喷到他的眼睛,只见那七十多岁的老男人,大哭着滚倒在地,从病房里翻滚到长长的走廊上,见病友围观,他哭诉道:“我要去死,她骂我、凶我、咒我,我活不下去,平时都是我让她……”
妻子在一旁无辜地望着大家:树上生成咯样,只系我一个人照顾他。照顾了二十四天,县里十三天,抚州十一天,他一双皮鞋要垫烂八双鞋垫才丢掉,多喷了药不舍得……一边向众人解说一边拉老夫,那老夫像撒泼小孩样从她手中挣脱,又爬滚向前,观看的人越来越多。护士走来劝抚道:不要难过,你这心脏病气不得,她喷不来我来帮你喷。在大家七言八语的劝说与护士的帮助下,老夫在妻子的搀扶中回了病床。次日,只见妻子牵着他在走廊上漫步。我见了笑:这样多好!那老夫有些不好意思,瞧着妻子羞赧地回道:谢谢啦,她嘴不好心好。
谁都期望被看见,看见是疗愈的开始。
在综合楼外,常见坐在轮椅上的病人,有母女推着四十几岁痴呆的男人,有老夫推着挂着吊瓶的老妻……
医院,各色家庭,缤纷情态的展览馆,生命难题的活动中心。
而住院部后花园里,有几个人在健身器械上运动着。紧挨的小区有一个篮球场,年轻人劲头十足地喊着,流着汗跑着。阳光明媚地洒落在紫藤萝、杜鹃花和葡茎通泉草花上。大的鹁鸪、黑的乌鸫、小的椋鸟在飞鸣,水池里的虫豸与蝌蚪在游弋……一切都欣欣向荣,在不老的春秋里,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的模样。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有人说看留下什么,有人说为了信仰,有人说为了爱。生活原本乏味,回忆又夹杂着无聊的伤痛,唯有把热腾腾的现在一天天过好。
我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也许活着仅是活着,活着就是一切。我只知道在婚姻里茫然不知所措的我,依仗简单的服务与可怕的疾病,挣脱了狭小的自我漩涡,它们使人少思断想,引向存在的洒脱。世上自有平衡法则,劫难有着另一种空间,大大小小的难,它们能够相互吸附与自我消解。
最近看了一个2021年戛纳电影类全场大奖的视频:高楼居舍里,男女唇枪舌剑,激烈争执,致使室内两人之间墙板断裂,整栋楼一分为二。男女各自逃生,却在途中不期而遇。目光交汇之际,一方危急、恳切,另一方犹豫、回头,最后还是选择不顾一切跨越鸿沟飞赴,彼此携手。楼厦倾覆的刹那,两人相拥共死,又在一堆灰烬里重生相爱。
有多少憬悟与幸福要靠灾难来催化?它驱赶恐惧和怨恨,劫后方知珍惜。婚姻让我们真实而赤裸,让我们不时在另一种空间里穿梭奔逐,亦人亦兽。生活藏有一个巨大的逆反定律,凡是我们抗拒的,都会持续。“插梅寄柳神仙计,两物生成共一枝。”对于这桩需要神仙计才能保留的婚姻,假如它属于我,我不能避开,假如它不属于我,盲目地追逐,在强求中堕落,连上天赐予人最基本的生存之能都会撂弃我。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有的话语都是浮在空中的泡沫,唯宁静和磨难能悄然改变你行走的步伐。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能渡自己。
挽歌般的秋雨敲打着门窗,落叶在瑟风中飘零。寒来暑往,一年已将尾,我和丈夫在看似平静的冷漠中各自生活,听命于内心,漫长拉锯,像两个棋手在无用的奔忙和喧嚣的树荫下,做着梦。
看不见的爱,终将在岁月的蝶变中向阳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