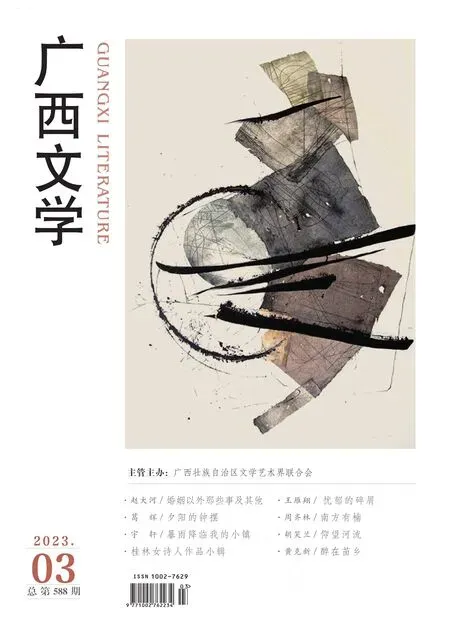楠木留痕 评论
胡 巧
历史与家族的传承,始终蜿蜒在中国人的心结之中,先祖、故居、旧物在个体记忆的重重叠压下,往往浓缩为蕴含巨大情感能量的精神所指。《南方有楠》的主题指向恰是在这样的精神所指下完成家族记忆的回溯,个体与家族、记忆与时间、寻根之途与血脉重访,借助文字的通道,在狭小的缝隙中向着天空打开。楠木作为情感载体和叙述符号,连接一个家族从清末至今的动荡与温情,见证其内部的悲喜与死生。
作品围绕楠木板展开家族叙事,家族历史、血缘亲情和价值理念都寓于楠木之中。它随着先祖流离至南方,陪伴了“我”与妹妹的童年,最终进入了儿子的婚房,楠木板的流转之中,隐含着血脉传承与生命延续。它也在这个家庭的沉重与苦难之处、在疾病和死亡带来的压抑气氛里,带给“我”与家人一份来自先祖的遥远的安宁。篾匠父亲手中的竹子与姥姥捡拾的杂木均为一家生计,这些木材易枯易朽,而楠木不同,具有出色的品相、奇异的功效和坚韧恒久的品质。此外,楠木本身的特质蕴含了家人对后代文化品格的期许,是这个家族传承的象征与精神寄托。
书写故乡、追忆亲情的散文中,多数时候,“我”以第一人称回溯童年旧事、亲情记忆等。情载于个人经验和家庭往事,便于捕捞细节与情感的真实,而书写时不免沉浸其中,易走向伤逝感怀的漩涡。《南方有楠》这篇散文以第一人称写就,所写却并非是作者自身的经验,在文章结尾,作者揭示故事中“我”实为辉叔,前文所写均为辉叔家事。以文字处理他人的讲述,假托亲历者的视角代入他人的家族记忆,其中必然有大量对细节与心理情感的想象和虚构。第一人称视角的选择推动着叙述之“我”与故事中“我”的共振,并在“我”之外去触摸父亲及他人的情感。而“我”之所以能够代辉叔去书写这段记忆,去想象那些细微的感受,正是因为类似的家族往事在某种程度上已是集体记忆的一个侧面。安土重迁、骨肉相附、敬畏先祖、寄情旧物,这是一个民族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传统,也是“我”之代言能够成立的基础,在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细节的准确与真实与否,而是决定我们的共通的情感模式。“我”试图复原辉叔关于家族的记忆,但无论如何熟悉,楠木故事始终是二手的经验,缺乏亲身的体察。若论遗憾之处,或正是部分行文由此而生“造情”之嫌。
“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地!”故居虽拆,辉叔仍于楠木板中感受先辈的气息和生命的延绵,在对楠木故事的反复讲述中达成精神的还乡。这是辉叔对于童年记忆、家人离去的缅怀,也是对家族历史的追忆,是对自己从何处来的铭记。而从听故事者到叙述者,借此文,作家借助故事之壳实现与一个家族的命运相遇,在故事之外完成对辉叔的纪念。人世浮休,时间堆叠在楠木的纹理中,若再问“归去来兮,君归何处”,楠木的清香会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