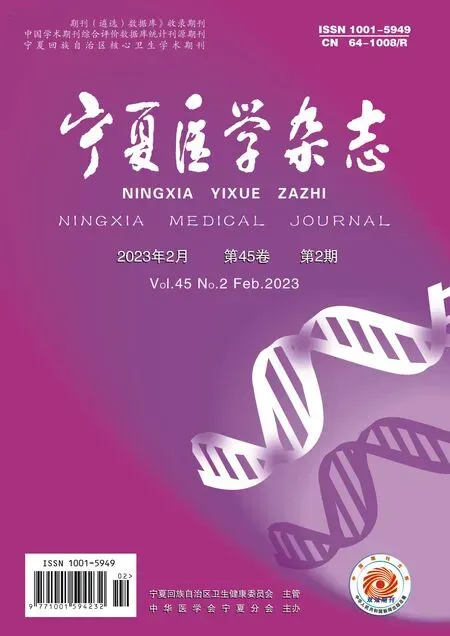生物材料在牙槽突裂治疗中的应用
甘欣怡,马 坚,于丽丽,黄永清
牙槽突裂是颅面区的先天性畸形,临床上常常与唇裂、腭裂同时发生,而在不同人群、地域及环境等情况下,牙槽突裂的发病率有明显差异[1],它常常会造成不完整连续的牙弓、牙缺失、牙异位萌出、阻萌等问题[2]。这不仅对牙槽突裂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造成负面影响[3],还会影响患者的咀嚼功能,妨碍正畸和正颌治疗。目前治疗牙槽突裂的方法是采用早期手术和面部重建,但此方法常常被认为是具有争议性的[4]。牙槽突裂区的重建最常用的方法是在混合牙列期进行二期植骨术,骨源常来自自体髂骨。自体髂骨植骨存在以下不足:自体骨植骨术后吸收明显,3个月时平均吸收率为35.74%,最严重的有近一半吸收,6个月后,平均吸收率为55.89%。现在,组织工程为牙槽突裂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即将具有促进细胞和组织再生作用的人工定制支持物用于修复牙槽突裂区。牙槽突裂的再生方案是利用具有功能性的生物材料,生物活性再生分子和可调节Int的募集干细胞来促进缺损组织的自我修复。此修复方案的关键是重建高度血管化骨骼的功能[5]。目前组织工程对牙槽突裂的治疗主要是以下几种。
1 3D生物材料
3D生物材料需要为牙槽突裂所导致的缺损部位的细胞和组织的生长提供空间和框架[6],主要起到递送作用。它不仅需要具有支撑条件的结构特征,如多孔结构及力学性能等,还需要具有一定的生物学性能,如生物活性、生物相容性、生物降解性等[7]。骨生成、骨传导和骨诱导能力是支架作为骨移植材料所需具备的3种基本功能[8],而有研究表明它会受到孔径、形状及互连的大小的影响[9]。3D生物材料所使用的材料种类很广泛,如生物陶瓷、聚合物、金属材料、复合材料,这些材料通过不同的制作方式制成的仿生3D支架已经用于治疗牙槽突裂。
1.1 生物陶瓷:生物陶瓷可制作成能够模拟天然组织的3D支架[10]。其可分为生物活性陶瓷和生物惰性陶瓷[11],主要用于修复和再生缺损的肌肉骨骼和牙周异常的部位。Hongshi Ma等人[12]根据植入后与组织结合的能力,将生物陶瓷分为3类。其中羟基磷灰石(HA)和β-磷酸(β-TCP)是最常见的人工合成磷酸钙材料。HA在天然骨组织中含量达60%,具有成骨诱导作用。β-TCP作为另一种常见的磷酸钙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植入机体后可直接与骨结合,在rh-BMP2后可异位成骨[13]。目前,临床上已经将生物陶瓷材料应用于治疗颌面骨缺损了,3D支架空间内部逐渐被新生骨组织替代,新生骨和骨小梁结构样组织填充在缺损区域内[14],但如何再生出具有生理性、生物学特性的骨组织结构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需要较大的样本量来评价生物陶瓷材料对牙槽突裂修复的疗效[15]。
1.2 聚合物:近年来,聚合物作为功能高分子材料之一,其年增长率一般都在10%以上,其中用于修复细胞和组织的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的增长率达到了50%。由于它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以及医疗安全性,所以可应用于整形外科、伤口护理等[16],其中几种高分子材料已经用于修复口腔黏膜和颌面部骨,如牙槽突裂[17],包括聚ε-己内酯(PCL)、聚乳酸(PLA)、聚癸二酸甘油酯(PGS)等[18]。这些聚合物可以在受控条件下大量合成,从而确保均匀和可重复的性质,同时还能生产出特定的结构,并且通过改变聚合物本身或结合不同聚合物来控制支架的降解性。还能降低感染和自我免疫原性的风险[19]。MARTiN M等人[20]制作了由多壁碳纳米管和聚己内酯制成的膜复合材料,证明了它们对人牙髓干细胞黏附和增殖的能力,并促进它们向允许骨再生的骨样表型的成骨分化,因此可以用于牙槽突裂的再生。但是聚合物作为一种材料,长期移植后的钙化问题,以及与血管吻合度等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各种材料在体内的长期疗效也有待观察[15]。
2 干细胞
成体干细胞在特异性诱导因子存在的条件下,可以多方向分化,它可以分化成机体的各种组织,并发挥不同生物学功能[21]。
2.1 脂肪干细胞:脂肪干细胞(ADSCs)已经证明了具有分化为骨和软骨的能力。有研究报道提取自体ADSCs,它可以在没有任何支架的情况下完全分化为3D成骨样植入物。对兔模型的研究表明将ADSCs植入特定的尺寸胫骨缺损可明显提高矿物质含量和骨再生[22]。对狗模型的研究表明,在供体部位自体移植物可用性或发病率有限的情况下,潜在的植入(HA/TCP)双相骨替代物的ADSCs中的6个,能够重建颌面部骨的缺损,因此证明它们是可以修复牙槽突裂的自体骨的替代物之一。ADSCs还具有在受损部位促进周围神经的再生的能力[23]。有研究表明,ADSCs在注射入机体后可以存活在神经系统中,同时可以分泌许多促神经愈合的因子[24]。虽然已有实验证明脂肪干细胞在动物体内具有颌面骨再生的能力,但在人体内的实验报道还较少。鉴于人伦安全等问题,临床还未得到广泛应用,所以ADSCs在人体内的疗效及安全性还有待考量[25]。
2.2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是一种多能干细胞,具备向成骨细胞、肌肉细胞、脂肪细胞、软骨细胞、成纤维细胞等多种细胞分化的能力[26],已有实验及临床研究证实BMSCs结合支架材料具有治疗牙槽突裂的可行性[27]。但BMSC的活性随着人年龄的增加而降低,并且BMSC的生物活性支架如何在人体内建立有效的血液循环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28]。
3 再生因子
3.1 纤维蛋白胶:纤维蛋白胶(FG)作为一种骨诱导分子,是由凝血酶对纤维蛋白原作用后形成的天然生物聚合物[29],它可以应用于修复颌面部缺损的整形外科与颌面外科。富含血小板的纤维蛋白(PRF)是一种含有TGF-β1等大量生长因子的纤维蛋白,具有刺激多种类型细胞的增殖和分化的作用[30]。FG作为PRF生长因子的来源,也能够促进颌面部软组织与硬组织的愈合。有研究表明,PRF根据不同的浓度梯度对牙髓干细胞的增殖活性也有不同的增强作用[31]。同时,PRF生长因子还具有长期的生物效应。PRF的纤维蛋白网络允许血管生成及形成、神经发生,以及在再生部位移植物存活所必需的内皮细胞的迁移[32]。不过,凝血酶与纤维蛋白原最佳适配浓度,仍需进一步研究。
3.2 骨形态发生蛋白2(BMP-2):BMP-2是成骨调节因子,具有最强的成骨诱导能力,是骨组织工程中应用最广泛的生长因子之一。目前在临床上已开展了BMP-2用于口腔颌面部骨再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理想的治疗效果,但也有部分临床研究发现BMP-2的骨再生效果并不理想。将来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证据,进一步综合评估BMP-2的临床疗效。
4 复合材料
单独使用上述材料存在诸多缺点,无法满足临床要求,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结合各类材料的优点制备一种复合材料,来突破单一材料的不足。
4.1 壳聚糖复合二甲双胍材料:壳聚糖是从蟹壳类动物外壳提取的天然生物活性成分,主要作为一种固化剂在组织工程中应用,在增加支架机械强度的同时于生物体内能有效降解,且不存在免疫原性[33]。二甲双胍可刺激机体干细胞进行成骨分化,因其具有热稳定作用,所以在支架材料内能够缓慢释放,进而维持整个成骨过程。有研究证实壳聚糖复合二甲双胍材料对于骨组织再生的促进、骨组织代谢作用,且修复区域的新生骨与支架材料能够完全融合[34]。此复合生物支架材料在骨缺损修复中表现出良好的修复再生作用及组织相容性,但在临床研究中仍存在许多局限性,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来评估壳聚糖复合二甲双胍材料的临床疗效[35]。
4.2 聚乳酸/骨粉/丁-乙二酸丁二醇酯复合材料:聚乳酸(PLA)是广泛研究和利用的可生物降解和可再生的脂肪族聚酯,它可以随着时间将应力转移到受损区域,从而允许组织愈合。丁-乙二酸丁二醇酯(PBSA)具有良好的生物力学性能和生物可降解性[36]。利用3D打印技术将PLA、PBSA和猪骨粉(BM)材料混合,采用3D打印制备出替代骨。研究表明3D打印的PLA/PBSA/BM复合支架具有良好的生物学性能和生物相容性,能有效修复骨缺损,为骨细胞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微环境,促进骨细胞的生长[37]。这种复合支架在骨组织工程修复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但也缺乏广泛的临床应用,目前仍无法正确评估此复合材料的临床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