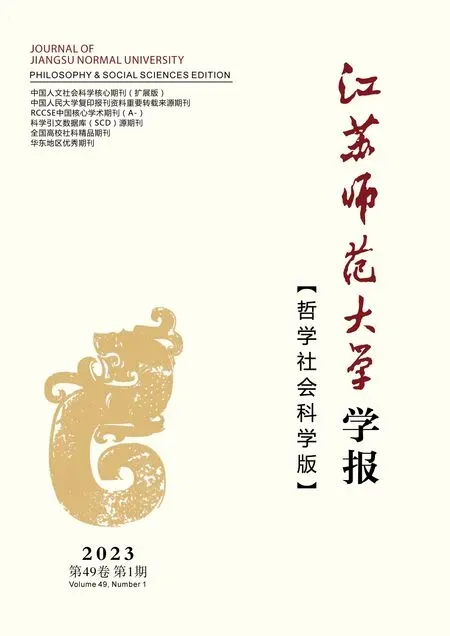徐文长与“徐文长”的戏曲评点
张勇敢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在中国戏曲评点史上,碧筠斋嘉靖二十二年刊刻《古本西厢记》,这是今知最早的戏曲评点本。大约这部坊贾主导的商业型评本问世十年后,徐渭以文人身份涉足当时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戏曲评点,为戏曲评点注入强大的动力。徐氏评点的《西厢记》流播坊间,旨在射利的书坊敏锐地嗅到了徐评本的商业价值,刊印了诸多冠以徐渭名号的戏曲评本,留存至今的便有六种。学术界讨论这些批本时争议很大,徐渭本人的戏曲评点有何特色及价值?冠名徐文长的戏曲评本如何认定?题署徐氏名号的序言又该如何定性?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继续探讨。
一、徐文长的戏曲评点
徐渭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不仅撰有闻名于世的《四声猿》,而且著有全面展现南戏风貌的《南词叙录》。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徐渭还是最早从事戏曲评点的文人,王骥德对其评点《西厢记》的情况多有记述,如“往先生居,与予仅隔一垣,就语无虚日,时口及崔传,每举新解,率出人意表。人有以刻本投者,亦往往随兴偶书数语上方。故本各不同,有彼此矛盾不相印合者。”(1)王骥德:《题记》,《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六,万历四十二年刊本。又如“天池先生解本不同,亦有任意率书,不必合窾者;有前解未当,别本更正者。大都先生之解,略以机趣洗发,逆志作者。至声律故实,未必详审。”(2)王骥德:《评语》,《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六。徐渭仕途坎坷,生活困顿,一生辗转多处,有段时间和王骥德“仅隔一垣”。根据徐朔方先生的研究,徐渭“嘉靖三十一年迁居目莲巷,与其弟子王骥德仅一垣之隔。盖三十七年冬迁塔子桥,三十八年即徒(徙)”(3)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徐渭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据此可以判定,早在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徐渭已经开始了《西厢记》的评点工作,这是今知最早的文人评点戏曲记录。他评点之时不拘文意,故能时时出新,发人深省,堪称“随兴”而题、“任意”而书之评点。再借助上述“本各不同”“前解未当,别本更正”等记载可知,徐渭的戏曲评点应当持续数年,并在多部《西厢记》上施评,且各部评本的观点存有差异。
遗憾的是,徐渭生前不曾自刻评本,亦无好友为其出资刊印,题有徐渭手批的文本已经佚失。今见冠以徐渭字号的《西厢记》评本颇为复杂,其间有寓含徐文长部分真批而又经书坊增饰的评点本,又有杂糅众本批语而成的托名评本(见下文)。此二者或难以判定真正的徐氏批语,或与真正的徐评本毫无关系,都不宜作为探讨徐渭戏曲评点的有效史料。若想真切感受徐渭的戏曲评点,还须从频频记述徐氏评点事宜的王骥德身上寻求突破。作为徐氏弟子,王骥德熟悉其师《西厢记》评点:“余所见凡数本,惟徐公子尔兼本,较备而确。今尔兼没,不传。”(4)王骥德:《题记》,《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六。这部最具代表性的徐尔兼藏本亡佚不传,幸其部分批语以“徐云”面目进入《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王骥德曾明确指出:“余注自先生口授而外,于徐公子本采入较多。”(5)王骥德:《评语》,《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六。其间口授、采录部分,显然可以成为我们探察徐渭戏曲评点的文献。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中,王氏又指出“微辞”“方言”之注解,“大抵取碧筠斋古注十之二,取徐师新释亦十之二。”(6)王骥德:《自序》,《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首。而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凡例”中,王氏又说他引录的“天池先生新释”标以“徐云”(7)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凡例》曰:“凡采用碧筠斋旧注,及天池先生新释,并不更识别时,间揭一二。筠注曰‘古注’,徐释曰‘徐云’,今本直曰‘俗注’。”。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借助《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的“徐云”批语探析徐渭的戏曲评点,其间所得虽非徐评全部,但却能一窥徐氏评点之真貌,进而探知中国戏曲评点领域中的文人初评情形。
审视这些“徐云”批语可以发现,徐渭有时是对摘选的具体内容进行解释、分析,如评点《西厢记》首折〔后庭花〕唱词云:“‘衬残红’二句,只应上白‘怎生便知他脚小’意,‘休提眼角’以下,又推出一层意,‘慢俄延’以下四句,正脚踪儿将心事传也,‘刚刚打个照面’,正眼角耳留情处也。‘栊门’指莺莺进去之门,言其形之纡徐系恋,及门而举步差远,复打个照面,而传情无已也。”(8)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一第一套〔后庭花〕尾批。徐氏评点之时先摘词句,然后对其语义、文情等进行解析,此类文字主要以文本疏解为要。有时是对曲白进行鉴赏、评论,如“亵而雅,真妙手也”(9)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四第二套〔小桃红〕尾批。“此极亵之词,却用得免俗”(10)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三第一套〔赏花时〕尾批。“全篇皆梦中语,从天而降,模写如画”(11)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四第四套〔水仙子〕尾批。等,揭示了《西厢记》文辞及情境的精妙处。徐批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人”为中心的讨论,如对王实甫描摹莺莺美貌的曲文“解舞的腰肢娇又软”,徐渭批曰:“‘解舞’以下四句,形容略似妓人,与前‘颠不剌’数语相戾,且与前‘未语人前’数语又自不类。”(12)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一第一套〔幺〕尾批。徐氏认为此处摹出一位风情万种的倚门“妓人”,这不合莺莺矜持、娇丽之形象,且与前文“颠不剌”“未语人前”等摹画的莺莺形象大相径庭。人物形象之外,徐渭亦对人物语言予以观照,对于不合身份的酸腐之语,他批以“‘人有过’以下数语,不免头巾”(13)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四第一套〔油葫芦〕尾批。;对于写人效果较好的谐趣之语,徐氏则予以褒赞,如“回话夫人妙绝,末二语更俊”(14)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四第二套〔鬼三台〕尾批。。徐渭以“人”为视角的批语还有不少,如“‘无语低头’,只寻常扯凑,自他人旁观而状之即可,不应莺之自称。”(15)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五第一套〔金菊香〕尾批。又如“‘佳人薄倖’及‘无信行志诚’,俱不得实指莺莺说,盖此施于逾墙抢白之后则可。此时莺初无背盟之意也。”(16)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二第二套〔朝天子〕尾批。前者是说,莺莺低头自语的情态当为他人所见,与此相关的唱词不应出自莺莺之口;至于后者提及的“薄倖”诸语,则与莺莺言行及思想相违。这些批语通过曲白摘录、品评建构鲜活的戏曲情境,然后在生动的情境之中考察人物言行的得体与否,展现了徐渭对于戏曲人物书写问题的敏锐捕捉及细致思考。
作为中国古代最早从事戏曲评点工作的文人,徐渭借鉴《古本西厢记》的摘评体式,同时又凭借自身的戏曲创作及批评优势打开了《西厢记》评点的新格局。不无遗憾的是,文献佚失及书坊作伪令徐评《西厢》风采难以再睹,所幸《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引录的“徐云”批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这些以曲文、人物为对象的评点,今日看来或许不免显得内容单薄,但在嘉靖年间却是非常难得的戏曲论述。更为重要的是,“徐云”批语还有助于认识中国戏曲评点的初期形态、视角及内涵,其作为最早的文人评点所蕴含的特定戏曲评点史价值无法替代。
二、“徐文长”戏曲评点之讨论
万历中后期,多部冠以徐文长名号的评本涌进市场,今日可见者有《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以下简称“画意”本)、《田水月山房北西厢》(以下简称“田水月”本)、《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等多部。这批评点本不仅引发了古人的广泛关注,而且成为现代学术研究中的热闹话题,相关讨论主要涉及两点:
其一,“画意”本与“田水月”本的刊刻时序及关系。学者多从刊本形态及内容探究二者的刊刻次序,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张人和先生有云:“学术界一般认为田水月本刻于万历,《批点画意北西厢》刊于崇祯”(17)张人和:《田水月本〈西厢记〉与〈批点画意北西厢〉》,《〈西厢记〉论证》(增订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67页。。王钢先生对上述推论提出质疑,谨慎提出“似乎批点画意本更早一些”的看法(18)王钢:《也谈徐渭评本“北西厢”》,《文献》,1988年第3期。。和刊印时序密切相关的话题是,“画意”本与“田水月”本的关系。张新建从卷前序言、版本形态、出目总目、批语字体诸方面,比堪“画意”本与“田水月”本,指出二者在体制方面遵守碧筠斋本旧制,在吸收筠本注释的同时又做了大量的评释工作(19)张新建:《〈田水月山房北西厢〉与〈重订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之关系》,《文献》,1986年第2期。。此论谈及两部评本的底本问题,稍后王钢提出“画意”本、“田水月”本乃为王起侯刻本的挖改重印本的观点(20)王钢:《也谈徐渭评本“北西厢”》,《文献》,1988年第3期。。在指出二者同源共祖的同时,学术界也探讨了二者自身的内在关联,早期研究者提出“画意”本使用“田水月”本的原版,并通过挖版的方式添加批语(21)张新建:《〈田水月山房北西厢〉与〈重订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之关系》,《文献》,1986年第2期。;“田水月”本“似乎是原刻”,画意本“很可能是依据田水月本而重刻的”(22)张人和:《田水月本〈西厢记〉与〈批点画意北西厢〉》,《〈西厢记〉论证》(增订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67页。。近年来,研究者多认同“画意”本先于“田水月”本的观点,提出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增删本或翻改本,如“田水月”本应是“画意”本的翻刻本,前者是徐渭晚年评定本,后者是徐渭早期评本,前者在后者基础上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批语(23)杨绪容:《王实甫〈西厢记〉汇评》,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其二,“画意”本、“田水月”本等能否称为徐渭评本?这些标榜徐文长的评点本在明清时期非常引人关注,先有徐渭本人“滋喙”暨阳刻本,后有王骥德一针见血地声讨:“世动称先生注本,实多赝笔”(24)徐渭:《和唐伯虎题崔氏真诗》,《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六。。及至凌濛初评校《西厢记》时,亦以“赝笔”批判:“徐解牵强迂僻,令人勃勃。”(25)凌濛初:《西厢记凡例十则》,《西厢记》卷首,天启年间刊本。到了清初,毛先舒更是一语道破评本真身:“田水月本,改《北西厢记》最悖谬,举一端耳,合‘田水月’成‘渭’字,当是市佣伪托徐天池。”(26)毛先舒:《诗辨坻》,《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一集),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564页。明清文人对冠称徐文长的批本多持否定态度,斥之伪作的呼声不绝于缕。而现代不少学者以徐渭评点戏曲文献为依据,推论昔日的徐评本即为今日可见的“画意”本、“田水月”本。之所以论定二者为徐渭评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卷前有署以徐渭字号(“漱者”“青藤道人”)的自叙,且“田水月”本又有徐渭印章“田水月”之标志,这些直观证据确实容易让人信以为真。与此同时,又有学者感受到了这些刊本身上的商业色彩,从而谨慎得出真伪同存的学术观点。如蒋星煜先生认为《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徐文长批点本的”(27)蒋星煜:《〈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考》,《〈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页。,“被人议论最多的田水月山房本以及我所发现的明山阴延阁主人李廷谟订正的《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在内,都很难被证明是陈洪绶所说的‘真本’。”(28)蒋星煜:《六种徐文长本〈西厢记〉的真伪问题》,《〈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页。基于上述讨论可说,冠名徐文长的批本多有不同,各本须分别对待,杨绪容对此指出:“田水月”本与“画意”本最为接近已经失传的徐尔兼藏本,它们都是徐评“真本”,崇善堂翻刻“田水月”本而成的《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亦为“真本”;李廷谟《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不能算作“真本”,明后期刊印的《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很可能是徐评赝本(29)杨绪容:《徐渭〈西厢记〉评点本系统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前贤时俊已对冠名徐文长的《西厢记》评本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前辈学者如张人和、蒋星煜等小心求证,时下学者如黄季鸿、陈旭耀、杨绪容等细心比对,谨慎推理,确实解决了不少复杂的学术难题。学术界虽然取得某些共识,但其间存在的分歧也很明显,这批评本身上还有不少待解之谜。朱万曙先生谈及徐文长评点系统时指出:六种评本表现出一脉相承的关系,各本评语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又有不少批语是相同或意思相近的。它们的刊刻时间难以考订,究竟孰先孰后,谁影响谁,也难以确定(30)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219页。。斯言甚是。无论是评本的刊印时序及内在关系,还是诸本的真伪程度及属性,都存在着明显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声音,这批评点本显然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在中国戏曲评点史上,士商协作是万历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戏曲评点生成机制,书坊纷纷借鉴名公资源打造“名公”评本,“李卓吾”“陈眉公”“汤显祖”等皆是书坊倾力打造的评点“明星”。作为有明一代“奇”人的徐渭,无论是其全面、卓越的文艺才能,还是其狂荡不羁、傲视权贵的“狂人”形象,抑或是引锥自戕、举斧击颅、击杀继妻的“异士”行为,都使徐渭成为晚明社会的焦点人物。再加上徐渭真实的《西厢记》评点经历,徐文长自然容易成为书商的重点作伪对象,今见冠以徐文长名号的评本即可视作书坊打造的“徐文长”评本。这批评点本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而言,“画意”本、“田水月”本借鉴徐渭批语,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徐评本。我们前文列举的“徐云”批语,有不少在“画意”本、“田水月”本中难觅踪迹,相对于徐渭“无语低头”之批,“画意”本“似他人语”(31)《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卷五第一套〔金菊香〕眉批,明刊本。之批不免显得乏善可陈。较之徐氏为“无信行志诚”所作的评语,“画意”本批以“‘信行’‘至诚’,红自述己德”(32)《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卷二第二套〔朝天子〕眉批。。此批不仅浅显,而且存有明显错误,因为剧中“谁无信行?谁无至诚?”是红娘对张生“你姐姐果有信行”疑虑之回应,“画意”批语将之视为红娘“自述己德”实有不妥。鉴于“画意”“田水月”批语与真正的徐批在文字表述、解析程度等方面差距较大,且不乏有违《西厢记》文本内容的低级错误,我们很难相信它们是真正的徐文长评本。但不容否认的,“画意”“田水月”本参考、借鉴了徐批内容,上述“画意”本中的“似他人语”即与徐批视角完全一致,而前引“徐云”卷一第一套〔幺〕曲尾批又见于“田水月”本。故此我们认为,“画意”本、“田水月”本直接或间接地汲取徐文长戏曲评点的内容,是寓含部分徐批而又经书坊增饰的“徐文长”评本。至于直接冠名的《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它不仅袭取“画意”本的部分评语,而且大量抄录容与堂、起凤馆等书坊刊印的《西厢记》评语,可以称为杂糅众本而成的托名评本。稍后出现的《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同样是杂抄、拼凑而成,它们只是袭用徐氏名号而与真正的徐批毫无关联,更可称为书坊基于商业利益而伪造的“徐文长”评本。
三、对“徐文长”戏曲评点的两点认识
“徐文长”是晚明书坊炮制的“名公”评点个案,其研究离不开以评点本为本位的细致辨析,同样少不了晚明时期“名公”评点视域的综合审视。拓宽研究视野,将“徐文长”置于“名公”评点的生态环境中,“徐”评本的真实面目与历史意义才能得以更好地呈现。现以已有的学术成果为基础,对“徐”评研究中关注不够、争议较大的两个问题略作阐述。
(一)“暨本”:今知最早的“名公”评本
今见最早的“名公”评本是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刊刻的标以“李卓吾先生批评”的五部作品。一年之后,“徐文长”评点的《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记》面世,此时距徐渭评点《西厢记》已有50余年的时间。徐渭评点戏曲的时间约早于李贽40年,徐文长的坊间盛名不不逊于李卓吾,何以“徐文长”评本晚于“李卓吾”评本呢?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万历坊间早有“徐文长”评本出现,这便是今知最早的“名公”评本:“暨本”。
“暨本”之名见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评语”:“今暨阳刻本,盖先生初年略之笔,解多未确。又其前题辞,传写多讹,观者类能指摘。……暨本出,颇为先生滋喙。”(33)王骥德:《评语》,《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六。徐渭曾在多部《西厢记》上面施加批语,这些批本在文人群体或市井坊间流传,并成为书坊炮制名家评本的资源,暨阳书坊即汲取徐文长批语打造“徐文长”批本。诸葛元声应邀为“暨本”作序:“苧罗乡王君起侯父,幼抱奇案,擅华未露,诵读之暇,一见文长手稿,即欣然命梓。”(34)诸葛元声:《序》,《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卷首。王起侯籍贯在西施故里“苧罗乡”,此处位属诸暨,亦即唐五代时改称的“暨阳”,此次王起侯刊刻的《西厢记》即为王骥德提及的“暨本”。万历三十九年,《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以“重刻”之名问世,它与王骥德描述的“暨阳刻本”的形态、特征相同,故其翻刻底本当为王起侯刊刻的“暨本”。从“暨本”到“画意”本,剧中批语或有变化,但前者的主体面貌应当保存在后者中。另有书坊在“画意”本的基础上增删批语,刊成《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早出的“暨本”已经成为后来“徐文长”评本的建构基础,“画意”本相应地可以用来返观佚失“暨本”的形貌。“暨本”卷首不仅含有诸葛元声撰写的绍介评点、刊印情况的序,还有多篇署曰“漱者”“青藤道人”“秦田水月”撰著的叙言。就批语一端而言,“暨本”确实含有徐渭《西厢记》评本的批语,同时也有大量批语实系书坊人员增写,此为书坊打造“名公”评本的常用伎俩。这部最早的“名公”评本不容乐观,因为据其翻刻的“画意”本即存在多方面的舛误。以“漱者”之序为例,其间“碧筠斋”题为“碧筠齐”,“齐本”“齐正”为“斋本”之误,“崔张”误作“董张”,“陶宗仪”误作“陶客仪”。不止如此,“画意”本的卷前目录与剧中目录也不一致,如《僧房假寓》与《僧房假馆》、《斋坛闹会》与《清樵目成》、《衣锦还乡》与《衣锦荣归》等。有理由相信,这些讹陋也会存于“暨本”身上,此或为徐渭对其“滋喙”不已的重要缘由。
“暨本”尽管校勘不精,但其在中国戏曲评点史上的意义还是非常突出的。依据存世的戏曲评点文献,我们认定万历三十八年的“李卓吾”评本为“名公”评点之开端,但在徐渭逝世的万历二十一年之前,“徐文长”评点的“暨阳刻本”已经出现。所以“暨本”是今知最早的“名公”评本,它比“李卓吾”评本至少早出18年。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在万历前期诸家书坊纷纷推广校注为主、评批为辅的戏曲评本时,暨阳书坊已经富有前瞻性地开发“名公”资源了,晚明时期蔚为大观的“名公”评点由此拉开序幕。
(二)“自叙”:能否作为徐评真伪的判定依据?
《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今存多部藏本,各本卷首自叙篇数不等,这种情形应为内容缺略和后人错订所致,实际情况为该书卷前当有分别署为“漱者”“青藤道人”“秦田水月”的序言(35)陈旭耀:《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三篇题署徐渭字号、印字的序言,成为今人认定徐渭评本的有力证据,但在伪评盛行的万历后期,我们不禁要问:它们真的出自徐渭之手吗?
卷前三篇自叙,首为“漱者”之《叙》,曰:
余于是帙诸解并从碧筠斋本,非杜撰也。齐正(斋本)所未备,余补释之,不过十之一二耳。齐(斋)本乃从董解元之原稿,无一字差讹。余购得两册,都偷窃。今此本绝少,惜哉!本谓董(崔)张剧是王实甫撰,而《辍耕录》乃曰董解元。陶客(宗)仪,元人也,宜信之。然董又有别本《西厢》,乃弹唱词也,非打本。岂陶亦误以弹唱为打本也耶?不然,董何有二本?附记以俟知者。漱者。(36)“漱者”:《叙》,《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卷首。
此叙不明“董西厢”与“王西厢”之别,认为董解元撰著两部《西厢》。“漱者”乃徐渭别号,我们实在难以相信在戏曲界热烈讨论《西厢记》的晚明,撰有戏曲作品、著有戏曲理论的徐渭竟会如此懵懂无知。其实从《南词叙录》提及北曲杂剧的情况来看,徐渭对杂剧文献是十分熟悉的,其《南词叙录》开篇即云:“北杂剧有《点鬼簿》,院本有《乐府杂录》,曲选有《太平乐府》,记载详矣。”(37)徐渭:《南词叙录》,《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黄山书社,2009年,第482页。而《录鬼簿》分别列举“董解元”“王实甫”,前者以创始之功位列卷首,后者则附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这些情况应为徐渭知悉。基于此序存有《西厢记》常识性错误,我们不得不怀疑“漱者”的真实身份。
次为青藤道人《叙》,云:
余所改抹,悉依碧筠斋真正古本,亦微有记忆不明处,然真者十之九矣。白亦差讹,甚不通者,却都碧筠斋本之白矣,因而改正也。典故不大注释,所注者正在方言、调侃语、伶坊中语、拆白道字、俚雅相杂、讪笑冷语,入奥而难解者。青藤道人。(38)“青藤道人”:《叙》,《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卷首。
“青藤道人”亦为徐渭之号。此叙说“改抹”悉遵碧筠斋本,上述漱者叙说“诸解”皆出自碧筠斋本,自己“补释”只占十之一二。若此,“青藤道人”“漱者”的戏曲评点与碧筠斋的校注、评批具有高达百分之九十的相似度。我们知道徐渭的戏曲评点是一种“随兴偶书”“任意率书”的评点风格,所言、所论多“出人意表”,试问其评本怎么能与校注为主的碧筠斋本持有90%的相同批语。“画意”本是以“暨本”为基础的重刻本,其间作品题旨之发掘、人物情态之鉴赏、叙事艺术之揭示等内容令人欣喜不已,我们实在难以相信这些品评性质的批语会出现在中国最早的戏曲评点本——碧筠斋本之上。所以无论是从徐渭评本与碧筠斋本的相似度来考虑,还是从嘉靖年间碧筠斋本的评点视角、价值来推测,我们都很难相信撰写叙言的“青藤道人”“漱者”就是徐渭本人。
最后为“秦田水月”的《自叙》:
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我煦煦也。岂惟剧哉?凡作者莫不如此。嗟哉!吾谁与语?众人所忽,余独详;众所所旨,余独唾。嗟哉!吾谁与语。(39)“秦田水月”:《自叙》,《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卷首。
该序后署“秦田水月”,钤有“文长”“酬字堂”二印。其间“秦田水月”为徐渭印字,“文长”“酬字堂”分别为徐氏的号、宅名,三者都将序言作者指向徐渭本人。序言并举“本色”“相色”,并对二者予以通俗化解释,最后表明“贱相色、贵本色”的文艺观点。从题署、内容等方面来看,这篇富有文人色彩、理论思想的序言是有可能出自徐渭之手的。但在前述两序真实性堪忧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得不对“秦田水月”之叙保持一定的警惕。在此序真假难以直接判定的情形下,不妨看看晚明的一部题署徐渭编选的戏曲选本《选古今南北剧》。该集卷首有署曰徐渭的自序:“渔猎之暇,曾评订崔张传奇,予差快心,亦差挂好事者齿颊。已而旁及诸家,随手摘录,都无标目,亦无诠次,间忘所自出。总之,此技唯元人擅场。故予所取十之七八,而近代十二三。”(40)“秦田水月”:《序》,《选古今南北剧》卷首,明代清远斋刊本。序言以徐渭口吻自述,且题“秦田水月漫题”,序后更有“文长”“酬字堂”二印。该序言之凿凿,且有徐氏题名、印名、宅名,但《选古今南北剧》却非徐渭摘选。因为该集前三卷几乎全部录自《雍熙乐府》,甚至连编排顺序也一样;同时集中还出现了徐渭逝世之后的作品,这明显是一个假托徐渭的选本(41)徐朔方:《托名徐渭的〈选古今南北剧〉与〈古今尺牍振霞云笺〉》,《文献》,1991年第3期。。《选古今南北剧》的序言显然是他人伪作,与其题署、钤印相同的“秦田水月”之叙或亦如此。
对于“徐文长”评点的数部《西厢》评本,卷首题为“漱者”“青藤道人”的序言多因错讹不堪而引人注目,令人生疑。蒋星煜即云:“这两篇题语是否真的出于徐文长的手笔呢?要作出否定的回答也拿不出根据。使人们最困惑的是:像这样一个戏曲专家,会不会分不清董西厢与王西厢呢?”(42)蒋星煜:《〈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考》,《〈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页。上述质疑甚是。晚明的戏曲评点中,托名题序现象并不少见,如“李卓吾”评本题有“李贽”“卓吾”“秃翁”“卓老”等名号的序,又如“陈眉公”评本上的“继儒”序,皆为此类。所以立足作伪成风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得不对问题重重的序言作出伪名题作之推论。合而言之,标署徐渭不同字号、印名的序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们当为书坊装饰评本、壮大声势之伎俩,不宜视作判定徐评真本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