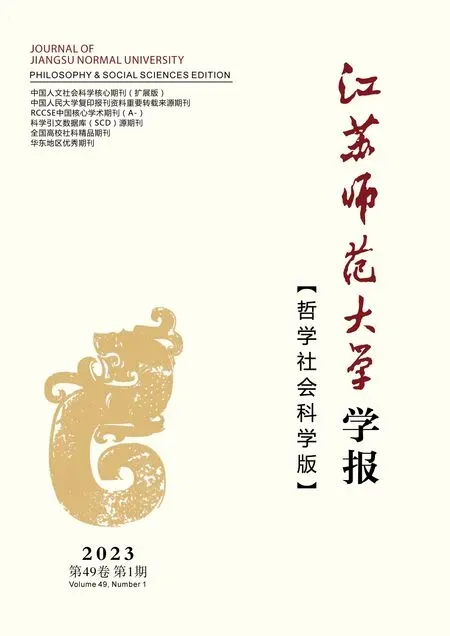中国佛学对主体的解构
董占梅 石义华
(江苏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主体是西方哲学中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诚然,佛学没有“主体”概念,但是主体问题也是佛学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佛学对主体的态度不是简单的“高扬”,也不是简单的“贬抑”。既不是简单的肯定,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总的来说,佛学是要打破加于主体之上的种种限制,努力超越主体的有限性,达到主体的不断自我更新。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步骤:“否弃”主体;寻找主体的替补;最后达到主体的复活或者是重新挺立。主体的这种自我更新符合辩证法的自我“扬弃”。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否定精神也有相通之处。笔者把它称为“主体的涅槃”。
后现代主义有许多主张。比如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体系,主张碎片化,等等。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尽管多种多样,但也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这就是轻视单纯的建构,重视解构。相对肯定性来说,后现代主义更强调否定。它在对事物的理解中也总是从其暂时性的方面去理解。在对于主体的看法上,后现代主义与佛学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如后现代主义强调解构、强调主体的生成性或暂时性、主体的碎片化。后现代主义的这些观点与佛学存在相似之处。譬如佛学“无常”与“无我”的主张,就带有对主体的“否弃”性质。这种思想体现在中国佛学中,就是主体被视作一个“假名人”“无位真人”。
一、“假名人”:一个“伪主体”
主体概念具有认识中心、价值中心的含义。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一般态度是否定。主体也是许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拉康、福柯、德里达等学者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对主体进行了清算。拉康则彻底消除了理性、自我意识的中心地位。福柯通过对权力话语的分析,阐述了自己的非理性主义观点,从而动摇了主体的中心地位,因为主体正是理性的产物。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摧毁了理性自我同一的幻象,也摧毁了主体的自我同一。
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清算也是有其思想来源的。这个来源就是精神分析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等观点。第一,精神分析主义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对自我三层结构的分析,即对本我、自我、超我三方面的分析,既揭示了人的自我统一的虚假性,也揭示了本我的重要地位。在弗洛伊德看来,本我是具有基础性的,是人的各种活动的内在驱动力。理性、意识即自我,事实上不过是本我与超我的仆人,而非带有中心性、支配性的主人。并且,自我处于一仆二主的窘境之中,因为它既要想方设法满足本我的永无餍足的需要,又不能违反社会道德的要求以及个人的良心。第二,现象学对于主体的中心地位是一个挑战。主体概念带有的认识与价值中心性质,是为现象学所反对的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胡塞尔的现象学开辟了超越主体客体二元对立式认识论的框架。虽然后人对现象学也颇有微词,但现象学对二元论的批判,却被包括后现代主义者在内的很多思想家所继承下来。第三,就存在主义来说,萨特主张虚无在人的本质之先;海德格尔以存在取代“存在者”、取代人的位置。第四,在结构主义那里,主体性更是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首先,它是结构主义对人的能动性的祛除。结构主义认为,“人只是构成结构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关系项,它本身没有独立性,只是由结构所决定的,因而是被动的,而不是能动的。”(1)徐崇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37页。从结构主义的原则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的身份不是由它自身决定的,而是由它所处的系统的结构以及它在系统中占据的位置所确定的。人的思想言行也不能不受到结构的影响。结构对于人来说,具有先验性。人们只能在既定的结构中活动,而不能随意选择结构。受结构的制约,人不可能成为历史的主人,不可能实现存在主义所极力阐扬的创造性与绝对自由。其次,它是结构主义对人的中心地位的消解。结构主义针对主体的中心地位提出了“主体移心”论。“所谓‘主体移心’论,就是否认个人在认识和实践中的作用,也就是否认思维主体能够在认识论上居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地位,而把人溶化到客观化的、无个性的和无意识的结构之中,认为这些结构决定着人的全部行为,就是人的全部生存的结构,而主体则是消极被动的,是某种外在力量的表现。”(2)徐崇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结构主义的去中心使得主体失去了作为认识中心、价值中心的地位,也失去了在实践中的支配地位。这些就使得主体概念丧失了其原有意义,主体从理论上被取消了。
不少后现代主义者也被视为后结构主义者,如福柯、德里达等人。他们拒绝后结构主义者的称号,声称自己仍然活动于结构主义的范围内。事实上,一个人的思想如何并不一定像他本人所声称的那样,后结构主义者对主体的清算有他们自己特有的方式。福柯消解人的方式是通过他所发明的“考古学”以及对权力话语的分析实现的。他通过对历史上人的概念的考察,得出的结论如下:人并不一直具有独立的意义;人的性质与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人、主体有着不同的意义;其具体内涵(或者说是人的本质)随着历史、文化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着。人的理性、创造力也是有限的,这就是说,他对于物的支配能力是有限的。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福柯认为人不过是一种语言构造,一种话语效果。因此,在尼采放言“上帝死了”之后,福柯开始“哀悼”“人之死”。尼采谋杀了上帝,而福柯“终结”了人,德里达则对包括主体在内的一切都持有解构的态度。
主体也是其他后现代主义者要颠覆的对象。首先,拉康就不承认主体的自足与自主。在他看来,自我讲述的不过是“他者”的话语。他沿着弗洛伊德的道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揭穿了主体作为自我统一物的假象,揭示了主体对于“他者”的依附关系。其次,巴特也认为主体居无定所,人们谈论主体的时候就是在谈论他者,这样的主体不过是一种话语效果,是语言的产物。“罗兰·巴特断言,在汪洋大海般的文本漩涡里,作者死了。”(3)汪民安:《后现代主义性的谱系》,见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主义性的哲学话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在巴特看来,作者不是文本的主人,不是语言的操纵者,而陷溺在语言的罗网里,被语言缠缚。巴特还用多元论思想拆解主体的统一性。他认为人的身体有多个,肉体的,精神的,文化的(人为的),其相互关系是差异而非同一。巴特赞成禅宗的思维方式,他说:“整个禅宗都在进行一场战争,反对把意义亵渎。我们知道,佛教对任何肯定(或否定)引入的死胡同加以堵塞,它劝说人们永远不要被下面四种命题所缠绕:这是A——这不是A——这既是A也是非A——这既不是A也不是非A。”(4)罗兰·巴特:《符号帝国》,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9页。巴特认为,佛教的这种方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所建构的范式是一致的。他们都对语言持消解的态度,使语言达到意义的“零度”。这样一来,作为语言产物的主体也失去了确定性,失去了自己的确切内涵,染上了虚无性。
佛教因缘法认为,人不过是由“四大”“五蕴”和合而成,本身绝无确定性、实体性,不过是一个假相而已。这也是佛学割裂人自身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人与外部事物关系后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离开了其所处的各种关系,我们无法确定一个人的本质。但另一方面,佛学的这种认识也破除了主体的实体性,因为人的本质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其本质也由“四大”“五蕴”这些要素决定,或谓人的本质取决于 “正因” 与“缘因”二者的结合。在涅槃学者看来,“正因”即人固具的、内在的成佛依据,它是永恒的,也是常驻不变的;“缘因”是指成佛的外在条件,即成佛的外部因素。吉藏在其所著《大乘玄论》卷三中介绍关于“正因”佛性的十一家见解时说:“然十一家,大明不出三意。何者?第一家以六法为正因,此之两释,不出假实二义,明众生即是假人,六法即是五阴及假人也。”吉藏认为,关于“正因”佛性的十一家见解,事实上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以心识即真神、阿赖耶识之类为正因,另一类以众生或六法为正因。后一类中又可分为两种,以众生为正因和以六法为正因。何为众生?应当是指精神性的觉悟主体。六法是指色、受、想、行、识,“五蕴”与由此“五蕴”和合而成的人。众生也好,六法也好,都是“假人”或曰“假名人”而已。“如同轮轴和合故名为车”,人也是“诸蕴和合的产物”。应当说佛学较早地发现了概念的不逮性,认为名称是不真实的,是人为地赋予事物的,因此才称其为“假名”。事实上,它们都“无有自体”。《大涅槃经·狮子吼品》中以盲人摸象为喻,认为无论是说“色”还是“识”或者“我”,都如同是盲人摸到大象的牙、鼻、腿等,就以为摸到了大象本身,这是片面的。真正的佛性也是这样,“非即六法,非离六法,……众生佛性非色不离色,非我不离我”(5)《大正藏》第12册,第556页。。这就是说,无论哪一种要素,或是众生之我,都不是佛性本身。部分或是部分简单的和不等于整体。应当说这种认识还是符合辩证法的观点的。在佛学看来,作为整体的人也同样没有实体性,作为系统性思维的过渡,“五蕴”这种要素说,对主体的实体主义理解是一个冲击,是向关系性思维过渡的必经阶段。
除上述因缘法外,佛学对人的主体性的破除,其所采用的另一种工具是“空”或“无”的观念。在小乘佛学那里,就把“涅槃寂静”“灰身灭智”当作追求的目标。小乘禅法通过“四念处”即“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来破除对自身的执着,或说是对自己身体的贪爱。因为这种贪爱在佛学看来就是无明,是使人沉溺苦海不得觉悟的原因。但佛学所采取的方法,却是唯心的,是恩格斯嘲笑过的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土里以逃避现实危险的办法。事实上,这种方法根本不能消灭任何成佛的现实“障碍”,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
佛陀破除人的主体性的第三种方法就是缘起论。缘起论是佛陀的创造,也是佛法的理论基石,由它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由若干要素组成,且是一个随着其内部组成要素的生灭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里,佛陀事实上向我们展示了其思维方式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他的思维的动态性。缘起论破除了实体性思维方式的僵化性。在缘起论的视野中,一切都失去了其永恒的意义,一切都不会被看作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被视作一个不断改变自己固有面目的过程。
这里所提到的佛陀的后两种观点,在中国佛学中皆有表现。它们也都是中国佛学所坚持的根本观点。华严宗法藏认为:一切现象(华严宗所说的“法”)都是“从缘而起”,并“无自性”,这种看法就是缘起观与诸法皆空观点的结合。事实上,缘起论和诸法皆空的观点本来就是一致的。笔者从法藏的观点得出人没有永恒不变的主体性的结论。“无自性”的说法本身就包含否定主体性的意义在内。禅宗也有类似的看法。它认为世上的一切都不具备真实性,只是一心之所幻化。一心不起,万象皆空。即如《大乘起信论》所言、慧能大师颇为认可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6)赖永海主编,尚荣译注:《坛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9页。。黄檗禅师认同《金刚经》的说法:“三十二相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八十种好属色,若以色见我,使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一切现象都是虚幻不实的,如果监制其为实体性的存在,那都不是正确的见解,无法得出真理性的认识。相反,如果能够认识到所见到的现象都是虚幻不实的,这才看到了事物的真相,认识了佛教的真理。甚至人们心目中所谓的佛,连同认识主体自身的存在都没有真实性,用金刚经的话说“如梦幻泡影”。“空”才是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真相。《金刚经》是禅宗崇奉的重要经典,黄檗禅师在这里就引用了《金刚经》中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赞同《金刚经》中的看法,认为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虚妄的,经典上说的佛所具有的种种异相也都不过是假象而已,也就是说佛绝非是有什么具体形象的实存之物,而是一种虚灵不昧之物,是不受具体形象以及具体事物中所蕴含的道理束缚的大智慧。“佛与人生”都是虚妄的,因此他们也都不可能成为万物的中心,更没有什么主体性。
对人的主体性的讨伐,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应当说,对人的主体性的讨伐,后现代主义绝非始作俑者。其真正的前奏是维特根斯坦、萨特等人的思想。佛学对人的主体性也不乏否定,但讨伐主体性并非是要彻底消灭主体性。恰恰相反,这种方式是主体性的另一种完成,甚至可以说是主体性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膨胀。
二、“无位真人”:主体的否定性
佛学在本体论上所持的是一种否定性本体论,在对主体的看法上,佛学同样是否定性的。在原始佛学那里,佛陀就主张“无常”“无我”,并认为人我之见恰是万恶之源。只有否弃我见才能获得解脱。佛学的三科法门就是为了破除人们对“我”的执着。这里的“无”主要的应该被理解为否定而不是一无所有。把“无”理解为一无所有、理解为纯无是被黑格尔所批评过的错误观点。这在佛教中也被视作错误的观点,佛学称其为“顽空”“恶取空”。这是为佛教所极力排斥的观点。佛教主张:“宁起我见如须弥山,不恶取空。”因此“无常”“无我”的说法,是没有永恒之物,也没有固定形态的“我”。同样,西方哲学中所谓的“主体”也没有自己的固定形态,正如福柯所说,像沙滩上的人脸那样容易变形、消失。佛学与后现代主义一样都是在对主体的否弃中克服自我的封闭性、僵化性,从而使主体的形象跃动起来,并为主体拓展出无限的发展空间。可以这样说,不管是后现代主义,还是佛学,其所否弃的都不过是那种自我封闭的、有限的、作为认识中心的、实体性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其所产生的根源乃是对象化的思维方式。
佛学主体的否定性首先表现在对主体固定本质与形象的否定。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大景观。维特根斯坦早年追随罗素,探索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哲学的新出路。他和罗素一起所做的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寻求科学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对哲学命题进行语言分析,但他们并未能真正地寻找到一种使命题表达变得科学的有效方式。这是不是说维特根斯坦和他的老师罗素所做的工作完全是无意义的呢?绝非如此。他们虽未实现自己的初衷,但他们成功地发现了“科学”地表述真理的不可能性。于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了断裂。后期维特根斯坦从追求严密、科学的表述走向了语言游戏论,走向了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道路。语言游戏论是多元真理观以及后现代主义其他理论的前奏。当本质被抛弃以后,主体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空壳”,成了一个虚无。于是存在的本质就成了主体要去建构的东西,这给予主体极大的创造自我或者说是自我创造的自由,也给了主体以不堪忍受的自由的重负。萨特就声称人要负起自己自由的责任。而后现代主义给了人们更加沉重的自由的重负,正如费耶阿本德所主张的那样,“怎么都行”。当外界、当社会不再给人任何道德戒律的束缚,不再给人的道德处境提供必然性的答案,人们不得不自己为自己的行为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由于人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在后现代主义中,主体更是丧失了总体性、统一性和中心地位,变成了一个去中心的碎片化的东西,从此,主体也不再有明确的身份。
佛学中的主体也同样没有固定的形象,没有固定的本质。佛学称之为“无相”。这里的“无相”同样不能理解为没有任何形象,因为在佛学看来这有执着于“空”的倾向,是一种有违正法的“边见”,是“恶取空”,所以,把“无相”理解为没有什么固定形象更为合适。没有固定形象的东西也很难用语言来表述,所以大乘佛教在主张无相的同时,也主张“离言”。佛性论是佛学探讨主体的重要领域。但无论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都认为万事万物包括人并不存在什么“性”也就是本质。小乘佛教讲无常、无我,大乘佛教则明确讲万物皆空,“无自性”。对万事无常、无我、无自性的认识就是对主体性的否定。即使是大乘佛教的佛性论,其中很重要的认识还是认为佛性为空:
佛性者名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智慧,所言空者不见空与不空……中道者名为佛性。(7)《大正藏》卷一二,第523页,转引自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众生佛性犹如虚空,虚空者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内非外。(8)《大正藏》卷一二,第568页,转引自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这里正如赖永海先生所说的那样,“一方面,它大大淡化了部派佛教的‘补特伽罗’说以及如来藏说的‘神我’色彩,另一方面,又沟通与扫相绝言之般若学的联系,——实际上,以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之‘第一义空’释佛性,完全是般若学之有无相即之中道观在涅槃学上的体现。”(9)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涅槃学对佛性的探讨,其总的倾向仍然是认为佛性的真谛是“第一义空”,也就是非有非无,非空非不空的。作为一个自我相异之物的主体,使得人们很难认清它的面目,或者干脆说它的面貌是不可认识的。佛学的中道观主张,佛性总是逸出自身,变成另外的东西,并且它是由缘起作基础。这使得佛学中的主体说也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相似,没有自足性、统一性和中心性,也没有自主性。
在临济宗那里,非有非无的佛学中道观体现在“无位真人”的提法之中。《临济语录》记载:“上堂,云: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入,未证据者看看。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位真人?师下禅床把住云:道、道,其僧拟议,师托开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便归方丈。”(10)雪窦重显法师、圆悟克勤法师:《碧岩录》,王诚、陈树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无位真人”这种说法被视为临济宗的思想精髓。“无位真人”也就是自性,是佛性,是人活泼泼的当下生活。只不过这种人生是完全自然随缘的,它没有造作,不落阶级果位,因此也不受任何事物或观念的束缚,所以是完全自由的。义玄曾对弟子们这样说:“你若欲得生死去住,脱著自由,即今识取听法的人,无形无相,无根无本,无住处,活泼泼的,应是万种施设,用处只是无处。”(11)(唐)《慧然集·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见《大正藏》,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版,第47册,第498页。“无位真人”无形无相,无根无本,所以也没有任何系缚,完全像《庄子》中所向往、所描述的“不系之舟”。“不系之舟”比喻没有任何羁绊的自由状态。义玄使用的“活泼泼”一词体现了义玄对僵死概念的拒斥。有句俗语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这是因为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用朱熹的话说,带有“万紫千红”的特点。同一概念及内容不断更新,社会生活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临济宗的棒喝中就体现着一种对传统讲法方式的突破,体现着一种不拘格套的自由精神。当有人拟用语言定义“无位真人”时,义玄怒喝:“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言下之意就是“无位真人”没有具体形象。它“无根无本”,也不是由人和他物所决定的。“无位真人”事实上什么也不是。这样就避免了佛学所谓的偏见、边见。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佛学对基础主义的反对态度。
义玄从“无位真人”又引出“无依道人”的概念。“无依道人”也作“无衣道人”。它与“无位真人”所指是相同的,都体现着“主体” 的否定性。“无依道人”就是无所依凭,不依靠应机教化时运用的种种方便,不依靠佛祖,不依靠幻想中的绝对洁净的极乐世界,也不依靠语言文字。一句话,“无依道人”是不依靠任何外物的内在之我。因为依靠他物就会受制于他物,就无法自己做自己的主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义玄提出一个与佛陀提倡的三皈依不同、在常人看来颇有点惊世骇俗的主张:“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他让人们不但不尊重任何成见,甚至也无需拜伏在佛、菩萨、禅宗祖师的脚下。这事实上是叫人们不要被他们的教法、理论限制了自己的头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思想上真正的思维自由。由于中国佛学是承接印度佛学而来,义玄的“无位真人”或“无依道人”也有着佛学史上的依据。作为禅宗思想重要来源的《金刚经》中就有一句名言,传说六祖慧能就是听人讲到这样一句话而灵机触发获得觉悟的:“菩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义玄继承发挥的就是佛学史上的“无住”思想。他说佛“常在世间”,但“不染世间法”,也就是不会被现实生活中的是非、善恶所困扰。他认为,人们要获得解脱,“莫随万物”,就是不为客观世界的必然法则所左右。佛的认识并不脱离现实世界,不是脱离日常生活的现象,而就是源自现实生活本身。佛与迷人的不同只在于,佛从不被世间万象所染污,对世间之物无所染着。不执着是“做佛”的必要条件。因此,人们要想获得解脱,成佛做祖,就应当效仿他们的精神,让自己的意识、观念符合佛教的不执着精神。在《庄子·逍遥游》中我们可以对应地寻找到和义玄相似的观点: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未数数然也。
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2)庄周:《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
在庄子看来,御风而行的列子虽然有相当的自由度,但还是有所依凭,只有顺应自然,完全达到“恶乎待”,并消灭自己的主体性即“无己”才可称其为至人。
总的来说,义玄的“无位真人”或“无依道人”和庄子所描述的“恶乎待”“无己”的至人都是达到了完全自由之境的人,他们也都是否弃了自身一切的人,他们否弃了佛、方便、语言,否弃了功、名和己身。通观《庄子》一书,论及“死”的地方约有180处。庄子对于死的态度是豁达的。他认为,思想境界合乎道的所谓“真人”,对生死没有执着之心,而是随顺自然。他不会因为活着而留恋生命,也不会因为畏惧而厌恶死亡。其对于死亡的态度与其说是厌恶、恐惧,不如说是悦纳。庄子甚至把死亡称作休息。他认为死亡对于人来说是“大块”带给人的一种“休息”。庄子的“近死”之心,就是对万事万物不取不着之心,也就是不依靠任何外物的自由之心。庄子也好,义玄也好,其宗旨都是无别的。从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于人、主体的看法也就容易理解了。消解主体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内容。福柯声称“主体已死”,德里达倡言“人已终结”,巴特尔宣告“作者之死”,等等。当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之后,紧接着的是人、人的主体性也跟着走向了黄昏,走到了尽头。应当明确的是,后现代主义所宣称的“人之死”、“主体” 的死亡,等等,其所终结的是旧的价值理念的“死亡”,而不是什么肉体上的、事实上的死亡。破除旧的价值理念为重树人的全新形象扫清了道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是在其能动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现的;抽象的理性自由显然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自由是人的实践的自由。义玄的无所执滞只能是纯精神方面的,无助于解决任何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因为仅凭思维和想象连一根稻草也举不动。此外,人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从现实、实践出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这也是马克思终结传统的意识哲学后得出的基本结论。而义玄的“无位真人”或“无依道人”则有脱离现实生活、脱离实践的倾向。这也是许多佛教宗派共有的不足之处。不过,这只是义玄思想的一个方面,他也曾这样说,佛法并不是远离人间,它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具体说就是“著衣吃饭,困来即卧”,离开了这些进行的所谓宗教修行不过是“痴顽汉”的认识和做法。这里,义玄的思想又显露出与个人日常生活相结合的倾向。
总的来说,禅学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思想不仅仅在风格等外在形式上,而且在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伦理思想、主体观等具体内容上都显示出相似或相近的认识与结论,显示出一定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在主体观方面,后现代主义对主体采用的是解构的态度,而中国禅学对主体观采取的是否弃的态度,这也符合佛教的基本观点或者说对世界的根本看法——空论。但无论是后现代主义思想还是中国禅学思想,都无法完全把主体这一思想从自己的观念中完全驱逐出去。他们放逐主体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主体之后充分而自由的发展。
但是,主体是无法彻底从哲学中被驱离的。就像水中按葫芦,主体的每一次被否弃或解构,不但不能使主体彻底消失,结果都使其得以以全新的形象复归。
后现代主义认为,文本的原意是不存在的东西,“文本”会不断被解构。由于原意是一个“踪迹”,它的缺场使得人们不得不为它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替代品。对于禅学中的主体来说,它的宿命就是被否弃,但人们也为它寻找到了如此之多的替代品,如羯磨、佛性、如来藏、阿赖耶识、真神、法身等概念,主体也通过许多诸如此类的概念一次又一次地得以复活。
在禅学主体的替补与复活过程中,也同时印证了“解构”的“踪迹”。在禅学中我们看到,禅学否弃了统一的、确定的主体形象,否定了恒常不变的主体存在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主体沦为没有确定身份的流浪者。但主体是难以被彻底打压的,因为完整的哲学或禅学体系没有了它总是有缺憾的,所以主体不断被否弃,但总是一次又一次顽强地使自己重新浮出水面;一次又一次被放逐,但禅学与哲学王国又总是到处留下它若隐若现的“踪迹”。主体被驱除以后,所留下的空隙如此之大,以致禅学和哲学家们不得不经常重新找寻它的替代品,甚至于直接使已被他们宣布死刑的主体起死回生。所以,在佛陀用缘起论、三科法门以及三法印揭穿了“我”、揭穿了所谓的主体的假面之后,在中国禅学史上又出现了真我、真人之类的主体的替代物或者是新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