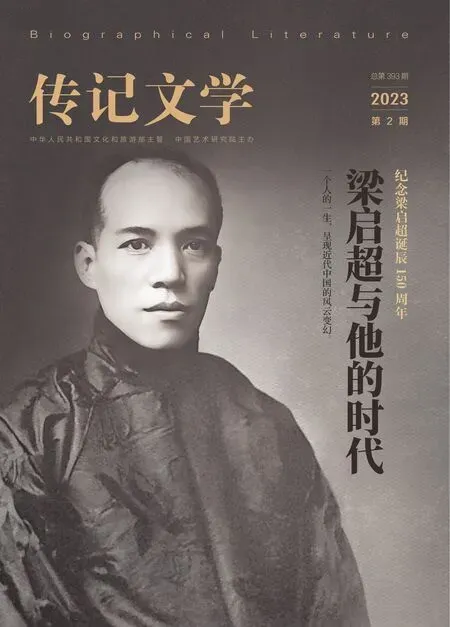我与闻黎明先生的学术交往
李光荣
闻黎明先生是我认识较早、交往时间较长的著名学者之一。我和他相差近十岁,沟通起来却没有障碍。这缘于我们对西南联大及闻一多的研究和崇敬,当然,也与性格有关,他那种平易近人、坦荡纯洁、真诚友爱、关心他人、乐于助人的品格恐怕是任何人都能接受的。我与他的交往是纯学术的,没有掺杂别的任何东西,说我俩的关系亦师亦友,并不是一句套话。
几件往事
我与闻黎明先生有三十多年的交往,他住在北京,我住在西南,见面的间隔时短时长,总的来说并不算多,系心灵相通型。由于研究的对象一致,思想越来越趋同,及至后来做共同的课题,见面就越来越多。这里摘几件事说说。
我俩相识于1988年。那年11月,云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云南师大)举行50周年校庆。云南师大是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独立而发展起来的,校庆日也是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纪念日。纪念的一个内容是举行学术研讨会。我从当时供职的蒙自师范专科学校去参会。闻黎明先生则刚从蒙自考察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回来,在会上介绍西南联大在蒙自的情况。那时,蒙自的哥胪士洋行正作为西南联大遗址筹划开放,南湖里新建起了闻一多纪念亭和纪念碑石。听得出,他对于蒙自纪念西南联大和闻一多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举措较为满意。我感觉他这次来昆明的一个意图是追寻闻一多的足迹,而我则在蒙自寻找西南联大情况多年。会下我向他作自我介绍,他颇感亲切,便约细谈。当晚,我去他的房间,他向我了解西南联大在蒙自的详细情况,我向他请教研究选题问题。说到学术研究,他的话滔滔不绝。我告诉他在蒙自艰难追寻西南联大踪迹的所得,及得不到完整材料的困境,以为他会推荐鼓励我继续走下去,然而没有。他主张我研究楚图南,认为研究者不多,而在云南占有“地利”,容易做好。后来想想,这是因为当时西南联大研究还没兴起,材料奇缺,研究条件不具备,他正在做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还没面世,闻一多研究的条件也不成熟,不易出成果;而主张研究云南名人,出于他的历史学背景,也考虑到研究基础问题。我们谈得很畅快,不觉已近深夜一点,我才离开。那时,他正当年,我还年轻,第二天照常开会。
从2003年起,我除了讲课和开会外,白天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了。一天,我在老旧报刊室看报,转身去换报纸,却看到闻黎明先生在埋头阅读,走近轻声喊他,他抬头见我,很是惊讶,便相约走到室外,到天井边。我告诉他我申请到一个西南联大的国家课题,为此天天来查找资料。他则是为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专程来昆明查找资料。我们简单交流了情况。为抓紧时间看报,我约他晚上边吃饭边聊。傍晚相见,问他喜欢吃什么,他说在这儿当然要吃米线啰。到了桥香园,他争着买票,我说“这是尽地主之谊”,他说“咱俩谁是这儿的‘地主’都难说呢”!对呀,他家曾是昆明人,比我进昆明早得多。我买票选离演出舞台稍远的“台厅”坐下,去服务台以票抽奖居然中了,他高兴地说“这是趣事”。汤碗上来,他不放腰果,说“这不是本来有的”。吃时碗里一点红色都没有,他却被辣得满头大汗,我纳闷,他说“是胡椒辣”,我才知道胡椒有这么大的力量。一会儿歌舞演出开始,我们几乎听不清对方的声音,只好不谈。他对民族歌舞看得津津有味。吃完后一起走回云南师大,他去专家楼整理白天拍摄的报纸照片。
后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增多,有时在昆明,有时在武汉、黄冈,还有一次是在日本。2007年11月,云南师大在昆明举办“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真是学者云集,大咖相会,有来自日本的学者小林基起、杉本达夫、斋藤泰治等,有郭建荣、梁吉生等老一辈学者,还有许纪霖、雷颐、杨奎松等文史名家,不言而喻,日本学者和史学名家是闻黎明先生请来的。这些人的出席为会议增加了学术分量,他们的发言激起了会场的热情,还形成了现场讨论。这次会间,他忙于陪客人,我俩没多聊。在武汉、黄冈召开的闻一多学术研讨会上,我俩几次见面,每次都谈得很愉快。2019年11月在黄冈,他总被一些学者或学生围着,我想年轻人比我更需要他的指点,便没去抢机会。在从浠水回黄冈的汽车上才与他谈《国立西南联大史料长编》(以下简称《史料长编》)的选题问题,由于该书的收集策略有变,我还是没有敲定选题。后来在昆明开会,一天中午,我俩和徐思彦编辑一起,才确定为编文论集。日本见面仅有一次,是在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受樱美林大学之邀,在日本工作几年了,对东京相当熟悉。国内去的代表多不懂日语,他一直陪大家开会和参观,为大家照相,他是会上最忙的人。
2016年11月,《史料长编》的编辑工作启动,我在他的主持下工作,与他相聚的时候多起来了。2018年7月申报关于西南联大史料收集整理的国家重大项目开始以来,我们的联系更为紧密,他是首席专家,我全力支持他。课题申报下来后,我负责一个子课题。为了这两个项目,我们每年都开会相聚,近两年若不是疫情阻挠,相聚会更多一些。
2018年11月1日,“西南联大研究文库”在云南师大呈贡校区举行新书发布会,我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与他主持的第一批史料书在会上亮相,我俩参加了发布会,接着参加西南联大学术研讨会,再到龙泉街道参加闻一多公园奠基典礼。这期间他是核心人物,很忙,但还是抽时间介绍西南联大后代与我认识或联系。
2020年,我去昆明出席项目检查工作会,和他同住云南师大专家楼。路上碰到芭蕉,一般人喜吃香蕉,却不知芭蕉更好吃,想居住在北京的他也可能如此,就顺便买一柄送他。谈完工作离开时,他竟然要我“带走”。我有些惊愕:我俩交往已三十多年,同桌吃工作餐也多次了,他竟还如此认真!也许在他看来,这会打破我们学术交往的纯洁吧。但这不值几个钱,我一边说“下不为例”,一边走出了门。

本文作者与闻黎明先生(右)在学术会议期间合影
他近些年多次做手术,越来越消瘦,走路有点“打飘”,我暗自痛心,又不便明言。2021年3月,我俩走在路上,他的脚步没以前快了。我忍不住说“您家有长寿基因哦”,意在鼓励他。其实,说这话显得稚拙。因为他的家谱、闻一多先生的原话,他自然比我清楚。但我真不知道怎样劝慰他。
最后一次见他是2021年12月25日在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会的换届会议上,那是线上见面,他一如既往快乐地笑着。由于任期已满,他从副会长任上退下,做了学术委员会成员,我也不再担任理事,忝列于学术委员会中,心想来年4月的闻一多学术研讨会上还可以再见。选举后他立即提出:此群保留,作为工作群使用,可知他对闻一多研究的诚挚期望。
我是很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因此与闻黎明先生的联系由稀疏到密集,再到节制,起初是书信,后来是邮件,再后是微信,其间贯穿着电话。尽管用电话、微信联系很方便,还是能不扰他则不主动联系。对此,他有些不满,曾批评我不在微信群里提出问题讨论。但他不明白这是我能做的对他身体健康的爱护。
没想到2022年的第三日,他就撒手人寰,年仅71 岁!如今,我确实有一大堆问题,却没法跟他求教讨论了……
为研究西南联大走在一起
闻黎明先生学历史出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攻近现代思想史;我学的是中文,先后在蒙自、昆明、成都的大学任教,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俩学科不同,研究方向相异,工作地点也相去甚远,本不可能在一起共事,却因热爱西南联大,有研究西南联大的共同志向而走到一起。
而且,我俩的学术道路都有些相似:由闻一多而西南联大。
作为闻一多先生的孙子,面对闻一多先生事迹不清的状况,他做出了编写年谱长编的计划,并于1985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列为科研项目,历经五年而完成,再于1994年7月出版发行。这是以一己之力完成的一项学术大工程,它不仅是闻一多研究者的案头书,也是研究中国现代史包括教育史及西南联大的重要参考书,由于史料的周全客观,出版后誉满学界。他接着写出了《闻一多传》等专著,卓然而为闻一多研究的大家。闻一多先生的晚年与西南联大紧密相连。研究闻一多便会了解到西南联大的部分历史,就会被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品格吸引,自然进入西南联大研究。他在《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后记”中说:“《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传》出版后,我的兴趣便转移到西南联大研究上了。”正是这一顺理成章的脉络。
我的西南联大研究胚胎于云南师大,我的老师中有几位是西南联大的助教和学生,我们班的卫生区域是以闻一多衣冠冢为核心的烈士陵园,每周打扫。毕业后我工作的蒙自,正是1938年西南联大文、法商学院所在地,在那里我开始搜集西南联大的资料并研究,研究方向与选题后来得到樊骏和钱理群先生的支持。为了研究西南联大,我经过多方努力于1996年调回云南师大中文系任教。有趣的是,我选择闻一多为切入点研究西南联大文学,这就进入了闻黎明先生的“领地”,于是加强了与他的联系。由于获得国家课题,我投入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研究,闻一多研究的成果仅作为论文呈献。结题后出版了《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西南联大与中国校园文学》《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等著作,算是进入了西南联大研究的队列。
就这样,闻黎明先生从历史学出发,我从文学出发,经过闻一多研究而进入西南联大研究,走到一起了。
在完成涵括西南联大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第三种力量”和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西南联大的抗战轨迹”研究后,闻黎明先生酝酿着一个更大项目:全面收集整理西南联大史料并进行研究,为此拟将西南联大研究的队伍组织起来。
2016年,我与他在武汉相见,他告诉我计划编辑《史料长编》,说正在积极推进这项工作,要我安排好自己的研究,准备承担任务。会后,他赴昆明,在云南师大的支持下,组织了编委会,确定了各分卷名称,邀请了部分作者,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落实了第一批集子的编辑,工作效率相当高。他在11月27日的邮件中告诉我:“这件事,我最初只是想由西南联大研究所出面编辑,现在学校把它上升为工程,准备申请国家重大项目……总之,学校这次下了决心,不论这件事最后能做到什么地步,终究会产生一批成果,然后我们再逐渐将它完善。”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是一项西南联大研究的基础性大工程,只有他才推得动,也只有他才能主持;但我又感到他的书生气,他对高校教师的工作特点不太了解,对工作过分理想化,难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
之后,他与我频频通信,讨论《史料长编》的编辑体例、选题、编者等问题,交流编辑工作进展的情况,并敦促我着手相关选题的编辑。
2017年4月14日,他给我来邮件:“你承担的西南联大史料编辑,不知进展如何,很是挂念。师大希望明年纪念西南联大在昆成立80周年前推出一批成果,你的大作在内定之列,时间紧迫,如有什么为难处,望及时告知。出版方面,社科文献出版社已表示乐意接受,师大提供出版资助应无问题,兄可放心。”收到来信,我感到他对我的殷切希望,可我现在已无法抽出手来编辑史料了,遂及时告诉他:“您原说春节前有商讨,后来没有,我就松懈了。春节后,云南师大饶书记委托副书记张玮等与我见面,他们当时也没说《史料长编》事,而要我为校庆出两种书,我答应了。……事已至此,请您原谅!”他立即回复:“(书)如果是资料编辑,仍可入长编。”我答:“一是著作增订,二是作品选编。”后来,著作增订出版了,作品选因故没有编成。
那时,他在日本樱美林大学做客座教授,有专门的研究课题,还要分出精力来抓《史料长编》事宜,真是够费心的。之后,他在昆明召开过几次《史料长编》编委会,我都参加了。但我忙于手里的国家课题结题,实在没时间编辑史料,没报选题。待手里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和他与《史料长编》责编徐思彦老师一起讨论了一个选题,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着手编辑。此是后话。
云南师大80周年校庆后,国家社科办公布当年重大项目选题,云南师大设计的“西南联大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在列。云南师大请他主持申报,他拉我做子课题负责人,我俩便投入这项工作之中。申报成功,《史料长编》在一定程度上并入了其中。
闻黎明先生为什么会投入西南联大研究呢?还是在2016年11月27日的邮件中,他说:“你曾说把自己献给西南联大了。我也是这样。每次我走进师大,看见家祖的塑像和衣冠冢,都感觉自己应该融化到这所学校里。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感情,我才愿意接受师大的邀请,参加这项工程。”他有心理情结,我有学历渊源,这是我俩走在一起的深刻原因。
一项未了工作
记不清什么时候,应该是在2000年之前,我向闻黎明先生谈到将写“闻一多的后十年”,把闻一多的单一形象扭转一下。八九十年代,闻一多被塑造成一个横眉怒目的形象,而我理解的闻一多,是丰富亲切、具有诗人的情愫和浪漫的情调、多才多艺的,当然还有学者的严谨丰厚。闻黎明先生听后表示认同,鼓励我多方收集材料,深入思考后再动笔。当然,那时候只是一种想法,提出来征求他的意见,真要去做,还有漫长的路。
研究闻一多必读《闻一多年谱长编》,可此书出版后很快售罄。不得已,我写信给闻黎明先生,希望得到一本。结果他自己手头也没有。后来在孙党伯老师的帮助下,我才买到《闻一多全集》和《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收集了那么多的材料,既给读者带来方便,又给研究者带来望洋兴叹之感。经过认真地阅读思考,我便选定闻一多的思想性格进行研究,并且获得了初步成果。
2003年,我又写信给闻黎明先生,向他报告我的研究情况,并希望他给予指导。他在当年6月24日的回信中说:“《闻一多的后十年》计划,感觉很好……对一切宣传、研究闻一多的工作,我们从来都愿意积极帮助。”信中让我研究方面请教余嘉华老师,资料方面去云南师大图书馆和省图书馆,还告我他的电子信箱,“希望我们在网上联系”。
大约2005年春,我俩偶然在图书馆相遇,他说,前年申请到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课题“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心”后专程来昆明,得到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计划把有关史料再细查一遍。我见他用相机公开拍摄,而我以抄录为主,拍摄总有些遮掩,很是羡慕。休息时谈资料收集与研究工作,他说,1998年《闻一多年谱长编》一书被北京大学列为古今中外60 部必读和选读书目之中,颇感意外,也说明史料工作在学术研究中地位的重要。他说时略有骄傲状。是啊,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五年初稿,之后再“加工”,十年面世,费去多少心血,好评不断是实至名归。不识相的我,却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书中有一些错误。他不仅没有不悦,还虚心地承认了。他似乎早已知道,正在等待修订的机会。后来得知,书稿完成后他在不停地收集资料,包括这次的彻底细查,其中一个目的也是为修订作准备。他白天拍摄,晚上整理,十分辛苦,面有疲惫状。但机会难得,我还是请他为研究生讲一次课,并说没有报酬,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俩把讲题商定为“谈《闻一多年谱长编》的编撰”,讲座为听者开阔了学术眼光,反响良好。后来的历史证明,“年谱长编”一类书出版盛行,是闻黎明先生开的头,可见《闻一多年谱长编》影响很大。

2017年11月,本文作者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学术发言
由于资料不足和对一些问题认识不到位,我的《闻一多的后十年》未能动笔。我决定先写文章发表,以慢慢积累和逐渐深入。我从闻一多的戏剧工作这一学界极少学者关注的内容入手,自2001年开始发表系列文章,梳理闻一多的戏剧活动,讨论他的戏剧创作,评价他的艺术贡献。其间,与闻黎明先生互通过一些书信,讨论研究情况。
2009年,我去武汉参加闻一多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得到许多收获,尤其是和孙玉石老师作了深入的交谈,获益颇多。从交谈中知道“数据库”这种资料贮存软件,回来后积极促进西南民大图书馆购买,以解决获取资料问题。会上,闻黎明先生被选为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我被选为理事,但没见他本人出席会议,心里有些失落。
2016年,我俩又在闻一多研究会上相见,很是高兴,便约定当晚交谈。可他谈客盈门,很晚才轮到我。我向他报告近些年闻一多研究资料的收集情况和对闻一多的思想认识,也谈及我的困惑,当说到《闻一多的后十年》的思想主线还没有找到时,他想了一下,接着我俩一齐说出三个字:“人民性。”说罢,我俩哈哈大笑。那情那景,永难忘怀!这说明我俩对闻一多的认识有了一致的思想,我当然感到由衷畅快。但我接着说,“人民性”是政治概念,不能完全概括闻一多,也不是我想写的闻一多,没有最终与他达成完全的一致。
日本闻一多研究会拟于2017年11月在早稻田大学召开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闻黎明先生将会议邀请函发给我,并说会议为我提供全部费用,希望我出席。我没单独出过国,他还来信指导我怎么办理手续。到了日本,我才知道,以这种规格从国内邀请的都是陈国恩、商金林、陈平原这样的闻一多研究名家,此外就是单位代表,只有我是断断续续发过一些文章的研究者。邀请人员肯定是闻黎明先生推荐的。我明白这是他对我在闻一多文学与戏剧及后期思想方面所做研究的抬爱,在感激的同时心生惭愧,暗自下决心努力做去。
这时,我要完成另一个国家项目“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编年索引与综合研究”的结项,他呢,研究重心转向了《史料长编》工作,次年我和他共同投入了国家重大项目“西南联大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的申报与研究,关于闻一多的交谈少了。但我从未放下对闻一多的思考,他也相信我不会放弃闻一多研究。闻黎明先生离世后,王立老师说,去年闻先生还告诉他,李光荣在四处搜集闻一多研究资料。这是一种深刻的理解、一种心照不宣的信任。多年来,他不间断地向我发送《闻一多研究动态》,也包涵着对我的期望和鼓励吧?
2021年年底,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会换届,我和闻黎明先生都成了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这又促进了我对闻一多研究的思考,我再次把自己的研究计划作了排序,并想到:《闻一多的后十年》书成后,定要请闻黎明先生作序。这是我从没对他说过的话,因为我相信他不会推辞。
未竟的事业
由于《史料长编》启动时我无所作为,心里过意不去,当另一项工作出现的时候,我便大力支持了闻黎明先生。这就是国家重大项目“西南联大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的申报。我俩的微信记录下了我与他的工作情况。对于这项国家重大项目,他经历了不同意、不参与到不主持申报,最终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工作的转变过程。
闻黎明先生曾在2016年11月27日的邮件中告诉我云南师大准备以“史料”为题申报国家重大项目,2018年7月国家社科办公布招标选题,我就与他用微信聊上了。9日,我问他:“国家重大招标项目第166 号是您推荐的选题吗?”他说:“估计是云南省社科办何主任推荐的。他说今年是西南联大80周年纪念,趁着这个机会容易批准,而且通过饶书记找到我,饶书记很积极,可我没接受,说等我们的成果出来一些再说,现在申报也缺乏学术实力。”他接着打听后告知:“是云南师大科研处报的。”我告诉他:“不瞒您说,选题一公布,我校科研处老师就通知我准备申报。我说:‘估计是闻黎明老师提出的选题,他正在做这事,我也是他的一员,不便抢报;我先了解一下题目推荐情况再答复。所以,我希望您申报并愿意支持您。如果您不报,我有可能从命去竞争。’”他回复说:“这样吧,你出面申报,事还是那些,由我和大家来做。我不图什么重大不重大,和我没关系,我已经退休了。我只想做有价值有意义、能成为文化遗产的事。”过会儿,他又说:“学校要找我谈,动员我出来。”我说:“好呀,请您勿推辞!”
11日,闻黎明先生又来微信:“邹院长来电话,说师大书记校长上午找他谈话,要我挑头申报,看来躲也躲不开了。他们现在就着手标书,我打算17 号去昆明,按长编下设11个子课题的设计,社科重大也得成立至少5 个子课题,其中文学活动请你全面主持,切勿推辞,你还愿意承担哪些部分,亦请速告。”我回:“好的。‘文学活动’我当仁不让,遵命力行。艺术活动也是我的专项。我平时关注的还有办学历史和抗日行为等。”我还建议他:“子课题的设计要打破原来的11 个分支,按照国家社科的分类去设计,如‘学术研究’分散在各学科而不宜单列,‘艺术活动’也可以纳入文学称‘文艺活动’,有的只能合并或舍弃,待申报下来再作调整或纳入。”
12日,我俩继续讨论项目申报的事,他说:“文学艺术列一个子课题,都交给你,怎样?其他课题你也可以参加,但子课题负责人规定只能主持一项。”我表示:“如果文学艺术子课题由我负责能够确定,我就要落实课题组成员了。”
13日,他发我标书,要求我填写。我说:“‘文学艺术’子课题论证书我会写的。但要在了解整体设计的前提下填写,否则,各个子课题各吹各打不统一,会出问题的。”
18日,他给我发来微信:“招标表填写得怎样了?……这次请了两位拿到过社科重大课题的专家,一位是我们所所长王建朗,一位是中山大学的桑兵,论证会时间要看他们什么时候方便,一俟确定马上告诉你。论证会后,还要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标书,争取8月中旬定下来。”我的回信是:“子课题我要在了解总体计划的前提下才能填写,所以您拿出总体论证后告我,我根据您的计划填写。我已组织了课题小组。”
31日,他给我微信,说“项目申报会商会”定于8月7日举行,还写上了“敬请出席指导”几字,十分客气。
8月5日,他通知我:“7 号上午主要是请桑兵、王建朗、李世愉、李光荣、何飞、徐思彦介绍重大课题申报经验,下午研究申报书具体事项。”
6日,我俩通电话并在微信上即时交流,围绕子课题的设置及其负责人进行了讨论。
7日下午,项目申报组在上午会议宏观交流的思想基础上确定子课题及其负责人,并讨论了相关问题。让我负责“学人著述”。
8日,我开始考虑填写子项目申报书。我很不适应这种“倒着做”的方式,不了解总课题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对于子课题的要求,还是硬着头皮去想,支持他的申报工作。
10日,我给他微信:“我现在碰到一个棘手的分类问题:‘学人著述’与‘报刊资料’是包含关系。我爱人宣淑君曾在图书馆工作。她来昆明了,我问她,她说只能按文献的载体形式划分才能分清。她提供了图书馆馆藏文献分类法:1.图书;2.杂志;3.报纸;4.音像资料;5.数据库。我们无音像资料,但多了档案,有数据库,把杂志和报纸合在一起也是可以的,但著述只能叫图书。……图书指册书。‘学人著述’可改称‘图书’——子课题名为西南联大档案文献汇编、西南联大图书文献汇编、西南联大报刊文献汇编。‘文献’与总课题名重复没关系。其实‘资料’二字也在总课题题名上的。恭候回复。”他读后马上回答:“很好,你转给邹建达,这部分他负责。”这则微信决定了我们最后申报的子课题名称。
11月7日,我转发“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最终名单”给他,他说:“心有余悸呀,目标那么高,规模那么大,做不好怎么办!”我说:“肯定能做好。”
他回国后,我俩见面谈话多了,微信往来减少了:一是考虑到他忙,多用电话联系;二是他身体不好,尽量少打搅他。
但正在课题组成员齐心协力争分夺秒攻关、需要他掌舵的时候,他辞世了。我们课题组成员对他何等难舍啊……
如今我们纪念闻黎明先生,而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完成他的未竟之业,认真努力,按照他提出的要求,高质量地完成国家重大项目的结项及其后续研究,为西南联大的研究贡献力量,把西南联大的文化传播开去,使其在中国文化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