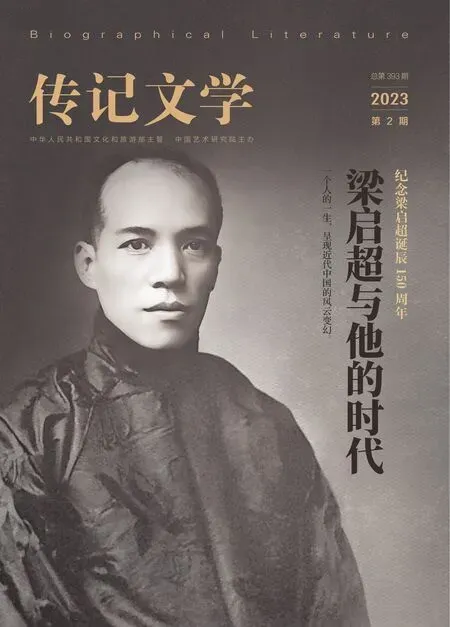文学选择了我
周瑄璞
一
我出生于河南农村,父亲在西安工作。两三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了西安,我在家乡跟祖父祖母长到9 岁半,转学到西安跟随父母生活,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留守儿童”。整个70年代,我在乡村度过,伴随耳畔的祖母的故事、歌谣算是我的文学启蒙吧。当然,或许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因素,让我天然地走向文学的怀抱。

一个乡下孩子初到西安,与父母很有隔膜,颇为陌生,不愿与他们交流,外部世界所有一切在自己内心聚集酝酿,这或许是我写作后迷恋心理描写的原因?总觉得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真正的情感,而外部,总有这样那样的虚假和不可靠。小小的孩子已经觉得自己很大,好像什么都知道,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认知。有一次在课堂走神,看着窗外想,十一二岁真的是人生最好的时候,能看到和感受这个世界,懂得了一些事情,又没有太多具体的烦恼和压力,要是一直这么大就好了。当时,我们姐妹几个没有城市户口,在那个一切凭粮本的80年代,吃高价粮,生活很困难。我能明显感到与班上同学的物质差距,内心非常自卑。他们都是父母双职工,而我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干临时工,挣得虽然不比他们少,但老家的哥哥和各种亲人需要接济,我父亲时常欠着同事的钱,这个月发了工资,还上个月的。敏感如我,觉得别人看我们的眼光不太一样,这或许就是海明威解释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原因吧——“源于童年的自卑”。这种心理落差应该是造就一个人爱好文学的强大动力,因为在那个文学世界里,有你内心所需要的一切,有各种各样的人物陪伴着你。当然,也得益于我父亲爱好阅读,家里常年订有《小说月报》《八小时以外》《儿童时代》《少年文艺》《陕西少年》《中国少年报》。直到现在我都很奇怪,在当时经济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父亲竟然花钱买书订刊,从不吝啬。家里刊物和书籍挺多,小伙伴和同学放学后常来我家阅读。前些年遇到一个小学同学,她说还能记起小时候在我家看书看到天快黑了,一个人背着书包匆忙回家的情景。
那时看过的《儿童时代》,有一个连环画《灯花》,故事很曲折,我每个月都盼望父亲从单位拿回杂志。韩伍老师画的灯花姑娘,美丽而一身正气,指头肚胖胖鼓鼓。还有一位画插图的陆秒坤老师,他的风格比较活泼,画的人都是中间大两头尖。他们曾经带给一个孩子丰富的阅读体验和内心世界。写到此处,我上网搜了他们的名字,得知陆秒坤老师已于20世纪末去世;而韩伍老师长得清清瘦瘦,可他画的人都是方方正正的呀。世界真是很奇妙。

大约三四岁,摄于西安市万寿路照相馆。父亲抱我走进去,坐在一个高凳子上,摄影师叔叔从黑布蒙着的大照相机里伸出头,手拿新疆人跳舞的铃铛环摇动逗我笑,扔向高处又接住,我咧嘴一笑,他手捏快门。
我还曾在《少年文艺》上读到一个重组家庭对待反叛调皮孩子的故事,是以孩子的第一人称写的,继父那么耐心地关爱和宽容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直到一家人相互接纳,其乐融融。那种微妙的情绪和稍微涉及成年男女情感的神秘,让我没来由地激动、紧张,一个人躲在蚊帐里哭。
现在人们提起80年代,我就想起我的儿童时代和青少年时期。那时的暑假好漫长,天黑得很晚,可以坐在门外小凳上长久地看书。而有一次语文考试的作文,我却得了零分,因为审错了题目。作文题目是《记一次观察》,我充满感情地写了老师带我们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参观过程,事后非常懊悔。
十二三岁时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起床都要呕吐,跑到院子里一根电线杆跟前去吐,也吐不出什么,就是头晕难受,有呕吐感。父亲带我去医院也查不出什么病因,吃没吃药也忘记了,随后这种症状自然消失。后来,我的侄子到了这个年龄,也是那样吐了一段时间。多年前,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是一种少年儿童容易出现的症状,原因不明,不用治疗,过了那个时期自己会好。生命历程真是挺神奇的,每个阶段都有风景和问题,好像从儿童向青少年过渡,必得有个什么仪式或纪念,犹如蝉和蛇的蜕皮,就像人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也会有一些病症来提醒你,它们是时间早已埋伏在那个路段耐心等待你的套餐打包项目。
二
中学之后,我的数理化成绩很差,到最后完全不懂,只对语文、地理这些科目感兴趣。当时大学还没有扩招,一个班也就是考上两三个人,我自然与大学无缘。待业两年之后参加工作,成为一名电车售票员。那6年的经历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记忆深刻。辛苦、狼狈、凌乱、愤懑,只想离开。有时候,在车上半天也不愿说一句话。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下班后去车棚取自行车,蓬头垢面,又累又饿又烦。车子摆放得很密,旁边一个自行车车把插进我的车把中,我的车子一时拉不出来,我抬脚就向它们踢去,所有的车子哗啦啦连着倒下。我拽起我的车子,推着骑上,扬长而去,一路流泪回家。那是我这个善良如羔羊的人此生唯一一次对这个世界进行攻击与伤害。
我想有一个文凭,以此摆脱在车上工作,能有机会进入机关,于是参加了自学考试。为了能够晚上上课,我三年里固定上头班车,每天5:40 出车。因为太早,大家都不爱上这个车次,轮到了很不高兴,便时有迟到现象,误了发车时间,而我固定下来,队长和同事们都皆大欢喜。幸好家住得近,我每天早上5 点起床,中午1 点下班,回家吃饭、收拾、睡觉,晚上7 点半赶到十几站远的城里(西安人把城墙以内叫作城里)西大街夜校上课。下课回到家10 点半,读书、看报,收拾完第二天的东西,就赶快睡觉。有一次,我被闹钟叫醒,睁眼一看,天已大亮,哎呀完了上班迟到啦!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这是下午。那几年的日子像是上足了发条,紧张而辛苦。现在回忆起来,年轻真好,身上总有一股奋斗的力量。
有一年元旦节日,减少早班车。我前一天没有去调度室看班,早上5:30 赶到单位才发现我那个车次调为八至四(当时公交车次分为早班、八至四、下午晚、延点),9 点多才出车。于是骑车回家,脱了外衣穿着毛衣毛裤继续睡觉。9 点起床,骑上车子就跑。到单位后,我脸上起了一片扁疙瘩,奇痒难忍,随后脖子、全身都有。这是从热被窝里出来冲了冷风,得了荨麻疹。从此变换季节、湿冷天气就会起一身疙瘩,尤其手指关节处,好像由骨头缝里钻出大量细小毒素,最是痒得恼人,直到十多年后,中药调理痊愈。
车厢则是一个社会窗口,每天上演节目,我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尝受诸多人情冷暖。正常乘客之外,还有逃票的、小偷、流氓、无赖。那时,小偷很多,每条线路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好像他们也分了地盘,总之我见到的都是固定熟面孔。穿得很好,有时买票,有时不买,我们也不敢招惹他们。因为有条线路上一个售票员小姑娘,是先进工作者,小偷下手时她提醒乘客注意,结果在晚班时候,她被小偷报复,用刀片划破脸。我们参加工作培训时,就说到这个案例,被告诫不要多管闲事。于是,我们学会了和小偷相安无事,在小小的车厢里各行其是,他们下车时零度眼光看我们一下,不屑?示威?感谢?拜拜?总之不知什么意思,而我们也会长长松一口气。有一次,我看到小偷盯着一个女孩身侧的小包,眼里燃起烈焰,仿佛生出了好多双手,恨不得扑上去一把夺来的感觉,可是车厢里人很少,他无法靠近,他被那欲望的烈火燃烧着,样子非常可怕。还有一次,在我关门的前半秒钟,一个男子跑上车来,紧握一个女式小包,靠在我的票台上。他的手还在颤抖,肯定是在这一站旁边的市场上偷来或抢来的,而包的主人,此时一定正在路边哭泣、呼喊,转眼之间她永远跟自己心爱的小包失散了。多年之后,我写此文的现在,那些小偷们也都老了,成为真正的社会渣滓,死活不知。还有一个60 岁左右的老头,身材修长,气度不凡,穿着讲究,夏天在车厢里,专门接近少男,紧贴到身后。彼时人们还不太懂这些事,小鲜肉们只是走开,尤其一些农村少年,面带惊异和恐慌地从他身边躲开。终于有一次,听到一个售票员说,那老家伙在他车上被人打了,口鼻流血,落荒而逃。后来,阅读茨威格的小说《情感的迷惘》,我想起这个可怜而讨厌的老头。总之,人生百态、社会千面,都在小小的车厢里上演。
当然,也有美好的一面。一对男女青年在站台上告别,姑娘上车来,脸儿绯红,目光迷离,她长得很美,戴着崭新的嫩黄色丝巾,折痕清晰可见。她陶醉在爱情之中,坐在那里,痴痴呆呆,我让她买票,喊了两声,她才回过神来。一个猥琐中年男,打破礼貌距离,靠在我座位旁边的栏杆上,随着车的晃动时不时碰到我的胳膊,我让他站远些,车厢里那么多地方呢,他依然不动,说他就要站在这里这是他的自由。我提高嗓门赶他走,打算报告司机,靠边停车,突然旁边站起一个中年人,一把将他推开,高声呵斥,那小子吓得吭也不吭,滚一边去了。我因为常年头班车,很多乘客也都是固定的,进站时候如果看到黑暗中有个身影在奔跑,我会一直开着车门等他(她)上来,于是得到他们的认可。有些姐姐和阿姨,最爱站在我身边,手握扶手,和我说一路话,还送我小礼物,给我介绍对象,给我写信。我去过一位阿姨家里,彼此来往了多年,她给我讲述她的人生经历,挺传奇的。她长得很美,写一手好字但腿有残疾,一个高知家庭的健全小伙子爱上了她,男方家想了很多办法,制造各种分离,怎么拆也拆不散。二人经历了几年的苦恋,最长的时候小伙子被派到外地工作,一年见不上面。二人顶着重重压力结婚生子,相爱相守。她儿子一路学霸,出国留学、定居。我调到出版社后,她还去找过我,送我一瓶国外生产的护肤品。前几年给我打过电话,这几年没有联系了,或许是跟着儿子定居国外了。我也被人送过诗歌情书,临下车,脸儿红红,放在我的票台上,匆忙走了。先后有几位男青年,专门等到我的车,上来站在身边,帮我递钱、递票、查票、维持秩序,到终点站下车,走到对面站上,等我们车调头发车,他又上来,即使我不理睬,依然热情地协助我工作。有一个小伙子,几个月风雨无阻陪我跑车,我还记得他打伞站在终点站眺望等待的样子,试图将联络延伸到车下,直到他看不到一点希望,从此消失。我那些年里一心想离开这个环境,所以不会对车厢里诞生的追求者感兴趣。
后来,我如愿考进机关,做了十年报纸编辑。到现在还偶尔做梦,我在拥挤的车厢里售票,手里握着票板,零钱多得抓不住也数不清,对票价不清楚,账算不到一起,或者回场交票款,找不到票房。
以上讲述难免琐碎,也并不是对创作产生什么深远影响的大事,但毕竟是我自己的足迹,现在看来,十分珍贵,我很愿意越过几十年时光,将它们打捞起来,作为纪念。
三
后来,我从车厢那样令人烦恼的工作环境到万人大企业的机关里工作,初始挺满意,再也不像在车上那样,必须踏着点上班,晚几分钟就是责任事故,机关8 点上班,9 点到也可以,甚至快10 点出现,也没人说你什么,只要不耽误工作。我负责编辑八开小报的一个版面,半个月出一期报纸。经常写点小文章,在报纸上发一发豆腐块。几年后,觉得人生这样平淡可不行,必要有所追求,好像有什么使命在召唤我,也是对文学真心热爱,我仍然编织着作家梦,于是尝试写作,发现自己有语言天赋,是当作家的料。同样一件小事,我记录下来就很生动、鲜活,可读性强,思绪流水般涌来,云里雾里的语言一写就是一大串,我告诉自己,应该珍惜上天赋予的这种能力。
我想要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总觉得有一个远方,在召唤我。我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幸福在彼岸,文学是船。”
陈忠实老师说,文学就是名利场。我们必须先认识到这个前提。所以,不是我选择了文学,我其实没有选择的权利,是文学眷顾我、选择我,给了我一点先天的才能,那我必须抓住这一点,使它无限放大。我一刻也不能懈怠,我要一直写下去。
多么卑微而渺茫,一个年近30的女人,已经有了孩子,同辈们以“美女作家”之名跃上文坛,闪闪发光,而我还是一个国营企业机关文员、文学爱好者、地方晚报通讯员,名字偶尔出现在报纸副刊角落,连文坛的边都没有摸着,只是远远地观望着。怀抱女儿的我突然醒悟了般,此生要以写作为志业。一个作家的力量,更多来自于内心,跟接触过什么人群、遇到什么契机没有太大或者必然的关系。你得先成为一粒种子而不是一块石头,自己要有发芽的先决条件。
世纪之交,孩子正小,我白天上班,晚上带着她写作。那时还没有电脑,我伏案在前,她站在身后趴我背上,不停地捂眼睛、搂脖子、揉头发、要抱抱,终于我生气了,扯住孩子一把扔到床上。她大声啼哭,我默默流泪。后来想了办法,晚上8、9 点跟她一起睡觉,定闹钟4 点起来写作,写到7 点,收拾出门上班。等到孩子大些了,她爸爸负责接送,我回家做饭,经常是步履匆匆,有时需要小跑,时间总不够用,我必须在晚上8 点半之前收拾好家务,坐在电脑前,中间还要穿插着给孩子作业签字,招呼洗漱、睡觉。后来看到一幅漫画,一个女人长了许多只手、许多只脚,来应付家务、孩子和工作,我不禁唏嘘,这不就是我吗?
再后来有条件白天写作,到点要做饭,洗衣机在转,开水壶在烧,它们发出叫唤,我起身处理,然后再回到电脑前。这就是一个女人的日常和写作,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很珍惜时间,也很守时,因为我最知时间的珍贵,上天给每个人都是每天24 小时,你做了这样,就做不了那样。你若熬夜,就得晚起;你若少睡,就会伤身。但你如果真的爱一项事业,就会想办法克服困难,专注于它。因为没有人逼你写、请你写,文学事业少了谁都行,而你不能没有文学。你对你自己口口声声无比热爱的这个事业,只能无怨无悔、如若初见。
虽然起步晚、起点低,但我志向远大,要写就写大部头。这个想法源自我阅读的那些经典名著,每一部都是一个丰富而辽阔的世界,《约翰·克利斯朵夫》《悲惨世界》《静静的顿河》《浮士德》《复活》让我看到人世间与大自然的博大广阔、艺术境界的崇高、人类爱的丰厚;《大卫·科波菲尔》催人奋进,逆境中追求人生价值;《双城记》里立于大时代下风雨之中街角的那所房子,是温暖的港湾;《人生的枷锁》告诉我一个人真的可以做到身残志坚,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再微小者也要奋力发出光和热;我啃了一个冬天的《尤里西斯》,至今记得清早起床,炉边阅读,拿笔做记号,前后对照人物与情节,终于领略了意识流;《白鲸》《海上劳工》《呼啸山庄》《荆棘鸟》描绘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赖以生存,人在天地之间犹如微尘和水珠,但要执着地怀抱理想和欲望,经久不息地去燃烧、去热爱、去奔赴;巴尔扎克的作品,是丰富喧嚣的现实生活;而茨威格,是深邃幽微的心灵世界,与我的性格比较契合,所以我更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语言的推土机和传送带,吞吐量巨大。
伟大的作品视角多样,可以广角镜,又能显微镜;可以旷野经受风雨,也能温柔乡里沉醉;大至自然万物,小到眼波回眸,诗与远方和鸡毛蒜皮都值得我们心怀敬意。大地、山河、梦想、奋斗、苦痛、热爱、忧伤、欢乐、回忆、展望,这都是文学。
好作品如此之多,她们各个不同,却又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情感丰富的脚步从未停止。每一部作品,都是在人类文明长河的堤坝上,再加固一点,哪怕是一毫米、一微米,众志成城,要始终保证人类文明的河流奔涌向前。
阅读能改变一个人、塑造一个人,让我们知道人应该怎样活着。在此基础上,才是指导写作。读《百年孤独》,乌苏娜年老之后失去视力,还在摸索着做活,并且不让别人看出来她瞎了。我想起我的祖母,在我记忆里,她也是这样没有一天不劳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母亲鲁意莎,永远在劳作,永远在受苦受难。我的祖母也是这样的啊!我是否也可以写一写她?这世上人,不论住在哪里,却原来都是相同的,而优秀作品就是要写出这种人类的共性。
90年代初,我阅读《平凡的世界》,一个月里读过两遍,就想背起包到陕北去寻找。我相信在那些黄土的褶皱里,有一个双水村,有那样一群人。多年之后,再读一遍,下定决心开始写作长篇小说。
阅读让我明白,有多少勇气与真诚,作品才会有多大的力量。比如《平凡的世界》,无论从哪一页打开,都能被作者的真情打动。
《多湾》动笔是2007年,但是在更早几年,我已经有此想法,我要写一部自己想要的那种长篇小说,我制定的标杆就是前面列举的那些世界名著。或许有些拉大旗做虎皮,但“取法乎上,方得其中”,高标准是必须的。于是,我经常回到故乡寻找灵感。小说毕竟是虚构,我所要写的祖母的故事,其实几千字就能讲述,而要撑起一部长篇小说,需要了解的太多太多。那些我出生之前的风物、人情、吃穿用度、社会现实、时代特色,都要掌握,并且要像考古工作者一样,划清年代,提供真实的道具和样貌。总之要写出50 万字的作品,你得先拥有60 万字以上的储备。
文学作品不只是讲故事那么简单明了,而是写人,写时光,写日常生活,写细细碎碎的生命记忆和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心灵世界,写那些界限不甚清晰的事物。故事可以虚构,但细节和情感必须真实。茨威格说过:“其实作家用不着虚构,只要能保持日益精进的观察与倾听的本领,就自有各种形象与事件连连不断地找到跟前,让他做它们的传话人。谁要是常常致力于解释他人的命运,那么,会有许多人向他倾诉自己的遭遇的。”当我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在别人面前,人们会主动向我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各种各样的事情。于是,你会听到属于每个人的生动语言,会得到许多生活片断和逼真细节。不要轻视那些最为普通的人,农民、无业者、家庭妇女,每个人都是一部书,每个人内心都有波澜壮阔的世界,只不过有的人隐藏很深,你要用你的真诚让他们打开心扉,或者以己之心来度他人,于无言处感受喧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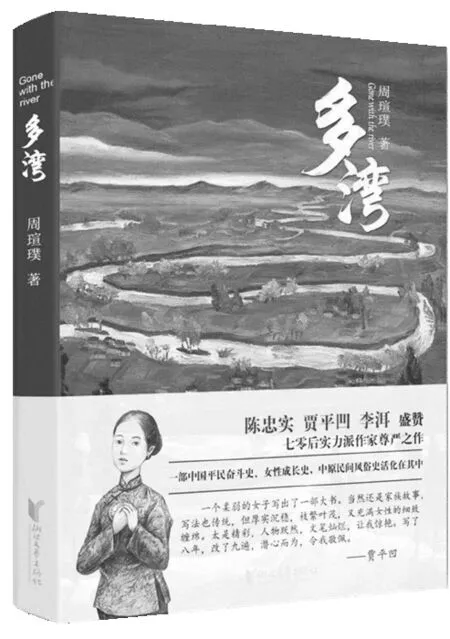
周瑄璞:《多湾》
《多湾》之后,我的作品多写河南农村。四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西安,当我一想到农村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就是河南农村,好像那里的农村才是农村,那里的生活才是乡村生活,只要书写乡村,笔端就指向也只能指向那片土地。
我在作品中所写到的乡村,不论是季瓷的河西章、罗锦衣的罗湾、尹秋生的尹张、甄宝珠的甄庄,还是正在写的人与事……其实,都是我大周村的模样,闭起眼睛看到、想到,小说中的人物就在这里出没。我写到都市生活,无论是哪里的都市,发生多么新奇的故事,在我心里,大致范围出不了我家楼下那几条大小街道。当我写到罗锦衣在绿城步步高升,成为处级干部的时候,需要给她找一个单位,苦苦而不得。一天买菜路过一个设计院,我站在马路对面,对着那个院门观望了几分钟,看到进进出出的人与车。于是,罗锦衣的设计院诞生了。而尹秋生为了送礼,站在李队长家门口等待主人归来时看着楼下不远处城墙上的灯火,也正是从我家楼上看出去的夜景。作家只有写自己熟悉的风景,才能心里踏实,写出胸中锦绣。
四十多年前的夏天,那个转学而来的乡下孩子,看着城市的一切都那么新奇。她怎么也想不到,多年之后,她会成为一个作家,笔下有写不尽的都市和乡村。她细细回顾人生路上的所见所感,将它们零敲碎打地用于自己的作品中,将自己的人生记忆、生命体验,慷慨地分送给她笔下的主人公们。
所谓作家,就是要用物质的肉体、这百来斤的血肉之躯,合理调配使用,使其像机器一样正常运转,像煤炭一样良性燃烧,尽可能长、尽可能多地转化出属于精神的蚕丝。以期将来,物质的身体死去,精神的产品留存,成为能够汇入你所仰望和热爱的那条长河的一朵浪花。
如果能够选择,我愿意让生命在书桌前定格,将最好的一面留在世上,我的大脑还算清醒,我的肉体能够自己掌控,我不愿意老迈昏聩不能自理拖累家人,度过一段没有尊严的日子,在令人厌弃中离去。
命运已经爱我,以文学塑我,命运如果足够爱我,请让我将来死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