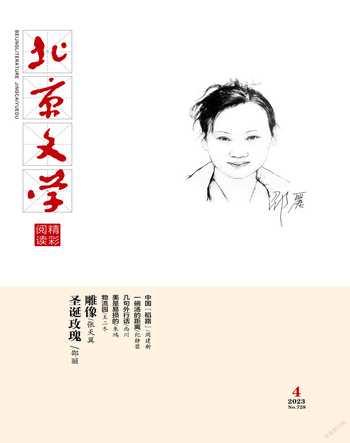如梦令
蔡勋建
我出生那年是甲午年,可谓“惊天动地”。
——历史这样记录着:1954年6月中旬,长江中下游发生三次较大暴雨……长江出现百年罕见的流域性特大洪水。与我有关系的是长江中下游的一个支流华容河溃堤决口,整个兔湖大垸一片汪洋,才开镰没几天金黄色的早稻和那些长得十分喜人的棉花、大豆、高粱都泡了湯。在一个叫五田渡的地方,靠华容河堤脚的一个土砖茅屋里,我的年轻的母亲倚靠着一个木床痛苦地呻吟着,她很自信,她不管我愿不愿意也要拼命把我送到这个“水深火热”的世界……
这一天是农历六月二十一,一个考验我们母子的日子。我似乎对这个世界有着最初的莫名的抵触和抗拒,因此所谓“呱呱坠地”不属于我,本应该属于我的大喊大叫而没有发生,这可吓坏了母亲,接生婆一只手抓起我的双脚一把倒提起,另一只手在我的屁股上狠劲地拍打,我终于经不住这种“酷刑”,最终发出一声长啸,算是“回应”了眼前这个陌生的世界,还有那些陌生的期待的目光。
六月三伏天,最是火热的时节,我来到这个世界。这欢迎的阵势也太隆重太热烈了。不久,水才渐渐退去。可有一天,我们家那土砖茅屋忽然起火,家里人和左邻右舍都只顾忙着抢救家什物件去了,全然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再没有沉默,而对这个世界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呐喊……人们惊魂未定之际,我的母亲回过神来霍然大喊一声“我的儿吔”,冲进火海,把我从摇窝里抢了出来。母亲的头发被火燎得焦煳,她从火海中搂着我冲出来的一刹那,熊熊燃烧的房梁訇然倒塌几乎砸到她的脚跟,我仍在惊恐万分地哭号。我的左小腿已经被火神光顾过了,而且,从此给我永远留下了一幅海岛模样地形图。
我本属马,可邻居街坊硬说我像牛。我出世了,我的麻烦也就来了。我母亲的表姑妈我的表姑奶奶天天来瞧我,说我活生生一条牛犊(读e,第三声)子,索性就叫“沙牛”吧,她们根本不管我同意不同意,没几天我就“臭名远扬”了。我们湘北华容边鄙之地,叫公牛为牯牛,母牛为沙牛,你看这不是寒碜人吗?当年我那大大咧咧的姑奶奶一句消遣涮我的玩笑话——我不知当年姑奶奶对我“男命女名”究竟是何“居心”——居然就铁板钉钉地成了我的乳名小号,让我苦不堪言,几乎受用终身。后来,我发蒙读书有了学名,长成甚至有了字号,可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诨名就像牛皮癣一般死死地赖着,铲之不掉,挥之不去。
我知道,名字对于一个人,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但我更深知一个让人感到侮辱、羞辱、耻辱的符号,会对人造成多大的伤害与灾难!少年慕虚荣爱自尊恐怕是天性,我又怎禁得那些挖苦、嘲笑、奚落等与我那绰号结伴同行,为了一个让人站立不起、总是被别人“打倒”的名字,从小学到中学,我曾经恨不得钻山打洞般地逃离……
许多年后,我都不敢面对故乡,因为只有故乡认得我,故乡的人更熟悉我,就因为一个让我尴尬让我“痛”的名字。倘若回乡下老家,遇见年长者一时认不出我来,偶尔回过神来他会让你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哦哦是沙牛回来啦!”那一声惊诧不打紧却是当着一大堆晚辈小孩的面,我顿时就像一个人赃俱获的贼,满脸通红,一下子从耳根红到脚跟。也有客气的,他不当面叫你,却在背后指指戳戳着说“沙牛回来了”,好像回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牛,一条走失多年的母牛。一个混账名字,居然是我的软肋我的七寸,有的人奈何不了我时,他会在一个让我窒息的地方等着我——在我的乳名小号上大做文章。我有一个叫三九的小学同学,他“斗”我不赢的刹那或是向我挑衅的当头,他的“杀手锏”和“杀威棒”就是扯起喉咙喊歌来羞辱我:读书怕过考哟,种田怕打草,奶猪仔最怕阉猪佬;癞子怕剃头哟,沙牛怕牯牛……那种居心叵测的“儿歌”的杀伤力是极可怕的,那时候,我连钻地坼缝的心都有。
1966年,我12岁,我人生的第一个“轮”。这年我考入县最高学府华容一中,与“炮打”“火烧”热烈邂逅,与“轰轰烈烈”“惊心动魄”欲罢不能。
九月初,极少挑担负重在乡下做裁缝的父亲破例帮我挑着行李——一个木箱,一套铺盖,从华容河北端出发,走过新生大垸,翻过黄湖山,穿过黄湖山峡谷,从黄湖山西麓进入华容一中校园。那时学校周围还没设围墙,唯见古木森森,松涛飒飒,父亲放下行李担,手抚龙鳞般的松树对我说:“伢儿,你可是我们家第一个进华容学府读书的人啊!”
父亲的期待之殷,尽在这一意味深长的感叹之中。按说作为农家子弟,我没有理由不好好表现,刻苦读书,可当时“文革”那种形势场面让我这个懵懂少年既是一头雾水,更有满腹困惑、迷惘和惊惧。这个初中我只混了两年就辍学了,英语仅仅识得26个字母,俄语学会了“起立”“坐下”,代数只上到“有理数”,大白天开批斗会,晚上跳“忠字舞”,或者看高年级的学兄学姐们表演活报剧。
县学府校园里的高音喇叭绝对是一流的,其分贝之高,让方圆十几里都能听到喧嚣,其功能之广,让学校几乎所有活动都能在喇叭口解决,开批斗会召集人最是方便了。有两首“革命歌曲”使用频率最高,一个是《看见你们格外亲》,一个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黄湖山东南麓,是一中的正大门,也是学校通往县城的大道,那是一条煤渣路,那条道上写满了疯狂与荒唐:被打成黑帮分子而头戴黑高帽、挂着大黑牌子的老师们,在全校几千学生排着长长的队伍的簇拥下从那里走出校门,过华容大桥往河西,穿四牌楼至西门打转,游街一个来回上十里地……
父亲对我不放心,每周六我回到家里,他都要刨根问底盘诘:你没有参加什么组织吧?我头摇得像拨浪鼓,我说我是“逍遥派”。父亲先是一愣,随即睁大眼睛凶巴巴地问逍遥派是么子派?我说么子派都不是,父亲马上说:逍遥派好,逍遥派好!
学校食堂也仿若战场。那时学生开餐吃桌席,一张四喜桌为一席,八个人吃一席,大概是四菜一汤,炒大白菜、炒白萝卜片、青椒炒榨菜,还有个小荤菜什么的,汤是霉豆渣汤,每天每餐大同小异。大米蒸饭有两盆,每盆一斤二两,铝盆。那种开餐的场面是盛大的,大饭厅平面摆放几百桌,吃饭的动作也是神速的,简直就像打仗,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战斗。场面真是骇人,只要饭厅的大门一打开,那些早就拥在门口敲盆击缶的学生们顿时如潮水般涌入,捷足先登者会抢先抓起一只铝盆,用钢叉或钢勺把先将盆内米饭画上一个十字,——虽然那十字就一横一竖,但绝对不是公平准确的横直两根线,严重地倾向一边,四个四分之一,是绝对不相等的——再用勺把顺铝盆内壁搅一圈(防止米饭巴盆),然后瞄准四个半月形的其中最大的一坨,用钢叉撬起往自个儿碗里撂,接下来就是如何向菜进攻了。当然能这么干敢这么干的绝对不是我们这些使用竹筷子被称为“乡巴佬”的农家子弟,而是家住城里的“小霸王”所为。这样的结果是非常尴尬非常难堪的,像我这样的乡里伢子,经常是吃上最小最小的那一坨米饭,那是名义上的四分之一,这还算是走运的,最吃亏的要数本桌的女同学,男生们殊死战斗之时她们按兵不动,等到她们动手时已是一片狼藉,盘中所剩无几,能吃上一小角儿米饭是幸运的,最后连霉豆渣汤都喝不上的往往就是她们。
1977年,我“将”了父亲一军,父亲说那是“抠底将”——没经过他同意我退伍了。我不知我触到了他的底线。回到家那天,父亲很不高兴,黑着个脸。见到街坊邻居也有些躲躲闪闪,好像有什么见不得人似的。老实说,我在部队当兵六七年,本来是很有可能穿上四个兜兜的干部服军装的,不是我不努力,只是没有想到最终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竟然是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当希望总躲在绝望之后你看不见摸不着时,何去何从,你就要下决心了,于是我坚决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后转”。回就回了吧,这倒没什么,只是我心里还是有些难过,我用什么来安慰你,我的父亲。自从1970年冬,16岁的我当上了汽车兵,第一次离开家离开他,他的眼睛就一直守望着我,哪怕千里万里关山阻隔他也目不转睛,其实那也是一种望眼欲穿——他巴不得我的肩上扛个星回来,可惜那年代还未恢复军衔制。
我有兄弟四人,可能我是父亲最寄予厚望的,我在部队超期服役三年据说他曾在乡党面前夸下过“海口”。后来,父亲知道了是他“影响”了我的前程,内心非常歉疚,看到我滞留在家,他心事沉重。其实,我才觉得压力山大,一同退伍的战友们一个个被市里县里招工走了,有去运输车队的,有去机关单位开小车的,我却一次次坐失良机,原来的那种“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青春自信和技术自信被一次次的招工失败渐渐抵消。年龄在增长,青春在消磨,我真的要认真考虑再一次离家了,再不走就真的走不了了!再不走,我这个大队小学代理校长就真的会“转正”留下;再不走,我就真有可能留在大队当干部——据说公社里那个抓党群的副书记在党员培训班上已经“看”上我了;再不走,父亲就真的会拿根竹棍来撵我了,他生怕我窝在家种田。我在父亲的幻想与翘望中匍匐着,等待时机,我的前途似乎只有两个词四个字:“提干”“上班”——这都是多美好多体面的字眼!前头那两个字永别了,后头这两个字,对于我这个回乡的汽车兵来说,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这不,说走就走了。
我迫不及待,一步就跨进了县城,目标是县商业车队,工作是卡车司机,属性是“亦工亦农”。在那年月,亦工亦农是体制的一种产物,用劳动部门的术语说,就是一种计划内的合同工,用社会“俗话”说,就是也工也农,工人职业农民身份,说白了就是一个吃“背背粮”的货车司机。我真的是饥不择食了,连一个几乎就是一个临时工的“空当”也不放弃了。
我的身份在车队被严格地区分着。首先,你是个代班司机,就是驾驶员谁家里有事谁请了假,那你就去顶班,你要随叫随到。其次,你是一个没吃“国家粮”户口还在农村的合同工。食堂里掌大勺的刘师傅是个国家职工,他手中打菜的钢勺从来只向那些正式职工倾斜,他的笑容从来不送给我。后来他退休了又留在车队当门卫,退了休也不减威,有时为啥事也不忘记他国家退休职工的身份对我嚷嚷。在那个严格以“国家粮”给人定等级分尊卑的年月,我们这些吃“背背粮”在城里谋食的汉子,一个个把自尊藏得很深很深,生怕被人碰伤。
俗话说,黄土也有翻身之日。不知是我的执拗,还是我的幸运,终于感动了上帝,后来我不仅翻身招了工,还有了几次身份置换。
调到商委工作后,我登了一次鼎山。鼎山在我心中相当于泰山,虽然海拔不高,却也十分险峻。站在鼎山——我湘北家乡版的泰山——之巅,远望着人们手足并用气喘吁吁从西北角陡峭处往上爬,不禁感慨万端——人生何尝不是在爬山?只是我有所不解,为什么越是陡峭险峻越是挡不住人们向上的步伐?
是的,我一直都在攀爬那座属于我的鼎山。我不敢这山望着那山高,可我的遭际中却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就在我左冲右突困兽犹斗折腾多年好不容易招工、解决粮食户口,然后又获机遇改行之际,又遇上了新问题。
时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赖以谋生的县商委原本好生威武,管辖着粮食、商业、供销、外贸、石油、烟草、盐业、药材等八大单位,忽一日,县里宣布机构撤销。一个偌大的机关、一支偌大的队伍似乎随着一声哨响就地解散了。
这年三月,我被疏散到粮食局,没想到报到当日就遇到了一道坎,当时粮食系统人事直属省厅统管,下面进人必须先报省厅审批,由于事涉改革大局,当时也就“先斩后奏”了。我手里虽然捏着县人事部门开具的介绍信,那不好使,真正进入还是要走程序,最后还是局长亲自带上一摞我在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以“人才引进”为由申报,好不容易过了省局这一关。
前些年,我潜心于文学创作,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我是被人“发现”并推荐去县商委工作的,先是借调,后来正式调入,主要是编辑《商业简报》,写写材料,这让我彻底告别职业开车生涯。由于不是干部,我的身份又以一个新名词——“以职代干”——来确认。也有说“以工代干”的,就是干部岗位工人身份,也是体制的产物,那时如我这样的“同行”不少。
我发现,一个单位人头总是用所谓编制来控制的,问题是占了编制的人撇开什么背景不说,他可以不干事或者说他干不了,可钱照拿。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没占到编制但还得要“一颗栗子顶一个壳”地干,只能好好表现,寻找机会。我属于后者。既不是干部,也不带编制,那个日子就不好过了。好在局长开明也挺爱才,任命我为某股副股长,括弧,保留正股级。自然这也是对我最好的安慰,我自己也这样想,我毕竟是“从上头下来的”,可人家那老资格在局里待了几十年的老股长不高兴了,生怕你是来抢班夺位来了。给你一张办公桌,整天面无表情,老人家自己忙得不得了,就是不安排你做事,你插不上手也就只能是每天几张报纸一杯茶,日子过得那个憋屈得慌。
不久,局里成立政工办,命我“主政”,实际上我也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手下无一兵一卒,工作职能也很简单。局长很期待地对我说,今后局里有关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事情就統归你管。这就有事干了,那些年年年都评市级省级文明单位,政工办可是重任在肩,责无旁贷。事实上干完这些本职工作之后,我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本单位系统的宣传上,就是外树形象,用笔发言。大量的有分量正能量的纪实性报道走向媒体,有的则冠以“报告文学”在大报小刊发表,单位声名鹊起,我的知名度也随之提高。但有一件事你不敢想,那就是提拔,人要求进步这很正常吧,可你是个“白坯”身子——不是干部,没门。每年县委组织部门都会下来考察科局级领导班子推荐干部,说还是说“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可你还得要有那资格。我呢,那也就是“早谷米打糍粑——不够格”,虽然早谷米也是米,但黏不上。
又一座大山挡在面前。不是干部,你提拔难,要提拔,你得先录干。不是干部,更有尴尬的时候,那就是年度的公务员考核与岗位清理,你连干部都不是却还占着一个主任的岗位,鸠占鹊巢,这哪成啊?这时候你还不要太着急,因为事情还都是要人去干的,更何况有些事儿未必是谁都能干得好的。末了,单位上领导出面向上报告保留几个“以职代干”岗位,于是我们得以幸存。我们这些被保留下来的“人才”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报考国家公务员,一条是等待过渡(机构改革或上面下达转干指标),报考我是不敢,就只能是等待过渡了。可等待是漫长的,不一定有结果,在这种焦灼的等待中,我还要解决好文凭问题,还得创造一些留得下站得住的理由。
1990年,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热播,万人空巷。我心里百感交集,也有一种渴望。
2014年仲夏。某日,收到一则短信,我大吃一惊。让我吃惊的不是这短信的内容,而是发短信这种形式以及短信的语气。这则短信正儿八经地通知我,根据某某部门指示要我准备办理退休手续。语气完全是居高临下毋庸置疑的,发短信者是局人事科长,一个我曾经共事多年的“铁哥”。铁哥科长没有给我打电话而是给我发短信,这让我感到庄重严肃,公事公办。
我要退休了,這是真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这不是真的,我以为这不过是时间跟我在开玩笑。因为在我看来我早已是“退”了“休”了的,所谓退休也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给我“补办”一个手续,然后发一个退休证。这有个说头。
2006年三月,县领导约我谈话让我“退线”,问我还有啥意见啥要求,还一再表示“今后待遇不变”。我说没啥意见,反正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下呗,不过我得郑重声明,我的实际年龄离52岁“一刀切”还差四五个月。那次谈话很简单,没几分钟就结束了离开了,我心里明白,结束的不只是职务,而是一种生涯;离开的不只是单位,而是一种舞台。我提前几个月“退线”,有人对我说干吗不“坚持到底”呢?我说为什么呢?那人又说谁谁谁就表示“差一天也坚决不下火线”,硬杵着。我却很坦然,那有啥呀,不就一个“带蚌壳的”(括弧,享受正科级待遇)XX长嘛,那样抗着杵着有意思吗?
我很配合,也很快地腾出了办公室,交出了钥匙。按本地约定俗成的模式,你退线了,就可以不去机关上班了,换句话说你彻底自由了,放羊了,你快活了。老实说,这种日子并不快活,你很快会被边缘化,越边缘化越会有失落感,而且你还会有你意想不到的问题接踵而来。
果然,问题来了。首先遭遇的是以前每月的手机话费补贴给你取消了。平心而论,抹去这几十百把元的补贴也在理,你不在领导岗位不办公事还补贴个啥呀,问题是上面那位领导说的“不变”那话尚言犹在耳,这事儿虽小,却也让人憋屈,不是钱的事。
我原来那单位,全系统几千人,曾经是人喊马嘶,热闹得很,如今呢,门前冷落车马稀了。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作用决定存在。一个单位其作用淡出职能退化而日渐式微那是很正常的了。可人心不稳,局里一把手换过好几位了,谁会愿意给一个没事干守摊子的单位“站台”呢,这不,又有一个局长没来几个月又调走了。没多久,县里决定我们局与某局合并,我就是在这种状况下退线的,一退就是8年。整8年提前离岗彻底赋闲,工资开始是签领的,后来就打卡了,这就越来越与单位组织没有往来,不是自个儿“玩失踪”而是生生“被遗忘”。所以说,退休手续是“补办”的。
回到退休这个话题。这就很有些尴尬了。先是县里主管部门一个按章办事的电话提前通知局里人事科,某某某要办退休了,于是人事干部就通知本人交两张照片拟办退休证用。到了退休时间——顺延一个月,你就去领退休证,从此你的名字进入了另一个行列。而这个过程,没有谁找你谈话,没有谁为你开会,没有……就像一枚熟透了的果子(后来我觉得自己太自恋,这样的比喻太美好了),自动地悄无声息地从树上掉下向地面滑落……
说来也巧,我拿到退休证那天,迎面正好碰到一文友,我想与他坐坐,没想到这位主政某局的诗人局长谢绝了,理由是他要去参加本局老同志退休茶话会。这真是尴尬人偏遇尴尬事,哪壶不开提哪壶。是我“退不逢时”吗?也对。我办退休时,我那单位刚好宣布与某单位合署办公,原机构虽撤销,但一直貌合神离,“两地分居”,名义上的局长有一个但基本不理这边“朝政”,说不上是群龙无首,也不算是我人无归属……
那一刻,从我曾经的“铁哥”科长手里拿到退休证的那一刻,从我有心邀请老朋友上茶楼遭婉拒的那一刻,我猛然惊醒了,人生的确如梦,退休了,就远远不是什么边缘化了,而是要被滚滚红尘彻底淹没……那一夜我失眠了,我想我们“50后”这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除了上述这些,还有诸如文凭问题计划生育问题都曾让我们十分尴尬。是的,我只能说尴尬,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尴尬,好在虽然说“尴尬”也是“坎”,但最终还是被我们“越”过去了。我一次次的身份置换,都无不见证着我在不屈不挠地穿过这些“尴尬之门”。
人生总在穿越,尽管人生如梦。
特约编辑 白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