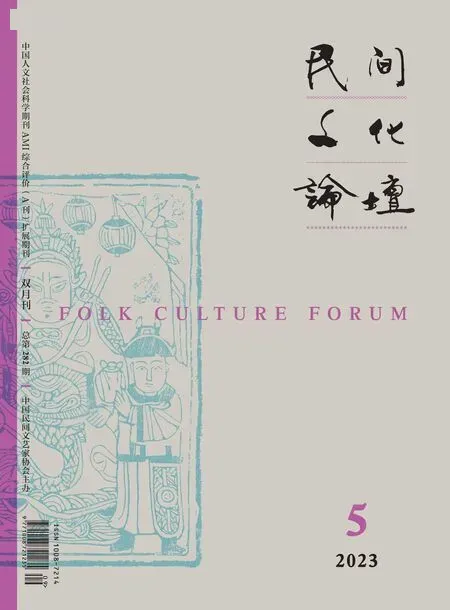松茸的“非进步”*故事
—— 评《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
赵 强
一、引言
借助民族志讨论自我与他者的具体内涵以及二者关系的研究贯穿于人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古典时代的人类家通过对传教士、商人以及探险家从世界各地搜集而来的民族志材料进行拆解,并重新分类排比,构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史。这一宏大的人类叙事将西方文明置于演化序列的最顶端,并将非西方社会按距西方文明的远近放置在序列的不同位置。20 世纪20 年代,以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为代表的现代人类学家对古典人类学家的宏大叙事提出了激烈批评。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古典人类学家的演化叙事既不具有学术研究上的科学性,又带有极强的民族中心主义色彩。因此,在方法上,其一方面主张将理论建构和材料搜集合二为一,放弃宏大的“全人类”叙事,强调对一个特定时空坐落点的“分立群域”的研究①[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译序”,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年,第1 页。;另一方面,也主张人类学家不应再借助民族志标榜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而是应该借助来自“遥远的异邦”的发现,去挑战西方文明自以为是常识的内容。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在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等理论的启发下,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R.Wolf)批评了先前人类学研究将其研究对象描述为与世隔绝且“没有历史”的人群的做法。沃尔夫指出,自1400 年以来,人类世界日渐成为了一个由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这种彼此关联的过程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非西方社会不断被卷入到大的政治经济体系中。①[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贾士蘅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年,第3 页。简而言之,在沃尔看来,根本不存在与世隔绝、封闭、单一的文化、社会和民族。所以,人类学的研究不应执着于寻找纯粹的原始人,而应该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土著社会发生的变化。自沃尔夫以后,人类学家认识到民族志不再是对一个封闭的时空坐落点的研究,而是对“小地方”与大的政治经济体系遭遇的过程研究。不过,与沃尔夫将土著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遭遇视作是不同生产方式的相遇,并认为西方社会在这场遭遇中占据主导地位不同,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则将这种遭遇看作是不同文化体系的碰撞。并且,在这场文化的碰撞中呈现出的不是强大的西方社会主导土著社会的过程,而是看似弱小的土著社会并接西方社会的过程。②[美]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332 页。除了上述争论外,人类学家也开始日渐意识到对这种世界体系的呈现需要将传统民族志的“单点”研究拓展至足以追溯文化间遭遇联系的“多点”研究。
与上述经验现实对于民族志的挑战相伴随的是以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思潮。就人类学与民族志而言,格尔兹指出,人类学并非是一门探求规律的科学,而是一门理解意义的艺术③[美]克里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年,第5 页。;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并不能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果规律,而只能实现人类学家、研究对象以及读者不同层次的理解。在上述反思潮流的影响下,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对于自身学科知识生产方式的反思,其典型代表便是马库斯(George Marcus)与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合编的《写文化》一书。该书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人类学知识生产基石的民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制造”出来的,人类学借助民族志研究所宣称的“真理”与“科学”不过是特定修辞和权力的结果,人类学家应该坦诚承认自身研究过程的主观判断,接受民族志只能呈现“局部真理”(Partial truth)。④[美]乔治·马库斯、[美]詹姆斯·克利福德:《写文化》,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29—55 页。
21 世纪伊始,在经历自身学科内部的知识论⑤王铭铭:《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民族研究》,2015 年第3 期。的反思后,伴随地质学家提出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时代的来临,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又重新聚焦于经验世界。不过,与先前的民族志研究不同的是,这种经验研究试图处理的是“自然与文化”这一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其反对传统人类学将自然与文化割裂开来看待的观点,而认为应更加注重特定社会中人与非人的关系的研究,其代表人物包括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和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知识界将带有上述风格的研究统称为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⑥Eduardo Kohn,“Anthropology of Ontologie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44, no.1(August 2015), pp.311~327.。
本文要讨论的罗安清(Anna Tsing)的《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一书便可放在上述脉络中看待。《末日松茸》英文原版出版于2015 年,2017 年被翻译成法文,2019 年其中文版面世。该书是罗安清继《钻石女王:一个偏远之地的边缘性》(Diamond Queen:Marginality in an Out-of-the-way Place, 1993)和《摩擦:全球关联的民族志》(Friction: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2005)两本书之后,被引用和评论最高的一本书①克洛蒂尔德·里奥多尔、希普利恩·塔塞:《如松茸般脆弱:评〈末日松茸〉》,王立秋译,https://www.douban.com/note/786410378/?type=collect&_i=5692372IjiNV0g,发布日期:2020 年12 月1 日,浏览日期:2021 年1 月12 日。。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示,罗安清试图寻找一种资本主义废墟上的新可能。这种新的可能绝不是“进步”话语意义上的重建,而是一种多元物种合作共生的可能。罗安清通过将松茸放置在全球政治经济的裂缝中与多元物种的合作共生中来看待,用民族志的方式讲述了“人类世”时代下的“非进步”的故事。这种“非进步”的故事既是理论,更是一种方法。作为理论,它向我们展示了经验世界如何在交染和不可规模化的基础上作为一种人类与非人类合作共生的集合体而存在;作为方法,它则展示了民族志的多点研究、复调叙事以及人类与非人类合作共生的整体观。
二、“非进步”故事的理论表达:集合体、交染与不可规模化
“人类世”这一术语最早是由荷兰的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家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在2000 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的。2002 年,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人类地质》(Geology of mankind)一文,并在文中详细阐述了“人类世”的具体意涵,作为一个具体概念的“人类世”也由此产生。他指出,“人类世”是对“全新世”(Holocene)的替代,其代表着地球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时代。在他看来,“人类世”跟以往时代的最大的不同在于人类活动对于地球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地球的历史演变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按照克鲁岑的讲法,此处的人类活动在时间上是指1784 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的活动,具体是指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导致的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预能力。②姜扎福:《“人类世”概念考辨:从地质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 期。
尽管,“人类世”最初是作为一个地质学概念而被提出的,但它也在人类学中引发了广泛的谈论。2016 年,Ethnos杂志上发表了罗安清、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人类学家对于“人类世”概念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罗安清指出,“人类世”一词实际体现的是现代人类自负的一面,因为“人类世”背后所隐含的是相信人类可以借助理性能力超越“自然”限制的启蒙运动式的人观。在罗安清看来,正是这种理性的“人”造成了现代社会的混乱。所以,她认为“人类世”带给我们最大的承诺就是让我们对自己先前的认知持有一种批判性的思考③唐娜·哈达维、诺伯鲁·艾希卡瓦、斯科特·吉伯特、 肯尼斯·奥维格、安娜·青:《5 位人类学家共议“人类纪”》,王潇宇译,https://www.sohu.com/a/152488384_806115,发布日期:2017 年6 月27 日,浏览日期:2021 年1 月15 日。。在《末日松茸》一书中,罗安清又进一步阐明了“人类世”背后理性人观的具体表现,并将其表述为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的进步故事。罗安清指出,“人类世”并非开始于人类的出现,而是始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现代资本主义基于“人定胜天”的信念在全球不断扩张,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科技进步、经济增长、民主发达”的进步故事。这种进步故事相信只有人类具备展望未来、创造世界的能力,非人类则只是为人类的“进步”事业服务的。不仅如此,在这种进步话语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背后的人观被视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力;整个历史的进程都被这种“进步”所主导,人类也必将随着“进步”的不断胜利迎来“历史的终结”。针对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的进步故事,罗安清指出,其揭示的不是人类的自信,而是人类的自负,它将人类推向的不是“明日”,而是“末日”。
如果说“人类世”和资本主义背后所隐含的“进步”是一种幻象的话,那么“非进步”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罗安清提出了三个关键的概念来回应上述的问题。它们是“集合体”(Assemblage)、交染(Contamination)以及不可规模化(Nonscalability)。“集合体”是相对于有固定且明确边界的“群落”(community)而言的,其聚集的元素既包括人类,也包括非人类,“同时集合体也并非只是聚集起各种生存方式;它还参与塑造了这些生存方式”①[美]罗安清:《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张晓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7 页。以下引用该书只随文标注页码。。那非人类与人类是如何聚集在一起并相互塑造呢?罗安清的回答是:这种聚集的过程并非只有人类在创造,非人类也参与其中。并且这种创造并非是在带有明确目的和假设的前提下展开的,而是不同物种之间基于“无意向协调”(unintentional coordination)模式展开的。对于罗安清而言,关注集合体及其内部不同元素的无意向协调,是一种“可能重振政治经济和环境研究的方法,它意味着要观察在不同生存方式中聚集的时间节奏和范围之间的相互作用”(第17 页)。总体而言,集合体有助于我们超越之前的“进步”叙事,让我们可以关注“零碎的景观、多重复调的时间性、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不断的变化的组合”(第13 页),这种关注不再是寻求某种确定、均质、单一化的力量,而是要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多元物种协作共存的可能。
既然集合体的核心在于开放式地接纳不同元素之间的无意向协调聚集,那么一个聚集的过程如何能成为“突发事件”并使之大过所有部分的总和呢?答案是:“交染。”“交染”的提出是为了批判进步叙事下的“自足个体”。在罗安清看来,世界根本不存在绝对自足的事物,任何存在都带有交染的历史。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通过交染而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仅仅看到那些无情的个体的扩张征服策略”(第25 页)。换言之,交染的目的不在于扩张和进步,而是在尊重差异基础的上的协作;它可以创造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却并非自足演化轨迹上的单纯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拒绝被‘总结’的、是特殊的、基于历史的、变化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第31 页)。
“不可规模化”是相较于“规模化”(Scalability)而言的。罗安清指出,“规模化”作为一个术语源起商业领域而并非技术领域。在商业领域,规模化指的是一个公司在不改变自己本质属性的基础上的扩张能力②Anna Tsing,“On Nonscalability : The Living World Is Not Amenable to Precision-Nested Scales,”Commom Knowledge, Vol. 18,Issue 3(Fall 2012), pp. 505—524.。一个规模化的研究计划只认可那些符合其研究计划的数据,它们排斥那些不确定性和足以改变事物性质的多样性。所以,规模化的本质是进步话语下的均质化的扩张,其最核心的表现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这种“交换价值”背后隐含的是价值观是相信任何东西都可以从其生长的物理世界和文化世界拔出,被投入到一个标准化和均质化的范畴去看待。但不可规模化的提出并非是对规模化的取代,因为非规模化只是一个描述概念,不涉及好坏的评判,当代的经验世界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规模化的现象。尽管如此,不可规模化与规模化的变动式拼嵌仍越来越成为当下资本主义商业的积累的核心方式。
三、松茸的非进步故事:政治经济的裂缝与多元物种的共生
(一)政治经济的裂缝中的松茸
在《末日松茸》的序言中罗安清写道:“这本书想告诉大家,如何通过密切关注不确定的世界,并思考财富的累积方式,继而能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同时,避免采纳它逐渐崩坏的假设。不强调发展进步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模样?它看起来可能东拼西凑的:财富之所以能集中,是因为计划外的区块所产生的价值皆被资本据为己有。”(第6 页)所以,与一般的关注资本主义如何按照标准化的流程在世界各地规模化的过程不同,罗安清揭示了,全球供应链中的松茸,实际呈现为资本主义规模化与不可规模化拼嵌的结果。这种拼嵌体现在松茸的生产与消费两个核心环节。
罗安清指出,松茸的采摘完全是在一种毫无企业招聘、培训和规范的情况下进行的,人们采摘松茸虽是为满足特定的生计需要,但是他们却很少将其视作一份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工作去看待,而是将其当作可以体现美国理想价值的“自由”去追求。同时,因为拥有不同的社会经历和历史记忆,不同的族群对于“自由”的理解也呈现多种含义。如对于退伍白人艾伦和杰夫而言,松茸采摘的森林生活是艾伦远离战争造成的心灵创伤的方法,杰夫通过把采摘松茸视作一场狩猎,使自己重新在森林景观中体验了自由的生成。对于柬埔寨难民而言,重返森林只是为了享受美式自由带来的安全感;而恒则认为,只有在山里他的生命才是完整的。对于苗族人王柴和杜而言,在森林中采摘松茸则夹杂着战争、狩猎和乡愁等各种社会记忆。相较于其他国家的人而言,松茸采摘对于老挝人来说,虽不涉及直接的战争体验,但却是其挑战界限和摆脱困境的尝试。
不仅松茸的采摘有别于正统资本主义积累的进步叙事,松茸采摘完成之后的售卖也同样如此。罗安清形象地把松茸由采摘者售卖给临时收购者的整个过程称之为“保值票”(open ticket)市场。“保值票”实际上是对购买蘑菇行为的称呼,它意味着“采摘者可以向买手要回当日所支付的原价和最高价的差额”(第82 页)。在罗安清看来,“保值票”市场上演的买方与卖方之间的互动过程与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完全不同,它像是一场戏剧的展演。这场戏剧上演了松茸的分拣,讨价还价、等待三个节目。就分拣而言,白人的分拣像杂技、老挝人的像皇家的舞蹈。买手利用语言、亲属关系、族裔或者特殊奖金来讨好采摘者固定向他供货更是常有的事。除此之外,当采摘者对所有出价都不满意的时候,等待也成了一幕自由的展演。简而言之,“保值票”市场通过将采摘者、买手与现场代理勾连起来,形成了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展演的场所,这种互动不只是交易松茸和金钱,还包括对战功的炫耀和对自由的追求。
当松茸被从保值票市场带出时,它便从采摘者和买手中的“战利品”变成了真正的“商品”,它会被分级、包装、运往日本。为什么在美国采摘的松茸会被运往日本,这其中固然跟全球化的大时代有关,但在罗安清看来,其中还夹杂着美国与日本近代以来的复杂关系史。同时,罗安清指出当松茸抵达日本之后,被售卖以及最终被消费的过程,也并非简单的资本主义规模化的过程。对于日本人而言,松茸不只是某种稀缺的高价商品,更是一种精品赠礼。在日本,“几乎没有人购买一朵优质松茸只是为了自己食用,松茸可以建立人脉,作为礼物,松茸与人际关系密不可分,松茸成为了人的延伸。”(第145 页)具体来说,当作为商品的松茸被运输到日本之后,它首先会被卖给批发商,然后再通过拍卖或者谈判的方式卖给中间商,最后再由中间商卖给特定的消费者。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批发商还是中间商,松茸在他们眼中都不是简单的商品,他们除了在售卖过程中赚取特定利润外,其核心工作在于找到最适合使用松茸的人。经济因素固然是决定这种适合性的一个方面,但具体的社会文化因素也非常重要。比如,这些中间商会建议宗教皈依者购买松茸送给其精神导师,这是因为松茸代表了一种严肃贵重的承诺。总而言之,流转于全球政治经济裂缝中的松茸并未完全作为商品被生产和消费,而是承载着诸多社会文化的意涵。
(二)多元物种合作共生中的松茸
同样,在本书的序言中罗安清写道:“在这个期望值降低的时代,我想寻找一种以变动为本的生态学,多元物种能既不和谐又无需争夺地一起生活。”(第6 页)这种多元物种合作共生的故事克服了进步故事中只允许人类作为主人公、且只相信人类具备创造这个世界的能力的看法;转而提倡一种没有人类英雄,甚至将景观作为主角的故事。对此,罗安清以芬兰北部、日本里山、中国云南以及美国俄勒冈州东部四个地区的松茸为个案,向我们呈现了松茸与其他其他物种合作共生的四重奏。
作为自然物种之一的松茸在上述四个地区都首先面临跟其他自然物种协作的要求。由于松茸最主要的宿主是松树,所以松树成为了观察的起点。罗安清指出,松树的生长得益于与真菌、松鸡、乌鸦、喜鹊、星鸦和人类等的交染和无意向协调。多元物种之间互动结合成集合体,向我们展示着人类与非人类共同创造历史的过程。当松茸被通过农耕和工业化等手段彻底带进人类进步的事业时,其在上述四个不同地区也并非完全呈现出协调一致的进步声音,而是依靠各自地方情境呈现出诸多因素的纠葛和缠绕。就芬兰北部的案例而言,持有现代化观念的芬兰林务人员将森林视为稳定的和可再生的,但森林实际却又是无止境、历史性的。二者的矛盾使得芬兰的案例呈现的不是工业化过程中林务人员对松树的定期砍伐和现代化的园艺管理,而是“松树的生长没有按照林务人员预先设想方案进行”的不和谐景象。在日本里山,松茸成为了一个保育运动的实践项目。罗安清指出,里山的保育计划是我们在废墟上复苏的可能,其目的在于“重建农业干扰,教导现代人如何与活跃的自然共存”(第216 页)。与日本里山松茸的怀旧重建不同,中国云南的松茸体现的则是农民积极利用的一面。这跟中国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运动有关。如大跃进运动时,森林被视作“绿色钢铁”;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引入和现代环保主义的兴起也对松茸和森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样,美国俄勒冈州东部的松茸背后也承载着美国早期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土著印第安人的血泪教训。
总结来说,上述四个地区上演的与松茸有关的多元物种互动向我们展示了非进步下的人类与非人类互动的故事。在这一过程当中,松茸与各种生存方式汇聚在一起,彼此既自成一体,又相互协调,协调的出现与消失都取决于历史变化的偶然事件和无心的干扰,在这里没有进步、单一的节奏,有的是复调、缠绕和不稳定性。
四、小结:非进步故事下的民族志的想象力
罗安清的《末日松茸》基于全球化和人类世这两个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实际,开启了民族志新的想象力。
(一)从多点田野研究到政治经济的裂缝
民族志的多点研究最早是由著名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提出的。在马库斯看来,多点民族志的提出是人类学为适应全球化来临的方法调整。早在1972—1974 年间在汤加王国首次做田野的时候,马库斯就强烈地意识到汤加社会呈现的“去中心化”甚至“国际化”的现象无法依靠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单点研究去完成①[美]乔治·马库斯:《十五年后的多点民族志研究》,满珂译,《西北民族研究》,2011 年第3 期。。20 世纪80 年代,伴随着反思人类学的兴起,马库斯在其和克利福德主编的《写文化》一书中发表了一篇名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当代民族志问题》的文章,在该文中马库斯使用了“多场所的”(multi locale)一词来指代世界体系下的民族志研究可能。
马库斯以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经典研究《学做工》为例详细阐述了“多场所的”民族志研究可能性。其指出与传统民族志研究只基于对研究的特定地点的地方知识的深度把握不同,威利斯的研究虽是基于工人阶级为何子承父业这一主题,但是要明确地回答上述主题,除了要知道他们在家庭和学校的表现外,还必须要了解到这些男孩将来在工厂会成为什么样的人。②马丹丹、[美]乔治·马库斯:《文本、民族志与在地化:关于写文化的整体理解》,《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1 期。如果说该文只是马库斯开始尝试思考世界体系下民族志新的可能性的初步结论的话,那么1995 年发表在人类学年度评论杂志上的《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志:多点民族志的出现》文章则标志着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正式提出。在该文中马库斯指出,多点的民族志的提出是长期存在的民族志实践模式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甚至是全球化现实的调适。多点研究超越了诸如“本土”与“全球”以及“生活世界”与“系统”等的二分,所以其民族志既在世界体系之内,又在世界体系之外。多点民族志出现在跨学科工作的新领域,诸如媒体研究、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其他的文化研究。其核心在于关注现实世界的移动性和流动性。所以“多点”并非仅指数量上的多,而是指整体需要意义上的多。它强调要跟随人、隐喻、故事以及生命历史的流动而变换场景和地点,目的在于在整体上呈现出这个复杂的世界体系,同时又不至于落入地方和全球的任何一端。③Marcus, George E,“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24, no.1, 1995, pp.95~117.
就《末日松茸》而言,本书的研究体现了跟马库斯所言的流动性相似的多点田野作业。罗安清追溯了松茸如何从美国被生产出来后在日本被消费的过程,作者随松茸的流动变换田野研究的地点和场景,以期勾勒出世界体系中的松茸全貌。然而,罗安清的研究又并不止于为多点民族志做注脚,也带给我们重新理解多点研究的新可能。她虽是借助多点研究来呈现全球化时代的松茸贸易,但并没有仅关注松茸场景的变化,而是更加详细地阐明了松茸在全球产业链的裂缝中的意义。总而言之,罗安清的松茸贸易研究既通过多点揭示了松茸在世界体系中的连贯性,又看到了松茸在“多点”中不同含义,以及松茸从“点”到“点”之间发生的转译。
(二)人类与非人类共生的整体观
整体观是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核心,尽管不同时代以及不同派别的人类学家对于何为人类学研究的“整体”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们大抵都同意这种整体关涉的对象是人类的社会与文化。罗安清在《末日松茸》中挑战了这种基于自然与文化二分的传统人类学的整体观,她指出,传统自然与文化的二分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学只承认人类的理性创造力,而忽视了非人类的存在的能动性。借助交染这一概念,罗安清指出非人类与人类一样具有创造力。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人类对于非人类的征服,也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相互缠绕、干扰以及共生。就松茸而言,罗安清指出,松茸是在与其他物种的协作和人类无心的干扰中出现的,在其中自然代表的非人类存在并不是被人类征服和统治的对象,人类也并不是所有存在演化序列中最高的和最自足的,相反,人类与非人类的存在是彼此协作共生的结果。①在该书的第二部分结束时的“插曲:追踪”部分,罗安清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的协作共生的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比如菌根(mycorrhiza)的概念以及生物学家斯科特·吉尔伯特的共同协同发展(symbiopoiesis)的概念。罗安清在此处的观点与著名人类学家蒂姆·英格尔德(Tim Ingold)的观点不谋而合,英格尔德也认为人类学研究的整体应该是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互动和结合。所以人类学的研究应该抛弃传统的自然与文化的二分法,真正地将非人类的存在纳入到其研究视野中。当然这种纳入并非是将非人类的存在视作特定的工具和外在的限制,而是将其视作与人类一样可以创造历史和世界的行动主体。同样,也正是基于上述的整体观,罗安清呼吁一种合作的人类学,这种合作人类学固然包括人类学家与各种报道人之间合作以及与其他学科等的合作②[美]乔治·马库斯:《超越仪式的民族志:合作人类学概述》,陈子华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1 期。在该文中马库斯指出合作人类学有七种形式,但是并未涉及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讨论,在这意义上罗安清的合作内涵更广。,但更包括非人类与人类的合作共生,这种合作的目的在于真正确立一种超越私有化和商品化基础上的人类学知识生产方式。
(三)“复调”叙事
“复调”(polyphonic)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俄国文学批评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作品时提出的。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作品中作者并非是上帝般的存在,而是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不断进行对话的谈话者。小说中的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变成了有独立思想的主体。③李春香:《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世界文化》,2020 年第5 期。20 世纪80 年代,伴随着人类学内部反思民族志书写的实验民族志的兴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调书写也被引入人类学内部用来批判传统民族志中只有人类学家独自发声的书写方式。由此出现了强调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互为主体式的多声部民族志和对话民族志等书写形式。④在乔治·E.马尔库斯与米开尔·M.J.费彻尔主编的《作为文化的批评的人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一书中将该种类型的实验民族志称之为“现代主义的民族志”。极端的例子是杜也尔(kevin Dwyer)的《摩洛哥对话》(1982)。
在《末日松茸》一书中,罗安清虽也采用了“复调”这一概念,但是却跟上述复调式的民族志有所不同,罗安清借助“复调”论说的是“非进步”的故事。在她看来,传统人类学的叙事多强调某种单一化的演进方向,而复调叙事则试图讲述出单一化之外的故事。就松茸而言,在全球供应链中它没有被完全规模化,而是被诸如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边缘身份以及对于自由的追逐、美日之间复杂的关系史等复调节奏所包裹。松茸的另一种复调节奏表现为其并没有完全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是在与其他物种相互缠绕和人类无心干扰的情境下,与他们共同书写着世界的历史,这种历史不是追求效率和竞争的进步历史,而是多元物种合作共生的非进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