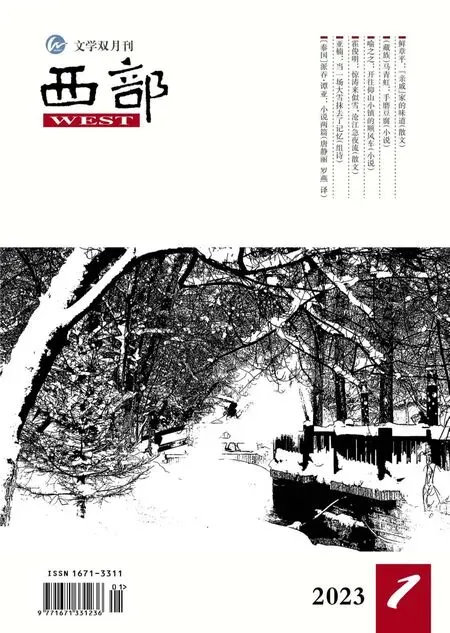花幔
〔泰国〕萝·詹草合萍帕 著
吴圣杨 译
十年前……!
花月十八岁,美得像手里拿着的花。那天是公主的生辰日,她作为年轻一辈的宫女之一,提前去了“外花园”。
宫女们正尽心尽力地布置场地,以招待即将到来的熟客。有的在女生体育竞技场地张罗,有的去迎驾的楼阁做准备,各忙各的,也有好几人因比较熟悉客人,留在接待篷负责接待工作。
用来挂楼阁窗子的花幔还未完工。宫女们串鲜花时喜欢变着花样,习惯成性,所以就连得赶紧串好的普通网格的花幔也不放过,此时还串个不停。花月受不了接待处的喧闹忙乱,说话的时候,偷偷把流苏系到花环上,差不多快干完活了。
“真漂亮,花月。”一个熟悉的声音夸道。花月循声望去,看到说话的青年男子,脸红了。过了好一阵子,对方俏皮地笑道:“我是说你的流苏。”
“喂!你乱说,尼帕。”另一个面容严肃的青年男子打断了他的话,“等她把花环并到花幔的时候,你再夸不好吗?那时才能说好看。你瞧,主体部分在下面,末端在上面,你还说它好看。”
“你才不会看呢,德查,”名叫尼帕的男子幽默地回道,“花月的流苏是真的好看嘛。”说着,他擅自从盘中拿起一串说,“施舍给我吧。”
“糟糕!小心点儿尼帕,都掉了。喏!那边喊了。你瞧,德查哥!”她朝表情严肃的男子抱怨,“玉兰掉了一朵,喏!看看你朋友干的好事。”
德查弯腰去捡。
“尼帕,你要一朵就行啦,别想着要整串。一会儿花幔毁了,我就得跟着倒霉。”
尼帕摇头。
“捡的我不要!是鲜花就得硬要才好。”
“硬要才好!”这句话含义深邃,那天花月没想太多。后来,她想起来的时候,心里掠过一丝苦楚。
“我自己来,有的捡总比没有强。”德查自言自语。
“德查哥真好!你喜欢捡掉下来的花吗?”她笑问。
“还行吧。拾遗的花儿,想闻就闻,想扔就扔。”
“想闻就闻,想扔就扔!”德查要是知道这句话将来某一天会搅乱自己的心情,他肯定不会说了。
“我这么喜欢花,你倒是不问。”尼帕故意逗她,“花月真无情。”
“等搞完活动,我把整副花幔送给你。”
“那我就去你家讨去。你现在不住宫里了,是吧?”
花月见德查哥的脸紧绷着,于是没有直接回答。
“我一个星期还要去宫里几天。你和德查哥一起去家里也行,德查哥常在家住。”
“德查哥!”尼帕对着正在摆架子的朋友说,“从今天起,我拜你为师,做你的爱徒。以前没见你邀请我去花月家。”
德查忧心重重地望着花月妹妹天真烂漫的脸。
“我担心姑姑会头晕。她习惯清净,不喜欢我们带客人到家里闹腾,对吧,花月?”
花月端起流苏花盘起身,准备去楼阁。她答道:“是的,除了德查哥的客人。”
我们来说说尼帕·蓬萨尼这人。他的家世背景和王室有关,因此德查和花月的姑姑,也就是君拉雅,把他和别人区别对待。于是,尼帕就有机会经常跟德查去家里“讨要花幔”,虽然从来没有带花幔回去。有时德查没陪着,当他碰到尼帕的时候,就会问道:“昨天去哪儿了,去花幔那里了吧?”“尼帕!听说昨天花幔那里有点心招待是吗?”
结果,自从公主生辰庆典之后,“花幔”的意思变了。
至于君拉雅·文班亚,她年轻时曾为宫女,后来因为要抚养父母双亡的侄女花月,不得不辞去宫中职务,像个修女般深居简出,在家怡然度日。她是花月父亲的姐姐,是德查父亲的堂姐或堂妹。花月记不清小时候的事,只知母亲叫占达拉,父亲叫布沙,均已去世多年。
君拉雅曾接受过较高水平的泰式和西式教育,年轻时总在上层社会的社交场所出入,思想一直很新潮,但很奇怪,她对花月的管教却很保守。花月高中毕业后就在家深造,所学内容主要是家务事。生活的其他方面,花月从没觉得委屈,但好几次因学习这件事深有感触,因为她的社交范围变得很窄了。虽然她不必像年龄相仿的女生们得专心学习,但她也没有该有的社交活动,与异性的交往一直仅限于德查一人,而德查是同一族系关系很近的亲戚。
有一天尼帕进到客厅“里面”,按礼节拜见了姑姑,姑姑不悦,因为德查也跟着。出来后,尼帕在下面招待客人的房屋和花月单独聊天,德查躲到卧室小睡去了。前面说过,花月不太会社交,她不假思索地问尼帕:“您为什么常来?以前不见您像现在这样来得勤。”
“我来讨花幔,你不是说要把整副施舍给我吗?”
姑娘睁大眼睛,双眸像金星一样闪烁光芒。
“当然不是那样的。您不知道我们是开玩笑的吗?”
“啊?不是吧!我真的是来讨要花幔的。花月,你就是永不凋零的花幔,虽遮挡了视线,但透露出清新的灵魂。”
尼帕说完笑笑。自公主生辰庆典那天以来,花月一直记得他的笑容。尼帕说话的时候,她激动地盯着他。
“您是第一个说我很漂亮的人。”
“刚才我好像没有哪个字夸你漂亮吧?”
“但您真夸了!庆典那天您说流苏系在花幔上漂亮,现在您说我是花幔,那不就是夸我漂亮吗!”
尼帕开怀大笑。
“你喜欢被夸吗?喜欢让我爱吗?”
这就是尼帕·蓬萨尼!花月心跳了,连忙毫不掩饰地回答:
“太喜欢了,但愿您真的爱我。”
这对恋人的恋情发展没有一点儿曲折。男方是一个情场老手,女方则未经世事。像风暴一样猛烈直白的情感表白,有时也有魅力。
“我真的爱你!”尼帕说,“我会爱你到地老天荒。”
女方等着他继续说,他却道:
“把扇子递给我,太热了。德查怎么能睡得着!那你的温情哥哥德查呢?”
花月按他的吩咐递过扇子,尼帕趁机用力捏住她的手,又问道:
“德查这家伙,从没跟你说过他爱你吗?”
花月乌黑的大眼睛露出奇怪的神情,但没有否认。她说:
“德查哥曾好几次说爱我……怎么啦?每次我遇到烦心事,比如因为姑姑的原因,德查哥会帮我开脱,安慰我,不让我觉得委屈,他说就算没人爱我,他也会一如既往地爱我。”
“那你为何又要我爱你呢?”尼帕随口说道,“德查一人爱你不好吗?”
花月黯然神伤,望着仍被尼帕捏着的手说:“有什么好的?德查哥爱我就像哥哥爱护妹妹那样,但您……您让我心跳,当您说很爱我的时候,我有种莫名的幸福感……感觉非常不一样。”
他揉捏着她细嫩的手,然后举起贴到自己的脸颊。花月回过神来,连忙收手,但没表示反感。
“他那是把你当妹妹爱,而我把你当花幔一样爱。”
“当花幔一样爱!呀……!怎么爱呢?”
“你等着瞧!”说着他吻了几下她的手,“吻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好多,但你得一直是花幔。”
“我当然情愿当花幔不当妹妹。”花月心想,他说的“还有其他好多”到底是啥?不管怎样,如果能让我像现在这样感到无比幸福,我愿作花幔。
很快花月明白,“其他好多”指的是什么了……!
在德查的陪伴下,尼帕来花月家和她交往了几个月后,终于有机会在家里过了一夜。那天晚上,君拉雅病重。自从医生认定她的慢性肠病已到了晚期后,德查连续好几天住在家里。君拉雅的病情反反复复整整两个星期。当德查、花月还有家里的其他人轮流守夜看护,个个疲惫不堪的时候,君拉雅也没了求生的欲望。那天晚上,当她和德查单独相处时,她对德查说道:
“我老早就把所有的财产留给你了,律师会处理好,他很清楚。”
“那花月呢?”德查压抑着无比的痛苦说,“她可是您的亲侄女……比我跟您还亲。”
病人厌烦地看着他。
“财产和声望,守不住的话就跟没有一样。花月父母守不住财产和声望。你要是还爱我和这个家族,你就得接受这份遗产,并担负起照看花月的责任。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要拒绝我吗?”
德查沉默了一会儿反驳道:“能不能给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为什么我继承了本该属于花月的财产?我虽不如姑姑富,但还不至于要这样霸占妹妹的财产。”
“我留给你的,怎么能说是你霸占呢!”年长女士努力地说,“但主要是因为花月不是你以为的亲人……她不是真正的文班亚家族的继承人,她是她母亲占达拉的私生子,不是布沙的亲生女儿。”
“姑姑!”德查情不自禁喊道,接着镇定地说,“我听说占达拉婶婶不仅貌美,人也很好呢。”
病人把目光转回蚊帐顶。
“但是她的丈夫和情人不好。”
病人接着说:“她的丈夫只顾自己吃喝玩乐折磨妻子,而她的情人只会伤害她。这个女人多愁善感,像花一样要人闻、要人问。占达拉想认错,但我问过那个情人,他不愿意公开两人关系,所以我没让占达拉向她丈夫坦白。说了也没用,布沙从来不去想女儿是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去赛马场赛马的时候因血管爆裂死了,占达拉生下女儿也走了,把这个无辜的小孩留给我抚养。花月太像她母亲了,你得好好照顾她!我想……想让你俩在我走之前把婚结了。后天……行……吗?就邀请亲戚来就行了,我病成这样,人家不会介意,他们会以为我就是想在走之前把侄女安顿好。那么财产是谁的就不奇怪了,只求别……别让花月知道家丑就行。”
因为用尽了气力,病人说完就昏睡过去。德查没来得及反对,他起身去把护士叫回来看护病人,自己想溜到下面客房休息会儿。他想好好思考一下怎么跟花月说明仓促结婚的事。
大楼建在高地上,周围种着芒果树,屋后的石阶通到下面平地。有条小道岔向另几栋房子,其中一栋住着德查安顿下的尼帕。德查靠着芦荟盆站着,心里开始琢磨,长辈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君拉雅·文班亚是远近闻名最注重声誉的人,而他才是家族真正的继承人,怎么从她手里接过这个任务会感到为难呢?在此之前,他从不曾对花月反感。姑姑肯定没怎么觉得难受,因为她没因这件悲哀的事情损失什么,也就是花月母亲和她的情人以及丈夫三个人之间的丑事。
想想就觉得身为丈夫的布沙真可怜!他应该也爱妻子,谁不爱……像花月那样的女子呢,花儿一样纯洁美丽,仙女一般温柔善良!但是花儿和仙女是取悦人的事物,被用于创造爱情故事和梦,自然会被玷污而失去光彩。因为现实生活也好,爱情和梦想也罢,都是不洁之事!女人就像花……或者花幔,把所有的难看掩在背后。即使未沾染爱情和世俗污浊的君拉雅,也不得不长期像花幔一样遮掩着丑事。花幔……表面上看美丽动人,但假如有一只手伸过去揭开这副掩盖女人真实存在的花幔……若用情去揭开,我们会看到什么?是不是都像占达拉那样的爱恋、痴情和对生活失望?历史会不会重演?
“有其母必有其女。”
德查想起这句老话心里一紧。花月身体流淌的血里带有花幔多情的基因,能躲开这个普遍的规律吗?花幔!他从哪里听到这个词的?花月曾经很高兴被夸像花幔。谁夸她的?情场老手和深谙世事的尼帕!他从一开始就直言花月是花朵。现在德查不能对这件事视而不见了……假如他得保护家族的名声,就得像君拉雅一样把所有的秘密掩藏在花幔之后。
一阵鸡叫声惊动了月光下发呆的他!
德查意识到自己在石阶上站到深夜了。原本想溜到下面房屋休息会儿,看来不行了。
“得把花月叫醒才行。”他想,“正好她要起来接下半夜的班看护病人,看看后天的事怎么办,免得说我和姑姑擅自决定太欺负人。”
德查抬手对着月光看了看手表,正好夜里十二点!从晚上七点他上去接班照顾姑姑算起,花月已经美美地睡了五个钟头了。除了在楼上陪护病人的人,估计谁都睡得很香。德查正准备按照原来的想法上楼叫花月,却瞥见远处一个白衣身影急匆匆地沿着楼下那条小道走来。
楼下这条小道两边葱郁的无忧树正开着花,花香弥漫在空气中。小道通到大楼后梯右边的南梯,从那里可以上到花月的卧室。德查见白衣影子像鬼一样,埋头向前径直走向南梯。德查下意识地从中间梯子跑上楼,然后抄走廊近道拐到花月房间那边。没人在,每个房门都是紧关着的……除了花月的房间门留有一道门缝!德查像精神错乱的人一样开门进去。脚被门口金边产的折叠屏风绊了一下,“哐当”一声。床上透明的蚊帐里不见花月,苍白的月光照着空寂的房间。德查坐在床边,眼睛盯向大开的房门。
白衣影子踮着脚慢慢走近床边,双颊泪痕清晰。
“德查哥!”白衣人僵硬地站着,“德查哥!”
“过来这儿,月。”德查拍拍床,“从下面房子来吗?和尼帕待了几个小时?和他在哪里聊天呢?还穿着睡衣!我到你房间来不见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偷偷到下面房屋睡的?”
“我……我……见……就见他一会儿。”
“夜里!”德查起身,眼放怒火,“夜里一会儿!谁敢保证你不是过去两三个钟头了,傍晚楼上照看病人,下班后到下面房屋值夜班!”
“德查哥!”
“就会说这句话!德查哥!德查哥!见鬼去吧!我就是吃别人剩饭的人!妈的!花幔……花都掉光了吧,眼泪一次性流完是吗,月妹?”
他抓起她的一只手臂,紧紧攥住,花月蜷缩着坐到床上。
“有其母必有其女。”他低头耳语,“当丈夫的可怜吧?但这个丈夫不像那个丈夫。”德查忘了她不知道那件往事。怒火把他燃烧得像疯子一样。花月想掰开他的手,但无济于事。她的脸红得像狸红瓜。
“哟……!丈夫?德查·文班亚而已!休想,富翁先生,谁叫你来找我的……说做我丈夫的?”
花月用另一只手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
德查的神经本来就紧绷着,最后这记耳光,把“温情德查”变成了“凶狠德查”。花月感觉被他从床上拎起来,锁在双臂中。一开始,花月以为他会扇回她,于是闭眼等候,结果等到的是疯子的狂吻。在铁钳般紧夹着的双臂中,在强烈的亲吻夹杂着咒骂中,在两个剧烈跳动的心脏中,在一阵混乱中,花月知道了尼帕最近说的花幔之价。
“你是花幔……是遮人眼睛但透露内心的帘幔……爱你到地老天荒……温情德查……他爱你像爱妹妹一样……我爱你像爱花幔一样……亲吻是其一……还有其他好多……”
确实是!还有其他好多。当花月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还隐约听到德查在她耳边咒骂:
“母女俩一样淫荡……一样坏……!但第一个孩子得是老子的,好吗,花幔女?老子好就好在残羹也吃,剩饭也捡……哈!但好歹得吃得像丈夫一样……老子来捡残余的尊严!……”
天明月落之际,月光还映照在楼南房间透明蚊帐里的一张脸上。那张脸又一次红了,像发烧病人的脸,两边还挂着泪痕。
君拉雅百日祭这天,文班亚夫妇都在灵柩间。
德查·文班亚盘腿坐在地毯上和最后到场的一位长辈客人说话。花月·文班亚坐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看着仆人们整理槟榔盘。这对夫妻总喜欢各自待着。
“德查,君拉雅的头脑看来还像原来那样清醒,”客人说,“临走前还能把侄女门当户对地安顿好,看到她嫁人。那天你们办完婚礼,第二天晚上又得邀请宾客来是吧?”
“是的!姑姑第二天早上走的,招待客人的物品几乎不用收。”
“节奏把握得很好!”客人夸道,“就可惜没来得及看到侄孙出生。”客人笑着望向花月。德查心像被针刺似的一紧,但没说什么。客人告别走后,德查撑地收腿,然后抱膝坐着,面带愠色,像个老头。
德查回想起那晚。三个月比十年的时间还长。
为什么呢?日子太长了,不就是因为苦闷吗!做错事的人,不仅是他、花月,还有尼帕,但他比谁都痛苦。结婚那天,他见尼帕忙里忙外帮助招呼客人,然后当天辞别去了外府。他见新娘花月打扮得清纯美丽。他见什么事情都安排得很妥当,好像已经筹备多年。他没有怪怨尼帕,没再和花月纠缠那天晚上的事,除了第二天在病房外再次见到花月的时候,他冷冷地问道:“见到姑姑了吧,她跟你说了什么?”
“说了,我们明天一定得结婚,就请关系比较近的亲戚来参加仪式。”
“愿意吗?”
花月沉默许久,最后天真地反问他:
“还有的选吗?”
见德查绷着脸不说话,她继续平静地说:
“第一个孩子一定是德查哥的。”
花月看到德查双眼流露出某种神情,她几乎吓倒在地。德查见花月猛地后退,笑问:“你觉得孩子会长得像谁?”
花月好想扇他一记耳光,然后跑去跳楼。她想起尼帕的话,越发崩溃。“吻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好多”,这句话是头脑里的风暴,吹得她心都快碎了,魂也快飞了,感觉自己像花幔一样,被挂起来的时候还很光鲜亮丽,人见人赞,庆典一结束,便被取下来丢弃。
“就像花幔,”花月含着泪,“因为他没有机会选择理想中的父亲。”
结婚后的前两个月,花月极其悲伤,谁见了都以为是君拉雅去世造成的,但德查知道有好几重原因。一是尼帕无情地离开,二是花月对自己的妻子身份不确定,还有,他好几个晚上住在原来的地方,事先没有告诉她一声。他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每次他翻身,花月总像被谁掐了一样突然惊醒。但上个月,花月就睡得像个婴儿,看他时眼光像他母亲多过像他妻子,而且花月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情绪外露。德查无比恼火。
“尼帕先生来访。”女佣人彤素在旁边说。
“哦?”德查只说了一个字就停住了。
“尼帕先生从宋卡回来,晚上九点才到,他想上来见您。我说您和夫人都在楼上。”
“多事!”德查说。
“请他到楼上来,彤素。”花月说。
彤素觉得德查说“多事”这句话的时候,是泛泛地说,没有特指谁,所以她欣然听从指示,下楼去请贵客上来。
尼帕·蓬萨尼滔滔不绝地说到深夜。
他没有一丁点儿羞愧的样子,这就是尼帕·蓬萨尼!花月只听他说了半个小时,就睡觉去了。
尼帕走之前,聊到她。
“花月看起来比以前精神多了,德查,真的!要不是见她有身孕了,我还想追她呢。”
德查的脸即刻变黑,有种莫名的惊恐使他声音有点发颤。
“花月怀孕了吗!你怎么知道?”
朋友笑得全身乱颤。
“傻瓜蛋!她肚子这么明显,谁都看得出她怀孕了,你不知道吗?要当爸爸了还这么糊涂,连我都不如。”
“你厉害!”德查望着尼帕,“你是主角当然知道,我就是个配角,所以才糊涂。”
“德查!”尼帕提高嗓音,然后想起什么,“你有什么理由这么说!”
“理由!理由就是姑姑去世前两天,花月去你房间和你偷偷摸摸待到半夜……没错吧!你想否认就当着姑姑的遗体否认吧。”
尼帕朝君拉雅灵柩俯身跪拜,然后说:
“没错!”他声音颤抖地说,“但你只说对了一部分,我曾经对花月有非分之想,因为我不知道你爱她。问她也没问出个什么,她像个未经世事的小孩一样,那天晚上……”他停顿了一会儿,“那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半,我躺在小屋前的椅子上等她,一直打盹,她站在身旁叫了我几声才醒。她脸苍白,浑身发抖,哭着问了我一些七七八八的问题,比方说,真的爱她吗……我说是的。接着问假如她一分钱财产都没有,我还爱她吗……我还说是的。又问如果她没有家世背景呢……我又一次保证。然后问我能否当晚带她私奔,我让她给我一年时间。她说当晚她非走不可,只要我带她离开曼谷就行。我只好跟她坦白我不能当晚就娶了她,我还得依靠父母扶持,让她再等一年或者六个月。她望着我好像望着偷腥的猫,最后说:‘这就是你说的爱我像爱花幔一样!这就是你说的还有其他好多!很好!很高兴全都知道了,那我就靠自己了。’”
“我确实曾经那样哄她,所以我怎么摆我的理由,她就是一味地坚持她的想法,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事。”
“我知道。”德查小声地说,“后来呢?”
“她跑回大楼,我怎么叫她她都不理。哎!德查,事情都还没说明白,要我睡眼惺忪地拐带一个大家小姐私奔也太难为我了吧。事情就是这样。我想不出你为什么会认为花月做出了那样离谱丢人的事?”
德查沉思,尼帕继续说道:
“那你干吗还要和她结婚?然后……然后……和她发生关系?你也太不可理喻了!”
“我有我的理由,不能说。”德查为自己开脱,“奇怪的是花月任由我怎么骂你和她,一点儿都不反抗,怀孕了也不说……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尼帕怜悯地瞪着德查。
“你一向那样,你老婆才懒得跟你说话。哪个女人能像玻璃一样通透,让我们男人看得一清二楚。否则她能像花幔吗?再天真,也有不少隐秘的事情。你可能没给她好好说话的机会吧?你霸道,她就只好闭嘴。她处罚你的办法,就是看戏一样看你一个人窝火。”
德查沉默了,最后说:
“今晚住这儿吧,尼帕,明天再聊。”
尼帕马上拿起帽子和手杖。
“就一个晚上够了,老兄,再加一个晚上我害怕。我不想第二天晚上再听你诬陷我是你孩子的爹。”
尼帕走了。德查在卧房门口踱来踱去,许久才硬着头皮进房,没想到花月还躺在床上看书。德查进卫生间磨蹭好久,出来后在梳妆台继续慢慢吞吞扑扑粉,抹抹花露水。花月关了床头灯后,德查才在梳妆台前说:
“刚才和尼帕聊天,知道我们聊了什么吗?”
床上没有回音。
“就是那天晚上的事!你醒来去接班看护姑姑了吗?”
“去了。”
“偷听了全部的对话吗?那个秘密?”
“全都听到了。”
“不像话,我去你房间找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搞得我误会。如果你说听到姑姑说的话,我就知道你没有去尼帕那里待多久。”
床上又好久不回应。
“为什么有机会不解释,让人以为我不好?”
“为了让你知道我母亲不得已才那样做。一开始时,我的念头是不好,但没到那个地步,我仍然是好人。母亲骨子里可能根本就不坏,她可能原本是好人,但命运让她后来变成坏女人,怎么能说她骨子里坏呢?那天晚上你太伤我的心了!我没机会解释,而且……而且也觉得自己不好。实际上让我变坏的是你,我的好哥哥!”
梳妆台那边许久没吭声,床这边也保持沉默,最后梳妆台那边出声打破了寂静。
“过来这儿,月。”声音像那晚上一样强硬。
床那边仍然没有反应。
“怎么啦,”德查埋怨,“过来一下不行吗?”
“为什么得我过去?”床上的应声显得特别骄傲,“你得过来我这儿才对。”
“哟!现在有啥了不起的,得让老公爬进去见。”
“哦,花月现在是文班亚夫人了嘛!而且正式成为文班亚家族后代的母亲了……怎样!”
梳妆台那边急切地问:
“啥时知道的……呃……我是说文班亚家族后代的母亲?”
“确切地知道是上个月,刚好三个月了。”
“难怪睡得像个孩子似的,神气得像只孔雀。”
床那边没答他。
“会像谁呢,这孩子……?难道会像花幔?”德查笑着嘀咕。
“还像德查哥呢!来睡吧。”
德查乖乖站起身来向床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