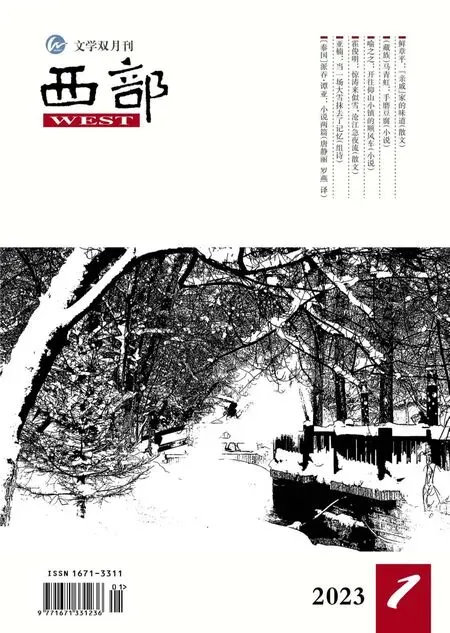转圈
刘畅
一
因外地有疫情,寒假过后,女儿推迟一个月返校。女儿回校后,我松了口气——那口气原本是吊着的。我从容不迫地清洁打扫,扔掉女儿书桌上的双眼皮胶等零碎杂物,收拾好床铺,叠好衣橱里的衣服,躺在女儿的床上伸了个懒腰。
周五下午,女儿打电话说要回家,她在家附近的教辅机构找了份教小朋友画画的兼职。我和他去学校接,车停在校门口,空旷的路不时有电动车、汽车经过。女儿走出校门,长发披散,脸上涂着粉底,眼线用黑笔勾画,靓丽又冷峻。女儿上车后坐副驾驶座,手里捏着手机。我坐直腰身,瞟了眼她的手机,手机里的表格中是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据。
他问在哪儿吃饭,说家附近有家菜馆没吃过。车开到漓江路,他停车,我和女儿进菜馆。服务员递过菜单,海鲜套餐,人均四百至八百元。我看菜馆的环境,不值。他也觉得贵。我说,你不能吃海鲜,算了吧。他犯过痛风。他出门后抱怨,我讨厌他时不时地抱怨,恼火得想踢他一脚。他另找了家盐城菜馆,三人在小包间里围着圆桌坐下。女儿闷坐着,我问是否有事。女儿说上铺的女同学谈恋爱了。我说和你有什么关系。女儿说女同学每晚一两点还在打电话,让男朋友赔礼道歉,说怎么不跳楼去死。女儿说她在宿舍做设计,女同学问东问西,说躺平不挺好,女儿只好买张小桌子放在床上。我说是挺烦人,影响你们睡觉了吧,宿舍里的其他女同学什么意见。女儿说她们也受不了,但都不愿说。我说找辅导员?他说让孩子自己解决,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还说周围越吵闹越考验定力。女儿说你说得倒轻松,换你试试,她电话要打到何时,难道要等她谈恋爱分手才行?他说不要和同学闹矛盾,请同学吃吃饭,多关心关心,她或许正苦恼呢。女儿说下学期租房住,你们别拦我。他说女孩子租什么房,你可以回家。知女莫如母,我知道女儿遇到了不开心的事。吃了饭,我看女儿心情好了点,轻声问她综合评分出来了没有。女儿大一获得过一等奖学金,大二更加努力。女儿说二等奖学金,我以为我分够高,没想到还有人比我更高,我有压力了。我说没拿到一等奖学金不高兴吧,女儿说自己根本不在意。
一星期后南京有了疫情,学校停了线下课。女儿打电话说想回家,说上铺的女同学已经回家了,同班的男同学请假连夜“逃”出南京。我说,上铺的女同学回家了,没人吵你们,不正好吗。他说,你考虑清楚,回家就回不了学校。女儿主意已定。正好女儿佩戴的牙齿保持器裂了缝,口腔医院停诊,但可以处理紧急情况,比如制作保持器这样简单的操作。我打电话给辅导员请假,晚上和他去学校接女儿。
二
他回安徽看望患脑梗后生活不能自理的爸爸,我让他快回南京。他刚回家第二天,他老家查出一名阳性,小县城开锅了,连夜做核酸。南京这边,社区网格员打电话,让他3+11居家。我犹豫着要不要报公司,周一工作多,有份报道要交总部。公司让我居家办公,三天两检。居家两天、周末两天,再下周,根据政府要求,公司通知继续居家办公。十二天不用去公司,我不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每天在家,我依然保持着工作状态,收集防疫照片,写新闻稿。新闻标题要新颖,小标题整齐对仗,我像要上战场的战士,保持着满血状态,赋予文字以力量,但我已到了失去力量的年龄,两个不同的我随时切换,被瓜分得支离破碎。我明年五十岁,有人说五十岁是新的开始,尤其是女性,对物质不再有过多的追求,不再被情欲困扰,不再依赖男性,在精神上走向独立。我曾经充满活力和能量,工作之余,写诗画画摄影无一不尝试,还时常参加画展艺术展文艺沙龙。我讲究衣着,冬天大衣高跟鞋,夏天套裙连衣裙,首饰成套佩戴。一次,媒体的朋友看到我说,你别忘了,你到哪里都有光彩的啊。朋友的语气带着肯定,也带点遗憾。我老了吗?憔悴了吗?没有自我了吗?我害怕不再具有吸引力和爱的能力。更让我痛苦的,是无法保持专注和平静。
女儿中午起床,吃过午饭后坐在客厅的长桌旁做设计。她每天除了吃饭喝水去卫生间,就坐着。客厅里原本有电视、组合沙发。春夏季节,躺在沙发上,风从窗口吹进来,皮肤凉丝丝的很是惬意。但坐沙发有个麻烦,得不时整理沙发坐垫,不然就皱巴巴的,像在客厅里放了张单人床。他俩任凭家里怎么乱,都泰然自若,我像个老妈子似的跟在后面收拾。家里养猫后,沙发扶手被猫抓破,只是一处小缺口,也显出破败来。我扔掉了被猫抓破的沙发。有次外出游玩三天,留下猫在家,猫在长沙发上拉屎撒尿,我反复擦拭,客厅里依然弥漫着咖啡烧焦般的猫尿味,我干脆将这张沙发也扔到楼下。客厅里的电视很久没开,便让他把电视带给了他爸妈。房子里的陈设变了,生活方式也变了。经过优渥的顶峰,日子归于平淡。人生平常事在未曾经历过的人的肩上都是一座山峰,我向下落,落回地面,让我结结实实落回地面的还有工作。我刚进公司在办公室,北京来了新领导后重组专业和人员,一批技术骨干辞职,同在公司就职的家属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被迫辞职。同在公司工作的他辞职的第二天上午,人力资源部打来电话,让我去后勤公司。在后勤公司工作十多年,升职的事总也轮不到我。前几年,配电房女主管提前退休,我也想退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人力资源部咨询。人力资源部主任说我是管理岗,如想提前退休需要提前五年申请转为工人岗,但已来不及,接着讲人力资源政策,听得我云里雾里。后勤公司换新领导后,我这样不上不下的,依然像螺丝钉,时不时被一把螺丝刀拧紧。去年部门调来90 后男主任,我痛定思痛,一改自命清高不食人间烟火的文艺范儿,憋着一股劲完成工作,还努力提高情商,注意言谈举止。主任的心,海底针。我找后勤公司领导。领导说你可以提副主任,他们说你超龄了。一年后主任调至其他部门,吃散伙饭时,两个80 后同事和主任说着亲热话,说要跟主任混,我对他们说的话提不起兴趣,仅出于礼貌在听——不能不合群。主任一支接一支抽烟,一杯接一杯喝酒,包间小,窗又打不开,我被二手烟熏得头昏脑胀。回家后,我几乎无法站立,躺在床上,头痛恶心,肚子咕咕响,脊背疼痛,胸口发闷,喘不过气。我浑身无力,只想躺着,不想动弹,不想说话。我感到大脑缺氧,只有平躺着,血液才能回流到心脏,输送到大脑。他说别中招了吧,明天去查核酸。我给主任发信息说明天请假,有工作微信联系。主任回复:好的,你在家吧,你休息吧。我看着手机里的“你休息吧”四个字,越看越不是滋味,我真的可以休息了吗?
三
清明放假三天,他说天天待在家里死气沉沉,我们意识到不能再闷在家里。他说外出走走,女儿说想拍照,说去看绣球。我问哪儿有绣球,女儿上网搜,说去武朝门公园。我从柜子里找出相机。我让他拎相机,他不乐意,说你想带就自己拎。
转三趟地铁到武朝门公园。武朝门公园坐落于明故宫遗址之上,故都建筑高大宽阔,而今灰飞烟灭,留下来昔日瑰丽的痕迹和日常的烟火气。公园北门附近有块血迹石,装饰有云纹纹饰,我想到“五马分尸”,不寒而栗。奉天门遗址石刻园放着石基座的角座、须弥座,十数个两米见方的柱础。女儿走到雪松下的石头角座旁,双手一撑,爬上去,坐定,头发甩向一边,摆出pose。我刚拍几张,女儿跳下来。我说别动,给我点时间。女儿拿过相机看照片,埋怨道,你不会拍!我想起年少时让妈妈帮我拍照,我也对妈妈说,你不会拍!历史如同轮回。
女儿站在绣球树下,脱掉灰色格子外套,露出苹果绿汗衫。她身后的木绣球树蓬勃舒展,绣球花花瓣匀圆,色泽奶白,花簇瀑布般压向青石雕栏。草地上落着的白色花瓣,重重叠叠如电脑绣花,如手工玉连环。年轻女孩穿着款式时尚质地粗糙的衣裙,在绣球花前欲斗丽影。中年妇女披着围巾,面若脸谱,动作夸张。摄影爱好者们拿着相机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冲到绣球花前按动着手中的快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春色和青春令人恼,刀锋的两面一面是欢笑,一面是愤怒,眼前密密麻麻的人仿佛嗡嗡叫的苍蝇让古朴幽静的公园聒噪不已。
我拍了几张,女儿拿过相机看,加重了语气说,你真的不会拍(意思是不如同学拍得好)。他站在雪松下看手机,衣服松垮,挺着肚腹。他年轻时瘦而结实,现在肉堆在身上。我看着他,眼里露出厌恶。他走过来,说和女儿拍合影。下午三点,阳光偏西。女儿迎着光,睁不开眼。意兴阑珊地拍过合影,我跟着他和女儿漫无目的地走。目之所及,公园里的人都拿着手机,做网络直播的男女拎着直播架,寻找角度,面对手机做微笑、甜蜜状。经过金水桥时,穿白裙的胖女孩坐于桥沿,晃荡着小腿,桥底的水向上冒着凉气。另一个女孩蹲在桥对面用手机帮她拍照。我担心女孩会掉进水里,我总是没来由地担心和焦虑。他走到我身边,拎我肩上的相机,说他来背相机。我恼怒道,别装,你早干吗呢?女儿不知我生气,兴致盎然地指着路边的草地说,在这儿拍,在这儿拍。我猛回头看向她,拍什么拍,你不是说我拍得不好吗?女儿没料到我发脾气,大声道,谁惹你了?你是不是有病?你再这样我就走!我没料到女儿会发火,我只是耍小性子,等他俩来哄,偏偏女儿接了我的茬儿。
女儿转身就走。我知道事情搞糟了,赶紧跟上她。我感到周围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有的人甚至转过头来。我目视前方,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走进武朝门。武朝门是宫城的正南门,是传达皇帝圣旨及朝廷文告的地方,也是皇帝处罚大臣“廷杖”的地方。武朝门由灰砖砌成,逆光的门洞近大远小,门洞尽头是粉色的花、浅绿的树。真美呀!我拿起相机拍摄,一张、两张。构图不错,我给自己点赞。我抬头看女儿,女儿走到了公园南门。她转身看见我,立即向左拐。女儿个高腿长,我个矮,肩上还背着相机,总是跟不上她的步伐。女儿大步走过金水桥,走过石刻园,在公园里绕了半个圆圈。我跟在女儿身后,心急火燎,脑海里冒出“相亲相杀”“最爱的人也是最恨的人”这样的词语和句子,还浮现出刚看过的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的电影《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里母亲和儿子在雨夜街头的画面。我一边走,一边承受着心撕裂开来的痛苦。公园草地上,一块块方型基石如同列队的士兵在时间的序列里沉默不语。女儿走到绣球树下。绣球树像是舞台背景,拍照的人、被拍的人是静态,我和女儿是动态。我和女儿成为舞台的主角,此刻正表演着矛盾和冲突。女儿见我紧跟不舍,索性迈开腿跑起来,她扭动着腰身,长发上下飞舞;我跟在她身后,踉踉跄跄,费力地迈着步子。女儿见我追了过来,加快速度,像一只鹿,跃出公园的北门,离开了我的视线。我停下来,站在公园北门的栅栏旁喘着气。扫码进门的游客像游进海里的鱼,我被惊涛狂澜推到一边,头脑一片空白。
我不明白为何如此拧巴,每天都拧巴,连带着一家人都拧巴,而始作俑者竟是自己?我漫无目的地走出公园北门,对面是明故宫,街道上车辆来来往往。我向右走,看到了女儿,她站在慢车道的花坛旁低头看手机。她在打车?她想去哪里?路口的红灯亮了,一辆正在快速前行的出租车紧挨着斑马线停下。我走到女儿身边,意识到不能再和她争执下去,便把语气软下来,带着祈求的口吻对女儿说,你知道我不舒服,都躺了三天了。女儿说,你有病。我说,是的,快更年期了。你去哪儿,回家?带钥匙没?女儿说,不回家。我说,坐地铁,现在有疫情,坐滴滴危险。女儿说,不坐地铁。我说,那就打车。我看着女儿,我想好了,她到哪儿我到哪儿,绝不让她离开我的视线,至于他在哪儿,我顾不上了。女儿问,爸呢?我打电话给他。你们在哪儿?打什么车?我在地铁口,难得出来一趟,走走不好吗?他寻过来,拎过我肩上的相机:你自己带相机又想让别人拎,不是对人不尊重吗?男的应该照顾女的呀,我心里嘀咕道。
四
我说去前湖,我喜欢湖。女儿也说去前湖。经过中山门,过路口,路右边有条小径,沿小径向里走,眼前豁然开朗,成片的二月兰仿佛为我们预留的惊喜。看着满山坡盛放的二月兰,我的心柔软了,拿出相机给女儿拍照,女儿也耐心地帮我拍,我们的合影显得亲密无间,母女情深。山谷间有曲水,曲水边的木栈道上放着露营用的折叠桌椅,小女孩坐在椅子上,她身旁的椅子上坐着她的小伙伴泰迪犬。
明才子张岱和一干好友聚集山间,每个朋友都带着一斗酒、五盒饭菜、十盘蔬菜瓜果以及一床红毯,依次铺开席地而坐,沿着山坡铺了七十多床。在张岱的日常里,玩乐、饮酒、美食,能繁绝不从简。相比古代贵族的生活,一顶帐篷难以改变现代人内心的匆忙和焦虑,但至少可以暂时放松心情。人们忘记一米线距离,玩耍着,欢笑着。此刻,在心灵深处,灵魂栖居的地方,一种更深刻、更微妙的光在阳光下、草叶上被点燃了,让我忘记了工作和生活的烦恼。在大自然面前,委屈和愤怒多么微不足道。
水从山中来,经大石向下跌落,于平缓处集为水塘,在山谷间蜿蜒成溪。沿水声向前走,前湖边的城墙用钢筋连接,有螺旋形状的梯通向钢筋“桥”。湖面映照着一角天空,一截小桥,一棵灼烧的树。女儿说划船吧。三人套上脱开边线露出泡沫的救生衣登船。女儿坐在驾驶座,手扶方向盘,长发被风吹起,年轻的舵手成熟而理性。船行处,水纹荡漾,前方是桥,右岸是植物园。
湖面有风,他取下帽子让女儿戴。女儿说不用,不冷。船转弯后向西。女儿惊奇地叫道,小鸭子。我沿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一只翅膀还没长硬的灰色小鸭子将嘴巴伸进水里,又展开翅膀离开湖面,划出一条晶亮的弧线,是天鹅。我们看见了天鹅。左边的湖面还有一只小天鹅,两只小天鹅一前一后漂浮在湖面上,享受着天地光华。我看着两只小天鹅,为自己的阴郁感到惭愧。女儿早就忘记不开心,阳光照在她的高鼻梁上,勾画出一道金色的轮廓。船在湖面兜了一圈,他说回去吧,有点冷。思绪的垂线拉离湖面,上岸后,我回头看前湖,湖边的小径被树木遮挡,树下,孙子搀着老奶奶,如同柯罗的风景画。回家后睡了一觉,血液滋养着面容和头发。醒来,我的脸上有了笑容。
又到周末,我问女儿,晚上和我一起睡?不。女儿回答。我进卧室,关灯,刚想睡,门被推开,手机的手电筒光刺进来,女儿扑到床上。我吓了一跳。他听见动静,站在卧室门口问,今晚和你妈睡?我让他把女儿的枕头、被子拿过来。我趴在床上,女儿骑在我的腰上,趴下来喊,妈妈,妈妈。我说,下来。她躺在我身边,把脚放在我的腿上,和我聊天。女儿说我是山顶洞人,又蠢又慢。我说你是什么人,女儿说当然是新潮时尚的啦。女儿说你发现没有,绿茶活得都很好,你向绿茶低低头,她们会给你很多,不皆大欢喜嘛。我说我对自己灰心了,我还能干什么呢?我不忘前嫌,说起那天下午在武朝门公园。
哪有女儿和妈妈那样说话的?气得我脑血管疼。
你才气我,你才让我没面子,我脑血管也疼。
你为什么跑?
你不追,我不会跑。你想过我有多难堪吗?旁边都是人。
你跑我才追,你不跑,我就停下来。你跑出去,让我担心。
我跑出去,你就说不了我。
你站在那儿是想打车回家?你没想到我会过来?
我早知道你会过来,我就要在你面前打车。你上车,我就把你推出去,我就要折磨你。我已经打车了,但没带钥匙,就取消了。
你不是想回家吗?
我不想回家,我出来就是玩的,干吗回家,我就要折磨你。
你干吗让我打电话给他。
我早就看到我爸站在地铁口,他站在那儿,挺可怜的,傻傻的。
我把被子往女儿的肩上拉了拉,转过身准备睡觉。
你不觉得你正在幸福之中吗?女儿说。
五
学校出现了密接人员,宿舍被封控,辅导员让女儿继续请假。女儿居家时间长了,对我和她都是考验。我掐指一算,自女儿回家,每天只睡五小时,睡眠时间和女儿高考期间相同。我站在电子秤上,五十五公斤。我照镜子,穿紧身衣也不显胖。
这天下班回家,客厅的灯没开,窗帘拉起一半。女儿坐着,桌上放着外卖包装盒。我打开客厅的灯,放下包,到洗手间将换洗衣服泡在盆里,拿出塑料袋里的水果和蔬菜去厨房。我想早点休息,只好抓紧时间做家务。我打开冰箱,拿出黄瓜拍碎凉拌,洗净生菜切丝放白醋,洗小青菜,切西红柿,下面条,加热提前炖好的牛肉,洗蓝莓,半小时做好晚餐。女儿拿着苹果平板坐到餐桌前,面色发白,说肚子疼。
吃饭后收拾碗筷,铲猫屎,收拾垃圾,带猫粮下楼,一系列动作如同电脑程序。流浪猫灰灰趴在花园长椅后的矮墙上,邻居扔了件小孩穿旧的红毛衣,灰灰当床铺用。我放下猫粮,坐在长椅上。灰灰吃过猫粮,跳到毛衣上舔爪子,就餐后清洁是猫的好习惯。我抬头看香椿树冠、暗蓝的天空,加深着呼吸。
回到家,我放下钥匙,轻手轻脚回卧室,洗澡,关灯。刚过晚上八点,我累得不想动,躺在床上想睡但睡不着,脑袋里思绪跳跃。我躺了会儿,起床坐到女儿身边,打开笔记本电脑,我已习惯坐在她边,哪怕她的手机里放着抖音。我把手放在笔记本电脑键盘上,像钢琴家弹奏钢琴。我刚进入旁若无人的状态,蜷在椅子上的女儿出了声。
我没参加省赛,我以为难,又要交钱。同学都报名了,有三分之一入围了。入选省赛可以加好多好多分,我来不及了,没时间,没机会了。
你不是不停地做设计参加各种比赛吗?
我参加的是学校的比赛,整个大一我都在忙,不知道做这些干什么,有什么用。
如果太累,就放弃吧。
不是你们想让我保研的吗?女儿反问道。
我愣住了,原来是我不甘心。不想保研就别争取,你既然不想在南京,就考到外地去,一次考不上考两次。
你别想,我就应届考一年,考不上就找工作。
先确定目标,想想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有目标,不知道要干什么。
女儿不再说话,低头专心致志地抠手指。我干坐在一旁,再没心情敲电脑键盘。我看了眼女儿的手指,也尝试着用指甲抠自己的手指,抠了几下,火烧般地疼。“今晚让我绝望。”我头脑里冒出这句。真不错啊,多好的句子。我起身回卧室。女儿说你干吗,快来陪我。女儿总是让我坐在她的身边,问我设计方案如何、如何修改等我回答不出来的问题。今晚,我没因她的叫喊停住脚步。我回卧室,关灯,躺在床上。本以为女儿上大学会轻松点儿,女儿却还和高考时一样忙碌。回想女儿备战高考时,我和他早起晚睡。女儿高考前一星期,他突然痛风发作,走路时只好跳着脚。他去医院开药吃,脚不疼了继续开车来来回回接送女儿。女儿在家,我每天围着她转,做饭端茶洗衣,努力做合格的长工。女儿考上大学,接着考研、找工作,工作后继续,圈越画越大,我们费尽心力地奔跑,依然没能从中脱围。
你写下头脑里转动的轮子
你追赶它,有时你会飞起来
地球是一只轮子,它无法自己跑
人类的手推动它
向日葵是太阳的轮子
车轮发出铁锅的焦煳味
闪电的轮子滚滚而过
带动黑夜的马车转动在头顶
无法理清思绪,我索性打开手机,看法国和奥地利合拍的电影《钢琴教师》,于佩尔饰演女主。女儿晚上回家,客厅没开灯,妈妈早就等候着,妈妈问女儿哪里去了,女儿说去散步不可以吗,我要透透气。妈妈夺过女儿的包,找到一件新买的连衣裙,妈妈打开皮夹,查看支票,说你疯了吗?女儿回房间打开衣橱找衣服,问妈妈灰色外套呢?妈妈说不知道,女儿上前抢夺衬衫,妈妈将连衣裙撕开,女儿扑向妈妈,抓扯妈妈的头发。妈妈坐在沙发上哭,我有心脏病,想气死我你就继续吧。妈妈按着头顶的头发,说这里真的破了,还有这里,你为何这么做?女儿说我真的很抱歉,让我看看。女儿坐到妈妈身边,拨开妈妈稀疏的头发,她看到妈妈破了的头皮,抱着妈妈哭了。妈妈也哭了,说,我没事,我们确是脾气暴躁的一家。
于佩尔的表演的确神经质,我拽着枕头塞在肩膀处,眼皮子沉沉的。不知过了多久,卧室门被推开,我以为天已经亮了,谁知还是夜晚。女儿走进卧室,我背朝门的方向躺着,并不转身去看。女儿进卫生间,猫在门外叫。女儿拉开卫生间的门对猫说,喊什么。女儿的声音柔和了点。她心情好了,不钻牛角尖了。女儿边洗澡边听手机里的音乐。我看手机,零点。我调整好睡姿,闭起眼睛继续睡觉。女儿洗过澡,走到床边,打开床头柜上的台灯。她站在床前,光着脚,头发湿漉漉的。她把手机递给我,看,我入选了。她设计的海报《谷雨》入选青年设计师联盟的设计展。我说不错呀。女儿脸上带着笑,我不想教小孩子画画了,女儿说。你自己决定,按你的意思来。永远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我接着对女儿说,也对自己说。
女儿回房间,我打开手机找公众号,看女儿设计的海报。放下手机,已是凌晨。我闭上眼,不知不觉睡去。四周先是暗的,接着是女儿设计的海报《谷雨》的色调,明媚的春色,一抹半月般的彩虹挂在天空。忽然,天空再次暗下来,周围有人在跑。我本来是歇着的,也跟着跑起来。我跑到松树林,松树下有花盆,花盆上围绕着松毛虫的丝,毛虫围成一个圆圈转下去,没有起点,没有尽头,它们一直转下去,忘了进食,忘了回巢。我跑到海边,一只羊被扔到海里,其他的羊也跟着跳到海里,我害怕也被扔到海里。身边的人都在跑,我不知要到哪里去,他不在身边,女儿也不在身边,没人帮我,我只好迈开腿,以胯部为圆点,先抬左腿,抬高后向后蹬去,再迈右腿,循环往复,像提线木偶。明媚的色彩不见了,雨从天而降,洪水上涨,道路塌陷,我的腿变成车轮般的橡胶质地,身体如同沉船,脚底是黏稠的泥泞,我喘不过气,发不出声音……
六
5月中旬,学校复课,已请假在家的女儿回不了学校依然在家。周六晚,我去钴岭路看展览,我很久没看展览,当然大家都一样。我问女儿去不去,她先说不去,又说去。我快速做好煎牛肉粒、意大利面,盛在盘子里端给她。她发过邮件吃晚餐,回房间稍作收拾,穿绿短袖衫、绿半截裙,她比在学校时胖了点儿。我和她打车到钴岭路。展览刚布置好,海报也是刚贴上墙的,一个男的探头看向窗内。展厅原本是民居,三个小展厅,小厨房改成酒吧间,有间一人位的卫生间。外间展厅墙上贴着九十九张揉皱的白纸,每张纸的折痕都不一样。策展的女孩烫着羊毛卷,穿黑色长裙,脚上是平底皮鞋,脸上带着笑。瘦男孩拿着相机拍照。开幕式用的点心放在“祖母的抽屉”里。葱香饼干像树叶堆积着。气窗外落着枯树叶,像山水画。我和女儿在展厅里转悠,几分钟就看完了展品。女儿上高三时来过展厅,女儿的高中离展厅近,他去学校接上晚自习的女儿,再到展厅来找我。上高中时的女儿穿着校服,朴素而温和,脸上带着笑。展厅靠墙的角落有件视频作品,放在鸟笼里的肺一呼一吸,伴随着女性的呼吸声,柔软的肺挤压着鸟笼的铁丝,粉色的血水印在白色的桌布上。女儿看着视频作品,说不错。她走到门外,坐在长木凳上,我坐在她身边。门外有棵梧桐树,一盏铁艺路灯。艺术家坐在左边椅子上抽雪茄,雪茄燃起,散发着枯树枝燃烧的味道。我坐在门外,耳边响着展厅里的呼吸声,我以为在病房里,而不是在牯岭路,以展厅为中心,四周都是大医院,没有人不在医院里,无论走到哪里,都逃不出去,我感到压抑,这确实是一件好作品。女儿站起来,说走一圈,不回去了。她说就那件作品好,我说艺术家也在,去聊聊,加个微信。她说为什么要聊,看作品就行,不需要认识。
女儿愿意和我一起步行,我打算走得久一点儿。我和她从钴岭路向西走,再向南走,再向西走,路像枝丫一样分着叉,深入颐和路公馆片区的腹地,很容易迷路,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终于找到出口。我和女儿走到北京西路,再沿着北京西路走向草场门桥旁的水木秦淮。远远的,有灯光,墙上的投影里放着巴黎时装周的表演视频。乐队在唱民谣。女儿走累了,坐在露天观众席上看手机。我坐下来,听歌手唱歌,慢慢忘记了肺的呼吸声。广场上,孩子们拿着荧光棒跑来跑去,年轻的妈妈照顾着幼儿。女儿说要吃烤冷面,要不就吃烤鸡腿。我说吃烤冷面。我不愿女儿吃“垃圾食品”,但我意识到需要做出让步,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不也喜欢吃零食吃方便面么。女摊主干净利落地挥舞着手中的铁铲做好炒冷面,抹上自制的酱盛在盘子里。女摊主说,多加了一个鸡蛋,你俩一起吃。吃过烤冷面,我和女儿慢慢向前走,走到草场门桥,走向草场门大街。我们知道必须要去的地方,我们并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