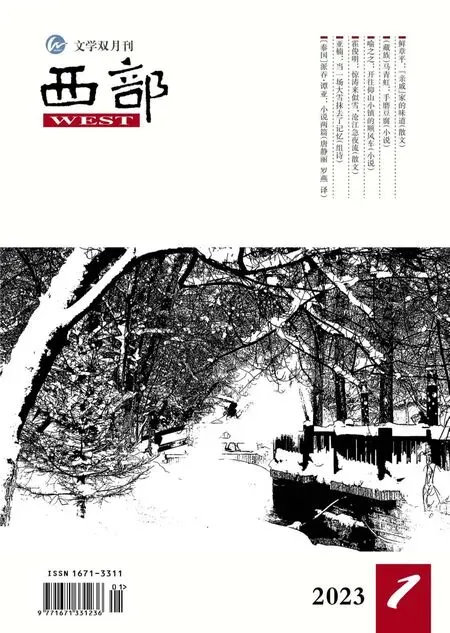手指
周军成
听她们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右手像鸭蹼,手指是连在一起的。是接生婆用一根红线一点点割开的。
这是我妈经常和一些女人们说的。
她们以为我小,听不懂。可我懂,那时我两三岁吧。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停地看手,放在眼前看,推远了看,透过阳光看。
阳光从手指缝里漏过来,先是很少的几缕,然后越聚越多,就像一些哄抢者拥过来,很快指头就找不见了,然后指头和我一起被光吞掉了,再然后我就看见一个我从没到过的地方,见到一些从没见过的人。
这么多年了,我还是这么看着手,担心手指会再长到一起。我想,如果不看着它们,不紧盯着它们的话,它们说不定真会往一块儿长。
我的手指虽然没有再连回去,我的记忆却不停地往回走,路过我的童年,我父亲的童年,以及更早的岁月。透过指缝,我看见早年的天空、土地、劳作的人、飞翔的鸟,还有从远路上回来的人。
他是我的爷爷,他在我父亲五岁时就去世了。
他只有九根手指,另一根手指被他哥咬掉了。
那年我也五岁,我婆一边抽着水烟,一边说着我爷的事情。水烟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那些事情被那些咕噜声弄得断断续续。
“你爷死得早,那时候你爸才五岁。
“他算盘打得好,能用算盘算命。
“他被土匪绑了。因为咱屋里种了两亩大烟。
“他是被吓死的。”
……
那天是冬天还是夏天?天阴还是天晴?有风还是没风?没人知道,因为太早了,早到那时间里的人没有活着的了。
那天,两个孩子为争夺一串沙枣打起来了,打着打着,一个孩子就把另一个孩子的一根手指塞进嘴里咬掉了。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爷,一个是他哥;一个五岁,一个八岁。哥哥把那根带血的指头吐出来,扔上了房顶。
开始我不信,我只是看着我婆手里的白铜水烟锅发愣,看着看着我就信了。我想起我小时候很怕我大爷,只要看见他,便拔腿往家里跑。我一直不知道这到底是为啥。
后来有人到那片房顶上找那根手指,没找到。是被猫叼走了,还是被鸟衔走了?没人知道。也可能被一阵旋风卷走了,或者凭空就没了。
我婆说我爷是个读书人,虽然少了一根手指,并不影响他把字写好,把算盘打好。每到年节,他是村里唯一能给人写对子的人,在周家寨、两宜镇,很多人都知道他。有一年,他考到了西安的一所学校,什么学校不清楚,清楚的是他因为少了根手指,体检不合格,被学校退了回来。他到底少的哪根手指?没人记得了。
从西安回来后,他想总得找点什么营生干,便挑起一副油担子,走村串巷去卖油。不知道他读没读过“卖油郎与花魁”的故事,可能读过,也可能没有,而村野间不可能有什么“花魁”,更不可能有那种美事儿等着他。他早早地挑着担子出门,晚晚地回来,可就是没卖出多少油。
几天后,他卖油卖成了笑话。
可能因为不好意思,也可能是他根本就没动脑子,他挑着油担子走得很快,到村巷里喊一声“卖油喽——”,喊完就挑着担子走了。他边走边喊,等人家拿着钱、碗和盆子从家里出来买油的时候,他早就走远了。村里人说他干不成啥事儿。
家里那时有六七十亩地,只有一个长工,他总不能在家闲着。他是个读书人,但不是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身体还算不错,人也勤快,就开始去干地里的活。
他经常天不亮就去地里。早春的一天,天色灰暗,没什么星光,也没有月亮,天被裹在很厚的云里。他摸黑起来,赶着一头牛和一头驴准备去耕地。家里有一片地在村子的东北面,要过一条深沟,也可以说是一条深谷。深谷两侧的土崖上,有不少洞穴,有些是野鸽子、燕子和野物的窝,有些就不知道是什么了。谷下的路本身就是一个陡坡,从深谷里出来就到了塬上,往左拐再走一段就是家里的地。继续往东的路是通往乌牛乡(现在叫范家镇)的,再往前走就是黄河滩了。这片黄河滩附近,藏着十八股土匪。
他赶着牲口,从村子里刚出来,就被两只狼跟上了。狼在村口可能已经等了不少时间,终于等到有人出来。狼把自己藏得很好,把声音弄得很轻,并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像是经验丰富的特工,让前面的人和两头牲口没有一点察觉。
他走到地里,套上牛开始耙地,耙地扬起的尘土让他更看不清两只狼正向他靠拢过来。当他忽然看见四只发光的眼睛,狼已经离他不远了。他想,是狼,仔细看,就是狼。这时,牛停下了,愣愣地站着,边上的驴已经瘫倒在地。
两只狼站在他两边,没有嚎叫,一起向他冲过来。他挥舞着皮鞭,狼后退几步,似乎在想新的策略。在它们还没想出来的时候,大路上有了马车的声音和人的声音。两只狼不舍地离开了,边走边看,渐渐地走远了。
那年月,乡间的狼多,经常有孩子被狼叼走。当村里的青壮年下地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在家的时候,狼会悄无声息地进到村子里,叼走家禽牲畜和孩子。在野地里被狼围困,也不算什么稀奇事儿。
我四婆,也就是我爷的一个堂嫂,小时候就被狼叼走过。一天黄昏,几个两三岁的孩子在打谷场玩耍,大人就在不远的地方,一只狼从身后扑过来,大嘴咬住了她的细腰,然后叼着她向北面的山坡逃去。她哭叫挣扎着,把旁边的孩子都吓傻了。她凄厉的哭声也把一边的大人惊着了。有人看见了狼,喊:“娃被狼叼走了!”拿着铁锹、叉子、扁担的村民开始追狼。狼叼着孩子,跑不快,追赶的人越来越近,狼撂下孩子跑了。因为人追得急,狼没来得及换口,我四婆有幸活了下来,但是她的腰上一直留着两排狼牙印,伴随了她的一生。
夏日的一个黄昏,我舅爷为孩子过满月,我爷去两宜镇喝满月酒。酒后,他晕晕乎乎地往家走。到村口的时候,他没进村,而是向那条深谷走去。他要去看看塬上的那块地,大片的苞谷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罂粟花。他种了两亩罂粟,前一年开始种的,收得不错,今年周边的村子有些人家也在偷偷种,刚刚开花。他穿过高高的玉米地,拨开正在抽穗的玉米秆,向里走去,走着走着就有了便意,他便解开裤带脱裤子蹲了下去。有人拨开一层层苞谷秆走过来。他感到有点不对劲,提起裤子站起来向周围看了看,什么也没有,只有风把苞谷吹得来回颤动,便又蹲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觉得一阵风向他刮来,不,是人。
“谁?”嘴还没闭上就挨了一脚。紧接着,他的头被一根硬物敲了一下,他便什么都不知道了。他被绑了,装进麻袋,扔上了一驾马车。
他从两宜镇的南门出来时,看见过一辆马车,还有两个骑马的人从他身边过去。他向谷口走的时候,那两个骑马的人迎面回来了,与他擦身而过。他没觉出什么,其实他已经被人家盯上了,人家在他跟前晃悠了好几次。
“他被‘胡子’绑了。”婆说,“那年咱屋里种了两亩大烟,要不你爷也不会被绑。”
那时,百姓们谈匪色变,黄河滩有不少土匪,至于是哪股土匪绑的他,弄不清楚。只要被土匪绑了,就不容易活下来,即使把赎金付了,人也不见得能活着回来。在沙苑,有一曹姓的大户,当家的被土匪绑了,要两千大洋的赎金,曹家一时没凑够,土匪就把曹大当家的的脊背用刀划开,浇入油用火点燃,他受刑不过跳进一旁的井里,人被捞出来后就死了。曹家人拿着两千大洋和几包烟土,只领回了当家的的尸首。
我爷知道自己被土匪绑了,想着自己活不了了。那天天黑,土匪的马车经过一片墓地时,墓地里突然窜出一只狐狸,从马车前穿了过去。马不知怎么就惊了,狂奔起来。颠簸中,有个麻袋掉了,摔在了地上。马车上摞着好几个“肉票”,掉了一个也没引起土匪的注意,或者嫌再找回来太麻烦。我爷逃脱了。
我爷躺在麻袋里。麻袋的口是系着的。他躺到了天亮,被上坟的人捡到了。人家解开麻袋上的绳子,把他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吓得不会说话了。他被抬进跟前的一个村子里,村里竟然有人认识他,他被人送了回来。
他躺在炕上,一直没有下来。
一天,他似乎醒了。伴随着病痛、阴暗和草药的味道,他撑起身子,对我婆说:“把算盘拿来。”
“算啥?”
“命。”
“算盘咋能算命?”
“我算算。”
那是一九四六年秋季的一天,他在病榻上打着算盘。算盘声很脆,算盘珠噼里啪啦的碰撞声滚到门外,传到了邻舍和巷子外,很多人都听到了。
我婆说过,我爷不光字写得好,算盘也打得好。他手指飘忽,如一阵旋风。那天院子里真有一股旋风,携带着树叶、尘土和疾病的气味,让窗纸颤抖了那么几声,然后就翻墙逃走了。
经调查,精准农业应用系统在全县的农机专业合作应用达到99%以上,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但由于受使用者文化水平、经济承受能力和传统农业种植的影响,精准农业系统发展缓慢。
算盘声停了下来,周围的声音也停了下来,只剩下寂静。突然,算盘摔破了这种寂静。他把算盘扔到地上,算盘珠四处逃窜……
第二天,他就走了。
我爷的灵柩摆在堂屋中间,被白布、纸人、纸马、纸牛和各类冥品的纸扎物包围着,一旁穿丧服或孝服的人在弥漫的烟雾里或跪或站。天已有些黑了,油灯和烛光昏暗。不知怎么,棺材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仔细听,声音又没了。过了一会儿,有“砰、砰”的声响传来,像是一种硬物碰着棺材板发出的声音。惊恐的气息突然就弥漫开来,人群炸锅了,争先恐后地向堂屋外跑去。他们以为诈尸了。跑的时候,有人跌倒了,有人扭了脚。跑出院子后,他们站在门外议论着:
“真有声音?”
“真有。”
“他在敲棺材板。”
“你说他没死?”
“我咋听到还有算盘声。”
“还有一个娃娃在笑。”
“咋能有娃娃的声音?”
“才娃呢?”
“没见。不知道钻到哪儿去了。”
这时,我父亲也就是他们说的“才娃”,从堂屋哭着走了过来。
那天,我婆和亲戚们在堂屋守灵。我婆试图按住年幼的父亲,让他跪在身边,但他像老鼠一样,很快就溜走了,到处乱钻乱窜。他钻到棺材背后,玩着玩着就睡着了,一只老鼠从他身上爬过,把他弄醒了,他用手拍了拍棺材,觉得声音不大,几乎听不到,就捡起身边的半片瓦,敲了一下,然后两下、三下……他看见人都往外跑,咯咯笑出了声,可他看见所有人瞬间不见了,就害怕了。
那时候他五岁,他被吓哭了。
我婆的那个水烟壶,她不在的时候,我试着抽过,可我抽不出烟来,只会把水从烟锅里吹出来。
“你爷是被吓死的!”我婆说,“虽然郎中和旁人都说是‘伤寒’,但我知道,他是被吓死的,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我问婆:“这烟壶是银的吗?”
她说:“白铜的。”
那时间我觉得它应该是银的才对。那是一九六八年,我五岁。
我没见过我爷,不知为什么却时常想起他,想起那根沾着唾沫的、有着污黑血迹的手指,孤单地在房顶上待着。我想起多年前的那个房顶,以及房顶上的阳光、鸟粪和猫的足迹。
现在我坐在自己家里,已离开千里之外的老家五十年了,但我依然想着那根手指。我自己家的屋顶上有没有一根指头?想着想着我就有点心慌。
这时,我又伸出手看了看。十根指头,一根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