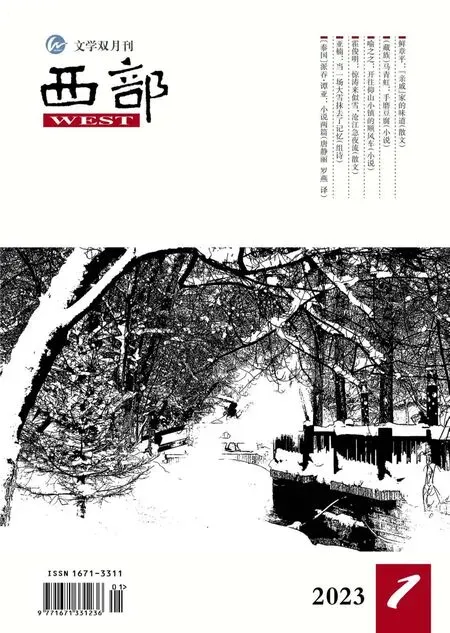稻花鱼
(侗族)陈永忠
稻花奶奶这几天都过来陪公公说话。她劝他把断角的牯牛卖了,他舍不得。
他说,它陪我好多年了,成了兄弟。兄弟,就要一辈子在一起,不能分开的。你不记得了吗?那年还是你陪我到集镇上买的,当时它才两岁,一晃都二十几年了……对了,你的花妹子还能不能抓鱼?
咋个不记得,那个时候,它还是头小牛犊,身上的“旋”长得好,是头打牛的好苗子,你一眼就看中了它。你牵它,它不肯跟你走,它舍不得离开牛母亲。没办法,只好央求主人家配合,把它母亲一起“请”了回来。还好,牛主人就是邻村的,平常赶集都要经过咱村,顺道的事,人家没啥说的。你为了感谢人家,还留人家同你喝酒。牛主人酒足饭饱后牵着牛母亲赶路。小牛犊关在圈里,看着母亲离去,不停地叫唤,牛母亲没走几步,回头应和着不肯迈步,可是哪里经得住主人催促……那场景,跟人世间的母子离别一个样,当时我都淌眼泪了……
这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稻花奶奶说着说着竟然有些伤感。她稍停了一会儿,调了调情绪,接着又说,这么多年来啊,你每回牵牛走过田埂,我抱着花妹子远远地望见你们,那一天就很舒坦,就过得很快。还有,好多次我同花妹子一起坐在斗牛场的台阶上,看小牯牛在围场上打架,我们为它鼓劲,欢呼着:噜噜噜……小牯牛已经长大了,个子高过了你,身段滚圆壮实,毛皮闪着油光,两个角弯得像两把镰刀,身子里随时都攒着一股劲儿,一上场就把对方碰翻在地,差不多回回都得第一名。你看你们得了好多奖旗,家里都挂不下了,你还把几面挂在牛圈边。
嘿嘿,可不是,我的“伙计”是赛场上的英雄,十寨八庄哪个不晓得……你们家花妹子也是不错的,它同你来过几次,我送它鱼吃,它就不想跟你回去了。好几个晚上,我听见它同耗子打架。耗子哪是它的对手,吓破了胆,好久都不见它们闹腾了。我还见它守在稻田边,看样子,它一定是想抓条稻花鱼吃。
那背时的,一有好吃的就忘记回家,没良心的东西,下次不准你再那样惯它。还好,能帮你把山耗子撵走,也不枉你那几条鱼。你看我们两个,想得多合意,我的花妹子帮你抓耗子,你的牯牛帮我犁田,多好啊。春耕时,我那一亩多的大田,你们半天就犁完了。吃晌午饭的时候,我割了很鲜嫩的草,还包了米饭,给你们送到田埂上。牯牛的长舌头在草堆上一卷,像一阵风,嘴里发出脆生生的声音,看样子真饿坏了……还有你呀,饭量大得很,我担心不够吃,洋瓷碗上面还扣了个大菜碗,你硬是吃得一点不剩。
……
公公同稻花奶奶在牛圈边胡乱摆着龙门阵,从眼下到他们年轻时的光景,记忆像开闸的水。说到动人处,两人眯了眼,裂开皱褶的嘴唇,空洞的牙床还歪着几颗老牙,像个刚开始长牙的孩子……画面在阿朵的手机里流动,直播着,她也眯了眼。屏幕上大批粉丝的弹幕像雪花一样飘着,这是山村里没有标榜“爱情”这两个字的甜言蜜语。有个网名叫“渔舟子”的杭州网友说,太纯粹了,不敢相信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纯粹,有机会我要过来看一下。还问阿朵,欢不欢迎?怎么说呢,这人也问得好生奇怪,你要真的来,不欢迎你就不来了?阿朵想。还有,他说的纯粹是什么意思?
阿朵的村庄就是这个样子——
早晨掀开窗,吹进一缕清凉,吹进一阵欢快的鸟鸣。清凉看不见,只看见远山近草,葱绿是寨子的底色,是这个季节的表情;欢快的鸣叫也看不见,不知是从哪棵树上、哪丛绿荫中发出来的。
好久没用心去呼吸这新鲜的空气,去欣赏这悦耳的鸟鸣。张开身体,尽情地伸个懒腰,穿上那件蓝色的T 恤,阿朵拉开木门,“嘎”的一声,外面的人知道她起来了。
后阳沟蹲着的老人在“嚯嚯”弄出声响,也不转头。
朵儿,起来了。
公公不叫她杨阿朵,她爸她妈也不这样叫。就算是朵儿,已经许多年没人叫了。
公公,你恁个早。
年纪大了,瞌睡少。你怎么不多睡会儿?
睡够了,不能再像那几天那样,昏天黑地地睡。
补补瞌睡也应该。前段时间累坏了吧?
公公又要割牛草?
阿朵晓得公公的牯牛还关在牛圈里。阿朵家的木屋,后面靠着山林,林子里杂树丛生,松木、樟树、野枇杷……花草见缝插针,密密地蔓延着。松鼠在树的跑道上奔跑,林间舞台上画眉正在调嗓,蚂蚱伏在草叶上,随时准备立定跳远,蝴蝶的裙摆在野花丛中旋转着——在阿朵的眼里,她家的后山并不是童话,那里曾经有她一段真实的童年时光,只是快要想不起来了。自从上了中学,再没有多余时间和心绪流连于山野。只有发愣的时候,这些画面才会从脑海深处溜出来,那时她会会心一笑。
木屋前面围了圈矮墙,青青的石块砌成,有半人多高。一株月月红倚着门楣,随意地开着,墙上稀疏长了些不知名的花草,它们无所事事,好像专为一缕风吹来,摇一下身子,趁机往墙的那边探一下头。也间或爬了些青苔,足以见证这户农家在这里住得有些岁月了。进了小院门,火砖铺地,站在院子中间,三间大瓦房正面而立,左边厢房,右边粮仓。
墙外左侧不远处,有一小片竹林,牯牛就关在竹林下面的牛圈里。这般好居所,如果是一位诗人,在好多月夜或者雨夜,说不定会吟出很般配的诗句来。它沉默寡言,吃饱喝足后,躺下反刍吃进去的青草。那也是有声音的,只是很小,必须离近了才能听见。
这个时节,到处是庄稼,不便将牯牛放出来。公公每天早晨趁太阳还未起床就出门,割一担带露水的青草回来喂它。公公的牯牛是头打牛,过节的时候要拉出来同其他寨子来的牛斗一场。因此,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绕他的宝贝疙瘩转,把它照顾得安安逸逸。
你自个儿煮点东西吃,在学校吃惯了。
你吃吗?我多弄点。
不要,农村人,你见过哪个吃早餐?做趟活路转来再吃。
阿朵拧开水龙头,白花花的水从那根深色的塑料管子流出来,流在杯子里。管子是去年才拉进屋的,寨子上方一里外的山涧里,有股源头活水,凭着自然的落差,山泉就自动来到了家里,省去了过去担水的劳力。
她也像公公一样蹲在阳沟坎上,“唰唰”地刷牙。洗漱完毕,把昨晚的剩饭剩菜倒在锅里炒热。这时,公公起身出门了。
晚饭是阿朵做的。她把公公的酒倒满,公公喝了一口,有些夸张地咂咂嘴,很享受的样子。
享福喽!自从我的朵儿放假回来,公公就吃现成的啦!
公公觉得朵儿做的红酸汤好不好吃?
好吃,咋个不好吃。你同哪个学的?你爸妈常年在外头打工……
公公还不晓得,阿朵有几天去了对门寨,去跟人学做红酸汤,已经学会了。
公公眯着眼喝了一口阿朵给他盛的红酸汤。嗯,味道还不错……要是再有几条鱼煮起,就没得讲了。
公公想吃鱼了?明天赶集,我去买几条来。
那些鱼呀,不晓得从哪里弄来的,不香,不要。要吃就吃咱们自己养的稻花鱼。
那我明天把门口大田里的稻花鱼捉几条来?
要不得,要不得,还小哩,等打了谷子才成。你想,现在稻禾正在扬花,鱼儿吃了禾下落花,正是长个的时候哪个舍得现在就去捉……哦,对了,你们哪个时候放榜啊?
放什么榜?
就是考没考上大学呀?
这个……朵儿可能没……
阿朵躲避着公公的眼睛,公公也不好再问。阿朵的成绩不好,严重偏科,从考场上下来,她心中有数,就没指望能考上。回到家这些天,在公公面前,考试的好坏她从不提及。公公自知平常关心不到孙女,向来也很少打听她的学习。往后何去何从,阿朵也不是没想过,她翻来覆去问过自己,不上大学,难道就没有出路了吗?
转眼,寨子前面这坝稻田从青绿转成一片金黄。
视频回放着公公劳动的影像——
阿朵一直关注网络直播红人李子柒。阿朵关注她好长一段时间了,她的那些视频同阿朵生活的村庄非常相似。阿朵在心里已经为自己做好了打算。她试着录了家里种地用的各种劳动工具,比如犁耙、锄头、镰刀等等。可是,她觉得视频的画面应该有一条线将其串起来,于是,她想到了从公公每天的劳动入手。
公公,你看你多好看啊,还有你的打牛,膘肥体壮,皮毛油光水滑的……
阿朵把手机移到公公眼前,公公眯起眼睛。
啊哈,两个老家伙,老都老了还录,丑看得很……
视频里,公公先是看见自己牵着牯牛到小溪沟喝水的样子——他佝偻着腰,一只手在背后牵着绳索,一只手扶着烟斗……画面一转,牯牛伸长脖子,鼻孔喷着水气,冲着镜头走来,冷不丁舔了下手机,画面就模糊了……
公公快看,它还看镜头呢,还走过来舔我的手机……
司伟、李雷利用Nerlove供给反应模型估计了东北、黄淮和其他产区的供给弹性,分别为0.98、0.44和0.32。由于查找的文献中,只有司伟和李雷的研究结果涉及目标价格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价格弹性,因此本文将他们的研究结果作为大豆供给弹性的基准值[13]。
真是不讲规矩,坏了不?
没事,公公,快看,又是你——
接下来的一组镜头是公公起床后做的事情。他用木盆从塑料管子里接了水,放在磨刀石旁。这块朱红色的石头也不知公公是从哪里弄来的,方方正正,斜斜地嵌在阳沟边上,由于经久来回磨蹭,石面中间凹两头翘,像块弯弯的腊肉。公公从板壁架子上取下镰刀,蹲在地上,攉水将磨石打湿,右手握住刀柄,左手同时摁住刀背,“嚯——嚯——”一下一下来回磨。磨了一面,反过来再磨另一面,这样反复几次,公公的镰刀明晃起来,端进眼前,拇指迎着刀锋轻抹几下,看锋利不锋利。他似乎还不确信,又将镰刀贴在自己的腮帮子上,往下轻轻一拉,好些花白的胡须掉了下来……公公这个举动有点突然,似乎吓着了阿朵,镜头有点晃动……嗯,可以了。公公十分满意地将镰刀从腮帮子上拿开,又揣进眼前,噘着嘴吹了吹还粘在刀口上的几根胡须,起身反手将镰刀插进腰背的刀挎里,担上草筐出发了……
早些时候,阿朵直播这些场景,屏幕上炸开了锅,网友们表示,太新奇了。阿朵一边播一边解说,这是镰刀,那是磨刀石,镰刀磨锋利了一会儿才好割草……
哇,少见,怎么不用机子割?
这样刮胡子好吓人,太不可思议了,不怕割伤吗?
大惊小怪,一看就知道没到过农村。有人表示不屑。
……
网友们千奇百怪的问题,不可能一一回答。阿朵顾不过来。接着,她的镜头跟着公公到了田坝子里。绿油油的稻浪扑面而来,空气里流动着清新湿润的味道,一些虫子不知躲在哪里,偶尔会发出细细的叫声。稻禾开始扬花了,细碎浅黄,沾着露水,藏在叶片间。窄窄的田埂,人走过去,青蛙慌不择路地往稻田里跳。草尖上挑着亮晶晶的露珠,鲜嫩诱人,公公心上是喜欢的——青草是牯牛的粮食。他放下草筐,从背后取出镰刀,蹲下身子,“唰,唰,唰”,出手干脆快捷,挥舞着的镰刀,刀锋很有节奏地一口一口咬过去,只听见脆生生的声音,所到之处,嫩草无处可逃。每一株草儿握在手里,实在,舒坦。多么鲜嫩啊,公公自己都想往嘴里放一把,牯牛一定很喜欢。他像收割粮食一样,心里愉悦而小心翼翼……公公肩上担着青草,扁担忽闪忽闪地走在田埂上,跃动着的草尖儿仿佛还在肩上生长。
到了牛圈边,公公放下担子,牯牛有些等不及了,将头从栅栏空当间伸出来,轻轻地叫唤着,口水流了一下巴。
饿死鬼投胎啊,有点出息好不好?
公公取笑着他的伙计,赶紧把嫩草送到它嘴里,抚摸着它的头,同它说话……
多吃一点,别着急,还有呢。
牯牛本来正津津有味吃着草,听公公这么一说,它暂停了咀嚼,两只大耳朵往前收了收,眼睛看着公公,舌头轻轻地舔了一下公公的手。
公公腾出另一只手,拍了拍它的脑门说,发什么呆?不好吃吗?
它摇了摇头,鼻孔喷出一股气,又恢复了刚才的样子。
……
牛是这样喂养的呀?以为是吃饲料的呢。
屏幕上,渔舟子弹出字幕。
阿朵又看见他了。
呵呵,吃草,吃青草,农村哪来饲料喂它啊。再说也用不着,大自然就是它的粮仓,阿朵对着屏幕说。
公公同牛讲话,它能听懂吗?
能啊,相处久了,牛通人性。
太神奇了。
没什么,万物有灵。
……
阿朵同公公讲,好多人收看哩。她只能同他这么说,不能说点击率已经有好几万了,公公明白不了。
公公看得入了迷,越看越喜欢,就问,你爸妈能看到吗?你弟弟能看到吗?阿朵说能,都能。哦,对了,公公,网上有个叫渔舟子的外地人还夸你呢,说你帅,磨刀帅,割草帅,养的牯牛也帅。
这孩子,什么帅不帅,用在你们年轻人身上还行……老喽,老喽,别丢人现眼才是……公公摸出烟斗裹了一杆烟。
阿朵又放她同对门寨稻花奶奶学做红酸汤的视频,公公揉了揉眼睛,说这个老太婆……公公笑了,笑得有点害羞。
夜风中飘着淡淡的桂花香。公公烟斗里的老叶烟忽明忽暗,像天边的小星子。
唉,时间过得多快啊!他取下烟杆,忽然问阿朵:
你同你爸妈打电话了没?
打了。他们让我去那边。
你去不去?
不去。我在家陪公公。
我老了,陪不陪不要紧,你自己的事你要想好。
我想好了,我在家也可以做成事的。
阿朵不同公公讲她搞直播也能养活自己,公公明白不了其中的道理。
阿朵只说,过些天有个外地人要来看你。
外地人?为哪样要来看我?
对,就是之前同你说的那个叫渔舟子的人。他看到我录你的视频,就想来听你摆龙门阵。
咱们这里穷,怕吓着他,让他别来了。
脚长在人家腿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人家喜欢你播的,你得感谢人家。
夜很安静,稻田里时不时“咚”“啵”地响着水声。公公说,那是鱼儿在跳动,过些天就可以放水捉了。
对了,稻子扬花那段时间,你录了吗?
录了,可是没看见鱼儿吃稻花。
这些精灵害羞着哩,哪敢当着咱们朵儿的面吃啊。别说你,公公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也很少见到。等放水捉鱼时,你可要记得录,那时一个二个膘肥得很,爱人得很。
这天,公公挥动锄头,将门口大田的田埂挖了个豁口,稻田里的水缓缓向这个豁口流来。阿朵支好手机,将撮箕安在豁口上,以防鱼儿趁机逃跑。饱满的稻穗佝着头,专等人们将它收进谷仓。一条条青背红尾的鱼儿跟着流水游走,以为流水会带着它们私奔,于是拥挤着,弹跳着,浩浩荡荡。这个美好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它们憨态可掬的形象却上了网络,直播到了天南海北,这可不是山村里每一条稻花鱼都能有的待遇。
傍晚,阿朵遵公公的吩咐去对门寨请来了稻花奶奶。
稻花奶奶头发花白,但很茂盛,足够绾起一个高高的发髻。发髻上横插着一只亮晶晶的银簪子。前额还戴了一朵红绸做的月季花。
公公在水龙头下剖鱼。那些膘肥的鱼儿,经过清水退泥,看上去清清爽爽,灵动诱人。公公剖鱼的动作十分麻利,仿佛不是劳动,而是操作一门艺术。阿朵则在灶房同稻花奶奶预备煮开红酸汤。她揭开坛子,舀出红艳艳的汤汁,连同公公剖好的稻花鱼,一起放进铁锅里,架在火堂的三脚架上烧煮。红酸汤是按照稻花奶奶教她的方法早就炮制好了的。
那时,稻花奶奶告诉她,做红酸汤并不复杂,就是将本地的小西红柿洗净,捣烂后放入坛中,一层西红柿一层盐,最后在上面淋点白酒,密封后放于阴凉通风处,发酵一个月左右即可。稻花奶奶叮嘱她,酿制过程中千万不要沾油。阿朵用心记下了,回来便着手独立操作。刚才舀出来的红酸汤,稻花奶奶很满意,直夸阿朵聪明,一学就会。
柴火很旺,火苗子像条长长的舌头,尽情舔着锅沿,不大会儿工夫,酸汤煮沸了。过了一会儿,稻花奶奶让阿朵放入木姜子、辣椒、葱、姜等佐料。
夜晚透着凉意。火堂的火光照在脸上,让人感到一阵阵温暖。铁锅里的酸汤鱼冒着热气,通红的色泽叫人着迷,鲜香扑鼻而来。公公让阿朵给稻花奶奶倒点酒。公公举起酒碗,稻花奶奶跟着举起来。第一句话,他们好像不知道从哪里说起。阿朵给他们一人盛了一碗酸汤,又夹了一条鱼。公公尝了一口,只说,这鱼不错的,这酸汤……公公转而对阿朵说,朵儿做的酸汤好是好,可还是比不了你稻花奶奶,得多学着点。公公夸奖稻花奶奶时,她用手抚了一下自己的脸颊,说这酒劲太大了,脸膛发烫,得少喝一点。公公接过话,谁让你烤这么好的酒送我,都把我惯坏了,别处的酒像喝白水,没有味道。想当年……哎呀,你就别说了,孩子在这里呢!公公还要说什么,稻花奶奶害羞地打断他的话,说今年的鱼格外肥美……稻花奶奶说是少喝一点,到后来她还是喝了不少,然后开始唱起歌来:
久不吃酸打捞蹿
久不打鱼忘记河
久不唱歌难开口
久不喝酒心难过
……
公公受到感染,放下酒碗,起身取来他的芦笙“嗡嗡”地吹……美妙的声音多了一些别样的滋味。两个老人好像完全忘记了还有阿朵在场。
次日,阿朵去看稻花奶奶,回来说稻花奶奶病了。
昨晚还是好好的,怎么就病了呢?公公不相信。昨晚,他们放肆地唱了一回,吹了一回。两个老人都有些醉意了。阿朵送稻花奶奶回去,一路缠稻花奶奶讲讲和公公的故事。老人家真喝多了,但步子还算稳,就同阿朵摆她和公公年轻时的龙门阵——
稻花奶奶有个妹妹,叫稻子。人家说她们姐妹俩是一对寨花。本寨,还有周边的好多寨子,小伙子们都巴望着,要是能同姐妹中的一个对上几句山歌,那一定是很快活的事。可是,两朵骄傲的花偏偏一个也看不上。这让那些年轻人沮丧又没有办法。
稻花奶奶说,朵儿,你想啊,那时,我心中有人了——他就是你公公。你公公年轻时很迷人,纯粹就是一头壮实的牯牛。六月间爱光着膀子,在门口那个大水塘里洗澡,一口气能从塘口游到塘尾。他经常挑柴从我家门口经过,我和稻子常常在阁楼上绣花。当看到他远远过来的时候,我们姐妹俩就相互取笑,你看他那么勤快,油光光的肩臂,像几股粗实的麻绳,多有劲啊!想不想要他做阿哥啊!我们表面上是把他往对方身上推,可是谁都晓得,我们都喜欢他。有一天,我不知怎么的,竟然失手把一张即将绣好的绣帕掉下去,正好挂在他身后挑着的那捆柴尖上。等我急急跑下去,他已经走远了。
命啊,都是命啊。快到家门口了,稻花奶奶摇着头,不说了,不说了……你回去吧,没事,我今天高兴。明儿我过去,帮你把那些鱼收拾了。
怎么说病就病了呢?公公火急火燎赶过去。
两天后,阿朵看见稻花奶奶出现在斗牛场的看台上。公公的牯牛这次却输得一塌糊涂,还被打断了一只角。
公公的牯牛输了。公公骂它,你说你傻不傻,打不赢你不晓得跑,为哪样硬碰硬,把个漂亮的角也给折断了。痛不痛,嗯?牯牛任公公帮它包药,眼睛里似乎晶莹着泪水。公公不忍再责怪它,反而自责起来,都怪我,明明晓得你年纪大了,还让你去斗。人都有老的一天,咋个没想到你也会老呢?我是老糊涂了!
阿朵又在录公公同牯牛说话。此情此景,她有点录不下去了。
公公,回吧。阿朵收起支架,叫公公回屋。公公站起来往回走,刚走几步,脚下一歪,险些摔倒了。阿朵急忙上前扶住。阿朵感觉公公一下老了许多。刚到院坝,他们看见稻花奶奶站在那儿。
我是怕你苦闷,过来陪你说说话。稻花奶奶说,这是晒好的干鱼,还不是你让阿朵捉来送我的,我哪里吃得了?这酒,劲头可能比上次那锅还大点,你悠着点喝,别喝多了!
稻花奶奶进屋吧。阿朵走过去,接过她手上的东西。
今晚我们炒干鱼吃,你们两个老人家只管摆龙门阵,我来做,阿朵说。
吃饭的时候,给公公倒的酒,他一口也没喝。稻花奶奶也跟着难过,吃了两筷菜就放碗了。
阿朵原想听听他们说话,故意躲到隔壁房间捣鼓手机。可火塘里安安静静的,只有火苗漫不经心地燃烧着,发出细细碎碎梦魇一般的声响。一会儿,稻花奶奶大声叫阿朵,她要过对门去了。
阿朵送稻花奶奶,一边走一边说话。
稻花奶奶说,你公公的苦闷我懂,这些年他一个人,你在外面读书,你爹妈又不常回来,只有这头牯牛陪着他。别看它是畜生,经常在一起,通了人性,他们成了老伙计……现在牯牛打断了角,你公公难过……
那你呢,还不是一个人呀?
我,我啊,对,我也是一个人。可是我又不是一个人……我天天只要远远地看着他要么牵着牛,要么挑着草,走在田埂上,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
稻花奶奶不让阿朵送了,可阿朵的手依然挎在她的臂弯里,继续往前走,说,上次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我想听。
稻花奶奶笑了,有些害羞地继续说,上次不是同你说到我的绣帕被他拿走了吗?不对,不是拿走,是我不小掉下去,挂在他的柴尖上。
那年六月六赶歌场——瞧瞧,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这一代都不兴了,不晓得,可我们那会儿就是那样过来的。那年啊,可热闹了,村村寨寨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聚在马郎坡……好多小伙来同我们对歌,你公公自然也在。他故意把那张花帕举过头顶摇来摇去,他的那些同伴就起哄,说信物都得了还唱什么,过去把她拉过来呗!可是谁也不晓得花帕子是谁的。推搡着,让他唱几句逗逗我们这边的女孩子。你公公拉开架势,开了腔:
哥从妹家门前过
花帕打着哥脑壳
两个妹妹一样巧
喜欢哥的是哪个
当时,有点难为情。好像是我故意掉给他似的,瞧他那得意的样子。我让稻子唱,打击一下他的气焰,于是稻子就胡乱接嘴对过去:
对面哥哥好没羞
青天白日当小偷
偷了妹妹花帕子
还敢对歌羞不羞
这下,他可来劲了,判定那花帕子是稻子的。在大呼小叫的起哄声中,他像一只亢奋的画眉:
哥不羞
哥就是个俊小偷
别的东西我不要
只把妹妹心偷走
这样一来,稻子一时接不下去哑了口。待我再要反击一首时,他却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得胜离去了。
某个月夜,稻子偷偷溜下吊脚楼,跟着他走了。一定是这中间,稻子背地里与他私约了几回,把我蒙在鼓里。我后悔自己无动于衷,失去了他,可这理往哪里说去。
我将自己关在阁楼上,成了一只哑了嗓子的雀子,任凭哪只画眉来叫,都唤不起我的回应。从此,我同稻子断绝了姊妹情。我恨她,恨她夺走了我的心上人。
稻子就是你奶奶的小名,不知道你晓得不?可是稻子也是福薄,她同你公公生活了五年就得病走了。临走时,让你公公把我叫去。她从他手里把那张花帕子要回来,交到我手上,你公公才知道那张花帕子是我的。
阿朵生来就没见过奶奶,也没人同她说。要不是稻花奶奶这回说了,她还不知道他们之间竟有这么一段过往,不免心里唏嘘。
那个人说他春天就来,阿朵又同公公提起这事。这时离一年一度的“二月二”不远了。公公却问阿朵另一件事,你爸妈和弟弟回不回来?阿朵摇头。
怎么能不回来呢?人家会笑话的。二月二是我们寨子最大的节日,要祭祖的。
节日来临的前几天,公公让阿朵又给她爸妈打了电话,那边还是说不能回来。公公摇着头,叹了口气,唉,真是一年比一年冷清了。
寨子上许多年轻人都没回来。这二月二已经不像个过节的样子了。
节日那天,稻花奶奶一大早就把公公和阿朵叫了过去。老少三人简单地吃了顿饭。
过了“二月二”,春天真就来了。
这天早晨,公公照例割了一挑草回来,可是他的牯牛却起不来了。多嫩的青草啊,还沾着露珠,他捧着喂它,它不开口,眼睛半闭着。公公趴下身子,用头轻碰它的头,你怎么了啦,老伙计,你不是挺能打的吗?碰呀,使劲碰我啊?牯牛稍稍挣扎了一下,想站起来,可口鼻里的气息只有出来的,没有进去的。公公把脸转向一边,过了一会儿,又转过来,轻抚着它的脑门,触摸它那只断角……老伙计,你真的不行了吗?牯牛努力地抬起眼皮,两颗大大的泪珠滚落下来,接着眼皮又耷拉下去……那好吧,走……走吧,你先走,到那边等着我……公公久久地坐在牛圈边抽烟……傍晚时分,牯牛咽气了。公公将它埋在牛圈里。
阿朵挂着泪,直播了公公同牯牛最后的告别。她不忍录牯牛咽气那一幕,只把镜头对准将要落山的太阳,直至山村的夜幕拉上。
阿朵的镜头转了一下场景——牛圈边,昏暗的月光下,公公的身旁挨坐着稻花奶奶,他们的背影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同样黑乎乎的手机屏幕却潮水般弹出字幕和感动的表情……
渔舟子发了一串流泪的表情。过了几秒钟,他私信阿朵,说公公失去了牯牛,肯定好长一段时间都缓不过劲来,你得多安慰安慰他,天气再暖和一点我就来同你陪陪公公。阿朵回他,我还真有点担心公公,可是牯牛在他心里的位置,恐怕没有人能够替代……你还是别来了……村子也并不如你想象的那样,只怕会让你失望……不管怎么说,感谢你一直关注我们……
稻花奶奶的花妹子不见了。阿朵感叹道,一只没有力气行走的老猫,怎么就不见了呢?稻花奶奶哀伤地说,花妹子是不想老死在家里,它肯定是找了一个它该去的地方,它不愿意让人看到它死去的样子。
这天晚上,阿朵在隔壁房间剪辑视频,后来又同渔舟子聊天。突然听见火塘边公公的芦笙又“嗡嗡”地响起来。阿朵透过半开的房门,看见稻花奶奶眯着眼,默默地听。两个老人今晚又喝了点酒。
阿朵赶紧打开手机悄悄录像:稻花奶奶听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是那张绣帕,是稻子还给她的那张。她把它系在公公的芦笙上,公公停止吹奏。稻花奶奶唱起那首歌:
对面哥哥好没羞
青天白日当小偷
偷了妹妹花帕子
还敢对歌羞不羞
公公接着唱:
哥不羞
哥就是个俊小偷
别的东西我不要
只把妹妹心偷走
稻花奶奶原本黯淡干涩的眼睛里,有一丝亮光闪烁。她没有往下唱,看着公公,很满足的样子,说这歌终于是我同你唱了,这绣帕我亲手系在芦笙上,你可别搞丢了。阿朵从手机画面里看到,那张绣帕绣着一条可爱的稻花鱼。
公公把系着花帕的芦笙郑重地放在方桌上,然后坐回凳子,说好久就想把它给你,可是……只见公公从荷包里掏出一只银手镯要往稻花奶奶手腕上套……
稻花奶奶摆了下手,想离开凳子。
公公说,准备了好多年,一直放着……你这是……不喜欢吗?
不是,老都老了,还兴这个……
戴着吧……再坐一会儿吧。
稻花奶奶本来要起身的,又将身子缩了回去。她反复摩挲着手镯,这么亮,什么时候打的呀?背在身上有些日子了吧?
公公只顾抽烟,不言语。
唉,时间也不多了……稻花奶奶莫名其妙说了这样一句。
夜长着,还早呢,你怕睡不够啊。
我是说,牯牛死了,花妹子也走了……
唉,它们怎么说走就走了……
稻花奶奶不再说话,抬眼望了一下芦笙上的绣帕,又看向公公。
过了好一会儿,公公起身。
你上哪里?
我去给牯牛添把草。你没听见它在叫唤吗?
哪有啊,你的伙计早没了,你好生听听,是我的花妹子在叫唤。
你比我还要好笑,你的花妹子不早走了吗,哪会是它在叫唤。
这些天夜里,我老听见花妹子在角落里叫唤,我几次起来找,喊它,它就是不肯见我。
你是想它了。
你呢,是不是也这样?
咋个不是,以往我习惯起来给它添夜草,现在还改不过来,好几次走到牛圈边才……
稻花奶奶没有接下去。时间似乎静止了。
阿朵,今晚不要再送稻花奶奶过对门寨了,留她多陪陪公公说说话……渔舟子在屏幕上弹出一句,紧跟着,其他人也表达了同样的建议。
不知什么时候,阿朵已经坐到两个老人的身边。
她搂着稻花奶奶半边肩膀,说,奶奶,你还是住过来吧,和公公有个伴。公公,你说呢?阿朵看着公公。
这个,是不是给在外面打工的两口子说一声?稻花奶奶也看着公公。
公公朝地上磕了磕烟头,说有哪样可说的,早就是一家人了。那小子小的时候,衣服裤子不都是你给收拾的吗?整天姨妈姨妈地叫个不停……还有,后来,他们出去了,朵儿又丢给你好长一段时间。还是咱们朵儿有良心……
稻花奶奶搬来同公公住在一起了。有时公公也会陪着她过对门寨。人们经常会看到两个老人一前一后,或者肩并着肩,在寨子里走动。
春天的花开得太热闹了,让人不会相信突然的夜雨就会将它打落在地。头几天,稻花奶奶还好好的,一点病的样子都没有。可是这天早上,阿朵知道了不好的消息,稻花奶奶安详地走了。她是什么时候将自己最漂亮的嫁衣穿在身上的,只有公公清楚。她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亮堂堂的银饰像花一样开在银发里,一如前几日还开放着的李花,绚烂、圣洁。公公看上去并不哀伤,他端详着稻花奶奶幸福的面容,握着她的手,轻轻理她额头的发丝,说,瓜熟蒂落,瓜熟蒂落了,你在那边等着,一定要等着我……他一片一片展开稻花奶奶留给他的绣帕,一共十三张。十三,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有特殊寓意的数字。每一张都绣着同一个图案,与那天系在公公芦笙上的那张一模一样。
阿朵同公公讲,那个想来听你摆龙门阵的人,过几天就要来了。
公公没有反应,像没有听见。公公不喝酒,不抽烟,也不磨镰刀,只是静静地坐在门口。他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