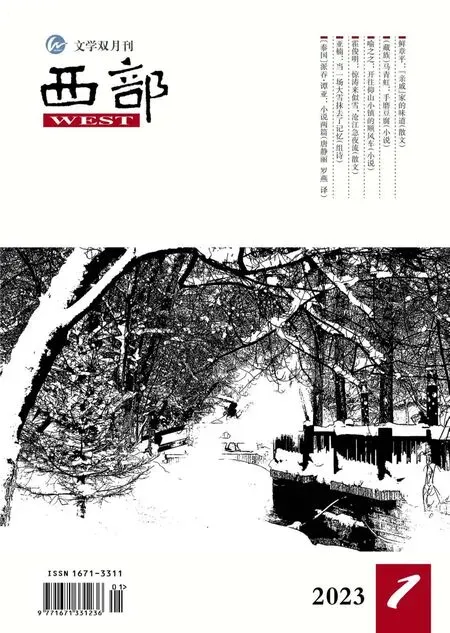途中的跋涉者(组诗)
麦豆
飞鸟飞过河面
飞鸟飞过河面
倒映出它的影子
永恒的身影
一闪而过
它在世界里飞
偶尔被看见
给予愉悦
但从不给予理解
途中的漫步者
在房子里,你也许会想
窗外还是冬天
因为房间昏暗
午休时分昏暗不明
但从你推开门
呼吸第一口空气开始
世界就在改变你
你把自己交给世界
世界会告诉你
沿途的蜡梅正在盛开
金黄的蜡梅
无需语言
只要你站在它的面前
静静观看
或者闭上眼睛
什么也不想
语言是什么
有时,你会觉得
世界并不说话
但世界的意思
你都能明白
那么,真正的
语言是什么
它必是一个
沉默的世界
眼前的喜鹊
如果它们只是喜鹊
字典里的喜鹊
甚至记忆中
童年的喜鹊
它就不可能是
在冷风中吹的喜鹊
眼前的这一只
站在树枝上鸣叫
鸣叫即心灵在自语
即它是孤独的、现实的
没有同类的
拥有语言的这一只
雪
天空在飘雪
时断时续
早晨,上班路上
它就在飘
中午,散步途中
它仍在
若有若无地飘
冷风中,我想
深夜,它应该会停
或者,它只飘落
在自己的世界里
婴儿
他有一双眼睛
我注意到他
只盯了我一眼
便迅速离开
继续寻找
对一个新世界
而言,人类
再普通不过了
一生,或瞬间
有一天,我
突然发现
红色的树在蜕皮
具体哪一天,我忘了
事实上,人不需要
完整的一生
有那么几个瞬间
就足够了
表演
午饭后散步
这是什么表演
如果是,它的观众又是谁
观众是否也感到厌烦……
新开的桂花
让我停下脚步
凋零的桂花树
再次让我停下脚步
沿途尽是词语
走在路上
像对着观众朗诵
一本诗集的一些句子
12月14日,初雪
是这样一个时刻,打开清晨的窗户
记忆已是梦的一部分
飞鸟划过屋脊,它不是飞鸟,是寒风中的
一片树叶。太阳照着蓝色的雪
阳光不再刺眼,兔子在雪上
留下一行清晰的脚印,没有兔子
全村人站在一条河的河面上聊天,跺脚
不用担心冰层碎裂
河水弄湿棉鞋
时间让它们统统沦为梦境
在梦里,兔子开口说话,求饶猎人
放它一命,麻雀成排
站在电线上,一声枪响,将它们全部惊散
我们钻开厚厚的冰面
另一种以捕鱼为生值得同情的动物
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雪后的窗户里
只有我,铁栅栏,覆盖
薄雪的屋脊
飞鸟,兔子脚印,蓝色的光,湿透的棉鞋
记忆已是生活的一部分
它们已连同梦,在太阳升起之后
消失得无影无踪
加固河堤的挖掘机
河边的挖掘机
让我想到青年时代的父亲
它们在挖土
将土从土中挖出
在土中挖出一条又长又深的坑道
供人类在坑道中施工
或者,它们将一根根长长的
涂满黑色沥青的松木
在人的牵引下
用它刨土的铁斗
将松木用力压进岸边的淤泥里
它在加固一条苍老的河流
它们埋头干活,尽管它们从不咳嗽
也不会突然没有力气
但它们仍然让我想起青年时代的父亲
一身蛮力,像极了陷在泥水中
举步维艰的父亲
在一条河的岸边,在记忆中
那块栽种棉花的土地上
艰难地挖掘着……
雨季已过,危险的汛期
已过,它们在劳作
提防下一个雨季的到来
尊严或活着
冬天,大雪纷飞之际
我再次凝视窗外的世界
大雪纷飞的世界里
活着的意义再次被我深思
那些在寒冷中呼吸的生命
应该有尊严地活着
否则,只有死亡
配得上一个皑皑白雪的世界
遥远的生活
有人将喝干净的果冻袋子
吹了口气,扔在路边的
自行车篮子里
我知道它是空的
有人将正在腐烂的橘子扔掉
我知道它们其中有橘瓣
仍然甘甜
有人将啤酒瓶故意敲碎
扔在河岸上
但我知道,日子艰难的时候
碎玻璃也可以
捡起来,装进绿色蛇皮袋
背到废品收购站卖钱
遥远的生活中发生过一些难堪的事情
但它们的真实使我更加富有
路旁的栅栏
路边的栅栏是路的一部分
站在路的两旁
规定着路的宽度
它同时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随身携带
不可翻越
它在确认
也在怀疑
我们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