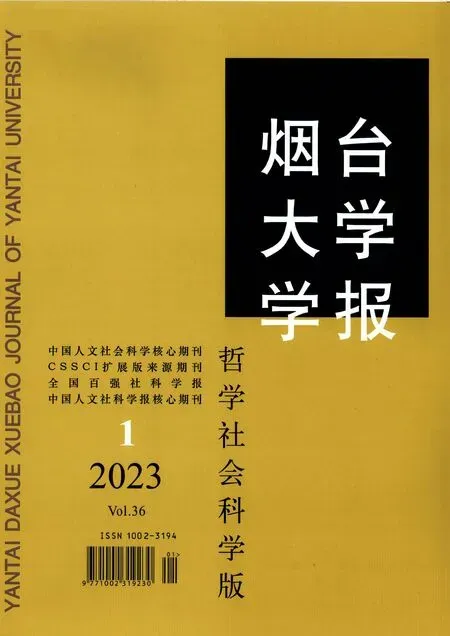宋高宗初期的驻跸之争与迁还中原的中兴目标
穆 琛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促成这一发展优势的内生动力正是古代中国各民族人民不断追求与践行的“大一统”思想。从中国历史政治格局上看,孕育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其内涵实现了三次重要演进:一次是秦汉时期,“华夷之辩”秩序初定;一次是隋唐时期,“华夷一家”之势渐成;一次是元明清时期,“华夷一体”格局定型。(2)参见胡静:《“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辽宋夏金蒙时期是由“华夷一家”向“华夷一体”的推进时期,各政权间彼此发生着自在的政治碰撞、经济互补、文化交汇和思想破垒,长城南北日益加深的一体化不断解构着传统的“天下”秩序,这对“大一统”的格局发展和思想深化至关重要。然而对这一趋势的研究,现有成果往往集中在辽、夏、金、蒙元等北方民族政权对“大一统”观念的接受与融入,以及他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贡献,忽略了同一时期两宋政权为实现“大一统”而做出的努力。事实上,在多政权并立的政治环境中,宋室虽然被迫南迁,却始终没有放弃迁还中原的中兴目标,且试图以狭隘解读“华夷”“中国”“正统”观念的方式重塑“大一统”内涵。本文即从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八年(1138)间的驻跸之争入手,对南宋初期迁还中原的践行路径和“大一统”秩序的思想认知进行分析。
一、驻跸之争的五个阶段
“驻跸”本指帝王车驾出行、巡幸途中的短暂行止之事,历代王朝正史也多有帝王驻跸的记载,含义基本无差,唯有南宋的“驻跸”情况比较特殊。靖康二年(1127),金人攻陷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宋遗臣拥立康王赵构(庙号宋高宗)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但即位册文并未对定都何处作出说明,仅称“冀清京邑”,可见应天府只是南宋立朝中兴的暂驻之地。时人有言,“万乘所居,必择形胜以为驻跸之所,然后能制服中外,以图事业”。(3)李纲撰,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七八《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793页。南宋对驻跸地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宋金关系的影响,是当时民族关系格局的一种独特体现,也是关乎赵宋中兴、回望中原的一项重要决策。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八年间,宋高宗数次更换驻跸地点,并就此与大臣们展开多番讨论。结合宋金关系,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初立之争
时间跨度为建炎元年五月至十二月。早在金人扶植张邦昌伪楚政权之后、宋高宗即位之前,即建炎元年三月至五月间,宋人关于驻跸地点的争议已见端倪,当时讨论的主题是康王应从何处即位:一说直接在济州(今山东济宁)幕府;一说奉王渡江,驻军宿州;一说移驾扬州;一说趋向应天府。宋高宗即位后,这一问题演变成了大臣们对中兴根据地的考察。这并非是由某一核心人物有意进行主导,而是大家各自基于对宋金局势的认知和预判,自觉、自发进行的意见表达,并先后产生了六种观点:一是知同州唐重、直秘阁郑骧主张西幸关陕,“驻跸汉中,治兵关中”,(4)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0页。或是“定都关中”,希望占据百二山河之地势,治理恃力为强的秦地之兵。二是东京留守宗泽、尚书兵部员外郎张所、尚书祠部员外郎喻汝砺坚持回銮故都汴京,因其为“祖宗二百年积累之基业”,(5)宗泽:《宗泽集》卷一《第六次乞回銮疏》,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5页。中州之地不可弃。三是尚书右仆射李纲认为当前“惟邓(州)为可以备车驾之时巡”,(6)李纲撰,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六三《议巡幸第一劄子》,第672页。既有山高城宽、民风淳固的优势,又兼顾西召陕兵、北援京畿、南取巴蜀财货、东输江淮谷粟的便利。四是礼部侍郎朱胜非建议巡幸襄阳,“接蜀、汉而引江、淮”,(7)朱胜非:《乞幸襄阳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6页。能够制动南北,实现号令四方、以图中原的目标。五是中书侍郎黄潜善、知枢密院事汪伯彦主张南幸淮甸。六是卫尉少卿卫肤敏、吏部侍郎刘珏、尚书右丞许景衡、中书舍人刘观等提议暂且规避金人屯据两河(河北路、河东路)的威胁,南渡金陵(又称建康、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8)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第214页。
南宋初立,宋高宗对驻跸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靖康年间入质敌营的经历和伪楚张邦昌的主动让位令他十分忌惮金人借机南袭,即位当月便命翁彦国修缮江宁府,以备巡幸,并遣通问使周望、副使赵哲出使金军,以“祈请二帝”为名试探金人对南宋政权的态度。七月,宋高宗颁布《独留中原诏》,表示要亲督六师、应援故土,同时将元祐太后和六宫迁往东南安置。这表明,此时的宋高宗对恢复故土缺乏谋划,为退守东南铺垫退路,也意味着驻跸关中、汴都、南阳、襄阳的构想无法施展。所以,诏书颁布不久,他便听从黄潜善、汪伯彦的请求,改成巡幸东南退避金人。但后来他又被李纲“失中原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9)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第210页。的顾虑说服,决定驻跸南阳(时属邓州辖境),并遣观文殿学士范致虚先赴南阳“修城池、治宫室”。这时,主张南渡的刘珏、许景衡以南阳兵弱财殚、金人将逼近汴京为由上告高宗,再次动摇了高宗往南阳措置的决心,折中考虑后,最后议定驻跸江北的维扬(扬州别称),命知扬州吕颐浩修备城池。十月,宋高宗移跸扬州,驻跸州治。
(二)第二阶段:避敌之争
时间跨度为建炎二年正月至三年八月。建炎元年十二月,金太宗以张邦昌被废之故起兵,称“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10)《金史》卷七四《宗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6册,第1698页。命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右副元帅完颜宗辅、都统完颜娄室分率三路,自河南、山东、关陕渡河侵宋。南宋大臣们以北方不宁为虑,再次陷入如何移跸的争论。其中既有旧观点的深化,如宗泽连上二十四封《乞回銮疏》,希望宋高宗返还汴京;黄潜善、汪伯彦“无复经制两河之意”,(11)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建炎元年九月》,第241页。坚持永驻扬州;秘书省正字冯楫、户部尚书叶梦得、中军统制官张俊、起居郎兼权直学士院张守、迪功郎张邵、中书舍人季陵等人认为,维扬背向大江天险,不宜屯驻,“非据建康无以镇东南之势”。(12)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第532页。又有新观点的提出,如知枢密院事张浚、江淮两浙制置使吕颐浩建议“奉上幸武昌”暂驻,再行趋陕之计;和州防御使马扩以“幸巴蜀之地,用陕右之兵”(13)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第480页。为上策,都守武昌为中策,驻跸金陵为下策;御营司都统制王渊提议“钱塘(杭州)有重江之阻”。(14)徐梦莘编纂:《三朝北盟会编》(丙集),《炎兴下帙二十五》,上海:大化书局,1979年,第12页。
金人南侵,宋高宗南渡的指向性依然十分明确。建炎二年八月,他派人将户部所余金帛从行在扬州运输到江宁府,以备不虞,并采纳吕颐浩、叶梦得的建议,将江、湖、二广的“纲”运赴江宁府,闽、浙纲输往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惟川、陕、京东西、淮南纲赴行在”,(15)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建炎二年八月》,第403页。为南移做好了经济上的准备。建炎三年正月,金人攻陷天长(今安徽天长),宋高宗仓促南渡至镇江,向群臣征求“姑留此,或径趋浙中”(16)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建炎二年八月》,第456页。的建议,显然有继续南下的意图,这也是王渊敢于提出驻跸钱塘的直接原因。二月,宋高宗经由镇江、常州、平江府、秀州(今浙江嘉兴)等地退往杭州,以州治为行宫。鉴于大臣们对驻跸建康的呼声较高,宋高宗还在移跸途中颁布了《抚慰维扬迁徙人诏》,声称暂图退避只是稍安之举。三月,金军退师,宋高宗随即表示“移跸江宁府,经理中原”,(17)徐梦莘编纂:《三朝北盟会编》(丙集),《炎兴下帙二十五》,第11页。却因御营都副统制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而搁置。这场叛乱由武将发起,成为宋高宗改变退避心态、以求和图国是的重要诱因。(18)刘焕曾、任仲书:《试论“苗、刘之变”》,《史学集刊》1990年第2期。再加上金元帅右监军完颜宗弼滞留江北,对宋军穷追不舍,迫使他在平息兵变后做出三项决定:一是向张浚询问方今大计,许其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任陕蜀之事,置司秦川经营;二是遣使北上请和,致书完颜宗翰传达去尊号、奉正朔、为藩臣之意,“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19)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三《建炎三年五月》,第562页;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第608-609页。宋高宗五月已遣使洪皓,并作《致金左副元帅书》,《要录》没有收录书信具体内容。但据《要录·建炎三年八月》记载,“朝议以为敌师且至,而洪皓、崔纵未得前,求可使缓师者”,可见洪皓二人之行没有成功,此次遣使杜时亮、宋汝为,依然有《致金左副元帅书》,《要录》收录全文。引文内容即来自八月遣使记载,但宋高宗削号称藩的意图在五月已经形成。三是移跸江宁府,更名为建康府,称其“载惟藩潜之名,实符建启之兆”,(20)徐梦莘编纂:《三朝北盟会编》(丙集),《炎兴下帙二十九》,第39页。企图据建康实现中兴事业。
(三)第三阶段:定居之争
时间跨度为建炎三年闰八月至十二月。宋高宗因担心敌情反复,主动向大臣们发起两次关于驻跸地点的商议。第一次是以御笔示随驾百官:“大江之北,左右应接,我所守者一,由荆、襄至通、泰,敌之可来者五、六,兵家胜负,难可预期。朕欲定居建康,不复移跸。与夫右趋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危,孰利孰害……条具以闻。”(21)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第613页。第二次是专门召集武将询问驻跸之地。这次讨论由于完颜宗弼的再次进兵而被迫中止,主要形成如下观点:其一,针对御笔“右趋鄂、岳”的提议,江、浙(江南路、两浙路)士大夫以道路遥远、馈饷难继为由反对,主张固守东南。其二,武将之中,张俊、御营使司都统制辛企宗建议自岳州(今湖南岳阳)、鄂州南幸长沙,行南退之策以避敌锋。其三,起居郎胡寅主张审择建康、南昌或江陵设立行台,安置太后、六宫与百司,若要进取中原则“惟荆、襄为胜”。其四,张浚坚持经理汉中,北控六路兵力,南据两川物资,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希望宋高宗早为西行之谋。其五,尚书考功员外郎楼炤客观分析江、浙局势,认为当前兵力如果能够保有淮南,就该驻跸建康,渐图恢复;若无法保淮南,则应以长江为险,“权都吴会,以养国力”。(22)《宋史》卷三八〇《楼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33册,第11715页。
战事稍歇时,宋高宗首次表现出对驻跸问题的主动性。“定居建康”是他从苗刘叛乱和群臣谏言中得到的经验,“左驻吴、越”的想法得益于驻跸杭州的先例,“右趋鄂、岳”则是对张浚、吕颐浩西幸川陕计划的接受。宋高宗将驻跸方案限定在三者之间,既有经略东南的积极性,又有对“定居建康”的迟疑。他评价江浙士大夫的观点为“以家谋”而非“为国计”,认为张俊和辛企宗劝幸长沙是因为“不敢战”,对此非常失望,可见此时宋高宗有意变被动为主动,为中兴事业做准备。但当他权衡过楼炤所言江、浙局势之后,又没能坚持据守建康的想法,而于建炎三年十月退返临安,东至越州(又称吴会、会稽,今浙江绍兴)。十一月,完颜宗弼自和州(今安徽马鞍山)渡江南来,攻陷建康、临安。宋高宗认为金人“必临浙江追袭”,采纳吕颐浩“登舟幸海”的建议,于十二月自越州移跸,经明州(今浙江宁波)、定海(今浙江舟山)、台州,落脚温州。
(四)第四阶段:措置之争
时间跨度为建炎四年至绍兴四年。建炎四年间,宋高宗尚在温州,为了妥善处理金人渡江导致的残局,他连发三封诏书,鼓励群臣条陈驻跸方案和守御之策:“将来敌骑北归,或尽数过江,或留兵守建康、杭、越,当如何措置,及于何驻跸。”(23)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一《建炎四年正月》,第713页。不同于以往讨论的是,大臣们不但针对驻跸何处提出看法,还根据内外局势筹谋了具体方案。吕颐浩建议暂驻会稽,再趋浙西,同时应亲御六师策应江北,以入蜀为最终目标。张浚仍然以驻跸关陕为中兴大计,主张先幸武昌、再幸关陕。御史中丞赵鼎主张待金人北还,回跸浙西(两浙西路,含临安、平江、镇江等地)或建康,若要进取中原,则应西向荆、襄,以公安为行阙,屯兵襄阳为屏翰。京西南路提点刑狱公事李允文与转运副使陈求道请幸鄂州。襄阳镇抚使桑仲、庆远军节度使邢焕请幸荆南训兵。翰林学士汪藻、中书舍人胡安国、吏部员外郎廖刚、右宣教郎王彦恢、布衣吴伸均主张暂都金陵,但各有所侧重。汪藻和王彦恢认为保有金陵必须北渡经营淮南,过江屯田、营建寨栅,以为藩篱;胡安国更加强调对荆湖北路各重镇的筹划;廖刚在提出经营建康之前,还曾建议以“幸闽之说”备一时之急;吴伸则将金陵视为“万一未复神京”也不至于“久居于海隅”(24)吴伸:《论经国大要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84册,第273页。的选择。知枢密院李回与御史中丞富直柔等考虑到聚众为盗的贼首李成正恃金人南犯而盘踞江东,建议宋高宗“移跸饶、信间”(今江西鄱阳、上饶),平定内乱,削减抗金的后顾之忧。
金人退师后,宋高宗对驻跸的思考开始重视守御措置。大臣们据此形成的驻跸方案也以积极回跸、沿江安置为大致思路,虽然在驻跸地点上与前几个阶段区别不大,但对守备谋划的构思却是前期讨论中所没有的。这一阶段,宋金关系的变化也为南宋专务固守提供了可能。完颜宗弼在北返途中,遭遇浙西制置使韩世忠的重创,金人对宋军战斗力的认识有所改变。张浚为了牵制金人兵力,贸然发起富平之战,导致关陕五路(鄜延路、邠宁路、环庆路、秦凤路、熙河路)尽失于金,战事随即转向西北。在金左监军完颜昌的劝说下,金太宗采用“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25)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七《太宗文烈皇帝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13页。策略,册立以刘豫为傀儡的伪齐政权,实现对中原的统治,宋金在中原地区的正面冲突得到缓解。在这种局势下,宋高宗经制东南、巩固政权成为迫切与必然。建炎四年四月,宋高宗回跸越州措置,一方面“稍复藩镇之制”,增设镇抚使一职,析地处以便宜之权,鼓励帅臣御敌立功,换取世袭资格;另一方面,命荆南镇抚使解潜筹备巡幸事务,且婺、衢、信、饶、归、峡、夔诸州蓄钱粮,收州船,皆备巡幸,这正是一条西通川陕的桥梁路线。绍兴元年,宋高宗考虑到“使号令易通于川、陕,将兵顺流而可下,漕运不至于艰阻”,(26)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九《绍兴元年十一月》,第1021页。移跸临安,专注于内定规模、修政中兴,直到绍兴四年金与伪齐合兵南侵,才下诏移驾平江府,率六师亲征。
(五)第五阶段:国是之争
时间跨度为绍兴五年至八年。绍兴四年十二月,金太宗病危,金兵渡淮北归,伪齐不战而溃。次年(1135)正月,宋高宗谓“虏已退遁……当乘此时,大作规模措置”,(27)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四《绍兴五年正月》,第1592页。随即向老臣问询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绥怀之略,大臣所言多有涉及到驻跸之所。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进言中多抱有定居建康的考量,这与宋金势力的相近有很大关系。金人在关陕的战事接连遭受和尚原、仙人关、饶风关挫败,中原刘豫的南侵也因湖北制置使岳飞收复襄阳六郡而被滞缓,在此背景下,以李纲、张浚、张守、吏部侍郎晏敦复、侍御史张致远、资政殿大学士王绹、监察御史刘长源、左司谏陈公辅等大臣为代表,均主张定都建康为中兴根本,以荆襄为屏翰,以淮南为门户。另有大臣提出不同想法,如荆湖北路安抚使王庶认为,“欲保江南,无所事;如曰绍复大业,都荆为可”;(28)《宋史》卷三七二《王庶传》,第33册,第11547页。赵鼎却认为建康是显敞冲要、四达交争之地,若舍二浙泽国险阻之区而居建康,乃“先自致于颠危之地”。(29)赵鼎撰,李蹊点校:《忠正德文集》卷三《经筳论事第二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60页。
敌兵北还,宋高宗终于将攻御措置问题置于驻跸之先考虑。这是他明显区别于立朝之初的态度。他以建康修葺未就为由,暂时回跸临安,命大臣们缮治建康行宫,又趁此派人往温州奉迎太庙神主,令知临安府梁汝嘉修馆充作临时太庙,同时规定修馆不能过兴工役,“俟移跸日,复充本府使用”,(30)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五《绍兴五年二月》,第1909页。这说明他不打算久居临安,已有意定行都于建康,渐图恢复。绍兴六年九月,伪齐再犯,宋高宗至平江亲征,在主张“有进无退”的张浚与倾向“保江之计”的赵鼎之间,毅然听取张浚的建议,诏告次年驻跸建康。然而移跸未久,便发生淮西军变,行营左护军副统制官郦琼裹胁四万将士、十万百姓投奔刘豫,导致南宋对抗金军的前沿重地两淮地区瞬间空虚。失去地利和军事保障的宋高宗最后决定“复幸浙西”,将行都定在了临安。
二、迁还中原的思想碰撞
宋高宗初期关于驻跸问题的讨论,既是处理民族关系的现实问题,也是民族关系的理论问题。面对不断变化的宋金局势,宋高宗和大臣们展开多次讨论,虽然各种观点纷陈,却普遍认为迁还中原、重归正朔才是中兴之目标。在此共识下,他们通过驻跸观点上的各种分歧,展现出迁还中原的四种践行路径,彼此间的思想碰撞真实还原了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思想。
(一)回銮派
这一派的大臣以宗泽、李纲、喻汝砺、张所等为代表,主张近故都之地而居,比如故都汴京或南阳,因此,又可以称为汴京派。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执着于对“中原”和“人心”的强调,这恰恰是其如此看重汴京的深层次原因。张所曾将迁还汴都的必要性总结为“诚有五利”:奉宗庙、保陵寝;安抚人心,无解体之患;系四海之望;释早先河北割地之疑;早有定处,以便专于边防。这五点利处即为还都汴京的阐释,第一、三、五利对应“中原”,第二、四利对应“人心”。具体来看,首先,中原是天下之根本,而汴都又是中原之根本。“中原者正统也,割据者霸统也”,(31)喻汝砺:《上黄相论迁都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78册,第2页。王室再造、中兴复成的重要标志便是据地中原,弃中原则“不足以一天下”;中原之中,赵宋祖宗以汴京为肇造“大一统”的根基之地,驻跸在外意味着失去了“大一统之绪”,只有回跸汴京才能“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32)宗泽:《宗泽集》卷一《第二十次乞回銮疏》,第20页。需要注意的是,李纲虽主张巡幸南阳,却只是将它作为城池未备、防秋已迫的次选,他表示南阳地近汴京,可“示不忘中原之意”。其次,得天下需得其民,回銮汴京是人心所欲。金人猖獗南侵,致使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之民“怀冤付痛”,京师将士、商旅、农民、士大夫皆无所依归,即便如此,他们坚持不顺北敌,“自保山寨者……为争先救驾者又不知几万数”,(33)宗泽:《宗泽集》卷一《第二十一次乞回銮疏》,第21页。万邦百姓颙望宋高宗“归安大内”。若不及早返汴京,不但会失“天下睽睽万目”之心,还会引发更多的叛贼作乱。
实际上,“中原”与“人心”既是回銮派大臣坚守驻跸观点、反驳其他观点的关键因素,又是南宋拓进恢复、实现中兴的重要依据。参与驻跸讨论始末的大多数其他人,包括宋高宗本人,在内心依然认可将汴京作为都城,因为驻跸并不等同于迁都。而宗泽等人最明显的不同就是他们前瞻性地思考了如何以拓进求恢复,从一开始就将“天下人主”地位置于首位。这一点可以从李纲的《议巡幸》得到体现:“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势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则藉巡幸之名使国势不失于太弱;二则不置定都,使敌国无所窥伺;三则四方望幸,使奸雄无所觊觎。议者或欲留应天或欲幸建康,臣以为皆非计。夫汴梁,宗庙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34)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五八《议巡幸》,第637页。这段话传达了三个信息:一是可分立别都,二是别都不当久居,三是汴京系天下根本。三者呈现递进式关联,说明李纲的设计方案本身就兼顾了不迁都和可巡幸两层内涵。而其他大臣都是单纯考虑如何驻跸,暂不涉及择都问题。
在国朝初立、局势紧蹙的情况下,回銮派的观点仅仅活跃于高宗朝的前两年间,随着金人势力的不断南移和宋高宗以求和图国是的态度转变,中原最终成为“大一统”思想中的理想成分而非现实成分。回銮派也遭到其他大臣的批评,主张南渡的大臣皆以兵弱财殚、密迩盗区、漕运不继、金人再犯为托辞,称“三镇未复,不宜居危地”,(35)许景衡撰,陈光熙点校:《许景衡集》附录《〈宋元学案〉本传:忠简许横塘先生景衡》,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567页。还引靖康教训,指责他们的观点不合时宜,一味盲目固守“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缓急,必当从权”。(36)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八上,建炎三年正月尽二月条,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其实,在宋高宗即位之初,两河地区失陷于金人者不过十余郡,张所、傅亮等杰出将领积极经营两河,宗泽、李纲等人也成功联结了抗金义军,形势已不可与靖康年间同日而语。这些指责充分说明,他们关于驻跸的分歧根源于中兴路径与战和思想的冲突。
(二)西幸派
这一派的大臣以张浚、唐重、马扩等为代表,主要有两个观点,分别看重关陕、川蜀,因此又可以称川陕派。这派大臣将川陕地区作为中兴之根本,有他们的考虑。从地势而言,关陕、川蜀二地是历来公认的军事战略重地,“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37)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历代周域形势八》,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28页。具有地狭而腴、唇齿相依的地形优势,“控制陕西六路,捍蔽川峡四路”,(38)《宋史》卷四四七《唐重传》,第38册,第13187页。便可形成对金人的军事制衡。从兵备而言,“京师以秦兵为爪牙”,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中兴大势须“擁四川之饶,据五路之强”,(39)喻汝砺:《上裕蜀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77册,第393页。是拱卫京师、恢复中原的重要力量。从民族来说,川、陕西陲有党项人的西夏政权与宋、金角逐,还有唃厮啰政权解体后散居河湟地区的众多分散势力,堪称“壤界之国”,若能“通夏国之好,继青唐之后”,(40)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二月》,第32页。便可成犄角之势牵制金人。从文化而言,关陕地区还有一项独一无二的优势,即“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4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二月癸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9页。事实上,迁都关陕的念头在宋太祖晚年即已产生,“迁河南未已,终当居长安耳”。(42)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七《河南二》,第2137页。长安作为汉唐“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它的繁荣强盛成了政权地位的象征,宋人对定都关中的向往昭示着对“大一统”秩序的追求。尤其是五代十国以来北方民族政权经久不衰,关陕地区屏翰中原的作用愈发受到重视。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给辽国,北宋时刻面临着迫近长城防线的北方势力威胁,迁都长安之议历经北宋君臣多朝争论,至金人灭辽攻宋、赵宋由北入南之时再次被提起,连回銮派宗泽都承认若不都汴京,据长安则“祖宗大业可以永保”,可见其地的重要性。
综合来看,在宋高宗初期的驻跸争议中,川、陕二地是受责难较少,却也是反响甚微的一种观点。因为这派大臣对中原的渴望以“据蜀险,就六路形势,力治兵战,以图恢复”(43)徐梦莘编纂:《三朝北盟会编》(乙集),《炎兴下帙二十三》,第631页。的诉求表现出来,虽与回銮派相异,却同样有着力战拓进的迫切性,这对于“不识兵革”“上下恬嬉”的南宋来讲仍有很大难度。即便后来张浚委婉地提出先幸武昌、再趋川陕的两步走计划,仍被部分大臣抨击。比如建炎三年六月,久雨不止,宋高宗认为这是天灾谴告,季陵竟将其归咎于西幸派的“奸谋”,若奉高宗“由下引之以及中,由中引之以及上”,(44)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四《建炎三年六月》,第573页。道途远涉,容易引起“人情皇皇”,给歹人制造窥伺之机,“常雨之证,恐或由此”。张守还认为,将士中以西北人居多,西行之谋是他们出于“可图西归”的自私考虑,而非中兴赵宋的大计。当然,宋高宗在一定时期内也对驻跸关中的想法表示过支持,许以张浚便宜之权置司川陕。而张浚冒进发起的伐金战争,不但直接导致了关陕五路的丢失,还进一步暴露了宋人“事权俱重,体统未明”(45)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三《乙未上皇帝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6页。的军事弊端。其他大臣对西幸派甚或张浚本人的批判更加激烈。他们一面弹劾张浚专权独断,“自陕以西,不知有陛下”,一面暗含对朝廷西幸决策的攻讦,“去年议幸蜀,人以为不可,朝廷以为可,故弛备江、淮,而经营关、陕。以今观之,孰得孰失?”(46)《宋史》卷三七七《季陵传》,第33册,第11647页。这番言论使西幸派希望倚仗川陕实现中兴的构想再无实现的可能。
(三)南渡派
这一派大臣占据多数,在不同阶段提出了建康、镇江、平江、临安、越州、温州等驻跸地点,其地皆位于中原之外、长江下游以南的江南两路和两浙两路辖地,因此又可以称江浙派。这派大臣的核心态度是据东南之势退守缓图,与其他派系相比,他们是唯一同意与金议和、将驻跸地点迁离中原的人。这一派的立论基础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自然条件与环境优势。江浙地区虽远离中原地区,却具有依靠长江、“天险可据”的地理优势,是南宋退守固存的天然屏障和心理寄托,且东南之地“沃壤数千里”,“素号富庶,诚可因以为资”,(47)徐梦莘编纂:《三朝北盟会编》(丁集),《炎兴下帙一百二十二》,第287页。京都百需“悉取给于此”。二是宋金关系与战和形势。征伐之战必先以“中国富盛,兵甲精锐,我有万全之势,彼有可乘之隙”,(48)胡舜陟:《奏陈御戎策之策劄子》,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73册,第112-113页。而宋高宗初期的军事水平无法完全与金人相对抗,且已失中原,兵不可妄用,讲和、守御“诚为今日之先务”。但退守东南与议和并不等于幸敌之不来,偏安一隅,而是为“俟军声国势少振,然后驾还中都”(49)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第213页。争取时机。对此,刘观有比较恰当的阐述,“别诏老将总六师,据长江以自卫,徐观金人所向,然后设奇出伏,以攻其南北,使金兵不专,则其势易乘,而吾可以得志”。(50)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建炎元年九月》,第251页。此“志”便是还都中原。
客观地说,宋高宗初期的所有驻跸观点中,南渡派是持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派,因为他们试图通过“以议和求国是”的方案实现固存缓图、恢复中原的目标,且与宋高宗以东南为回旋之地的心思不谋而合。从北宋遗臣提议康王渡江即位,到宋高宗移跸于建康、镇江、平江、临安、越州、温州等地的经历,再到南宋最终将行都定在临安,南渡派始终活跃在驻跸争论之中,并形成有别于其他派系的三个特点。
一是能够根据局势变化,适时调整具体对金策略和驻跸地点。高宗即位之初,南渡派的驻跸言论基本围绕建康展开,“建康实中兴根本之地”,(51)陈克、吴若著,吕祉编:《东南防守利便·进东南防守利便缴状》,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有“内以大江为之控扼”“外以淮甸为之藩篱”(52)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六《绍兴二年七月》,第1143页。的战略条件,占据犄角相依、纵横交互之地可以实现退守固存的短期目标。金人迫近长江后,宋高宗“姑留此,或径趋浙中”的提问助长了大臣的南渡心理,镇江、平江、临安、越州、温州等地皆有了驻跸先例。随着宋金战斗力形成均势,南渡派自身又分化出兴兵力战、继续求和等不同态度,造成对驻跸地点有了不同取向,如吕颐浩曾建议宋高宗临平江亲征,秦桧坚持“解仇议和”,以至于驻跸争论的焦点最终由不同派系转移到南渡派内部关于定居建康与定居临安的分歧之中。
二是既有与其他派系之间的争议,又有派系内部的观点分歧。回銮派认为驻跸建康没有远见,只“偷取一时安适”,(53)李纲撰,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六三《议巡幸第一劄子》,第671页。且掷中州之地让与夷狄无异于“裂王者一统之绪”。西幸派认为东南虽是富庶要会之地,却缺乏精兵强将,若用溃兵疲卒、市井南民御敌则“婴儿搏虎不足以喻其危”,(54)徐梦莘编纂:《三朝北盟会编》(乙集),《炎兴下帙二十三》,第632页。若引重兵南向则“国势微弱,人心离散”。(55)《宋史》卷四四七《唐重传》,第38册,第13186-13187页。同时,南渡派自身也存在驻跸建康或是驻跸临安的分歧,导火索便是前文提及的在临安修建临时太庙的问题。支持建康的大臣认为临安建明堂、修太庙意味着定为久居之地,“不复有意中原”,会造成人心涣散,“欲图中原,必驻跸于建康”。(56)徐梦莘编纂:《三朝北盟会编》(丙集),《炎兴下帙七十三》,第465页。支持临安的大臣赵鼎却认为驻跸之地应当有由中制外之势,“外设藩篱之固,中严堂陛之居”。(57)赵鼎撰,李蹊点校:《忠正德文集》卷三《奏议下·经筳论事第二疏》,第60页。临安是泽国险阻之“中”,建康是显敞冲要之“外”,舍临安而择建康便是舍本逐末,况且从前移跸建康已逾半年,而进取之计、中原人之归正者、响应而起者都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不审时度势就妄图恢复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是当南渡成为必然选择后,其他派系会迫于形势参与进南渡的讨论。以张浚和吕颐浩为例,二者原是主张先幸武昌、后趋关陕的重要成员。五路尽失后,西幸关陕已经变得渺茫,张浚便加入到建康对临安的争论中,成为请驾建康的中坚力量。他客观分析了淮南的军事地位,“无淮南,而长江之险与敌共”,(58)《宋史》卷一二〇《张浚传》,第9册,第11304页。金人水陆并进,则深处临安亦不能安;又晓以人心向背利害,以建康为中兴根本,他说:“人主居此,则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临安僻居一隅,内则易生安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59)张浚:《请车驾临建康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87册,第368页。吕颐浩也建议把经营重心放在“浙右为当”,原因是当前“汉中止可备万人粮”,且贸然携万兵西向会使江、浙、湖、广之地弃于盗贼,“皆非国家之有”。
(四)南移派
这一派的大臣以朱胜非、胡寅、赵鼎等为代表,主张驻跸襄阳、荆州或武昌等地。这些地方均位于北宋旧都以南、长江中游以北且与中原边缘相接的京西路和荆湖路之上,因此又可以称京湖派。这里需要注意南移派与南渡派有差异,前者认可长江中游以北的中原之缘,后者主张长江下游以南的中原之外。南移派大臣将驻跸范围圈定在距离故都不远的荆襄重地,应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地理因素。荆、襄、鄂三角地带是“居中央以制四方者也”,(60)翟汝文:《忠惠集》卷七《劝移跸荆南劄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24页。左顾川、陕,右视湖、湘,下瞰京、洛,是襟带吴、蜀的控扼要区和北临故都的重要门户。赵鼎曾言,“欲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欲经营关中,当自蜀中始;欲幸蜀中,当自荆南始”,(61)赵鼎撰,李蹊点校:《忠正德文集》卷一《奏议上·论西幸事宜状》,第20页。意即措置荆襄才是经营关中甚至恢复中原的必要前提。就连后来的蒙元名将阿里海牙都清晰认识到“荆、襄自古用武地”,而事实正是忽必烈攻克襄樊成为灭亡南宋的关键转折。二是宋金关系因素。这派大臣对宋金关系持有“先固本根,乃议攻战”的态度,“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62)赵鼎撰,李蹊点校:《忠正德文集》卷三《经筳论事第一疏》,第59页。认为应在有完胜、克城把握的情况下才能行攻战之策。这种想法虽同南渡派一样力主暂退缓图,却不像后者那般拘谨、保守,也不如西幸派、回銮派的恢复之诉求迫切、激进,而是量力经制,权宜行事。
比较而言,南移派与其他三派的驻跸理念有所不同,存在重形胜与据根本的思路差别。其他三派大臣并非没有认识到京湖“血气周流,首尾相应”的形胜地位,却不以此为中兴根据地,仅视之为拱卫根本的关键缓冲带。他们在各自的驻跸和进取方案中都有阐述,李纲断言,“朝廷保有东南,制驭西北,当于鼎、澧、岳、鄂一带皆屯宿重兵,使与四川、襄、汉相接,乃有恢复中原之渐”。(63)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五《湖广一》,第3517页。卫肤敏筹划建康驻跸时也认同“江陵、襄阳尤为要害”,(64)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建炎三年二月》,第460页。建议扼险屯戍,将荆襄作为保有东南的上游重镇。这种认知差异意味着南移派在驻跸争论中很难占据优势,宋高宗对荆襄地区的几次重视也仅是将其当成号令易通川陕或是屯兵控扼东南的重要一环。
三、中兴目标的“大一统”认知
宋高宗初期的驻跸之争反映了各派大臣对如何迁还中原的思想碰撞,而这种思想碰撞的发生实质上是南宋对“大一统”观念进行狭隘辩解的结果。在整个驻跸讨论过程中,回銮派昭告着南宋迫切恢复“天下人主”地位的中兴目标,“四海来享来王”(65)宗泽:《宗泽集》卷一《第二十一次乞回銮疏》,第26页。是所有驻跸观点的共同追求;西幸派延续着北宋以来迁都关中的历史余音,“非幸关陕不可”(66)朱熹撰,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九五上《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上)》,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822页。的最终目标是恢复中兴之功;南渡派代表着大多数宋人以守待战的现实取向,“愿稍安于此”(67)周应和撰,王晓波点校:《景定建康志》卷一《大宋中兴建康留都录一》,于王晓波、李勇先、张保见、庄剑点校:《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成为驻跸中原之外的缓图要旨;南移派其实是看重关键形胜所在,“俟中原尽复”(68)徐梦莘编纂:《三朝北盟会编》(丙集),《炎兴下帙六十一》,第349页。同样明示了他们对“大一统”理想的呼吁。各派系虽然对驻跸地点和中兴方案各执己见,却都是以迁还中原、重归正朔为目标做出的努力。
但换一角度看,南宋初期之所以允许驻跸观点的争鸣,出现迁还中原的思想差异,根本原因还是宋人将“大一统”的内涵塑造成有利于自身政权的狭隘观念。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八年间,驻跸之争经历了曲折反复、复杂多变的过程,大臣们不断调整观点,宋高宗适时取舍,极少有贯彻始终的看法,因为无论何时何派,他们志在中兴的同时都存在“欲保守,则失进取之利;欲进取,则虑根本之伤”(69)徐梦莘编纂:《三朝北盟会编》(丙集),《炎兴下帙七十三》,第465页。的顾虑,这种矛盾心理是贯穿驻跸之争始末的顽疾,也是南宋在面对北宋中后期以来南北政权对立局面时无法自愈的沉疴。所以,南宋即便想“循周、汉故事”,也因异于前代的政治环境而不得不把“华夷”关系、“中国”身份、“正统”地位奉为要义,这与汉唐盛世的“大一统”史实区别甚大,也与金人南渡的“大一统”追求全然不同。
首先,汉唐“大一统”是基于“天下”体系的一种理想主义政治秩序,而南宋“大一统”是基于“中国”身份的一种利己主义正统论。
西汉董仲舒以时间、空间、文化来定义“大一统”的主要内容:一为应天制月(改正朔),二为居必“中国”(别华夷),三为纯统色衣(制礼乐)。(70)董仲舒撰,曾振宇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应天制月,强调政权训“统”为“始”、接续前代承继天命的合法性,以战国阴阳家邹衍育于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为重要参考。汉之火德,唐之土德,宋之火德,皆循先代有德王朝之序,这在自汉唐至两宋的“大一统”观念中从未旁落。但居必“中国”作为强调天下秩序中心地位的代名词,至南宋已有很大变化。汉唐时期,中原王朝通过“外攘”“怀柔”“威服”手段建立起辐射周边的朝贡和册封体系,“中国”是这一体系的中心,统而不治、协和万邦的共主地位是汉唐凭借强盛国力宣示德威的成果。而北宋自立朝以来就与契丹(辽)政权成南北并立之势,契丹也积极建设以自身为中心的“大中央国”朝贡体系,澶渊之盟更加直接确立了辽、宋平等的政治格局,“中国”成为南北多方政权的竞争目标,传统上“蛮夷率服”的中原独尊地位遭到冲击。两宋之际,蔡绦无视燕云十六州未复的事实,称宋太宗攻破北汉而“天下始大一统”,“中国”开始凸显作为汉地中心的专有性,这种转变实际是为了将“大一统”的标准由“天下”重“一”转向“中国”重“统”。
到南宋时,自恃“中国”而居“大一统”之“正统”成为宋人对抗金人的自我防线。从“中国”来讲,其重心已经随着驻跸地点的南迁,呈现南向趋势。建炎三年,宋高宗暂留临安,时人评价该地“区区一隅”,宋高宗写给完颜宗翰的书信也称钱塘“在荆蛮之域”,但到绍兴九年天眷和议后,金人归还“河南”境土,宋高宗竟称移东南乃“虚内以事外”,中原故土已成“外”地,“荆蛮之域”变为“内”地。宋人对“中国”的界定不再以中原地域为限,而将其与政权本身对等起来,有了重政权而轻地域的特点,宋孝宗时有言“楮弊流行于中国”、宋宁宗时有言“敌反恣其暴,谓中国之无人”(71)蔡幼学:《育德堂奏议》卷六《请对劄子》,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即为明证。从“正统”来讲,这一时期“中国”内涵的演变首先便是南宋为了塑造自身“正统”地位而采取的自我封闭式辩解。宋室南渡,向金称臣,颠覆了“崇正统于中国”的传统优势,既然居必“中国”是“大一统”重要的资格条件,那么只有将政权与“中国”对等,才能确保“正之所在而统从之”。(72)周密撰,王根林校点:《癸辛杂识·正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页。理学家朱熹为了证明南宋的“正统”身份,还将“理欲之辨”“正统之余”等概念引进“正统”论中,斥责金人不可为“中国”,为宋高宗称臣求和的无奈之举进行辩解。(73)参见崔明德、穆琛:《朱熹民族关系思想初探》,《贵州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至此,两宋将“中国”不断南移,“中国”的变化又牵引着“大一统”内涵的变化。既然汉唐时期的“中国”与南宋时期有所不同,那么二者对“大一统”的理解必然不同。
其次,金人“大一统”是服务于疆域“大统一”的一种现实主义追求,而南宋“大一统”是服务于“严防华夷”的一种封闭主义华夷观。
女真人开国之初只侧重于对政权的建立,称皇帝号,国号“大金”,建元“天辅”,并遣使寻求辽国册封,与当初西夏李元昊上表北宋“册为南面之君”的做法如出一辙。伐辽诏书言“今欲中外一统”,也仅仅以金人本土为“中”,以辽疆域为“外”,意在建立取代辽政权的本位势力,对宋金关系尚且停留在“有南即有北,不可相无”(74)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四《太宗文烈皇帝二》,第65页。的认知上。两宋之际,金人尝试将中原地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宋之旧封……理宜混一”,(75)钱熙祚刻本:《大金吊伐录》卷四《行府告谕亡宋诸路立楚文字》,文殿阁书庄,第163页。“混一”之“一”有了并入中原的思想准备,甚至当宋高宗数次遣使,请以“局天蹐地”之小邦存于“荆蛮之域”时,金人指责他“窃人汴邑,僭称王号”。(76)钱熙祚刻本:《大金吊伐录》卷四《回康王书》,第175页。绍兴七年,金熙宗废刘豫伪齐政权,创建行台尚书省,对北宋旧疆由扶植“贤人”间接治理转向行政官署直接统治,将中原政治、经济实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对于南宋,从金太宗的“穷其所往而追”,到金熙宗的“俾尔越在江表”,再到海陵王的“天下有四主,南有宋,东有高丽,西有夏,若能一之,乃为大”,(77)《金史》卷一二九《奸佞列传》,第8册,第2782页。宋金之间时战时和的状态变换可以佐证金人内部并非完全满足于南宋称藩。金章宗时期(南宋宁宗时期),以《大金德运图说》为标志的“德运”之议、“正统”之论开始强调金政权的“大一统”资格,这一事件至少说明了两件事:一是金人对“大一统”思想存在由无到有、由被动认知到主动吸收的过程;二是在宋高宗时期,金人不断强化的“混一天下”意识还不是真正想要媲美汉唐“大一统”秩序的自觉,他们效仿汉制“大一统”的首要原因是这一观念契合了他们扩充疆域“大统一”的本意。
与金人相比,南宋的确意图恢复汉唐时期基于天下体系的“大一统”理想秩序,只是迫于北方民族的冲击,这种追求对华夷关系的重塑不是简单以“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78)《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三年十二月壬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6067页。为目的,而是真切达到“尊王攘夷”、隔绝夷狄融入“中国”的极端程度。宋人背离了“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79)韩愈撰,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注释》卷一《原道》,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0页。的古训,刻意消减“华夷”“中国”观念的地域和文化分量,将其与政治地位、民族身份紧密贴合,出现诸如“北戎强大,阴盛阳微,故阴雨为灾”,(80)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上)卷九,建炎三年四月尽六月,第220页。“谨华夷之辨,不使入居中土,禁其猾夏之渐”,(81)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七《元帝晋纪》,宋嘉定十一年刻本,第154页。这类“严防华夷”的言论层出不穷。这段时期对“内修政事,外攘夷狄”(82)晁公溯:《嵩山集》卷五一《试恭南进士策问一首》,清抄本,第834页。的号召除了政治排他性外,还有狭隘的文化和血缘排他性。从南宋政权自身而言,自恃“中国”、隔绝夷狄是他们为了合法践行“大一统”思想而采取的正当做法,自我闭合的思想倾向与宋高宗初期不断南迁的驻跸经历相互配合,使得决策集团议和、南渡、退守、缓图的一系列抉择具有了合理性。但从整体历史发展而言,契丹辽政权、党项西夏政权、女真金政权,以及后来兴起的蒙元政权,都主动学习中原政治体制和文化模式,建立起堪与两宋齐驱又兼糅民族特色的一套“大一统”观念,南北之间封建化差距的逐渐缩小、民族思想的不断破垒和华夷身份的重新洗牌成为10至13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可见,南宋将华夷关系不断割裂的做法,与辽夏金元积极促成的民族交融进程存在明显的利益相悖。既然宋、金对华夷身份的界定不同,那么他们对“大一统”的追求必然相异。
四、余 论
宋高宗初期关于驻跸问题的争论,无论是对南宋政权的发展结局,还是对古代中国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的历史走向,都具有关键作用,是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一块重要历史拼图。西幸派重形胜、求恢复,所以选择川陕;回銮派重人心、求正朔,所以选择汴京;南渡派重缓图、求退守,所以选择江浙;南移派重形胜、求退守,所以选择京湖。从南宋之初西幸派、回銮派、南移派、南渡派的势均力敌,到中原、关陕相继沦陷后南渡派的一家独大,驻跸之争体现的不仅是宋金关系渐趋稳定的变化趋势和宋高宗决策集团退守缓图的主流态度,更是各派大臣皆以迁还中原、重归正朔为目标的终极诉求,以及“大一统”思想传承至此南弛北张的蜕变历程。前二者是表,后二者是里,驻跸之争由表及里展现了南宋在多政权并立时期的历史定位。
辽宋夏金元时期实为由复数“中国”走向单数“中国”的过渡时期,(83)赵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7页。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分别建立的辽、夏、金、元政权接续更迭,与两宋政权对峙。南宋作为曾长期自恃“正统”的汉人建立的政权,在这场变局中发挥的承接和促进作用不容忽视。从政治格局上讲,这一时期不再是中原政权独尊、四方来朝的“大一统”模式,汉唐时期理想化的天下体系遭到瓦解。南宋退据江南使汉人政权的优势地位消失,其成为众多追求实现“大一统”格局的政权中的平等一员,这才是真正体现“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典型。从民族关系上讲,这一时期不再是以“中国”为中心、内华外夷的大汉族秩序,辽夏金元有针对性地“用夏变夷”,加速了各民族的全面互动交融。南宋向金称臣后汉人群体的身份发生颠覆,成为参与进不同政权之间民族凝聚和意识认同的重要部分,这也是促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步骤。这样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宋高宗初期的驻跸之争所造成,反之又对南宋政权造成巨大冲击。一方面,南方文人儒士为了标榜正统,开始凸显“中国”作为汉地中心的专有性和作为汉人身份的唯一性,将“大一统”标准由汉唐时期的“天下”重“一”转向服务自身的“中国”重“统”。另一方面,北方深处金元的儒士群体有了直面华夷身份、变通“中国之道”的契机,主动调适“中国”作为道统文脉的包容性,将“大一统”塑造成与金元统治者疆域“大统一”意识相得益彰的一种理念。南北双方对“大一统”内涵的反向认知,决定了南宋“大一统”在承继汉唐“大一统”理想的同时,又以偏执的严防华夷思维刺激了金元“大一统”的迅速发展,这种南弛北张的双向互动缩小了封建化进程的差距,成为“大一统”内涵蜕变的助力剂,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式更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