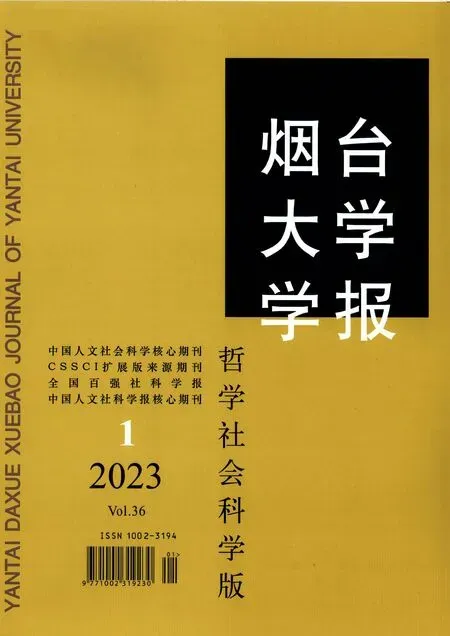新冠感染疫情下西方排外主义的发展态势与走向
——基于国外文本讨论的海外华人问题评析
刘 泓,田 耘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民族学系,北京 100081)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1)为行文方便,以下多简化为“新冠疫情”或者“疫情”。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最大威胁。目前,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达六亿,死亡人数超六百万。即使疫情已经造成了惊人的损失,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流行”短期内仍难以看到尽头,疫情常态化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国际人员流动的背景音,疫情带来的影响已经从多个方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从国际视角看,全球经济受阻,供给端复苏困境造成了需求端的活力下降。全球范围人口流动受挫,全球化进程的推进面临诸多困难,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本土主义复苏的加持下,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排外主义加剧了现有的族裔歧视现象,对全世界移民与少数群体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冠疫情的政治化、标签化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受到了污蔑,海外华人随之处于这场“污名化狂欢”的风口浪尖。本文旨在通过评析国外学界新冠疫情视角下的海外华人研究,探讨新冠疫情之下西方的排外主义表现形式及其产生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一段时间西方排外主义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一、新冠疫情下西方排外主义的表现
通常说来,西方排外主义主要指西方国家土生族裔或先来的移民对后来的移民在心理上和行为上的歧视与排斥,排外主义与多种社会思潮联系密切、相互交融。新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实质上都是排外主义的延伸或演化。随着支持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方国家的普遍兴起,排外主义的回潮已经完成了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变。随着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对疫情污名化的出现,西方排外主义较疫情之前更具攻击性和针对性,其表现形式也更加具体。疫情政治化、媒体污名化与仇恨犯罪,成为防控新冠疫情过程中针对海外华人的西方排外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疫情政治化
虽然历史上将疾病与“外国”和“外国人”等相关联的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曾出现,但并非每一次疾病流行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排外主义爆发与种族主义盛行,疫情与排外主义之间并非存在必然联系。但当国家通过偏执的言辞和排斥政策暗中强化、鼓励和延续排外情绪时,(2)Gover Angela, Shannon B. Harper and Lynn Langton, “Anti-Asian Hate Crim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xploring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45, no. 4 ,2020, pp.647-667.疫情的政治化则会将疫情带来的不安激发为过激的排外情绪。
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出台的传染病命名方法强调,切断具体地区与疾病之间的关联性,避免对地理位置与种族群体的污名化、避免疫情政治化,这对当今社会十分重要。尽管大多数西方国家与公职人员最终放弃了“中国病毒”等言论,但不管这种改变是出于突然的“利他理解”还是出于“政治算计”,其损害已经切实产生,“中国病毒”的提法将新冠疫情与中国和海外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西方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的疫情的政治化倾向,将排外主义比较系统地体现出来。托德·哈特曼(Todd Hartman)的研究指出,疫情期间西方的反移民排外情绪与西方民众感受到的来自病毒的威胁直接相关:只有当受访者焦虑程度较高时排外情绪才会显现,而病毒与移民之间的关联性则是人为创造的。(3)Hartman Todd, Thomas Stocks, Ryan McKay, Jilly Gibson-Miller, Liat Levita, Anton P. Martinez, Liam Mason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ffects on Nationalism and Anti-immigrant Sentiment”,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021, pp. 1-12.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举动造成了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而相关的“紧张情绪”在本就边缘化的群体身上被成倍放大。
伍德蒙教授(Edmond S. W. Ng)指出,发表诸如“中国病毒”与“中国过错”等煽动性言论,在西方国家常常成为政客们逃避正面回答紧迫问题的有效方式。(4)Ng Edmond, “The Pandemic of Hate is Giving COVID-19 a Helping Han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102, no. 6, 2020, pp. 1158.西方国家的相关态度也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时任巴西教育部长亚伯拉罕·温特劳布(Abraham Weintraub)甚至提出,COVID-19是中国控制全球计划的一部分,(5)Agence France-Presse, “China Outraged after Brazil Minister Suggests Covid-19 is Part of ‘Plan for World Domination’”, The Guardian, 7 April 2020.民众对中国的愤怒被迅速转嫁到华人,乃至亚裔美国人身上。(6)Li Yao and Harvey L Nicholson Jr, “When ‘Model Minorities’ Become ‘Yellow Peril’—Othering and the Racialization of Asian American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Sociology Compass, no. 2, 2021, pp.1-13.泰勒·雷尼(Tyler Reny)表示,疫情初期的西方精英言论导致排外态度与对疫情的担忧交织在一起,而为了获得选举胜利,特朗普政府主动迎合排外主义受众的心理预期,有意无意地加深了这种联系。(7)Reny Tyler and Matt Barreto, “Xenophobia in the Time of Pandemic: Othering, Anti-Asian Attitudes, and COVID-19”, 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 , 2020, pp. 1-24.
部分西方国家的主要政治领导人拒绝佩戴口罩,声称佩戴口罩是个人软弱或缺乏男子气概的标志。(8)Karni Annie, “Pence Tours Mayo Clinic and Flouts Its Rule that All Visitors Wear a Mask”, New York Times, April 28,2020.部分政府官员也公开支持反对戴口罩的声音,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口罩令”等强制措施涉嫌危险,而忽视了“这些人在行使他们相信的权利的同时,将其他人置于危险之中”的现实。(9)Ren Jingqiu and Joe Feagin,“Face Mask Symbolism in Anti-Asian Hate Crim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no. 5, 2021,pp. 746-758.
(二)媒体污名化
周秀华教授(Chou Sylvia)认为,在当今以种族不平等为特征的西方政治体制中,新冠病毒感染等流行病加剧了受压迫群体的边缘化趋势,而媒体歧视性的报道是促成这一现实的重要推手。(10)Chou Sylvia, Wen-Ying and Anna Gaysynsky, “Racism and Xenophobia in a Pandemic”, Interactions of Online and Offline Worlds,2021,pp. 773-775.疫情的政治化使得部分国家错过了遏制病毒蔓延的黄金时期,而社交媒体在“信息茧房”的作用下更是加剧了排外主义愈演愈烈的趋势。
当未知传染病新冠病毒感染出现时,西方公共传媒与私人社交网络都参与了信息的传递与事件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体在此次疫情初起阶段起到了重大的误导作用,对健康风险的关注在第一时间被移植到了带有种族意味的新移民的讨论上。德·罗莎教授(De Rosa)追踪了疫情初起阶段意大利公共媒体的报道倾向。在意大利的案例中,大众媒体最初扮演了一个安抚民众的角色,通过将疫情称为流感来弱化危机的严重性以稳定民众情绪。当西方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对疫情形势的理解发生分歧后,大众媒体陷入了两难境地,在健康优先还是经济优先的选项上稍作犹豫后,大众媒体选择了被称为政治宣传的一环:通过将新冠疫情的爆发归因为中国人与动物之间的“野蛮的”接触,从而来减轻疫情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威胁意象。意大利媒体在疫情初期“成功地将疾病原因投射到外部群体身上”,以此为大众提供了虚假的安全感。(11)De Rosa, Annamaria Silvana and Terri Mannarini, “The ‘Invisible Other’: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COVID-19 Pandemic in Media and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Papers on Social Representations, no. 2, 2020, pp. 5-10.
对比文献数量可以发现,西方社交媒体吸引了诸多学者们的目光,对排外情绪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信息茧房”的存在导致排外情绪在同一群体中不断深化。赛夫丁·艾哈迈德(Saifuddin Ahmed)对疫情期间社交媒体使用、疾病风险感知与对中国移民的偏见态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疾病风险感知与中国移民的定型和偏见呈正相关。其研究显示,仅使用社交网络获取相关信息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形成刻板印象与极端偏见。对经常参与讨论交流并拥有更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的受访者而言,形成刻板印象的机会则显著降低。(12)Ahmed Saifuddin, Vivian Chen Hsueh-Hua and Arul Indrasen Chib, “Xenophobia in the Time of a Pandemic: Social Media Use,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 Against Immigrants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2021, pp.1-18.济教授(Jiun-Yi Tsai)的文章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观看“左翼”新闻、相信数据同时拥有更多信息来源渠道的受访者表现出的排外情绪相对较低。(13)Tsai, Jiun-Yi, et al, “Intergroup Contact, COVID-19 News Consump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igital Media Trust on Prejudice toward As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Cross-sectional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20, pp. 1-16.赖特教授(Chrysalis Wright)考察了美国大学生群体对新冠疫情相关虚假信息的分辨能力与其排外主义倾向之间的关联性。他的研究数据表明,21%的受试学生无法识别与疫情相关的虚假信息,白人受试者排外心理的发生率较高,感染新冠病毒的受试者、无法识别虚假新闻的受试者与产生强烈排外偏见的受试者群体高度重合。(14)Wright Chrysalis L and Hang Duong, “COVID-19 Fake News and Attitudes toward Asian Americans”, Journal of Media Research, no. 1,2021, pp.5-29.有学者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假说,认为是强烈的排外情绪导致受试者难以正确处理疫情相关的信息。(15)Paschen Jeannette, “Investigating the Emotional Appeal of Fake News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 Contributions”,Journal of Product & Brand Management, no.29(2), 2019,pp.223-233.卡莱布·齐姆斯(Caleb Ziems)对社交网络的分析表明,“仇恨”和“反仇恨”的用户彼此间开展了广泛互动,两者并非生活在孤立的两极社区中。此外,齐姆斯发现所谓“仇恨”具有传染性,与“反仇恨”账号相比,宣传仇恨情绪的社交账号吸引了更多的关注。(16)Ziems Caleb, Bing He, Sandeep Soni and Srijan Kumar,“Racism is a Virus: Anti-asian Hate and Counterhate in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2020, pp.90-94.
周文英教授(Wen-Ying Sylvia Chou)比较了社交媒体中“新冠病毒”和“中国病毒”的使用情况,分析了社交媒体中反亚裔情绪的表达方式问题。针对2020年3月9日至3月23日之间发送的推特研究发现,在495,289个与冠状病毒相关的标签中,约有20%表现出反亚裔情绪,而在777,852个与“中国病毒”相关的标签中,这一比例约为50%。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这一调查结果在进一步证实社交媒体上语言的污名化潜力的同时,也意味着现代社交媒体缺乏自主应对排外主义的能力。(17)Sylvia Chou, Wen-Ying and Anna Gaysynsky,“Racism and Xenophobia in a Pandemic”,Interactions of Online and Offline Worlds, 2021,pp. 773-775.
(三)仇外心理和种族偏见
尽管仇外心理和种族偏见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西方就已经存在,但新冠疫情的爆发将既有的针对特定群体的仇恨激发出来,为“仇恨犯罪”提供了借口。学者们认为,新冠疫情下的“仇恨犯罪”是由对疾病传播的无知和恐惧所驱动,谣言与错误信息是激化这种恐惧的重要原因。有些反应可能源于对历史事件和文化规范缺乏客观认识和理解。
2020年3月19日至5月15日,亚裔美国人开发的网站Stop AAPI收到了近1900份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歧视亚裔美国人的报告。具体事件包括抵制亚裔餐馆,欺凌亚裔美国学童,在公共场所对亚裔美国人进行口头和身体攻击等。(18)Ren Jingqiu and Joe Feagin, “Face Mask Symbolism in Anti-Asian Hate Crim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no. 5(44), 2021, pp. 746-758.学者们发现,大量疫情之下出现的“仇恨犯罪”以亚洲人为防控疫情而佩戴口罩作为开端。口罩作为亚裔象征之一,引发了西方部分公众强烈的排外情绪。
即使从排外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口罩的抵触也是不理智的。熙安财教授(Hee An Choi)认为,口罩作为一种意象在疫情背景下被赋予了政治与文化意义,符号化的口罩作为权力与控制的象征,针对亚裔群体的种族歧视与暴力行为合理化。(19)Choi Hee An and Othelia EunKyoung Lee, “To Mask or To Unmask, That Is the Question: Facemasks and Anti-Asian Violence During COVID-19”,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Work ,2021, pp. 1-9.任景秋教授(Ren Jingqiu)指出,仇恨犯罪的实施者所展现出的排外情绪恰恰源自他们与亚裔的共同点,亚裔美国人与白人在阶级、国籍与文化等方面的关联性日益增长,而在疫情中佩戴口罩作为防护,几乎成为唯一可以异化亚裔身份的象征。(20)Ren Jingqiu and Joe Feagin, “Face Mask Symbolism in Anti-Asian Hate Crim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44, no. 5,2021, pp. 746-758.
“非典”和MERS造成的死亡与伤痛在东亚地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集体创伤记忆,(21)Wong Tessa, “Coronavirus: Why Some Countries Wear Face Masks and Others Don’t”, The BBC,March 23, 2020.而亚洲之外的公民则可能缺乏此类意识。在经历过传染病爆发的国家,戴口罩被视为避免疾病传播的公民责任,甚至是对抗致命疾病的反抗象征。(22)Ng Edmond, “The Pandemic of Hate is Giving COVID-19 a Helping Han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no.6(102), 2020, pp. 1158.学者在对比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化后发现,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等亚洲国家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已形成使用防护口罩的传统。(23)Lynteris Christos, “Plague Masks: The Visual Emergency of Anti-Epidemic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Medical Anthropology: Cross Cultural Studies in Health and Illness, no.37 (6),2018, pp. 442-457.任景秋指出,“如果你不在公共场合使用口罩,别人会对你另眼相看,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害怕你成为潜在的病毒传播者,也意味着你缺乏社会责任感”。(24)Ren Jingqiu and Joe Feagin, “Face Mask Symbolism in Anti-Asian Hate Crim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no.44(5),2021, pp.746-758.亚裔对戴口罩的看法不仅仅在于注意个人保护,而是重视集体道德理想和公民行动,其核心在于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利益。
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口罩也同样被赋予了特殊含义。面部遮盖作为文化象征一直以来与罪犯存在联系。在疫情流行的最初几个月,媒体对新型冠状病毒问题的描述,甚至放大了相关的刻板印象。有学者在统计后指出,美国多地媒体使用亚裔戴口罩的相关照片比例过高。疫情中华裔最常见形象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戴着面具的亚洲人,看起来孤独且严肃。”(25)Burton Nylah, “Why Asians in Masks Should Not be the ‘Face’ of the Coronavirus”, Vox, March 6,2020.公开佩戴口罩的有色人种在这种情况下引起了相应的负面情感投射,针对戴口罩的人展开的仇恨犯罪,在西方口罩文化的背景下从一定程度上被合理化了。
“仇恨犯罪”是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历史嵌入性复制和累积效应下的集中表现,也就是说,西方国家施暴者实施暴力的目标是通过将亚裔标记为“他者”,从而使其失去被平等对待的资格,通过破坏其归属感达到排除“他者”的最终目的。(26)Kim David Haekwon and Ronald Robles Sundstrom, “Xenophobia and Racism”, Critical Philosophy of Race ,no.2(1), 2014, pp. 20-45.从这个意义上说,“仇恨犯罪”推动并延续了带有种族意味的社会排斥,维护了施暴者乃至施暴群体的优越感,使其在新冠疫情之下维持着对正常秩序的某种掌控感。
二、西方排外主义表象背后的“他者”认知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将西方国家某些具有地方属性的社会现实戏剧性地呈现出来,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民主主义或世界主义的诸多臆想遭到了驳斥,基于阶级、民族和性别等相互交叉的不平等现象被揭露出来,针对基于亚洲面孔的“中国恐惧症”“社会耻辱感”和身体攻击的事件在西方国家纷纷出现。通过探究“瘟疫”与外来民族之间的关联性可以发现:新冠疫情下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数量飙升并非偶然,“瘟疫”与亚洲移民之间的关联性在欧洲等地早已建立。
从16世纪梅毒在欧洲和亚洲的传播开始,“瘟疫”与“他者”之间的关联就已经被建立起来,在此期间几乎每个受到影响的国家都将梅毒的爆发归咎于邻国或敌人。(27)Tampa Mircea, Matei Clara, Benea Vasile and Georgescu Simona Roxana, “Brief History of Syphilis”,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Iife, no.7, 2014, pp.4-10.2001年英国口蹄疫爆发时,亚裔特别是华人社会成为了”瘟疫”的替罪羊,当个体缺乏关于“他者”的可靠信息时,基于特征的归因便似乎很自然地将来自与外部群体成员相关的社会类别进行污名化处理。(28)美国第一部以种族为基础的排外法案——1882年《排华法》在担忧亚洲移民会对西方文化构成威胁的情况下设立。1899年12月,在檀香山发生的淋巴腺鼠疫病例,引起了夏威夷卫生当局的过激反应,当地4500余名华人被关入隔离营,患者的房屋则被付之一炬,华人因民族身份被当作了传染源。尽管随后确认了疾病的传播途径为老鼠与跳蚤,但中国城地区的华人在疫情期间依旧经历了被强制隔离、疫苗强制接种等不公待遇。因相关分类引发的刻板印象和耻辱感随之被激发,并对本群体以外的社会成员滋生偏见,与“他者”的互动被赋予了非理智性的潜在后果。在防控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与病毒起源并无关联的海外华人也经历了“他者化”的过程,部分希望避免潜在疾病的西方民众,将病毒带来的未知的恐惧转移至华裔群体。2020年4月17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表了一篇推特评论,批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于当年2月在旧金山唐人街访问中支持亚裔美国人的行为,同时在另一条推文中宣布他已经“关闭了通往中国的边界”。这样的措辞模糊了中国与华裔之间的界限,增强了“中国”这一概念中持久的“他者”意味。
探寻相关表象背后的动因,可为认识新常态下可能发生的社会变化提供一定的基础。(29)Roberto Katherine, Andrew Johnson and Beth Rauhaus, “Stigmatization and Prejudi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 no.42(3), 2020, pp. 364-378.有学者通过分析意大利媒体对疫情的报道,总结了意大利在疫情流行初期的社会状况。意大利作为2020年2月前后欧洲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在第一批感染者确诊之前,其媒体便展现出对“亚洲人”“中国人”“黄种人”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假设。意大利民众针对“东方人”和“中国人”的偏见、仇恨言论与身体攻击,一方面揭示了新冠病毒重启种族主义机器的具体路径,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排外主义对科学与逻辑的抵触。经过中国经验验证的防疫措施,在带有偏见与仇恨的言行中遭到质疑,而排外主义则破坏了人们对当前局势进行理智判断与反省的路径。(30)Miyake Toshio, “‘Cin Ciun Cian’(Ching Chong): Yellowness and Neo-orientalism in Italy at the Time of COVID-19”,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no.47(4), 2021,pp. 486-511.
将”瘟疫”与外来者相联系也绝非西方国家的特权。在智利,新冠疫情同样激起了强烈的排外情绪,种族主义与反华热潮卷土重来。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文化话语,强烈地再现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有学者认为,这场流行病揭示了智利政府最近在“中国崛起”的时代试图表达多元文化主义的肤浅和问题性。(31)Chan Carol and Maria Montt Strabucchi, “Many-faced Orientalism: Racism and Xenophobia in a Time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in Chile”, Asian Ethnicity, no.22(2), 2021, pp. 374-394.与亚裔人口众多的秘鲁或巴西不同,智利的亚洲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与智利的民族历史和身份无关。华人乃至亚洲人被视为“属于”其他地方,并被视为最新的移民和“永久的外国人”。(32)Chan Carol, Maria Montt Strabucchi and Creating and Negotiating, “Chineseness through Chinese Restaurants in Santiago, Chile; and Montt Strabucchi and Chan, Questioning the Conditional Visibility of the Chinese”, Asian Ethnicity, no.22(2), 2021,pp. 374-394.与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不同,“中国—智利人”或“智利—中国人”听上去既笨拙又不正确。出生于智利或被认定为(东亚)后裔的智利人,往往被描述为“一个真正的智利人,但有一张中国人的脸”,而“中国人”“亚洲人”或“东方人”则被认为是外国人,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则是“不可理解的”。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中国人被比喻为吃老鼠和蝙蝠的人,因此与肮脏、不可信、服从权威、不思考相联系。智利所发生的事情与其他地方(东亚)少数民族所发生的事情相似,那里的社会回到了其最恶劣的偏见模式。卡罗尔教授还指出,新冠疫情对中国人或亚洲人的代表性,揭示了特定东方—西方二分法的新性质。新冠感染疫情见证了关于中国人在智利“他者化”的观念的加强,并揭示了最近政府批准的试图将智利表述为一个全球化、多元文化、多元化国家的脆弱性和肤浅性。(33)Chan Carol and Maria Montt Strabucchi, “Many-faced Orientalism: Racism and Xenophobia in a Time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in Chile”, Asian Ethnicity ,no.22(2), 2021, pp. 374-394.
不论大规模的仇恨犯罪将持续多久,新冠疫情都已经加深了世界各地华人的“他者”化。在历史上,这种“他者化”的进程始终处于反复加深的过程之中,意识到“他者化”的存在,则是从民族化的恐惧中吸取经验教训的第一步。解决后疫情时代排外主义所带来的问题,首先需要防止““瘟疫””与“他者”之间关联的进一步加深,这不仅需要生活在海外特别是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华人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公共管理部门层面的系统调整。
三、新冠疫情下排外主义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海外华人面临的压力
在防控疫情、排外主义与经济衰退的多重压力之下,生活在西方国家的海外华人面临着多层面的压力。在疫情应对方面,海外华人大多佩戴口罩,在保持个人卫生与社交距离方面的表现比较积极,对疫苗的排斥也不显著。(34)Andrew Hay and Maria Caspani, “Fake flyers and Face-mask Fear: California Fights Coronavirus Discrimination”, Reuters, February 14,2020.但由于华裔心理健康服务的使用频率普遍偏低,后疫情时代海外华人的心理问题值得关注;在应对排外主义与仇恨犯罪方面,海外华人学生往往希望通过线上教育中的交流机会减轻偏见;在疫情影响之下华裔经济受到一定冲击,在排外主义影响之下其经济复苏还需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有学者分析了当前美国的疫情数据,从现有数据来看,亚裔美国人确诊比例在17个州中高于平均确诊比例。(35)Le Thomas, Leah Cha, Hae-Ra Han and Winston Tseng, “Anti-Asian Xenophobia and Asian American COVID-19 Dispar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no.110(9), 2020, pp. 1371-1373.有研究显示,华裔美国人在预防新冠病毒感染中最为积极,包括接种疫苗、注意个人卫生、保持社交距离和阅读相关新闻文献等。数据显示,亚裔美国人倾向于具有高水平的自我感知健康素养,这种素养与其社会人口因素(如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平)基本无关。(36)Hyunsuk Jeong, Hyeon Woo Yim, Yeong-Jun Song, Moran Ki, Jung-Ah Min, Juhee Cho and Jeong-Ho Cha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People Isolated Due to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Epidemiology and Health, no.38, 2016, pp.1-7.基于相关研究结果,学者们对市政管理部门提出建议,认为遏制反华裔排外浪潮迫在眉睫,其中与华裔社区合作,推动疫苗接种进程将有助于社区防疫工作的快速推进。华裔心理健康服务使用率较其他民族而言显著偏低,由于排外主义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当得到重视。(37)Wu Cary, Yue Qian and Rima Wilkes, “Anti-Asian Discrimination and the Asian-white Mental Health Gap during COVID-19”,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no. 44(5),2021, pp. 819-835.尽管新冠疫情对种族主义心理影响目前还不清楚,但它带来的压力可能严重损害华裔美国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关于大规模创伤和疾病爆发的研究表明,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焦虑、药物滥用)和亚临床应激反应(如愤怒、恐惧、睡眠问题)持续数月或数年的可能性,在后疫情时代存在显著提升的可能。(38)Goldmann Emily and Sandro Galea,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of Disasters”,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no.35(1), 2014, pp.169-183.对于华裔美国人来说,“将新冠疫情政治化”和“寻找替罪羊”举措所导致的排外情绪,可能会产生严重和长期的负面影响,并可能导致自杀想法的增强。(39)Chen Zhansheng and et al, “Life Lacks Meaning without Acceptance: Ostracism Triggers Suicidal Though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no.119(6), 2020, p.1423.感到不受欢迎或受到威胁的心理状态,使其容易产生过度紧张、焦虑、持续恐惧、愤怒、内疚或羞耻等创伤症状。(40)Cheng Hsiu-Lan, “Xenophobia and Racism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Mental Health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nd Scholarship, no.3(1), 2020, p.3.有学者对疫情之下荷兰华人的心理健康进行了研究,认为华人对病毒的恐惧与其他民族相比并没有明显不同,是排外主义、社会隔离与种族主义对华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尽管病毒并非具有族裔性,但随之而来的排外主义为美国的华裔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压力。新冠疫情使得华裔美国人遭受了“仇恨犯罪”的威胁。疫情爆发以来,华裔在一定程度上长期被认为是对美国社会经济与公共健康的威胁,一些华裔美国人开始选择隐藏自己的华裔身份或声称自己是美国人,以防止“仇恨犯罪”袭击。有学者曾指出,如今的美国已经将华裔美国人视为“荣誉白人”,但目前的危机已经清楚地表明,相关认识充其量只是一种错觉。斯泰西·黛安教授(Stacey Diane)指出,增强批判意识可以有助于减少排外主义与种族主义对华裔的影响。(41)Litam Stacey, Diane Araez and Seungbin Oh, “Ethnic Identity and Coping Strategies as Moderators of COVID-19 Racial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s among Chinese Americans”, Counseling Outcom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no.13, 2020, pp.101-105.一项研究表明,鼓励华裔美国人彰显其美国性与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帮助他们获得大多数白人的认可。前总统候选人安德鲁·杨(Andrew Yang)建议华裔美国人通过穿红、白、蓝三色衣服来反对种族主义,凸显其美国性。(42)Yang Andrew, “We Asian Americans Are not the Virus, but We can Be Part of the Cur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020.但事实证明,这些做法并没有直接解决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问题。大多数袭击事件发生在大城市,如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美国人传统上认为这些空间比美国其他地区更自由、更宽容。但仅在纽约市,截至2020年4月,纽约市警察局的“仇恨犯罪”工作队就已经调查了14起案件,其中所有受害者都是亚洲人。堪萨斯州一位州长说,他的城镇是安全的,“因为它只有少数中国居民”。目前尚无法确定这种现象是否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但可以确定的是,反华事件和“仇恨犯罪”的潜在上升趋势表明,西方国家白人民族主义和排外心理在显著增长。(43)Tessler Hannah, Meera Choi and Grace Kao, “The Anxiety of Being Asian American: Hate Crimes and Negative Bias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no.45(4), 2020, pp.636-646.
新冠疫情控制失利给西方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与医疗风险,在少数族裔群体中被放大了。这相当于一种结构性暴力,使得包括华裔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少数族裔移民在疫情面前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首先,新冠病毒感染在这些群体之中的发生率较高,华裔等少数族裔移民群体的感染风险更大,因为他们更可能生活在贫困和拥挤的住房中,工作或工作的方式更不稳定。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停止工作不仅是一种生活不便,而且是不现实的。增加了感染几率的群体也更易将疾病传播到拥挤和高密度居住区之中。克里斯托弗·胡(Christopher Ho)指出,44%的NHS医疗工作者是非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人口,华裔医务人员同样在经历排外主义带来的仇恨犯罪的攻击。(44)Ho Christopher, Alice Chong, Anand Narayan, Erin Cooke, Francis Deng, Vikas Agarwal, Carolynn DeBenedectis, Lori Deitte, Ann Jay and Nolan Kagetsu, “Mitigating Asian American Bias and Xenophobia in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ow You can Be an Upstand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no. 17(12), 2020, pp.1692-1694.
其次,在西方国家的非裔、亚裔等少数族裔更容易出现重症感染病例。迄今为止的研究都表明,患有基础性疾病将会增加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导致重症的风险。(45)Wei-jie Guan,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in China”, N Engl J Med, 2020, pp.1708-1720.如糖尿病或心脑血管病等在非裔、亚裔等少数族裔中更为高发。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中33%的住院患者为非洲裔美国人,而白人则为18%。(46)Shikha Gar and et al, “Hospitalization Rat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Iaboratory-confirmed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NET, 14 States, March 1-30, 2020”, 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 no.69(15), 2020, pp.458-464.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许多移民群体,特别是非法移民,在疫情中难以得到帮助,随着这一群体病情的恶化,疫情的传播也更加不受控制。
对全球知识流动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中国与西方大学交流项目,也在疫情爆发后出现诸多变化。在疫情爆发前,旅美中国留学生人数位列世界第三。2020年全球流动性的相对停滞,使得预备留学人员开始谨慎地对待海外留学的决定,学者们认为,如果没有更多的压力,新冠疫情之下的教育移民的流动性将大幅受挫。首先,西方国家对中国研究人员和学生的各种怀疑日益增加。其次,以防控疫情为借口的暴力犯罪和反亚裔事件的频繁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开始怀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安全性。最后,考虑到西方国家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管理不善,中西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恢复。尽管一些西方国家承诺会遏制其中一些问题,但中国学生和家长对留学西方的看法已经开始发生改变,特别是随着中国近年来着力改善国内高等教育部门的举措,会使得一些学生的留学计划进一步受到影响。(47)Allen Ryan and Ying Ye, “Why Deteriorating Relations, Xenophobia, and Safety Concerns Will Deter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to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o.11(2), 2021, pp.1-7.秋叶大辅列举了疫情期间美国高等院校中发生的排外事件,认为学校与教育者有责任减轻疫情带来的排外情绪,创造平等和谐的学术氛围。(48)Akiba Daisuke, “Reopening America’s School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rotecting Asian Students From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Frontiers in Sociology, no.5, 2020, pp.1-7.
疫情对美国等国家华裔社区的经济情况的影响最为严重。斯黛拉教授评估了疫情以来纽约的餐馆、食品零售店和新鲜农产品供应店的关闭情况,对新冠病毒流行高峰期纽约的六个社区进行了横向的比较研究,认为与纽约其他社区相比,华裔社区关闭的食品企业比例更高,华裔少数民族社区的经济产业受到疫情的影响最大。(49)Stella Yi, Shahmir Ali, Rienna Russo, Victoria Foster, Ashley Radee, Stella Chong, Felice Tsui and et al, “COVID-19 Leads to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Food Retail Environment in New York City: May-July 2020”,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Minority Health, no.5, 2021, pp. 1-7.
疫情爆发后,在一些西方国家华裔社区生活的老年华裔移民感受到了更多不便。年龄歧视附加于排外主义之上,使得老年华裔移民的生活处境更为窘迫。很多老年受访者自我认定为高风险群体,这导致他们比年轻人更加容易进行自我隔离,在其流动性和社会互动性开始减少的同时,他们所面临的心理压力也随之增大。(50)Hwang Tzung-Jeng and et al, “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 no.32(10), 2020, pp.1217-1220.此外,该项研究还对老年长期护理机构、老年人死亡率,以及媒体所报道的对老年歧视的上升给予了关注。(51)Qianyun Wang, Ka Kei Liu and Christine Ann Walsh, “Identities Experiences and Impa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ld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no.14(2), 2021, pp. 1-19.该研究指出,较年轻人而言,年长的华裔移民更难获取与疫情相关的信息,新冠病毒流行下的老年华裔群体遭受了人际交流与互联网的双重排斥。(52)Seifert Alexander, Sheli Cotten and Bo Xie, “A Double Burden of Exclusion? Digital and Social Exclusion of Older Adults in Times of COVID-19”,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no.76(3),2020, pp. 99-103.
四、西方排外主义的发展走向
从历史上看,由疫情衍生的排外主义早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对海外华人群体产生了影响。新冠疫情爆发后,西方排外主义的蔓延不仅进一步造成了社会割裂,其带来的反智行为也给疫情防控造成了诸多阻碍。后疫情时代的排外主义将走向何处,成为各方广泛关注的问题。新冠疫情之下,海外华人面临的排外主义使得他们的生活相比其他民族而言更加难以回归正轨。
防止排外主义恶性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个人层面、社会层面与国家层面共同努力。从个人层面上看,排外主义激发了海外华人身份认同度的提升,海外华人内部更加团结,反抗排外主义的力量随之得到加强。从社会层面上看,加强各渠道沟通交流,防止海外华人被进一步边缘化,将有助于削弱因防控疫情所带来的社会偏见。从国家层面上看,消除、降低“仇恨犯罪”率不仅是对少数族裔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更是当前西方国家遏制社会割裂的重要举措。
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归属感与自我意识觉醒等议题已吸引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海外华人积极反抗排外主义压迫的努力有目共睹。(53)Gao Zhipeng, “Unsettled belongings: Chinese Immigrants’ Mental Health Vulnerability as a Symptom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no.61(2), 2021, pp.198-218.李勇教授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法国华人群体对排外主义的反抗行为。他认为,相较一代移民而言,越来越多的二代移民已意识到旅居法国的中国人持续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并通过互联网媒介组织了相应的反击。他指出,新冠疫情爆发成为法国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的催化剂,反种族主义运动正在华人群体中觉醒。(54)Li Yong, “La Confrontation des Diplmés Chinois au Marché du Travail Français: une Insertion Incertaine”, Connaissance de l'emploi , no.145, 2019, pp.1-4.研究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的大众媒体有关少数族裔群体的新闻报道,依旧过分强调与族裔相关的负面信息,推动少数族裔群体的社会参与度提升及群体形象改善势在必行。尽管“中国病毒”被用来宣传反华情绪,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也出现了“吾非病毒”等口号,以此消除族裔耻辱感,团结并强化华人的声音。社交媒体平台随之被视为谴责和反对种族主义言行的重要渠道,在声援少数族裔社区并向成为虐待目标的人群提供支持方面,社交媒体平台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55)Sylvia Chou, Wen Ying and Anna Gaysynsky, “Racism and Xenophobia in a Pandemic”, Interactions of Online and Offline Worlds, no.111(5), 2020, pp.773-775.李家伟提出,通过网络技术筛选推送内容或许有助于减少网络中排外行为的传播与加强。维护安全的网络环境,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网络安全的重要议题。(56)Lee Roy Ka-Wei and Zhi Li, “Online Xenophobic Behavior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A Commentary”, Digital Govern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no.1(2), 2020, pp.1-5.
学者们已普遍认识到,正面应对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对西方社会的挑战势在必行。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本质主义”对“东方国家”的认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旧沿着种族主义惯性前行,并且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几乎没有受到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冠疫情的爆发为西方“普世价值观”与“民主范式”敲响了警钟。海外华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日常生活交流或媒体话语中出现的种族主义言行进行抵制,更需要社会层面上更深层次的构建与更广泛的合作,以应对种族主义的攻击与挑战。西方国家若要建设一个更为包容的社会,需要通过自我反省来抵抗西方中心主义的固有思维。(57)Miyake Toshio, “‘Cin Ciun Cian’(Ching Chong): Yellowness and Neo-orientalism in Italy at the Time of COVID-19”,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no.47(4), 2021,pp. 486-511.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展开了这类讨论。达拉尼克斯·史蒂文森(Nix-Stevenson)试图从远程学习的角度探讨排外主义的应对之策,他认为,线上交流有助于揭露特殊时期由于隔离而产生的偏见,协同合作与资源整合可为在校学生提供消除仇外言论的机会。(58)Nix Stevenson, Laura Shelton and Jennifer Smith, “Fighting Back Against Anti-Asian Xenophobia: Addressing Global Issues in a Distance Learning Classroom”, Middle Grades Review, no.6(3), 2020, pp. 7.基姆教授(Grace Kim)指出,新冠疫情揭露了原本经过自由主义修饰的种族歧视,而人们并未对此进行积极尝试以消除种族主义所带来的影响。如果在后疫情时代人们依旧忽视族裔平等方面的缺失,那么恢复疫情之前社会生态的企图只能是一种妄念。(59)Kim Grace and Tanvi Shah, “When Perceptions Are Fragile but also Enduring: An Asian American Reflection on COVID-19”,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no.60(5), 2020, pp. 604-610.此外,为了应对华裔等移民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激增,社区应当提供基于多元文化背景的心理健康服务。除了改善国家对全球流行病日益增长的威胁的有效应对外,恰当的心理咨询也有助于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减轻少数族裔群体耻辱感和心理创伤的影响。(60)Phua Kai-lit and Lee Lai Kah,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Epidemic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 An Agenda for Research”,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 no.26, 2005, pp.122-132.
海外华人的文化认知与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有着紧密联系,疫情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造成的紧张关系也深刻影响着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为消除或减少仇外心理问题,西方国家政府部门需要客观认识疾病与歧视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对少数族裔群体的污名化是对全球发展的重大威胁等相关现实。(61)Manomita Das,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tigma and its Implications-observations from COVID-19”,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Open, 2020, pp.1-27.从1918年流感大流行、2003年SARS疫情和2014—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不断提醒人们,只有在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基础上,具有充分社会适应性的防疫措施才有可能奏效。(62)Melissa Leach, “Echoes of Ebola: Social and Political Warnings for the COVID-19 Response in African Settings”, Science, Medicine, and Anthropology, no.6, 2020, pp.1-5.公共卫生官员、教育官员等政府公务人员之间则需要组成一个有机决策的机构,在全球危机中解决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公平等至关重要的矛盾冲突,国家领导层则需要果断表达反对排外主义的坚定态度。在SARS大流行期间,有的西方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了快速反应倡议,以应对反亚洲情绪,其中包括监测在普通民众和媒体中出现的污名化态度与行为,并与亚裔社区合作,制定和部署若干文化干预措施。(63)Bobbie Person, Francisco Sy, Kelly Holton, Barbara Govert and Arthur Liang, “Fear and Stigma: The Epidemic within the SARS Outbreak”, Emerg Infect Dis, no.10(2), 2004, pp.358-363.政府出面以技术手段打破社交网络中的“信息茧房”,将是疫情下互联网发展的重点,但是“右翼党派”在一些西方国家执政局面的确立,会使得相关应急系统难以被成功激活。
此外,新冠疫情全球爆发时如何有效应对,为学者们提出了“构建更加符合社会现实的决策流程”的基本任务。研究表明,预先规划、公开对话是西方国家公共卫生系统有效运作的关键,也是接受公共卫生服务不足的少数族裔移民群体争取公正待遇的前提。(64)Katerina Tsetsura and Dean Kruckeberg, Transparency, Public Relations and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7.同时,西方国家政府出面,培训参与相关服务的公务员和组织领导多样化社区建设势在必行,将提升文化传播能力和社会公正水平纳入员工培训计划,加强公共服务公告和沟通范围及能力,对于减少污名化、克服陈旧观念和减少或消除排外暴力行为至关重要。(65)Roberto Katherine, Andrew Johnson and Beth Rauhaus, “Stigmatization and Prejudi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 no. 42(3), 2020, pp. 364-378.
五、结 语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对疫情的污名化使得排外主义较之前更具攻击性与针对性,其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化。疫情政治化、媒体污名化与“仇恨犯罪”,成为新冠疫情爆发过程中针对海外华人的西方排外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
透过部分西方媒体和民众对“瘟疫”爆发与外来族体关联性的认知,我们可以看到新冠疫情下西方国家针对华人或亚裔的“仇恨犯罪”数量飙升并非偶然,“瘟疫”与华人或亚洲移民关联性的确定在西方国家早已存在。解决“后新冠疫情时代”排外主义所带来的问题,首先需要防止“瘟疫”与“他者”之间关联性的进一步加深,这不仅需要华人自身的努力,更需要西方社会公共管理部门做出系统的调整。
从海外华人角度而言,排外主义提升了华人群体的族裔认同感,借助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传播效力,海外华人群体也在积极与排外主义进行斗争。在应对疫情方面,海外华人习惯于比较积极地佩戴口罩,保持个人卫生与社交距离,对疫苗的排斥也不显著。但由于华裔心理健康服务的使用频率普遍偏低。“后新冠疫情时代”生活在西方国家的海外华人要摆脱排外主义带来的诸多影响,尚面临着重重阻碍,包括解决因排外主义引发的心理问题,应对排外主义与仇恨犯罪,通过利用线上教育的机会开展交流以减少或消除偏见,复苏深受疫情爆发打击的经济生活等。
新冠疫情下的排外主义绝非华人群体做出反抗就可消解,遏制排外主义进一步发展仍需相关西方国家各方的协同努力。从个人层面而言,由排外主义所激发的海外华人身份认同成为反抗排外主义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以技术手段打破社交网络中的“信息茧房”,将是疫情下互联网发展的新方向。从社区层面而言,加强各种渠道的交流并防止海外华人被进一步边缘化,将有助于削弱由疫情带来的偏见。从国家层面而言,消除仇恨预期不仅是对华裔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更是当前西方国家遏制社会割裂的重要举措。
通过对国外学界有关当前新冠疫情下海外华人问题研究的梳理分析,可发现一些相关的研究不足。首先,一些针对当前海外华人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数据收集的层面,缺乏理论性的归纳与总结。其次,部分西方学者对于新冠疫情依旧保持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错误地相信中国与疫情爆发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有的研究文章依旧基于病毒起源于中国的论调进行思考,认为华裔在疫情中的遭遇并非全无道理。比如,瓦莱丽·伊姆布鲁奇认为,纽约华裔应当建立独立的、安全的食品网络,尽可能减少与中国之间的联系。诸如此类的错误偏见必须予以批判最后,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排外主义的后续发展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