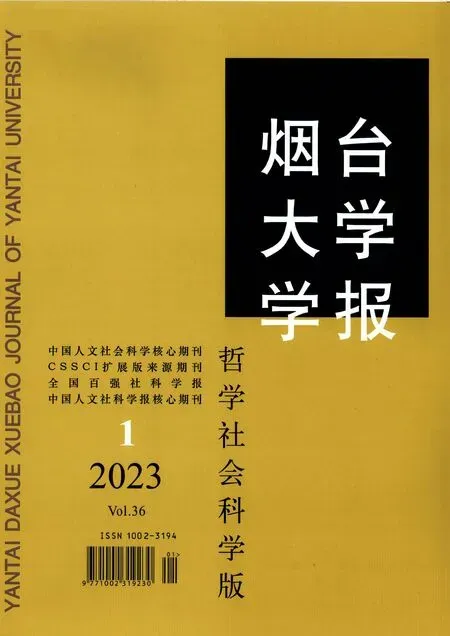语言研究中的祖题
——哲学论争是学术繁荣的摇篮
丁金国
(烟台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在语言哲学领域里,有两个命题既古老又年轻:一是“人类语言的个性与共性”,二是“语言本体的约定论和本质论”。前者探讨人类各语言间的差异性和共有特征及规则;后者着力点在于探讨语言本体外在语音形式与内在意义之间的关系。说其古老,是因为一切语言理论缘起,几乎都肇始于此,故而我们称其为语言理论的祖题;说其年轻,因这两个古老的命题一再地被重复。然而,我们从循环中发现,每一次论争都不是此前的简单复制,而是一次新的飞跃,是学科进步的重要表征。
一、古代的“本质与约定”之辨
远在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古希腊人就在哲学论战中,对“本质与约定”进行过两次论争。依据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记载,第一次争论是在克拉底洛(Cratylus)、赫尔摩根(Hermogenes)和苏格拉底(Socrates)三人间进行。前两者的观点相左,克拉底洛认为事物的名称是由其本身性质决定的,赫尔摩根则认为任何事物的名称并非由其本质决定,而是按习惯约定产生。因此前者被称为“本质派”,后者则称为“约定派”。亚里士多德也属后者,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因为任何名称都不是根据本质产生的”。与亚氏相对的是盛行于公元前四世纪末的斯多噶学派。他们主张名称是按本质形成的,最初的语音是对事物的模拟。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由此引发了史上第二轮论争,即类比论(analogia)与变则论(anomalia)的争论。类比论认为不同语言间的相似形式说明其有相似的范畴,而相似的形式结构和范畴意味着其受相似的规律所制约;变则论则认为,客观事物与其称谓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世上不同语言的存在,是因为其各自存在着对世界的观察、理解、解释的方式不同所使然,因而各语言都是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存在于世。这场持续二百多年之久的论争,论辩双方为驳倒对方,集中全力对语言符号从意义、语音和语法进行探索。论辩中描写最系统、精细的是语法。最早有柏拉图对语句的基本构成要素的划分,认为句子是“最短小的言语”,是由名词和动词作为基本构成单位连接起来的。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语句分析,在名词与动词二分外又增加了一类——连接词,即用于连接名词与动词的词,实际上其包括了今天的连词、系词、代词及冠词。除词类划分外,他还提出了“格”的概念。由上可见,亚氏所作不是单纯的集成,而是开创性的,他为传统语法的建立做了基础性的工作。斯多噶学派继续对语法范畴进行研究,他们把词确定为五类:动词、连词、成分(包括代词和冠词)、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将“格”从“混沌”中分离出来,认为“格”的概念只与名词发生联系,并为各个格命了名:直接格(主格)、间接格(包括属格、与格、宾格)、呼格。哲学的论辩和语言结构的分析描写,使古希腊的语言研究开始转向,从哲学的角度转向语文学,在继承与检讨前辈成果的基础上,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前170—前90)为适应罗马人学习希腊语的需要,编写出了第一本系统的语法书《希腊语语法》(或曰《读写技巧》)。从语音切分和描写入手,逐次对句子、词进行描写。他认为句子是上限单位,是“表达一个完整思想”的单位,词是最小的单位。对于词类的划分,特拉克斯逐一对八类词下了定义,从而使词类理论系统完备。这八类词是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连词。并确定名词有性(阳性阴性中性)、数(单数复数双数)、格(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呼格)及类(原类派生类)等范畴,动词有时、数、人称、语态等形态变化。经过特拉克斯的详尽整理和体系化的《希腊语语法》,完成了以分析描写语言现象本身为目标的传统语法的奠基性工程。
古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的语法学思想,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发源于希腊的“本质与约定”的论争引入到拉丁语的研究中。这时最著名的语法学家是瓦罗(Marcus Varro,前116—前27),他编写出第一部《拉丁语研究》。与希腊人的语法体系比较起来,虽无更多创新,但因其谙熟拉丁语,所以在论述的过程中证据充分、说明入理,常被后人引述。瓦罗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类比论与变则论双方的对立观点,在介绍材料的同时对拉丁语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他在词源方面的贡献在于区分了派生构词和屈折构词,认为词的屈折变化具有很强的规律性,而派生形式则随着词根和用法的变化而不同。在形态学方面,瓦罗在认真考察了拉丁语的性、数、格变化体系及结构功能的基础上,依据词的屈折形式的变化类型,将拉丁语的词划分为四类:一为有格变化的名词、形容词;二为有时态变化的动词;三为既有格的变化又有时态变化的分词;四为两种变化都没有的副词。他对各类词的功能作了说明,如名词与形容词用于指称事物,动词用于陈述,分词用来连接,副词作为配属与动词连用。在分析动词的时态范畴时,他完全接受斯多噶学派的理论,区分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态,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语态以及完成和未完成两种体态。对于名词的格变化,他注意到希腊语有五个格而拉丁语则有六个格,即多出一个“夺格”。继瓦罗之后,普里西安(Priscian,约六世纪左右)以特拉克斯的语法为宗,系统地描写了古典拉丁文学中的语言,集成为《语法原理》。至此,古希腊、罗马学者完成了对语法学的创建工程,该书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古代语言哲学和中世纪语言学的基础和桥梁。如果说“约定与本质”的论争,就人类语言整体而言是微观现象的探讨,而自瓦罗的《语法原理》以“普世”姿态问世后,语言研究的视角则有了从宏观把握的共性论与个性论的区分,从而开创了语言研究史上的新纪元。
人类历史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6世纪古希腊、罗马的本质与约定之争,距其万里之遥的东方中国,同样也在发生着“本质与约定”的论辩。春秋战国之际,随着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新秩序的酝酿之时,关心国家命运、百姓疾苦的圣哲们,发出“正名”的呼喊。在“正名”的呼喊中,引发出“名”与“实”之间关系的思考。存世文献最早的论述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探求“名”源是老子的初衷,然断言“名”生于道,则有失偏颇。倒是墨子在梳理各家论说的基础上,提出“以名举实”(《墨子·小取》),荀子补充说“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荀子·正名》)。“举实”“期累实”,即以概念反映客观事实。学界公认的荀子“约定论”说得更深刻:“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为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为之实名。”(《荀子·正名》)史上第一次以如此明确的语言表述语辞的音义关系。先秦圣哲的名实之辨,其直接结果是引发人们对语言符号的意义的关注,从而引发出两汉对汉语语义的兴趣,值得重点提及的是四部与语言学相关的语义研究著作,它们是《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一般认为非出自一人之手,当是由汉初学者将周秦以来对古代典籍的训释递相增补缀辑而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3卷20篇,今本19篇,分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在编排上该书前三篇采取“同义类聚”的方法,把词义相同、相近或具有相关性的词辑为一组,用一个常用的词予以解释,如《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后十六篇是名物训释,所用方法主要是以共名释别名,以今义释古义,以“雅言”释方言殊语的“义训”。因其是汉语训诂学史上第一部集古今典籍注释的大成,所以后世对儒家经义的解释,多以《尔雅》为宗,或为之注,或为之疏,或辑佚,或考证,遂使研究《尔雅》成为专门的学问,称之为“雅学”。
《方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著作,作者系西汉末年的扬雄(前59—18)。《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原本为十五卷,今存十三卷。其体例仿《尔雅》,分类排列,唯不标类名,将源于不同方言的同义词汇积聚为一组,用一通用词予以解释,指明通义后,再分别注明每个词的通行区域。扬雄是在前人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地收集与整理了古今、方俗的词语,并亲自进行方言调查,历时27年才把《方言》完成。《方言》不仅为训释先秦两汉典籍提供了依据,还为研究古汉语的词汇和汉语史留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方言》第一次勾画出汉代方言的分布轮廓,在方法上以各地的活方言为记录对象,摆脱了文献记载和文字形义的限制,并能结合时间和地域分析语言事实,创立了方法论上的优良传统。后代学者为《方言》作注疏的著作有多种,影响较大的有晋郭璞的《方言注》、清戴震的《方言疏证》和钱绎的《方言笺疏》。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从字形研究语义的书(下文简称《说文》),作者许慎(约59—147),字叔重。该著于公元100年启稿,完成于121年,历时二十二个春秋,共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连同卷末序目分15卷。全书根据小篆的形体及偏旁结构分为514个部首。其体例是先讲字义,其次讲字形与字义、字形与字音之间的关系。字义解释以本义为主,形体分析依据“六书”理论,字音标注则采用“读若”法。该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贡献在于:第一,创建了汉语字典学,其所创立的部首,使汉字开始有了系统的分类、排列和检索的方法,对后代的字书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直至现在还是字典编排的主要方法之一;第二,对汉字结构及用法的六书理论,经过许氏的整理和阐发,其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为汉语文字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三,保存了篆文的写法系统,为研究商周古文提供了完整的资料;第四,保存了汉以前古训古音,无论其谐声或声训都是汉语词源学和古音韵学研究的重要依据。因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以后世研究、征引、阐发之作不断出现,以至形成“许学”或“说文学”。《说文》问世以来影响较大的研究著作有南唐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及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仅清代专门研究《说文》的著述就达二百多种。《说文》的缺点是释义还有笼统、粗俗之嫌,对字义的解释还有不少误疏和穿凿之处。
《释名》是一部“因声求义”探索语源训解词义的著作,作者为汉末人刘熙(字成国)。全书收录先秦两汉词语一千五百余条,分为八卷二十七篇: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器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由此可见,《释名》收词范围较之《尔雅》宽泛得多。声训在刘熙之前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释名》是集声训资料之大成,经整理、阐发体系化为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词源学性质的专著。《释名》所用资料不仅采自文献典籍,也还有大量的民间口语。至于解释,则完全是“声训”,分为同音相训和近音相训两类,以此来解释事物名称的由来。本书的特点是:所训释的词语都为通常之事物,训释词语的目的不在于训经释典,而完全是为了语言研究。正如刘熙在序中开宗明义所讲:
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
刘熙的“义类”说,对于启示人们从语音出发探究语源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因声求义”成为训诂学上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史上对《释名》多有批评,主要是有些训释似主观猜想,穿凿附会较多。该书到了清代才有注本,最早是毕沅的《释名疏证》,清末有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及《释名疏证补附》。
由先秦“约定与本质”的论辩所产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从词义、语源、文字、语音四个方向,对汉语的形、音、义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拉开了中国古代语文研究的序幕,确定了汉语语义型语言的历史地位,强化了汉语特异性的特征,为汉语语言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故我们称之为“两汉四典”。两汉四典的出现,使先贤们认识到:汉语异于世上任何一种语言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语义性,只有从语义入手研究汉语,才能有所作为,一切妄图将汉语拉入“语言普遍性”的套子,最终都必定走向歧途。
二、“共性与个性”的千年对撞
就语言哲学整体而言,“约定与本质”的论争是音义关系微观现象的求索,而自罗马人瓦罗的《语法原理》出现后,语言研究的视角则从微观个体转向宏观普世“共性”的探索,瓦罗的《语法原理》虽无更多创新,然却有着界标的作用,标志着古典时期的终结与新的语言研究纪元的开始。自此以降,求索共性和寻找差异始终是交替进行,二者犹如语言研究历史长河里的两股潜流,不时地漩起激浪,此起彼伏,交替进行,推动着语言科学的发展与繁荣。欧洲中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经过唯实与唯名、经验语法与唯理语法、语言同源与个性差异的论辩与探索,迎来了语言学术史上最灿烂的时代。
中世纪后期语言学史上值得提及的是思辨语法,它是经院哲学与拉丁语结合的产物。思辨语法认为,所有语言结构的底层有一种共同的、普遍的语法。这种语法不是以语言形式为基础,而是以理性法则为基础。其着力点不是描写具体的语言,而是在于探究语言的共相,因此研究者被称为思辩语法学派。思辨语法所蕴含的深层哲理,可以认为是中世纪思辨语法学家们留给后代的一份重要遗产。(1)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1-103页。与之相对的是经文艺复兴洗礼、民族语言研究的觉醒所兴起的各民族语言的经验语法的诞生。直接受唯理思潮激励和笛卡尔唯理哲学的影响,法国学者阿尔诺(A.Arnauld,1612—1694)和朗斯洛(C.Lancelot,1615—1695)写就《普遍唯理语法》,并于1660年出版。唯理语法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普遍的,表达思想的思维规律是一致的,而语言则是思维的体现,所以语言与思维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研究语言是语法的任务,研究思维是逻辑的任务,既然语言与思维存在着内在联系,那么语法与逻辑之间也就自然地存在着内在联系。由于受人类的理性和思维的一致性和普遍性使然,因此各个语言的语法也应具有普遍性。《普遍唯理语法》不是一部法语语法,作者的初衷是要写一部适合于一切语言的语法理论著作。我们认为《普遍唯理语法》主张思维第一性的原则更接近真理,其所提出的语言普遍性的命题,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极富启迪性。《普遍唯理语法》的语言共性观,影响着二百多年的语言研究,直到洪堡特(W.von Humbotldt,1767—1835)的语言相关性理论的提出,才在同质语言观的和声中响起了异调。洪堡特认为:“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一切语言研究的理由和极终目的均在于此。”(2)转引自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即民族语言。”(3)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第52页。这在语言研究史上,是第一次对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所作的最为深刻的揭示。
人类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随着梵语发现所带来的学术震荡,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语言研究的热情。在比较希腊、拉丁和梵语之间的同源关系时,欧洲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语言学家,先后有史莱格尔(F.Schlegel,1772—1829)、克里木(J.Grimm,1785—1863)、拉斯克(R.Rask,1787—1832)、葆普(F.Popp,1791—1867)等。史莱格尔在《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1808)一书中提出了“比较语法”这一术语,并指出“比较语法可以给我们一个关于语言谱系的焕然一新的知识”。(4)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等译,第189-190页。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创建过程中,别具一格的代表性人物是德国语言家施莱歇尔(A.Schleicher,1821—1868)。他从达尔文进化论得到启示,提出“语言是有机体”,认为语言也像自然有机体那样,按照一定的规律成长、发育,同时也将走向衰老和死亡。从上述理论思想出发,他提出了语言进化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的假说,认为语言的生命与其他生命机体一样有成长期和衰老期,以“史”为界,史前是语言的发展阶段,从有史时期开始,语言的历史就是一部衰老史。在语言的成长阶段,由简单形式变成高级形式,即由孤立形式变为黏着形式,由黏着形式变为屈折形式。发展到屈折形式的最高阶段后开始逐渐衰退。基于“语言进化的三阶段”,施莱歇尔把世界语言依发展顺序分为孤立语、黏着语和屈折语。他参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树形图,绘制出人类语言谱系关系树形图。至此,由洪堡特、葆普所提出的语言发展三阶段论,经施莱歇尔的阐发,标志着语言类型学的正式产生。然而,突出语言的有机性,强化物质性,完全忽略语言的社会性,是“有机”理论的最大谬误。
正当历史比较语言学凯歌行进之际,在语言学故乡德国,兴趣广泛、涉猎阔博的洪堡特于1800年代始则集中精力于语言学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部与语言相关的著述,其中最著名的是《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27—1829)。该著作完整地阐述了他关于语言的本质、语言与言语、语言的功能、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民族精神、语言类型学、内部语言形式等理论,为普通语言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洪氏认为,语言本身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能力(Energeia),这种能力为全体人类所共有,人们可利用有限的手段进行无限的创造,语言创造性的本源在于个体的言语能力。然言语个体,无例外地从属于特定的民族,故而每个民族铸就了特定的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民族语言中显现得最彻底。由此,洪堡特断言:“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即民族语言。”(5)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第52页。在语言研究史上,这是第一次对语言间的差异性所作的最为深刻的揭示。与民族精神相关的概念是“内在语言形式”。学界对其阐释迥然,多数认为内在语言形式是“语言的语义结构与语法结构的总和”。笔者认为,内在语言形式具有丰富的内涵,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它潜隐在语言内部,为每一种语言所特有。如汉语里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最为突出的是“喻”。对于国人的思维方式,冯友兰认为,“着眼于内涵,用联想方式挖掘并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用横向比喻来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特点”。(6)转引自徐通锵:《语言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页。徐通锵认为国人的思维方式,不是三段论思维,而是“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7)徐通锵:《语言论》,第47页。“比类”即通过横向比喻,将不同事物联系起来,以揭示其本质特征。
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出身于莱比锡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1857—1913),以其渊博的学识,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洪堡特语言异质论的沃土中培育出语言共性论最系统全面的壮苗——《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划时代的著作,提出了一系列普适性理论范畴,如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共时与历时、聚合与组合、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等。然索氏为便于其同质语言观的展开,“从言语活动中排除言语,得到语言;又从语言中,排除外部语言要素,得到内部语言要素;再从内部语言要素中排除历时语言事实,得到共时语言系统”。(8)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兹撮其要概述如下:
1.“语言是一个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符号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但这种结合是任意的。任意性不等于“约定性”,索氏认为“约定性”所约定的各部分是既成事实,而任意性所联系的各部分在预定之前都不成形。全部语言事实所组成的体系,都是由任意性原则所制约,故而称为“第一原则”。
2.语言现象分为言语活动、语言和言语。索绪尔认为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物理、生理、心理和社会几个领域。为了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首先就应该把语言与言语区分开来。语言是同一个社群集体所共有的符号系统,所以是社会的、心理的、抽象的,语言的存在方式是:1+1+1+……=1(集体模型);而言语则是属于个人的、具体的、现实的。语言与言语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对立体,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要使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9)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第35-41页。
3.共时与历时的区分。索绪尔认为共时(synchronic)和历时(diachronic)是两种对立的现象,“共时是在一根横的轴线上研究在某一语言的结构内各个部分的关系;历时是在一根纵的轴线上研究一种语言态和另一种语言态前后的继承关系。”(10)许国璋:《论语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第141页。在语言分析的时候,应将共时和历时分开讨论,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二者是互相排斥的。
4.语言的系统性与符号的价值。按照索绪尔的思想,语言的个体符号不纯粹是语言事实,而只是系统的组成要素,这个系统所代表的才是语言。组成语言系统的各语言符号的功能,不是由其自身决定的,而是由组成语言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也就是说,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与其他要素处在相互对立之中,其各自的价值是由它们在语言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离开了以对立为基础的系统,则根本不存在个体要素的价值。系统不仅意味着组成系统的各单位之间的彼此联系,更重要的是组成系统的单位相互的对立与差别,正是这种“对立”“差别”显示出了语言符号的价值。索绪尔的“系统”和“价值”理论,揭示了语言运作方式的核心问题,是他对理论语言学具有独创意义的贡献。
5.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索绪尔以其超人的睿智,从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高度抽象出两种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语言系统中的两种根本关系。不但语言符号(词、语素)处在这两种关系之中,而且构造符号的音位和意义也都处在这两种关系之中。”(11)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3页。所谓组合关系,是指组成语言线性序列中的各要素间的横向关系。组合关系的构成要接受一定的组合规则制约,不同的组合关系是由不同的组合规则所使然。由于组合关系是依照时间顺序展现的,因而它排除在同一时间内出现两个语言单位的可能性。与组合关系相对的是聚合关系,它是指在语言线性序列中,可以出现在同一位置上的语言单位之间的一种纵向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潜在关系,因为出现在现场的只有一个,其他成员都以潜隐的形式存在于语言使用者的意识里。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提出是索绪尔对语言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
6.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索绪尔认为一切与语言系统有关的东西都属于内部语言学,一切与系统无关的,都属于外部语言学。脱离语言的外部现象,针对语言系统本体的语法、词汇、语音和语义等平面所进行的研究均称为内部语言学,它是以描写特定语言的共时态为主要目的的研究;与内部语言学相对的是外部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系统及其发展与外在条件密切相关,语言与民族之间,语言史与民族文化史之间,语言与政治之间,语言与社会的各种机构、组织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这些构成了语言系统的外部因素。
二十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结构语言学最辉煌的年代,其方法论原则无论在空间或时间上影响都是空前的。它的影响遍及哲学、逻辑学、文艺学、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经济学,甚至建筑、音乐、美术和舞蹈等,在科学研究中出现了全面结构主义化的倾向。结构、系统,能指、所指,共时、历时,横向组合、纵向聚合等原则,几乎无处不在。结构主义作为哲学思潮,尽管在20世纪下半叶由高峰走向低潮,但其所创建的方法论原则并没有失去它昔日的光辉。依据我们自身的体验,每当在研究中遇到困惑时,到索绪尔的理论宝库中浸润,总会有所启悟、有所发现。对于语言研究者来说,只要坚持系统与结构、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聚合与组合、内部与外部诸原则,就会一往无前。
三、“结构与功能”齐驱
结构主义的兴起,以其强有力的冲击波,迅猛地扩展到不同的学科领域,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思潮。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哲学思潮的结构主义,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影响所及不仅限于语言学,社会科学其他研究领域也从中汲取了营养。在当代,语言学之所以被誉为“领先科学”,是与索绪尔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索氏所开创的现代语言学,以其下列特征区别于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的系统性和语言学的自主性;重视语言的共时性研究;主张区分语言与言语,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在方法论上强调描写优于解释,归纳重于演绎。索绪尔的这些理论原则,被视为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自然也就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主导思想。
针对索绪尔的同质语言观,萨丕尔(Sapir E,1884—1937)在论证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时提出了语言对思维的决定性影响的论断。他说:“真实的世界是在该族人的语言规范的基础上不知不觉地建立起来的。”(12)转引自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241页。萨氏的学生沃尔夫全面接受了其“人的思维、经验和行为受制于语言”的观点,他说:“每种语言的体系(换言之,语法)不只是思想声音化了的传达工具,更准确地说,它本身就是思想的创造者,是人类个体理性活动的纲领与指南……我们研究自然界是按照我们本族语为我们指出的方向来研究的。”(13)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伍铁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38-339页。因其论述极端,故而学界称之为“语言决定论”。对其仁智之辩,一直延续至今。
正当索绪尔的结构同质语言观风靡之时,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A.Martinet,1908—1999)针对索氏的理论原则提出质疑。他认为语言研究诚以语言为依据,但言语是语言的赖以存在的根基,唯有丰富多彩的言语活动,才为语言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功能选择。所谓“语言结构”只不过是某些语言学家所“杜撰的框架”,因此,“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是站不住脚的。语言之所以有交际功能,正是语音实体和语义实体的外化功能所使然。马丁内认为必须坚持共时与历时并重,对语言结构进行共时考察时,不能抽掉其历史发展背景。语言的现实的相异性远比相同性大得多。
对索氏的理论持质疑态度的还有英国的弗斯(J.R.Firth,1890—1960),在当代语言研究领域里有两个重要发展是与弗斯的名字分不开的。一是弗斯认为:人类语言各自都有自己的发展背景,任何言语交际都脱离不开其生存的社会情境,故“统一性(unity)是最不适用于语言的概念”。(14)转引自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417页。意义是语言研究的中心,情境是语义研究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弗斯另一个重要发展是“韵律特征”。认为语流是由语声单位和韵律单位构成,语声是按顺序排列的音段,韵律则是对音段起修饰作用的超音质音位,诸如语调、声调、停延等。弗斯的弟子们如帕默(F.Palmer,1906—1984)、罗宾斯(R.H.Robins,1921—2000)、韩礼德(M.A.K.Halliday,1925—2018)、莱昂斯(J.Lyons,1932—2020)及利奇(G.Leech,1936— )等秉承师训,发展和充实了弗斯的思想。其突显语境、注重实用,以语义为核心的研究道路,对二十世纪的语言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学术思想最活跃的世纪,“波”起于洪堡特,推动和张扬的是索绪尔,与之对立冲撞的是马丁内、弗斯和韩礼德,接续结构主义的是乔姆斯基。20世纪下半叶,从美国结构主义的营垒中杀出来的乔姆斯基(N.Chomsky,1928— )于1957年出版了《句法结构》。该书开篇就宣称:“我们打算建立一种公式化的一般语言结构理论,并且打算探讨这种理论的基础。”(15)此段话语见《句法结构》前言第二句,写于1956年8月1日。详见乔姆斯基:《句法结构》,邢公畹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页。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乔姆斯基革命”的开始和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无论是哲学基础、理论观点,还是研究方法及最终目标,都与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理论原则相左。乔氏认为描写语言学的分布、替换的原则,用来对话语进行切分和分类,只能对语言结构的表面现象作出一定的描写,却不能对语言结构的内在关系作出解释。普遍语法决定了人与生俱来就有获得任何一种人类语言的能力,所以生成语法的研究对象不是具体的语言,而是抽象的语法。其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根据有限的公理化的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用演绎的方法生成无限的句子,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乔氏理论一经问世,立即使平静的学坛鼎沸,嘉许与赞扬、置疑与批判蜂起。在此后相当长的岁月里,乔氏对自己的理论一直处于修正、否定,再修正、再否定的行进中。从“经典理论”“标准理论”“扩充的标准理论”到“管约理论”“最简方案”,经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历程,尽管往日的辉煌已黯淡,然其所力主的同质语言观并未完全消隐,依然激荡着语言哲学领域的迴旋游动。乔氏的贡献,不仅推进生成理论自身趋进,而且波及到数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一直到生物学、脑神经科学。更重要的是在论战中,催发出新学说、新理论。就语言学自身而言,如“格”语法、生成语义学、生成音系学、认知语言学、生物语言学等。有鉴于乔氏理论本身有脱离语用实践之嫌,又从反向催化出诸多交叉学科的产生,如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篇语言学、语用学、心理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甚至韩礼德的系统功能理论都可视为反向作用的结果。尽管学界对生成理论褒贬不一,平心而论,乔氏不断地作理论探索、进行修正,推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隆盛;其敢于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襟怀与人格魅力,着实令人敬佩!
四、结 语——人文精神与科学主义的比竞
二十世纪下半叶,在生成理论论争的刺激下,整个语言学领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中国的汉语学界出现了以检讨《马氏文通》为鹄的,全面清算以语法研究为中心的普世语言观,最先发起者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者申小龙。申氏认为:“整个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困惑是西方语言流派中科学主义思潮与汉语独特的人文特征的深刻对立。”(16)申小龙:《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中国的语言学必须走自己的路,彻底摆脱西方科学主义的束缚,建立起属于中国自己的本土文化基础上的语言研究。申氏对追逐西方理念的批判,在年轻学子中引起强烈反响,旋即掀起一股批判《马氏文通》以来统治汉语学坛百年的同质论巨澜,当时被誉称为“龙卷风”。申氏的言论虽有些偏颇,但却击中当前汉语研究的要害,激起主流语言学的愤怒,一时间主流学者们利用各种会议、讲堂进行反击。新老之间的这场论争,延续了数年之久。申氏为创建“文化语言学”新体系的努力虽未获得完全成功,但确乎催发了汉语学界学者的深度思考,在对百年《马氏文通》研究反思的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字本位”(徐通锵)、“语言研究的三个平面”(胡裕树)、“语言理据”(王艾录)、“语言文化互构”(辜正坤)及“汉外对比理论与原则”(潘文国)等主张。百年来崇为显学的语法研究,一下子从圣坛上被推了下来,逐出语文教育的课堂,与之相对的传统文化开始进入各级语文教育领域。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竞争的第一回合,以人文精神略胜收场。但普世语言观所经营的以语法研究为中心的百年老店,岂能轻易地关门大吉?经营者们正利用手中的学术资源,从四个方面进行重振雄风的迂回战:从语法中心转向到语篇,从篇章结构中阐释语法原理;从论语析句转向到话语修辞,从修辞关系中梳理、寻找语法关系;通过对外汉语教学强化和固守语法阵地,在留学生的练习中发现和阐释语法现象;在方法论上,依然坚守“国际接轨”期盼国外新理论的输入和科学化条分缕析,力图以精细化突破瓶颈。对于这些努力,能否恢复当日的辉光,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需要弄清的是科学主义与科学的区别,我们否定的是科学主义,但科学精神还是需要的。所谓科学精神,就是一切从事实出发,重证据,重材料,重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也不能笼而统之讲,而是要立足于具体的语言,从特定民族文化着眼,构建以民族精神为枢纽的人文精神。论及汉语研究的人文精神,我们认为应从汉语的特质入手,以“象喻”为核心,从音象、形象、义象、序象切入,考察汉语的特质。
对于汉语的特质,中国语言学史上许多方家都曾谈论过,既有长篇巨著,也不乏点睛式的睿言隽语。郭绍虞、王力、徐通锵、潘文国等均有精湛的论述。德国哲人洪堡特早在二百年前就敏锐地发现,汉语将所有的语法形式的功能赋予了“意念运作”(the work of mind),以及用为数不多的虚词和语序来联结意义(connect the sense)。他认为,正是因为汉语语法形式的阙如,从而使汉民族的心智结构得以特殊发展,以补偿语言形式上的欠缺。也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汉语高雅的形式美。(17)转引自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166页。“心智结构的高雅形式美”,通俗地说,就是“象喻”。这既是国人思维的固有模式,也是汉语的本质在具体运行中的外显形态。因此,在对汉语本质的思考探索中,抓住了“象”,就抓住了研究的核心。汉语中的“象”分布于音、义、序(即组合规则)。
“象”在语声中的显现,分别通过音节、声调、节奏和语流旋律体现出来。如现代汉语节奏运行的规则是以双音节为主,间之以单音节。“2”是稳定的重心,是汉语韵律的润滑枢纽,但其控制因素是声调。声调的静态值具有相对性,在语音链上因相互影响而发生谐变。在音节、音步、节奏点、节奏群各个层次上,为适应不同的句调、语调的需要,都会发生与之相谐的变化。声调的抑扬起伏,在语流的延顿、抑扬主轴上,叠套着平仄、长短、轻重、快慢等韵律的回环、复沓,演示着汉语所特有的宫商之妙。对此赵元任曾精辟地比喻为“小波跟大浪的关系”,认为在起伏的大浪上,仍有许多小浪在波涌。(18)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79页。语义中的“象”,通过描摹性方式而得以显示,西语是从假设概念出发,用演绎推理的方式来论证事理;而汉语则是从具象性的直觉概念出发,调动语用者身心的知、情、意整体来体悟,用暗示的方式隐喻事物的真谛。以具体的“象”来表述抽象的“理”,是汉语示义的描摹性特征的集中体现。这种描摹性显现于汉语的各个平面上,既存在于语言体系的成分,又表现于话语语流的各种关系,更广泛潜散在语用的各种模式上。完全可以说,这是民族思维方式之质,融解于语用本体之术,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减少事理的抽象,凸现具象的描述,凝练而成的汉语自身的描摹性特征。汉语以象摹义不仅存在于静态的体系里,更广泛地存在于动态的话语中。修辞中的主要修辞格,差不多都具有摹象功能。语用中的摹象不是杂乱无序,而是具有明显的规律可寻。如国人的时空观念,严格遵循“时间顺序”和“整体部分”原则。在线性序列的语义流向中,时间先后和空间大小的有规则排列无处不在,这些原则折射在言语中,于是就有了“大人不见小人怪”“上行下效”“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可见,汉语确实是普遍遵循了空间大小律、时间先后律、心理重轻律。
汉语在组合上的特征,以单音节为基础(显形于“字”),这种无“形变”与“音变”约束的单位,天然地赋予了汉语在话语运行中的自由。它既无特定类属的管辖,又无形式规则的制约,可以“随机应变”“独来独往”,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能伸能缩、可前可后的结构功能,从古至今,这种灵活善变的伸缩性(elasticity)一直在延续。汉语中能动、灵活的弹性绝非是毫无约束,而是在“二元对称”序象的制导下运行。所谓“二元对称”是指语流中前后结构的呼应与连接现象,如“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我们认为二元对称表达格式,其含义超出了语法的内涵,是话语结构的骨架和意脉流动的模型,可视为序象的基本生存单位,是汉语“平衡表述机制”的底层。从复合词的构成、语词的组合、句间的组接到话语整篇的连贯,二元对称都无处不在。它体现了汉语语用者之间的一种语用默契,代表了方法论上“互文见义”的暗示机理,充分展示了汉语“对偶”结构在声气中的逻辑脉络,是中国阴阳哲学“无独有偶”的极致。这些都足以说明,我们的语言结构决定了我们的认知方式和对意念的表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