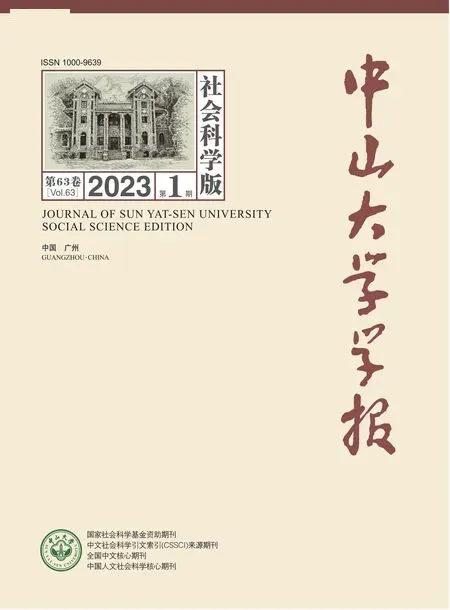编 后 记
本期含“名家特稿”“学术争鸣”“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三个专题专栏,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17篇。
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体,大概都有一种主流的风格,同时也有羽翼这种主流的次生风格。主流的诗人自然星耀四方,而稍次的诗人,虽总体光彩不如,但也以其自具面目而各占一方。一种文学生态的形成,大致都有这样的情形,主流性、丰富性与独特性构成一个时代一种文体的生态特征。唐代诗人灿若星辰,贾岛当然不是其中最闪亮的一颗,但他的独特性依旧是唐诗中不可忽略、无法替代、独具意义的。在贾岛的时代,韩愈、孟郊曾予以“狂怪”之评,乃是糅合了为人为诗的特点而言的。盖韩、孟所感知的贾岛的个人气质与诗歌风貌,皆不失其因狂生怪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一种评价往往根源于一定的机缘,却也往往遮蔽了另外的因缘,持此以衡诂全人全诗,便时常会有悖逆之处,譬如“狂怪”与诗歌批评史上影响更广泛更深远的“清僻”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具体呈现在五古与五律中,又有着怎样的差异?诸如此类的问题,皆非锐眼判断、辨入毫芒,不能道其故。鲁迅在《看书琐记(三)》中说:“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要了解花开的样子,其实关键正在于了解花“非开不可的缘故”。葛晓音对于贾岛奇思“入僻”以及在不同诗体中表现差异的分析,与鲁迅所持的理念堪称桴鼓相应。
哲学思考的问题或者方向,总是可以找到万泉汇流的地方,这种思想的趋同乃是根源于人性在本质上高度的相似性。无论是逻辑严谨、下语镇纸的严肃判断,还是激越和狂想的诗性表述,褪去万象的斑驳,直面的往往是直抵人心、直截痛快的透彻之悟。这就是行走在无限繁复与极其单一之间的哲学。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的被认知大体兼有这两种形态,他因为反对法国启蒙哲学,因此而被视为反启蒙的旗手;但赫尔德对德国启蒙哲学的期待,却同样是字正腔圆,为人称道。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先驱与自由主义者的双面性,使得其人类学历史哲学的实际面目不免显得复杂甚至模糊。刘小枫对赫尔德的“重新认识”,也因此有了特别意义。
学术争鸣的初衷是求真求实,毕竟一锤定音的学术可畅想而难落实,学术的兴味也部分地体现在这里。鲁迅《小杂感》说:“创作是有社会性的。”学术研究也同样具有社会性,认同、部分认同与否定乃是学术史的常态。本期刊发饶龙隼、曾海军分别与赵义山、赵汀阳商榷的两篇文章,前者关注的是明代小说中是否存在诗词曲的“寄生”问题,后者关注的是理学是否可以作为哲学的身份问题。因为问题客观存在,所以商榷确具意义。诗词曲在小说中的存在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鉴于其文类差异,将诗词曲作为小说的“寄生”现象,此前曾作为一种主流认知而被广泛接受,赵义山堪称是这一说的代表。饶龙隼则从古代小说原本就是诗文共生、韵散结合的角度,认为将诗词曲作为“寄生”的产物,其实是泯灭了古代小说的文体特征。换言之,饶龙隼认为小说文体中包含诗词曲,本就是明代小说文体的应有之义,以诗词曲为小说之“寄生”,意味着对明代小说文体形态认知的偏颇。“寄生”,意味着先有独立的诗词曲,然后才能寄生于小说之中,饶龙隼认为这种情形事实上基本是不存在的。这一争论因为各持立场,直觉暂时不会终止。赵汀阳《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一文自在《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发表以来,引发的讨论似乎就没有停息。何以一篇关于中国哲学的身份问题的文章能吸引大家的关注,这里面其实涉及遵循中国哲学的历史传统,还是遵守现代科学的学理规范问题。其实即便各执一说,也可能各蕴其理,关键是问题以怎样的方式出现。曾海军认为赵汀阳的论题本身就存在着“模仿复制”疑案,如此疑中有疑,案中有案,确实将相关问题的复杂性直陈了出来。本刊欢迎富有学理和学术锋芒的讨论文章,盖问难与答难,就一直是中国学术的一种书写方式。学术当然需要坦然面对寂寞,但过于寂寞的学术,其实也让人五味杂陈的。
在中国文体的群落之中,似乎很少有作为表现手法的“赋”与作为专门文体的“赋”,如此两相照应、紧密结合的。一字而光耀两方,这大概也部分地体现了中国文字和文学的神奇之处。“赋”作为聚敛和铺陈的意义,也是赋体的题材所自然规定的。在赋体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篇幅、题材和形式的种种变化,但“主物”始终贯穿其间,未曾旁落。无论物类如何变化,赋体与物的彼此依存关系一直存在,当然在物与情、事等的关系上一定会有着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变化。易闻晓从文体分别与题材交互的角度讨论赋体文学的主物特性,应该说是抓住了赋体和赋字的要义。
由主物的文学可以进一步考察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物”概念。早期中国哲学著作的中“物”“百物”“万物”概念层出不穷,是绝对的高频之词,而且各具精义。统观世界之大,大抵“人物”二字可略穷其底蕴,而在王国维那里,其所谓“无我之境”,也不过将人作“物”而已。则世界归根到底,“物”是最强悍的存在。但“物”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也有足启人思者,前诸子时代好以“百物”表示不同族类的总和,而晚周诸子则常用“万物”指众多个体之物的总和。从族类到个体,其实是物自觉的过程,这种物自觉又带来了“形神”“形名”等观念的变化,其间容摄、否定所在皆有,而终究为诸子学的发展奠定思想基点。以此而言,追究诸子学的起点,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物”概念,乃是必须深入把握的。刘伟此文展现了早期“物”概念从混沌到自觉的过程,值得一读。
由物再回到人。魏晋玄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生死观,玄学以儒道互补为基本特色,这是生死问题讨论的思想基础,玄学之“玄”因此而有了相对稳定的讨论空间。据今常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这意味着生死观是这个世界必须面对的问题,何以视生,何以视死,就不仅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人类共同之事。在生与死之间,养护出生命的意义。曹植是建安诗坛的标志性人物,其诗歌久已驰名,但其所作《髑髅说》则受关注者尚鲜。实际上这篇《髑髅说》不仅受到《庄子》的影响,其浸染张衡《髑髅赋》之处,也是有迹可循。作为一篇模仿《庄子·至乐》之文,在承续庄子基本精神取向的同时,在义理思辨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启发了魏晋玄学家的生死观,具有玄学序曲的价值。既然“死者归也”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被提出,则由此进一步思考自然与名教的问题,也就变得十分自然了。孙明君此文由一文而起,但关涉的问题其实大且重的。
史书是一国文化的历史底蕴所在。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着眼现在和未来,史书所展现出来的智慧都是弥足珍贵的,新时代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是建立在扎实而稳健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这就是史书修订的现实意义。多年前,中华书局启动了正史系列的修订工作,现已陆续出版,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可信可靠的读本。景蜀慧主事的《陈书》修订,即是其中之一。修订工作的方向除了及时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之外,对于相关历史版本的搜罗、考订与对勘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景蜀慧对日本静嘉堂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种完整传世宋刊本《陈书》递藏和版叶作了细致的比较,不仅昭示了版本源流,也为新的点校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陈王朝三十三年的历史因此而更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中美关系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备受瞩目,大国之间的博弈所带来的不只是当事两个国家的动荡和变化,而是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要的影响。历史上的中美关系就充满了多变甚至迷幻色彩,在一百多年前的庚子事变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初,美国曾经相当保守,似乎固守着道德传统。但随着战争的发展,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终究与联军协同参战。即便后来美国调整了战略,穿梭在参战与调停两端,其欺骗性和隐蔽性也曾一度迷惑了清政府,但终究留给清政府的不过是短梦一场而已。百年前的耻辱当然不容重复,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方法多样,但自身的强大才是铁门限。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一任务离不开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本期邀请戚聿东主持相关专栏,分别就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切入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和企业绩效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专栏讨论的是大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问题,相信会对企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期多篇文章或直接商榷学术观点,或针对问题立论,在补偏救弊的基础上,贡献各自的智慧和思考,使相关学术史的格局更为方正宏大。学术史的发展难免反复无常,其中既有螺旋式的上升,也偶有螺旋式的下降,甚至有不明原因的散失。但发现问题,一定是发展学术的一条重要路径。一如体检之下,发现隐患,从而有针对性地疗治,才能更好地呵护健康。此喻虽未必十分贴切,但总是现象之一则无可怀疑。此前释读欧阳修作于安徽阜阳的《采桑子》组词,每于首句“群芳过后西湖好”心存疑惑,盖欧公未免与常人不同过甚。后研读材料方知,此时的欧阳修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以至于视力大衰,视物模糊,则花开花落庶几无甚区别。而因病带来的大量饮水也必然带来其行动的不便。如此种种因素而合成了“群芳过后西湖好”之心境。余曾感赋三诗,录如下:
诗人染恙转称雄,有病呻吟数醉翁。任是西湖花烂漫,也须谢后与君同。(其一)
醉翁懒看满池荷,渴痼中痟莫奈何。注若漏卮如未已,小溲四望只呵呵。(其二)
山花一任自销魂,老病经春总闭门。待得群芳凋谢后,再缘湖畔过晨昏。(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