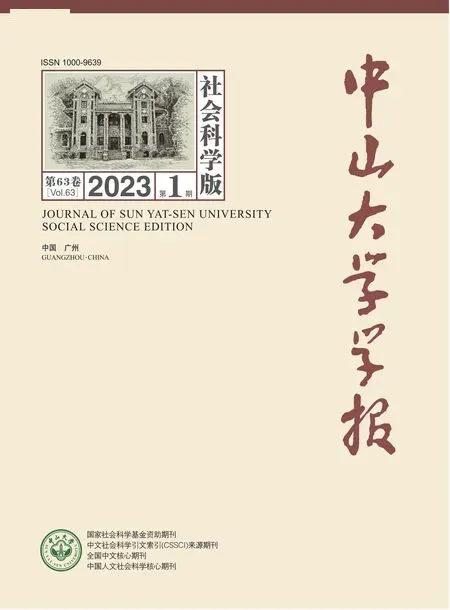宋金盟誓岁输“绿矾”解 *
——兼论金初的尚色与德运
邱靖嘉
金天辅七年(北宋宣和五年,1123)三月,金、宋两朝就交割燕京、岁输物资等事项达成协议,订立誓书,见于金宋往来文书汇编《吊伐录》第七篇《宋主誓书》①佚名:《吊伐录》卷上《宋主誓书》,《四部丛刊三编》,景印钱遵王钞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a—7a页。。 这份誓书是宋朝依据金国誓草修订而成的②按《宋主誓书》下有题注曰“系依草再立”,金国誓草见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4,宣和五年二月九日癸巳,《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1a—12a页。, 其中在宋约定每年交送给金国的物资中,特别增添了一项“每年并交绿矾二千栲栳”。“绿矾”,文献记载或写作“碌矾”,它是一种矾类化学制品,在宋辽金时代与盐类似属于官府的禁榷货品。“栲栳”是笆斗一类用竹篾或柳条编织成的盛物器具,形体中空而圆③牛尚鹏:《试谈“栲栳”之词义、理据及语源》,《唐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84—86页。, 在此作为一种计量单位,其具体相当于多少斤两却已不详。不妨以装盐的箩斗作一参照,南宋福建地区的盐箩,每箩省秤约为107.5斤④参见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 绿矾与盐同为颗粒状结晶体,其计量单位或有可比之处,若按一“栲栳”百斤计,则“二千栲栳”为20万斤,即使保守估算,可能至少也有十几万斤,数量不可谓少。清代学者俞樾曾有疑问:“按绿矾之数多至如此,不知金国何所用之也。”⑤俞樾:《茶香室丛钞·四钞》卷28,“绿矾二千栲栳”条,《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99册,第374页上栏。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然当代学者无人在意,未作解释。其实,如若细究,这条看似不起眼的记载颇堪玩味,或许还能牵扯到其他一些历史问题,有必要展开讨论。
一、绿矾的产地和用途
“矾”是人类日常生活中应用十分广泛的一类化学必需品,在自然界中可供直接使用的天然矾很少,而需要通过对矾矿石进行焙烧、煎炼和加工提纯才能获取。中国古代很早就已掌握了这种技术工艺,提炼出来的“矾”品种繁多,最常见的主要有五种:绿矾(亦名青矾)、白矾、黄矾、黑矾、绛矾①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唐·新修本草(辑复本)》草玉石等部上品卷3,“矾石”条注云:“矾石有五种:青矾、白矾、黄矾、黑矾、绛矾。”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98页。。 其中,绿矾的化学组成式为FeSO4·7H2O,今学名七水硫酸亚铁,纯者为浅绿色透明结晶,是中国古代最早被制造和利用的一种矾,大多通过焙烧黄铁矿(古称“涅石”)而制得。至宋代,有的地方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制取方法,以铁釜煮胆水(即天然硫酸铜溶液)炼铜,通过置换反应获得绿矾溶液,再经煎熬便成绿矾晶体。这种绿矾是炼铜的副产品,成本更低廉②以上皆参见赵匡华:《中国古代化学中的矾》,《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106—119页。。
从五代时起,所有“矾”的生产和销售便被官府所垄断,成为一大宗禁榷商品③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9,后汉隐帝乾祐三年十一月“(王)章聚敛刻急”条,胡三省注曰:“至于矾禁,新、旧《唐书·食货志》皆未著言其事,是必起于五代之初。”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册,第9559页。, 宋、金因袭之④脱脱等:《宋史》卷185《食货志下七》专记榷矾,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533—4537页。脱脱等:《金史》卷49《食货志四》记“金制,榷货之目有十”,其中就包括“矾”,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93页。。《文献通考·征榷考》记云:“榷矾者……五代以来,创务置官吏。宋朝之制,白矾出晋、慈、坊州、无为军、汾州之灵石县,绿矾出慈、隰州,池州之铜陵县,各置官典领,有镬户煮造入官。”这里提到北宋时期绿矾的主产地有山西的慈州、隰州和安徽池州铜陵县,其中慈州兼产白矾和绿矾,隰州制绿矾主要是在温泉县,此外“汾州灵石亦有绿矾”⑤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征榷考二》“盐铁、矾”,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1页。《宋史》卷185《食货志下七》亦有同源记载,第4533页。。 这些地方采用的都是以当地所出矾矿石煮造煎炼的传统制取方法⑥唐慎微撰,曹孝忠校勘:《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3,玉石部上品“晋州矾石”条,引《图经》曰:“今白矾则晋州、慈州、无为军,绿矾则隰州温泉县、池州铜陵县,并煎矾处出焉。初生皆石也,采得碎之,煎炼乃成矾。”《四部丛刊初编》,影印金泰和甲子晦明轩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4a页。, 其工匠单列为“镬户”。其年产量在宋太宗至道年间为“绿矾四十万五千余斤”,至真宗末年“增二万三千余斤”⑦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征榷考二》,“盐铁、矾”,第441页。, 后来到北宋末应该又有所增加。如此算来,金人向宋朝索要的“绿矾二千栲栳”,或许大约能占北宋绿矾主产区年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在与北宋并峙的辽朝,也有一处出产矾石的矿藏。《辽史·地理志》载西京道奉圣州有矾山县(今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乃因其地“山出白绿矾,故名”⑧脱脱等:《辽史》卷41《地理志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6年,第582页。, 辽朝应当在此地设置了专门炼制白矾、绿矾的场务。女真人起兵灭辽,建立金国,在天辅六年攻取辽西京后⑨脱脱等:《金史》卷2《太祖纪》,天辅六年三月,金军至,西京先降复又叛乱,至四月“复取西京”,第36—37页。, 必定也占领了矾山县⑩按天辅六年十月金主阿骨打即驻军于矾山县所在的奉圣州(脱脱等:《金史》卷2《太祖纪》,第38页),直至十二月伐燕京。。不过,天辅七年二月赵良嗣使金求取西京地,金太祖阿骨打遂特许将“西京、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等州并土地、民户”给与宋朝,并遣银术可(或译作“宁术割”)持国书及白劄子使宋订立誓书⑪佚名:《吊伐录》卷上《答宋主书》《白劄子》,第2a—3b页。又《金史》卷60《交聘表上》记云:“(天辅七年二月)癸卯,遣孛菫银术可、铎剌报聘于宋,许以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等州,其于西北一带接连山川及州县,不在许与之限。”第1389页。。 遵照此意,则奉圣州及其属县矾山当割属宋朝,那么金国将失去其境内唯一一处矾石产地,无法制取绿矾,因此银术可才在与宋宰相王黼商议修订誓书内容时,特别指出“已许了西京,要碌矾二千栲栳”①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5,宣和五年三月一日甲寅,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第1b页。, 也就是让宋朝每年给金国输送一定数量的绿矾作为物质补偿。大概宋朝方面也知晓这一情况,所以表示了理解和应允,遂将“每年并交绿矾二千栲栳”写入誓书。
实际上,“矾”这一类化学品在古代社会中的应用范围很广,如制药、炼丹、冶金等,需求量大,但其最主要的用途乃是用于染色。其中,绿矾又是最重要的一种。绿矾与某些草木果实中的鞣质相结合可生成黑色化合物,是古代染黑工艺中的媒染剂。这种技术工艺至晚在先秦战国时代即已出现,染色也是绿矾最先被人应用的生活领域②以上皆参见,赵匡华:《中国古代的矾化学》,《化学通报》1983年第12期,第55—58页;赵匡华:《中国古代化学中的矾》,《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107页;赵匡华、周嘉华:《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07—508页;赵承泽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76—277页。关于“矾”的主要用途,漆侠《宋代经济史》亦谓“矾主要充作染色之用,染坊以及家庭煮染都离不了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下册,第912页)。。 因古时黑色亦称皂色,而绿矾用于染黑,遂又名“皂矾”③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1,石部“绿矾”条记云:“绿矾可以染皂色,故谓之皂矾。”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校点本,1975年,第677页。, 可见绿矾在染色业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金人之所以向宋朝索要大量绿矾,恐怕主要不是为了炼制什么灵丹妙药,而应与绿矾最主要的日常社会功用有关。
二、金初军中的旗服尚黑
关于金国索要大量绿矾的主要原因,张棣《金虏图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值得注意的线索,其记云:
一、旗帜。虏人以水德,凡用师行征伐,旗帜尚黑,虽五方皆具,必以黑为主。寻常车驾出入,上用一色日旗,与后同乘,加月焉。三旗相间而陈,或数百队,或千余队。日旗即以红帛为日,刺于黄旗之上;月旗即以素帛为月,刺于红旗之上。又有大绣日月旗二。如祫享、大礼、册封,一一循古制,旗无大小,皆备焉。然五方、五星、五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凤外,又有五星连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马二,鹰隼二,太白二。近御又张一大旗,其制极广,绀绘神物,以猛士执之,又有数十人护之,各施大绳,以备风势,名曰“盖天”。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引张棣《金虏图经》,第5b—6a页,文字据国家图书馆藏明湖东精舍钞本、明郁冈斋钞本及许涵度刻本校正。此段记载又见于旧题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34“旗帜”条(见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81页),系抄自张棣《金虏图经》,个别文字稍有不同。
张棣本为金人,后投归南宋,撰《金虏图经》一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书名作《金国志》2卷:“承奉郎张棣撰。淳熙中归明人,记金国事颇详。”⑤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5伪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此书今已佚,唯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录,涉及金朝的女真风俗、政治制度、地理建置等多方面内容,各条记载年代断限不一,史料价值很高,有学者考证其记事下限为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张棣应是宋“绍熙中”而非“淳熙中”归明人,具体入宋时间当在南宋绍熙三年(1192)或其后不久⑥孙建权:《关于张棣〈金虏图经〉的几个问题》,《文献》2013年第2期,第131—137页。。 以上有关金人用旗制度的记载,提到的各种旗帜大多都见于《金史·仪卫志》,当有所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起首所谓“虏人以水德,凡用师行征伐,旗帜尚黑”,即使除黑旗外还有其他颜色旗帜⑦如《三朝北盟会编》卷63,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丙子,引《河东逢虏记》谓金军至河阳,“皆黑旗、黄旗、白旗”。第10b页。, 但“必以黑为主”。这里牵涉到金朝德运的问题,按有确切记载表明金世宗朝定为金德,而《金虏图经》称“虏人以水德”则反映的应是金初至海陵王时期的情况,对此下文另有讨论①参见曾震宇:《金初“以水德王”探析:立足于金海陵王一朝的考察》,戴仁柱(Richard L.Davis)、曹家齐、韦祖松主编:《岭南宋史论丛》,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604—633页。关于所谓金初“水德”的说法,尚有疑问,说详下文。。在此期间,金人“凡用师行征伐,旗帜尚黑”,可以找到其他史料来加以佐证。
南宋绍兴四年(1134)王绘出使金朝,路遇一队金兵,“有百余骑拥一老胡,皂旗高旌皆全装,老胡容儿秀整,乃聂儿孛堇”②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62,绍兴四年九月十九日乙丑,引王绘《绍兴甲寅通和录》,第3a页。。这支由女真聂儿孛堇率领的部队,旌旗招展即为皂黑之色。早前靖康元年(1126)初,金帅斡离不率军围困北宋都城汴梁,一夜忽有人将“红灯笼置诸城上,又城西北隅易建独脚皂旗,其中饰以雁,非本朝军中物”③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3,靖康元年二月三日己亥“尚书左丞蔡懋为行营使”条,引沈良《靖康遗录》,第8b页。,后得知此乃金人安插在城中的内应所为,“皂旗亦金人之所建者”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4,靖康元年二月五日辛丑,引朱邦基《靖康录》,第11a页。。可知这种装饰有大雁图案的“独脚皂旗”当是金军的标志性旗帜,聂儿孛堇骑队所举皂旗或即此类。其实,在金人攻城时,有一种很独特的战法是“多用黑旗上城”⑤李心传著,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壬寅“起复朝请郎王圭言”,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册,第206页。, 宋金之际的相关战例不少。例如靖康元年十一月,金军攻怀州,宋守将范仲熊记录城破时的情景,“蕃人已打散城上兵,城上十数黑旗子”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1,靖康元年十一月六日丁卯,引范仲熊《北记》,第14a—14b页。, 即是金人举黑旗登城。闰十一月,陈州之战,宋人谓金军“云梯辐凑,来者不绝……一贼身带十数旂,其卒争取,各诣其长求赏,但见黑旗旁午,人方疑骇而走,洎六人者登城,众遂披靡”⑦汪藻撰,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3,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91页。。意谓有金兵在军前争取黑旗,奋勇登城,致使宋军疑骇溃散。同月,金军攻汴京宣化门,搭桥渡护城河,二十一日,“桥成。先有黑旗子三人(按恐当作‘三十余人’)先登岸”,被宋军击退,不久“黑旗子复如前登岸,城中弓弩箭如雨,贼兵略不顾”,击溃城下宋兵;二十四日,金人推火梯攻城,据称“贼皆登城,舞黑旗鼓噪”,然因遭到宋军顽强抵抗,遂退⑧石茂良著,程郁、余珏整理:《避戎夜话》卷上,《全宋笔记》第4编第8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67页。按《三朝北盟会编》卷68,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日辛亥,谓“金人攻宣化门急,欲涉河而过,先有黑旗子三十余人已登岸”(第13b页),与《避戎夜话》所记二十一日战斗为一事。; 二十五日,金兵再登城,宋将吴革“率使臣亲兵赴南薰门东策应,手射死执黑旗者十许人”⑨《靖康要录笺注》卷16,靖康二年三月六日“又云”,第1712页。据《三朝北盟会编》卷84,靖康二年三月六日丙申引文(第2a页)可知,此段记载当出自《宣和录》一书。, 但最终城陷。这几次战斗金军无一例外皆是先令黑旗子冲锋上城,舞旗鼓噪,其目的大概是鼓舞己方士气,同时对宋军构成心理震慑,故宋鸿胪寺主簿邓肃作《靖康行》诗描述此战云:“雪花一日放濛濛,皂帜登城吹黑风。我师举头不敢视,脱兔放豚一埽空。”⑩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00,引邓肃《靖康行》,第4a页。至南宋绍兴四年,金围攻濠州,“将官杨照躍上角楼,以枪刺贼之执黑旗者”⑪李心传著,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绍兴四年十月丙申,第4册,第1540页。, 可知金人的攻城战法依旧是“多用黑旗上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说明金人行军作战惯用黑旗,足证金初女真人“凡用师行征伐,旗帜尚黑”,所言不虚⑫按《金史》卷107《张行信传》记载金宣宗朝参议官王浍提出“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遭张行信批驳,称“浍所言特狂妄者耳”(第2366—2367页),不足凭信。。
其实有迹象表明,金军不仅“旗帜尚黑”,而且其将官兵卒的衣着可能也多为黑色。蔡絛《铁围山丛谈》记有这样一个故事:
建炎当三祀,北马将饮江。于是天子幸明而越。隆祐太后龙舆驻豫章,行台从焉。时警报益亟,有郎官侯懋、李幾凡三人者,每至城东南隅,得园林僻寂,私相谓曰:“使敌一不可避,得相与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几,行宫南迈,仓卒之际果不克奔,而敌骑已遽入矣。三人者得如约,共窜于林,因伏堂之巨梁上,夜则潜下取食而还伏焉,累十数日矣。幸略无人至者。一旦忽多人物且沓至,三人但伏梁之上,计:“此岂皆避敌者耶,胡为而至哉?”语未已,即有黑衣数十百人继来,共坐于堂,命左右逻捕男女,无少长悉以挺敲杀之,积尸傍午,向暮尽死始去。当是时,三人者伏据于梁,惙惙然,向脱一仰其首见,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谓得免,况已昏夜。①蔡絛著,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8页。
它说的是建炎三年(1129)金军挥师南下,欲剿灭宋高宗赵构政权,宋室分两路南逃,一路是赵构奔江南至越州、明州,另一路则是隆祐太后往江西,中途驻跸于豫章洪州(即南昌),金人亦分兵追击。洪州方面不断接到金军将至的警报,从行宋官中有侯懋、李幾等三人,为躲避金兵,找到城东南隅的一处僻静园林,相约如敌来则伏于园中厅堂的大梁之上。后金兵果至,三人依计躲藏。一日天明,忽“有黑衣数十百人继来,共坐于堂”,将捉捕到的男女老幼全部敲杀,直至昏夜这群“黑衣”才散去。显然这些滥杀无辜的残暴之徒就是一支金军小队,约有百人之多,而且他们皆身穿“黑衣”,这是一条能够反映金兵服色的史料。又《金史》记载,大定十五年(1175)二月,“有司言东京开觉寺藏睿宗皇帝皁衣展裹真容,敕迁本京祖庙奉祀,仍易袍色”②脱脱等:《金史》卷 33《礼志六》,第789页。。“睿宗皇帝”是金世宗之父,本名完颜宗辅,在金初灭辽伐宋的战争中领军四处征讨,功勋卓著,官至左副元帅,天会十三年(1135)卒于军中,世宗即位后被追尊为帝③脱脱等:《金史》卷19《世纪补·睿宗》,第408—410页。。金东京辽阳府开觉寺所藏睿宗真容像应该是世宗即位以前供奉的,画中睿宗身穿“皁衣展裹”。按“展裹”是辽金时期对公服的一种称法④脱脱等:《辽史》卷56《仪卫志二》记载:“公服:谓之‘展裹’。”第1008页。,“皁”即“皂”之异体字,由此可知,长期担任军帅的完颜宗辅亦着“黑衣”,其后世宗朝将睿宗真容像迁入东京祖庙奉祀,因当时已定本朝德运为金德,尚色发生变化,所以特别提到迁庙时需“易袍色”,这一细节亦可透露出金世宗以前军中的尚黑之俗。此外,南宋前期出使金朝者,“故事,使者入北境,当服黑带韀”⑤李心传著,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十一月丁亥,第8册,第3537页。,或许也有助于说明当时金人的服色偏好。
综上所述,正因金初师行征伐,旗帜、服饰皆崇尚黑色,而旗、服为消耗品,金正规军人数至少有数万⑥金军围攻汴京时,《三朝北盟会编》卷32,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癸巳,引李纲《传信录》曰:“金人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人。”(第4a页)这六万人应该是金军的最主要战力,其中又以三万女真人最为精锐,这些正规军想必要配备相当数量的黑旗、黑衣。此外,金军中还有大量强征河北、河东汉人所组成的签军,《三朝北盟会编》卷29,靖康元年正月八日甲戌,引郑望之《奉使录》记金人萧三宝奴云:“河东国相二十万(原注:国相谓粘罕),皇子郎君一头项三十万。”(第4b页)这一数量估计是包括签军而言。, 再考虑到民用需求,这就需要大量的黑色染料用于纺织。尽管绿矾也可以用于冶金、制药,但这方面的用量相对较少,绿矾最主要的功用还是作为染黑工艺所必需的原料⑦按如前所述,绿矾主要作为媒染剂应用于古代染黑工艺,这已是科技史学界的共识。但文献中并无绿矾在染色时具体用量的记载,而现代染色工艺与古法不同,目前尚未见复原古法染黑的定量研究。不过,既然绿矾在古代社会中的最主要用途是染色,则想必其需求量应该是最大的。。 基于这一社会生产生活的常识,再结合以上对金初军中旗服尚黑的论述,我们有理由推断,金国在特许将西京及部分附属州县让与宋朝从而失去矾矿的情况下,要求宋朝每年“交绿矾二千栲栳”,其主要目的是保证这种染黑原料的供应来源⑧至于在此之前,女真人如何获得染黑原料,因史料匮乏尚不可考,估计可能有贸易、掠夺等途径,但物资来源并不稳定,所以金人才在盟誓中特别提出要求宋朝岁输绿矾,以保障供应。, 既可保障军需,也可掌控这一禁榷物资,这也是目前看来较为合理的解释。不过,此后不久金主阿骨打病逝,其弟吴乞买即位,撕毁誓约,出兵伐宋,最终并未将西京之地交与宋朝,所以岁输绿矾之事也就作罢了。
三、女真尚色与金初德运
上文尝试解释了金朝向宋索要绿矾的主要用途,这得益于张棣《金虏图经》提供的关键线索。不过关于这条记载,还有一个遗留问题有待讨论解析。《金虏图经》谓“虏人以水德,凡用师行征伐,旗帜尚黑”。如上所述,金人行军作战旗帜、服饰确实多尚黑色,但这种服色喜好是否与德运有关呢?
自秦汉时代正统观念确立之后,历代王朝都要讲求正统,宣示其政权合法性来源,这成为传承久远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而“五德终始说”(又称“五运说”)则是正统观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由汉迄宋历代王朝皆热衷于议定德运,藉由五德终始的理论框架来阐释其统治合法性,金朝则是最后一个以德运寻求正统的王朝①参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4—617页;刘浦江:《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据学者研究,金朝曾多次议德运,可以明确的是金世宗朝定为金德②佚名著,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卷35,大定十五年“长白山封册礼”册文云:“厥惟长白,载我金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42页)《金史》卷6《世宗纪上》大定三年“十二月丁丑,腊,猎于近郊,以所获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第133页),“以丑为腊”正与金德相配,知金德确立当不晚于大定三年。, 章宗泰和二年(1202)十一月甲辰,“更定德运为土,腊用辰”③脱脱等:《金史》卷11《章宗纪三》,第259页。, 后宣宗贞祐二年(1214)二月又重议德运,但不了了之,直至金末仍奉行土德④参见陈学霖:《金国号之起源及其释义》,《辽金史论集》第3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89—300页;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31—40页;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89—203页。。 然而关于金世宗以前的德运问题,则尚存争议。《金虏图经》记载“虏人以水德”,“旗帜尚黑”,这无疑明确表示金朝前期曾为水德。而且无独有偶,在宋代文献中似乎还有一条旁证。《新刊宣和遗事前集》记有这样一个故事:
(宣和五年某日夜,宋徽宗与林灵素飞天,同游广寒宫)见二人于清光之下,对坐奕棋:一人穿红,一人穿皂,分南北相向而坐。二人道:“今奉天帝敕,交咱两个奕棋,若胜者得其天下。”不多时,见一人喜悦,一人烦恼。喜者穿皂之人,笑吟吟投北而去;烦恼之人穿红,闷恹恹往南行。二人既去,又见金甲绛袍神人来取那棋子、棋盘。徽宗使林灵素问:“早来那两个奕棋是甚人?”神人言曰:“那着红者,乃南方火德真君霹雳大仙赵太祖也;穿皂者,乃北方水德真君大金太祖武元皇帝也。”言罢,神人已去。⑤佚名:《宣和遗事》前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据《士礼居黄氏丛书》本排印,第63—64页。
在这个故事中,身穿红、皂两色的对奕者是宋太祖赵匡胤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因北宋定本朝德运为火德,色尚赤⑥参见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2—106页。, 故宋太祖穿红,而金为水德,色尚黑,故金太祖穿皂,这与《金虏图经》所记相合。美籍华裔学者陈学霖先生首先注意到这条材料,并解释说金前期当继承辽朝之水德⑦陈学霖:《宋金二帝弈棋定天下——〈宣和遗事〉考史一则》,《宋史论集》,第211—240页。。 然刘浦江先生的看法不同(以下简称“刘文”),认为“《金虏图经》和《宣和遗事》的水德说分别代表金、宋两国民间的说法”,“建立在五德相胜说的基础之上”,与汉以后王朝德运例来以五德相生说为理据不符,且明确表示金初直至海陵王时代,“金朝尚未确定其德运所尚”⑧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93—195页。为避繁冗,以下提及刘文,不复出注。。 近年,香港学者曾震宇又撰文发表新论(以下简称“曾文”),他在上述两条史料之外,又找了几则其他记载认为可以印证金初德运确为水德,并解释金以水德王的原因是女真人出自北方的玄武神崇拜信仰和以水克火的五德相克说,又称金水德乃是来源于辽朝为金德①曾震宇:《金初“以水德王”探析:立足于金海陵王一朝的考察》,戴仁柱(Richard L.Davis)、曹家齐、韦祖松主编:《岭南宋史论丛》,第604—633页。为避繁冗,以下提及曾文,不复出注。。 然而这一论断存在漏洞,并不能成立。
曾文坚信金初为水德,除《金虏图经》和《宣和遗事》的说法外,还举出了四条以黑色代指金人或金国的记载,分别见于蔡絛《铁围山丛谈》和赵彦卫《云麓漫钞》。其中一条是上文已征引过的建炎三年,侯懋、李幾等三人所见滥杀无辜的那群“黑衣”人,即指金兵,另外三条史料是:
(1) 洛阳古都,素号多怪。宣和间,忽有异物如人而黑,遇暮夜辄出犯人。相传谓掠食人家小儿,且喜啮人也。于是家家持杖待之,虽盛暑不敢启户出寝,号曰“黑汉”。繇是亦多有偷盗奸诈而为非者,踰岁乃止。此《五行志》所谓“黑眚”者是也。不数年,金国寒盟,遂有中土,两都皆覆。(《铁围山丛谈》)②蔡絛著,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3,第45页。
(2) 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为四方之神。祥符间避圣祖讳,始改玄武为真武,玄冥为真冥,玄枵为真枵,玄戈为真戈。后兴醴泉观,得龟蛇,道士以为真武现,绘其像为北方之神,被发黑衣,仗剑蹈龟蛇,从者执黑旗。自后奉祀益严,加号“镇天佑圣”,或以为金虏之谶。(《云麓漫钞》)③赵彦卫著,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9,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8页。
(3) 绍兴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侵晨,日出如在水面,色淡而白,中有二人,一南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黑,相与上下,甚速。至日中,光彩射人,以水照之,祗见南白一人,余不见。是年十二月逆亮送死于淮南,方悟黑人为亮云。(《云麓漫钞》)④赵彦卫著,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10,第177—178页。
从内容来看,这三条记载均属符谶之说。第一条相传北宋末洛阳地区夜晚有怪物掠食小儿,号称“黑汉”,后南宋人硬将其说成是正史《五行志》中提到的“黑眚”,因水生祸,视为金国败盟伐宋之征兆。第二条谓因兴醴泉观得龟蛇而绘北方之神真武像⑤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宣和四年五月十八日乙亥,引蔡絛《北征纪实》记云:“(宣和四年)雄州地震,已而雄州之正寝忽元(玄)武见,龟大如钱,朱蛇仅若筋,每行必相逐。二帅(指童贯、蔡攸)拜之,藏以银合,置于城北楼真武庙。明日启合视之,龟蛇皆死矣。”(第2b页)《云麓漫钞》所谓兴醴泉观得龟蛇或即指此事。,“被发黑衣”,“从者执黑旗”,按五方配五色的习俗,北方为黑,故画黑衣、黑旗本不足为奇,然南宋人却以此为“金虏之谶”。第三条记金海陵王完颜亮征南宋,一日清晨日出时有人见水面上浮现南白、北黑两人,然水中倒影却只有南白一人,后完颜亮兵败被杀,南宋人遂以北黑者指亮。它们显然都是金灭北宋、掳走二帝之后,在民间散布的种种传说,纯属牵强附会,其故事本身荒诞不经,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皆以黑色为北方金人或金国之隐喻。按照曾文的思维逻辑,既然以黑指金,自可说明金行水德,其最主要的依据还是上引《金虏图经》的记载。诚然,金初金军旗帜、服饰尚黑,但这一定是代表五德终始说中的水德吗,会不会有其他解释呢?
实际上,在女真族习俗中本有尚白和尚黑两种颜色喜好。金朝将女真集团各氏族厘定为“白号之姓”和“黑号之姓”两大姓氏群体⑥按《金史》卷55《百官志一》记“白号之姓”包括金源郡二十七姓、广平郡三十姓、陇西郡二十六姓,“黑号之姓”包括彭城郡十六姓(第1229—1230页),共计九十九姓。而姚燧《牧庵集》卷17《南京兵马使赠正议大夫上轻车都尉陈留郡侯布色君神道碑》则谓“金源郡三十有六,广平郡三十,皆白书”,即“白号之姓”;“陇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书”,即“黑号之姓”(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1201册,第586页下栏),共一百一十姓。两者对女真氏族的划分不同,有学者认为前者可能是金初完颜勖撰《女直郡望姓氏谱》所定,而后者系金章宗时重新改定的姓氏谱,参见朱希祖:《金源姓氏考》,原载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2卷第3、4合期,1934年,收入氏著《中国史学通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68—374页。。 其中,宗室完颜氏乃“白号”之首,金人在解释“大金”国号时明确称“完颜部色尚白”⑦脱脱等:《金史》卷2《太祖纪》,第26页。, 又《三朝北盟会编》卷3载女真风俗亦言“其衣服则衣布,好白衣”⑧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重和二年正月十日丁巳,载女真始末,第4a页。。 由此推测,所谓“白号之姓”盖即得名于女真人的尚白之俗,同理“黑号”之名恐怕就与女真人的尚黑之俗有关。其实作为人类最朴素的视觉审美,这种对于白、黑两色的崇尚观念在北方民族中并不罕见,如蒙古人也同时存在着尚白和尚黑两种颜色喜好①参见李自然:《蒙古族尚白原因及表现方式》,《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3期,第115—117页;白翠英:《蒙古孛额教的尚黑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3期,第102页。。 契丹人尽管可能以尚黑为主,但在辽代流传的“青牛白马”祖源传说中,“青牛”其实就是黑色②参见陈述:《哈喇契丹说——兼论拓拔改姓和元代清代的国号》,《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第67—77页。,与“白马”相对,亦显示出这一对色彩的重要意义③如王可宾即将契丹“青牛白马”传说归入北方民族以黑、白划分氏族集团的习俗,参见氏著《女真人从血缘组织到地缘组织的演变》,《辽金史论集》第2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12—213页。。 不过,白、黑两色所代表的含义当有所不同,在象征统治权力的首领旗纛上黑色似更为尊崇。例如《南齐书·魏虏传》记载鲜卑人的车服之制,“轺车建龙旗,尚黑”④《南齐书》卷57《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7年,第1092页。,《魏书·太祖纪》也提到魏太祖拓跋珪出行车驾“车旗尽黑”⑤《魏书》卷2《太祖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2页。。《元史·舆服志·仪仗》首列“皂纛,建缨于素漆竿。凡行幸,则先驱建纛,夹以马鼓。居则置纛于月华门西之隅室”⑥《元史》卷79《舆服志二·仪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957页。关于蒙古旗纛,参见马晓林:《马可·波罗所见蒙古皇家旗纛》,《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115—129页。。 这种源自北方民族传统的“皂纛”亦被中原王朝所承用,成为皇帝卤簿仪仗的必备元素⑦脱脱等:《宋史》卷148《仪卫志六·卤簿仪服》,记云:“皂纛,本后魏纛头之制。唐卫尉器用,纛居其一,盖旄头之遗象。制同旗,无文采,去鎞首六脚。《后志》云:‘今制,皂边皂斿,斿为火焰之形。’金吾仗主之,每纛一人持,一人拓之。乘舆行,则陈于卤簿,左右各六。”第3465页。。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金初女真军“凡用师行征伐,旗帜尚黑”,可能就是来源于北族旗纛尚黑,进而影响到军旅服色。至于女真人原本的尚白之俗,则在议定国号等其他方面得以体现,兹不赘述。总之,金初军中的旗帜、服饰尚黑,只是金人源自本俗的颜色喜好而已,实与德运之说没有任何干系,世人往往见到“尚黑”就附会为“水德”是极不可取的⑧譬如如众所周知,《史记》记载秦为水德,色尚黑,但最新研究表明,秦朝并未采用五德终始说,秦人尚黑乃是当时人的一种普遍审美,所谓秦用水德之说其实是西汉正统观形成之后,汉儒为支持革除秦政的政治主张而构拟出来的,参见陈侃理:《如何定位秦代——两汉正统观的形成与确立》,《史学月刊》2022年第2期,第5—18页。。
由于金军一路南下,攻城掠地,所向披靡,其标志性的黑旗、黑衣给宋人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故有邓肃《靖康行》诗所谓“皂帜登城吹黑风”之叹。正是这样一种深刻的心理印象,使得南宋时人们附会出了各种传说,将许多与“黑”有关的怪异之事均视为“金虏之谶”,如上引三条《铁围山丛谈》和《云麓漫钞》的记载;并按照汉人的五德终始观念比附为水德,如《宣和遗事》的故事就是由此而来。《宣和遗事》的文献性质乃是平话小说,今传本是元代书会在宋代话本基础上重新整理编定的⑨参见王利器:《〈宣和遗事〉解题》,《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第57—63页。, 不能当作一手史料来看待,前引红、皂二人对奕的故事显然是杜撰出来的,其以金太祖为“北方水德真君”,应是宋元时人的穿凿附会,不可当真。而曾文却又据此及《云麓漫钞》所载“金虏之谶”,强作解人,推定金人受道教思想影响有北方玄武神崇拜的信仰,为奉行水德的一大动机,又失之远矣。
那么,张棣《金虏图经》记载“虏人以水德”又是否可信呢?上文提到,张棣大约是在金章宗明昌三年或稍后归宋的,当时金朝已定为金德,但张棣却未言及,刘文解释说可能是金世宗未将本朝德运诏告天下,一般士民未必家喻户晓。除去世宗一朝,曾文认为张棣的记载可反映金初至海陵王时期当为水德。然而刘文举出了一条很有力的史料,可以证明金前期未定德运。《大金德运图说》收录有一通“省奏”云:“尚书省奏准尚书礼部举,窃闻王者受命开统,皆应乎五行之气,更王为德。方今并有辽、宋,统一区夏,犹未定其所王。”①佚名:《大金德运图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648册,第321页下栏,第313页上栏。据刘文考证,这份尚书省奏当作于海陵王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间(1151—1153),金主完颜亮已有一些正统意识,欲一统天下②关于金朝正统观的形成过程,可参见宋德金:《正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70—85页。, 但这通“省奏”说得很清楚当时“犹未定其所王”,说明金前期朝廷尚未讨论德运,故张棣所载“水德”之说恐怕只是金朝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
这种“水德”说之所以会在金代民间流行,盖一者金初军中尚黑,恰巧与水德之色相合,二来或与海陵朝“以水克火”的符谶有关。《金史·地理志》谓沃州本为宋庆源府,金“天会七年改为赵州,天德三年更为沃州,盖取水沃火之义”③脱脱等:《金史》卷25《地理志中》,第603—604页。。 此事宋人亦有记载,周煇《清波杂志》云:“虏改吾赵州为沃州,盖取以水沃火之义。识者谓沃字从‘天’、‘水’,则著国姓,中兴之谶益章章云。”④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12《虏改沃州》,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15—516页。关于金改赵州为沃州的原因,绍兴二十九年出使金朝的周麟之留下了记录:“沃,吾古赵州也。予过赵,问所以易名者,州人曰:‘往年此邦忽天开,有声如雷,流火涌出。虏疑其为赵氏复兴之祥也,改今名,且取夫以水沃火之义。’或又曰:‘沃之文,天水也。赵氏之兴,其谶愈昭昭矣。’语虽不经,不可不纪。”⑤周麟之:《海陵集》外集《中原民谣·过沃州》诗序,民国九年韩国钧辑《海陵丛刻》本, 第4b页。由此可知,赵州更名是由于海陵王时期当地忽有流火涌出,而赵宋为火德,故金恐为“赵氏复兴之祥”,遂改名沃州以厌之,取“以水沃火之义”,不料民间反因“沃”字从“天”“水”而衍生出“赵氏之兴”的谶言。这说明金代社会也流行五德相胜的观念及其相关的符谶言论,曾文以此为金初水德的动机之一,然上文已言明,金海陵朝官方未定德运,这些“以水克火”的符谶可能只是诱生了民间流传的金为“水德”之说⑥类似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元代,参见曹金成:《元朝德运问题发微:以水德说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140—153页。。
此外,据曾文解释,金初之所以定为水德,还与辽朝的德运有关。辽咸雍元年(1065)《耶律宗允墓志》言“我国家荷三神之顾諟,乘五运之灵长”⑦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19,452页。, 说明辽朝亦有五运之说,但具体是什么德运,目前所见辽代文献及石刻资料均缺乏记载。前辈学者仅从《大金德运图说》中找到一条金人的说法,金章宗朝讨论德运时,“秘书郎吕贞幹、校书郎赵泌以为圣朝先(当作克)辽国以成帝业,辽以水为德”⑧佚名:《大金德运图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648册,第321页下栏,第313页上栏。。 冯家昇、陈学霖、刘浦江等诸位先生皆认为金人以辽为水德,当可信从⑨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页;陈学霖:《宋金二帝弈棋定天下——〈宣和遗事〉考史一则》,《宋史论集》,第219页;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89—192页。。然而曾文却以此系孤证,不以为然,并找了两条史料试图说明辽朝当为金德。其一,辽大安九年(1082)《景州陈宫山观鸡寺碑铭》云:“我巨辽启运,奄有中土……土俗传说,曾观山峰有金鸡之瑞,因以名焉。”⑩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19,452页。曾文以此处“金鸡之瑞”为辽金德之证。按此陈宫山观鸡寺始建年代不详,但至少北魏时即已存在,见于郦道元《水经注》记载⑪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4,“鲍丘水”引《魏土地记》云:“蓟城东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鲍丘水又东,巨梁水注之,水出土垠县北陈宫山,西南流迳观鸡山,谓之观鸡水。水东有观鸡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3页。, 故所谓以“金鸡之瑞”而名寺乃北魏以前事,与辽朝德运风马牛不相及。其二,建炎元年七月傅雱使金所撰《建炎通问录》,记载他与金馆伴使的对话,傅雱问金朝崛起有何“朕兆以应受命之符”,馆伴云:“别无符谶,只是大辽曾占国中金气旺盛,以此应谶。”⑫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10,建炎元年七月四日壬辰,引傅雱《建炎通问录》, 第9a页。“占”字原涂改不清,今据国家图书馆藏明郁冈斋钞本校正。曾文径以此所谓“金气”证辽为金德,但据上下文义可知,时人显然是将“金气旺盛”视为金国兴起之符谶,亦与辽朝德运无关。曾文此后又列举了几条宋人记载指佛为“金狄”的说法,试图进一步解释辽为金德与佛教有关,但其实,这些记载同样也都是以“金狄”指金国,而与辽朝无涉①例如叶寘《坦斋笔衡》云:“徽宗崇尚道教,凡当时诏命与夫表章,皆指佛为金狄……其后女真起海上,灭辽国,陷中原,以金国为号,正谶金狄之祸。”见叶寘著,孔凡礼点校整理:《爱日斋丛抄》附录一《叶寘〈坦斋笔衡〉二十一则》“金狄”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50页。。 总之,曾文所举辽为金德的史料皆理解有误,其论点无法成立。
就目前所知,文献记载中仅提到“辽以水为德”。除了上引《大金德运图说》秘书郎吕贞幹、校书郎赵泌之说外,其实在同书中还有另一处较为隐蔽的记载,前人皆未注意:
翰林学士承旨党怀英取苏轼《书传》之说,以为禹以治水得天下,故从水而尚黑,《书》云“禹锡玄圭”是也。殷人始以兵王,故从金而尚白,《诗》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是也。钦惟太祖皇帝兴举义兵,剪辽平宋,奄有中土,与殷以兵王而尚白理同。本朝宜为金德,此盖遵太祖之圣训,有自然之符应。谓宜依旧为金德,而不问五行相生之次也。②佚名:《大金德运图说》,第312页下栏。
金章宗朝的德运之争,党怀英主张定为金德,他援引大禹开创夏朝为水德尚黑、殷商代夏为金德尚白的典故,指出金灭辽的情况当与商革夏相仿,言下之意,即以辽朝与禹夏同为水德,故金朝可循殷商之先例为金德,而不必顾忌五德相生的传统理论。党怀英乃是金代中期的文坛领袖,自大定二十九年至泰和中致仕之前,奉命刊修《辽史》十余年③参见脱脱等:《金史》卷125《党怀英传》,第2726—2727页。, 想必对辽朝掌故十分稔熟,所以党怀英称辽为水德,很可能有辽代文献的原始依据,可印证前引吕贞幹、赵泌“辽以水为德”之说。至于辽朝水德的来源,刘文解释乃是继承石晋之金德,可备一说④苗润博《被改写的政治时间:再论契丹开国年代问题》(《文史哲》2019年第6期,第104—105页)对辽朝正统性来源问题提出异议,认为辽人当承唐统而非晋统。但关于辽朝的确切德运,目前尚缺乏辽人的直接记载,仍需存疑待考。, 此外或许也与契丹人尚黑之俗有关。若辽为水德,按照五德转移理论,辽金鼎革,金朝无承用胜朝德运之理。从总体的记载情况来看,金初当未定德运,张棣《金虏图经》所谓“虏人以水德”之说并不能代表金朝的官方立场。
结 语
本文研究的起因是对宋金盟誓约定岁输“绿矾二千栲栳”这样一件小事产生兴趣,试图解释其缘由,然在文献记载中没有任何现成答案,那么我们就要从绿矾是什么、有何功用入手去加以思考。这就需要了解绿矾的化学组成、制取工艺、主要产地、实际用途等相关科技史知识,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方能予以解释。因金初金军旗帜、服饰尚黑,而绿矾正是用于染黑的主要原料,需求量大,金国在答应将包含矾矿的辽西京部分地区给与宋朝,以致无法自行生产绿矾的情况下,所以特别要求宋朝每年“交绿矾二千栲栳”,也就容易理解了。这一研究案例所带来的启示是:第一,掌握科技史知识或可为某些历史问题的考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而历史学问题意识的引入则可为科技史的外史研究开辟新的问题空间。第二,对于某些无任何直接记载的历史问题,我们的研究思路不必逐奇求异,而是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常识”方面去加以考虑分析,或许自可通解。
至于本文附带讨论的金初尚色与德运问题,笔者想要强调的是金初军中旗帜、服饰尚黑,其实源自于北方民族固有的尚色习俗,与中原王朝的德运之说无关,后世学者不应将此类“尚黑”现象视为“水德”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