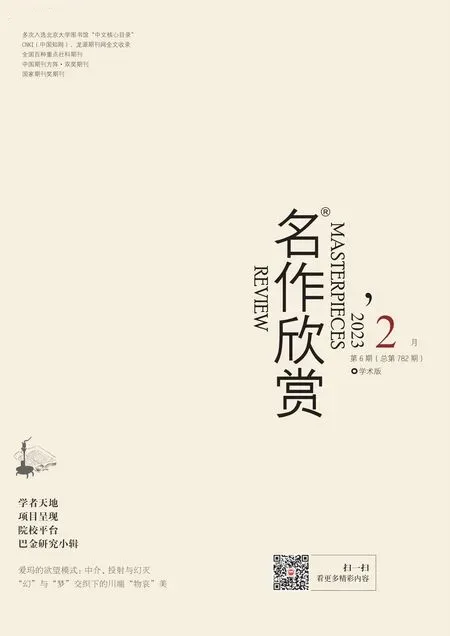浅论《罪与罚》中的犯罪动机问题
⊙杨清淼[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洞察人心的作家,享有“心理学家”的赞誉,对此他却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可这个称谓并不贴切,我不过是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者,即全面展现人心的深度。”为了真实呈现“日夜风波起”的人心和“世人心更险于山”的事实,作家观察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尤其处于社会底层被欺凌和被侮辱者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审视人心最隐蔽的角落,准确描述病态心理和精神疾病,这种写作风格与其人生经历相关。作家18岁时首次发作癫痫,这类神经精神疾病令他承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也给他机会“管窥”神秘力量和体验创作激情。28岁时因参加反对沙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他被流放西伯利亚。这期间作家从律法与哲学角度审视现实,思考恶行的成因。
一、犯罪主题的创作
19世纪40年代,欧洲各国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人们开始思考,既然人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与痛苦皆源自不公正,那么人自身可以按照公正原则建立尘世的生活。“如果能基于理性和公正安顿生活,那么人们会立刻成为幸福的人儿,导致罪恶、痛苦和犯罪的种种原因也会消失。”这种思想很快被俄罗斯的年轻人接受,而“特殊又强大的人能改变历史进程”的观念在年轻人中甚是流行。19世纪下半叶,不断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导致俄罗斯村庄逐渐衰败;农奴制改革加剧了人民的贫困,激化了各类社会矛盾,犯罪率不断增长。于是,犯罪与惩罚成为那个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主题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1年创作完成的小说《死屋手记》中最早提及了犯罪与法律惩罚的问题,但并没有深入研究犯罪问题。后来,他在《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多部作品中深入讨论犯罪与惩罚的问题。
作家描写罪犯的素材主要来自其本人在鄂木斯克监狱的经历,“在这里他遇见过罕见的心地善良和内心纯洁的人们。同样在这里也见过一些杀人犯,他们之所以杀人不是因为贫穷、饥饿和嫉妒,而是处于就想这么干”。在西伯利亚的见闻令作家意识到:人是世间最难以破解的谜;人的罪行越多便越易于沦为恶之奴,越容易丧失选择的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的自由是指每个人绝对的、无条件的责任,即一旦选择这样或那样的道路,人便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正是带着这样的认识,作家创作了小说《罪与罚》,深入探究主人公的犯罪动机。
二、小说《罪与罚》的创作背景
《罪与罚》是作家在狱中构思的首部以犯罪为背景的哲学心理学小说。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1859年10月9日)中,他写道:“我将在12月开始写一部小说……这是一部忏悔小说……我所有的心血都将投入到这部小说中。我是在监狱里构思的,躺在双层床上,在悲伤和自我毁灭的困难时刻……”作家从狱友口中获悉各类罪行,并对这些罪人的行为和性格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在监狱里,他第一次与普通的俄罗斯人,或者说与他们中“最坏的”人面对面交流。作家发现即便是在这些罪犯身上也藏着高贵的品质和坚定的信念。
1865年9月,《主张》报先后刊登了两篇报道:商人之子格拉西姆·奇斯托夫用斧头劫杀厨娘与洗衣妇;放高利贷的法国人贝克及其助手列昂季耶娃被谋杀,凶手竟然是思想成熟且有远大志向的19岁的格鲁吉亚公爵米凯拉泽。这两则报道中的青年罪犯成为小说《罪与罚》主人公的原型。基于对现实及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作家成功塑造了一位秉持理论杀人的罪犯拉斯柯尔尼科夫。
三、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动机问题
小说《罪与罚》中理智聪颖、内心温暖的穷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目睹并经历着人间疾苦,他不停追问:为什么有些人品德高尚、与人为善却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人是“卑微发抖的生物”,还是有“权力”违背道德原则的世界统治者?“我”是地位低下、能力有限的普通人,还是创造规则的“全能者”?为了验证自己是否属于像拿破仑那样的人,精神困顿的主人公打着维护公平和正义的旗号谋杀了高利贷者阿廖娜及其妹妹莉扎薇塔。很多研究者认为,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行主要是无视戒律,其次才是违反法律的谋杀罪。一个能够违背道义的人就是“为所欲为”之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上帝面前犯了不信之罪,在人类面前犯了谋杀罪,然而谋杀实质上是不信之罪的直接后果。关于主人公的犯罪动机,研究者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著名文学评论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认为,促使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的真正动机是难以忍受的社会环境;哲学家和文评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指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动机源自不可遏制地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施的念头;苏联文评家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基尔波京强调拿破仑式的理想与弥赛亚情结之间的冲突是主人公的杀人动机;伊戈尔·维诺格拉多夫认为促使主人公杀人的是错误观念,即“人自身规定自己的良知界限,人凌驾于善恶之上”。
细读文本后不难发现主人公的犯罪动机十分复杂,大致可分为如下三层。第一层源自压抑许久的愤怒和仇恨。为了供他读书,母亲与妹妹不但倾尽所有家财,而且开始屈尊忍辱地讨生活,这种牺牲令拉斯柯尔尼科夫痛苦不已,再加上还不起的高利贷,令他陷入愁苦郁闷之中。当最后一件值得典当的物品被迫低价抵押给阿廖娜时,他内心积蓄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随后便计划谋杀这个放高利贷的“虱子”。起初他还犹豫不决,但一天他在小酒馆无意间听到两个年轻人的对话。其中一人历数阿廖娜的罪恶并直言应该杀死她,将其钱财用于拯救他人的公正事业,因为“一个人的死可以换来一百个人的生——这笔账是最简单不过的!而且这样一个痨病鬼,这样一个又蠢又狠的老婆子,她的一条人命摆到大众的天平上,又算什么呢?充其量不过像一只蟑螂或虱子,也许连这也不如,因为这老太婆是有害的。她在坑害别人”。这时主人公发现不止自己萌生了谋杀阿廖娜的念头。最终,压抑许久的愤怒和仇恨坚定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决心。然而,杀人后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并没有得到解脱,相反,他受不了良心的折磨,比以前更加压抑和痛苦,这是他犯罪后的自我惩罚。
第二层源自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秉信。在向索菲亚坦白自己的罪行时,拉斯柯尔尼科夫承认了自己杀人并非纯粹为了钱,而是借助杀人令自己成为拿破仑那种人,即强者、统治者和立法者。“倘若拿破仑处于我的境遇……他就会毫不犹豫,不让她叫喊一声就把她掐死了!……于是,我也……效仿这位权威……毫不犹豫地……杀了她……”这种效仿体现了达尔文主义的伦理观:“谁强大,谁智谋和精神超人,谁就是人们的主宰!谁胆大敢干,谁就真理在握!谁能藐视一切,谁就是人们的立法者!谁最敢干,谁就最正确!”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很快作为社会法则被世人接受,达尔文主义发展为社会伦理观。目睹周围人的悲苦生活,尤其是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不幸,加之自身陷入窘迫困顿之境,特别是妹妹杜尼娅为了生计被迫嫁人的屈辱,主人公坚信:人分为两类:“普通的人”和“特殊的人”。第一类人是“低级”的材料,他们因循守旧且安于现状,过着低三下四的生活;第二类人是有天赋且能提出新见解的真正的人,他们“有权让自己的良心越过某些障碍”,“推动世界前进,引向预定目标”。虽然如此,主人公认为“不管第一类人还是第二类人,都有完全一样的生存权利。总之,所有人都有完全平等的权利”。秉持这种理论的主人公认为阿廖娜是坑害他人、损害他人生存权利的普通人,而自己作为有思想、有知识的大学生,不但有能力提出新见解,还应该有能力反抗不公平和非正义。这种念头令他寝食难安。最终,他打着杀富济贫、维护社会公平的旗号,通过谋杀阿廖娜来验证自己属于那类人。殊不知,当他决定谋杀阿廖娜时,他已经违背了自己的理论:所有人享有生存权。所以,拉斯柯尔尼科夫不过是假以理论杀人的犯罪分子罢了。
第三层源自实施自由意志的渴望。自由意志是涉及人类行善或作恶的能动性问题。“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此处仅提到善恶二元论,并没有展开论述。后来奥古斯丁指出自由意志实质是一种取舍问题,即追求小善而舍弃大善。为追求眼前利益而违反道德秩序的行为被奥古斯丁视为罪恶。根据奥古斯丁的哲学理论,自由意志是用来行恶的。他认为自由意志除了犯罪外毫无意义可言。对此,英国佩拉纠提出了反驳的观点,他认为自由意志具有行善和行恶的两种选择。而康德则认为,自由意志与服从道德律的意志是一种完全相同的意志。根据这个概念,自由意志并不是那种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满足意愿爱好和欲求的东西,相反,它完全可以对人的非理性冲动和欲望进行理性控制。在论证实现“至善”的历史过程时,康德多次强调“应该始终把人看作目的而不只是手段”,认为实现“至善”便是要把“社会团体转变为道德的整体”,在各种契合关系中达到和谐,强调“至善”的总体性、和谐性和公正性。据此,康德提出“促进作为社会之善的至善”的义务和“通过你的努力使你配享幸福”的义务论,最终使自由意志成为道德法则的存在根据,道德法则成为自由意志的认识根据。
文本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自认为只要有胆识行凶,那么他就能完全自发地作恶,突破行善的道德法则。为此,拉斯柯尔尼科夫利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反抗手段,施行自由意志,试图建立新的道德法则。在选择被害对象时,为了降低愧疚感,他选择杀害邪恶又无用的阿廖娜,并冠之以维护社会公正的理由;可是实施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无辜善良的莉扎薇塔也惨死在主人公的斧刃之下。阿廖娜的高利贷者身份与其无限压榨他人的贪婪成为拉斯柯尔尼科夫谋杀她的理由,这确实降低了他的负罪感。可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源自情感和社会身份层面的双重杀人动机影响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由意志实施。当主人公杀死阿廖娜且不慌不忙地翻找财物时,他差点成功验证了自己所谓的自由意志。可莉扎薇塔闯入了杀人现场,惊慌失措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迫不得已地杀了她。可以说,完全无辜的被杀害对象莉扎薇塔导致主人公的验证失败——因为杀害莉扎薇塔,他背负难以承受的罪责,开始质疑自己的理论。根据奥古斯丁的学说,自由意志的界定本在于无条件地、自发性地实施恶行。所以说相较于姐姐阿廖娜,莉扎薇塔更适合验证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由意志。可是杀害无辜者的愧疚感令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精神近乎崩溃,承受着源自良知审判的精神死刑,这比法律惩罚更痛苦不堪。这种惩罚是其自由意志实施的直接后果,向大地忏悔、主动自首和接受流放西伯利亚的惩罚都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承担后果与责任的举措。
四、结语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和思想代表了19 世纪60年代俄国底层社会青年愤世嫉俗的现象,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哲理性思考,并借助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对话表达质疑:人是否能够突破伦理道德?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首与忏悔最终表明了道德法则对人具有自内而外的约束力,也表达了作者对信仰和大爱的肯定。但作者的态度并不能解决世间根本的恶的问题:为什么无辜者要承受无妄之灾?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发生凌辱性和压迫性行为?这一系列问题始终困扰着人类,人类也以不同的方式生生世世地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