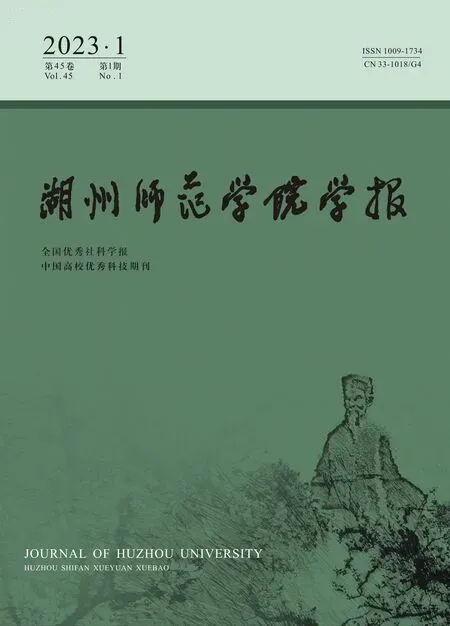“审父”意识中人类生存平衡的构建*
——重探《白鹿原》的生命自觉与文化自觉
赵书豪,卢兆旭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一、引言
《白鹿原》出版至今三十年(1993-2022),关于其的评述与阐释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热度,且以影视剧与话剧等方式呈现在大众视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逐渐纳入市场体系,在纯文学式微的境况下,能像《白鹿原》保持如此阅读热度的当代文学作品甚是少见。“寻根文学”的折返式找寻,“先锋文学”的实验性突破,“新写实”的现象式反映等,当代文学经历了曲折的探索与频繁的变轨,却无法脱离两大创作主题——一是对人的发现,二是对个体生存平衡(1)本文的“生存平衡”,意指人类对已有生存资料进行调配重组,对已有文化进行承继与剥离以实现人类群体延续性存在的可能,是一种生命体存在的自觉、自省与自建。的构建。
陈忠实作为文学陕军中的一员,根植三秦大地,承续柳青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同时一改以往现实主义作品的革命叙事以及阶级人物架构,回到对生命的思考,对民族灵魂的勾画,对传统文化的客观审视中去。半个世纪的风雨荒凉,一片原的河山更替,三代人的生死叛离,浩浩汤汤。细观这部“民族的秘史”[1]2,可以发现陈忠实的着笔点落在了人与文化上。陈忠实曾说:“我和当代所有的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2]28现当代文学史上首先为民族画魂的人当属鲁迅,《阿Q正传》《祝福》《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一系列“充满悲剧色彩”的小人物群像,不幸不争,可怜可爱,“存在于生存绝望的边缘上”[3]32。间隔了将近七十多年的历史,我们的国民灵魂到底有没有变化?五四时期各文学流派的“创”与新时期先锋文学的“创”同是在历史变革的精神空档期对文学创作流向的考量与实践,不同的是,“与五四作家视启蒙和拯救为己任相比,先锋作家缺少痛切承担的勇气。面对父辈文化的腐朽、衰颓本质,先锋作家选择了背负绝望的逃亡”[4]64。先锋文学后出现的《白鹿原》或许给我们提供更为全面的审视视角,它既拥有担当的勇气,也不乏剥离的果敢。
《白鹿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白鹿宗族的父子关系,父的羁绊与子的叛离贯穿小说始终。子辈对父辈观念的破与立成为白鹿原半个世纪风雨飘摇的一个导火索。“审父”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母题,鉴于西方个体私有制经济的父本位与中国血亲宗族式群体私有制的父本位有着质的不同,故我们的“审父”意指“一种以平视的姿态对某类先验的秩序性存在(人情和事理)进行理性的、客观的、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的意味的观照和审度”[5]21。如果说,“‘五四’文本中父子冲突模式的出现标志着审父意识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最初觉醒”[4]63,那么《白鹿原》中父子关系的对立与冲突便是“审父”模式在新时期文本中的成长与成熟,它超越了简单反叛与解构的“审父”模式,开始意识到承继与建构的历史担当,由“审父”向“审文化”转变。关于《白鹿原》中传统文化的象征与文化表达,评论家的阐释不尽相同。在文化象征层面的阐释中,张国俊认为《白鹿原》的文化象征是“仁义观念……形象地深刻地展示出关中文化观念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6]36;郜元宝认为《白鹿原》的文化象征归于道教,“《白鹿原》在‘寻根文学热’沉寂多年之后继续‘寻根’,但其所寻之‘根’糅合儒、佛、道而以道教文化为主导”[7]98;高洪娇等人则从“白鹿”这一意象象征中阐述文化自觉,“陈忠实选择了‘白鹿’这一意象来寻求内心的审美理想在古今融合中得到延续。从‘白鹿精灵’到‘白鹿精魂’,……这是一种内心的觉醒,更是一种文化的自觉”[8]165。在文化表达层面的论说中,南帆的“文化尴尬”说则认为《白鹿原》文本中“儒家文化的‘修身’即是压抑欲望,封锁力比多的出口。……儒家文化与现代性话语可能存在的深刻矛盾”[9]65;王春林则将“小说的基本冲突理解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宗法文化谱系与所谓的革命现代性之间的碰撞交锋”[10]48,将冲突具象到宗法文化与革命现代性二者之间。一部“秘史”,其内涵必定丰富多元,对《白鹿原》的解读远远没有穷尽。时间是一部作品最恰当的度量衡,站在三十年后的当下,以“审父”意识重读《白鹿原》,可以看到表层里的“审父”蕴含着“审文化”“审生命”的旨归,父与子的矛盾对立是传统宗法文化与现代革命文明交锋中所呈现出的文化自觉,更是人类延续中构建生存平衡的一种生命自觉。
二、审父的序曲:父的羁绊与子的叛离
封建宗法文化中的父子关系在稳定的时代可以持续维系社会秩序,父子由亲缘关系的根向价值关系的本延伸。“‘父’不只是‘子’的自然生命的来源,而且也是‘子’的文化生命乃至价值生命的来源。”[11]161当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父子关系粉碎个体对生存平衡的构建或经历历史断层期时,便会造成父的羁绊与子的叛离。《白鹿原》以浩大的篇幅呈现出动荡的20世纪上半叶白鹿原上白家父子、鹿家父子、鹿三父子以及田氏、冷氏父女的生死叛离。
(一)白家父子
从白秉德到白嘉轩再到白孝文与白灵一代,白家三代人的生存里深烙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生命与价值生命。当白嘉轩在父亲白秉德病榻前对即将面临的三年服孝与娶妻生子感到左右为难时,白秉德的回答是“你守三年孝就是孝子了?你绝了后才是大逆不孝”[1]9。这里涉及到宗法社会的孝道观,儒家的“孝子‘嗣亲’之道,可分为两方面:一为肉体方面,一为精神方面。其肉体方面,又可分三方面:一方面为养父母之身体;一方面须念此身为父母所遗留而慎重保护之;一方面须另造‘新吾’以续传父母之生命”[12]265。“孝道”的最终落脚点是生殖,是血脉延续,白嘉轩六娶六丧的传奇生命历程,更加诠释了宗法孝道观的稳固性特征。婚娶往往是传宗接代的代名词,作为个体的情感因素考量较少。然而从白嘉轩的下一代白孝文开始,历史的变轨与社会的动荡,宗法社会固有道德伦理开始受到现代革命文明的挑战。
白孝文与白灵是白家第三代中最具反叛意识的个体,传统宗族概念里长子与女子本是最守“礼法”的两种身份。然而在白孝文与白灵的身上我们看到“父”与“子”的决裂,看到“长子”与“女子”背离传统宗法的道德伦理规范,寻求构建生存平衡的本能。白孝文的生命轨迹在“性”上发生了转折,“性”仿佛成为白孝文重构生存平衡的井喷口,也成了与白父决裂的宣示牌。在与田小娥野合之前,白孝文始终走在父亲规划好的儒雅仁者道路上,长于耕读世家,习于白鹿书院,成于一族之长。与田小娥野合后,白孝文开始沉于毒色,面临着野狗分尸的生命终结,所幸鹿子霖弄巧成拙,白孝文走出了白鹿原,获得了重建生存平衡的可能。但在白孝文重新建构的生存平衡里,一改儒家的仁义与宽厚,成为游刃于功利之间的历史投机者。传统宗法文化在他身上破得彻底,也立得难堪。与白孝文不同,白灵对父亲的叛离始于“求新”,从拒绝缠脚到外出求学再到参加革命,白灵展现出新一代人对未来十足的热情与渴望,是一种生命自觉。逃脱宗法制度的场域,何其之难,白灵的反叛是坚决的,“你要是逼我回去,我就死给你看”[1]120。父子关系抹去了血脉温情,“那一刻,他似乎面对的不是往昔架在脖子上颠跑的灵灵,而是一个与他有生死之仇的敌人”[1]121,这种完全对立的位置,于父于子皆为生之所痛。但是对于生命而言,其要延续,要发展,革命是必然要求。
(二)鹿家父子
鹿家父子同白家不同,白家始终保持着白鹿族长的威严姿态,而鹿家在原上的口碑是“家风不正,教子不严,……根源自然要追溯到那位靠尻子发起家来的老勺勺客身上,原本就是根子不正身子不直修行太差”[1]572。较白家而言,鹿家仿佛一开始就游离于儒家宗法文化的边缘。吊诡的是白鹿原上家风不正的鹿家第三代人并未出现像白孝文一样的历史投机分子,而是成为革命的先锋,尽管鹿兆海的牺牲缘由迷离不清,其意义值得商榷,但一代青年的家国担当不可否认。
鹿家兄弟的反叛同白灵一样,始于“求新”。鹿兆鹏是鹿家的长子,这位长子从父辈那里接到的价值使命不是成为白鹿族长,而是成为读书人,“到老太爷的坟地放铳子”[1]64。当然,担当成为读书人使命的同时并不能搁浅传宗接代的责任。鹿兆鹏与鹿冷氏的结合,是在鹿子霖的巴掌与鹿泰恒的拐杖下完成的,这门婚事像是被挟持的两个人一同完成一场生涩的表演后牺牲了,也未能满足观赏者的欲望,一场可以预见却无力阻止的悲剧发生了。以致完婚之后,鹿兆鹏逃跑般离开白鹿原,始终未与鹿冷氏一起生活。以出走表示叛离,相比于五四惯有的迷茫出走,鹿兆鹏出走的目的很明确,他走向了革命前线,破旧的同时尝试立新。鹿家子弟中,对鹿兆海着墨较少,他游离于鹿家与白鹿原之外,由读书走向革命再到牺牲,仿佛脱离了宗法道德要求的羁绊。因此,鹿家的父子叛离主要是以婚娶为岔口,子辈与父辈分道扬镳,各自承受与担当各自的时代使命。
(三)鹿三父子
鹿三父子以长工的身份寄居于白鹿原,黑娃是在鹿三否定、白嘉轩强硬的合力拉扯下成长起来的孩子。鹿三眼里“那个慌慌鬼!生就的庄稼坯子”[1]68,进入校园不久就退学了,退学的原因除了对书本知识无趣外,还有反感于“对不住白家叔叔的好心”[1]69的“魔咒”。可以说黑娃生来就背负着寄人篱下的重担,他的成长始终无法脱离鹿三与白嘉轩主仆关系所产生的卑微感的羁绊。有评论者称白嘉轩与鹿三主仆之间超越了契约关系上升到了亲情层面,根据文本细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黑娃的认知里,这种主仆关系产生的一点微弱的温情并不能予其以生存的安全感。因此,当黑娃长到了可以出门熬活的年纪,他并未接受父辈从一主而终生的生存方式,而是希望“攒些钱买点地”[1]124。传统宗族社会,土地对一个农民的意义不仅仅是生存资本,更是繁衍资本。没有土地意味着只能将生命依附于他人身上,失去生身自由,这导致黑娃骨子里注定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
黑娃与鹿三父子关系的叛离始于主仆阶级性的压制,爆发于“小娥之死”。表面看黑娃、小娥的野合与白孝文相似,事实上黑娃与小娥之间的情感成分是肉体与精神皆有之,而白孝文更多的是肉体之欢。当然,不论是肉体之欢还是精神之乐,均无法在宗法社会的场域中找寻到存在的合理性。碍于宗法道德的规约,鹿三以田小娥“害的人太多了,不能叫她再去害人了”为由,亲手将梭镖刺入其后心。小娥的死使黑娃与鹿三之间产生不可弥合的裂缝:“大!我最后叫你一声算完了。从今日起,我就认不得你了。”[1]346鹿三父子关系断裂,仿佛未影响鹿三对黑娃的认知,黑娃一直以“谬种、劣种”的模样存在于父亲心中。父对子的强烈否定与强力压制,形成了黑娃强有力的反抗意识,压制与反抗势必会产生叛离,只是导火线长短决定了爆发时间的早晚。
(四)田氏、冷氏父女
传统父本位的宗族环境中,对女性而言,其与父亲之间的情感较为淡薄。宗法文化对女性的规约较多,从父、从夫、从子,简单说是从男而终,原本的血亲关系变为从属关系。原上两位悲剧女性田小娥与鹿冷氏便是在这种严格的从属关系中萎缩凋零。
田小娥是白鹿原上最具抗争意识的旧女性,受父之命嫁作举人妇,却只是郭举人“泡枣”的工具,作为人对性的本能需求被剥离。当生命本能与纲常规约发生冲突时,往往会导致个体的反抗与叛离。但田小娥对田父的反叛不是强力的决裂,而是转移到对“父母之命”的婚姻反抗中去,受于传统女性的视野局限,使她忽略了宗法社会场的强大,臆想着与黑娃私奔到一个可以容身的地方,不幸的是,脚下的这片土地上能生长出来的苗都是经过宗法文化筛选过的种子。田父作为老书生,对田小娥与黑娃结合的要求只是“一条戒律,再不准女儿上门”[1]145。因此,作为传统女性,田氏父女的叛离始于人对性的本能需求,这种本能几乎无法纳入一般的善恶评价体系之内。与田小娥的主动叛离预示其悲剧命运开始相反,冷氏父女之间冲突的爆发便是鹿冷氏悲剧命运的结束。鹿冷氏嫁入鹿家是父亲冷先生维持与白鹿两家和谐关系的权宜之计,鹿冷氏对“守活寡”的现状不满却也无力反抗,父家与鹿家在白鹿原上的地位不允许她表达出强力的叛离,所以鹿冷氏的反抗注定只能是死亡。鹿冷氏“工具性”的使命是父亲赋予的,也是父亲结束的。这对父女关系在悲恸中凋零,在沉默中消逝。
三、审父的变奏:传统宗法文化的承继与剥离
父子关系的叛离只是“审父”的序曲,《白鹿原》文本所呈现的不单单是“审父”,而是“审父”向“审文化”的延伸,“审文化”是“审父”的变奏。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这里的文化取其狭义之意,“主要指精神文明”[13]3。父子对立冲突进一步讲是传统宗法文化在历史变革期受到挑战所引发的“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指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13]1伴随历史的发展,文化以一种类于进化的方式进行着自我更新与自我剔除,以寻求存在于不同时空的合理性,其中,普适于一定地域、一定人群持续繁衍发展的文化会得到承继与开拓,相反,压制其发展,阻碍其延续的文化会逐渐被剥离。在《白鹿原》中呈现出来的“文化自觉”体现为宗法文化中旧有秩序面对革命现代性的挑战时,宗法文化中仁义人格的承继以及宗法文化中女性定义的剥离。
(一)宗法文化中秩序的现代挑战
白鹿原上的秩序是依托稳固的“主仆关系”“传宗接代”等宗法文化来维系的。白家父子是白鹿宗族的族长,事实上是宗法社会秩序的维持者即原上统治者。“主仆关系”的稳固使得原上的生产生活得到保障,“传宗接代”保障了族长继承人与宗族人口数量的稳定,若非历史变轨,一纸“乡约”统治一片原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当革命的火苗吹到白鹿原上,以往“主仆阶级”“传宗接代”稳固的生存秩序在白鹿村第三代人身上开始发生猛烈的动摇,在革命现代性面前摇摇欲坠。
以“传宗接代”来维持宗族秩序必定会牺牲个体对婚姻的自由选择权。白孝文、鹿兆鹏二人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非自主婚姻的初衷是“咱屋里急着用人”[1]113。正所谓“结婚之功用,在于造‘新吾’以代‘故吾’。‘新吾’之希望,在其能继续‘故吾’之生命及其事业,为其‘万世之嗣’”[12]264-265。白家希望子嗣繁衍以连任白鹿族长,鹿家是希望子嗣绵延来继承祖上的“勾践精神”为老爷子放铳子。父母之言的婚姻关系对白孝文与鹿兆鹏而言,这种规约似儒家的“修身”理念,它并未考虑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能欲求,更多的是以工具性的结合来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在20世纪人的自我发现之时代背景下,这种纯粹靠血亲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断然会被摧折。当然,源于血脉的亲情关系可否从社会秩序中彻底退出,成为一种纯粹的温情?或是在一种社会秩序的设立中可否完全抛弃血亲温情的参与?这一问题仍值得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将血亲关系彻底纳入社会秩序建构中是行不通的。这种反思是现代性带来的挑战,是一种文化自省,更是文化创建的基础。白鹿原上的另一种秩序维持方式便是试图将“主仆关系”纳入血亲关系中去,鹿三是白嘉轩父辈的长工,到了白嘉轩、白孝文一代,仍将鹿三看作自家人。实际上,这并未解除鹿三以寄居的方式游离于白家外的仆人身份,这种无根的卑微感在黑娃身上得到了强烈的回应。首先是对白嘉轩“神像”模样的反感,之后是伙同鹿兆鹏在原上掀起“农协风暴”,要求分割土地。黑娃的反叛是宗法文化“主”对“仆”的压制与剥削的必然反映,只是这种反映需要一个历史契机,一个合适的节点去呈现。
(二)宗法文化中仁义人格的承继
“审父”意识,既然是“审”,必然是以冷静的、客观的、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宗法文化。在20世纪中国,破传统文化的风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一次决绝的反传统行为都被时间证明是周期性的情绪表达。没有理由去彻底推翻一种可以维系一个民族无间断繁衍的文化,在人类史上也未出现像中华文明一样不间断传承的文明。宗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基因。早在《白鹿原》面世之初,雷达就指出:“《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了传统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2]152陈忠实所赞赏、挽悼的传统文化人格到底是怎样的人格呢?这个问题各家说辞不一,我们不妨从《白鹿原》中的仁义人格说开去。
仁义人格在《白鹿原》中有一条清晰的承继主线,从朱先生到白嘉轩再到黑娃。朱先生是“关中大儒”形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4]51,“四为”无一不源于责任感、源于担当。仁者爱众,义者奉公,正是这种仁义担当使得中华文明历经劫难不断代。朱先生凭借“为富思仁兼重义”[1]59的小字条化解白鹿两家争买李寡妇土地之事;只身前往兵营,免三秦父老遭屠城;“慷慨陈词、扫荡满川满园罂粟”[1]624;铁血柔肠赈济八方荒民。白嘉轩视朱先生为圣人,将朱先生的修行之道视为自己的治身之本,在“交农”事件中合全原之力搭救鹿三与和尚,“以德报怨”式的为曾经打折自己腰的黑娃求情,接济曾与自己针锋相对的落难兄弟鹿子霖。到了白鹿原上的第三代人,这种仁义担当在黑娃身上最能体现。在农协风暴遭遇挫折时,黑娃的不退缩绝非是革命觉悟使然,而是他认为“不讲义气不守信用”[1]208非人之所为,包括后来的上前线、入保安团、为鹿兆鹏的同志打掩护多为黑娃对“义”的践行。黑娃最终拜于朱先生门下“学位好人”,住进“学仁巷”,愿做私塾学堂先生。当然有评论者诟病这些反差性太大的情节设计使得黑娃人物形象失真,但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不失为陈忠实所赞赏、所挽悼的人格,是一种对仁义担当的文化基因能够得到承继的期许。
(三)宗法文化中女性定义的剥离
《白鹿原》中的女性描写引发了“女性主义”主题的讨论。有评论者称《白鹿原》“极大地丑化与伤害了女性形象和女性情感”[15]79,提出要重新论证《白鹿原》的经典性。还有评论者指出《白鹿原》对女性的书写“昭示出传统男权社会的价值立场”[16]161。“男尊女卑”的性别观是传统宗法文化的既定事实,用历史事实呈现出来的现实主义文本来定夺作者的价值取向略显偏颇。拨开所谓的女性丑化、妖魔化的面纱,细读文本,我们可以看到《白鹿原》对宗法文化所定义的女性是呈现剥离趋势的。
原上第三代女性从鹿冷氏到田小娥再到白灵,是宗法社会女性定义剥离的主线。鹿冷氏是遭受传统父道观羁绊最多的女性,除了女性身份之外,她还是白鹿原最有德行的医者的女儿,白鹿原上门第属二的鹿家的儿媳,重重规约使鹿冷氏只是有了反抗的意识,却没有叛离的可能。比鹿冷氏更进一步,田小娥的反叛充满原始力量,她是“一个没有任何机遇和可能接受新的思想启迪,纯粹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性要求,盲目地也是自发地反叛旧礼制的女人”[14]72。因此,田小娥的反叛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意识,而是开始觉醒,开始落到行动层面上去。被赋予“白鹿”象征的白灵成为彻底剥离宗法文化对女性规约的第一个,她走出白家,走出白鹿原,脱离宗法文化对女性的压制圈。从意识到觉醒再到叛离,宗法文化中的女性观显然成为文化发展的绊脚石而被一步步剥离,这是文化的自省与自新。
四、审父的旨归:人类构建生存平衡的自觉
由父的羁绊与子的叛离到传统宗法文化的承继与剥离,是“审父”向“审文化”的上升。“审文化”并非从《白鹿原》文本中才呈现出来的,事实上,刘再复早在《“共鉴”五四》中就提出“‘五四’是个‘审父运动’,父亲代表孔子”[17]61。如果说“五四”的审父审的是孔子,那对孔子的审判是强力的,更多的是批孔而非审孔,缺乏一定的理性。此外,五四的“审父”也绝非单单审孔子,审的更多的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宗法文化。20世纪对中国而言是个觉醒时代,“‘五四’是‘人—个体意识的觉醒’”,是人对“个体灵魂主权”的宣读[17]2。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鲁迅的作品,狂人的觉醒,祥林嫂对魂灵的质疑,“娜拉出走”后怎样,“铁屋子”里的呐喊。中国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对个体的关注意味着必须打破宗法社会对个体的强力束缚,重新寻求一种人类生存平衡的可能性。不论是“审父”还是“审文化”,其落脚点都是人,是对人的生存平衡问题的思考。由此,“审父”“审文化”“审生命”三者之间呈现交叉上升的趋势。“审文化”所引发的“文化自觉”最终指向是“生命自觉”,即生命在繁衍过程中拥有构建生存平衡的本能。因此,不论是对文化的承继抑或剥离,均以文明进化为导向,以寻求当下生存合理性为目的,以维持人类社会持久的长足的进步为旨归。
《白鹿原》中所呈现出来的对宗法社会的仁义人格的“挽救”,对宗法妇道观的剥离,对宗法秩序的考量,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当下历史时期构建生存平衡的一种生命自觉。仁义担当是宗法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后接续下来的文明,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动荡期,中国面临着山河破碎的危机,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投入到这场空前浩大的救亡图存浪潮中去,若非这种仁义担当,我们民族的生存平衡何以构建?中华文明何以延续?因此,与其说仁义人格的承继是“文化自觉”,不如说是历史动荡期中华儿女构建生存平衡的“生命自觉”。与之相反,宗法社会妇道观在革命现代性面前土崩瓦解,在“文化自觉”中被逐渐剥离。革命现代性不仅仅是物质文明,更是精神文明。纯粹的物质文明或纯粹的精神文明都会导致病态的现代性。宗法女性观中女性缠足以及“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约显然阻碍了女性迈向现代性的可能,鹿冷氏的意识、田小娥的反抗、白灵的叛离,源于生之本能,是维持个体生存平衡的自我建构。当个体生存平衡被打破时,生命会有一种重新构建的本能。由此,宗法文化对女性的压制势必会出现女性的生存斗争,这是一种生命的自觉。此外,《白鹿原》对于宗法秩序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对一纸“乡约”下长幼有序、主仆相敬、静谧谐和的白鹿原的留恋,另一方面是对维持这种秩序的“主仆关系”“传宗接代”所隐含的压制因素的忧虑。任何一个稳定的历史时期都需要一定的秩序性,“秩序”本身无关好坏,只是不合时宜的秩序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人类的发展当有一种“生命自觉”去调整、改革现有秩序以适应其可持续性的生存与繁衍。
五四时期,鲁迅对这种个体生存构建中所呈现出来的性格裂变称为具有中国“国民性”的“老中国儿女的魂灵”。陈忠实将之称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关于陈忠实在访谈中多次提及的“文化心理结构”,李建军做了专门的论述,与李泽厚提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在于,陈忠实于“文化心理结构”之前加了“人物”二字[14]40。陈忠实指出:“所谓‘文化—心理结构’ 只不过是一个表层的问题,更深层、更本质的,是稳定而普遍的‘人性—感情结构’。”[18]51当然,此处的“人性感情结构”稳定性是相对的稳定。文化可以呈现出多样性的繁荣,相对而言,人性在本质上具有一定的贯通性,某些最本能的、最自觉的情感,几乎不受时空、地域、种族的限制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生命自觉”便属于人类最本能的情感之一,通俗讲就是求生的欲望与求美的愿望的合一。不同于动物的是,人类力求的生存平衡是可持续的,是朝向下一代人,朝向未来的。因此,人类构建生存平衡的道路更为艰辛,它是一个历时性的任务,需要更为敏锐的忧患意识与自觉意识。“老中国儿女灵魂”的“国民性”与“文化心理结构”所表述的状态是一种现存的、不稳定的、有待剥离的文化势态,我们可以看到自五四时期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开始,“审父”主题间断性的反复出现,源于“文化自觉”“生命自觉”的生存拷问贯穿了现当代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审父”的旨归即人类构建生存平衡的生命自觉。
五、结语
“审父”意识下重探《白鹿原》的文化自觉,可以看到父的羁绊与子的叛离背后是传统宗法文化的承继与剥离,而对宗法文化的承继与剥离终归于人类构建生存平衡的自觉。20世纪破坏传统文化最突出的两个时期,一个是五四时期,一个是“文革”时期。然从五四时期的鲁迅到20世纪90年代的陈忠实,大约隔了七十年的时间,二人的文化观却惊人的相似。鲁迅站在世纪初为中国文化发展所立之言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9]56的理性、客观、发展的文化观,陈忠实站在世纪末自述《白鹿原》的现实意义在于使人们意识到“我们应该努力承载我们这个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同时也要毫不含糊地去剥离我们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中腐朽的东西,……使我们的民族能尽快一点进入一种比较高度文明的一个时代”[20]。现代性的道路上,尽管会间断性的出现情绪上的复古与去理性的先锋,但客观的、理性的、发展的文化审视始终在进行。这种“文化自觉”的旨归是为人找寻构建生存平衡的合理性。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觉醒之一便是对人的发现,“作为民族文化进步准则的,也只能是对人的价值的认识”[13]161。“文化自觉”伴随着人的发现与人构建生存平衡两大主题的成熟走向“生命自觉”,这种“生命自觉”在文化承递,人与非人生命、人与自然环境相处模式探寻中,凭借生命本能的自我调整、自我革新、自我重建完成人类生存平衡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