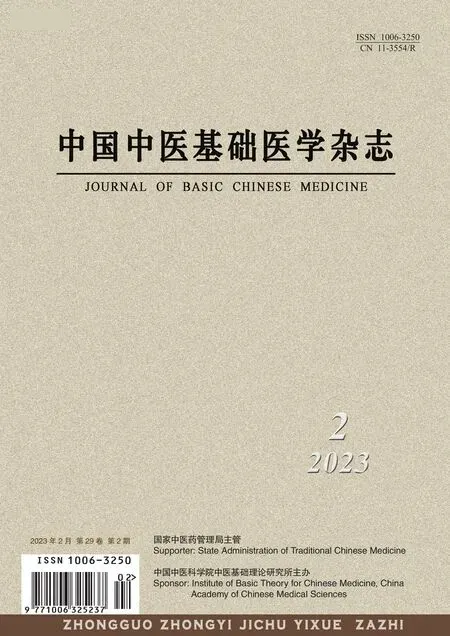探析《内外伤辨惑论》中蕴含的五运六气思想❋
陈 曦,李丹玉,莫雅婷,陈术胜,杨 薇
(1.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北京 100040;2.深圳市眼科医院,广东深圳 518040;3.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医院,湖南长沙 410011)
李杲生于1180年,卒于1251年,晚年乃太阴湿土主令。其生活年代正值战乱,人民疲于奔命,饮食失节,内伤脾胃导致的疾病屡见不鲜[1]。在其师张元素脏腑论病和五运六气思想影响之下,李杲总结前人理论,结合大量临床诊疗经验,撰写了《内外伤辨惑论》,论述世人用药之误,同时独创“阴火”理论[2],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其脾胃学说独成一家,被称为“补土派”。他认为脾胃在人的生命活动中作用重大,分析了五运六气变化对于人体产生的影响。李杲的脾胃理论思想内核,如“脏气法时”和“气运衰旺”便是应用五运六气理论的体现[3]。他在论治脾胃疾病时始终围绕天人合一思想,并将此思想贯穿于其著作中,在其著作中可挖掘到蕴含的五运六气理论。
1 在治疗方面的体现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提出“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的治法理论[4],李杲据此提出“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即甘温除热的观点。他认为脾胃内伤、心火内盛导致发热,若用辛热药物,有可能重竭脾阴,故在内伤脾胃疾病治疗过程中,以益气升阳、苦寒泻火为大法,用药以辛甘温或者归经为脾、胃经的药物为主。如在参术调中汤中谓“火位之主,其泻以甘”,以甘温之品黄芪泻热补气,与桑白皮配伍为君。
李杲深诲“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乘之也”[4]19五行生克制化传变规律,应用五运六气理论中的运气胜复论,阐发机体与五运六气变化之间的关系。其多次阐述大胜大复机理,认为“有胜之气,其必来复也”。如《内外伤辨惑论》中的神圣复气汤论述:“治复气乘冬,足太阳寒水、足少阴肾水之旺。子能令母实,手太阴肺实,反来侮土,火木受邪……此皆寒水来复,火土之仇也”[1]21。此段言明了脾土胜、肾水复的关系。由于脾土克制肾水太过,冬季时太阳寒水当令,肾水旺盛,反侮脾土,故出现“食少”“大小便不调”“肠鸣”等症。而子能令母实,金为水母,肺金气实,肺金相乘肝木,故出现“两胁缩急而痛”“膝下筋急”等症。肺金反侮心火,心火受邪,故出现“胸膈闭塞”等症。神圣复气汤为治疗寒水来复、肺肾之气旺盛,导致脾土、心火受侮之方。该方以附子、干姜、白术健脾温肾助阳,祛除下焦虚寒。以黄柏、黄连苦寒之药泄阴火。以羌活、防风、细辛等疏散上焦风热之邪。该方与《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所言“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各安其气”理论相合[4]183。又如在朱砂安神丸中言:“热淫所胜,治以甘寒,以苦泻之。”该方以黄连苦寒之药泄热除烦,以甘草、生地泻火补气为臣。该方契合五运六气司天用药理论,当司天之气,热气淫胜之时,选用苦寒之品清热泻火[4]180。
2 在方剂配伍方面的体现
2.1 补中益气汤
探讨李杲学术思想,难以绕过补中益气汤。《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提出“下者举之”“衰者补之”[4]184,李杲据此创方,方中蕴含其应用五运六气理论“补脾胃升清阳”的思想[5]。该方由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人参、当归、炙甘草组成,药物多甘温入脾经,且多为辛甘发散之品,可助长春夏生发之气。因此本方具有升阳补虚,充盈元气,兼有行滞之效,主治气虚发热,症见身热自汗、气短乏力、脉大无力等,临床疗效显著,应用于多种发热和脾虚气陷病证中。此方治疗痰饮咳嗽时,于不同时节增添归肺经药物调整功效。在春温时节,脾阳不足无力升发,肺气不利而咳,添加佛耳草除肺寒升肺气、款冬花润肺下气;在夏季邪气损伤气阴,使得虚火内生,致咳嗽有痰时添五味子、麦冬寒凉药物养肺之阴、清除虚热;夏季无痰咳嗽时加人参、麦冬、五味子清肺火,同时预防暑热伤阴;在天气寒冷时,多为寒邪所致咳嗽,添干姜、砂仁等温热药物温中散寒。
2.2 升阳散火汤
升阳散火汤是升举阳气、发散郁火的代表方。张元素结合五运和五脏配属关系,认为:“木郁则达之,谓吐令其调达也;火郁则发之,谓汗令其发散也;土郁则夺之,谓下之令无壅滞也;金郁则泄之,解表利小便也;水郁则折之,谓抑之制其冲逆也”[6]。李杲通过对张元素所阐发五运六气理论的理解,提出“火郁发之”的思想。全方以风药为主,主治脾胃气虚,升降失常,阳气郁滞,郁而发热的中焦火郁证,表现为蒸蒸躁热、口苦舌干、身体困乏、大便不调、小便频数。该方由柴胡、升麻、防风、独活、羌活、人参、生甘草、炙甘草、葛根、白芍组成。柴胡为君药,疏肝解郁,发散少阳郁火;独活、升麻、葛根、羌活、防风为臣药,升麻、葛根发散阳明郁火,升举阳气,羌活、防风发散太阳郁火,独活发散少阴郁火。六味风药气薄升浮,疏通三焦,发散郁火。人参、炙甘草、生甘草为佐药,人参补脾胃之气,生甘草泄脾脏郁火,炙甘草健脾和中,三药相伍补脾泄热,针对脾气虚弱之证。芍药和甘草为佐使药,芍药泻火敛阴,散收并用防止损伤阴气,同时两药合用酸甘化阴,调和肝脾。全方疏泄肝火兼顾补脾益气,治疗脾胃虚弱而生郁火,对于梅核气、干眼、咳嗽等多种疾病颇有疗效。
3 在用药方面的体现
3.1 四时用药
李杲重视脾胃,与脾主四时理论密不可分。《素问·太阴阳明论篇》提及:“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4]60。李杲深以为然,认为若不本四时,便是以顺为逆,故提出“随时用药”理论。治疗中随着运气变化,根据四季时令,用方有所加减。春季增添清凉风药,夏季增添大寒药物,秋季增添温气药物,冬季增添大热药物,顺应《黄帝内经》所述“春食凉,夏食寒,秋食温,冬食热”四时用药原则,做到“四时为宜,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4]31,避免损伤脾胃。如《内外伤辨惑论》所载:“假令夏月大热之时,伤生冷硬物,当用热药木香见丸治之,须少加三黄丸,谓天时不可伐,故加寒药以顺时令;若伤热物,只用三黄丸。何谓?此三黄丸时药也。假令冬天大寒之时,伤羊肉湿面等热物,当用三黄丸治之,须加热药少许,草豆蔻丸之类是也,为引用,又为时药。经云∶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此之谓也,余皆仿此”[1]33。服药亦遵时顺自然,如《内外伤辨惑论·辨内伤饮食用药所宜所禁》提及草豆蔻丸的使用:“如冬月用,别作一药,不用黄芩,岁火不及,又伤冷物,加以温剂,是其治也。然有热物伤者,从权以寒药治之,随时之宜,不可不知也”[1]27-28。此中亦可看出李杲受张元素“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思想的影响,运用五运六气理论顺应气候变化进行脾胃论治。
四时用药理论在脾胃虚弱治疗中的应用不止于此。李杲认为,春气升浮风胜,浊气不降,少加风药,以伸阳气。若初春犹寒,少加辛热药补春气之不足,故添加白术、防风、升麻、柴胡、人参等。夏季暑气胜,加入黄连、黄柏、知母、石膏等散寒气,泻阴火之上逆。长夏湿土胜,加白术、苍术、泽泻等药物分消湿热之气,加五味子、麦冬、人参等药物益肺气、助秋损。秋季燥气胜,加陈皮、草豆蔻仁、砂仁等药物泻其燥邪。冬季寒气降,加干姜、附子、吴茱萸、肉桂等大辛大热药物,泻阴寒之气。在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选择上,认为春宜吐,夏宜汗,秋宜下,冬周密。用药契合《黄帝内经》中用温远温、用热远热、用凉远凉、用寒远寒的原则。如用寒凉药物时规避寒气主令,不单单是冬季气候,还有气候偏寒的太阳寒水司天的年份,这些均可体现李杲在脾胃疾病论治中五运六气理论的应用。
3.2 风药使用
研究李杲用药特点不难发现,其擅用风药治疗内伤和外感病证。风药最早是张元素根据五运六气学说“风为木运,肝所主时”所提出。他开创了“药类法象”理论,将药物按性能分类为“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种[7],风药主要指风升生类药物。李杲继承发扬“药类法象”理论,认为“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8],在疾病诊治中擅用风药,并称可以升发春夏之气的药物为风药。
风气无形,其性轻扬开泄,善行数变,动摇不定,无孔不入,表里内外可达。风药气薄质轻,多辛温发散,灵动变化,无处不至,具有解表透邪、祛风除湿、通达经络、升举清阳、开郁散结、宣发郁火等功效,又可入肝胆,助胆气春生。此外风气通于肝[4]10,风药禀“春生之气”,应风木之象。肝木不舒,则风滞肝郁,合理使用风药,顺应肝木曲直特性,可以疏肝开郁、条达肝木,如树木修枝,方能枝繁叶茂。该法针对肝气亢旺克制脾土,导致脾胃内伤,应《黄帝内经》“木郁者达之”之理,对于内伤脾胃病治疗效果显著。因风药走窜不定,易伤阳气,在使用风药过程中,需要注意顾护身体正气。故李杲运用风药后,严守中病即止的原则,避免过剂。李杲遣方用药可谓是别具一格,用药精准,对于临床用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4 结语
李杲对五运六气研究颇深,丰富发展了五运六气理论,其脾胃论治思想,与五运六气理论联系紧密。《内外伤辨惑论》作为补土派代表人物李杲的第一部著作,系统阐述了内伤与外感病证,提示:诊病要整体审查,把握要点;治疗要结合五运六气理论,调节胜复之气,以顺应自然,使人体阴阳平衡;借鉴学习前人方药时要辨证论治,注意五运六气的变化,不可因循守旧。其倡导的“补土”思想为后世医家诊治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现今《内外伤辨惑论》中脾胃论治思想仍在临床治疗中具有指导作用,提出的补脾胃生元气、甘温除热理论,以及所创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清暑益气汤等方药盛行至今,对多种疾病疗效显著,其所蕴含以五运六气理论指导脾胃论治的思想值得我们细细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