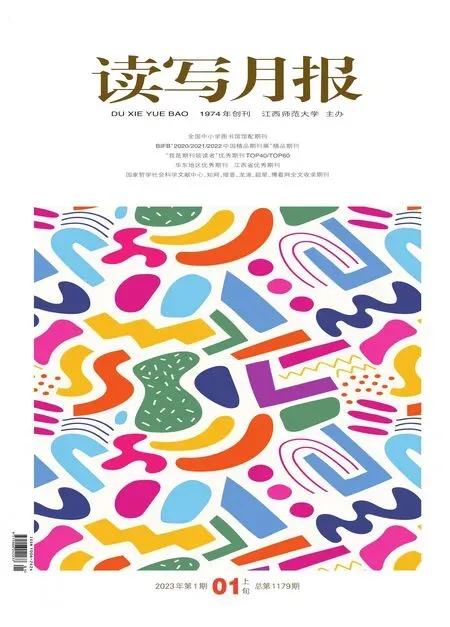矛盾溯源:本位主义影响下的三种表现
——《雷雨》(节选)新解
李传贵
本位主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阶级和国家利益的集体主义相对应。从道德的观点来说,本位主义的定义在本质上就是自私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对于社会人际的利益方面。本位主义掌控下的价值观念通常是牺牲他人(包括集体)的利益而达到“私我”的目的。而这种具备“残酷、自私、怨妒”性质的本位主义思想,从古到今一直在社会的人群中充斥着,于当时《雷雨》的故事背景有所揭示,对当下的现实反思亦可提供借鉴。①
《雷雨》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1925年正值新旧世界更迭交替的时期,封建传统道德观、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同时激烈交锋。《雷雨》作为一部成功且极具影响力的话剧,典型的矛盾冲突无疑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它既推动话剧情节的发展,深化文本所要表现的主题,并且是介于语言和人物之间搭构连接的桥梁;通过富有表现力的舞台语言得以塑造、通过人物角色的性格得以典型、通过人物形象的行为得以呈现。从矛盾溯源的角度审视《雷雨》,矛盾冲突集中在周朴园、鲁侍萍等关键人物的性格、身份和行为上,具显于性格、生活和角色三种表现。
一、性格本位:无可奈何的冲动或克制
冷酷的周朴园难掩对“侍萍”的怀念,在多次追问中呈现他内心世界独白的感性,但是在外显行为上却是极力克制。在见到“四凤妈”的时候,周朴园与其展开了内容丰富的对话,主要围绕着一个话题:打听侍萍。故事线追溯到周朴园年轻时,他既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也是青春正盛的“初恋者”,他与侍萍的人生交集始于此。周朴园作为少爷,而侍萍只是一个女佣的女儿,两个人当时产生了情感的火花,并且生下来两个孩子。两个人的情感结合能冲破阶层身份的藩篱,来自青年时代性格冲动的加持。当周朴园抛弃侍萍和孩子的时候,是一个贵公子为了迎娶有钱人家的小姐。显然,当时的周朴园是有资本家“理性”的,也包含着在家族责任和父母之命的要求下抛弃侍萍的无奈。对比周朴园这两次情感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在选择和佣人的女儿在一起时是基于性格的“感性冲动”,当他选择抛弃旧爱和觅新欢——有钱人家的小姐时是“理性克制”的。但是,无论他人生选择的呈现是感性还是理性,都是基于主体性格做出的判断,总的前提是“我愿意”。这一点在文章节选的对话中也得以体现,当“四凤妈”进一步地透露暗示有关侍萍的事情,周朴园总是以“低吟”“苦痛”“汗涔涔”“惊愕”状,表达自己对侍萍的悔恨;但是当他知道眼前人就是侍萍时,却以一种严厉的态度并且试图用金钱收买来掩饰当年的事实,这表达出周朴园作为“自然人”性格上的自私无情,表达出周朴园作为“资本家”性格上的谨慎与冷漠。②
懦弱的鲁侍萍再次与周朴园见面于“周家”,终究是源自一种作为“了却旧愿之情人”和“念子心切之母亲”的本性冲动,但是仍然选择克制自己以假借四凤之母的身份。侍萍的性格是懦弱的,所以她选择妥协,并不想在这次重逢的契机中索取什么,只是试探性地表达了自己想见儿子的愿望。侍萍的懦弱导致她在被周朴园抛弃时只能选择“忽然地投水而死”,而不敢为自己做主;她被救起后在外乡活着必须再嫁一个人,嫁给一个下等人;在她必须养活儿子女儿的时候甘愿“过得很苦”,也不能再来周家。因此,懦弱的母亲和贫穷的家庭养育了一个懦弱的女儿,荒诞地来到周家做了佣人;懦弱的母亲和贫穷的家庭产出了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鲁大海”,荒诞地来到周家做了工人。侍萍与她的孩子们两代人都与周家莫名地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的方式是“仆人”而非“主人”,导致这般结果的原因与侍萍性格上的懦弱解离不开。四凤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她和周家少爷纯真的爱情幸福在那个雨夜被摔得粉碎,她在母亲的懦弱面前跪下发着毒誓绝交于周家。③鲁大海在被周家的仆人和周萍重重地击打,打得头破血流时,因为侍萍的懦弱,她没有说出事实,没有有效阻拦而保护被打的儿子。正是周朴园和侍萍这一辈人在性格上表现出的“自私”,没有考虑过亲生儿子鲁大海做工人的痛苦,也没有考虑过周萍幼而无母的痛苦,为这部话剧的后续埋下了矛盾冲突的种子。
二、生活本位:同一场域重逢的折磨
如果说在性格本位中,矛盾冲突的起因是拘于“人与自我”,那么在生活本位中,矛盾起因的呈现是假借一种“人与环境”的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人际交互。
生活富足的周朴园仍然存留着“旧雨衣”“旧衬衣”。周朴园与侍萍的矛盾冲突不仅表现在青年时期两人相爱上,也不仅表现在中年两人重逢之时,而是在文本中更多地表现为前后间隔时间里持续不断的怀念和悔恨。因此,在“周家”这同一个场域中,周朴园和侍萍的矛盾冲突更多地依托时间线的变化而展开,具体指喻在“关窗户”和“旧雨衣”“旧衬衣”这些行为和物品中。相对于富足的生活状况,“旧雨衣”和“旧衬衣”的存在显得格外惹人注目,也正是这些物品的存在和保留,展现了周朴园作为封建大家长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忏悔。周朴园虽总是睹物思人,借此缓和自己内心对侍萍的愧疚,但是他在实际行动中并未寻找过侍萍或是她的坟墓。在与周朴园内心戏的鲜明比照下,一个自私冷酷的伪君子形象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脑海中。
儿女双全的鲁侍萍仍然牵挂着“周萍”。从侍萍的角度来看,她对“周萍”的牵挂是她与周家未了结情缘的符号。从文本中周朴园和侍萍的对话可以看出,侍萍对周家似乎还存留一丝幻想,或者说是对周朴园当年的抛弃还渴求一个合理的解释。侍萍在未与周萍相认的时期,她已经是四凤和鲁大海的母亲,也有自己虽然贫苦却较完整的家庭,但是这次她仍然选择回到了周家,和周朴园进行了如此坦白的对话。可见,她作为一个母亲,有着牵挂自己每一个孩子的原始欲望,她当时甚至根本不曾考虑周萍是否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在周萍怒打鲁大海时,侍萍作为两个人的母亲,心里有着两次重叠的痛,与此同时却也有着明显的感情倾向,她舍不得伤害甚至是批评周萍这个近乎三十年没有见过面的儿子。
在周家,期盼相见却“不允再来”。“周家”是一个固定的场域,但是它在不同时间阶段内对周朴园、侍萍、周萍等人而言具备不同情感内涵的寄托。④在周朴园和侍萍这一辈人分道扬镳之前,周家无疑是他们欢乐的伊甸园;而在节选文本描绘的时间刻度处,周家对于周朴园来说仅是一个居所,对于侍萍而言更是一个伤心之地。基于生活本位,周朴园有着对寄托了怀念初恋侍萍之旧物的自私,内心期盼能够重回当年抛弃侍萍之前,修改自己的选择,甚至是在现在再见侍萍一面。侍萍有着与儿子周萍相见的愿望,渴望重回周家了结旧日的尘缘,但这都仅仅是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白。当侍萍故地重逢,周朴园再见侍萍,此时此刻的周朴园小心谨慎、冷酷紧张,侍萍懦弱慌张、忧心忡忡,鲁大海和周萍剑拔弩张,“周家”俨然成了一个“战场”。当彼此失意灰心之后,周朴园说:我让你看看他(周萍),以后鲁家的人不许再到周家来。侍萍说:好,我希望这一生不至于再见你。重逢,本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此时此刻却化为折磨。
三、角色本位:阶层不同的角色异化
当自然人被赋予某种社会角色,他应当肯定或者接受更多的现实牵绊,这也是戏剧中矛盾冲突起因在个人本位主义观念下“个人与社会”层面的表现。
仆人鲁侍萍和贵公子周萍之间,有母子亲情却难以相认。如果侍萍不是佣人女儿的角色,那她会不会不被抛弃?如果周萍当年被侍萍带走,那母子关系会不会更和谐?在角色本位之下,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思维,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愿景。⑤鲁侍萍是佣人的女儿,她对资本家雇主的奢靡生活是有憧憬的,甚至是极其希望拥有的。因此,她离开周家的那一年内心或有不舍,或有失落,这种生活的落差间接促成了她投水自杀。身体健康的小周萍作为侍萍的大儿子,在侍萍离开周家时留在了周家,其中原因不仅包括周家老夫人对子孙的重视,也有侍萍期盼儿子能够过上富足、奢靡生活的私欲。也正是侍萍这种心理促成的现实,导致了她与自己的儿子难以再相见。周萍俨然已经融入周家少爷这个角色之中,他是否会认可这个佣人之女作为亲生母亲?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在文本中有依据:(侍萍说)“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儿子?”在侍萍和周萍母子见面的真实情境中,一位涉世经验丰富的老母亲已然观察到身份差异导致的这份微妙变化。
工人鲁大海和雇主周朴园之间,有父子血脉却反成仇。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雇主和工人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但是它不应当是局限于“周家”这个场域的归属。鲁大海和周朴园不仅是雇主与工人的关系,他们也是父子,这个事实对周朴园来说是已知的。鲁大海并不知道周朴园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他的角色仅仅是工人,或是反抗剥削压迫的工人代表,因此他完全凭借“工人”这一社会角色赋予他的责任与周朴园进行斗争。而周朴园在得知鲁大海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之前,同样展现了作为资本家压迫工人的本色:鲁大海的断指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周朴园得知鲁大海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后,他便有了双重的角色身份:其一,当鲁大海代表工人抗议时,周朴园让仆人把他无情地拖走;其二,当周萍和仆人击打鲁大海时,周朴园厉声地说“不要打人!”发话及时,语气坚定,可以窥探到一丝源于父爱的怜悯。
工人鲁大海和贵公子周萍之间,兄弟关系却拳脚相向。本是同父同母的两个人,因为不同的社会身份,处于各异的生存环境,生成了不同的性格特征,享有或富足或贫穷的截然不同的生活。冲突产生的土壤如此肥沃,滋生了两个人作为资本家少爷与工人、周朴园名义上的儿子和隐匿的儿子、侍萍二十年未见的儿子和亲手养活的儿子多重角度间的矛盾。在文本中,周萍和鲁大海在“父母”的见证下处于同一场域,两个人的矛盾冲突一触即发:(周萍说)“你这种混账东西,打他!”(鲁大海说)“放开我,你们这一群强盗!”很明显,周萍在维护父亲周朴园的权威,鲁大海在争取工人群体的尊严,已知的身份角色给“自然人”赋予了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责任,因此产生了不同的行为,这正是《雷雨》中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在角色本位层面最典范的体现。
四、结语
《雷雨》作为戏剧体裁的经典之作,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专注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因此这个大家庭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故事串起了整个戏剧的情节,不论是家庭秘密还是身世秘密,无数的家庭矛盾纠葛映射了当时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也深刻地表现了腐朽的人情世故、资本主义社会大环境下个人本位主义的盛行及其危害。
——周朴园对侍萍的情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