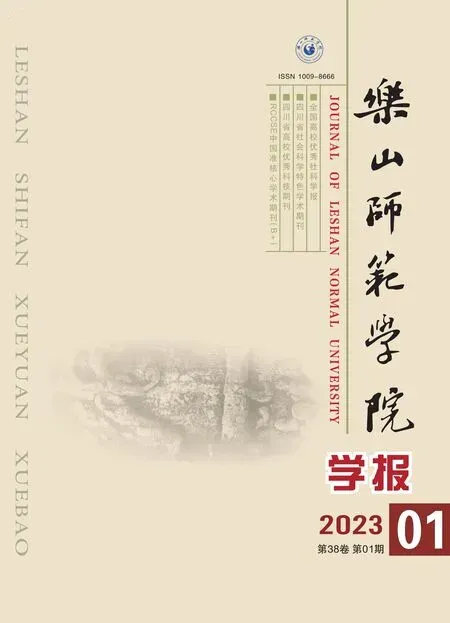苏轼与文同研究二题
张小花,庆振轩
(1.兰州交通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苏轼与文同的交往是宋代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二人不仅有姻亲之谊,而且互相引为诗词、绘画艺术上的知音。二人相互唱和、交游的诗词及书信较多。苏轼与文同交往的作品已有学者罗琴先生加以统计,本文在前人学者开拓之功的基础上,进行查缺补漏,得出85首(篇)的最新数字,并经过详细考察,确定几篇难以系年的作品的具体写作时间。同时,对苏轼与文同“从表兄弟”的关系进行考证,厘清概念。以期对苏轼与文同研究的深入和细化提供借鉴。
一、苏轼有关文同诗文创作篇目考订
检索文献,苏轼父子与文同颇多诗文、书信交往,罗琴《文同与二苏的交游及交往诗文系年考》一文对此详加考述并加以系年,其开拓之功自不待言。但罗女士个别诗文的系年及统计篇目还可讨论。
文同有关苏轼的诗文今存19首(篇),苏洵有关文同的诗1首,苏轼有关文同的诗文79首(篇),苏辙有关文同的诗文55首(篇)。[1]
有罗琴先生大作在先,后之研讨文同、苏轼交游诗文者多祖其说,如:库万晓《文同和苏轼关系研究》一文即沿述其论;喻世华先生有多篇研究苏轼大作发布,亦在文章中写道:“根据罗琴女士的考证——苏轼有关文同的诗文79首(篇)。”[2]但详加检索,据罗琴一文统计苏轼与文同有关诗文篇目或有失误。
首先,罗文某些字面易令人重复计算。比如文中《小简》出现3次:“熙宁十年,丁巳1077年,文同60岁”[1],引苏轼《小简》2篇。其一为文同与苏辙议儿女婚事,苏轼作《小简》:“今日沿汴赴任,与弟同行。闻与可与之议姻,极为喜幸。”[1]其二为“文同寄赠六言小集,苏轼有书答谢。苏轼《小简》:‘寄惠六言小集,古人之作,今世未有见。’”[1]“元丰元年,戊午1078年,文同61岁”,再引苏轼《小简》一篇:“见乞浙郡,不知得否?——若得与兄联棹南行,一段异事也。”[1]此三篇《小简》分别见于苏轼《与文与可书十一首》之三、之五、之九。
苏轼与文同书信往来,《苏轼文集·佚文汇编》卷二收《与文与可十一首》,其中六首皆作于元丰元年。又收《与文与可三首》,亦作于本年。而对苏轼的这三篇《小简》没有明确其已收于《与文与可十一首》,极易引起重复计算。
其次,罗文在文末认为苏轼与文与可交游诗文“尚有以下诸作写作时间地点不明,未能系年,即苏轼的《文与可琴铭》《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戒坛院文与可墨竹赞》《文与可枯木赞》《跋文与可论草书后》《跋文与可纡竹》《与可拾诗》”[1],共计七篇。但其“熙宁四年,辛亥1071年,文同54岁”[1]即有以下一段文字:
苏轼过颍州(安徽阜阳),拜谒欧阳修,盛赞文同诗才。《仇池笔记》卷下,“余昔时对欧阳公颂文与可诗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世间元有此句,与可拾得耳!’”[1]
查苏轼《仇池笔记》卷下有《与可拾诗》,文字与罗文所引完全相同,则《与可拾诗》可以确定为苏轼熙宁四年(1071)之作。文字表述可明确为“《仇池笔记》卷下《与可拾诗》条”,且不可重复计算。而《文与可琴铭》,罗琴女士明确其为“元丰四年,辛酉1081年”[1]苏轼所作,文曰:“苏轼作《文与可琴铭》,写明‘元丰四年六月二十三日’。”[1]如此,则《与可拾诗》与《文与可琴铭》不可列入难以系年之作。如此之类,易引起篇目计算的差误。
最后,涉及苏轼与文同交游的诗文尚有未系年,及未被列入难以系年篇目者数篇。罗文“元丰元年,戊午1078年”[1]下引苏轼《与李公择书》云:“迈往南京,为舍弟此月十一日嫁一女与文与可子,呼去干事。”[1]此书见于苏轼《与李公择书十七首》之五,注云“元丰元年秋冬作于徐州”[3]5606,但文与可亡后,苏轼作于元丰二年或三年的《与李公择书》,却未被收录。其文云:“与可之亡,不惟痛其令德不寿,又哀其极贫,后事索然。而子由婿其少子,颇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贤而文,久远却不复忧,惟目下不可不助他耳。”[3]5626此信见于苏轼《与李公择书十七首》之第十五。苏轼与友人书信往来颇多,其《与朱康叔二十首》第一书亦涉及文同身后事:“与可船旦夕到此,为之泫然。想公亦尔也。”[3]6471该书“元丰三年四月作于黄州”[3]6472。
元祐元年,文同之子文务光病逝之后,苏轼寄书劝慰文同夫人,书云:“事已无可奈何,千万宽中强解勉也。舍弟妇自闻逸民之丧,忧恼殊甚,恐久成疾。”(《与亲家母一首》)[3]8635-8636
苏轼《文骥字说》,作于元祐三年(1088)。文骥为文务光之子,文同之孙,苏辙外孙。文务光死后,苏辙接女儿与外孙来家,并亲自教育。苏轼为其取名并写《字说》,这在苏轼的文集中并不多见,足见他对文骥的疼爱与厚望。此文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作于元祐三年九月十八日;后一部分作于是年十月。文曰:
马之于德,力尽于蹄啮,智尽于窃衔诡辔。以蹄啮之力为千里,以窃诡之智为道迷,此之为骥。文与可学士之孙,逸民秀才之子,苏子由侍郎之外孙,小名骥孙,因名之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字之曰元德。元祐三年外伯翁东坡居士书。
东坡居士言:骥孙才五岁,入吾家,见先府君画像,曰:“我尝见于大慈寺中和院。”试呼出相之,骨法已奇,神气沉稳。此儿一日千里,吾辈犹及见之。他日学问,知骥之在德不在力,尚不辜东坡之言。元祐三年十月癸酉门下后省书。[3]1046
关于古人命名取字的渊源,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云:“按《仪礼》,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辞,后人因之遂有字说、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辞之滥觞也。虽其文去古甚远,而丁宁训诫之义无大异焉。”[4]苏轼为文同之孙命名文骥,字元德,以“千里马”譬喻侄孙,期望他日后学问道德一日千里。
苏轼与文同的神交终东坡一生。元符三年(1100)二月苏轼所作《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三首之一曰:“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山僧自觉菩提长,心境都将付卧轮。”[3]5065诗作感怀文与可之墨竹传神写照,对幼子苏过得其真传感到欣慰。此外,苏轼写作时间未详的《书张少公判状》亦少有论者言及,其文曰:
张旭为常熟尉,有父老讼事,为判其状,欣然持去。不数日,复有所讼,亦为判之。他日复来,张甚怒,以为好讼。叩头曰:非敢讼也,诚见少公笔势殊妙,欲家藏之尔。张惊问其详,则其父天下工书者也。张由此尽得笔法之妙。古人得笔法有所自,张以剑器,容有是理。雷太简乃云闻江声而笔法进,文与可亦言见蛇斗而草书长,此殆谬也。[3]7796
除上述篇目外,还有明代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录载,《苏轼资料汇编》收录,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十一引述,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引用并名为《书竹石后》一文,移录如下:
昔岁,余尝偕方竹逸寻净观长老,至其东斋小阁中,壁有与可所画竹石,其根茎脉缕,牙角节叶,无不臻理,非世之工人所能者。与可论画竹木,於形既不可失,而理更当知;生死新老,烟云风雨,必曲尽真态,合於天造,厌于人意;而形理两全,然后可言晓画。故非达才明理,不能辩论也。今竹逸求余画竹,因妄袭与可法则为之,并书旧事为赠。元丰五年八月四日,眉山苏轼。[3]8886
可见,苏轼与文同交游的诗文,在罗琴统计的基础上,去除复重,添加缺失,有关诗文应为85首(篇)。这是研究苏轼与文同交游的基础。
二、苏轼与文同是否表兄弟关系考证
在部分介绍文同或研究苏轼与文同关系的文章中,往往误以为二人乃表兄弟的关系,如徐丽《苏轼与文同》一文即认为:
苏轼与文同的交往就很独特,苏轼与文同是远亲,苏轼称文同为从表兄—不仅如此,文同的儿子还与苏辙的女儿结为姻亲,苏文两家亲上加亲,这种深厚的亲情和友情,使得苏轼在文同去世后十四年还有祭文同的文字出现,十分难得。[5]
有些文章在题目中径称《苏轼有个表哥叫文同》[6]、《苏轼表哥文同:诗词书画“四绝”》[7]。但揆诸实际,苏轼从未称文同为“从表兄”,苏轼与文同并非表兄弟关系。查阅有关史料,苏轼在与文同书信往来、诗文唱酬以及追念缅怀中,或称“余友文与可”“友人文与可”“吾友文君名同”;或称“与可老兄”“老兄”;文同之子与苏辙之女联姻,苏轼称文同“亲家翁”;文同去世,苏轼称其为“亡友”;有时苏轼谦称“劣弟”;在《祭文与可文》《再祭文与可文》中均自称“从表弟”。这一切都意在“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者也”。[3]1155但正如此,人们误以为苏轼、文同乃表兄弟。而此误传较早见于叶梦得,其说曰:
文同,字与可,蜀人,与苏子瞻为中表兄弟,相厚。为人靖深,超然不婴世事。善画墨竹,作诗赋亦过人。熙宁初,时论既不一,士大夫好恶纷然。同在馆阁,未尝有所向背。时子瞻数上书论天下事,退而与宾客言,亦多以时事为讥笑,同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听也。出为杭州通判,同送行诗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句,及黄州之谪,正坐杭州诗语,人以为知言。[8]
《宋史·文同传》沿用此次种说法,也说“轼,同之从表弟也”[9]。故而之后以讹传讹,历代许多文人学者均认为他们是亲戚关系。关于苏轼文同非表兄弟的问题,孔凡礼《苏轼年谱》、罗琴《文同与二苏交往及交游诗文系年》等文均有明晰的文字论述,兹摘录于下:
(苏轼和文同洋州园池三十首)《金石录续编》卷十六著录,题作《寄题与可学士洋州园池三十首》,下署“从表弟苏轼上”,此前云“熙宁九年三月四日东武西斋”—详考史实,苏、文实非中表,“从表弟”云云不过极言其亲近,非同一般。《佚文汇编》卷二《与张安道》第一简末云“从表侄苏轼顿首”。苏轼与张方平(安道)亦无亲戚关系,称“从表侄”,亦极言其亲近。[10]
罗琴女士亦就苏轼《文与可字说》刻石署名“从表弟苏轼”一事,从苏文两家的家世渊源加以考述:
苏轼作《文与可字说》。南宋乾道中汪应辰主持刻石于成都府治之《西楼书帖》有落款云:“熙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从表弟苏轼上。”文同为西汉蜀郡太守文翁之后,其后一支定居永泰。文同“曾祖彦明,祖廷蕴,考昌翰,皆儒服不仕”,“考公以公赠尚书都官郎中,妣李氏,仁寿县太君”。“文同娶卫氏,追封旌德县君。再娶李氏,封永和县君。”(范百禄《文公墓志铭》)三苏为武则天朝宰相苏味道之后,世居眉州,家世渐衰。苏洵妻程氏,苏轼前妻王弗,继室王闰之,苏辙妻史氏,苏、文两家皆不显,无官场之往来,分居永泰与眉州,无联姻之关系。因此,文同与二苏实无中表关系。苏轼自称为文同之“从表弟”,乃是表示一种亲密、亲切之意。[1]
之后研究者也认同孔、罗的论断,如彭敏《苏轼与文同的交谊》[11]、叶翔羚《苏轼的交游与文学》均引述了罗琴女士的上述结论;叶翔羚一文还根据“苏轼苏辙兄弟皆为亲族观念很重之人,若诗文作品中出现亲戚关系,一般会加以说明,在人名前冠以亲戚关系,然而在于文同的诗文往来过程中均无此现象”[12]作为旁证,再次肯定苏轼与文同绝非从表兄弟关系。
总之,因苏轼自称“从表弟”而撰文言苏轼、文同乃中表兄弟是望文生义。由此,苏轼有关文同的诗文中何以会蕴含特别深厚的情感,是我们要致力于探寻的所在。
三、结语
苏轼治平元年(1064)与文同初识,元丰二年(1079)文同去世,期间二人聚少离多,更多是通过诗词书画互通情谊,探讨书画创作心得,共同开创了湖州画派。苏轼钦佩文同的人品才华,视为书画艺术方面唯一的知音,同样也把自己视为文同艺术上的知己,文同默认这一事实。因此,文同的逝世,使苏轼失去了一位挚友,失去了艺术上的知音。正如他在《祭文与可学士文》中所写:“孰能惇德秉义如与可之和而正乎?孰能养民厚俗如与可之宽而明乎?孰能为诗与楚词如与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齐宠辱、忘得丧如与可之安而轻乎?”[3]6985因此苏轼才会在文同去世后的十几年间对故友念念不忘,不仅仅是对二人友谊的怀念和眷恋,也隐含着对知音难觅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