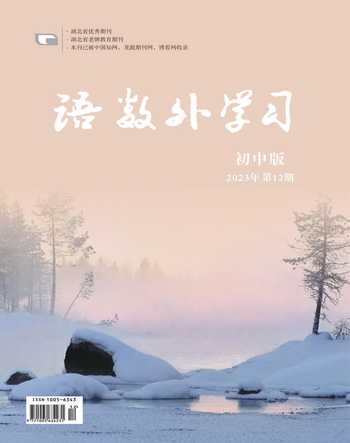雪浪花
杨朔

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过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激着海边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像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
几个年轻的姑娘赤着脚,提着裙,嘻嘻哈哈追着浪花玩。想必是初次认识海,一只海鸥,两片贝壳,她们也感到新奇有趣。奇形怪状的礁石自然逃不出她们好奇的眼睛,你听她们议论起来了:礁石硬得跟铁差不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是天生的,还是錾子凿的,还是怎的?
“是叫浪花咬的。”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插进来。说话的人是个上年纪的渔民,从刚靠岸的渔船跨下来,脱下黄油布衣裤,从从容容晾到礁石上。
有个姑娘听了笑起来:“浪花又没有牙,还会咬?怎么溅到我身上,痛都不痛?咬我一口多有趣。”
老渔民慢条斯理地说:“咬你一口就该哭了。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姑娘们,你们信不信?”
说得妙,里面又含着多么深的人情世故。我不禁对那老渔民望了几眼。老渔民长得高大结实,留着一把花白胡子。瞧他那眉目神气,就像秋天的高空一样,又清朗,又深沉。老渔民说完话,不等姑娘们搭言,早回到船上,大声说笑着,动手收拾着满船烂银似的新鲜鱼儿。
我向就近一个渔民打听老人是谁,那渔民笑着说:“你问他呀,那是我们的老泰山老人家,就有这个脾性,一辈子没养女儿,偏爱拿人当女婿看待。不信你叫他一声老泰山,他不但不生气,反倒摸着胡子乐呢。不过我们叫他老泰山,还有别的缘故。人家从小走南闯北,经得多,见得广,生产队里的大事小事,都得找他指点,日久天长,老人家就变成大伙依靠的泰山了。”
此后一连几日,变了天,飘飘洒洒落着凉雨,不能出门。这一天晴了,后半晌,我披着一片火红的霞光,从海边散步回来,瞟见休养所院里的苹果树前停着辆独轮小车,小车旁边的一个人俯在磨刀石上磨剪刀。那背影有点儿眼熟。走到跟前一看,可不正是老泰山!
我招呼说:“老人家,没出海打渔么?”
老泰山望了望我笑着說:“哎,同志,天不好,队里不让咱出海,叫咱歇着。”
我说:“像您这样年纪,多歇歇也是应该的。”
老泰山听了说:“人家都不歇,为什么我就应该多歇着?我一不瘫,二不瞎,叫我坐着吃闲饭,等于骂我。好吧,不让咱出海,咱服从;留在家里,这双手可得服从我。我就织渔网,磨鱼钩,照顾照顾生产队里的果木树,再不就 推着小车出来走走,帮人磨磨刀,钻钻磨眼儿, 反正能做多少活就做多少活,总得尽我的一份 力气。”
“看样子您有六十了吧?”
“哈哈!六十?这辈子别再想那个好时候 了——这个年纪啦。”说着老泰山捏起右手的 三根指头。
我不禁惊疑说:“您有七十了么?看不 出。身板骨还是挺硬朗。”
老泰山说:“哎,硬朗什么?头四年,秋收 扬场,我一连气还能扬它一两千斤谷子。如今 不行了,胳膊害过风湿痛病,抬不起来,磨刀磨 剪子,胳膊往下使力气,这类活儿还能做。不 是胳膊拖累我,前年咱准要求到北京去油漆人 民大会堂。”
“您会的手艺可真不少呢。”
“苦人哪,自小东奔西跑的,什么不得干? 干的营生多,经历的也古怪,不瞒同志说,三十年前,我还赶过脚呢。”
他正要讲述精彩过往的时候,休养所的窗 口有个妇女探出脸问:“剪子磨好没有?”
老泰山应声说:“好了。”就用大拇指试试 剪子刃,大声对我笑着说:“瞧,我磨的剪子,多 快。你想剪天上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 剪得动。”
西天上正铺着一片金光灿烂的晚霞,把老 泰山的脸映得红彤彤的。老人收起磨刀石,放 到独轮车上,跟我道了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 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 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 去。他走了,他在海边对几个姑娘讲的话却回 到我的心上。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 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 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 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笑笑说: “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