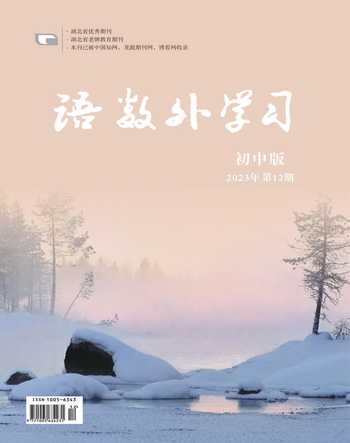黄河一掬
余光中
临别济南的前一天上午,我们来看黄河。厢型车终于在大坝上停定,大家陆续跳下车来。还未及看清河水的流势,脸上忽感微微刺麻,风沙早已刷过来了。没遮没拦的长风挟着细沙,像一阵小规模的沙尘暴,在华北大平原上卷地刮来,不冷,但是挺欺负人,使胸臆发紧。女儿把自己裹得密密实实,火红的风衣牵动了荒旷的河景。我也戴着扁呢帽,把绒袄的拉链直拉到喉核。一行八九个人,向大坝下面的河岸走去。
天高地迥,河景完全敞开,触目空廓而寂寥,几乎什么也没有。河面不算很阔,最多五百米吧,可是两岸的沙地都很宽坦,平面就延伸得倍加旷远,漠漠的天穹,下面是无边无际、无可奈何的低调土黄,河水是土黄里带一点赭,调得不很匀称。沙地是稻草黄带一点灰,泥多则暗,沙多则浅。上面是浅黄或发白的枯草。我对友人说:“这里离河水还是太远,再走近些好吗?我想摸一下河水。”
于是我们沿着一大片麦苗田,在泥泞的窄埂上,一脚高一脚低,向最低的近水处走去。终于够低了,也够近了。但沙泥也更湿软,我虚踩在浮土和枯草上,就探身要去摸水,大家在背后叫小心。岌岌加上翼翼,我的手终于半伸进黄河。
一刹那,我的热血触到了黄河的体温,凉凉的,令人兴奋。古老的黄河,从史前的洪荒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四千六百里,绕河套、撞龙门、过英雄进进出出的潼关一路朝山东奔来,从斛律金的牧歌、李白的乐府里日夜流来,你饮过多少英雄的血,难民的泪,改过多少次道啊!发过多少次泛涝,二十四史,哪一页没有你浊浪的回声?流到我手边,你已经奔波了几亿年了,那么长的生命我不过觸到你一息的脉搏。无论我握得有多紧,你都会从我的拳里挣脱。就算如此吧,这一瞬我已经等了七十几年了,绝对值得。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又如何?又如何呢?至少我指隙曾流过黄河。
至少我已经拜过了黄河,黄河也终于亲认过我。在诗里文里我高呼低唤他不知多少遍: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也听见
沙,也听见
华夏子孙对黄河的感情,正如胎记一般地不可磨灭。诗人流沙河写信告诉我,他坐火车过黄河读我的《黄河》一诗,十分感动,奇怪我没见过黄河怎么写得出来。其实这是胎里带来的,从《诗经》到龚自珍,哪一句不是黄河奶出来的?
……
想到这里,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对着滚滚东去的黄河低头默祷了一阵,右手一扬,雪白的名片一番飘舞,就被起伏的浪头接去了。大家齐望着我,似乎不觉得这僭妄的一投有何不妥,反而纵容地赞呼。女儿也相继来水边探求黄河的浸礼。看到女儿认真地伸手入河,想起她那么大了,做爸爸的才有机会带她来认河,想当年做爸爸的告别这一片后土只有她今日一半的年纪,我的眼睛就湿了。
回到车上,大家忙着拭去鞋底的湿泥。我默默,只觉得不忍。翌晨,友人去机场送别,我就穿着泥鞋登机。回到高雄,我才把干土刮尽,珍藏在一只名片盒里。从此每到深夜,书房里就传出隐隐的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