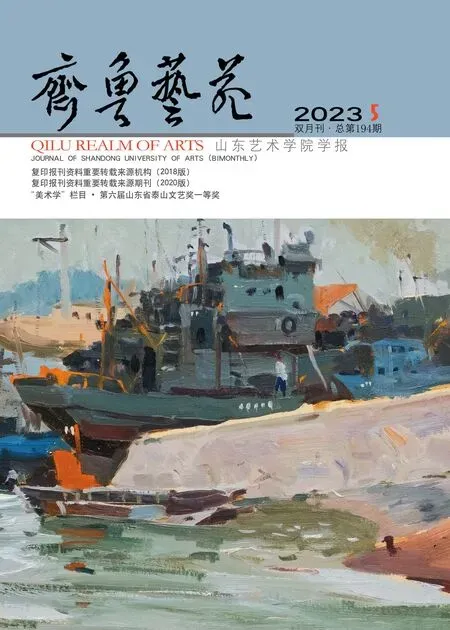文化自信视域下戏曲校园美育的价值与时代意义
付桂生
(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北京 100084)
中华戏曲是一个自成系统且有着独特气质的艺术体系,积聚了传承于古代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理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是今天的我们了解和领悟中国文化传统与精神命脉,在当下开展美育工作的重要载体。 在“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繁荣”的背景下,秉承“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立德树人”理念的艺术教育工作者,也应积极探索民族戏曲美育范式建立的可能与路径,拓展戏曲美育的形式与内涵,营造良好的戏曲美育生态。 戏曲走进校园,对培养学生民族审美意识自觉,促使其树立正确价值观念,提升内在精神品格,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近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戏曲文化建设和美育工作做出重要思想论述,国家政策大力扶持戏曲和美育的发展,陆续出台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政策,为戏曲美育建设提供了优渥的文化环境。 戏曲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将中华美育精神与核心价值观高度融合的“戏曲进校园”活动,带来了民族艺术之美,可以让学生近距离了解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中国人自己的道德观念、情感态度及价值标准,也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力,陶冶其心性,培植其情操,使之为最终“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发挥重要作用。
艺术是按照“美”的规律反映世界,其所呈现出的认知世界,是对生活的审美判断,“真正的情致饱含意蕴的价值和理性, 而且容易把它认出来”[1](P298)。 人们正是通过直觉感知,在“美的享受”中,接受了凝结在艺术作品形象中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品质修养。 东西方都有着各自的美育观念与传统,中国古典文化中“礼乐教化”的思想,就已经具备了劝人向善的审美意识。 《礼记·乐记》中言:“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 唯君子为能知乐。”[2](P177)近代美育观念首倡者德国美学家席勒1795 年在《美育书简》中指出:“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3](P116)现代美育理论于20 世纪初期传入中国,美育早期倡导者蔡元培曾说:“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4](P217)美育向来是东西方关注的重要问题,不同国家与地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体系。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艺术教育作为审美教育不可替代和缺失的重要途径,所发挥的功能日益受到重视。
一、戏曲审美形态与学生民族审美意识培育
戏曲在中华文化母体中孕育生成,将传统的诗歌、音乐、舞蹈、美术、说唱、杂技等多种艺术成分,融会为新的戏剧形态,集聚着中国古代文化精神,集中展现了民族艺术之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质。融万趣统一于“载歌载舞”的舞台呈现,将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语言和情感,巧妙地转化为虚拟性和程式化的戏曲语汇、舞蹈化的动作、音乐化的声音、美术化的妆服,歌舞并重而传神写意间,构成了中国戏曲独有的情感表意范式。 可以说,戏曲既是特色鲜明的民族情感表意象征符号体系,也与民族文化生活紧密关联,是彰显民族审美精神的智慧结晶。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戏曲属于晚成的艺术形态,宋元时期才确立了成熟的形态程式。 不过,华夏先民的戏剧意识,却可以溯源到上古时期,《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记载了上古之“乐”的情况:“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5](P20)上述记录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出“诗”“乐”“舞”中这种雏形的戏剧因子,一直于民族艺术土壤里孕育绵延,逐渐脱胎乐舞、散乐的束缚,向杂陈的汉代百戏、歌舞戏、角抵戏、参军戏等复杂的戏剧形态演进,从说唱体的叙述体向代言体的戏剧转化。 “中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籍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 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们始有纯粹之戏曲;然其与百戏及滑稽戏之关系,亦非全绝。”[6](P84)成熟的戏曲艺术即“真戏剧”,其歌舞及故事层面经由渐变发展,终在宋元杂剧时期,完成了成熟的蜕变,就此拉开了杂剧和南戏的大幕,并在朝代更迭的审美变迁中,赓续发展出明清传奇和地方戏,构成了中国戏曲历史的三个重要时代。
戏曲历史的演进和发展,是一个淘洗杂质、去芜存真的净化过程,历经不同社会形态的淬炼,留存至今的诸多剧种无疑是其遗珠。 它们分布在我们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环境中,而各具特色和风格,共同构成了中华戏曲文化的宝库。 在这其中,观众所能领略的是聚集了民族艺术形态的方方面面,突出表现在戏曲文学、音乐、表演三个层面。
戏曲的文学形态是诗词,它在整个戏曲艺术元素中,居于主导与统帅地位。 戏曲作为以舞台演出为目的的“剧曲”,可以说是诗词文化与叙事文学结合的产物。 “曲”作为音乐和文学的结合体,其撰文写作,以填词为主,“填词之设,专问登场”,展现出了诗词的格律韵味之美。 宋元杂剧、明清传奇阶段,戏曲成为文人抒怀言志、敦风教化的重要手段,促成了杂剧、传奇创作的高峰时期。 关汉卿、王实甫、高则诚、汤显祖、沈璟、李玉、李渔、孔尚任、洪昇等一批高质量剧作家的涌现,《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琵琶记》《清忠谱》等名剧的出世,促成了古典戏剧的璀璨时代,这些悦人耳目、触动人心的故事,词采高绝的为文之美,配合曲牌连套体音乐的烘托,以及载歌载舞的虚拟性和程式化的舞台呈现,极尽展现出了古典戏曲的审美旨趣。 清代传奇发展呈现式微态势,“花雅之争”的争锋与变革之后,发端于民间的众多戏曲剧种进入繁荣阶段,以京剧为代表开始走向戏曲舞台的中心,这种以表演为核心的戏曲新形态,促使其产生了由“文雅”向“通俗”的变迁,名角为主的流派欣赏风格,自由的板腔体戏曲样式等新的创作方式,也极大释放了民族戏曲的艺术活力,亦在历史进程中构成了当今戏曲形态的雏形。
戏曲始终是具有生命力和传承性的艺术,处于不断变革和更新的运动之中,它善于吐旧纳新,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进而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体系,成为了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化景观。 19世纪末20 世纪初期,国门敞开“西风东渐”,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戏曲从思想观念、舞台表意、艺术形象、剧场环境等多方面着手,逐渐走向了革新的道路。 以梅兰芳、程砚秋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家,以广阔的艺术视野和开放的革新精神,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自觉更新着传统戏曲艺术,使其与时俱进,并致力于京剧的国际化传播,孕育了民族文化自信的萌芽。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戏曲在国家力量的主导改革下,对传统戏曲进行“去其糟粕”与“推陈出新”的变革,传统戏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创作的蔚然成风,使整个戏曲领域呈现出新的格局和面貌。 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三种形态,普遍贯穿到不同剧种之中,风格不同、形态鲜明的戏曲剧种,共同构成了当代戏曲艺术的多样性,与时俱进为观众提供了多元的审美需求。 戏曲舞台上颇受观众喜爱的一大批剧目,诸如京剧《穆桂英挂帅》《白蛇传》、昆曲《十五贯》、豫剧《花木兰》《朝阳沟》、评剧《花为媒》、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等剧目,时至今日仍然是代表本剧种艺术水准且受观众喜爱的戏曲作品。回顾百年戏曲演进的审美风格,总体取向由“古”向“今”,艺术形态由“曲”向“剧”,古老戏曲将现代审美观念和舞台表意技法,融入到自身体系构建中,不断赋予戏曲艺术以新的活力。
戏曲作为中华艺术的集大成者,综合性地展现了民族艺术的方方面面。 当代戏曲艺术格局是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多元化格局,既有传统审美趣味浓厚的旧有剧目,也有展现时代风貌的新编剧目,不同地域特色、不同民族风格的剧种,积累着厚重的文化底蕴。 青年学生处于知识学习的最佳时期,对知识的接受和记忆是深刻持久的,戏曲走进校园依托美育活动参与培养,可以使学生心中深植戏曲艺术因子,对培育学生的民族审美意识自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戏曲美学精神与学生民族思想品格培育
中华文化的鲜明特性是稳定性和传承性,以及广纳中外文化为己所用的融涵力。 戏曲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观念的艺术化表达,戏曲形式表征的背后渗透着民族思想文化的魂魄。 “艺术创造出它所归属的那种文化的艺术肖像。 文化在这种肖像中发现自己的完整性、独特性的形象,发现社会历史的自我。”[7](P276-277)戏曲是中华思想文化的艺术肖像,以直觉可感知且通俗易懂的形式,让群众在娱乐审美活动中,感受中华文化精神的精髓。
儒家、道家和佛家形成于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传统农耕社会,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其求真、至善与向美的思想和观念,早以化入国人的世俗生活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伦理规范和精神追求。 当戏曲艺术含量和文化内涵积淀到一定程度便具备独特的符号体系,这种程式符号体系骨子里蛰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指向,是“儒、道、释”文化的审美呈现,直接影响了戏曲的美学理念和舞台形式构成。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讲求“礼仪”“等级”,直接影响了传统社会中的“秩序和规则”,反映在戏曲中“生旦净丑”行当的划分。 行当是社会秩序的抽象化表达,把人物性别、年龄、性格、外貌、身份包括声音的运用都类型化、程式化,即“聚类成性”。戏曲程式符号体系的背后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世人观念中,早已成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规范。 上至文人士大夫阶层,下至贩夫走卒的平民,无不是以“忠、孝、仁、义”的伦理观念或创作或品评或欣赏戏曲。 正如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所言:“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惯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8](P159)
道家文化是对戏曲美学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源头之一。 老庄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虚实相生”“立象尽意”等思想,直接影响了戏曲写意的形式方法和美学旨趣。 戏曲“虚拟化表演”是通过歌舞化的情感动作与生活拉开距离,戏曲演员在进行戏曲表演时,总是将生活素材通过行当功法转化为写意化的动作,以高于生活的艺术视角,演绎和传达人物形象的艺术美感。 这种程式化的表演方式,讲究“以形传神”的舞台表现手法,以超脱实物“象”的有限制约,来实现“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自由表达,正是这种假定性的空间,使得方寸舞台成为演员自由展现精神世界的无限空间。 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言:“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是有独创性的,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 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 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逼而神境生’。”[9](P271)
维系“虚”与“实”的统一正是戏曲达到写意的关键,“一桌二椅”的空灵舞台是为了把焦点转移到演员身上。 戏曲演员的衣装穿戴和功法动作也无一不是取法生活的符号化表达,从髯口、甩发、翎子、水袖、帽翅、靴底、腰带、脸谱等真实可见的装扮形象,到音乐化的唱腔念白、舞蹈化的身段工架、功夫化的荡子武打等功法技艺,经由戏曲演员娴熟的表演,在舞台上构建出艺术真实的虚拟世界,观众正是通过沉浸其中的审美享受,获得精神愉悦和情感满足。 此外,老庄文化在世俗生活中孕育出的道教文化,也广泛影响了戏曲的发展,元杂剧中“神仙道化”门类;民间戏曲中“酬神”活动,乡间社火表演、驱鬼祭祀赛会等演剧活动,都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戏曲活动,成为百姓世俗娱乐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传入中国对戏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在叙事上的成形。 印度佛教文学影响了民间叙事诗歌的发展,孕育出了敦煌“变文”,流播中原之后,发展出了寺院的“讲唱文学”。随着寺院讲经活动世俗化的发展,很多民间故事题材如王昭君故事、伍子胥故事、大舜行孝、西天取经等故事开始被吸纳其中,后续又延伸出的说书、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与变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戏曲成熟之后,众多佛教故事发展成戏曲演出剧目,如东汉初年传入中原的《佛说盂兰盆经》中,叙述了佛陀弟子目连拯救亡母出地狱的故事,成为目连戏《目连救母》的题材源头,这一故事后经其他戏曲剧种的移植,成为广为人知的劝人向善的剧目。 元代浙江永嘉地区流传的南戏剧目《祖杰》讲述温州乐清县僧人祖杰勾结官府仗势欺人的故事。家喻户晓的《白蛇传》《西游记》《西厢记》等剧目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 此外,寺庙在民间世俗生活担当着重要经济功用,冲州撞府、撂地为场的民间戏曲演出与庙会活动联系紧密,促成了民间戏曲的繁荣和发展。
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方式,向观众展现的不仅仅是悲欢离合的人间世相,更是把中华民族思想巧妙地融会到戏曲形式与内涵之中,“寓教于乐”的观赏状态,收获的不是浅层次的欢笑,而是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古人智慧和行为示范的信息,而这也正是戏曲自古有“高台教化”之称的根源所在。戏曲走进校园,不仅仅是将美的民族艺术形式带给学生们,而是连同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一同带到了学生面前,生动的观赏配合一系列体验性的戏曲活动,能够给予学生全方位的审美教育,对培育学生思想品格的作用自不待言。
三、戏曲审美思想与学生民族精神风貌培育
较长的历史时段之内,戏曲一直于民间文化的浸润中成长,从未中断与底层群众的精神联系,且长期保留着鲜明的民间审美特征,这种审美文化绝不是仅仅满足世人耳目止步于皮相之乐,而是在敦风易俗的教化中,传承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 法国艺术史家丹纳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0](P28)戏曲中所反映出的民族精神,鲜明地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千百年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面对灾难和危机的乐观态度,一是民族面对危机和侵害所展现出英雄情怀和爱国精神。
积极的乐观主义,是深植于我们民族血液之中的素质品质和具有传习力量的审美传统。 戏曲舞台上的作品是对百姓生活的艺术化呈现,观众既要看到真实的生活的一面,面对戏中人的生活不公,自然会联想到自身处境,需要宣泄内心的情感,同时也需要在精神上获得某种慰藉与满足。 这种民族审美心理的诉求,很自然地反映到戏曲创作层面,充分体现了中国式悲剧的核心特质。
悲剧概念被王国维先生从西方戏剧理论借用来对戏曲进行界定,他说《窦娥冤》《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11](P67)不同于西方悲剧中鲜明地强调个体与命运冲突的悲剧性,中国并没有产生出一部严格意义的悲剧作品,正是乐观精神的驱使,国人鲜有彻底的悲剧绝望情绪。 正如朱光潜先生说:“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悲剧,正如辞典中没有诗,采石场里没有雕塑作品一样。”[12](P243)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灾难作为悲剧的题材来源,不同民族所采取的表现观念与形式是不尽相同的,中国式悲剧的处理是把这种悲剧性寓于大团圆结局中,团圆代表着“真善美”理想的实现,以一种幻想的方式延宕心理情绪,从而达到完满的结局,从审美角度上并没有完全否定故事背后的悲剧精神,主人公在到达理想结局过程中所经历的悲惨遭遇和现实不公,亦能充分引发观众同情、怜悯或者愤恨、批判的情绪,因此东西方戏剧精神是相通的。
“有的人对中华民族精神认识不足,往往按照西方悲剧观念的标尺来衡量中国的悲剧,认为正义战胜邪恶的结局是‘光明的尾巴’,是‘粉饰太平’,会降低心灵净化的力量和麻痹人们的战斗意志。”[13](P5)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一种误读,事实上团圆之趣寓含悲剧性的情节取向,遍布于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戏曲作品中,既是其基本叙事特征,也是国人审美旨趣所在。 《长生殿》中月宫重圆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牡丹亭》中因爱死后重生结为连理的杜丽娘与柳梦梅,《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死后化蝶双飞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与织女》中鹊桥相会的牛郎织女,《白蛇传》中雷锋塔倒终成眷属的许仙与白蛇,《西厢记》中冲破藩篱结为良缘的张生与崔莺莺等,这些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创作,无不在彰显国人的乐观精神,是一种对美的热爱与赞叹。 当然,中国老百姓绝不是一味地活在麻木的团圆之趣中,面对社会不公正时,也会用复仇或舍生取义的方式换取正义。 窦娥、李慧娘等人鬼魂复仇,程婴、公孙杵臼、莫成等人的舍生取义,包拯、海瑞等清官的惩治权豪势要为民伸冤的正义之举,同样也彰显出国人对正义的期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赞美英雄和讴歌爱国精神是民族审美传统,是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戏曲中表现英雄和爱国主义的剧目数量众多,是戏曲题材分类中的重要分支,也是深受老百姓喜爱的常演内容。 岳飞、文天祥、杨继业、佘太君、杨宗保、穆桂英等反抗民族入侵的英雄,成为戏曲作品中的光辉人物形象,而这些作品,也被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类型剧目。 这其中以“杨家将戏”为代表,广泛存在于不同地方戏曲剧种中。 这些剧目有的侧重表现宏大的战争场面,如《两狼山》《金沙滩》《大破天门阵》《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穆桂英大破洪州》等;有些侧重表现传奇式爱情故事,如《佘塘关》《穆柯寨》《状元媒》等;有些表现战争背后的思乡之情,如《四郎探母》《雁门关》等。 剧种所涉及的众多角色,从祖辈杨继业、佘太君到子辈的杨延平、杨延广、杨延景、杨延辉等,再到孙辈杨宗保、穆桂英,后继杨文广等,以及八姐、九妹和孟良、焦赞、杨排风等边缘配角,无不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杨家男女老少祖孙数代人,早已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传奇与教育后代的典范。 此外,还有一些除暴安良、伸张正义具有反抗黑暗精神的豪杰志士,同样也是广受民间传颂的英雄人物。 元杂剧中“绿林好汉”,以“水浒传”人物为原型的水浒戏,构成了庞大的英雄谱系,寄托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戏曲作品里蕴含的精神气韵,承载着民族化的道德伦理与价值观念集成,它于历史时空中代际相传,可以说是养育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源泉,作为培育新时代学生民族精神风貌的重要依托,同样有必要在当今时代继续传承传播。
结语
学校作为美育工作的重要基地,直接担负着民族文化传承与振兴的重任,“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其需要解决的目标问题所在。 对于校园美育建设而言,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语境下,建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美育教育范式,是当下工作面临的紧迫任务,而丰富多彩的民族戏曲文化,恰是应当充分利用的宝贵资源。 在校园中传承和弘扬优秀戏曲文化,拓展校园美育的形式与内涵,对提升新时代学生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戏曲走进校园工作逐步推开,其有效地促进了美育教育体系的搭建完善,理论培育与实践推广等多层面亦卓有成效,随着国家政策高度重视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未来也会不断走向体系化建设的方向,取得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