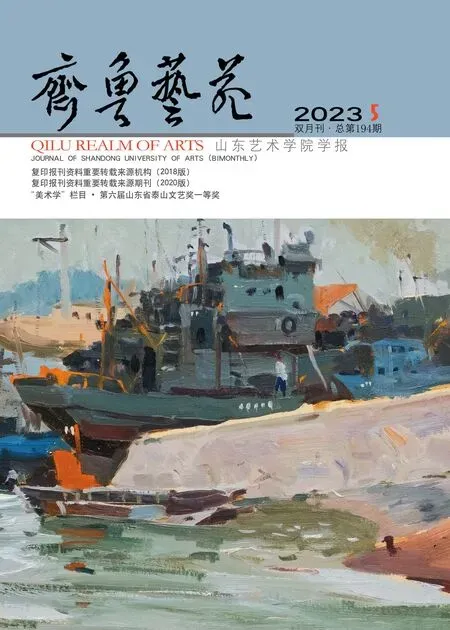被忽略的影像虚拟与现实存在间的对位逻辑
——论留守儿童影像的群体性错位现象
于 昊
(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留守儿童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类群体,我们通过对其现实境遇的认定,以及现实与影像中留守儿童形象的对照,能够发现两者间的差异性。“‘影像’是一个知觉心理学词汇,某物的影像就是它的精神复制品, 影像是认知与现实的关联。”[1](P37)留守儿童形象不仅仅是导演对现实存在的摹仿,而是导演对现实和影像的主体性重塑,并通过受众的接受过程生产其意义的影像符号。 同时,“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动,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2](P14)。问题在于,并非所有导演都具备留守儿童群体的切身性经验,他们感知经验的形成多依赖于现实生活中的刻板印象。 这就导致一批导演在留守儿童形象塑造层面,表现出对其群体现实状况较为一致的错位遮蔽及失真现象。
电影是导演将其在日常生活中所积累的经验,运用视听语言手段“还原”于影像画面中的伦理活动。 银幕上所“还原”的留守儿童形象、场景等是导演的心理意象,是存在于其主体意识中的“印象”,而且会随着主体意识层面上想象的浮动而相应发生变化。 然而对于观众而言,则没有这么复杂,电影是仅作为其单纯的体验对象存在。 “不论商业动机和美学要求是什么,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属于意识形态的;在避开日常生活的逃避主义的消遣的幌子下,电影实际在协助公众去界定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并找到它的意义。”[3](P1)观众在电影中所观察到的一切,不仅是创作主体意识层面的人物形象或事件,也是创作主体有意识“还原”后的产物,即“将日常生活经验中所见的‘现实’‘还原’为主体意识当中的‘现象’”[4]。 导演在塑造人物形象过程中的主体性是难以抹除的,几乎所有在电影中出现的元素都为其叙事目的服务。留守儿童形象作为影像叙事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哪些人物特征可以让观众看到,哪些人物信息又是模糊不清的或暧昧的,又突出了哪些信息,均展现出导演的主体意识以及情感取向。 导演对于留守儿童形象的塑造,包含了其意识层面上“留守儿童现象”的主观投射,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现实与影像的错位。 电影中的情节编排、叙述活动等都是虚构的,不存在真实的可能,但这些内容生发的艺术效果,却成功将它的虚构性予以遮蔽,观众也因其内容迎合了心理预设而接受认可。 因此,对电影中的留守儿童形象塑造进行真实性辨析,成为揭示导演深藏于影像叙事背后的创作动机、心理意象的有效手段。
“留守”作为与“外出”完全对立的状态存在。“社会急剧变迁的影响正日益入侵至日常生活的最基本单位——家庭。”[5]留守儿童、妇女或老人的出现,使得农村原生家庭本已在经济上承受现实压力的现实境遇中,又平添了亲情缺失所带来的心理层面上的伤害,而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概念,此时不得不面临着瓦解消失的风险。 作为某类农村现实环境中所存在的儿童群体,“留守”不仅成为其被标签化的称谓,同时,其也被视为带有故事情节线索的叙事元素,参与到导演的情节逻辑建构之中。 在以留守儿童为主人公的电影作品中,他们往往是被代言、被塑造的,其自身难以发声,正如斯皮瓦克的说法,“底层人无法说话”。 长此以往,电影中的留守儿童形象被植入了过多导演主观意图,而这些或刻板或扭曲的形象塑造对受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并建构了观众对留守儿童的心理认同。 在这些既有认知观念影响下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一种错误或刻板印象的再现。
作为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客体,电影中的留守儿童形象,却往往难以让观众对其拥有切身性的感知。 换言之,导演对于留守儿童形象进行何种塑造,部分决定了观众对于此类形象的感性认知。 因此,无论是积极正面抑或是消极负面的留守儿童形象塑造,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观众的既有认知产生影响。 毋庸置疑,影像再现过程中的留守儿童形象,势必与客观现实之间有着一定距离,电影中完全契合留守儿童群体的形象并不存在。 因为,“‘再现’并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reflection)或‘模拟’(mimesis),而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建构’(construction)”[6](P27)。 影像叙事中,符号的意义不仅在其表层,而且还必须与生成文本的社会、历史、文化等语境密切相关,“意义并不在事物之中,而是被建构的,被产生的。 意义是被再现的实践和运作产生出来的,通过再现系统得以建构”[7](P19-28)。 这就表明,一方面,导演对于场景、人物看似随意的选择,实则隐藏了明显的指涉功能;另一方面,电影画面中出现的任何元素,都必然受到社会语境、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 如果说,运用“典型化”策略塑造的留守儿童形象,最大程度符合了现实生活内在逻辑的话,既有的负面刻板认知,一定程度上会得到部分瓦解。 但同时,导演加深了观众对于这类群体的失实化认知。 “电影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呈现者,同时也可以通过镜头语言揭示社会被遮盖被忽视的一面, 电影对社会具有‘反分析’ 作用。”[8](P22)因此,如果留守儿童形象缺乏真实性的再现,则会对观众起到认知上的误导作用。 易言之,对电影中留守儿童形象的真实性进行辨析,则显得尤为必要和关键。
电影中留守儿童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导演如果盲目追求人物形象的刻板化、主观化再现,必定会引发观众的质疑:剧中人物形象的语言、行为,是否与现实生活的内在规律相契合? 在现实生活中,受各方条件的约束,观众难以直接观察、深入感知留守儿童群体内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而影像叙事则为观众近距离切身观察提供了路径。 与此同时,由于创作主体对于社会现实的认知程度及情感体验的不同,导致其在对于留守儿童形象进行塑造的过程中,不仅在影像叙事内容的建构、叙事主体的选取,还在影像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叙事策略的选择层面,都具有鲜明的指涉特性。
对于电影中的留守儿童形象而言,以“留守”为逻辑起点,可以衍生出“寻找”或“等待”的行为选择。 这一方面将其中蕴含的个人情感予以最大程度的画面呈现,使观众能够真切体会到隐藏于人物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另一方面“等待”与“寻找”作为解决“留守”问题的两种方式,可以此作为切入点,更全面、深入地辨析留守儿童形象塑造中的真实性问题。 现代城市空间中光鲜亮丽的生存图景,诱惑着身处农村空间中守望父母回归的留守儿童,长时间守望无果的客观现实,促使他们燃起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找寻家人团聚的欲望。 “乡村一直被定性为前现代的农业文明的产物,它与以城市化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处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9]相较于城市社会文化而言,乡村文化在现代城市流行文化的冲击下,被公众标签化为“落后”“衰败”“愚昧”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境遇下,传统乡村文化的处境、乡村文化的发展以及乡民对于自身生长环境的历史记忆,都出现了些许被“质疑”甚至是“反叛”的思维认知。 这为电影中选择外出寻找父母的留守儿童形象提供了看似充分的行为动力。 然而,现代都市生活的绚烂图景以及热闹繁华的商场街道,将来到城市之中的外来务工者和追随父母的留守儿童等底层人群抛入其间,在市场经济或物质文明所主导的社会现实中,“焦虑和骚动,心理的眩晕和混乱,各种经验可能性的扩展及道德界限与个人约束的破坏,自我放大和自我混乱,大街上及灵魂中的幻想等等”[10](P19),一系列诱惑持续冲击着外来务工者及其子女的世界观。 电影中,身居城市空间中边缘一隅的留守儿童及其父母,早已忘却或放弃了渴望完成身份上升的梦想,他们将能否摄取足够多的物质经济资本,作为其日常生活的最高诉求。 而此时来自于农村,前往城市空间中寻求亲情复归的留守儿童,在面临城市文明突如其来的冲击时,也逐渐迷失在光鲜亮丽的橱窗之中。 总之,通过文本细读,我们试图深入探讨电影中留守儿童形象在城乡二元空间内遭遇到的现实问题,进而将虚构影像与客观现实进行比照,最终完成对留守儿童塑造层面群体性错位现象的辨析。
一、影像建构与现实逻辑间的错位
21 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上逐渐出现了一批以留守儿童为主人公的作品,如《留守孩子》(刘君一,2006)、《指尖太阳》(黄河,2012)、《念书的孩子》(原雅轩,2012)、《念书的孩子2》(原雅轩,2013年)等。 留守儿童群体是特定社会阶段的产物,如今作为很难被忽视的一类形象,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中屡屡出现。 通过对不同作品中留守儿童形象的分析不难发现,导演塑造留守儿童形象的过程中,往往过分强调某一类人物特质,导致其遮蔽了整体性。 即便由于创作主体的主观介入,作品中的留守儿童形象难以完全与客观现实相匹配,存在某种遮蔽亦是合理;但纵观20 余年来,不同导演对留守儿童形象的塑造上,却出现了一种群体性的遮蔽或失真化现象——他们往往将留守儿童塑造为具有同质化、模式化倾向的形象。 最终,导致了作品中形象主体与客观存在物之间的错位。
错位,即与客观存在并非完全契合的状态、身份或位置。 所谓留守儿童形象塑造上的错位,即相较于真实存在而言的失真化再现。 某一部作品中,留守儿童形象塑造与现实群体间错位不可避免。但是,当我们将研究范围扩展至目前已有的影视作品时,这种错位就成为一种存在于众多作品或导演创作中而较为一致的倾向。 例如《凤山村的孩子》(张毅,2011)中的小凤、《亲亲哒》(马雍,2016)中的亲亲、《坚强的小孩》(李杨,2016)中的李自强等,导演为凸显留守儿童勇于承担家庭责任的“小大人”形象,而导致儿童群体应有的天真烂漫、活泼顽皮的天性被刻意遮蔽。 《留守孩子》中的杜小苇、王小福,《穿过忧伤的花季》(金舸,2012)中的向华萍等,他们因常年与父母分离而导致的反叛情绪或行为,却又使可能存在的“闪光点”被导演予以隐匿。 由此我们发现,不同导演在留守儿童形象塑造过程中,却呈现出某种共同的错位或遮蔽现象。 这种具有相似性特征的错位或失真,被称为群体性错位。
在表现留守儿童形象的电影作品中,除了反映城市中外来务工者以及来自农村老家留守儿童的生存境遇之外,也将镜头聚焦于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留守儿童在进入城市后所遭遇的现实问题。 他们面临着由现实生存压力所带来的挫败感与失落感。电影中留守儿童对于城市/农村空间的不同态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他们是否到城市之中寻找父母,以求与家人重聚的选择。 对于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留守儿童而言,他们在城乡之间往返运动的最根本出发点——对家庭结构由破碎向重归完整状态转换的诉求。 这种渴望在电影作品中被表现为:长时间留守经历的压迫下,为了寻求与父母的团聚,毅然走出农村,进而通过自身生活区域的转换,完成与父母在城市空间中走向团圆的行动;由于自身在年龄、经济条件以及对于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局限性,不得不在农村的老家承受“留守”所带来的负面情绪的同时,等待父母从城市归来。 他们对于不同生存空间的选择,隐含着其对现代城市文明/传统乡村文明的接受态度。 “现代城市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多族群摆脱农业生产后共同生活、交流思想的场所。 城市空间并非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只涉多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文化建构。”[11](P9)
无可否认,对于家庭结构完整的渴望,是电影中留守儿童内心深处最为殷切的期待与盼望。 这种渴望是长时间亲子分离影响下的必然结果。 因此,它是我们分析电影中留守儿童形象塑造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逻辑前提。 的确,在以留守儿童形象为主人公的电影作品中,这种家庭结构完整性的期待,直接将主人公的行为选择,导向了默默等待抑或主动寻找两类。 这种叙事逻辑在观众认知观念中得以确认。 导演也借此完成了引导观众沉浸于影像内容之中的首要环节。 某种意义上,以约定俗成的思维习惯为逻辑前提的叙事发生机制,能够拉近身处影院之中的观众与银幕中虚构的场景、情节之间的距离,进而引导观众产生心理认同,最终产生情感共鸣。 “根据大卫·波德维尔的电影叙事理论,叙事是一个艺术家和观众互动的完整‘过程’(process),观众的‘认知建构’是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由于认知建构模型十分倚重人类认知处理信息的作用,波德维尔叙事理论中的‘观众’(viewer or spectator)较先前叙事理论中的观众有着更强的主动性。”[12](P235)“在剧情片中,叙述是影片情节和风格互动的过程,它不断提示观众,并引导其从事故事的建构。”[13](P127)由此可知,波德维尔对于叙事的观点是建立在观众对于整体叙事的认知方式之上的,他认为观众通过自身的观影过程,经由影院/室内视知觉活动对电影所呈现画面信息的获取,对信息进行个人主观化的处理,而后完成自身对于影像叙事的最终建构。 留守儿童之于家庭内部结构回归完整的渴望,必然襄助于我们剖析其行为产生的动因。
严格来说,对于家庭内部结构回归完整的渴望,属于内含于留守儿童形象中的共性。 从留守儿童形象的整体性来考量,可以得知,亲子分离必然带来对于回归的渴望。 但此时,电影中是否以这种渴望主导留守儿童形象的塑造并非必然要求。 作为留守身份必然导向的心理情绪,它可以衍生出一系列行为选择的原始动机,也可以仅仅是塑造不同类型留守儿童形象的背景存在。 无论是家庭责任的承担者,抑或是行为失范的失足者,当我们排除掉这份渴望,冷静客观地分析导演通过“典型化”策略所塑造的留守儿童形象时,被留守身份过分遮掩的儿童身份、天性就显露出来。 因而,以此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便于我们发掘出隐藏于回归渴望背后可能存在的有违现实内在逻辑的失实化表现。 如前所述,电影中留守儿童形象实现家庭内部结构重归完整的诉求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追随父母的脚步离开农村,前往城市中寻找异地空间内的家庭圆满;二是迫于现实束缚,无奈留在农村家中,苦苦守望亲人的回归。 每一类行为选择,都会衍生出不同的人物命运,这为我们提供了不同角度,对留守儿童形象塑造层面出现的群体性错位现象进行剖析。
二、寻找家庭圆满的影像建构
以留守儿童为主人公的电影作品中,往往会呈现他们因长期饱受由情感缺失导致生理、心理双重伤害的现象。 因而,留守儿童试图借助前往城市中与父母团聚的行为选择,弥补心灵创伤的动机,就自然出现了。 留守儿童在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往往是被“丧失”的,他们无力针对自己的所处境遇发声。 众所周知,贫寒的家庭出身、落后的农村经济现状,成为推动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的原始动力。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持续推进,无数成功者的神话铺天盖地的袭来。 当深陷贫穷落后且文化衰败的农村空间内的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通过电视和网络了解到城市生活的五彩斑斓时,他们心中对于现代化的向往促使他们远赴他乡,寻找生活的新希望。 “轨道铺进了深山,尖锐的火车长鸣声打破了山村固有的宁静,以城市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渐渐渗透到了闭塞保守的山村”[14],经济发展的驱动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往乡村之外的生活,去往大都市拼搏的抉择,在他们心中成为了改善贫苦生活的美好希望。 电影中深陷衰败、落后农村空间里的留守儿童,选择前往城市寻求家庭圆满的内心诉求,不仅契合了对于更高层次生活品质追求的生存需要,同样也与自身渴望亲情复归的情感呼唤相迎合。 在此,建立在生存与情感双重需要基础之上的行为选择与现实生活过程中的内在逻辑相匹配。 因此,是否产生此种行为选择动机的真实性问题,在此处并不作为考量的重点。 如果说,我们排除了行为选择动机的真实性问题的话,那么,隐藏于人物内心的欲望诉求是否转换抑或如何转化为实质性外在行为的问题,则成为我们考量人物形象真实性与否的关键。
在众多电影文本中,我们难以通过某一类留守儿童形象的呈现,对其进行整体性概括。 无论是《亲亲哒》中勇于承担家庭重任的亲亲,还是《留守孩子》中调皮顽劣的王小福,抑或是《穿过忧伤的花季》中行为失范的向华萍,再或者《空巢里的孩子》(王鲸,2009)中守望父母回归的“北京”“青岛”等,他们都是社会客观存在的一隅。 因此,不难发现,留守儿童这一在现实中有明确指向的人群,在电影文本内具有类型多样的形象及多重能指,这也从侧面展现出影像再现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内涵的多义性。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留守儿童群体而言,他们没有“发声”的空间,或者说其“发声”空间是多数受众日常生活经验中较难涉及到的。 因而,导演通过影像再现后的留守儿童形象,可被看作是代替丧失“发声”空间和权力的留守儿童群体,向大众诉说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种“‘代表’或‘代言’,是建立在它们具有话语权的基础上,因此也承认了代表人和被代表人之间的阶层差异”[15](P30)。 抛开阶层差异性不谈,作为“代言人”存在,导演所选择的艺术再现内容,与此类社会群体的情感倾向及价值判断息息相关。 导演主动将自身的感性认知与情感体验隐匿于叙事之中,电影文本内的留守儿童形象的塑造,则成为其表达自身主体性价值取向的显现形式。 留守儿童形象的真实与否,不仅在于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还在于导演试图通过“典型性”塑造策略再现的形象,选择性地突出了何种真实。 因而,当我们对电影中的留守儿童形象进行真实性辨析的同时,依然需要额外关注导演为何选择将这般形象呈现于银幕之上的缘由。
对于电影文本呈现的留守儿童形象而言,城市空间于其精神世界中,被建构为“乌托邦”般的存在。 “‘u’‘topia’来自希腊文,前者表示否定,后者的意思是某个地方或地区。 ‘u’可以与‘eu’联系起来,表示‘美好’‘完美’,这两种意思联系起来,也就是一个虚拟的值得人们向往的至善至美的地方或国度。”[16]在以表现留守儿童的生活境遇为主的电影作品中,往往并未选择全景式地展现城市空间亦或城市图景的方式,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是留守儿童对于城市空间带有自身明显主观想象的认知。 电影主创者在建构影像画面时,甚至选择将一部分城市空间中真实存在却残酷的现实图景予以抽离,从而描绘出近似乌托邦似的“想象域”。 但是,当留守儿童毅然踏上前往城市寻找父母的旅途时,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便逐一出现。 《城市候鸟》(魏曦铭,2010)中,当外来务工者面对子女学籍问题时,遭遇到的是由于自身工作地点的非固定状态,而使来到城市上学的子女不得不处理留级、甚至是不得不在初高中或高考时回到农村老家的问题。 《小彪与狗》(周浩,2015)中,“小彪”所说的自己在小学时期随父母辗转各地的现实经历,也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这一点;曾随父母漂泊在外的小彪最终还是在家乡一个人与一条狗一起生活,早年间随父母一起的漂泊经历给予他的只有学业上的影响,即不得不因为频繁转校而留级。 《留守孩子》中,当王小福因迟到站在班级门口时,他口中念出的是给父母的一封信,是对于父母常年外出给其带来的情感缺失以及怨恨,电影作品将这种因留守经历所带来的负面情绪予以充分呈现。 这种负面情绪的释放,直接展现出留守儿童对于家庭团圆的强烈渴望。 但是,为了追求家庭内部的重归团员,主动或被动地前往城市与父母相聚后,他们的生活是否真如自我想象的一般美好? 电影作品所刻画的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城市中往往被视为难以融入当地生活的“他者”,而对于生活在农村之中的留守儿童而言,他们在同辈非留守者的视野中,恰恰也作为“他者”存在。 正如英国学者丹尼·卡瓦拉罗所言:“他者就在我们之中。当一个文化、社会或社群把某些个体当成他者加以边缘化时,它试图排斥或压迫的实际上是它自身的一部分。”[17](P123)然而,当留守儿童为了弥补内心需求而对家庭缺失的亲情予以追寻之时,种种现实困难却阻碍了他们跟随父母迁徙至城市的愿望实现。
电影作品对于家庭恶劣经济条件的展现,与父母前往城市的务工选择相契合,其同样符合现实生活逻辑。 但是,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由于家庭内部父母角色的缺席,上一代祖辈老人的在场,也是以留守儿童形象为主人公的电影作品里不可或缺的设置,然而问题在于同样留守农村中这些老人形象的塑造,往往与疾病缠身、年迈体弱的特征相关。比如《留守孩子》中,身患肺心病的爷爷;《童年的稻田》(朱晓玲,2012)中,在麦秸旁去世的奶奶;《遥望南方的童年》(易寒,2007)中,影片开始便已重病缠身的祖辈老人等。 毋庸置疑,现实农村环境中确实不乏此类体弱多病的老人,但电影作品中,同样留守家中承担照顾留守儿童责任的老人,却具有如此相似的人物特征,就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 因此,导演为了突出作品中留守儿童形象的苦情命运,主观上刻意塑造了具有严重同质化倾向的留守老人形象,其也与现实形成群体性错位存在。 这种以留守儿童形象苦难命运催生观众心中对其怜悯之情的方式,不仅未能营造出忧伤、悲凉的气氛,反而导致人物形象的真实性被削弱。
对于亲情的渴望、长时间分隔城乡两地的生活现状,被导演作为建构留守儿童行为合理性的基础,这种看似符合思维逻辑的因果关联,却忽视了儿童本身行为的逻辑性。 如果说,提议租车看望父母的想法,尚且与渴望和父母团聚的殷切希望相契合的话;那么,当这种想法转换为现实行为予以实施时,我们就难以仅仅以留守者身份,来考量人物行为的合理性。 因为看似缜密的叙事逻辑,却忽略了作为孩子的他们,根本无法完成租车的行为的现实,脱离儿童身份限定的行为选择,势必导致观众对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另外,前往城市后,是否能够真正满足他们心中渴望,在作品中同样没有直接呈现。 导演恰恰用最符合现实生活情感的逻辑构建,打破了电影作品中的真实。
《小彪与狗》(周浩,2015)、《米花之味》(鹏飞,2017)、《留守孩子》等对于此类问题进行反思与呈现的电影作品中,留守儿童的进城寻亲经历、农民工父母失败的城市体验,以及留守在家无力迁徙的低龄段留守儿童的现实境遇,都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身处偏远山村的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外出务工父母奋斗的失败结局。 “从家庭社会学的视角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伴随社会变迁而来的家庭结构断裂、家庭功能紊乱、家庭关系淡化、家庭生活方式变异的综合体现,它反映的是农村家庭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一种特殊的文化失调现象。”[18]对于留守儿童群体而言,由于父母外出所造成的家庭内部亲情的缺失,势必会让他们对外出的务工父母产生更为深切的思念。 这种长时间的情感缺失状态,导致了留守在家的子女,对于前往城市寻找父母,进而完成亲情复归的欲望诉求日趋强烈。 农村相对落后衰败的场域设定,也为这一切的发生设置了合理的前提。 正是因为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才使得外出务工、留守,进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生成的逻辑,显得顺理成章。 “于是,在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双重刺激下,新老一代农民的背乡弃土,乡村的传统人际关系迅速解体,乡村的生活意义和吸引力逐渐丧失。”[19]现代城市文明对于农村文明的全面影响,使得现代性文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身处农村之中的留守儿童们传递农村文化落后愚昧的观念。 “城市空间并非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只涉多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文化建构。”[20](P9)无论是对于城市现代文化的积极拥抱,还是说对于日益衰败的传统乡村文明的默默坚守,都被导演放置于留守儿童期待与父母团聚的内心渴望中予以再现。 观众对于留守儿童形象的既有认知所衍生出的怜悯之情,被导演通过苦情化的人物命运构建予以放大,最终将人物形象塑造的失实化表现,埋藏于不易被察觉的情感宣泄之中。
电影作品中留守儿童与父母形象设定,同样受到了经济发展以及城镇一体化建设的影响。 户籍归属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他们在城乡之间跨区域流动的不稳定性,即使其长时间生活在城市,流动状态却是难以改变。 追寻城市空间中家庭圆满的留守者,也同样因为留守农村而产生了远行城市的心理诉求。 衰败落后的农村空间与其中的留守儿童之间形成了某种呼应,农村作为与城市发展比较的相对落后者,与留守儿童一样成为“家庭”离弃之地的隐喻。 留守儿童形象,作为身处社会、家庭伦理之中的社会底层边缘人物命运选择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呈现出市场经济原则以及商品逻辑占据社会主要评价体系的现代城市的不确定性特征,同样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对于现代都市性文明的理性反思,对于逐渐逝去的传统乡村文明的感性怀念。 “留守”一词这个带有丰富内涵的称谓,作为与“外出”完全对立的两个词,成为导演或社会大众对于由同一家庭内部所分裂出的两种群体的称谓。“留守”不仅成为其被标签化的称谓,同时,它也作为带有故事情节线索的叙事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导演对于电影作品创作之初的叙事建构之中。 留守儿童自身情感缺失的现实境遇,在导演建构叙事过程中成为主人公的台词、行为等方面设计的起点。 对于留守儿童而言,除了俊男靓女、光鲜亮丽的繁华生活图景外,城市吸引他们的,更是远在其中的父母,这也成为他们身在农村老家,却对城市生活产生无限渴望的根本原因。 思念父母的情感诉求、关于城市图景的主观个人化的想象,构建起了每一个留守儿童心中对于城市的渴望。 此时的农村成为一切故事发生的起点,也成为故事中主人公感伤性结局的最终归宿。 但是,导演在表现前往城市寻求一家团聚的留守儿童形象时,却并未将这种客观现实呈现于画面之中。 他们仅以过程艰辛替换随时可能到来的未果而终的现实命运,试图用由留守身份牵动的行为选择,遮蔽社会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某种阻碍。
导演在建构影像叙事活动时,一定程度上会考量观众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刻板印象。 但是,其被自身价值取向驱使的艺术再现,同样存在着与客观现实严重错位的风险。 作为创作主体的导演,其对于留守儿童形象的主体性建构,不仅内含自身创作意图,而且“意在对读者的世界观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在伦理上绝对不是中立的,而是或隐或显地引出一种对世界和读者的价值重估”[21]。 换言之,观众作为观看实践的行为主体,进入影像叙事的阅读之后,必然会对经导演主观选择后呈现的内容予以判断,当其产生心理认同时,自身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留守儿童群体认知,也会产生相应变化。 因此,这种失实化的人物形象塑造,一定程度上必然存在着刻意误导/定向引导观众价值取向的可能。
结语
导演一味为主人公构筑外出寻找父母的行为选择,由此而进行情感和逻辑上的铺垫,即便确实能够建构起行为与现实逻辑之间的合理关系,但因为其过度关注留守儿童形象悲情命运与感伤结局的再现,反而形成了影像与真实间的错位,消解了影像再现过程中人物形象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