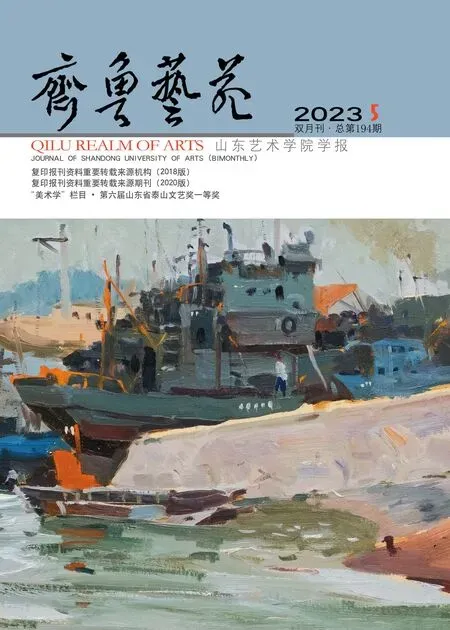感知在场
——表象呈现与身体临场
吴 鹏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 100102)
一、原初在场: 人是万物的尺度
莫里斯·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强调:“将主观与客观结合在一起,身体在感知活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人们身体的轮廓是一般空间关系不能逾越的界限。”[1](P52)事实上,人对外部现实世界的全部认识在根本上是感知的结果。 人的感知,如同展览营造中一座深不可测的博览设备库,为原初在场的主体地位提供宏大世界的自然信息和谱式结构。 “在人的所有层面的知识和理论的建构中,都通过了主观意识的中介,都通过了科学、技术和工程的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的中介。 就此而言,人的主体性的介入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人的认识发生的主体相对性的依据。”[2]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展览机制等不断发展的当下,我们研究以人为本的感知主体、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致力于展览展示的营造法式,推动学科在理论环境下扩充感知思维的意义不言而喻。 我们用理性知识通晓并构建原理,又开拓感性认知去作用于展览营造,在倡导还原艺术本质与个性创意的感知思维建设的进程中具有积极的探索意识。
公元前5 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在《论真理》中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观点在历史上显示过巨大的影响,也因命题理解、学术角度、研究层面各不相同而遭受过质疑、争论。 本文无意从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或是伦理历史等去揣摩与渲染此观点,而是从艺术的本质与展览展示学科建设本体出发,试图从“人”的价值尺度与当代精神对艺术设计和美术馆展览实践的层面阐释以人为尺度的美术馆感知之道的人文关怀输送。
从概念上来说,“人”一是带着个人意志的“个体”,二是代表全体意识的“人类”;“万物”则更为包罗万象,“存在”与“不存在”的普遍本质,数量、类型、场合、时空以及人与物、物与物、物与场的所有关系,是感觉的对象,流变的过程;“尺度”在赫拉克利特的朴素哲学观点里理解为“规律”,等同于“自然的平衡和秩序”。[3]普罗泰戈拉的命题实际就是为“万物”的规律寻找依据,而这个依据不偏不倚,只存在于“人”那里。 早期古希腊智者学派主张以人的眼光去认知和考察社会,对于历史长河的发展进程来说是对神权的抗争,明示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感知与思维、观念力和意志力提上日程。人,作为生命体,联结万物,承载万物,通过身体,去感知和认识世界经验,是自然科学和辩证哲学永恒的命题,并经历了心物二元、现象学到心物一元的变迁。 从柏拉图“用灵魂注视事物本身”、笛卡尔的“我思”以及尼采“一切从身体出发”,到现象学出现,二元论受到巨大冲击,胡塞尔描述下的身体,是“躯体”与“心灵”构成的结合点,只有通过对身体的“体认”,现象学才可以从苍白、抽象的自我,步入生机无限的“生活世界”。[4]胡塞尔之后的梅洛-庞蒂则在知觉现象学层面提出了“身体哲学”,身体成为连接世界的纽带,人拥有着诗意的审美在丰富多元的感知世界挺身而出。 到了技术革新的新语境时代,身体与技术的碰撞带来了感官之思的媒介交互。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其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包括身体器官及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媒介环境学新锐人物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 则继承和发扬了芒福德、麦克卢汉等人的媒介思想,用技术哲学范式的探究以及先锋的实践主义总结出了“人性化趋势”。 美国当代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则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跨越了技术哲学和现象学,提出了继物质身体、文化身体之后的技术身体说,身体在场决定了光亮之所。 “我们是身体,是文化的此在此世,更是技术的此在此世。”[5]当代展览展示的呈现方式多元丰富,展示理念与知识背景交迭发展,形态决定了感知的多维度和多触觉,这也是时代语境赋予人的“智域”的不断开拓。
艺术是一个精神文明的开放领域,是人的生活的最高表现。 人是自然之子,拥有自然的尺度,也会在社会形态下拥有价值和道德尺度,在艺术生产中拥有审美尺度。 人丰富的创造力、理解交流、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时间和空间里留下了动作的媒介和度量的痕迹,是探求无限和扩展的“未知世界”独一无二的尺度。 作为专门研究感性的学科,艺术本质的探源,是一条将感性深化融合的理性之路,这种“丈量”,是全面而整体的认知模式,是严密而科学的逻辑思维,更需要丰富的生活经验、深厚的人文素养、开阔的胸怀眼界和成熟的人类情感为依托。 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在《艺术与视知觉》的前言里阐述了沙夫尔-西莫恩《论艺术活动》中令人信服的基本观点:用艺术的方法把握生活的能力,并不是少数几个天才的艺术专家特有的,而是属于每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的,因为大自然给每一个健全的人都赋予了一双眼睛。 对于心理学家们来说,这就意味着,对艺术的研究,是对人本身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6](P7)在凝结着人类精神财富的美术馆殿堂,人的艺术创造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的策展项目、设计规划、教育传播以及美术馆管理等具体实践活动,思辨和深邃成为一种展览学科建设的精神气象,无不闪耀着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实际的人性呼唤与人文回归:思辨,意味着观念的交锋与融汇:深邃,指向着学科的人文厚度。阅读与思考展览展示的叙事转换,关怀人的现实生活的情景设计,展览营造机制的人性科学管理,在创造艺术和欣赏艺术的整体活动中重视人的价值,更好地掌握和认知艺术这个具体的事物,是一个连贯的、以人为本的、满足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求的文化脉络。 理解本质、发现意义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同时产生新的建设服务于实践,把人的精神实质贯彻到艺术展览事业,促发人的多维感知系统从而达到一种外观与内省的时代精神升华,生产出更多优秀的文化艺术成果。 黑格尔曾赞叹“人是万物的尺度——一个伟大的命题!”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凝聚的精华,这是以人为出发点探究美术馆感知之道的人文意义与当代精神价值所在。
二、 感知与展览
感知、想象、经验的对象构成了整个世界。 感知(Perception),是意识对内外界信息的觉察、感觉、注意、知觉的一系列过程。 它是人与空间关系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基于感觉的过程,通过真实的可见、可听、可闻、可想、可触的体验,从而调度人的组织识别与解释系统用以理解和表达外部世界。 感知不仅是对声音、温湿度、色状貌质等各种环境因素的简单整合,人的听觉、视觉、触觉的联觉,而且是对丰富的环境信息的全面体验、深入理解和情感输入。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感知表达有两种理解:其一,感知的表达可以是对于行为的通报。 在这之前海德格尔对于表达状态是这样说的,“我们不是在说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相反,我们是在看到人们对于事物所说出的东西”,“我们不是在说出我们所看到的事物表层,相反,我们是在看到人们对于事物说出东西的基础上进行感知”。[7](P71)
其二,感知的表达也可以是对于在行为本身中被感知到的东西的传述。 在这里海德格尔提出了被感知的存在者,这才是感知表达所要传述的东西,也就是事物本身。 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提出,感知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一种主动的追求机制。感知理论是人进入一个空间内部的主体感受和直观反应,它包含了人对空间的感觉、看法和理解,是人对外部环境的主体评价。[8]
身体的感知,或者说人的感知,在海德格尔那里表达为一种前视域的疏明之境,在梅洛-庞蒂那里引申为一种身体性的展开,而在结构主义学说中总结为某种先于意义的整体性结构,在后现代哲学体系里,感知主体往往被看作在文化场域中不断构建的欲望和象征的综合体。 “身体永远是冲创性的,永远要外溢扩张,永远要冲出自己的领域,身体的特征就是要非空间化,非固定化,非辖域化,身体的本质就是要游牧,就是要在成千上万座无边无际的高原上狂奔。”[9](P36)
概念是人类认知世界的经验事实,反映了事物和关系的本质。 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于感知的概念表述各有其详,但基本还是涵盖了感官信息和赋予感官信息意义的两重要素。 感知者、感知对象以及两者之间的感知关系构成了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感知事件。 本文基于人为尺度的美术馆感知之道——人在展览展示空间中呈现的感知便是一个特定的感知事件。 认知语言学研究者林正军其文章《英语感知动词词义研究的认知语义视觉》中提出了“感知路径”(perceptual path)这一概念。[10]他指出,“感知路径”的形成源于感知各成分之间的关系, 它主要包括对感知者和感知对象的概念化,以及两者之间以某种路径形式移动的无形物,如探查、刺激。 所以当感知事件被投射到概念域时,它可以表征为感知者、感知行为、感知对象。 在感知概念的生成过程中,执行感知行为的生命体被概念化为感知者,被感知的事物被概念化为感知对象,而两者之间的关系被概念化为感知行为。 因此,感知概念应运而生。 本文的研究是基于展览展示这一感知事件中感官感知和心理感知的感知路径。
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将艺术、哲学和科学区别为三种不同的规范,每种范式都有其自己不同的解读世界的方式:哲学创造概念,艺术创造感知的特定表现方式,科学创造基于元点、函数元素的专项理论。 德勒兹认为,这三种规范并没有高下之分,它们是解读和组织形而上的流动的不同方式。 在文化科学的逻辑研究领域,卡西尔(Ernst Cassirer)则通过文化科学的研究对象、感知方式和研究方法来确立文化科学的独立地位。 在量子力学领域、人机交互系统中,人类的推理、决策和认知过程借助量子范式的思想,描述了一种情感、认知和决策的建模过程中不确定的叠加状态。 临床医学应用上也有基于光学波动和压缩感知的超分辨超声成像研究。 随着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移动终端设备的智能化与集成化不断增强,要实现用户的精准画像,就必须把散落在不同空间和维度的多源感知数据有效融合起来,构建统一的、融合的用户画像框架。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汤姆·米契尔(Tom Mitchell)预测:“AI 未来有三大趋势:感知、自然语言处理、手机技术扩散。”通过精密算法,某些领域计算机软件的“感知训练”甚至会超过人类,这些“计算得来的感知”都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研发和运用到科技生活前沿。 “当代人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的相关研究具体揭示了自然环境、人之身体与意识或心灵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的统一性。 一方面,人对自然的研究必须通过意识活动的中介;另一方面,人对意识现象的研究也不能脱离自然环境和人之身体的作用。 这就启示我们无论是对自然的研究,还是对社会的研究,无论是对身体的研究,还是对意识的研究,都必须从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反馈回环的统一性关系中来获得。”[11]
感知边界的无限扩大,让当前时代背景下展览展示呈现多元丰富的面貌。 在不同的体制、地域和领域中,展览展示营造表象有诉说未来生活的区块链线索,有生命科学的艺术疗愈,有艺术商业的设计互联,食物、天气、化学能、机器、非物质、循环经济、修复、工作、城市……在一场场哲学思辨和故事叙述的呈现下,人的感知为多态共能的展览形式和内容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动力。 研究以人的感知为主体营造的展览展示,在多元和跨界并举的生态现状下,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状态,一方面,展览展陈体系要求学术机构、策展机制搭建可感可知的桥梁,以推广和诉知美术作品的内涵和艺术风尚的动态;另一方面,五光十色的展览世界也在要求受众需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扩大认知领域,才能更精微地感受展览展示营造的各种环境表达与传递的思想价值。 感知发展的双向机制赋予艺术的真正意义,就在于用丰富的向上的力量探索未知的不竭精神,用以改变与更新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奖金得主、著名心理学家劳伦斯·罗森布拉姆的力作《感知力》[12]用一种新奇的借喻方式、严谨的实验阐释人类五大感官能力和九种动物潜能,别开生面地揭示人类遗失的影响力来源:人内在的猴子和萤火虫,类似于征服奥斯卡的动画师——视觉是获得信息之源的最核心的感知力;人内在的蜘蛛,是教正常人作画的盲人画家,具有最可塑性的触觉;人内在的狗和老鼠,具有最具延伸性的嗅觉,是戴着眼罩爬行的心理学家,用以闻出机遇挑战,用气味施展隐形的力量;引导性的听觉代表是人内在的蝙蝠和兔子,是听出障碍物的使命山地车手,在寂静之声里处理任务;人内在都有一条变色龙,尝出白垩纪味道的侍酒大师——味觉,最容易受到干扰的感知力;而人拥有的多重感知力,是最强大的力量,用以掌握世间万物,如一只具有强大同感和联觉的雪貂,听见空间,摸到味道,闻到形状,尝出场景,看到语言。
当下展览领域,新的表现形式层出不穷,与之对应的人的感知之道、观看之道也必须发生必要之转变,需要参与者更多维的“情动力”。 “情动力”(affect) 概念源自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的《伦理学》,原指“事物层面的身体反应”,与人的一般情感相对立,是身体进行感应(affect)和被感应(affected)的能力。 德勒兹则进一步指出情动力不表示个人的感受,它脱离任何表达的主体,是一种前个体的强烈程度,并与来自身体的经验阶段的过程相关。 情动力是身体中通过与另一个“身体”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修改或变化——提高或降低身体的活性力量。 “情动力”视域下的感知就是“以身为目”——放弃视觉中心主义,让身体变成一个感觉的“无器官身体”。 超越表象与再现,摒弃主客体二分的认识论模式,让艺术释放出其差异性元素。 而这一切,都与“情动力”相关。 因此,有生命的主体在面对世界时采取的情感的和实际的态度消失在一种心理生理机制中,一切评价都应该是一种移情的结果,复杂的情境通过移情唤起了与神经器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快乐和痛苦的基本印象。[13](P85)很多关于时间的展览和艺术作品,各种绘画、诗歌、影像的载体,物理的、历史的符号,存在与流逝的个体经验……如何让时间“可视”? 如何捕捉创作者隐藏的无形本质? 如何连接展览生产者的时空编排节奏? 认知的前端是感知力,无论是展览展示的组织者还是参与观展的体验者,都需要最基础的感知力。 感知能力如何有效转换成“情动力”,展览空间设计中的应用互动营销策略、人和作品互动体验的过程本身就阐述了展览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基于展览的感知就是展览时间和空间、“物”和“我”的纽带,为展览展示的理论实践和深度传播提供了前提与预设。 感知在场的升华能帮助受众理解与思索,共情与游历一场场“时间的洗礼”。 所有连贯展览的目光、颜色、态度以及先验身体图示,在身体整体的每一个部分通过活性感知、外延思考,让展览在市场、技术和艺术关系层面得到有效的互动传播。 正因为展览展示是一门多元哲学,也有其本质、先验、还原和现象等客观思维,研究“人的感知”这一原点,阐明了展览四个维度关系中“体验”的重要性。 在人工智能、交通迭代飞速发展的当下,时空仿佛被浓缩,人们可以借助更多的工具和载体去探索外部世界,而无论社会如何日新月异,艺术“体验”是永远都替代不了的源动力。展览空间可以通过不同时期艺术作品的罗列、不同风格材料的艺术门类营造视域,在展览展示中被“唤醒”的审美意识,在感知思维中最富创造力。 展览排列组合和艺术历史文化的丰厚沉淀,会生产连续而多样的感官秩序,在整体的印象和事物的背景相互作用下,持久而又富于变化,是一场探索艺术本质的身体和智力运动。 “有些信号是直接通过神经通路运送的,并且显示出内脏(如心脏、血管、皮肤)或肌肉的状态。 其他信号是在血流中传递过来的,是通过对荷尔蒙,或葡萄糖,或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缩,或者通过血液的PH 水平而被传递过来的。这些信号被许多神经感受装置所‘解读’,这些装置根据它们的‘解读’标准的定位点而作出不同的反应。”[14](P109)展览理论的实践就是基于层出不穷、累计变换、革新思辨的感知思维在时空里集成、叠加、优化,并形成展览展示营造体系环节特殊的感知力。
在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疾速进步的新技术环境下,展览展示的信息界面由之前的直接面对面传递向参与想象、理解共鸣和民主协商的方向转变,这也决定了展览空间的叙事编排、光影色彩、材质肌理以及实时交互会需要更多基于展览感知的导向。 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场景的多维数据信息成为一种新型界面,一种创造与感知并存的界面。 界面是一种洞察人们需求的沟通方式,一般来说,展示界面分为以空间本身的组合形成的展览展示本体的构造界面,另一种就是以人为核心的感知界面。 展览展示功能的实现离不开空间占据的先决条件,实物、灯光、陈列以及虚实节奏,展览的构造界面是丰富布局和突出主题的设计范式。 而感知界面实际是人们的心理空间,通过人的感知测量,视觉、嗅觉、听觉等感官结合构造界面在心理上形成的空间感受。 例如视觉感官所形成的视觉界面,随着观众视觉的“扫描”,空间曲直、光效明暗、文本版面等跌宕起伏,往往会产生移步异景引人入胜的心理感受。 人在时空构建界面的双重游历,产生了一连串的感官认知转换过程,也就是展览展示中的感知。 这种转换过程类似于一种经验的收集,并“内化”成一个认知模式,并试图唤醒储存在身体记忆库里的编码,以点成线,形成一张“心像图”,与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Chase Tolman)提出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①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一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Chase Tolman)提出。 他以白鼠做实验,将一只饥饿的白鼠放在迷津内,通过食物来引导它们。 在开始的时候,白鼠在迷津中胡乱地奔跑,但是总会跑到死胡同,有时也会跑进正确的通道。 偶然间,它们发现了食物,并且随着次数的增多,它们犯错误的次数越来越少。 托尔曼认为,在这个实验中,食物为白鼠提供了目的和方向。 小白鼠在每一个选择点上都建立起了期望,即期望着各个选择点连接起来的线路能将它们正确地引向食物。 如果期望被证实,白鼠获得了食物,那么各个选择点联结起来的格局就得到加强。 当小白鼠在迷津中把所有选择点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迷宫格局时,托尔曼就认为白鼠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幅认知地图。 参见:蒋宁.托尔曼的认知地图对现代教学的启示[J].学园,2013,(15)。特别类似。
还有学者认为认知地图就是因果地图(Causal Map),认知地图表达的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就像“想法”的串联和原因映射的概念。 想法帮助人规划事情,做出决策,是连接无数个结点的矢量图。当然,这是心理学家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诠释认识,个体知识与经验映射现实并形成一种方式方法,实则也是获取信息、加工信息、解码信息并储存转换信息的过程。 展览展示中人的感知便也成为了强有力的“探寻”与“解码”的工具,在展示信息的刺激下,心里会产生判断,空间感知与人内在记忆的“认知地图”会产生大量的因子解锁呈现的资料,并对展览时空进行全方位的认知解读。 认知模式改变了人们对时空体验的拓增。 单一的观看模式以及信息获取方式削减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随着展览展示传播方式日益丰富,构建界面和感知界面的信息媒介,在“人”与“场”的连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空间为划分的构造界面为观众提供了井然有序的参观路线,展示界面的多维感知打开了展览的多重维度。 观众会由此整合出源于自身需求的感知系统而让传播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效,同时也对当下展示环境空间的设计、展陈布置、主题思想提出更高的要求。 只有富有节奏感和趣味性的在场感受,才会给观众一个乐于接受和反馈的机制,为展览学科营造良好的传播媒介、提供可靠的实践数据。 通过展示界面和建立认知地图,展览信息能顺利地到达“人”的联系中,获取展览实践的本质,真正体现展览营造中的“以人为本”。
三、展览感知测量
人在感知展览的行径中,会随时空的转移调度与展览感受相对应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体感以及触感等多方位的感官发动。 在不同的展览类型和时空体量中,人的这些身体感知会有前后次序、数量丰简、频次峰值等不同状态的呈现。 “对曾经真实地感知到的某个客体的那些痕迹性记忆,不仅包括对该客体的感觉方面的记录,如颜色、形状或声音,而且包括对动作调节的记录,这些动作调节必然伴随着感觉信号的收集;另外,这些记忆还包含着对该客体的必然的情绪反应的记录。 因此,当我们回忆一个客体的时候,当我们允许这些痕迹把它们内隐的信息变成外显的时候,我们提取的不仅是感觉数据,而且还有相应的运动和情绪数据。 当我们回忆一个客体的时候,我们回忆的不仅是一个实际客体的感觉特点,而且是有机体对该客体的过去反应。”[15](P124)
展览展示中有很多丰富细微的媒质材料,在各种多样的空间和时间组织下成为“形态序列”,通过人的感知,一点点、一步步的探查,其信息经过组织收集、筛选被判断为某种感受或感觉。 它们沉湎于形状、色彩、运动、声音等媒介和场地上,交换吸收,推理思索。 一个展览展示的空间在美学意义上的测量,唯一的尺度就是人,人的身体是一台“同时”扫描“空间可感可现可触事物的各项的数量与指数”的仪器。 通往大脑的感受纤维高速运转,起承转合,梳理记录,多样且交叉地传递一种稳定的信息流,混合着记忆线索,为展览展示行为生成直接而有力的引导。 作为言语和表达的身体,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体感和触感多维共振,可知的、未知的习惯规律,如同获得一个崭新的文化场,汇聚杂陈、引发释放的视听、五味、色触阈值和编码如同隐性的化学方程式,调剂着各种场次的呈现。 17 世纪,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r)清楚地预见了这一点。 他在《显微术》(1665)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关于感官,我们接下来要关心的是如何用工具来弥补它们的不足,就是说要为人体加装人工器官……既然眼镜已经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视力,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我们需要用很多机械发明来改进我们其他的感官功能——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16](P35)
在展览的指示下,观看的物质实践再造了另一个抽象的眼睛,疏离运动物质时刻,施展个人审视世界的特权。 “身体被缩减为其光学解剖构造,也就是单孔透视的最小认知图式(这一点在贡布里希、阿尔伯蒂或菜奥纳多那里都是一样的)。 在这一奠基性的感知中,画家的凝视将现象的变化截断,在被揭示的在场的永恒瞬间中,从时间的流动之外的有利位置观照视野中的景物;而在观看的时间中,观看的主体将他的凝视与奠基性的感知融合为一,成为最初顿悟的完美再现。 对指示的历时运动的删除创造出——或至少是试图寻找——一个共时的观看,这一共时的观看将把身体和瞥见隐藏在一个无限延伸的将影像作为纯粹理念的凝视中。”[17](P129)
视知觉是高度清晰的媒介。 现代社会中的工具属性和媒介意义,以及展示设计观念中的强秩序性和服务型特点在当下展览语境下越来越明显。赫伯特·拜耶(Herbert Bayer)通过《视野的图解》《360 度视野的图解》,以“视野”理论建构起了展览视知觉的基本逻辑,并以此成功地设计了巴黎装饰艺术家沙龙展德国展区第五展室、“胜利之路”展等重要展览。 这为我们重估和反思现代展览展示的视知觉价值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一种崭新的“晦涩”与“混沌”并存的视觉语言从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并且溢出野性设计的思维观念。 当下美术馆的展示实体最终是以“可知觉”的状态面对观众。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的视知觉理论建立在格式塔现代心理学的实验基础之上,认为知觉是艺术思维的基础,并由此提出了“张力”说。 他认为力的结构是艺术表现的基础,而“同形”是艺术的本质。 人们源自内心体验的审美是基于生理条件与之相应的视觉构成。 聚焦和捕捉,扫视与跟踪,在展览营造的时序运动中,人的感知觉察、识别明暗、方位、图像、形状等视知觉系统,为其高效呈现与转换提供了基本属性和过程。 要营造“美”,把无形的东西变成“可视”的,就必须选择和组织视知觉活动,描绘或呈现这一基本功能。 在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的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窗户出现在画面当中。 对于怀斯来说,“窗”是他基本框架展开的经典构图形式,是显示他清冷哀愁、连接世界的意象媒介。 “窗”充当了情感传递的工具和叙述故事的角色,画家笔下的线条和油彩从窗中慢慢飘散,十分静谧,静谧得像一个肃穆的梦境。 在其生活的环境里,他积累了大量视知觉素材,并清晰地感受、捕捉并描绘萧索而又宁静的感觉,把生活中常见的场景画成一首首发散着忧愁的诗歌,萧索、缓慢、安静、不忍打扰,这就是艺术家制作“美”的手段和状态,用以表现自我心灵深处的记忆与情感,这种视觉营造了一种冰冷颓靡的建筑上罩染了一层灵魂温度的经典画面。 人们正是在视觉呈现的内容和表达之间“观照”艺术意象视觉思维的痕迹。 在理论层次上,艺术的再现被当作一个感知对应的过程,称之为模仿(mimesis)。 “模仿观念可以被理解为在此过程中影像在不同的成功或失败的程度上与特定先在现实相契合。 这也是一个把感知材料从信息源,通过被各种(或许衰减)层次的‘噪音’干扰的渠道,朝着一个在理想条件下将复制并再次体验感知材料的接收点传递的传输模型。这个模型本身似乎并不在意这先在材料是毫无疑问地由经验感的数据构成,还是来自一个并无客观对应物的非经验‘ 阈’。 只要原初的视像(vision)——无论其本质是什么——被传递,那么模仿的条件就已然被满足了。 模仿论因此可以被总结为一个词——识认(recognition)。”[18](P54-55)在展览现场,人通过眼睛观察将展览环境中的无穷无尽的形状和颜色传递给有识别能力的大脑,并与展览空间和物件组织视觉反应,捕获形状和纹理、大小和距离、明度和光度、颜色和运动等信息互动。 视知觉是展览现场起支配作用的感官系统,展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视觉艺术的策划与传播,人的展览感知从视知觉系统起步,为空间信息提取无限的空间线索和画面知觉。 “而对一幅绘画来说,要想对人的心灵有所触动,首先必须向眼睛做出清晰的呈现。”[19](P327)从古典绘画到当代艺术,艺术家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形式各异、多元丰富的艺术视知觉形式,从最初的绘画、雕塑,到如今技术革新下的影像、装置和观念艺术,努力让艺术视知觉呈现出某种“画面”。 这种视知觉界面来源于文化的、时间的、地理的、生命的各种主题的叠加回忆或是纪念警醒,此界面所生产的展品顺序、空间度量、展览体积等秩序,可以激起观众感官和情绪获得精神渴望或是个体经验的思考。 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传统意义上的视觉艺术边界不断被打破、扩张,不断延续物质领域的精神潜意识和特定精神内核,也成为当代艺术的灵魂所在。 眼睛的感受传递给身体的感知机制,是一种赋予了时空回想、生命态度和尊严的仪式感,正如西班牙当代艺术家安东尼·塔皮埃斯(Antoni Tapies)对自己的创作所言:“给平庸的东西以威严,给日常的现实以神秘。”塔皮埃斯惯用的创作题材很多都是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微小元素甚至是废弃物,把一些废床单、绳子、水泥……用清漆、乳胶、颜料等堆积,反复表现空缺的人体局部以及旷远的断壁残垣。 这种几乎被抹掉了的环境记忆和被夸大了的微小之物,在陈旧和撕痕的大幅色块和毛发般的勾勒笔触下,用艺术家自己的理解就是把最接近哲学思维的大地颜色,融汇他的历史观照和思考传达现实语境的使命与形式。
在文本叙事转向场景叙事的艺术实践和艺术展览语境下,行业虽无意达成某种艺术视觉运动的共识,不过当下展览展示对于跃入眼帘的第一感知——“视觉感受力”的兴趣倾向还是比较明显。如何让观众与作品对话,如何体味画面或作品的形式语言,如何深度感知作品的符号解读和发现欲望,为了强化这样的“视觉感受力”,各种创作手段、表现手法以及新媒体艺术、装置艺术的国际对话、交流重组层出不穷。 在全球化背景的文化大时代,“身体力行”的参与是塑造展览展示开放形态和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生产的创作环节需要深刻的反观和探索“观念表达”的身体感知,艺术展览的展示则需要建立深刻感受力的精神通道,呈现展览本身“智”与“域”的有机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