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释“笑”:从青年到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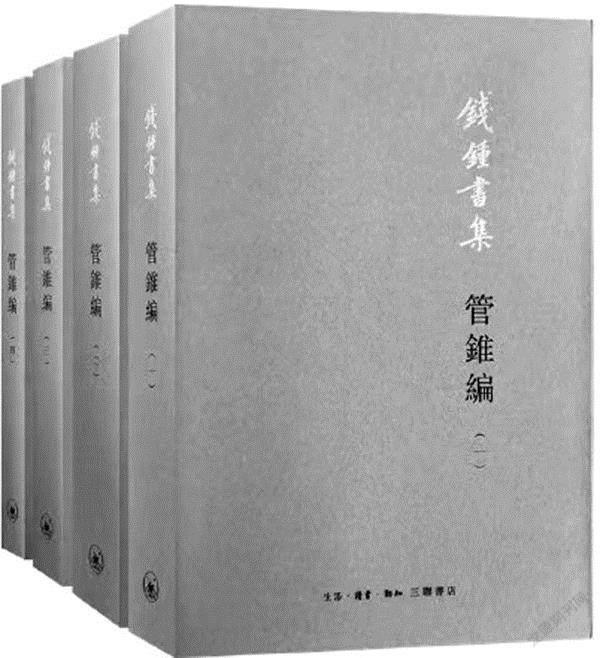
无论自觉与否,每个人都依据其內在尺度来体认自己活得怎样。差别仅在体认程度:要么“或深或浅”;要么“或明或暗”。
人作为价值动物,又以表情(脸色、眼神)来流露心绪或心境。“笑”是表征他体味快乐;“哭”是宣泄内心苦痛;“哭笑不得”“啼笑皆非”则标识其心理尴尬,左右为难,里外顿挫。
名门出身、禀赋迥异的钱锺书19岁考取清华本科后便名满京华,校长青睐,名师夸耀,其年轻时的两篇随笔《论快乐》《说笑》也写得才情飞扬,宛如阳光灿灿在青春脸庞。钱锺书晚年撰《管锥编》释“不亵不笑”也带“笑”字(时62—65岁),则与青年时释“笑”,同中有异,其味不薄。
乍看这是“朝花夕拾”。细读则不尽然,一朵由柔柔的脸部线条描出的青春微笑纵然灿若夏花,阔别卅年后再凝眸,不免染上沧桑。依此再去体悟黑格尔的箴言,说一个青年人对某成语的语义解读即使不错,总不如饱经风霜者能从中嚼出更广袤的意味。事情正如此。
青年钱锺书(以下简称“钱”)释“快乐与笑”,要点有四。
要点一,“快乐”即“快活”,愉悦让人觉得日子过得飞快,所谓“欢娱嫌夜短”;相反“一到困苦无聊,愈觉得日脚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别慢”,所谓“度日如年”,故钱读到《西游记》那句话“天上一日,下界一年”,会感慨这八字其实折射出某种人类想象:“天上比人间舒服欢乐,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间一年在天上只当一日过。从此类推,地狱里比人间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难度。”①
要点二,人的快乐蕴涵精神性即价值性,以此与“快乐的猪”划出异质边界。“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看见的。”②但钱坚执人的快乐不宜单纯得像猪一般植根于物欲之满足,比如“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乐,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筵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灵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的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怍”③。
钱说,一俟“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或“偏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赔偿”④。
钱按,“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但是谁知道他不也是个大傻子?”“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⑤。
要点三,着意于“幽默与笑”之关系,幽默可用笑来表现,然笑未必等同幽默。两者之差别,是笑纯属个体即兴,不宜被社会提倡,而幽默似已在被提倡。听得出此话中有话,钱年轻时对林语堂1932年主编《论语》《宇宙风》提倡“幽默”颇有异议(时钱22岁)。其理由是“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泛到口角边”⑥,此即纯属个体即兴,自由得、无拘无束得像天空之闪电。钱说:“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柏格森《笑论》(Le Rire)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情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Le mécanique sur le vivant)。”⑦
要点四,幽默不宜被提倡为社会(群体)选项,否则“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⑧。钱这般比较幽默有“真—伪”之别:
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和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有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绝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⑨
上述四点所贯穿的释“笑”青春版之特点,若曰满是咄咄逼人的才子英气;那么,《管锥编》释“笑”之晚年版则如老骥伏枥,但又巨匠肝胆沛然而未逊岁月,其差别仅在晚年版愈发沉潜若渊,大凡深读者皆可从这古雅文言中隐约耳闻某种时断时续、若有若无、懑雷般的“大音希声”。若就释“笑”的意蕴而言,晚年版与青年版无疑血脉归一;但就述学语式而言,则《管锥编》是将著者早年释“笑”的青翠嫩芽嫁接到苍苔斑驳的国故老根上了,反倒长得愈发气象苍郁,横空蔽地。
首先,针对青年版释“笑”本当蕴涵、有待发皇的第一悬疑,即人追求有品位的快乐迥异于“快乐的猪”缘由何在?《管锥编》竟将此青春悬疑之芽嫁接到距今近2500年《列子·杨朱篇》的“贵身论”古树上了。
《列子》借讬杨朱,说了好多上古哲贤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重点有两。一曰“贵以身为天下”,普天下没有比鲜活的个体生命更珍贵了,若“左手揽天下之图书,右手刭其喉,虽愚夫不为”⑩。二曰人欲活得快乐,除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还须享有名声,“令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尊荣则逸乐,卑辱则忧苦”,但又须有分寸,讲究度,切忌走向反面,千万不宜因“守名而累实”;“彼曲学枉道以致富贵,甚至败名失节以保首领,皆冥契于不‘累实之旨,谓为《列子》之教外别传可矣”11。
但症结还在于,当钱将“有品位的快乐”这一青春嫩芽嫁接到国故老根上时,竟刺激《管锥编》对古老“贵身论”萌生了新见解(宛如嫩芽抽出翠枝)。要害是在钱并不服膺《孟子》所谓“杨朱为我”,以及《淮南子》所谓“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之千古定论;相反,钱认为:“身体为‘我之质,形骸为‘性之本,然而‘我不限于身体,‘性不尽为形骸”12。既然言及“人所以为人”这一根本,就不必规避“人是会害羞的动物”这一道德原点。故大凡君子或很想当君子的人,“苟疾苦而不至危殆,贫乏而未及冻馁,险急而尚非朝不保夕,乃至出息不保还息,则所‘全之‘性、所‘为之‘我,必超溢形骸身体,而‘名其首务也”。诚然,此“‘名非必令闻广誉、口碑笔钺也,即‘人将谓我何而已”13。
这就启示后学,能有效区别“君子—痞子”的道德界限,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君子务必在乎自己在公众眼中不失人的模样;痞子则几不在乎自己在公众眼中的猴模狗样。这就迹近流氓的“无家无业无操守”。简言之,在钱看来,一个君子若真“贵身”,除“爱身惜生之外而复好‘名(approbativeness),此人之大异乎禽兽者也(the differentia of man par excellence)”14。《管锥编》依此在人类“有品位的快乐”与“快乐的猪”之间划了一道界线。
假定猪自有“猪的快乐”,然猪肯定不像人那般在意“有品位的快乐”,这又为何?这拟是青春版释“笑”本当蕴有、亦待发皇的第二悬疑,《管锥编》同样将此疑惑之芽嫁接到古籍之树,让古贤来回答。其聚焦点,当在人类比其他动物更珍惜每一个体生命的存在质量,因为热爱生命,故苦人生短促。《管锥编》辑集历代诗贤在此案留下的金句格言,熟门熟路得如数家珍:比如《北齐书·恩倖传》和士开所谓“即是一日快活抵千年”;又如仲长统《昌言·理乱篇》:“夫乱世长而化世短”;再如张华《情诗》:“居欢愒夜促,在戚怨宵长”;刘禹锡《问大钧赋》:“望所未至,谓予舒舒;欲其久留,谓我瞥如”;王建《将归故山留别杜侍御》:“沉沉百忧中,一日如一生”;《竹庄诗话》卷一八引许彦国《长夜吟》:“南邻灯火冷,三起愁夜永;北邻歌未终,已经初日红。不知昼夜谁主管,一种春宵有长短。”15最极而言之者,莫过于《管錐编》卷五所补订的《阿离念弥经》:“百岁之中,夜卧除五十岁,为婴儿时除十岁,病时除十岁,管忧家事及余事除二十岁。人寿百岁,才得十岁乐耳。”16钱按,“与《列子》语尤类”17。
或许,青春版释“笑”最亟待《管锥编》发皇的第三悬疑,是征答“不亵不笑”何谓?而欲探究“不亵不笑”之本意,又须先做如下两题:第一,为何说“突梯”即“滑稽”?第二,为何说“去级泯等”之“滑稽”,是旨在消解宗法“名教”对个体人格独立的心理束缚?
那么,名教之“名”与《管锥编》所强调、君子“贵身”须在乎的“人将谓我何”之“名”,有区别么?区别有三。其一,君子之“名”全系道德主体的自由选择、自励自律;名教之“名”,则是宗法秩序从外部加诸于个体的“角色”名分。其二,君子之“名”是主体对自身日常行为的自觉导向,除却内在良知,不顺从体外权威意志来诱迫自我“何者须为”“何者不为”;名教之“名”当相反。其三,君子之“名”对主体身心之价值召唤,唯求心安,无愧无怍地俯仰天地,坦荡一生,昭若日月;名教之“名”则是由体制化奖罚来驱动,无非“买卖”,“学得文与武,贷于帝王家”这十字,已将名教(“以名为教”)的功利实质说到骨子里了。“名教”方程式即此:你想从现行体制觅得功名利么?你务必先将“人所以为人”的独立、自由、尊严让渡给体制。如此“以名为教”“教化天下”,何愁天下英士不被体制收罗网中呢?
《管锥编》一针见血:“盖‘正名乃为政之常事、立法之先务,特可名非常名耳。名虽虚乎,却有实用而着实效,治国化俗,资以为利。《商君书·算地》:‘夫治国者,能尽地大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主操名利之柄。守‘名器,争‘名义、区‘名分,设‘名位,倡‘名节,一以贯之,曰‘名教而已矣。”18
亦正缘于名教之“名”植根于“利”(今谓“实惠”),古贤早已警示“其弊必至于末伪”19(东晋隐士戴逵《放达为非道论》)。“伪”即装模作样:公共场合人模人样;私下场合鸡模狗样。大凡“名教”教材无不注重“形象设计”:比如《礼记·表记》“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王藻》“君子之容舒迟: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论君子云:“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20
《管锥编》更在意孔子怎样面对如上“形象设计”:一方面《论语·学而》记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尧曰》记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述而》奖孔子之容止,亦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但另方面,《阳货》亦记孔子“莞尔而笑”,于子游有“前言戏之耳”之谑;《宪问》复载人传公叔文子“不言不笑”,孔子以为疑21。
孔子为何“疑”公叔文子“不笑不言”未必可取?《管锥编》巧妙地让韩愈来代言。钱认为韩愈颇解孔子之旨,韩愈《重答张籍书》云:“昔子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云:‘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即合并《阳货》及《淇奥》郑笺语意耳。钱又引韩愈《答张籍第一书》云:“吾子又讥吾与人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22
张籍讥韩愈“为无实驳杂之说”,无非韩愈作为中唐特立独行的诗人暨思想家深嗜传奇小说,其撰《毛颖传》亦属唐传奇一种,此谓“无实”;另,唐传奇就其文体而言分两类:一曰散文传奇,二曰诗性传奇如《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等。一篇之中,杂有诗歌散文诸体,引谓“驳杂”。韩愈予此“无实驳杂”有深嗜焉,有何可惊诧呢?这比终日沉迷酒色要高雅得多。此即“雅谑非虐”之旨:“谑—虐”之间有差距,何必因噎废食,将做人之持身谨重,迂腐地曲解成人的日常言行皆须“一本正经”得像正襟危坐,永远绷紧风纪扣的“标准像”呢?每个人本应有鲜活个性的生命样式,为何一纳入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宗法框架后,皆被铸压成不苟言笑的矜庄角色呢?
一味矜庄则近伪。“伪”至少可演绎两种情境:一是答而丢夫似的“伪君子”乐在其中;二是“伪君子”所主导的虚伪世风酷似阴霾会憋得“真君子”“透不过气”,于是也就逼得他不时想“滑稽”一番,此即《管锥编》颇欲笺释的“不亵不笑”。
《管锥编》引《金瓶梅》第六十七回温秀才云:“自古言:‘不亵不笑。”钱按,“不知其‘言何出,亦尚中笑理;古罗马诗人云:‘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此游戏诗中之金科玉律也”23(lex haec carminibus data est iocosis,/ne possint,nisi pruriant,iuyare)。欲解“不亵不笑”,要害在“亵”字何谓(“亵”何对象)。
《管锥编》是用“突梯滑稽”来回应这个“亵”字。钱认同“‘突‘滑、‘梯‘稽皆叠韵,‘突梯即‘滑稽也,变文以足句”之说法,且按,“‘突、破也,‘梯、阶也,去级泯等犹‘滑稽之‘乱碍除障,均化异为同,所谓‘谐合也”24。
钱强调“突梯滑稽”旨在“去级泯等”,其锋芒当是冲着宗法等级制而去。一拨拨“伪君子”既然是因依附宗法等级而得意得浑身油腻(不知今夕何夕),钱就要对症下药,宛若安徒生的无忌童言、说皇帝沒穿衣服一般,扒去“伪君子”的底裤,令众目睽睽顷刻爆发雷鸣般的嘲笑。“亵”字本含“体贴”“轻慢”“不恭”诸义。所谓“不亵不笑”,即指若不是不留情面地将“伪君子”演示的人性之陋曝光于天日之下,让其下不了台,有羞耻心的公众就没机会畅怀诽笑。
由此可鉴,“不亵不笑”所引爆的喜剧性诽笑,当比坊间因无聊而炮制的消遣性嬉笑,更蕴藉钱所会心的“笑理”。“笑理”有别于庸众寻开心时的“笑资”,因为前者蕴结着喜剧性诽笑所以饱含价值因子的审美机制,后者则不过是供庸众随机排遣所用。故当鲁迅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了给人看,这无形中是在为界定钱的“不亵不笑”提供参照——因为钱所青睐且擅场的“喜剧”恰恰相反,其特征是在剥去“伪价值”的内衣,体无完肤地戳穿了给人看,令公众在噙泪笑翻道德小丑之际,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人性之陋也有所警醒或涤荡。钱“不亵不笑”的价值底蕴在此。
以此为视角,重温莫里哀《伪君子》剧中的答尔丢夫,或钱为何雅谑其《围城》角色鲍小姐为“赤裸的真理”,也就怕将莞尔得更具深味。
【注释】
①②③④⑤钱锺书:《论快乐》,载《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9、21、21、21-22、22页。
⑥⑦⑧⑨钱锺书:《说笑》,载《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24、24、24、24-25页。
⑩111213141524钱锺书:《管锥编》卷二,中华书局,1994,第516、518、519、519、519、671、626页。
1617钱锺书:《管锥编》卷五,中华书局,1994,第172、172页。
1819钱锺书:《管锥编》卷四,中华书局,1994,第1247、1245页。
202122钱锺书:《管锥编》卷一,中华书局,1994,第91、91、92页。
23钱锺书:《管锥编》卷三,中华书局,1994,第1143页。
(夏中义,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王弼名教思想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