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茹与“新南方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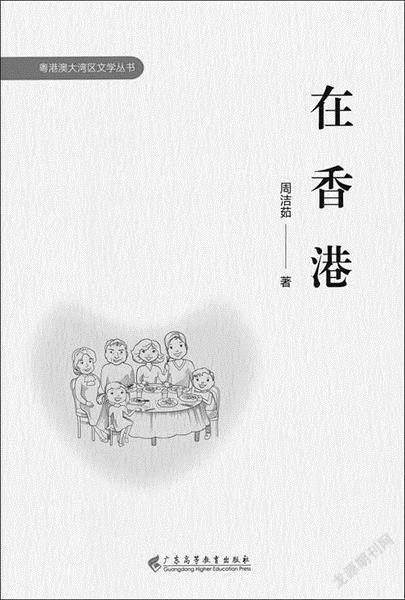
从20世纪90年代出道至今,周洁茹的作品给人一种强烈的空间感。尤其是她的城市小说,地理概念一直是最重要的部分,这似乎与她本人的旅居轨迹相关。据此,我们可绘就一幅文学创作地理图,以见证她从成名、离开到最后回归的游牧之旅。接近十年的美国经历,也使她的作品多了一层世界意识。一直流浪与漂泊,艰难地寻找存在的意义,最后将香港作为回归落脚点,也是她以“他者化”视角来观察世界的选择,以解域化思维和跨界身份对人性做深入地挖掘和思考。而支撑她走过一段又一段的人生旅程,便是爱。2015年是她正式“回归”文坛写作之年,开启了“新移民”系列,在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她也逐渐对香港产生认同感。香港在她生活第八个年头后正式成为心中的“这里”,对香港的融入使得她的写作精神和文本审美呈现出不少“新南方写作”的特质。2019年出版的散文集《在香港》,从一个“在”字可读出她本人对漫游者身份的确认,也可看出她重新出发的渴望,让我们见证这位当年的“美女作家”已转型成为“新南方作家”。
一、周洁茹与“新南方写作”的缘起
周洁茹出生在常州,位处江南地区。古时的“南方”基本指的就是江南一带,因江南长期处于文坛中心。在世界性的视野中,“南方”呈现的是复数性和混杂性特征,比较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的南方作家流派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现象等。近几年,国内各种期刊相继推出“新南方写作”评论专辑。“新南方写作”逐渐变成一个自觉的学术概念,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从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三个方面对这一概念做了定位和理论上的阐释。杨庆祥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范围定为“南方以南”,也就是: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①。无独有偶,周洁茹搬回离父母(或家乡常州)距离更近的香港,情感上希望“近一点点”。至于为什么选择香港?在一次访谈中,她是这样提到的:“我停留在香港,大概也是因为香港最后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美好的东西,而且香港一直在很努力地保护着这些东西。香港作家们的架构可能都是松散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混来混去,大家都要谋自己的生,以写作之外的方式。写作成为真正干净的一件事情。”②周洁茹用“停留”二字,实际上说明她对融入并没有很刻意,只是用一种“旅行者”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哪里觉得适合了就选择哪里,比较在意的还是拓展自己、自由写作并回归自己的内心。与此同时,环境对于她来说也不是特别重要,她曾用“流动的风”来形容自己与环境的关系③。刚开始,香港于她而言只是过渡之处,是她人生历程中的“中转站”,没想到停留了将尽八年后,香港正式成为“这里”,也是她承认已“在”的地理坐标。
周洁茹曾写过系列以“到……去”为题名的小说。表面上给人作为漫游者的周洁茹在确认方向乃至追求“寻找”本身的印象,但实际上聚焦的是在路上“来回”的没有安全感本身。没有去的地方而要“去”,不談“在”某个地方,因为一旦“在”,作家的在地感会很强烈。但周洁茹很少用“在”,从而提醒她需要改换生活地方之时,她的方向往何处前行,最终到达何处。在她的小说中,最重要的就是写与父母关系的小说。她没有办法陪伴在父母身边,所以与父辈间形成了很大的“距离”。而这个“距离”,只能通过作品拉近。比如《到深圳去》,让我们看到作为孩子的“我”,为了给父母寄行李,历经多重困窘艰辛,终于顺利过关到深圳,最后发出“好了!这不要紧了”④的释怀,让读者的心头大石放下,爱的力量油然而生。故乡对于周洁茹而言,是回不去的“家”,可她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活下去,直到回到故乡”⑤,这也是她永远要“去”的方向和目的地。
正因为周洁茹在写作中不会过多考虑自己与周围人和环境的关联,所以她的写作不会有太多的束缚,语言随着感觉和心灵一同呈现,没有太多的刻意雕琢,或为了谁而写作。虽然周洁茹的内心有向着父母的“北望”情结,但她的写作却不会“北望”,而是诚实的“向南方”,也就是立足当下生活的现实和人性的变化,回归自己真诚的内心,表现出一种叙事主体和叙事精神的独立,从而以自身写作的独特性来影响香港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她曾经说过:“如果我写的什么也能够让你哭,肯定是因为我不在高处也不在故意的低处,任何一个站在旁边的位置,我在里面,我写我们,我不写你们。如果我要写你们,我会告诉你。尊重他人的生存方式才能够得到你自己的尊重。诚实是写作的基本条件,如今都很少见了。”⑥诚实地面对写作与人生,是她的“新南方写作”的重要方向。
曾经大红大紫的周洁茹,看到“繁华将要落尽”的写作事业,便毅然决定离开中国,去一个能让她做出“不能写”理由的美国展开生活。十多年后,当她回来重新写作时,她已不再执着于“转身时的华丽”,而是用实际行动面对某些质疑的声音,即作品语言的过时。这种质疑使周洁茹非常愤怒,亦使她认识到回来写作的艰难,并持续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写下去。这种内心的叩问给了她前行的勇气和力量,鼓励自己“不过是多一倍的努力,我还活着,就接得回来”⑦。另一方面,支持她前行的理由,肯定是爱,来自父母的期许和爱,她十分同意齐邦媛对故乡的看法,因为“唯一还会爱我,对我有期许的,当然是父母”⑧。在香港的生活,也让她产生书写香港的想法,尽管她坚持的只是在香港写小说,而不是写香港小说,写作的方向仍然朝向故乡。至于写作的状态,她是期盼能“独立写作,内心自由”⑨,因自己是一个不属于地球的“飞来飞去”的流浪者。这种流浪游牧的精神属性正如评论者马兵所言,是与香港这座城市相洽的,而每篇标识出地名的小说,则显现出“她对空间的敏感和对空间所表征的政治文化身份的多重指涉意义的敏感”⑩。在她的心里,即使未能完全融入香港,也仍然不妨碍读者对她笔下“香港”的理解,即颓废色彩浓重的人间风情之地11。无论书写哪个地域的小说,都离不开对“人”的书写,不会因香港的地方性差异所在而忽略了对普遍性意义的理解。周洁茹的创作谈《在香港写小说》已显现出世界性的视野:“我写了香港人的生活状态。就冷漠到残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一点确实也是没有地域的界限的。所以对于我来说,香港人也是人,香港小说,其实也就是人的小说。”12实际上,周洁茹对大城市没有太多好感,在她的印象中只有生活过的小城常州是最亲切可爱的,但随着逐步融入香港生活,她意识到不管承认不承认,自己真的是“在”里面了。既然已“在”香港,总得还是要活下去,这促使周洁茹重新思考写作和生活,并将这些思考形成散文集《在香港》。
二、《在香港》与“在香港”写作
周洁茹作品众多,但在内心里,有一个信念始终支撑她前行,那就是:生活永远比写作重要13。因此,无论读她的小说还是散文,都会感受到发自她扎根生活后流露的“真情实感”。这种被评论者蔡益怀高度评价的“锐气和灵敏的触觉”14,使她碰触到生活的细节,进而书写这座城市的“华丽与苍凉”。这种书写生活的真情实感同样表达在新近散文集《在香港》。
《在香港》涵盖了四个专辑,分别是故乡、香港、写作、问答。收录在内的文章的时间跨度超过二十年,其中后两辑把写作和访谈的时间均标识出来,内容先后触及父母亲情、香港生活、创作谈以及访谈录等,可谓是周洁茹从出道至今思考人生和写作的时空集大成者。书名“在香港”给人颇有意味之感,初读题目以为全书贯穿的是周洁茹书写香港的内容,实际上是周洁茹在香港书写并思考人生,同时投射了她的“香港视角”。虽然这种视角被不少本地人认为是外来者而欠缺他们熟悉的“香港味”,但周洁茹不在意这些观点,而是持续她的本真写作。细心观察会发现,周洁茹更多地在散文抒发她对香港的感受,并得到她生活中的朋友的认可。对此,她曾做过一番解析:“散文就是生活……他们都是真正生活在香港的人,散文里出现的字、场景,都是他们每天要过的生活,真正的生活。”15重新回归写作的时候,她深知重启主业的艰难,也不无焦虑,可此时依旧没有忘记最重要的是生活,便写了很多散文,从中调整自己的写作状态。
香港生活节奏快,地方文化精神的传承在全球化语境下面临断裂的危机,对资本成长的追逐构成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周洁茹也不能置身事外,身份焦虑的事实同样发生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即使她一直觉得自己不属于地方。她的流浪情结甚深,所以更愿意做移居作家而不是移民作家。在这种情结的影响下,周洁茹选择“在香港”回望故乡和美国生活的点滴,与两地均形成若即若离感,成为她散文写作的特色所在。尤其在美国,她是没有办法写作的,但让她觉得神奇的是,离开美国后有了书写美国的动力。这种“不即不离”的返乡姿态,引发了评论者陈培浩进一步的思考:漂泊者该站在哪里,异乡人如何重建故乡?16这也就归结到中国文学史上的“家园”母题。
反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家园”母题,可以看到它既是对古代文学“家园”母题的继承,同时又具有开创性。这种开创性不仅可弥补文学史书写的不足,而且也可重构文学史上一些传统母题的模式以及深化其意义。“家园”一词在汉语中原本是对出生和栖居之地的经验性表达,它寄寓着熟识、亲近、眷恋、舒适等情感性因素,诱发着人的乡情、亲情和思乡感、归家感17。海德格尔诗学中的“家园”充满了诸多形而上的意味,如“接近源泉之地”“接近极乐的那一点”,且与“存在的敞开”“诗意地栖居”“澄明之境”等相联系。他认为家园(源自荷尔德林的名诗《返乡——致亲人》)“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18。因此,“家园”的内涵既包括出生和栖居之地的地理要素,也包括人们追求回归心灵原乡的精神要素。现代人对“家园”的阐释更接近于海德格尔的阐释,隐含着对人文家园守望的形而上意义。由此,对“家园”意义的追寻实际上也与人类对三大哲学难题的终极追问是一致的,那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对于周洁茹而言,眼中的“家园”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变迁,在无法真正“回归”的情况下,她选择用文字来建立精神原乡。
实际上,随着在香港的落地生根,香港也已经慢慢成为她心中的“此岸”而非“彼岸”。那么她是如何走进香港?对此她曾道出三句“真言”:生活在香港,对香港有感情,写作香港19。三个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活在香港”,只有“在”才会将所发现和观察的变成日常生活。因此,《在香港》的散文给我们亲切有爱的生活感,便源于此。
在“故乡”一辑里,周洁茹用“食物”缓缓带出故乡的“味道”。这种“味道”,包含对父亲身体逐渐变差的难受和痛楚(《父亲瘦了》《我以为我再也不会笑了》)、回味家乡食物的味道(《故乡的食物》《鱼片干》《萨其马》等)、自身曾与故乡或美国食物发生关联的回忆(《水煮鱼》《一个人的串串》《三丝鱼卷》《砂锅鱼头》等)以及当下在香港与食物发生关系的事件(《龙华酒店》《金雀餐厅》《冒菜》《食物与人生》等)等。酸甜苦辣滋味尽在其中,包括:有无法陪伴在双亲身边的无奈与痛楚、有青少年时期自由自在的生活气息、有长大回乡后品尝食物的孤独,更有在香港生活的各种喜怒哀乐等。五味杂陈,尽在这一辑得以展现。面对一系列的变化乃至于挫折,周洁茹并没有失去信心,而是相信总有一天会迎来希望。我们可从最后一篇《我以为我再也不会笑了》见证新生,“活下去”成为周洁茹在“故乡”一辑的关键词。只有念念不忘,她才能最终回到心中的“故乡”。
与其对应的“香港”一辑里,在地感颇为显明,世事变迁与人情世故两个主题在周洁茹的笔下慢慢流淌出来,耐人寻味。安排在该辑第一篇章的作品为《乌溪沙》,也是周洁茹在香港最喜欢的地方,因为这里带给她的不是“全香港最浪漫观赏夕阳的海滩”之感,而是對那段越南船民逃难史的诸多思考:逃难的船民“为什么离开家乡,为了更好的生活?你梦想的生活?很多人的离开,只是要活下去”20,给香港这一“迁徙之城”做了历史的注脚。半世纪后的香港,是否同样生活着一批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背井离乡之人?这些问题引人深思,历史感油然而生。收录在这一辑的其他篇章同样使人陷入对当下香港现状的思考,包含对某些人的生存现状描画(《利安邨的空姐》《利安邨的疯子》等)、也有对香港人际交往暖心情谊的流露(《香港的人》《香港服务》等)以及对近些年高涨的“本土意识”(《九龙湾》《马铁》《大围有个火锅店》等)。此外,不少篇章还涉及香港本地高效率的生活节奏及其对人日常的影响等,尤其是“语言”的使用牵连到背后的国际政治问题,描写了不少内地人在香港生活的无奈和压抑,让人唏嘘。然而,再不顺心也依旧需要过衣食住行的日子,所以在本辑的最后一篇《我有两条路》,周洁茹描画了普通人一天的日常,“高速而又不失秩序”成为港人典型的生活气质。在这一辑里,周洁茹从自身的经历回顾历史、反观当下并关联世界,思考的格局由此展开,“地方性”和“世界性”在此得以体现。
从前两辑可以看到,周洁茹并没有完全被环境牵制,而是放慢脚步,思考人生的来处,用心体悟城市种种细微的众生相。后两辑“写作”和“问答”则与前两辑形成呼应,分别由创作谈和访谈录构成。这不仅道出她二十多年的写作心路历程,也对自己“在香港”的回归之旅做了总结与展望。
周洁茹系统写作中断十余年,但创作谈是没有中断的,记录着她心里的诸多起伏与纠结。尤其对于“为什么写作”这件事,通过创作谈可以看得出她在近二十多年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在2017年的创作谈里,她总结了这段心路历程:“这个为什么,简直纠缠了我的整个人生,二十一岁说我写是因为我孤单,二十二岁说我写是因为我不自由,二十三岁说我写是因为爱,二十四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三十五岁,直到三十九岁再回来说,我写是因为爱。”21从视线只有“我”到逐步扩展至世界,人生经历的沉淀使她更为懂得“推己及人”的意涵。而收录在第三辑的最后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写散文(2019)》似乎给自己的创作留下阶段性总结,探讨的正是散文写作的目的所在。在周洁茹看来,写散文有两个原因:一是经常将小说和散文的语言倒过来写,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把小说写舒服了,散文写痛苦了”22,可以使自己在慢节奏呼吸中安静下来;二是让自己回到本真和自由的写作,而周洁茹判断文学的优秀标准正是自由。在香港如此高效率节奏的生活中,历经岁月淘洗的周洁茹能够学习调整自己的写作心境,实属不易。
如果说“写作”专辑更多涉及周洁茹的创作自述,那么“问答”专辑则是在此基础上做更多维度的拓展。该辑谈论的内容广泛,涵盖家乡、香港、工作、阅读、电影、音乐、写作等,而谈论“生活”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从多个方面回应了前面几个专辑,让我们对周洁茹的为人为文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比如对前面创作谈中提到的写作与生活之关系,周洁茹在访谈中做了回应:“不迎合,不抗拒,没有欣喜,也不必悲伤。我只写我想写的。”23然而,这并不妨碍她投入生活的洪流中,即使看似平静的文字依然有着浓郁的情感,因为她深信“我们当然是我们生活的参与者”24。在她看来,生活就是修行。修行并不一定要“走万里路”,而在小空间反思自我也是可以的。对于这类修行的人,周洁茹认为他们会时常思考“人是什么?生活是什么?为什么和为什么?都没有答案”。这是由于人的局限所致,但也算是有进修的心。另一方面,生活范围离不开所居住之地香港。前面三辑周洁茹以各种方式诉说了自己与香港的关系。在访谈录里,周洁茹用“寄居蟹”的心态做了形象比喻,而且如有来世绝不再做,由此可以回应前文提到的“流浪者”的心境。事实上,访谈录已成为对周洁茹创作最好的回应,而且充满哲理思考。对于读者普遍提到的问题,周洁茹在该辑最后做了“自问自答”。以一种朴实真诚的姿态面对读者,更为重要的是,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
由此可见,周洁茹的《在香港》站在香港回望故乡、立足当下,用文学审美方式描绘独特的个人体验,在尝尽人生百态的生活后,将人情冷暖缓缓道出。不管是家乡常州,还是美国或香港,它们之于周洁茹都是“他者”。然而,这种“他者”眼光并不影响周洁茹与这些地方的互动,反而因写作背后有“人”的存在,使得她的“新南方写作”有了更多反思的姿态,并在各个地方的互动写作中有了“世界性”的品质。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写作未来可期的方向。
三、《在香港》的地方性与世界性
相较于北方,中国南方的面积不算辽阔,但人文特征差异较大,文学创作风格驳杂,呈现出多元化的写作气象,使“南方”在不断新变中得以再生。不少学者和作家也关注到这点,期盼“新南方写作”能有“质”的突破,体现新的高度和境界。其中,曾攀认为“新南方写作恰恰是重新融通并提供多元化的镜像,为‘南方复魅与赋型:边地充沛的野性及诡谲的景象、区域链条中文化的复杂联动、海洋文明的广博盛大、发展与开放并置的国际视野,由是引触新的融合及创造,在充满未来可能的衍生中,不断激发‘南方的新变、新义与新生”25。也有学者从语言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像杨庆祥从现代汉语写作层面对“新生”加以阐述,并认为:“因为现代汉语写作版图的扩大,它不仅仅面对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在不同的民族和區域间进行语言的旅行、流通和增殖,因此,它的主权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一性民族国家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主权)无法抵达的地方,汉语的主权却可以预先书写和确认。”26由此成就“新南方写作”最有意味的地方。此外,“新南方写作”的世界性也是其中的要义和使命所在,如朱山坡心中的“新南方写作”应是“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关心的是全人类,为全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和独特的个人体验”27。唐诗人也有类似的观点:“新南方写作”在突出“南方以南”因地域文化差异有着不同的故事内容的同时,更应该强调“南方以南”的文学经验蕴藏着何种世界性品质28。在此基础上,蒋述卓认为“新南方写作”应该要体现建基于未来性上的超越性,即它不能仅仅局限于地理、植物、食物、风俗与语言,而应该是在一种多元文化形态中形成观察世界的视角与表达方式,代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无穷探索29。
可见,在还未完全成型的批评话语“新南方写作”面前,学者和作家对它是充满期待的。杨庆祥文章最后一句的“时间开始了”,则是对这一概念在批评话语体系中的落实发出了呼告。实际上,周洁茹早已通过写作为“新南方写作”涂抹靓丽色彩。从前文对《在香港》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洁茹的写作虽不拘泥于地方,但用南方的视角不断书写流动的“世界”。至于语言问题,这是周洁茹最为看重的部分,也是她创作主要依靠的元素。无论是英文写作还是中文写作,她的语言都颇有个性,轻而不失透明、细碎与尖锐,没有北方作家创作时背负土地的沉重负担,体现了南方写作语言的特性所在。从《在香港》的各个专辑和篇章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篇章之间看似各自独立、互不相关,实则构成一个可以互相联动的整体。资深媒体人傅小平曾把周洁茹长篇小说里的每个篇章比喻成“一座座水汽氤氲的岛屿”,并“连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整体”,也就是说篇章之间的安排是充满内在节奏感的,刚好契合了她所身处充满诸多岛屿的香港地理环境。与此同时,她也是很重创作篇章内部结构之人。内在结构的布局同样与感觉和情绪相关,充满“水汽氤氲”的混沌气息,并不容易让人轻易分辨。可见,语言上的“轻”、结构上的“氤氲感”以及视野上的流动性构成了周洁茹“新南方写作”的三个重要特征。
这种“氤氲”的流动感与香港流徙空间相关,也與周洁茹长期关注新移民的身份认同话题有所关联。文学审美上偏向后现代风格,如同颜敏曾形容周洁茹的城市书写像一篇篇“浮城沙画记”,形成“具有辨识度的都市流离美学效应”30。然而,这种叙事审美模式更多偏向突显漂浮的叙事主体,背后的思想创造仍有可提升的空间。随着年月沉淀,周洁茹已逐步放慢自己的写作速度,开始向内看,并将更多的反思与内省划入人心。这一点,在2022年的散文新作《此间》31中得以充分展现。文章的点睛之笔在于周洁茹读到苏东坡的《记游松风亭》中发出的感慨“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时,瞬间深感身心轻松自在,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放慢速度寻觅,也契合了前文提到她的“生活永远比写作重要”的信念。
《在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丛书”的其中一种,颇有前瞻意味。香港文化作为大湾区文化主体一分子,也会影响文学发展的走向,因为这涉及大湾区文化共同体的互动范式,而其中的文学与文化关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蒋述卓和龙扬志作为丛书主编,在为丛书作序时也提到这点:“总是从具体的主体开始,而由地缘、文化甚至血缘所塑造的情感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区内在的凝聚力量,并强化为一种建立在‘交往基础之上的‘地域共同传统(area co-tradition)。”32实际上,这正呼应了前文提到的“新南方写作”的超越性和未来性所在。
周洁茹曾把自己的创作比喻为盖“房子”,那么这座房子未来呈现什么新的设计和布局,是否出现如刘俊所期待的“周洁茹风(气派)”的文学“房子”出现33?周洁茹的写作在大湾区发展下的前景,值得期待。
【注释】
①26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②曹瑛、王芫、周洁茹:《〈后来的房子〉及其他》,《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6期。
③沙丽、周洁茹:《我判断优秀只有一个标准》,《山西文学》2021年第6期。
④周洁茹:《吕贝卡与葛蕾丝》,海天出版社,2018,第124页。
⑤邵栋、湘湘:《后记:我们都是飞来飞去的》,载周洁茹《吕贝卡与葛蕾丝》,海天出版社,2018,第198页。
⑥13周洁茹、王小王:《它本来就是一个飞船——关于〈岛上蔷薇〉的对谈》,《作家》2016年第8期。
⑦周洁茹:《十年不创作谈》,《南方文学》2014年第8期。
⑧刘雅麒、周洁茹:《飞来飞去(2017)》,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330页。
⑨周洁茹:《我当我是去流浪(2015)》,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188页。
⑩马兵:《游牧者周洁茹——周洁茹香港小说读记》,《南方文坛》2016年第5期。
1112周洁茹:《在香港写小说(2015)》,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183-184、185页。
14蔡益怀:《周洁茹的“香港故事”》,《中华读书报》2017年11月1日。
15邵栋、周洁茹:《双城记(2017)》,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350页。
16陈培浩:《在香港,望故乡——读周洁茹散文集〈在香港〉》,载周洁茹《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10页。
17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7页。
18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15页。
19戴瑶琴:《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时代的作家——周洁茹访谈录》,《粤海风》2021年第5期。
20周洁茹:《乌溪沙》,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90页。
21周洁茹:《我们只写我们想写的(2017)》,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230页。
22周洁茹:《我们的香港(2017)》,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215页。
23李浩荣、周洁茹:《关于小说集〈香港公园〉(2017)》,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337页。
24杨晓帆、周洁茹:《我们当然是我们生活的参与者(2016)》,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323页。
25曾攀:《“南方”的复魅与赋型》,《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27朱山坡:《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异样的景观》,《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28唐诗人:《“新南方写作”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29日。
29蒋述卓:《南方意象、倾偈与生命之极的抵达——评林白的〈北流〉兼论新南方写作》,《南方文坛》2022年第2期。
30颜敏:《浮城沙画记——读周洁茹小说集〈美丽阁〉》,《文艺报》2022年1月21日。
31此文发表在《香港文学》2022年1月号。
32蒋述卓、龙扬志:《区域文学的共时呈现》,载周洁茹《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序言第9页。
33刘俊:《房间有了,房子还没盖好——论周洁茹的小说创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徐诗颖,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香港文学中的‘香港书写与岭南文化认同研究(1985—2017)”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CZW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