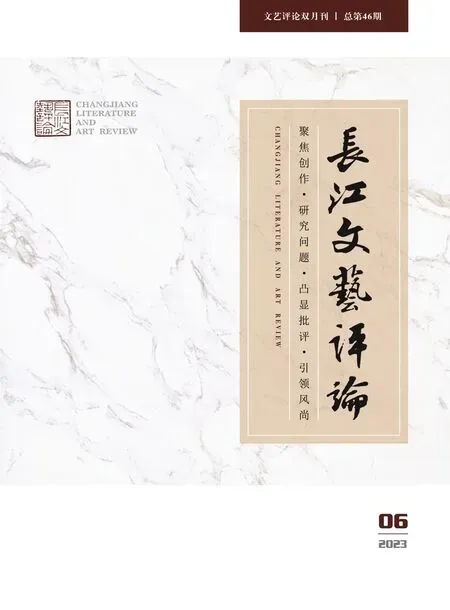论叶梅小说中的多元文化融通书写
◆张耀丹 钟进文
作为当代最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叶梅的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融通的特点,这也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所共有的时代特征。如果将多元文化看作是组成叶梅小说的不同声部,那么,叶梅的创作分别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千禧年两个创作节点[1]集中强化了作品中多声部共振的特点,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创作体系。巴山楚水间的土家族历史重书和女性群像塑造是其小说中最强的声部,而在近十年的持续创作中,叶梅又随着她一直以来关注的主体同步流动,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城市生活。可以说,随着时代变化和社会变迁,叶梅由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女性身份出发,关注人在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之中的具体生命体验,并在创作主题上有所变化,颇显与时俱进。因此,以叶梅的创作为案例,探究其小说创作的成因和样态,以及其中多声部互动的轨迹,或可为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创作提供某种动态的样本——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如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和多元文化形成有效互动,同时保有文化上的差异性。
一、求同——叶梅小说创作的先在逻辑
多元文化交融的痕迹贯穿于叶梅的不同文体创作。纵览其小说创作经历,自九十年代的转向开始,以开阔的心胸面对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就成了叶梅创作的重要主题[2],这自然离不开她对于鄂西这一多民族地区的集中描绘。人作为主体在民族之间、地域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流动,在她的小说里都有所体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使得多种文化因素得以互相流通,多元文化的交往也从这一时期正式在其小说中展开。
能够关注到这些复杂的声部并自然地表现出来,同作者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叶梅自身的成长经历就充满了多元文化的交往痕迹,民族之间、地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等多个维度她都参与其中,而且多元文化经验带来的迷茫在叶梅的小说中体现不多,可见与其同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有所区别,叶梅创作的迷茫期十分短暂,并在创作过程中迅速地接纳了多元文化对她的影响。这同她的文化背景有直接关联,也同她坚持散文和非虚构写作有一定的关系。在民族的交往方面,叶梅的书写虽然主要集中在土家族,但她的小说并不旗帜鲜明地标榜某一民族,而更像是关注鄂西这一文化地域上人们的共同生活。所以,除民族外,地域也是其小说书写的一个重要侧面,围绕着长江沿流和三峡两岸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山村和乡镇,就是她笔下人们共同生活的家园。纵观叶梅创作的前期,她描绘了许多非城市的图景,农民、地质工人、文艺工作者、基层干部是她最为关注的对象;而到了创作后期,城市中的公务员、知识分子、商人、务工人员是她书写的重点。而她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怀和对土家族文化载体的呵护,则贯穿于她整个创作生涯,她最出彩的作品也同这些题材有关。
作家复合的创作视角是促成作品拥有复杂声部的重要原因,而在叶梅身上,主流视角、知识分子视角和民间视角是她在写作时的主要立场,影响其作品成型的基调。多重立场之间往往存在着冲突,但叶梅可以观察到冲突表面下的互相连结,在创作中寻求到“同”的可能性,进而将多元立场交织杂糅到作品中去。
主流视角指作家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关注影响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事实,从宏观的角度来彰显社会的主旋律和把握时代的精神。细观叶梅在1979 年至1981 年创作的六篇小说[3],都能看到这一立场在其创作伊始的巨大影响。而在此后,叶梅的主流视角仍旧起着巨大作用,但更圆融地同其他视角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了更“润物细无声”的艺术追求。在《过了河,还有山……》中,多年前“我”做路线工作时的一桩盗窃案终于有了真相,在“我”看来本应互相怨怼的老歪和宋珍儿在离婚后却认了兄妹,如今宋珍儿还要去吃老歪的喜酒,“土家人情感的复杂要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4]。在作者的安排下,一场主流视角书写下的事件最终由民间的方式予以解决。在《青云衣》中,叶梅通过融合个人历史和地方历史,最终落脚到三峡移民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上去,以文人书写的手法和民间视角的加入丰富了宏观历史书写的单一视野。这种主流立场的强势在其非虚构创作中清晰可见。
在主流视角的积极介入下,其他立场通常会呈现出被遮蔽的状态,而在叶梅这里,知识分子视角和民间视角却被她同主流视角相结合,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使她的小说创作更上一个高度。如果说“民间”通常被认为是同主流的“官方”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相区别的一个概念,那么在陈思和的阐释中,则部分地揭示了叶梅创作视角里“民间”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指向的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寻找到的一种“新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5]。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往往有作为知青下乡的经历,叶梅也是如此。她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表述并不只有对于“伤痕”的反思,更多的是对于乡村生活和民间生活的真切感知。在下到恩施鸦鹊区幸福二队插队时,她用自己的双手劳作,认为“知青生活为我开启了生命中的另一扇大门,通向乡村和民间”[6]。所以在叶梅这里,知识分子立场与天地和民间立场相融了,她既怀有对民间生活和民间趣味的欣赏态度,也有着身为知识分子要为人民发声的启蒙热情。在她的小说《青云衣》中,向怀田与妲儿相遇相爱的段落同古代文人笔记小说中狐仙故事的写法如出一辙,其中对于山野和民间趣味的欣赏清晰可见。在《撒忧的龙船河》和《最后的土司》等土家族文化小说中,民间信仰表现于日常生活本身,跳丧、梯玛[7]、舍巴日[8]等民间文化意象频繁出现。至于为人民发声的启蒙热情,叶梅在她小说创作之初就有此倾向,并一直延续至今。无论是最早的《香池》还是《谢了的花》,到最新的描写城市边缘人生活的《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她都秉持着为劳苦大众发声并在书写中给予他们丰厚情感的态度,并把这种态度从“乡村民间”持续到了“城市民间”。
当然,体察叶梅创作视角的最根源处,必须要再谈其多种身份的交融,最重要的便是她天然的民族身份和女性身份,以及后天的职业身份。从民族身份来看,叶梅无疑是土家族和汉族的“文化混血”,其父是从山东到鄂西地区工作、定居的南下干部,文化上的根脉来自儒学兴盛的黄河流域;其母则是世居鄂西的土家族,受巴楚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滋养。从叶梅的自述中可以得知,她对于两种文化都抱持正面积极的态度,都将其视作自己的文化根脉。站在民族身份的角度,上述主流视角还有着另一层意涵——“主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说在国家层面,叶梅的书写内化了这种宏大的视角,那么在民族的层面,叶梅天然地达到了汉族文化和土家族文化的圆融,积极地站在中华民族整体的视角上对民族文化进行书写,真正做到了求同存异。实际上,她对于主流立场、知识分子立场和民间立场的共同坚持,也来源于儒家传统的“文以载道”精神,是儒家“天下大同”精神和作家私人表达的协商与对话。她的小说在民族标识上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典型的土家族文化小说,这些作品针对性地书写了土家族的历史和文化风貌,颇有为土家族作传的意味;二是不强调某一具体民族、但将少数民族文化意象自然加入小说的叙事,它们的共通点更在于地域,都是鄂西土地上各族人民的故事;三是民族性完全消隐的小说,代表作多为叶梅早期的“文革”反思题材和中后期的城市书写。因此,从这里可以窥见少数民族作家在书写民族文化时的现实,即少数民族文化通常和乡土空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三种类型证明了叶梅在民族文化表达上的种种努力,她关于民族文化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三种视角平衡和角力的场域,但她的思考并不止于此。在《歌棒》的结尾处,原生态歌手沙鲁因在城市中丢失了民族文化的象征“歌棒”[9]而不愿再进入城市,和他有过文化和情感双重链接的城市女性芳罗却在归城时意想不到地找到了“歌棒”,她紧攥着“歌棒”,心想:“沙鲁有了这歌棒,会不会再一次走进城市呢?”[10]这个问题也是叶梅自己在思考之后提出的问题,她在写作时的三重视角既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可以强调地方文化、重建民族立场,同时要以知识分子的立场来审视与乡土正相关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在与外来城市文明的互动中转型的困境。
除了在民族文化的书写上向深处开掘,叶梅还在女性书写中有着一席之地。她的女性身份使得她在初入小说创作的时候,就将目光投向了女性题材。首先,在她的作品中,以女性为主角、以女性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几乎占半数,从1979 年发表的《香池》到最近的《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从乡村女性境遇到城市女性生活,从家庭主妇到职业女性,叶梅从未放弃过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探索。其次,她在很多作品中都流露出女性对细腻情感的把握,将许多主流视角下的故事描绘得清新自然、别有志趣,有别于同时期其他作者的处理方式。在采访中,叶梅如此表述自己作为女性的体悟:“我愿意是一个懂得爱和被爱的女人,那爱是多种意味的爱,包括爱生命、爱生活、爱自然、爱亲人、爱朋友……”[11]这意味着叶梅愿意以女性充沛的情感与自在的女性主体,和世间万物都保持友好可亲的关系。最后,叶梅还在小说中对女性的主体性进行了开掘。在与评论家李鲁平的对话中,她说出了自己对女性的期望:“不要甘于做一个弱者……勇敢地爱和被爱,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12]这正是她在创作中探索女性主体性的注脚。
而叶梅多样的职业体验又是其“求同”天性的催化剂,使她不拘泥于一时一地,可以从多重角度来看待文学创作。观其履历可知,叶梅除了是一名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的作者,她还有着在剧团工作的经验,是一位出色的编剧。在文学创作之外,她还担任过恩施州的地方干部和《民族文学》的主编。这些职业身份都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痕迹。一方面,这些职业经验为她的创作提供了经验和题材;另一方面,这些职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甚至规约了她的创作,例如前文所述的主流视角的形成,很难说与叶梅的地方干部经历没有直接关系。而她的编辑身份使得她在之后的创作中呈现出谨慎的态度,并较其他创作者来说与读者的关系更为亲密。叶梅的一些作品往往难以追溯创作的原始时间,是因为她常常自觉收集读者的意见,综合自己作为编辑的专业思考,在多年后还对早已完成的作品进行题目和内容上的修改,如1986 年写就的《城市寂寞》,就被她改名为《偶寄》并改变了结尾基调,录入了2020年出版的小说集《青云衣》中。长期的编辑工作使她成为了一位在文学上精益求精的创作者,这同时也导致了她少有长篇小说出版———虽已有写成的长篇小说,但追求完美的心态和润色工作所需要的大量时间同其忙碌的编辑工作相冲突,因此她的创作重心仍在中短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上。
二、存异——叶梅小说创作的独特表达
在叶梅创作的“求同”心理基础上,作为她三重视角博弈的另一个侧面,就是她在民族文化表达、女性书写、地域书写和生态书写方面的独特表达。如果说“求同”是叶梅进行小说创作的先在逻辑,那么这些独特表达的部分则是她在此基础上对自己艺术追求的延伸,是她的小说有别于他者的重要标识。在叶梅的小说中,对于民族文化的挖掘之深,主要体现在她对于土家族文化的民族志书写和历史再造上,她使众多文本互相勾连,创造了如“龙船河”系列和“田土司”系列小说。而在女性书写方面,她又集中展现了鄂西这一地域上巴楚女性的整体风貌,以及由乡村到城市转型的女性生存实录。因此,对鄂西这一地域的塑造横亘了她小说创作的始终,鄂西既是她实际的家园,也成为了她小说世界的精神原乡,三峡以及沿岸聚落的命运与其小说就变得息息相关,叶梅随之将目光投向生态书写是顺理成章的。加之她作为女性书写者对世界抱持的充沛情感,以及她身为知识分子对于民生的关注和她的干部经历对地方发展的责任感,生态书写也成为了她一直坚持至今的路径之一[13]。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看来,地方是具有人类生活价值和意义的空间,包含着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和生态关系等,在地理维度之内承载了“人—地”活动的全部。人在空间之中产生了足够的经验并对其附着了情感之后,“空间”就转化为了“地方”。叶梅将其最凝练的经验和深刻的情感凝结在地方中,通过这些方面予以表达,民族、女性和地域在她的小说叙事中互相连接,使得她的小说中的鄂西世界完成了从故事背景到精神家园的升华。
在叶梅知名的土家族文化小说中,能够看到她对于鄂西土家族文学版图的追求和野心。她在漫长的文学实践中,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鄂西土家族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两个核心“龙船河”系列和“田土司”系列互有关联,叶梅在用多篇小说充实这两个系列的同时,还创作了其他对于土家族文化书写的篇目围绕其间,对整个世界观进行补充。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她为这一世界添砖加瓦的文学实践大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2010年前后,核心作品的建构集中于九十年代前后和2000 年前后,和上述所说其创作转向的两个重要节点一致。为此,她在“龙船河”系列和“田土司”系列成熟之前,就早已在其他短篇作品中埋下具有土家族文化意象的线索[14],这种积累才能最终使得其代表作《撒忧的龙船河》《山上有个洞》和《最后的土司》的文化指向清晰起来。在核心作品完成的同时,叶梅也在其他篇章中继续加强了这些元素,对这一系列进行巩固——在同年的《花树花树》里,故事一开始就以梯玛覃老二的出场来预测两位女主角的命运,这同样也是《撒忧的龙船河》中代表土家族巫文化的重要人物。在核心作品之间也有这种元素的回响,例如在2003 年《最后的土司》里,梯玛覃老二完整地旁观了土司覃尧、外乡人李安和哑女伍娘的情感冲突。作品之间因为这些土家族文化意象的缠绕,因此得以作为完整的系列呈现。
在塑造体量相对较大的核心作品时,叶梅往往会采用过去历史和当下日常双线并行的模式,使得作品在时间维度和内容上更加饱满,为土家族文化的魔幻现实叙述增加了空间。《撒忧的龙船河》的开场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也即主人公覃老大的“撒忧儿嗬”[15],已经死去的覃老大被撒忧儿嗬的力量所牵引,回顾了他作为桡夫子的一生。全文共八章,每章开头都是覃老大现下丧礼的一环,随即引出其生前所经历的每一段历史变故,插叙的方式让死与生并存、过去与当下互渗,增强了“撒忧儿嗬”的魔幻感,也掺杂了历史发展进程对于个体之不可抗拒带来的现实感。在2002 年成型的“田土司”系列核心作品《山上有个洞》中,叶梅更加游刃有余地使用了这一模式,将改土归流时期田土司的洞中藏宝传说、清匪反霸时期田红军的洞中逃难经历与当下农民进城务工时期田快活的洞中寻宝奇遇并置叙述,以同一个家族不同时代的人为描写对象,以过去历史传说的跌宕起伏映衬当下生活的空虚琐屑,不仅使得这一地区土家族的生存样态在时间维度上得到了丰富,还因此巧妙地体现出不同时期民族地区文化在外来力量侵袭下的反应和土家人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核心作品之外还有外围作品,其特点是有土家族文化的元素作为背景和补充,不直接影响故事本身的情节,通常篇幅较短,题材五花八门,但又隐隐与核心作品中集中的土家族文化元素相连,成众星拱月的态势。如上文提到的《酉水少年》《花树花树》和《歌棒》等,与《撒忧的龙船河》《最后的土司》共同构成了“龙船河”系列。而《黑蓼竹》和《山上有个洞》则构成了“田土司”系列。在这两个系列之外,另有《回到恩施》《青云衣》等作品独立成文,同前者一起组成了完整的鄂西土家族世界。
在女性书写方面,叶梅也有着独特创造,相较其他女性作家而言,她针对性地塑造了一批具有巴楚风格的女性群像。当背景为乡土时,她笔下的女性带有鲜明的土家族文化性格,当她的目光从乡土转移到城市中去的时候,这些巴楚女性又随之进入城市,以吃苦耐劳、敢爱敢恨、爽利大方的品性来应对城市文化的考验。从她2009 年出版的小说集《妹娃要过河》的名字上,就可见其女性书写的偏向———“妹娃要过河”是土家族民歌《龙船调》最为人所知的句子,体现的是土家族女性乐观开朗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爱情观。到了叶梅这里,“妹娃要过河”又多了一层意蕴。她为小说集作了一篇名为《妹娃为什么要过河?》的后记,其中说道:“现今这个时代,虽然还是以男性话语为中心,但女性已经有了更多的命运自觉……在河的彼岸,星空闪烁的彼岸有着女人的希望,虽然河水深浅不一,有着不可知的风起云涌,但过河——是一件多么诱惑女人的事情。”[16]“过河”在她笔下成了女性自主选择命运的时刻,《小都市跟前的草儿》中的草儿、《断根草》中的秀和春、《最后的土司》中的伍娘、《花树花树》中的昭女和瑛女、《五月飞蛾》中的二妹等,莫不如此。叶梅在处理女性题材时,试图找寻一条在制度和话语压迫的现实下,男女达成和解、健康地昂扬女性主体性的道路,地域性格和民族性格即为解题的关键。这些女性角色都有着巴楚地区从古至今的女性形象的影子,无论是充满野性之美的山鬼,还是追寻爱情至死的盐水女神,其中暗含的是巨大的人的主体性。直到《小都市跟前的草儿》里,看似腼腆内向的草儿突破了思想桎梏勇敢下山,靠自己的双手收获了生活和爱情——在土家族生活方式逐渐变化的当下,女性有了更多过河的可能性。昭女、二妹和李玉霞等众多女性,都勇敢地踏出了这一步。
但不管是民族文化表达还是女性书写,叶梅的独特创造都建立在地域书写的基础之上。叶梅在小说中对于鄂西地区的塑造是从外到内全方位的,从外层的角度来看,她在许多篇目中都花大篇幅描述了峡江地区多山多水的地貌特征;从内在的角度看,鄂西地区在文化层面上的所有内涵她均有涉及,包括民俗、文学和历史等多方面。叶梅的叙事无不与山水有关,像《尖山顶上》《过了河,还有山……》和《回山里去的人们》等篇目,从名字上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这层关系。在《门前那条小路》中,故事的发展就围绕着主人公门前难行的山路展开;而《山上有个洞》揭破了山中洞穴的存在之于鄂西土家族的意义,是土家人祖源神话里诞育先祖之地。水则更不必说,是峡江人赖以维生的根脉,影响着峡江人的命运。覃老大在江上与莲玉相爱,他们的儿子在江上消失,孙子又在江上与女子相识,滚滚江水承载了他们代际之间历史经验的延续。在《撒忧的龙船河》中,对河的描述部分地解释了其中蕴含的文化心理:“河水温润如脂,游动时如依偎在先人的怀抱之中……祖先就是沿了那河一步步迁徙而来的,河里有祖先流动的精液。”[17]水就是土家族人的生命之路。在民俗方面,叶梅花了较大笔墨来构建地方文化符号群,以《回到恩施》为例,在“剿匪”故事线之外的描述本不“重要”,但作者却执拗地详述了许多独属于鄂西地方的民俗文化。说到谭驼子给沈先生送的食物是合渣时,她另起一段写道:“合渣这东西说起来很多人都不懂,恩施过去穷人的日子常用一句话来形容,说是‘辣椒当盐,合渣过年’……合渣是土家族喜爱的食品,就是将黄豆用石磨磨过以后,连浆带渣煮在一起,加上切碎的青菜,最好是萝卜缨子,有一种略略毛糙的口感,吃起来很特别很有质地……”[18]在说到土匪向金川准备七月半鬼节的时候暴动,作者又写“鬼节是恩施人看重的节期,农历的七月初十到十五,都说:‘年小月半大,神鬼三天假’。长江边上的人到了这个日子要接出了嫁的女儿回妈屋,放花花绿绿的河灯,祭祀祖先鬼神,夜里将纸钱封了写上受领者的名字,到野地里烧化,叫作烧包袱。”[19]为了增强地域书写的一致性,叶梅将以方言土语和本地传统的文学样式融入到叙事中。土匪是“棒老二”,膝盖是“髁膝头”,表现重义忘利、不在乎生死的地方性格是“该死的卵朝天,不该死的万万年”[20]。在文学方面,叶梅不仅直接将巴楚地区大量传统的山歌直接置入文中以推动情节发展,如《之字拐》中以男女对唱来表现误会的解开,光其本身行文就颇有《楚辞》之风。她常描写人与鬼神天地的沟通,像梯玛覃老二在击丧鼓时与鬼魂覃老大的对话,伍娘在舍巴日上以浪漫巫性的舞蹈献祭的场面,既直接使用了巴楚巫文化的意象,又在语言上有着楚辞“激荡淋漓,异于风雅”[21]的特征。叶梅还在地方历史的重书上下了功夫。首先,她有意识地将地方知识系统引入叙事中,将地方历史传说和当地人民生存境遇结合,成就了鄂西地域魔幻现实色彩的“现实”一脉。其小说《青云衣》便是参考引用了向氏族谱、长江三峡县志和民国时期《勘测河道大纲》等地方知识来组织小说背景和情节,穿插了“清匪反霸”和三峡大移民等地方重大历史事件。《回到恩施》几乎可算是一篇为其父的野三关剿匪经历作传的小说,其中加入了许多从她父辈那里得来的地方记忆,主要情节直接来源于个人口述史。其次,在书写地方历史的时候,叶梅的目光并不局限于地方,而是以国家历史和地方历史互动的形式呈现。《黑蓼竹》以吴先生离家求学到跟随国民党部队定居台湾的历史脉络为主线,叙述了田佬、竹女和远在台湾的吴先生一生的命运纠葛,以人物表现鄂西地方与家国命运变迁的纠缠。总之,她所描写的人物无一不有着被地方和国家历史浪潮推动的命运,叶梅在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双重丰富下,才得以将鄂西作为完满的精神原乡呈现在文学版图中。
三、兼容并蓄——叶梅小说创作的多元文化互动共融
回顾叶梅创作的“多声部”,可以看到,她在小说中以较高的文字水准和文化表达方式,以及不断积累的个体经验,使得互动和共融两个动作在多元文化之间持续进行。究其根源,则在于叶梅形成了主流—知识分子—民间三方视角协商状态的达成,多元文化动态历史的呈现,以及多种经典模式叙事的形成。这三者分别构成了叶梅创作的基底、骨骼和肌肤,使得她在求同存异之上做到了兼容并蓄。
其一,叶梅在主流—知识分子—民间三方视角协商状态的达成,在上文中已有部分阐释。分而论之,叶梅虽以主流视角为初写作时的契机,但在其后数十年的文学实践中,她对此表露出呼应与疏离并存的态度。呼应在于其对于题材的选择和对于民族情感的表达,疏离则在于她对主流视野宏大话语中单一性倾向的抵抗,为知识分子视角和民间视角留有余地。当然,她一如既往地坚守知识分子视角,同时站在民间视角的立场上积极展现民间文化和民间生活。这三者在她的多篇小说中有机组合,才形成了她在多元文化中多次进行拣选排布的平衡状态。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协商、平衡状态的达成代表了其土家族文化小说、女性书写和生态书写的尴尬境地,即其中“存异”的部分并不能得到真正的昂扬。但实际上,正是这种协商状态的要求,叶梅才会在创作时对自己有着更高的追求。不妨把这些部分看作是她在三方视角平衡下的补充和额外尝试,更有益于对叶梅创作的理解。
其二,在叶梅的小说创作逐渐摆脱初期篇幅较短、题材简单的弱点之后,其中后期的创作都有意展现多元文化摩擦、交往直至交往、交融的状态,无论在民族记忆中还是在城乡变迁中,都包含着这种动态历史的呈现。叶梅小说中最激烈的文化碰撞主要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层面上,她通常会设置三类角色完成民族寓言的隐喻——— 一是代表汉族文化或其他民族文化的闯入者,二是既接受本民族文化教养,又被他者文化熏染的矛盾型人物,三是全然为本民族文化滋养的“土人”。在《撒忧的龙船河》中,因巴茶将覃老大和莲玉的儿子抱来养大,才使覃老大从一场风波消弭回归至安稳的家庭生活,但儿子作为两方短时间内激情结合的产物仍急速地在龙船河上逝去了,直到孙子那一代才完成了对两方文化的内融。在叶梅看来,融合是一定的,但“融合是在非常激烈的、近似悲剧性的碰撞中完成的。”[22]在新近的小说中,叶梅对民族文化碰撞的表达又进入了新阶段,在《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中,她以内敛的手法消隐了民族符号,这也是当下少数民族作家书写的另一种潮流。
其三,叶梅在过去的创作中形成了多种经典模式的叙事,其中展现了叶梅对于多元文化互动、多声部共鸣和二元语境互动的强调。当然,这种态度和她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在《穿过拉梦的河流》中她阐释了她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理解:“的确,当波涛汹涌的大江浩荡地奔向大海时,我们不能忘了在它的源头,那许多迷人而又多姿的河溪,它们来自冰川和大地深处、来自上天给予的每一滴甘露,它们以不同的表情,或粗犷或细腻、或缠绵或灵秀地汇到一起,于是大江才逐渐丰满壮阔起来。从古到今的中华文明正好比一条气象宏伟源源不断的大江,是由多源的绚丽缤纷的多民族文化所构成的。”[23]拉梦在藏语中意为“多民族”,其美妙而富有联想的音节也承载了她对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期待。首先,叶梅小说的经典模式之一便是民族志式的少数民族边地书写,其中涵盖了方言土语的运用、民族文化景观的呈现和民族记忆的重建等方面。其次,她还深度构建了外乡人闯入和乡人出走模式,其中典型代表就是“过河女”系列。这种模式虽涉及城市,但仍以乡土为主角,用乡土和城市的交汇制造文化交流的契机,借以展示城乡一体化等社会转型的真实面貌。最后,她尝试书写了城市文明对人的异化以及人对异化的抵抗,即以城市为主要背景,探讨人性本身的复杂及多样性。
可以说,叶梅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多元文化融通的意识,贯穿于她所有文体的创作。她对于多民族文化及文学还有中国各地风土民情的关注,是和她文化根脉上的混血以及地域文化滋养而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相生相伴的。纵览对叶梅文学创作进行研究的相关论文,研究者们几乎都从她小说中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女性意识和生态性来入手,这几方面确实都代表着叶梅创作的多个维度,尽管在某些研究者眼里,这些维度对于生长于山水之间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有一些“老生常谈”,但叶梅无疑是从中汲取养分并集大成的突破者,如上文所述,这同她多样的文化经验和职业经历是分不开的。她穿越单一民族而达成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连接,深入底层的对于人本身的关注,不仅能从她的小说中折射出来,也直接反映在其散文和报告文学甚至编剧作品中。除此之外,她在写作技巧上的圆融,以及在技巧之外的对人性的一点幽微的揣摩(例如在《最后的土司》中覃尧以断腿的李安去配哑女伍娘,因为他隐秘地想到“那人四肢不全正好合了伍娘的五音残缺,不会让他占人一头”[24]),都使得其小说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生动与深刻,其作品的耐读也正因此成就,她的小说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也便有了土壤——这也正符合了当下小说写作者会在写作时刻意将文本写得更易影视化的新潮流,叶梅多样化的尝试在很早之前就暗合了当下的流行趋势。近年来,叶梅仍持续着文学产出,而且又在新的尝试中继续耕耘——她将目光转向了非虚构创作,持续关注着生态书写和重新去认识儿童的精神世界,是真正的随着时代变动而进步的作家。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2023 年研究生科研实践项目“当代少数民族城市书写及其家园意识生成研究”(项目编号:BZKY202304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