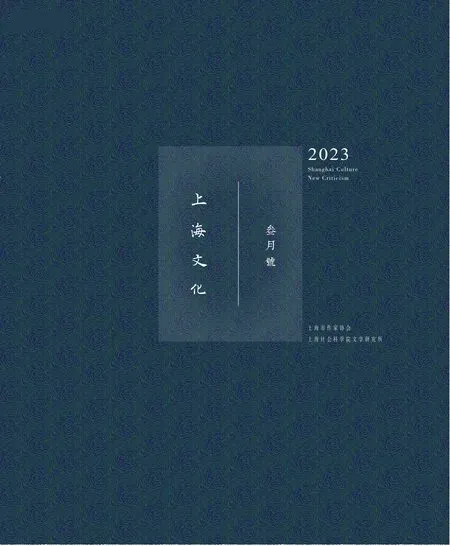一篇像小说的小说与一篇不像小说的小说 读莉莉陈小说集《游泳》
易思退
陈莉莉是幼教工作者,莉莉陈是小说家。她们是同一个,又仿佛不是同一个。当陈莉莉复归为莉莉陈的时候,她便可以远离一个孩童的世界写成人的故事。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她的小说里还隐隐透出一道恶童的目光。我这么说,是表明莉莉陈的小说与陈莉莉的身份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从她的相关履历来看,她写小说的时间略微有些晚。但我们应该知道,晚饭花(一种紫茉莉)总是在夜晚开放,而且不失芳香。
我一点儿都不怀疑莉莉陈编织故事的能力。就像她能把自己的姓名颠倒来写,她也可以把一个故事颠来倒去地写。有时候,她会进行一次叙事冒险,故意把故事性放在并不重要的位置,去经营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情节与细节。能把弱故事性的小说也写得那么有味道,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捕捉细节的能力和训练有素的叙事技巧。《总统套房》里面的一只老鼠,《游泳》里面两块薄薄的海绵,《回向》里面的十八粒安眠药等,都是跟叙事的逻辑链条紧密相连的细节,自带敏感的神经,隐藏在字里行间,只有在我们读完之后,才会一点点显露出来,仿佛深草里探出的昆虫的触须。
莉莉陈并没有憋着一口气讲故事,而是很放松、散淡地讲,讲到后面,那些散开来的话题慢慢归拢,就有了可以贯穿的线索,有了可以玩味的地方。她的小说也不适合一口气读完,一篇小说,读上十来页,放在那里,饭后回来,再接着读,也能接续气息。好在,她的小说并不长,一周之内,一本薄薄的小说集就可以断断续续地读完。
她写的大都是一些卑微人物,连带着人与时代之间的共振、人与人之间的秘响。她善于跟这些小人物打交道,乐于分享他们的秘密,更重要的是,无论发生多大的事,她都能沉得住气,而且总能置身事外地写,保持客观、冷静,也无风雨也无晴。在她的小说里,处处有情,却不抒情,甚至可以说是反抒情的——只要她觉得某处出现了抒情意味,就会有意压制一下。她对情感的控制是恰到好处的,对厌恶的东西,没有慷慨陈词,而是夹带几句微妙的嘲讽,至多也是笑骂几句。因此,她的小说音色虽美,调门却低。如果非要拿一样乐器比喻莉莉陈的小说,我想应该是钢琴。一个人,闲闲弹来,气度雍雍,没有青春写作的急迫,却有秋日般的简素与沉静,这恐怕也是一个成(晚)熟的小说家应有的一种状态。国内有好几位重要的小说家谈起浙江小说时都曾聊过莉莉陈,他们一致认为:她的小说虽少,但可以说是一篇算一篇。
在她的小说里,处处有情,却不抒情,甚至可以说是反抒情的——只要她觉得某处出现了抒情意味,就会有意压制一下
翻翻当下期刊上的小说,不难发现,小说家们仿佛已经摸透了小说这门手艺活,对措辞、语调的控制,对冲突、悬念的设置,都可谓驾轻就熟。然而,长期以来,小说家们的经验书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感觉的钝化与灵性的退化,也使小说变得越来越像小说。因此,他们写得越多,自我复制的倾向就越发明显。莉莉陈写得少,反倒避免了这种习气。《游泳》这本集子收录的十篇小说,大概已经倾其所有。读完之后,我却觉得很多小说家其实是不需要写那么多的。这里我姑且就集子里首尾两篇小说《游泳》和《王先生的父亲》谈谈自己的浅见。
从一个看得见的世界游到另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游泳》自然是一篇像小说的小说,跟集子里面的《总统套房》、《彭罗斯传说》、《幸福链》、《第三个人》、《地下室》等中短篇小说一样,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第一人称可以更有效地让叙事向内走,翻转到心理层面——有行迹与心迹的叠加,有显白之语与幽隐之意的交织,首尾整一,符合那种教科书式小说的套路。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十四岁少女,对周遭的世界一知半解,选择她作为叙述者就有了限制性视角,不仅使小说更具现实感,还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里的叙述者就像是用双手蒙住了眼睛,却从指缝间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这些事安安静静地发生,也安安静静地结束。
小说写了三次游泳,下面不妨借用三个数字罗列出来。1:“我”、小姨、罗医生(罗医生的太太朱护士长临时有事没来)三人来到离医院不远的江边游泳,“我”下水时,小姨与罗医生尚在岸上,“我”独自游向对岸的时候看到小姨还在跟罗医生说话,作者写到这里把人物的行动时间、话语时间都压缩到极限,甚至只是用一笔轻轻带过:“我看见两个人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都小到一块去了。”2:“我”、小姨、罗医生以及朱护士长四人相约去江边游泳,“我”发现他们三人好像发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但看上去又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这里仍然是一笔轻轻带过:“回去的路上,小姨和罗医生都一声不吭,唯独朱护士长一个人嘻嘻哈哈地说个没完。”3:“我”去江边,既没有小姨陪伴,也没有约上罗医生夫妇,而是独自下水游泳,但碰到了那个第一次游泳时主动跟我搭讪的男人,被他捉弄了一番,被水呛了一回,然后被告知:“以后不要骗人,你哪有十八岁。”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写得尤其细密,叙述节奏也趋于缓慢,让人感觉有些沉重起来。如果把这三次游泳再捋一遍,还会从中发现三次意外:第一次是在“我”身上出现了小小的意外(“我”游到对岸时,两个陌生男人跟“我”搭讪,问“我”年龄,“我”谎称十八岁,他们发出了啧啧声);第二次是在朱护士长身上出现不大不小的意外(她身上那个救生圈的气门芯竟无缘无故地拔掉了,她认定是小姨“逗”她玩);第三次意外还是出现在“我”身上(如前所述,我被那个陌生男人“验明正身”,所幸有惊无险),可谓是第一次意外的延伸。如果抽掉第一次游泳那一节,那么第二、三次游泳就少了铺垫和迂回。如果抽掉第二次游泳那一节,其余两次游泳就变成个人的历险记,虽然也是顺理成章,但小姨的隐秘情事就无从发现,人物也会因之失焦。如果抽掉第三次游泳那一节会怎样?也不行。一种隐隐不安的氛围已经在前面生成,扩散至此,有了更多的波动,也为后面的情节发展添加了推动力。由此可见,三次游泳、三次意外,环环相扣,表面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其实是按照叙事逻辑来排列。就外在逻辑来看,它是1+2+3的叙述模式,但就内在逻辑来看,则是1+X+3的叙述模式,这里面,X是一个未知因素,也是小说突然打破平衡的一个要素。小说里原本还可以有第四次游泳,但作者故意把它悬置起来,最后应之于梦。
说到底,这是一篇成长小说。当一个十四岁的少女谎称自己十八岁时,她是多么向往成人那种散发着荷尔蒙气息的生活,同样,她对那个成人的世界怀有强烈的好奇,比如:“我看见男人抽烟,吸进去的时候,眉毛一抖一抖的,说不出的惬意。”又比如:“听了男医生的话,我觉得很好奇,备皮是什么,为什么小姨听了会那么生气?”这些让她好奇的物事,最终都有了答案,但另一些物事之所以终归无解,仅仅是为了保留小说的原质和神秘感。
循此可以发现:作者在小说中安放了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然后又在一个看得见的世界与看不见的世界之间设置了一段距离:“我”与小姨的距离、小姨与罗医生的距离,罗医生与朱护士的距离,小姨与朱护士的距离,“我”与罗医生夫妇的距离,彼此间保持距离之后,就有了种种猜想。“我”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观看者,也是一个自我观看者。
跟大部分老练的小说家一样,作者有意拉开了与叙述者的一段距离,她葆有一种对日常生活的亲近之心,由此延伸出来的一种平实、精确的叙述,使小说中看得见的那一部分有了清晰的呈现;与之相反的是,叙述者对视点之外的部分进行了模糊化处理,拉开了她与人物的距离,也拉开了看得见的那一部分与看不见的那一部分之间的距离。
我把这个小说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倒过来捋了一遍,就发现,前面分布了很多个隐而不露的点,这些点与点之间交织成两条线,一条是明线,一条是暗线,这两条线随着情节的推进交替衍生。明暗之间,疏密有致,故而能制造出一种外在的轻松与内在的紧张。有时候,一篇小说情节太满、细节过多,原本舒缓的叙述节奏就会显得凝滞,但《游泳》不存在这个问题,读它的感觉就像是站在岸上,看一个人很从容、舒展地从这一头游到那一头。
一根笔直的竹竿如何变得曲折
谈《王先生的父亲》之前,容我先抛几句闲话。某日翻闲书,我读到一篇小文章《李三老的爱情观》,作者黄成援引了《笑林广记》中的一则故事:“有一天,一人持竹竿进城,结果,横着进不去,竖着也进不去,正踌躇着,旁人建议:可以向智者李三老讨讨主意。碰巧李三老骑着毛驴过来了,众人见他坐在毛驴的屁股上,就问他为何不坐到驴背上,李三老回答:这缰绳太长啦。”
作者要说的显然的不是笑话,而是一个看似笑话的话题: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这个人为什么非得手持竹竿?如果城门有竹竿那么高或者那么宽,自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城门只有那么大。”
“就像这位手持竹竿者,人们在情感问题上也难免握着长短不一的‘竹竿’,并用这‘竹竿’度量着一切……”
由此我忽然想到了莉莉陈的一篇文章。称之为“文章”,是因为它最初是作为一篇题为《我与我》的散文发在《野草》杂志的一个专栏上。很显然,作者是把它当作散文来写的,但我读了之后感觉它更像是一篇值得玩味的元小说。这些年,我在《野草》杂志上偶或读过好几篇莉莉陈的专栏文章,唯独这篇,不像小说,也不像散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想到,它后来作为小说收录到《游泳》这本集子里,题目也改成了《王先生的父亲》。
小说的起头很平淡,说“我”在理发店弄头发时,无聊地刷着手机,然后刷边上的杂志报纸,不经意间刷到了一条小新闻。新闻大致内容如下:“有为青年王先生考上大学,在大城市里打拼了十年,终于买了一套新房,他乡下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一路跋涉为他送来了一根青竹竿,竹竿在家乡寓意‘步步高’,摆在新房里可以占个好兆头。那天下雪,王先生的父亲在运送竹竿及其他大包小包的行李遭遇一路折磨(具体没有详说),由于不方便打伞,到了王先生家时,身上的棉袄与棉裤已经被雪水沁湿了。王先生接过竹竿的一刹那热泪盈眶,哽咽难言。”这个新闻提到了“热泪盈眶,哽咽难言”八个字,“我”虽然无法意会,却很想体会这种感受,于是就打算还原这段过程。我们可以说,新闻结束的地方,小说开始了。
没错,故事就这样展开了:“我”出于好奇,买了一根高及天花板的竹竿。小说中对竹竿的外观与气味以及如何手握竹竿的基本动作均有精细的描述:“右臂呈圆弧形,握拳向内,把竹竿护在圆心,竹竿下端离地保持十厘米左右,身体保持正直……”
怎么握确定之后,就是怎么走的问题。接下来,“我”开始仿效持竿进城的王先生父亲出门去坐公交车。无论在路上,还是车上,那根竹竿都须臾未离。寻常的路线,因为有了手中的竹竿而变得不寻常了。也就是说,小说中凭空多出来的一根竹竿,忽然使小说本身有了内在的超逸之气。此时的竹竿包含了一段明确的路线、一系列动作还原的过程、一个既定的目的地。与其说是“我”手持竹竿行走,不如说是竹竿带着“我”走。当“我”在途中上一趟厕所,再度拿起那根竹竿时,它的意义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转而发觉:“竹竿并不给王先生的父亲带来负累,相反,没有竹竿的话,长途旅行就是一种苦役,而有了竹竿他的一路行走就有了意义。竹竿就是需要,就是他对儿子对这个世界的需要。”前面新闻里提到的八个字“热泪盈眶,哽咽难言”至此也就有了新的诠释(包括质疑)。
竹竿的“意”固然立起来了,但作者还是要继续她的叙述。到了“我”规定的目的地——酒店,竹竿就失去它的意义了。这时候,我感受自己“跟王先生的父亲不一样,我的前方并没有一个等着竹竿的人。所以竹竿已经没用了。不知为何,这个事实让我有一点点难过。”读到这一句,我便依稀看出了作者的一点深意。行走途中的竹竿与抵达之后的竹竿,虽然都在“我”手中,却有区分:行走途中,竹竿是属于“我”的,也属于“我”想象中那个王先生的父亲的;抵达之后,竹竿是竹竿,“我”是“我”。我当初之所以判定此文是小说,是因为它虽然没有戏剧性情节,却有戏剧性暗示。作者在前面给自己设定了某种限制,又在后面打破限制,由此生发的戏剧性暗示,又使小说脱离故事本身,滑出很远的地方。那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想象与思索的地方。小说就此结束了吗?没有。“我”把竹竿带回了家,闲置门后。过了三年,“我”先生腌咸肉需要搭一个架子,就把这根竹竿断成几截。“我想起了竹竿后面的王先生父亲,和想象王先生父亲的那个我。现在的我跟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有了一段遥远的距离。”我与我之间相隔着一根竹竿,这根竹竿丈量的不是我与王先生父亲的距离,而是我与我的距离。这种对现实的介入与淡出,对内心的精微观照,使文本空间既敞开又封闭、既沉重又轻逸。
一个小说家是可以把一根笔直的竹竿写得十分曲折的
一根竹竿,在作者笔下,也是可以“度量着一切”的。比如,它可以度量一个“需要与被需要”的问题:当这个世界需要这根竹竿的时候,竹竿就变成了某种情感的对应物,也因之变得有意义了;当这个世界不需要这根竹竿的时候,竹竿就是竹竿,也谈不上什么意义了。
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我默默地将咸肉搁在竹架上,一层层地涂上盐巴。”读这样的文字你很难一下子激动起来,但有时候也难以平静下去。
谈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前头那个持竿进城的笑话了。持竿者有没有采纳那位骑在驴屁股上的李三老的建议?没有交待,也无须交待。解读这个笑话的作者说:“既然有竹竿,何必拘于城门的限制?”为此,他还在后面安放了几个结尾,试图让笑话变成寓言。然而,我们也同样可以把这个笑话铺衍成一篇小说。顺着这个思路,我们甚至还可以把这个笑话写成一篇卡夫卡式的荒诞小说:比如,把这个城门变成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带上一种隐喻的色彩。如此这般,那个持竿者的形象就扭转过来了,而读者也就不能再把他当作笨伯来看待了。他持竿进城,分几个步骤,每个步骤都伴随重重障碍与破解之法,然后又是不得其门而入的障碍……进一步说,我们还可以为这名持竿者塑造成一种很方的性格。在他手中,竹竿就是原则,竖执不能进城门,横执亦不能进城门。他思量再三,认为问题不在竹竿,而在城门。城门不够高,也不够宽,他就不打算进去。因此,持竿者可能会继续手持竹竿,继续寻找一座可以持竿而入的城门……我这么说,似乎有点扯远了。
其实我要说的是,一个小说家是可以把一根笔直的竹竿写得十分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