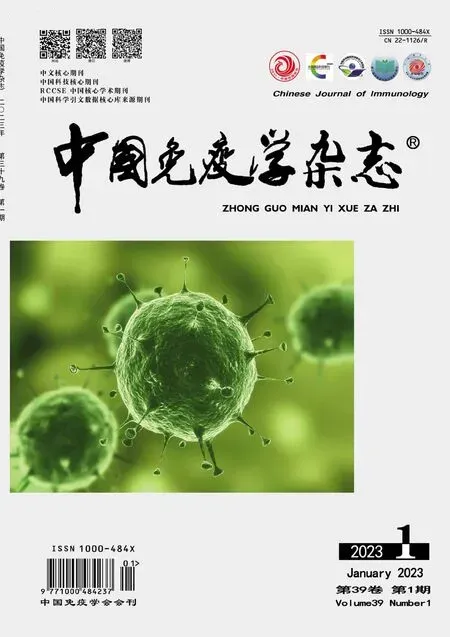短链脂肪酸在炎症性肠病中的作用研究进展①
陈文轩 张 哲 孙亚星 刘 霞 王斌斌 冯百岁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郑州 450014)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类慢性、复发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其确切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不明,目前考虑其与肠道菌群改变导致肠黏膜异常、遗传、环境等多因素相互作用相关。肠道菌群(gut flora,GF)在调节肠道稳态和IBD发病机制方面的作用已被广泛证实,不仅能够通过影响Th17/Treg平衡进而影响宿主肠道免疫功能,还能够通过分泌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 SCFAs)、色氨酸等,影响肠上皮细胞能量代谢及黏膜屏障[1-3]。作用机制研究发现,SCFAs可通过调节肠道免疫细胞功能、调控细胞因子释放、为肠道上皮细胞提供能量、维持肠道黏膜屏障功能等维持肠道稳态,本文就SCFAs在IBD中的作用及机制进行综述。
1 SCFAs概述
SCFAs是一类脂肪尾部由1~6个碳组成的羧酸,如甲酸(C1)、乙酸(C2)、丙酸(C3)、丁酸(C4)、戊酸(C5)、己酸(C6)等,肠道总浓度为0.5~0.6 mol/L,其中乙酸、丙酸和丁酸是肠道中最丰富的SCFAs(≥95%),摩尔比约为3∶1∶1,由盲肠和结肠内厌氧菌发酵不易被消化的膳食纤维(dietary fiber,DF)产生,是一类影响宿主免疫和能量状态的细菌代谢物[4-6]。不易被消化的DF包括抗性淀粉、菊粉、燕麦麸、麦麸、纤维素、瓜尔胶和果胶[7];厌氧菌拟杆菌门主要产生乙酸和丙酸,而厚壁菌门主要产生丁酸[8]。SCFAs主要通过被动扩散、与碳酸氢交换、转运蛋白一元羧酸转运蛋白1(monocarboxylate transporter 1,MCT1,由SLC16A1编码)和钠偶联的一元羧酸转运蛋白1(sodium coupled monocarboxylate transporter 1,SMCT1,由SLC5A8编码)4种转运机制被肠上皮细胞吸收,由肠系膜上静脉和肠系膜下静脉进入门静脉。肝脏中,乙酸和丁酸是合成胆固醇和长链脂肪酸的底物,丙酸通过三羧酸循环(tricarboxylic acid cycle,TCA)转化为葡萄糖[9-10]。此外,SCFAs也可直接通过下腔静脉进入体循环,对消化系统以外的组织/器官,如肺、肾脏和大脑等发挥重要作用[11-13]。
2 SCFAs介导的信号传导
SCFAs主要通过G蛋白偶联受体(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s,GPCRs)激活途径和组蛋白脱乙酰基酶(histone deacetylases,HDACs)抑制途径两条信号通路调节肠道、神经、内分泌、血液等不同系统功能,是调节代谢紊乱、调控机体免疫、维持肠道黏膜屏障稳态的关键因素[14]。
2.1 GPCRs激活途径 GPCRs也称游离脂肪酸受体(free fatty acid receptors,FFARs),在结构上为单体蛋白,氨基端位于细胞膜外表面,羧基端位于细胞内侧,其肽链反复跨膜7次,在膜外侧和膜内侧形成几个环状结构,构成细胞外环和细胞内环,分别接受细胞外刺激和调控细胞内信号传导。已发现的GPCRs有GPR41(FFAR3)、GPR43(FFAR2)、GPR109受体,在多种细胞上均有表达[15]。SCFAs通过激活GPCRs进一步激活异源三聚体的Gα亚基(主要负责与GPCRs受体结合)从Gβγ亚基分离,通过Gα亚基(主要包括Gαi/o和Gαq/11)调节细胞内多种信号传导[16]。通过激活Gαi/o抑制腺苷酸环化酶(adenyl cyclase,AC)活性,从而导致环磷酸腺苷(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cAMP)生成减少;通过激活Gαq/11激活磷脂酶C(phospholipase,PLC)促进内质网上的肌醇三磷酸(inositol triphosphate-3,IP3)受体激活,并导致内质网释放Ca2+;Gβγ亚基 也可触发各种下游信号通路(如AC、IP3)及激活ERK/Atf2、Stat3、Stat5和mTOR等关键信号分子[17-18]。β-arrestin2(β-Arr2)作为一种支架蛋白,是G蛋白信号的负调控因子,通过G蛋白脱敏GPCR信号诱导GPCRs内吞[19]。
2.2 HDACs抑制途径 HDACs是一种参与修饰染色体结构和调控基因表达的蛋白,水解蛋白质底物赖氨酸残基上的N-乙酰基,尤其是染色质核小体复合体组蛋白中乙酰化的侧链赖氨酸,抑制组蛋白乙酰化,抑制核染色质结构开放,沉默DNA[20]。作为基因激活调控的一部分,组蛋白乙酰转移酶(histone acetyltransferases,HATs,HDACs抑制剂)乙酰化组蛋白可增强染色质可及性,促进核易位和转录因子如STAT3、NF-κB、FoxP3、N-FAT和RUNX1与DNA结合,调控基因表达,而HDACs则逆转这一过程[21]。正常情况下,二者平衡存在,引起DNA表达多样性,在细胞和系统水平产生多方面影响;二者失衡可能导致NF-κB和AP-1调控的促炎反应基因持续转录,形成慢性炎症循环。研究表明,丁酸(10 mmol/L)、丙酸(10 mmol/L)以及HDACs抑制剂TSA(2 μmol/L)在相同条件下处理HDACs,测定HDACs活性发现,TSA组活性降低至原始活性的1%以下,而丙酸组与丁酸组活性分别为10%和30%,说明SCFAs与TSA一样对HDAC活性有抑制作用[22]。
3 SCFAs与肠道免疫细胞
SCFAs可通过调节几乎所有类型免疫细胞功能调节肠道黏膜免疫。固有淋巴细胞(intrinsic lymphocytes,ILCs)是分布于黏膜的异质性淋巴细胞,接受局部微环境细胞因子信号后,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及其他递质发挥免疫监视和免疫调节作用[23]。研究发现,SCFAs通过激活GPR43进一步促进ILCs成熟及功能恢复[24]。GPR43在中性粒细胞中高表达,SCFAs通过激活GPR43进而抑制中性粒细胞向炎症部位募集[25]。SCFAs可通过抑制HDAC活性抑制LPS诱导的巨噬细胞迁移、促炎细胞因子NO、IL-6和IL-12分泌[26]。丁酸盐通过诱导Zn2+结合HDACs活性位点抑制HDACs,促进Foxp3启动子和增强子保守非编码序列(conserved non-coding sequences,CNSs)组蛋白H3乙酰化,促进基因表达和Treg功能成熟,增强抗炎作用[27]。SCFAs还通过抑制HDACs途径上调Aicda、Xbp-1、Ada、CD69、Prdm1及Irak3基因表达,诱导B细胞分泌IgA[28-29]。
4 SCFAs与肠黏膜屏障功能
肠道黏液蛋白(mucus proteins,MUC)、抗菌肽(antimicrobial peptides,AMP)和IgA构成肠黏膜化学屏障,由肠壁细胞分泌并稀释、水解有毒有害物质,防止机体损害[30]。研究发现,SCFAs通过激活GPCRs促进MUC、AMP、IgA分泌,维持肠黏膜化学屏障,抵御病原体入侵[31]。肠上皮细胞中的claudin、occludin、ZO-1、ZO-2等多种连接蛋白形成上皮细胞紧密链接,构成上皮细胞机械屏障,其完整性在维持肠道平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2-33]。SCFAs通过激活AMPK、抑制MLCK/MLC2通路及PKCβ2磷酸化上调ZO-1、occludin、claudin-3和claudin-4表达[34]。低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α,HIF-1α)是一种协调屏障保护因子,肠道上皮细胞吸收SCFAs需消耗肠道约70%氧气,通过激活GPCRs上调Stat3和mTOR,促进和稳定HIF-1α表达,进一步诱导Tr1分化,并通过TASK-2通道提高肠黏膜中B细胞对炎症反应的灵敏性,维持肠黏膜免疫屏障稳定性[35-37]。此外,SCFAs还可通过调节增殖基因(包括细胞周期蛋白家族)和凋亡基因(主要是caspase家族及p53、Bax和Bcl-2)调节肠上皮细胞(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IEC)增殖和凋亡[38]。
5 SCFAs对细胞因子的调节
急性炎症导致肠道内免疫稳态被打破后,促进多种细胞因子(如IL-6、IL-8、IL-17等)释放,作用于效应细胞加重肠道炎症。SCFAs通过抑制HDACs途径或激活GPCR41/43途径,抑制巨噬细胞NF-κB介导的促炎因子(如TNF-α、IL-6、IL-12)产生、下调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及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VCAM-1)和细胞内黏附分子-1(intra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s,ICAM-1)等多种趋化因子基因编码,促进肠道免疫细胞抗炎因子(如IL-10、IL-4)产生[39-40]。SCFAs通过刺激GPCRs诱导前列腺素E2释放和抗炎因子IL-10表达,也可激活炎症小体,促进IL-18产生和分泌[41]。另有研究发现,SCFAs 通过HDACs抑制途径增强组蛋白修饰,增加HIF-α与IL-22启动子结合域的可能性,促进IL-22生成[42]。此外,SCFAs明显上调IL-17A、IL-17F、RORα、RORγt、T-bet和IFN-γ表达[43]。
6 SCFAs与肠道细胞能量代谢
IEC能量平衡障碍是CD炎症组织的典型特征。外来因素持续刺激IEC导致能量过度消耗或肠道本身能量供应减少是IEC维持能量稳态失败的主要原因。线粒体在维持IEC能量稳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4]。SCFAs能明显增加编码线粒体ATP合成酶亚基和编码线粒体解偶联蛋白基因表达,维护线粒体功能[45]。丙酸可作为琥珀酰辅酶a进入三羧酸循环,乙酸和丁酸可作为乙酰辅酶a进入TCA,明显提高细胞内ATP/ADP,为细胞供能[16,45]。此外,IBD患者和结肠炎小鼠中,转运蛋白MCTs表达下调,导致IEC中SCFAs水平下降。研究发现,丁酸可激活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PPAR-γ)功能,促进MCT-1和MCT-4等体内和体外转运体表达,促进IEC吸收SCFAs,为IEC供能[46]。
7 展望
综上,SCFAs在IBD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国内学者对IBD研究增多,IBD治疗药物除糖皮质激素、氨基水杨酸制剂、免疫制剂、生物制剂外,肠道益生菌、SCFAs也用于临床辅助治疗。研究显示,SCFAs可促进cAMP生成,或促进神经递质氨基丁酸(GABA)和NO通过脑-肠轴循环,从中枢调控肠道炎症;SCFAs在机体能量代谢、神经、内分泌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IBD临床治疗越来越趋向个体化,这些思路为SCFAs研究提供了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