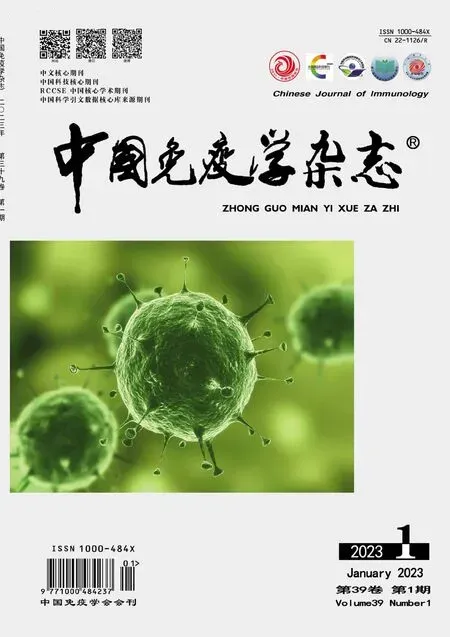尿路致病性大肠杆菌与宿主相互作用的研究进展①
周靖轩 袁春玲 向晨焱 王 君 邹黎黎
(三峡大学基础医学院,肿瘤微环境与免疫治疗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感染与炎症损伤研究所,宜昌 443000)
泌尿系感染(urinary tract infections,UTI)每年困扰着全球约1.5亿人,约有50%的女性在其生命周期中被UTI所困扰,其中25%的女性在首次感染后6个月内出现复发性尿路感染(recurrent UTI, rUTI),甚至部分患者在初次发生感染后1年内出现6次以上的反复感染,严重影响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导致UTI最常见的病原体是尿路致病性大肠杆菌(uropathogenicE.coli,UPEC),约80%的社区获得性UTI和50%的院内UTI均由UPEC引起[1-5]。在感染发生发展过程中,宿主表现出复杂的主要由尿路上皮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介导的免疫防御能力,如尿路上皮细胞的屏障作用、中性粒细胞的迁移和吞噬作用。除此之外,还有细胞因子的杀伤作用等[6-7];同时,UPEC的自身结构合并其分泌的毒力因子可打破宿主屏障,并对抗中性粒细胞的免疫应答以逃避宿主的免疫清除。鉴于感染期间复杂的病原体-宿主反应与病原体的侵入和反复感染密切相关,因此深入理解UTI中宿主-病原体的免疫相互作用势在必行,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膀胱上皮
膀胱上皮细胞(bladder epithelial cells,BEC)是宿主抵抗病原体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其不仅是一个高度致密的物理屏障,其上分布的各种细菌受体也可高效抵御UPEC感染。膀胱上皮(即移行上皮)由基底细胞层、中间细胞层和浅表顶层组成。浅表顶层也被称为伞状细胞,其表面有由尿空斑蛋白(uroplakins,UPs)组成的刚性斑块,在维持屏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8]。即便如此,UPEC仍可依靠各种生物作用打破BEC的防御作用[9]:①黏附作用。KAPER等[10],DUNCAN等[11]和CHAHALES等[12]研究发现,UPEC可通过与UPs结合而黏附至宿主细胞,虽然排尿期间尿液的冲刷作用可排出大部分的细菌,但残留的细菌会在营养丰富的尿液中完成增殖并定殖于尿道上皮。②入胞作用。伞状细胞中具有膜运输作用的细胞器:梭形囊泡(fusiform vesicles,FV),其功能受特定细胞膜内面的Rab GTP酶调节。BEC含有大量由RAB27b调节的FV,正常生理情况下FV作为额外膜储存在细胞内。当尿液积聚导致膀胱扩张时,FV以cAMP依赖性方式发生胞吐作用以提供膀胱扩张所需的额外膜;排尿后额外膜再次以FV的形式回到细胞内[13-15]。为了侵入上皮细胞,UPEC在细菌黏附的部位触发局部cAMP爆发导致FV融合至细胞膜。当这些膜回到细胞内时,黏附在细胞膜上的细菌被包裹在FV中从而进入上皮细胞内[9,14]。藏匿在FV中的UPEC不仅无法被溶酶体吞噬,而且可以迅速复制形成细胞内菌落(intracellular bacterial community,IBC)。这种结构具有生物膜样特性,可抵抗宿主先天防御和抗生素的杀伤[16-17]。③抑制溶酶体的吞噬作用。如上所述,膀胱上皮细胞表面具有迅速识别细菌入侵的受体,如Toll样受体(TLR2、TLR4、TLR5和TLR11)[18]。SONG等[19]研究发现,TLR4被激活后可上调细胞内cAMP的水平导致FV发生胞吐使得囊泡内细菌被清除至膀胱腔。为了躲避Toll受体介导的清除作用,UPEC从FV中逃逸至细胞质,此时细胞的自噬系统被激活,细菌被包裹在自噬体中并通过多泡体转运至溶酶体。然而,UPEC可调节PH值使溶酶体失活并在溶酶体内存活,这些失活溶酶体被位于溶酶体膜上的瞬时受体电位黏蛋白3(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mucolipin 3,TRPML3)监测到,随后迅速被排出到胞外[20]。感染后不久,宿主由TLR4介导的FV胞吐以及自噬相关的溶酶体排出发挥作用,这些高效的外排机制可在24 h内排出BEC内80%以上的细菌[14]。④上皮脱落。当所有外排机制均无法有效清除UPEC时,BEC激活最后一道防线即上皮脱落,从而清除被细菌黏附和感染的上皮细胞。BEC剥脱对于UPEC的清除至关重要,尤其是作为针对细胞内UPEC的一线防御[21]。严重感染者的尿液中含有大量脱落的BEC,表明上皮脱落是 一种常用的宿主防御机制[22-23]。上皮脱落由胱天蛋白酶-3和胱天蛋白酶-8相关的凋亡引起,为了对抗这种剧烈刺激,基底上皮迅速转变为快速增殖状态,在数小时内迅速替换脱落细胞并恢复尿路上皮屏障[24-25]。新近研究发现BEC死亡与NLRP3炎症体途径的激活和胱天蛋白酶-1激活有关[21]。然而,感染的BEC引发的上皮脱落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可以消除大量细菌,但也会使稚嫩细胞暴露于尿液中的细菌[23]。实际上,表面上皮细胞的死亡是由某些毒性UPEC有意诱导,以更好地到达BEC深层以形成静止的细胞内储库(quiescent intracellular reservoirs,QIR),从而在上皮细胞中持续存在。因此,上皮细胞中QIR的存在与膀胱感染的高复发和抗生素耐药密切相关[26]。
综上可知,BEC强大的屏障功能,高效的细菌外排机制以及彻底的上皮脱落能够有效抵御细菌的黏附与侵入。然而,病原体依旧可利用细胞膜上的UPs黏附至细胞表面,利用膀胱膜运输特性进入细胞内形成IBC,在上皮脱落时入侵上皮细胞形成QIR,导致UTI的反复复发与治疗难度增加。
2 中性粒细胞
中性粒细胞是膀胱炎发生后机体清除细菌的主要吞噬细胞,细菌入侵时激活BEC表面的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PRR)从而分泌IL-8,诱导中性粒细胞离开血管迁移至固有层,穿透基底膜和浅表上皮进入膀胱腔清除细菌[27-28]。但是那些被巨噬细胞分泌的CXC趋化因子配体1(CXCL1)和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募集来的中性粒细胞需要局部的肿瘤坏死因子信号传导才能穿过上皮的基底膜[27]。此外中性粒细胞的跨上皮运动也需要TNF,诱导巨噬细胞LY6C分泌第二波细胞因子,主要是CXCL2。它可以刺激中性粒细胞产生基质金属蛋白酶9,和IL-10一起启动中性粒细胞跨上皮运动[29]。中性粒细胞数量与细菌负荷成正比,在感染后2 h内到达膀胱上皮并在6 h达峰[30]。HARAOKA等[31]研究发现,中性粒细胞反应缺陷的小鼠对UTI的易感性显著增加且清除细菌感染的能力降低,表明中性粒细胞在细菌清除中扮演重要角色。中性粒细胞可将高水平的锌调集至被吞噬的微生物,利用锌的毒性可能是保守的先天免疫抗微生物反应[32]。但中性粒细胞释放的活性氧和细胞毒性产物可介导组织损伤。HANNAN等[33]研究发现,非甾体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或环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抑制剂对小鼠UTI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COX-2抑制剂在不影响BEC剥落和其他宿主固有清除的情况下限制中性粒细胞迁移至泌尿道,减少脓尿和黏膜损伤并降低慢性膀胱炎的发生率。虽然中性粒细胞可确保机体在排泄过程中及时清除细菌,但是中性粒细胞的募集在UTI期间可引起严重病理反应,表明尿液中大量的中性粒细胞是宿主防御的副产物[31]。然而过度的免疫应答也与炎症疾病有关。新近研究表明Forskolin可明显减少小鼠炎症组织中CD45+Ly6G+细胞(中性粒细胞高度特异性)的数量,适当减少中性粒细胞的产生减轻病理反应[34]。此外,Forskolin治疗的小鼠也可降低中性粒细胞IL-1β和TNF-α mRNA的表达。中性粒细胞的耗竭不仅可以减缓组织破坏,同时也可以减少细菌负荷[34]。
UPEC具有针对中性粒细胞募集和吞噬功能的毒力机制,通过下调中性粒细胞趋化、促炎、黏附和迁移相关的基因表达抑制中性粒细胞迁移。①上调吲哚胺2,3-双加氧酶(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IDO)表达。UPEC在体外以及细菌性膀胱炎的小鼠模型中均可诱导哺乳动物IDO1基因的局部表达[35]。研究表明,UPEC可减少体内外中性粒细胞经膀胱上皮的迁移,诱导中性粒细胞和尿路上皮细胞内的抗炎分子产生,如IDO[36-38]。IDO可介导犬尿氨酸的产生,在体外对黏附性中性粒细胞的形态学分析表明犬尿氨酸直接影响中性粒细胞的运动[35]。IDO参与色氨酸分解代谢,通过色氨酸局部匮乏以及犬尿氨酸的局部代谢分解产物来调节适应性免疫;UPEC在侵入小鼠膀胱后1 h内局部特异性上调IDO,导致中性粒细胞募集减弱;IDO缺陷小鼠中性粒细胞在UTI中迁移增强,使细胞外细菌的杀伤增加和感染减弱[35,39]。且进一步研究表明,UPEC会在膀胱炎期间诱导局部TNF-α分泌,从而破坏先天性免疫介导的锌毒性,TNF-α和IFN-γ的持续作用是UPEC诱导宿主中IDO上调的基础[39-41]。②释放YbcL。LAU等[38,42]的研究证实,随细菌裂解而释放存在于细菌周质中的效应物YbcL,可在体内和体外模型中抑制中性粒细胞跨上皮迁移。YbcL抑制中性粒细胞迁移需要尿路上皮细胞,并通过细菌暴露于BEC而增加细菌裂解从而达到释放YbcL的目的[42]。③分泌α溶血素。为了抵抗中性粒细胞的吞噬, UPEC分泌α溶血素发挥免疫调节和抑制粒细胞的趋化及吞噬活性作用[43-46]。④分化成丝。在IBC成熟期间,少数细胞菌落通过分化途径形成长度70 μm的非分离的丝状细菌[16,47]。当含有IBC的上皮细胞裂解时,UPEC从IBC中流出进入膀胱腔,而丝状UPEC(1~2 μm)则可以抵抗吞噬作用[16,48]。事实上,中性粒细胞能够吞噬比自身更大的颗粒(例如真菌菌丝),丝状UPEC的抗吞噬作用可能依赖于其大小超出吞噬的极限[16,49-50]。综上可知,中性粒细胞在UTI过程中募集和吞噬清除病原体,而UPEC为了抵抗中性粒细胞的免疫清除作用,上调IDO的表达、释放YbcL、分泌α溶血素抑制中性粒细胞的迁移与募集,还可分化成丝以逃避中性粒细胞的吞噬。
3 抗菌因子
泌尿道炎症反应主要通过激活Toll样受体(TLR)而引发。UPEC感染后不久,PRR即被激活,细菌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刺激TLR4激活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途径或诱导尿路上皮cAMP的增加进而导致IL-6和IL-8表达增加[51-53]。此外,NOD-样受体/胱天蛋白酶-1途径的激活也会导致IL-6和IL-1β的大量爆发[21,51]。这些细胞因子与BEC分泌的其他炎症介质一起导致免疫细胞迅速流入上皮细胞以抵抗细菌攻击,如抗菌肽(antimicrobial peptide,AMP),抗菌蛋白。Cathelicidin LL-37是由BEC分泌的小分子量的阳离子AMP,可直接杀死细菌。CHROMEK等[54]研究发现,感染5 min后BEC内的cathelicidin mRNA表达升高,敲除LL-37直系同源物的小鼠感染后1 h内膀胱UPEC负荷急剧增加,揭示了AMP快速和强大的抗菌作用。UTI期间防御素类AMP β-防御素也局限性增加[55]。这两种AMP都有助于细胞因子的产生、中性粒细胞的募集、溶解或抑制黏附细菌[56]。最近研究发现,可溶性模式识别分子五聚蛋白相关蛋白3(pentraxin-related protein,PTX3)可刺激补体介导吞噬从而预防UTI。感染后泌尿道中PTX3水平增加,PTX3敲除小鼠的抗感染能力降低。此外,核糖核酸酶7是另一种抗菌剂,对许多常见尿路病原体具有迅速和广谱的杀菌活性[57]。
为了应对机体细胞因子与炎症介质的作用,UPEC可通过:LPS修饰和效应子显著抑制抗菌因子的产生。UPEC可以稳定NF-κB抑制蛋白(inhibitor of NF-κB,IκB)从而抑制NF-κB活性并增加BEC凋亡[58]。研究发现,多个UPEC分离株可在尿路上皮细胞诱导低水平的IL-6和IL-8,并与已知的NF-κB刺激物共接种后能够阻止这些炎症细胞因子的分泌[59-60]。LPS的生物合成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UPEC LPS修饰可能产生一个低刺激性的LPS结构,抑或者是非刺激性LPS发挥主导作用[59,61]。然而,仅仅是LPS差异并不能解释细胞因子的抑制,其他机制和UPEC效应也可能有助于抑制细胞因子的分泌,例如亚裂解浓度的α溶血素可抑制NF-κB信号传导以及IL-6的分泌[62-65]。大部分UPEC编码含有Toll/IL-1受体(TIR)结构域的蛋白质,称为TcpC,与宿主衔接子MyD88相互作用以抑制TLR信号传导[66]。关于TIR结构域蛋白其他信号通路的进一步研究表明,TcpC可独立于MyD88调节TLR通路, 因此TcpC可能以更广泛的方式影响发病机制[67]。NLRP3炎症小体和IL-1β对于UTI的建立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UPEC是可调节NLRP3炎症小体激活和IL-1β释放的毒力因子,从而影响UPEC BEC的黏附与定植[21,68-70]。总之,在UTI期间尿路上皮分泌细胞因子、AMP和抗菌蛋白抑制或杀伤病原体,然而UPEC可通过LPS修饰和效应子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从而逃避宿主的清除,且一些促炎细胞因子具有改变UPEC毒性特征的能力[71]。即便如此,目前AMP作为疫苗抗原用于抗击UTI的新策略的疫苗开发上。此外,铁载体,黏附素等也可以成功防御UTI[72-75]。了解这些细胞因子是如何影响UPEC以及宿主的免疫防御,对制定针对这些细胞因子为靶标替代传统抗生素的治疗策略至关重要。
4 展望
UTI中宿主与病原体的免疫相互作用极其复杂,详细深刻的理解其机制有助于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比如针对病原体的黏附和生物膜形成过程、破坏细菌对中心粒细胞、细胞因子的抑制;针对宿主刺激感染的组织细胞对病原体侵袭反应增强从而引发和增强免疫反应。针对UPEC感染治疗的直接策略是针对细菌的生存力,膀胱上皮的黏附和生物膜的形成。而间接策略是通过刺激受感染的组织和细胞对UPEC入侵过度反应引发和增强免疫反应[76]。然而宿主的炎症反应是一把双刃剑,急性膀胱炎期间过度旺盛的炎症可增加组织的损伤,更容易发展为慢性复发性感染,导致病原体持久驻留在上皮内而无法被免疫系统清除。因此,宿主需要进行精细的免疫调节以消除尿路病原体,同时避免可能增加疾病严重性或促进持续感染的炎症反应。一旦形成慢性复发性感染,需要开发新的治疗方法以彻底清除细胞内驻留的细菌。关于泌尿系感染中宿主-病原体免疫相互作用的详细机制和相对应的治疗措施,亟待下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