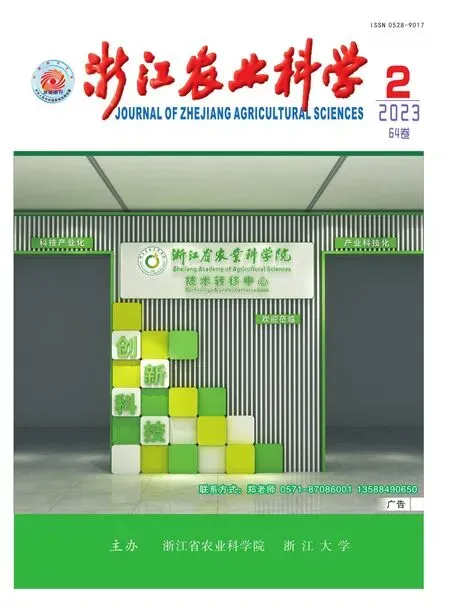香椿离体再生技术研究进展
李玲, 黄榕, 艾薇, 王友如
(湖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特色野菜良种繁育与综合利用技术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 食用野生植物保育与利用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 黄石 435002)
香椿是楝科香椿属落叶乔木[1],是我国传统药食同源木本植物。其树干通直,树体庞大,色泽花纹清晰,芳香耐腐,被誉为“中国桃花心木”[2]。香椿地理位置分布广泛,北至辽阳锦州一线,西至陕西延安市,南至广西广东一带,东至我国台湾省[3],喜温带和亚热带气候[4]。香椿也是唯一一个被我国命名“树上蔬菜”的植物,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胡萝卜素、香椿素和钙镁等营养元素,具有超高的营养价值,深受消费者的喜爱[5]。香椿药用历史悠久,早在古代就已知其具有清热利湿、利尿解毒等功效。《本草纲目》中记载:香椿叶、芽、根、皮和果实均可入药[6]。
基于以上香椿的材用、食用和药用价值特点,我国部分地区将香椿产业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农业现代化产业项目。四川大竹县被誉为“中国香椿第一县”,据相关数据记载,2020年该县的香椿芽销售1.1万t,产值达3亿元;四川简阳市香椿的种植面积近3 500 hm2;太和香椿近些年种植面积近235 hm2,香椿芽年产量达500 t[7]。香椿产业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香椿产业发展迅速,但种苗参差不齐、品系良莠不分和优质苗木供不应求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最大优点是能够快速大量地获得保持优良母本性状的再生个体,不受环境季节等因素影响,快速繁殖优良香椿种苗[8]。
本综述从微繁途径再生技术和组织培养再生技术2个方面总结香椿离体再生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为构建高效香椿再生技术体系提供借鉴。
1 基于微繁途径的再生技术研究进展
微繁技术是指以植物茎段、腋芽和顶芽等为外植体,通过消毒和无菌操作等一系列方式快速获得大量的能稳定遗传的丛生芽的一项技术。目前国内的香椿离体再生技术研究,大多采用的是芽微繁途径获得再生苗。
1.1 外植体选择
大部分学者在进行香椿芽微繁研究时,均是选取香椿(含腋芽的)的茎段、腋芽、顶芽或丛生芽作为外植体,这主要是由于香椿含芽处增殖系数相较于其他外植体较高。
覃兰英等[9]最早开展香椿微繁研究,以茎段为外植体发现,在基本培养基(MS)+0.1 mg·L-1吲哚乙酸(IAA)+0.1/0.5 mg·L-16-苄基腺嘌呤(6-BA)丛生芽诱导可达4~5个,从此开启了离体再生技术研究的序幕;康明等[10]以迁西香椿45 d无菌苗茎段(带侧芽)为外植体,在MS+1.0 mg·L-16-BA+0.1 mg·L-1吲哚丁酸(IBA)中发现有丛芽形成;谢文申等[11]发现,以香椿茎段为外植体时,在培养基MS+0.1 mg·L-16-BA+0.5 mg·L-1激动素(KT)+0.1 mg·L-1萘乙酸(NAA)中发现大约30 d后可形成丛芽;吴丽君[12]发现,选取福建香椿0.5~0.8 cm茎段时,在MS+0.5 mg·L-16-BA+0.5 mg·L-1NAA培养基中,20 d后小芽能长至1.5~2.0 cm;马勤[13]研究发现,香椿品系T4的茎段在MS+0.2 mg·L-16-BA+2.0 mg·L-1赤霉素(GA3)中芽的增殖系数可达3.38;许丽琼等[14]研究发现,3月采取孝感红香椿茎段(带1个芽)接种至增殖培养基MS+1.0 mg·L-16-BA+1.5 mg·L-1GA3+0.5 mg·L-1KT中,增殖倍数可高达4.7;周玉玲[15]研究红香椿一号的茎段发现,在MS+1.0 mg·L-16-BA+0.1 mg·L-1NAA+0.1 mg·L-1IBA+0.1 mg·L-1玉米素(ZT)培养基中芽的增殖倍数在6.0以上;张晓申等[16]发现,以郑州香椿3 cm长茎段为外植体时,在培养基MS+0.6 mg·L-16-BA+0.2 mg·L-1NAA,茎段的芽诱导率为66.7%;高鷃铭[17]以带小芽的茎段为外植体时发现,在培养基MS+1.0 mg·L-16-BA+0.1 mg·L-1NAA+0.1 mg·L-1GA3中,芽的增殖倍数为3.63;杨超臣等[18]发现,香椿茎段在MS+1.0 mg·L-16-BA+0.1 mg·L-1NAA+1.0 mg·L-1GA3培养基中,芽增殖倍数为4.82。由上可知,香椿茎段芽微繁效果较好,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丛生芽。
王春林等[19]最早以太和香椿腋芽为外植体进行芽增殖试验,在培养基B5+1.0 mg·L-16-BA+1.0 mg·L-1GA3中发现,1个月后繁殖系数可达6~7倍;陈彦生等[20]以腋芽茎段为外植体时发现,在培养基MS+0.2 mg·L-16-BA中3~5 d后腋芽就开始萌发,15 d后成苗率达73%;曹娟等[21]在研究红香椿腋芽时发现,在培养基MS+0.2 mg·L-1GA3+0.02 mg·L-1NAA中,增殖系数达3.8。
陈实[22]在研究南京香椿子叶、下胚轴(含顶芽)时,发现在B5+1.0 mg·L-16-BA+0.5 mg·L-1NAA培养基中生芽率达61.5%;袁应菊[23]采用太和香椿顶芽为外植体研究发现,接种在增殖培养基MS+0.3~0.8 mg·L-16-BA+0.1~0.2 NAA mg·L-1中,丛生芽平均每个可再生3个左右。
张晓申等[16]发现,以郑州香椿茎段诱导的丛芽为外植体时,在培养基MS+1.0 mg·L-16-BA+0.5 mg·L-1NAA中,丛芽的增殖系数3.7。马宗新等[24]以太和香椿的丛芽为外植体时发现,在培养基MS+1.5 mg·L-16-BA+0.08 mg·L-1NAA+0.01 mg·L-1GA3中,芽的增殖系数为2~3倍;梁明勤等[25]以菜用香椿的丛芽为外植体,在1/2 MS+0.5 mg·L-16-BA+0.5 mg·L-1GA3培养基中发现增殖倍数可达6.95;冯姗姗[26]在研究太和香椿的丛芽时发现,在培养基MS+1.0 mg·L-16-BA+0.1 mg·L-1NAA+0.5 mg·L-1GA3中,芽的增殖倍数达5.9。
经比较发现,腋芽茎段的萌发时间较短于茎段,且丛芽的诱导率也高于茎段,有可能是茎段木质化程度高于腋芽,在消毒过程中茎段较容易褐化死亡;或者又由于腋芽的幼嫩程度高于茎段,所以较易诱导萌发。
1.2 基本培养基
基本培养基是香椿微繁再生中的主要能量来源。目前微繁中常用到的培养基有MS、1/2MS、WPM、B5、1/2DCR、无离子水或是改良的培养基等。
香椿芽微繁途径研究进展表明,大多数采用的是MS基本培养基。王春林等[19]首次采用B5培养基对太和香椿茎尖和幼苗茎部进行诱导,发现均有成苗和生根出现;许丽琼等[14]发现,B5与1/2MS培养基对茎段培养的效果差异不大,分析可能与培养基本身的营养物质有关,但二者都不如MS培养基的营养全面;陈实等[22]经成分对比发现,MS比B5培养基的硝酸盐含量更高,表明MS的铵含量高于B5,铵对香椿外植体的生长发育有一定影响,认为B5培养基的效果较好于MS[14]。1/2MS培养基适用于香椿芽苗的生根试验,能在短时间内有效促进芽苗底部形成发达根系,便于后续移栽。
1.3 植物生长调节剂
植物生长调节剂是微繁技术中的关键因素。一般认为,当细胞分裂素浓度相对高于生长素浓度时,有助于促进芽的生长;当细胞分裂素浓度相对低于生长素浓度时,有助于促进根的生长和愈伤组织的形成[27]。
香椿在芽微繁中主要使用的细胞分裂素是6-BA,其次便是ZT和KT;最常用的生长素是NAA。6-BA是最常用的一种细胞分裂素。梁明勤等[25,28]认为,6-BA对香椿芽的增殖有显著影响,在诱导香椿芽快繁过程中6-BA浓度常控制在0.2~1.5 mg·L-1,尤其是低浓度的6-BA增殖效果最佳[29],当浓度越接近0.5~1.0 mg·L-1的时候,增殖系数较高,最高可达6.95[25]。6-BA还可以抑制植物的顶端优势,但浓度过高会导致外植体出现玻璃化和轻微白化状态[30]。陈彦生等[20]研究发现,在培养基中加入GA3,不仅可以促进腋芽增殖还可以有效降低玻璃化苗产生,也能降低试管苗木质化程度[24]。GA3的含量会在香椿休眠芽到萌发这一阶段内急剧升高[31],是影响香椿芽萌发的重要影响因素。周玉玲等[15]在研究红香椿芽增殖中发现,激素的影响效果由大到小依次为ZT、6-BA、NAA、IBA。
从近30 a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在香椿芽微繁的过程中,单一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是无法获得较高增殖系数的丛芽,一般情况下,细胞分裂素、生长素或者赤霉素等按照合适比例添加,才能获得较好的微繁效果。以香椿茎段、腋芽或顶芽为外植体的芽微繁技术相对成熟,可获得较高增殖系数的香椿无菌苗,为工厂化生产优质香椿苗木提供了技术支撑。一般使用的基本培养基是MS,细胞分裂素是6-BA,生长素是NAA,浓度在0.1~1.0 mg·L-1,1个带腋芽的茎段诱导的丛芽一般可达3~6个。目前关于香椿离体再生技术的报道大多还是以芽微繁的方式进行,仅有极少数是基于愈伤组织的再生技术,大多停留在愈伤诱导阶段,愈伤分化仍未有实质性的技术突破。
2 基于组织培养的离体再生技术研究进展
传统意义上的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是指先诱导外植体脱分化形成愈伤组织,然后再使愈伤组织再分化形成不定芽,最后诱导再生植株生根成为完整植株的过程。
2.1 外植体选择
目前香椿植物组织培养主要在以无菌苗叶片、幼叶或是在室外取幼嫩香椿叶片为外植体。最早进行香椿组织培养的是王春林等[19],以太和香椿的幼叶为外植体,在液体培养基B5+2.5 mg·L-16-BA+2.5 mg·L-1NAA 中发现在黑暗条件下培养可以10 d快速诱导愈伤形成,40 d分化成叶芽,且愈伤诱导率及不定芽再生率均不高。随后,许丽琼等[32]选取以孝感红香椿叶片为外植体,发现在培养基MS+1.0 mg·L-16-BA+0.1 mg·L-1KT+0.5 mg·L-1NAA中,6 d愈伤诱导率为100%,也有不定芽出现(培养基未记录)。之后,曹娟等[21]采用红香椿叶片为外植体,在培养基MS+0.15 mg·L-1噻二唑苯基脲(TDZ)+0.3 mg·L-1NAA+1.0 mg·L-1KT中发现愈伤诱导率为92.8%,且叶片愈伤组织在培养基MS+0.1 mg·L-16-BA+0.5 mg·L-1KT+0.1 mg·L-1NAA有不定芽产生;梁明勤等[25]以太和香椿嫩叶为外植体时,在培养基MS+0.3~0.8 mg·L-16-BA+0.1~0.3 mg·L-1NAA中有愈伤形成,但无不定芽形成;冯姗姗[26]以太和香椿叶片为外植体时,在培养基MS+1.5 mg·L-12, 4-二氯苯氧乙酸(2, 4-D)中愈伤组织诱导率为100%,叶片细胞团在MS+1.0 mg·L-1KT+0.1 mg·L-1NAA中有侧根出现。
在组织培养过程中,外植体的选取能够很大程度影响植物再生,不同植物的不同外植体建立起再生技术体系的难易不同[33]。目前,以无菌苗叶片、幼叶和室外取材叶片为外植体时,愈伤组织诱导相对容易,但仍存在愈伤组织分化的难题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2 基本培养基
目前香椿组织培养中所用培养基来看,主要培养基是以MS为主,也用到了B5培养基。
2.3 植物生长调节剂
叶片愈伤组织的诱导和分化,主要采用的细胞分裂素是6-BA,生长素是NAA,其次搭配KT、2, 4-D和TDZ。添加不同种类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至基本培养基中能够较大程度影响外植体诱导分化。适当浓度的NAA能有效促进芽的萌发,也能够诱导较多愈伤组织的形成[25]。2, 4-D对外植体愈伤组织诱导效率高[26],但是浓度过高会对外植体材料有一定的毒害作用[34]。在叶片愈伤诱导过程中,TDZ、NAA和KT或是6-BA、KT、NAA组合中,愈伤组织的诱导率均能够达到90%以上,因此KT和NAA对香椿叶片愈伤诱导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出现不定芽的培养基中均用NAA和6-BA处理,因此一定比例的NAA和6-BA可以诱导不定芽生成,但是两者浓度的比例还需进行适当调节。
总之,目前香椿组织培养的再生技术研究主要以香椿幼叶和叶片为外植体,在细胞分裂素BA、KT、TDZ和生长素NAA、2, 4-D组合下进行的愈伤诱导分化,一般细胞分裂素同生长素浓度比例在2~5 mg·L-1。总体效果呈愈伤组织诱导相对容易,效率较高,但愈伤组织分化十分困难。
3 离体再生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香椿离体再生技术大部分是以顶芽或腋芽为基础的微繁技术,基于愈伤组织诱导分化的香椿组织培养研究中,愈伤组织成功诱导案例比较普遍,但愈伤组织的分化几乎没有成功。
3.1 微繁效率问题
目前香椿微繁技术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繁殖效率不够高。影响微繁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外植体的年龄。在选取含腋芽或顶芽的外植体的过程中,未能选取最佳年龄阶段的茎段。年龄阶段的选取十分重要,如果选取外植体较为幼嫩,则会在消毒的过程中容易消毒过度,导致材料褐化死亡;如果选取外植体茎段较成熟,则会导致消毒不彻底,茎段染菌或是茎段不易诱导芽的萌发[35]。第二,最佳植物生长调节剂类型及其浓度配比。未筛选出最佳的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组合及其浓度配比。植物生长调节剂浓度及其比例对芽微繁再生技术产生较大影响。细胞分裂素使用比较多的是6-BA和KT;生长素使用比较多的是IBA、NAA和IAA,赤霉素GA3有一定的使用。6-BA使用浓度一般是0.1~1.5 mg·L-1,KT使用浓度是0.5 mg·L-1,IBA、NAA和IAA的使用浓度分别是0.1、0.02~0.5和0.1 mg·L-1,GA3的使用浓度是0.01~1.00 mg·L-1。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浓度一般控制在1~10 mg·L-1,增殖系数为3~6。目前香椿微繁途径中细胞分裂素TDZ和生长素2, 4-D的使用极少,TDZ具有很强的细胞分裂素的效果,活性是普通细胞分裂素的几十倍[36],2, 4-D可以诱导外植体表现出胚胎发生能力[37]。
3.2 组织培养再生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在香椿组织培养过程中,外植体类型及其年龄选择上,多局限于消毒叶片、茎段,而且这些叶片和茎段的年龄阶段并未明确说明。
在香椿愈伤组织诱导与分化的研究中,细胞分裂素使用较多的是6-BA和NAA,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的质量百分比在愈伤诱导过程中的比例为1~3;在愈伤组织分化中,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的质量百分比的比例更高达6~10。TDZ和2, 4-D在愈伤组织诱导分化中有初步应用,但目前这2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并未组合应用。另外香椿体细胞胚胎途径的诱导与分化研究几乎是空白[38]。
4 香椿离体再生技术研究的建议
4.1 微繁途径的再生技术
可选择不同基因型或不同种源地的香椿顶芽或腋芽为材料,探索微繁中的外植体恰当年龄段以及合适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类型及其浓度配比,建立高效微繁再生技术体系。
4.2 组织培养再生技术
外植体的选择上,可选用合适年龄阶段幼嫩种子苗的子叶、下胚轴或无菌苗的幼嫩组织或器官,如将叶柄、叶柄节或顶芽、腋芽作为外植体;也可选择发育未成熟的胚或者幼嫩生长活跃的具有能力细胞的组织或器官(如顶芽或腋芽或者器官间交接处的组织)作为外植体研究体细胞胚胎发生途径再生技术体系。在继代方式上也可考虑叶片近轴端或是远轴端接触培养基等[39],优化各种条件培养。对于基于组织培养的再生技术体系,选择恰当幼嫩年龄阶段的外植体尤为重要。无论是基于愈伤组织诱导分化的再生技术还是基于体细胞胚胎诱导分化的再生技术,笔者建议重点考虑细胞分裂素TDZ和生长素2, 4-D与其他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的联合使用,以期望达到较好的再生效果。
目前TDZ已经在很多植物组织培养中添加应用,如油菜、苹果、朴树、红花槭等,均发现它具有很高的细胞分裂素活性,可以有效促进芽增殖,对再生较困难的木本植物的离体芽增殖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40]。张小红等[41]曾在香椿愈伤组织诱导和芽增殖中添加了TDZ,发现当浓度高于0.02 mg·L-1时会抑制香椿生长,且容易出现较多变态苗;当浓度在小于0.02 mg·L-1时,能够有效地促进香椿芽的生长。该研究中只开展了TDZ和NAA组合的研究,未和其他植物生长调节剂组合。因此,在后续香椿组织培养研究过程中,可以用其他植物生长调节剂与TDZ组合,研究出最佳香椿愈伤诱导及愈伤分化的试验组合,早日建立起高效再生的香椿再生体系。为后续香椿分子育种与功能基因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有学者在研究灰堇菜时发现,在添加2, 4-D的MS培养基上,利用叶片愈伤组织开展的体细胞胚胎发生途径成功地获得再生植株[42]。李文静等[43]在研究野生荠菜中发现,2, 4-D浓度过高会抑制愈伤组织再生植株。2, 4-D目前在很多植物体细胞胚胎途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建议在香椿体细胞胚胎诱导研究中添加适量2, 4-D。
综上所述,香椿再生技术研究大多以微繁技术为主,基于组织培养的再生技术未见实质性突破,研究结果大多局限于外植体愈伤组织的成功诱导,愈伤组织分化鲜见报道。香椿的组织培养体系还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探讨,需要在恰当的基本培养基、合适外植体选择、合适植物生长调节剂类型及其配比上做出恰当选择。